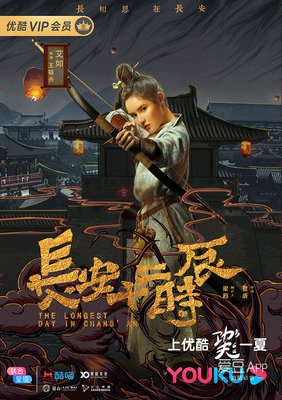《汉唐间史学的发展》读后感1000字
《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是一本由胡宝国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4.00元,页数:23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汉唐间史学的发展》精选点评:
●可惜没有再版了。《经史之学》、《文史之学》两篇继章学诚之后难出其右,《南北史学异同》经典精炼,堪称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的巅峰之作。附录很有意思,政治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论文。史学理论做到这程度就算成功了……期待新作
●也是基本史料读得熟,能归纳出一些一般历史学家习见而无意识的现象。
●最近又翻完一遍。看这样的书很享受:叙述质朴从容,没有繁杂炫目的名词、声嘶力竭的考辨,正所谓清通简要,举重若轻。有十分材料说一句话,而不是一分材料说十句话。
●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很见胡先生的功力。
●不甘于把入口处的光明当成出口处的光明的同老,在书中对史学史中一些习见且看似已无剩义的地方进行发掘,提出了为一般学人较为忽视的问题,并对之进行了尝试解答。就我个人的读后感触来说,书中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独立一题的阐释最有新意,亦颇显功力。
●我妈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坐得尾椎疼。
●硕士时候读的
●: K092.3/4636
●乐而忘返。
●每个字都是自己认真思考过的
《汉唐间史学的发展》读后感(一):《漢唐間史學的發展》札記
全書共八章並附錄二則,第一章敘述戰國傳統對《史記》之影響:人物籍貫記載格式,《太史公》彰明其子書之特徵。二章要義東漢經學衰微爲史學取得獨立地位創造了有利條件,而古文經學對史學影響頗大。三章論文史分離是南朝時人逐漸認識到文學的獨特性,而將史從文中獨立出去。四章論自東漢以闡明義理的經學出現了求簡趨勢,進而影響史學,故陳壽《三國志》甚簡。至南朝,史學講求敘事詳實而《裴注》出。五章,南朝史論實上接兩漢,而與玄學關係不大;北朝史學整體落後,故史論亦遜之。六章,雜傳之興衰與人物品評攸關,南朝皇權重彰且門閥固化,雜傳衰而譜碟興。七章,東漢以來求異、喜好山水的風氣是六朝地志興起的主因,山水詩則是此一風氣的另一端,亦因此六朝地志倍受注重實用性的唐人之批評。八章,南方史學私人著史風氣尤盛,北方則以官修爲主且重實用性。總體來說南北史學均向官修方向發展,南北史學之異同實源於南北經學之異同。
《汉唐间史学的发展》读后感(二):从战国精神到中州人士
此书是论述史学的,是对汉到隋唐之间的史学发展轨迹做推演的,论断有理有据,让人看着信服。
以下是门外汉看完的一点不专业总结。
战国精神:自战国末期以来,人的觉醒,成就了百家争鸣,司马迁纪传体《太史公曰》更是对战国精神的一种总结性体现;
经史简化运动:王莽当政时期简化经书,光武帝刘秀简化史书。
中州人士:以南阳、颍川、汝南三地为主要发力点,西汉以来政治中心从关中转移至此,文化中心从齐地转移至此;
政治上,颍川多为刘秀云台诸将发源,曹操也是背靠兖、豫二地;
文化上,南阳不属于三楚,虽为中州划在荆州学派,汉代经学转为魏晋玄学;
南北差异:北朝继承汉代,南朝继承魏晋。史书,北朝多以官史为主,政治色彩浓重,“崔浩”国史之狱;南朝私撰盛行,演变出了谱牒、裴注;
史论:荀悦和袁宏史论对历史多有评论褒贬,袁宏虽为玄学大师,未从玄学角度解释历史,至今空白。
《汉唐间史学的发展》读后感(三):读书笔记
读胡宝国先生的这本书受益匪浅,读完之后,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特点也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此书不同于一般著作的泛泛而谈。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是士族社会,士族这个阶层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玄学、史学有着重大深远的影响,然而具体到史学,士族阶层究竟是怎么影响到史学的发展、书写、特点呢?虽然说两汉经学大盛,魏晋南北朝经学式微,然而意识形态上式微的经学仍然对史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经学是怎么影响史学的呢?为何裴松之式的史注受到人们的赞誉,然而在六朝却又恢复了传统注经式注史的传统?一般著作都是泛泛之谈,却没有具体解释以上的问题,让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为何六朝的的地理志多记载异物志(稀有的动植物),而与地理无关呢?
书中都给出了非常详细的解释,观点严谨,材料丰富,使人信服。胡先生的基本功非常扎实,对史料的利用、解析可谓是到了极致的地步。读完此书后,对魏晋史学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一《史记》、《汉书》籍贯书写的差异
《史记》书中记述人物籍贯多为县,原因是以县为籍贯延续了战国以来的习惯。如《战国策》、《韩非子》中有相关的例证。
自汉武帝之前,诸侯国林立。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如何解决诸侯王的问题】,当时汉廷只有十五郡,郡这一行政单位对人们的影响非常有限。
汉武帝时期,解决了诸侯国威胁中央集权的问题。随着郡的增多,以郡为单位的察举制度、郡国学的建立、针对郡守刺史制度的设置等诸多措施的施行,使得郡对人们的现实生活有更大的影响。……司马迁以后,以郡为籍贯开始就行开来。
二经史之学
摘要:史学是在古文经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自魏晋已降,经、史逐渐分离,史学不再是经学的附庸。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国语》、《战国策》、《太史公书》依附于《春秋经》之下,史学没有独立的地位。在西晋,荀勖作《中经新簿》,分甲乙丙丁四部,史学属于丙部。东晋李充改定次序,属于乙部。为《隋书经籍志》所继承。
西晋频频使用【经史】一词,经、史发生了分离。宋文帝元嘉十五年,立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学。
《汉唐间史学的发展》读后感(四):经史的盛衰
经史的盛衰 —— 读《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札记 章实斋“六经皆史”的论断在后世得到了热烈的拥护。可是,如果说“六经皆史”的话,那么从前的“经”和史”是什么时候开始分离的?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用后世的学术分科的眼光去看,恐怕很难得出准确的答案。 在今人看来,《史记》无疑是一部具有史学开创意义的“大书”,可是,马迁此书原先并非名为《史记》。根据钱穆先生的说法,书名原是《太史公》。钱先生说,《太史公》是司马迁一家之私书,与孔子的《春秋》齐类,但是它和鲁国的《春秋》、晋的《乘》、楚国的《梼杌》这些当时的“史记”并不相同。也就是说,在当时,司马迁的书更接近《孟子》《荀子》之类的子书,而非后世所认为的史书。按照战国的传统,诸子之书才是“成一家之言”的私人著作。至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太史公》一书,更像是一本浸染于战国诸子学风、试图总结战国学术的私家著作,而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我国史书的开端。(关于《史记》五种体例的源流,可参看程金造《史记管窥》一书。) 马迁之后,经学开始在学术上占了支配地位。在汉儒眼中,经学是无所不能的。在这种局面上,我们后世所谓的史学依然没有独立地位,在《汉书艺文志》的书目里,只是将《太史公》等史书附于《春秋》经下。胡宝国认为,这在今人看来是贬低了史学,如果就当时而论,倒不如说是抬高了史学。诚如,如果不是因为如此,那后来经学衰而史学盛的演变也许就很难发生了。 在汉代,经学对史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在名称、体例,还是语言甚至注释上,史书中留下了大量地模仿经学的痕迹,著史的风气还没有形成。而史学与古文经学的关系尤其密切,这是由其自身的学术特点决定的。东汉的古文学家反对过多的微言大义,强调事实的考订补充,他们又热切地把《左传》纳于学官之中,这些事实,为人们重新认识《春秋》《左传》经书“史”的性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让我们看到了在经学泛滥的末代,史学兴盛的可能。 经学的衰落,主要是指作为意识形态的今文经学而言,而正由于古文经学的繁荣,才为史学的最终独立打开了一个缺口。后世经史的分离,最终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代。特别是在南朝,皇权不够强大,使得门阀士族私人修史变得盛行,而士人修史并不在于思虑一国之兴亡,他们借修史或是以求个人之不朽,或是记录家族的荣耀。六朝诗赋里常常人生无常的悲慨,分别寄托在了文学和史学之中。可是,当我看到书中有一份长长的名单:可考的东晋史家私修的史书至少有二十七部,然而,现在流存下来的只剩有两部了。读到此处,我不禁又悲从心来了。 这本小书的文风,有如民国学术的简约,更多了一分许多民国学人所缺乏的冷静,徜徉其间,如同在凝视着一片历史秋叶的枯脉。作者没有一叶知秋的感伤,而是在静静地讲述汉唐间史学的盛衰,淡看花开花落,而不以之为意。不知怎的,这让我想起了那位寂静主义的德国哲人,那个谈论生命与文化形式的西美尔。 西美尔说,个体生命一旦内在成为精神,就会渴望永恒,于是,内在涌动的生命精神,必然要寻求一种能够让生命无限流动的载体,而这,就产生了外在于人的文化形式。可是,生命与形式在历史之中,却处于一种潜在的对抗状态:文化形式作为框架,一旦获得了自己的合法性,就会与创造它们的生命精神保持一定的距离;而生命的本质是永 无止息的涌动,它必然要不断寻求新的形式来表现自己,从而否弃旧的形式。 透过西美尔的个体言说,我们或许更能够看清,无论是史学、文学,还是经学这些 文化形式的演变,与中国古人精神生命的深刻牵连。可是,只有少数个体生命所选择文 化形式足以承载他们不朽的追求,面对历史命运的残酷,只剩下我无尽的凄惶——此身何所托,千载不相违? 补记: 又读逯耀东教授的《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一书,若将此书与胡著两相对观,对于百代之前的那段学术升降,相信会有更为深切的了解。 虽然从研究范围上说,两书几乎是重合的,然而侧重点各不相同。对于经史分途这一曲折迂回的历程,胡著似乎更偏重从学术史的内部,指出史学脱离经学束缚的同时,得到了古文经学的滋养。而逯著在描述的这一过程时,首先注意的是,在史学主流的编年、纪传二体之外,出现了一系列非儒家价值体系的“新史学”写作形式,之后再进一步说明,这一现象与当时社会文化思想关系密切。 而如何才能更好地了解魏晋的时代性格呢?除了史学上新出现的大量别传之外,书中还特别注意了《世说新语》与魏晋史学的关系。《世说》将人物的言行分为三十六类,逯教授指出,作者的分类并非随意的,上卷篇幅最少,代表的是汉代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类型;而中卷的九篇,则是在“魏武三令”之后,儒家人格层次分化的转变期中出现的个性新类型;最后,下卷记录的已是“非汤武而薄周孔”的阮籍、嵇康辈了。无疑,《世说》是新旧价值交替时候的产物,它超越了《汉书·古今人物表》对人物的儒家道德评价标准。可以说,此章不仅揭示了魏晋人物品评风气对当时史学的影响,也是一篇很好的《世说》导读。 书中讨论《史通》与魏晋史学的文章,读了也让人获益不少。以往讨论刘知几的学者,往往容易只是注重反驳《史通》对中国史学的苛评。而逯教授则能够知人论世,特别论述了刘知几的“周身之道”。这与晚近流行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颇有相合,不过似乎还无人将刘知几《史通》与之相比附(已有人开始比附王船山了,恐怕不久也将会有人为此吧,一笑)。逯教授还注意到了“怪异乱神”的志异小说对魏晋史学的影响,这也算是肯定非儒家价值观念的一个旁证。 总的说来,逯、胡两书虽各有偏重,但在探讨魏晋经史分离、文史独立的原因时,都注意到了相当全面因素,所以并不显单薄。而对魏晋杂传与裴注《三国志》的研究中,胡著注意到了后世的演变,目光似乎要更长远一些。 史学具有独立的价值之后,同样被视为士人“不朽之盛事”,魏晋士人对不朽的追求,是促成我写原先那篇札记的原因,可是时人的著作在后世纷纷散佚,让我更加深切地感到某种幻灭。所以,我想到了西美尔,他那具有悲剧色彩的文化理论,虽抽象,却极深刻。无论古今中西,学术之升降,实是士人生死攸关的精神抉择。 ©taiyi123
《汉唐间史学的发展》读后感(五):细节决定一切——读《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札记一
自从多年前当米卢提出“细节决定一切”这一提法之后,这句话就在不同领域被借用,其确否当具体分析,但读胡宝国先生此书的第一印象就是此语,那就不妨借用一次吧。
魏晋南北朝史学似乎真已到了“细节决定一切”的地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料相比于隋唐以后来说,实在是缺乏得很的,基本史料就那些,这个领域的学者花上几年时间,大概也就能把基本史料读完了。当然,比起先秦秦汉来,魏晋的史料还是较多的,但应该看到,先秦秦汉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已依附于考古新发现。但凡有新的简牍、帛书发现,学者们一窝蜂而上,倒真是“预流”了,但也可看出学者们对史料缺乏情况下的无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许能说是学者们不愿意深入挖掘传统史料背后所隐含的重要信息了,选择新史料,很大程度上就是选择了便利。像辛德勇先生那样,能够从传统史料中挖掘出新问题,并作出重要研究的学者似乎越来越少了。)而相比于先秦秦汉的“幸运”,魏晋南北朝的研究者多只能默默耕耘于传统史料。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概是近现代史学研究最为深入的一个时期了吧,陈寅恪、唐长孺、周一良、田余庆等前辈深入、精深的研究,使得初入此段的学者颇感没有东西可以研究了。当然,既入魏晋之门,要想继续待下去,那也只能坚持发掘了。能发掘的是什么?大概就是细节吧。当然,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学者对细节的重视,也许也是有学术传统的,陈寅恪、唐长孺、田余庆等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前辈都是特别重视细节的。而可贵的是,这些先生在注重细节的同时,并不局于细节。他们往往通过小小的细节而阐释一个大的问题。
胡宝国先生(其实不如说将无同呢,比起其名,这个网名大概更为有名得多)此书虽以“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为名,但其“本意其实只是想讨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而胡先生师从周一良、田余庆等先生的学术背景,也使得胡先生的研究路数直接继承了他们的传统,即注重细节的同时通过对细节的解读来阐释一个大问题。我们不妨以此书第一篇《<史记>与战国文化传统》(以下简称“传统”)一文为例述之。
《传统》一文以“《史记》、《汉书》籍贯书法差异”为切入点,从《史记》籍贯书县、《汉书》书郡为中心,提出两汉政治文化的不同。对于《史》《汉》籍贯记载的不同并不是胡先生第一个注意到的,但对于这个问题,前人多只是将其作为细节问题,并未深入研究。但胡先生却特别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并以这个籍贯问题为出发点,看出了《史》《汉》所代表的不同文化背景,即《史记》代表的西汉前中期仍继承了战国文化,而《汉书》则是西汉后期到东汉时期文化的反映。从而,胡先生得出“政治上结束战国是在秦代,而文化上结束战国却是在两汉”的结论。这可以说是从细节中解读出了大结论。
当然,胡先生并没有在此打住,他又从《史记》书名、序、体例、对人的重视等方面对《史记》与战国传统进行解读。想必只要是看过这篇文章的人都能看出此篇虽以《<史记>与战国文化传统》为名,但不管是籍贯问题还是其他继承、差异,都是在说一个文化变化的问题。与其说是在写《史记》,毋宁说是借《史记》来梳理战国、秦汉文化的差异。胡先生此文盖以春秋及其前的文化、战国汉初文化和西汉中后期及东汉为三个颇有差异的文化分期,通过史学史的研究来解读文化史的问题。
无论是对细节的重视,还是从细节解读大的背景、问题的写法,多少都能看出其对陈寅恪、唐长孺、田余庆等前辈的史学方法的继承。
对于胡先生的结论,总体来说是佩服得很的,但是不是还有深入的余地呢?也许有吧。如对于《史记》,或者说《太史公书》的性质,胡先生只是推到了私人著作,只是说“这种以个人名字命名书的方式与《史记》籍贯书法一样,仍是来自战国的旧传统,诸子的书是成一家之言的私人著作,而《史记》也是要‘成一家之言’的私人著作”,此处不妨再进一步推阐,司马迁作《太史公书》原本也许就是为了规模诸子,使自己成为诸子之一吧。其目的可能不在作史,而是通过“史”的方式来阐释自己的理论、思想,这与先秦诸子的形式或有不同,但最终目的却是统一的。当然,这只是随便一说罢了。(李纪祥先生有《<太史公书>由“子”入“史”考》,《文史哲》2008年第2期,可参看。但此观点大概并未得到重视,或者说肯定。赵生群先生就在此文后的学术主审人语中就不同意直接将《史记》归入子书的观点。)
又如“史学内部的发展线索”节在论述《史记》对战国时期史书的继承时说“我也认为《世本》的确与《史记》有密切联系。这联系不一定是在体裁上,而是在内容上。我们知道,《史记》是以人为主的,而《世本》也是以人为主;《史记》记述皇帝以来以至作者时的历史,而《世本》也是从皇帝述至‘今王’。二书都强调通贯性。”而前文又引翦伯赞之言曰:“虽作为主题的政治人物地位不同,但以人物为记事的主体,则是相同的……书表在《史记》全书中所占的篇幅是很少的。例如《史记》一百三十篇中,本纪、世家、列传共占一百一十二篇,书、表合计只有十八篇。”对于这段文字同老并无评论,但从下文无一字及于表、志的论述中可以知道,同老也是同意翦老此说,并未重视表、志在《史记》中的重要性。但《史记》中本纪、世家、列传这些记述人物的内容与其说是继承了战国以来的史学传统,不如说是在政治文明不发达的情况下,英雄、传奇人物的记载肯定是史书的主要内容。战国之前,政治文明并未发达到记载政治制度的程度,故必然是以人物为主的。《史记》对于人物的记载,并不能看作是对战国史学传统的继承。相反,倒是表、志的创立可以看作西汉与战国时期政治文化的差异,而非对战国传统的继承。但恰在这点上,同老竟未置一词。同老在《我读<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写道:“将近二十年前,田余庆先生曾和我们学生说:‘要注意排除反证,没有反证的问题是简单问题,复杂问题往往有反证。反证必需在我们的考虑之中。’”同老此处对于表、志问题却未能以其老师的要求来深入分析。
同老此书本科时曾读过不止一遍,最近想起来了,就再读一遍。对于尚未入门的我来说,同老此书给予我的启迪颇多。这么一本好书,且以同老之盛名,竟然没有什么评论,真是可怪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