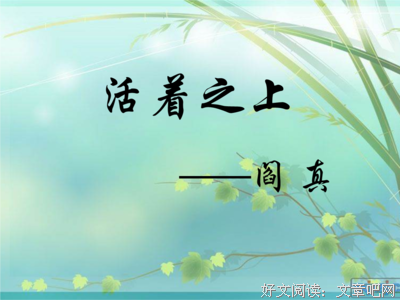《后现代状况》读后感锦集
《后现代状况》是一本由利奥塔 / Jean Francois Lyotard著作,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7.50元,页数:2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后现代状况》精选点评:
●最后一章“答读者问”和前面那些絮絮叨叨比起来简直是惊为天人。
●“语言游戏”之间的翻译也是一场语言游戏。
●维特根斯坦复读机
●哲学成为工作者的事物,和性成为性工作者一样,且并不高明
●读了一半放弃了,越往后读越看不懂,翻译几乎不说人话,读车槿山的译本去了。
●书是好的,看英文版都比看中文版清楚多,翻译脑子进水了吧
●讀完後唯一記得的概念,合法化
●解构得彻底 没有提出解决途径 后现代就是流变与不断的生成过程
●利奥塔我算是放弃了 他的脑洞和表达方式我进入不了
●家常读书
《后现代状况》读后感(一):后设论与合法的合法性
在“高科技社会中的知识状况”(利奥塔这样描述他定义为“后现代者”的研究对象)中,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提法。他说道:“所谓现代科学,仍然与正统的叙事学说有着显而易见的一致性,以‘后设论’的方式使之合法化。例如,在叙述者与聆听者之间,一句含有真理要素的话,要通过‘共识原则’才能被接受,必须要在理性心灵之间,尽可能获得一致性认同,这句话方可生效。这种法则,缘于‘启蒙叙事学说’。”这就引发了一 些疑义——“指导控制社会规范的那些典章制度是否真的有效。”可否这样理解,利奥塔指的是这些典章制度在设立之前与设立那一刻,它们并不具有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是在制度成立后后设的。这一点,在利奥塔看来,“我认为,我认为‘后现代’就是对‘后设论’的质疑”。可以说,在后现代语境中,合法的合法性遭到了存疑。
与利奥塔同声相求的,是阿伦塔,她指出宪法体制奠基性(founding)立法本身的悖谬:“如果宪法体制的权威来自宪法,那么制定宪法的权威来自何处?制宪者如何能具有正当的制宪权?”她认为,从卢梭到西耶斯,都遭遇了类似困境。德里达在对《美国独立宣言》的解构性解读中,同样指出,“以人民的名义”作出宣言的“我们”只有在宣言生效后才存在,在这之前,我们“何为”?只有在宣言效力形成的回潮之中,才生成了作为实体的签名者(见《悬而未决的时刻》),这其实也是利奥塔所谓的“后设论”——它对一切认为理所当然的叙事与表述发起了进攻,这种现代性政治典型的“无中生有”的模式,在后现代语境中也成了悬而未决的事件。
萨伯在《洞穴奇案》中,虚构了这样一个刑事案件,“五名洞穴探险人受困山洞,水尽粮绝,无法在短期内获救。为了维生以待救援,大家约定抽签吃掉其中一人,牺牲他以救活其余四人。威特摩尔是这~方案的最初提议人,但在抽签前又收回了意见。其他四人仍执意抽签,并恰好选中了威特摩尔做牺牲者。获救后,这四人以杀人罪被起诉并被初审法庭判处绞刑。”在不同的法官判决中,有法官就认为,四人制定的吃人获救的约法成立,四人无罪。但是,同样的问题出现了,是谁赋予这种吃人求生的约定以正当性?这位法官无论怎样为吃人者辩解,都会落入荒诞悖谬的圈套。
回到利奥塔,对于“后设论”的质疑,他认为最终会“遁入语言元素的语用学之中,那里拥有众声喧哗的语言游戏竞赛——如此一来,典章制度就随之消解,变成各种碎片——导致局部决定论的生成。”阿伦特与施密特都解决的不甚圆满的合法性问题,利奥塔的解决之道也许只能算是聊备一格——“靠科技性的运作指标,但这种指标和真理正义毫无关系。”
《后现代状况》读后感(二):这本译著翻译得差!
今天看利奥塔,偶然翻到一本笔名为“岛子”的人翻译的《后现代状况》,当我看到第30页的“后现代状况渐次摆脱掉合法化的盲目性偏执,如同异乡人逐渐适应了环境,摆脱了乡愁。”一句话简直惊为天人啊,这个比喻太牛叉了,我想利奥塔原来也是比喻的高手啊,天哪,简直又见到了一个本雅明似的。
结果!我于是热情地看了看本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的英译本,结果英译本是:“Still,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is as much a stranger to disenchantment as it is to the blind positivity of delegitimation.”(英文版第24页)
登时就崩溃了好不好,这个完全是两个意思好吧!于是又看了看车槿山的法文翻过来的译本,这句话车槿山的翻译是:“不过后现在与这种幻灭无关,也与非合法化的矛盾实证性无关。”这个算比较准确的翻译了。
我觉得一个文本从一种语言同时翻译成两种外语A和B,外语A和外语B的两个版本还是可以比对的,至少意思应该差不多,按照本雅明的话说虽然两者是不同的“瓶子碎片”,但毕竟是同一只瓶子上的碎片好吧。但是看“岛子”这个“异乡人”的意象,该是纯粹意淫吧。而且仔细比对了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的英译本,以及车槿山译本,和岛子这个版本的这句话所在那一段的译文,车本和英译本意思基本一样,岛子本的意思基本是反的,看来岛子原文都没有读懂啊。
另外还有个非常明显的问题,比如对利奥塔那句对后现代主义的定义的翻译上,我们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出问题:
(车槿山)利奥塔:“简化到极点,我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第2页。
(英译本)Lyotard:“Simplifying to the extreme, I define postmodern as incredulity toward metanarratives.”(第24页)
(岛子)利奥塔:“简而言之,我认为后现代就是对‘后设论’的质疑。”(第29页)
我对比了三个版本就可以看出,我不知道车本为什么翻译成“我们”,当英译本是“I”的时候,这难道是受我们在中文论文写作惯例影响?我们在写论文时确实常常习惯写“我们”作为提出论点的主体。但不管如何,其实车槿山这样翻无伤大雅。但是岛子的译本就很奇葩了,“后设论”是神马东西?难道岛子同志不知道“元叙事”这个概念?我看到这里已经很好奇“岛子”到底是何人了。
所以“岛子”这个译本实在是差,不值得豆瓣的7.4的总分,竟然没有人打1星,所以我给1星。我就实在不清楚那么多打5星的人到底是怎么想的。7.4这个分数太高,实在是太误人子弟的了。我真的很少吐槽的,但是我碰到这样的译本,真的是第一回啊。
看来以后看译著至少要拿一本英文本子在旁边翻着。如果够有兴致要直接看英文才行。
《后现代状态》推荐车槿山的译本,言简意赅,翻译准确。
参考书目:
[1] Jean-Franc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M], Translation from the French by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1984.
[2] [法]利奥塔著,车槿山译:《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M],三联书店,1997年12月。
[3] [法]利奥塔著,岛子译:《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M],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6月1日。
《后现代状况》读后感(三):这本译著翻译得差!
今天看利奥塔,偶然翻到一本笔名为“岛子”的人翻译的《后现代状况》,当我看到第30页的“后现代状况渐次摆脱掉合法化的盲目性偏执,如同异乡人逐渐适应了环境,摆脱了乡愁。”一句话简直惊为天人啊,这个比喻太TM牛叉了,我想利奥塔原来也是比喻的高手啊,天哪,老子简直又见到了一个本雅明似的。
结果!我勒个去,我于是热情地看了看本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的英译本,结果英译本是:“Still,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is as much a stranger to disenchantment as it is to the blind positivity of delegitimation.”(英文版第24页)
老子登时就崩溃了好不好,这个完全是两个意思好吧!于是又看了看车槿山的法文翻过来的译本,这句话车槿山的翻译是:“不过后现在与这种幻灭无关,也与非合法化的矛盾实证性无关。”这个算比较准确的翻译了。
我觉得一个文本从一种语言同时翻译成两种外语A和B,外语A和外语B的两个版本还是可以比对的,至少意思应该差不多,按照本雅明的话说虽然两者是不同的“瓶子碎片”,但毕竟是同一只瓶子上的碎片好吧。但是看“岛子”这个“异乡人”的意象,该是纯粹意淫吧。而且仔细比对了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的英译本,以及车槿山译本,和岛子这个版本的这句话所在那一段的译文,车本和英译本意思基本一样,岛子本的意思基本是反的,看来岛子原文都没有读懂啊。
另外还有个非常明显的问题,比如对利奥塔那句对后现代主义的定义的翻译上,我们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出问题:
(车槿山)利奥塔:“简化到极点,我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第2页。
(英译本)Lyotard:“Simplifying to the extreme, I define postmodern as incredulity toward metanarratives.”(第24页)
(岛子)利奥塔:“简而言之,我认为后现代就是对‘后设论’的质疑。”(第29页)
我对比了三个版本就可以看出,我不知道车本为什么翻译成“我们”,当英译本是“I”的时候,这难道是受我们在中文论文写作惯例影响?我们在写论文时确实常常习惯写“我们”作为提出论点的主体。但不管如何,其实车槿山这样翻无伤大雅。但是岛子的译本就很奇葩了,“后设论”是神马东西?难道岛子同志不知道“元叙事”这个概念?我看到这里已经很好奇“岛子”到底是何人了。
所以“岛子”这个译本实在是差,不值得豆瓣的7.4的总分,竟然没有人打1星,所以我给1星。我就实在不清楚那么多打5星的人到底是怎么想的。7.4这个分数太高,实在是太误人子弟的了。我真的很少吐槽的,但是我碰到这样的译本,真的是第一回啊。
看来以后看译著至少要拿一本英文本子在旁边翻着。如果够有兴致要直接看英文才行。
《后现代状态》推荐车槿山的译本,言简意赅,翻译准确。
参考书目:
[1] Jean-Franc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M], Translation from the French by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1984.
[2] [法]利奥塔著,车槿山译:《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M],三联书店,1997年12月。
[3] [法]利奥塔著,岛子译:《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M],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6月1日。
《后现代状况》读后感(四):后现代时期的思潮
人类的文化一直在发展变化。相比之下,其他动物的文化(如果有的话)就很少发展。动物的文化是固定的,因为它们的文化牢牢限定在它们的习性上,比如说,十万年前的狗,和今天现代社会里的狗,表现就差不多。那时候的狗发展出帮助人类除去秽物的习性,比如吃掉人吐的痰或大便,今天的狗也是如此,如果你给它们机会,它们就会展现出这种习性。今天的猫被人养在卧室里,甚至一辈子可能都不会见到一只老鼠,但是其本性依旧,尽管它们的独居本性导致人们以为猫很高傲,它们被赋予了一种新职能,即,给人类带来一种心灵抚慰,作用就像毒品直接刺激人的快乐中枢一样,不过仅仅消耗人的时间、注意力和“志气”,并不会像毒品那样直接伤害人的大脑某些功能,或者像抽烟那样影响人的肺和呼吸,或者像酒那样影响人的海马和记忆。Harari说,就像他的爱人在和他一起用餐的时候,眼睛离不开手机屏幕,他干活的时候也会忍不住去刷网上小猫小狗的视频。一定是他在《今日简史》末尾所提到的他练过冥想,所以他抗拒住诱惑完成了三本《简史》。
不是说人类的硬件能力有多强。蝙蝠的声纳、鹰的视觉和狗的嗅觉,在硬件上远超人类。人类智能的表现似乎有两点,其一是对世界建模的范围大。就像Humphry(?)所言,他用铅笔触一个蜘蛛网,蜘蛛慌忙爬出来看看是什么猎物,然后它一看是一个人用铅笔跟它开玩笑,骂骂咧咧就回窝里了——这是利奥塔在本书中所谓的“叙事知识”,但这根本就不能说是“知识”,所以利奥塔是搞错了,这只能说是一种meme,一种精神片段,而不能说是知识,尽管“知识‘必然是一种精神片段,但是不能说精神片段都是知识,比如一个谣言也会广为传播,就像上次美国大选,网络谣言说候选人希拉里绑架一些小孩到一个岛上做性奴,这个谣言也传播到了中国,很多中国人都信了,我记得当时我的第一直觉是“震惊”,根本就没有立即认为是谣言;Harari说这种谣言影响到了大选的结果,我是相信的,Gazzaniga说我们的大脑系统中,有很多的自动处理模块,这些模块仅仅像我们的“意识”即interpreter返回一个结果,而不会传递计算过程,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有一些想法、冲动或直觉,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是怎么来的,其中一些模块我称之为operatees,意思是,只要外界提供一种对应的“操作”,就会触发你的这些自动反应operatees,就会引发你的某些冲动或想法,无论是你否十分抗拒这种冲动或想法。我在很多书中都看到过关于这些自动反应机制的论述,如丹·艾瑞里的《怪诞行为学:可预测的非理性》、罗伯特·西奥迪尼《影响力》,还有更为科学的Kahneman的To think, Fast and Slow,Aronson的the Social Animal,也都有中文译本。Gazzaniga说,大脑有一个interpreter,就是现在你和我感觉到的这个“我”,他说,这个interpreter实际上是仅仅具有一种掌控全局的错觉。我相信我们肯定和Hamilton一样,对此深有感触,我们的很多欲望、冲动,我们的很多想法、行为,并不是完全在我们的掌控之下;Hamilton说,“我”就像一个内部力量相互冲突的政府派往海外的一个“大使”,受不同力量的推动,夹在中间,场面一度很尴尬,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听人说,“那不是我真正的意思”,“那不是真正的我”。此处实际上还涉及一个Damasio所谓的autobiographical self的动态变化、重构问题,不多谈。Humphry(?)实际上说,蜘蛛根本看不见铅笔和我,我和铅笔在它的宇宙之外——此处就涉及一个Holland所说的生命体作为复杂系统对外界所做的内部建模问题,在蜘蛛的大脑中,不存在对铅笔和人类的表征。相比之下,我们的大脑对世界表征的范围要广阔得多。但是,这还不是关键因素。
关键因素是,人类的智能有一种安装更新的能力。就像是人类的智能提供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升级软件、以及安装新软件,有点类似Daniel Dennett所谓的虚拟机的能力。这种能力并非人类独有,动物智能也存在受环境的塑造而更新schema的能力,Murray Gell-Mann在《夸克与美洲豹》中提到,狗也有更新自己图式,比如学会用新模块,即听从主人的话,抑制自己追逐猫或松鼠的原有模块的能力。相比之下,人类的智能要灵活得多,给新模块提供的空间要广泛得多。这种能力如此之强,以至于就像人们常说,人类进入了一种通过文化进化代替生物进化的模式。也就是说,虽然上万年来,人类的生物基础没有发生变化,基因、神经基础都一样,但是人类发展出惊人的“软能力”,即知识和文化。Jared Diamond在《崩溃》中提到,那些土著的孩子,进入其他现代社会,也学会了开飞机和用电脑,和文明人没什么两样。这或许说明,像列维·布留尔和Edward Tyler认为土著人,是智力上类似小孩子的一种人种,是错误的。Franz Boas如果真像罗伯特·赖特在《非零和时代》中所提到那样,出于一种政治正确式的担心,因为忧虑生物差异会导致类似希特勒这样人搞不人道的政治运动而趋向于一种同等优秀或不可比较文化相对论,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希特勒的这种运动本身犯了功利主义和自然主义错误,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以此来提出一种文化相对主义,正如赖特所说,不仅是不必要的,也是不正确的。赖特说,人类本性同一,因此任何社会的发展必然趋同,我认为他的这个看法是对的,也就是说Ruth Benedict在《文化模式》中所提到的存在一个great arc,不同族群从这个大弧上选取一些来构成自己文化的说法,只有部分是对的,一则在原始小族群分散在不同的环境中,才会出现各异的文化,就像世界各地的族群发展出关于本族和世界不同的神话传说一样;二则一旦文化逐渐发展,就会趋同,所有文化都趋向宇宙大爆炸理论,因为所有错误的模式都不断进行修正,而正确的模式只有一个。很多人哀叹这世界上不同的文化、语言消失,消失是必然,也仅仅在学术研究的意义上才是值得惋惜的。甚至未来有一天,或许这个世界上会只剩下一两种语言。
说人类文化在一直发展,就是指,文化作为一种“程序”,一直在扩展、完善。这种发展有痕迹可循。在原始社会,如Frazer所说就是巫术、神话,就是利奥塔所谓的“叙事性知识”,就是制度上的狩猎-采集生活和对应的图腾、祖先崇拜或其他宗教,就是邓巴所说群体上的150小群落。然后就是一路发展,更大的群体,意识形态上更为完整的宗教,科学的兴起,民族国家一直到今天的地区共同体。利奥塔强调,知识不仅仅是“科学”这种描述性的知识,前面提到,实际上就是囊括了所有对应meme的文化,比如“割礼”这种残害女性的习俗,这算什么知识?利奥塔并没有想到这些。他只是注意到,像“叙事性知识”,卷入在整个社会结构、权力和活动之中。 正是由于受这种观点的误导,利奥塔在社会学理论上,反对反对“有机体论”的帕森斯的系统论和马克思的阶级论,自己提出一种类似“语言论”的观点。现在来看,社会学研究合理的建模是复杂系统论,而“语言”,只是符号学的一部分,“符号”,只是系统互动中用于作为识别的tag的另一种称呼,对应的是Holland所提出的CAS3个机制中的tagging。利奥塔受后现代一些理论的影响,比如索绪尔和德里达的语言符号意义理论,或者还有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也开始迷信语言分析,实际上,语言仅仅是一个人际交互的工具,如Gazzaniga所说,语言实际上是用于实现一种“操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语言的人们包括Austin发现,语言自身不仅仅是一种表述,很多其他功能,比如“你去死吧!”就不是一种表述;因此,在语言内对语言进行纯粹的一种分析,试图通过语言来解决社会系统问题,是本末倒置了;在同样的意义上,哈贝马斯尝试以沟通作为着眼点来解析整个社会,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如果说后现代出现了后现代主义,那么也可以说现代出现了现代主义,前现代出现了前现代主义,古典出现了古典主义,原始部落时期出现了部落主义思潮。我的感觉里,很多人有一种蹭热点的感觉,提到“后现代主义”,就感觉自己逼格高了很多,写个东西就扯上后现代主义。不仅如此,后现代主义,在我看来,就如我上一次所谈到的那样,是一群才能欠缺的人,对现代主义的理想失败后的一种犬儒式的反应。有一个公式可以说古今通用,那就是,对于才华有限的人来说,他们搏出位的最有效的方式是破,打破常规、标新立异。芙蓉姐姐和凤姐都是这样成功的,无论她们是有意还是无意。我记得有人写过一篇出色的关于快手的文章,我查了一下叫《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看看这些人都在做什么,在表演一些惊世骇俗的东西,但是他们没有才能、财富、成功来惊世骇俗,于是就表演反向违反常规的往俗里走,表演装疯卖傻、带孩子表演黄段子、色情(显然不断被审查封掉),往坏里走,少年学社会人抽烟、喝酒,往怪里走,表演生吃死猪、生吃蛇、蛆,吃玻璃铁钉,表演自虐,炸裤裆、活埋。这是真正的原始大众文化,作者说,这些人或许会有百万粉丝,但是观看的往往和那些表演的人一样,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没有经受过现代教育的熏陶,生活在精神贫瘠的如同荒漠一样的世界中。我相信他们也爱看明星的综艺节目,但是这种世界,给这些亿万的农村人的刺激,或许和那些城市居民或对应的受过教育的阶层不一样。尽管这些城市居民、受教育阶层和中产阶级,自己的生活平淡无味,也需要寻求精神上的刺激,尽管他们的口味已经改变,并不喜欢去看俗、怪、贱,变成靠看明星带孩子、明星去田野里体验、明星去世界上旅游,通过这种虚幻的“代入体验”来哺喂他们空洞的内心。
原始时代,人们除了日常经验无所依托,只能靠一代代人的想象力编造故事;受原初智能的影响,尤其是故事倾向、拟人化错误、比喻建构,导致各种荒诞不经的神话和巫术。中世纪有宗教时代、封建意识形态的特征,而现代有宗教没落、科学和理性崛起的特征。如果说,理性和科学的崛起导致现代主义提出一种宏大的理想,而这种天真的乐观失败了,那么后现代主义,或许可以说,是一种对现代主义的反思,以及对问题的一种新的探索。现代主义,我还没仔细研究,印象中似乎是启蒙时代,受到新科学的激励,以为世界可以通过科学简单搞定,就像牛顿的物理世界那样,能够计算和掌控。不说科学上相对论和量子学使得这种简单世界的理想成为泡影,世界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谁也没有聊到,政治学和经济学、社会学面对的对象是一个复杂系统,复杂系统的特征之一就是非线性,至少目前来看,不可计算、不可预料,甚至就像高维空间、空间扭曲、量子现象那样不可想象——我们现在落到了蜘蛛的境地,我们大脑中没有对这些元素进行建模,这些成了我们大脑之外的东西;好在虽然我们不能想象,但是我们间接知道它们的存在,多亏我们的外接扩展“软件”,是它们算出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有限的智力,在不同的时代,都在构建一种关于世界和自身的paradigms,随着时代不同,paradigms在更替,就像Thomas Kuhn所提到的科学革命的方式。我不确定Kuhn是不是像普特南所说的是提出了一种相对主义,但我不认为无论是在科学上还是在文化上是存在一种相对性,实际上应该看作一种不断的升级,无论是范围、精细度和完善性上。不同在于,科学趋向于唯一的真理,即自然模型,而文化paradigms的更替不仅是关于自然模型,同时也关于人类社会自身。但是这并不适合艺术创作。艺术创作核心是审美,审美是什么?或换个问题,美是什么?一开始人们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至今似乎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我记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很多,比如说美是对称、均衡、比例,美是星星、是闪亮、是光辉,美是形式,美是实用,美是完善,美是真,是善,是太一,种种。这是我们经验上的美,对感受到的美的描绘。或许答案不在于这些对象或对象的特征,而在让我们产生这种美的心理机制,或说智能模块。比如说,利奥塔提到,塞尚是向印象主义的空间提出挑战,毕加索和勃洛克是向塞尚说不,而杜尚要突破的是艺术即绘画而绘画是立体主义这种观点。艺术风向的这种变化,和时尚的变化有点类似,总是要“新”,因为“新颖”本能上会给人带来一种快感,反复看同一种风格会审美疲劳,就像你反复吃同一种食物会厌腻,你的身体提醒你需要吃别的杂合营养,“熟悉导致轻视”,一旦烂大街就表示价值平庸,只有与众不同才有价值;同时,新的东西,可能表示一种创新能力,所以我们对“新”有一种本能的好感,甚至愉悦。我这样说,有点把审美庸俗化的意思,但是如果审美确实如此,我们就该勇敢接受,而不该沉浸在一种虚假的浪漫情怀之中。真的猛男(美女),敢于直面庸俗的美的本质。更何况,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种生物机制,让它不再庸俗。
利奥塔提到叙事性知识和科学知识的区别。他提到,叙事性知识“与内在的精神的平衡和愉悦的概念有关”,而现代科学知识对此毫不相关。什么意思呢?利奥塔的意思是,科学知识是关于自然的一些知识,比如遥远宇宙空间中的黑洞,或者通过基因编辑造出一种缺水就发光的土豆。但是,这种知识,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理想、我们的人生意义,没有什么大的相关。但是,叙事性知识,就像古代的神话谈到宇宙和神,和我们的诞生以及我们的任务,规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向。利奥塔说,因为科学的这种特性,人们已经对科学产生了“怀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科学推倒了我们的信仰,却没有给我们提供一种新的信仰。本来,人们是靠相信,宇宙存在一些原理,比如因果相报,或者存在一种神的秩序,比如宗教中听从上帝的教导,使得我们的生活存在一种依靠或遵守的标准。然而,科学告诉我们,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茫茫空间之中的一个尘埃行星之上,我们是生命算法的产物,我们甚至没有灵魂。于是,很多人从一种有依靠、有规可循、有意义的生活状态下掉了出来,精神上变得无家可归,崩溃了。因此他们对科学和科学家,都有一种不满。利奥塔这个看法,是有局限的。他仅仅看到了眼前所发生的情况,但是他没有看到,现在的这种“科学”,仅仅是关于自然,但是科学早晚延伸到“人和社会”自身。并不是说,一提科学,就仅仅是自然科学。社会、人自身,也是科学,不过是因为太过困难,我们的人文或社会科学还尚未或刚刚开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里查德·费曼说他才去搞理论物理,因为社会科学太难了,但是自然科学要容易很多,他说。所以,这是利奥塔对所谓的“科学”的一个误解。就像他遇到一个中国人,看到这个6岁的中国人身高1米,就说,中国人身高1米。利奥塔认为,科学家虽然采用一种科学的语言,但是一旦面对大众,比如在采访中,他们又回到传统的叙事方式,原因是因为“科学语言游戏希望其说法成为真理,但却没有能力凭借自己的力量将其合法化”。他还提到柏拉图、笛卡尔这些人都采取传统叙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真理”,这刚好对应了他所说的合法性问题。
所谓合法性,看上去,就是一种被肯定,无论是被认为为“真”,还是“有用”,还是其他别的什么。有时候是通过共识,比如得到其他业内人士的首肯,就像科学家的研究,这是一种共识论;有时候是被权力或资源提供支持,比如权力或资本对一些研究提供支持。显然,前者就是一种所谓科学的哲学标准,即,为科学而科学,为真理而真理;后者是一种政治标准,为发财而科学,为维护统治而科学。在谈到叙事知识和科学知识的关系时,利奥塔曾说,传统叙事知识对科学相当宽容,但是反之不然。利奥塔说,这是因为叙事知识自身没有规范,所以将科学知识看作一个变体。这种说法我以为是错误的。传统叙事知识是什么?是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并不求真,而是承担一种社会功能,所以对求真的科学并不在意,除非科学威胁到意识形态——实际上这正是历史上实际所发生的,科学反复威胁到了意识形态,于是权力,无论是宗教还是政权,都对科学进行过压制和招安。今天我们的社会里,难道没有对近代中古历史研究进行压制?上段末尾我提到利奥塔的一个错误,说科学家在采访中重回叙事方式,而不用科学语言,是因为要成为真理只能凭借叙事手段。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其一,大众听不懂科学语言,不得已,科学家才重回叙事,这是对大众智力的妥协,而不是为了什么成为真理;其二,当进入叙事语言,被科普之后,恰恰“真理”变得不那么真了。真理,仅仅存在于科学的语言中,因为需要有一种精确性。利奥塔说,科学性的知识不能自我证实是真知,也无法使别人知道其为真知,除非他诉诸另一种知识,即叙事的知识。这个说法非常的错误。科学性的知识是否是真知,是靠提供这种知识的人提供他获得这种知识的过程,任何具有相应的能力的人,都能够审视和检验他的这个过程,来核对对错。也就适合说,科学性的知识的真伪,在于其过程是否无懈可击,无论是在当代,还是在千秋。利奥塔的所谓“真知”,就是变成通俗的语言,编成故事,让人民“认同”,这简直是开玩笑。利奥塔反复强调,所谓科学知识,不过是一群科学家的共识。这是非常表面的一种看法。他说,后现代的知识法则,不是专家的一致性,而是创造者的悖论推理或矛盾论。这就是我瞧不起后现代的地方,后现代就像我提到的那个老罗举的例子,由于自己爱情收到了欺骗,于是就再也不相信爱情了。这是软弱的一种象征。如果说,以前专家的一致性,甚至智者的一致性都是错的,我们也完全不必因此再也不相信“一致性”或再也不相信有真理存在了。就像是说,一个人掘井,掘了10尺没有水,于是我们就认为此处掘不出水。这就是那个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的道理。别人做错了,你不一定把这种做法或这个目标都否定掉,可能只是这个人没有做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