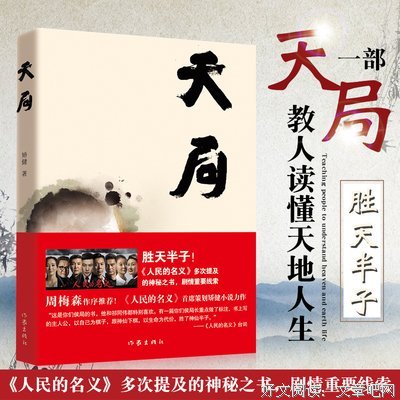塔窟东来读后感精选
《塔窟东来》是一本由王南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页数:21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塔窟东来》精选点评:
●周五晚上去大同随身携带了这本书。大同市里还有不少好地方没去,云冈石窟来回走了两遍。
●敦煌的后劲太大了,回家一年后依然沉迷。这本书不仅讲敦煌,而是讲魏晋南北朝及以后佛教建筑艺术东传,在华夏被翻译改造的过程,敦煌是其中的华彩,见证了许多灵感的迸发。
●这本实在太好读,五万言一气呵成,合上书页才发现五小时的车程刚刚过去三分之一,后面我该怎么办?! 书里远眺永宁寺塔、佛宫寺塔地平线上高耸浮图壮伟无匹的幻境犹在眼前,扭头看向车窗外却只有一片片施工中的住宅小区,梦想照进现实,也太残忍了一点。 138-139页卢舍那佛庄严宝相隐于装订中线不得而见,扼腕。 永宁寺塔与减法建筑是最喜欢的两节,永宁寺塔火焚后重现于海上,形灭神存既是幻望又颇有流传。关于石窟开凿施工的想象,则是这册中最让我感动几欲落泪的部分,匠师泉下有灵,也会欣喜有王老师这样的知音吧。
●买了舍不得读系列
●3.3。挑个刺儿,书名叫作塔窟东来似不妥当,东来指从东面来,东有向东,东行的含义,一般用为东去,放在此处也不合本义,作西来较合义。
●受教了
●越读越觉得无知
●太美了,又做了好多笔记。
●再去趟云冈
●印度窣堵坡在中国的演进,塔刹、石窟的起源和变化;在回家途中读完,顺便在到家第一天去看了太原永祚寺的双塔。
《塔窟东来》读后感(一):《塔窟东来》读后
此书主要讲了佛塔、佛窟、佛教壁画以及佛教雕刻四大方面。佛塔方面,从印度窣堵波演变为中国式的楼阁式佛塔、单层密檐式佛塔及其他类型。“相轮”则成为了塔刹。佛窟方面,则从印度有内无外式的佛窟演变为内外兼得的塔庙窟和僧房窟。从塔庙窟发展出的塔状中心柱窟(有的呈倒塔状)尤为重要,覆斗顶的创造则形成了壮美的中国式佛窟。从印度传来的“塔”是中国早期佛教建筑的重心,随着时光流逝,这一地位也逐渐消逝了。这也是佛教中国化的一方面表现。雕刻方面讲印度的较多。一方面受希腊影响的犍陀罗佛像进而演变为有印度特色的迦毕试式佛像。另一方面,笈多时期发展出了湿衣佛像和裸体佛像。受地缘影响,中原与西域多接受湿衣佛像,南亚、东南亚多接受裸体佛像。印度佛教壁画受其自身传统影响,“色情味”(八味之一)极其浓厚,表现了印度“既虔信宗教又眷恋传统,既寻求解脱又执着人生,既崇仰精神又沉迷肉感,既敬重苦行又陶醉爱欲”(王镛)的文化矛盾。而中国则尽量去除了不适宜本土的印度特色,将其变为了《洛神赋》中的神仙造型。“飞天壁画”尤为表现明显。
《塔窟东来》读后感(二):随手记
塔窟东来
所谓塔窟,即是佛塔和石窟,东来的意思是佛教文化艺术自印度一路东向传入中原地区,使得基于佛教文化的佛教建筑在中华大地广播落地生根,这就包括佛塔石窟以及附属于其上的绘画和雕塑。中国古代匠人如翻译经书一般将其本地化为中国佛教艺术自己的语言。佛教最早东汉即传入中原,但塔窟建筑却是在魏晋南北朝得到长足发展,作为汉唐两座建筑高峰的过渡时期,魏晋木制建筑因为各种原因荡然无存,相比汉朝通过陵墓认识其建筑面貌,魏晋则有了佛塔和石窟两类建筑资源,如《洛阳伽蓝记》描绘的九十丈浮图千尺北魏永宁塔,又如莫高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三大石窟。
本书的两大主题:
一为介绍中国如何本地化塔窟,吸收内化,结合中华风土人情文化习俗,创造出中国特色的佛教建筑,雕刻和绘画 。
二为对比中印,对佛教艺术主题如佛、菩萨等的殊途同归。
【天竺原型】
印度佛教建筑的最重要遗存:佛塔石窟,可从中一窥中国佛塔石窟原型。
造像艺术包括的庞大体系:佛 菩萨 药叉 药叉女 飞天等等。
【浮图千尺】
永宁寺塔
133米木结构杰作(2倍高于山西应县木塔),《洛阳伽蓝记》描写远近景特写及被火烧(三月不灭),仅仅存在十八年,北魏倾尽财力物力,“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火烧当年北魏也灭亡,颇有点气数已尽的感觉。
塔的发展
楼阁式和单层密檐式,木制到砖石,后加以琉璃砖瓦装饰 。
【云冈凿岩】
石窟晚于佛塔东来,保存了大量当时建筑题材的雕刻与壁画,以及包括壁画雕刻彩塑之类附丽于石窟中的佛教造像艺术。
石窟建筑之于魏晋南北朝,一如墓葬建筑之于两汉,是研究此时期木结构建筑的珍贵线索,堪称“石头的史书”。
【敦煌绘壁】
历代石窟变迁在莫高窟上得以展现,因其石质过于坚硬难以精雕细琢,故逐渐发展为除正面群塑外,其余皆以壁画表现,因此创作空间得以尽情发挥,而终为莫高窟之魂。
【极乐世界】
佛教东来,使得中国得以融合印度的艺术传统催生出中国自己的佛教艺术,从建筑角度则是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面貌(佛塔和石窟),另一方面,印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由于文化交流也受到了中国佛教艺术的反作用。
整体而言,比之印度,中国佛塔,石窟虽然在雕琢之繁复精细有所不及,但论及类型规模体量和空间等方面则青出于蓝,如敦煌的印度原型阿旃陀石窟反而被誉为“印度的敦煌”;附属于石窟佛塔的绘画及雕塑则是各擅胜场。
中国文化讲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因此在吸收印度佛教艺术时摒弃了最具印度特色的部分(艳情味),所谓于艳情中见悲悯,于恋世中求解脱的矛盾共同体文化互补特性,而追求自然气韵生动之超逸风骨,中国飞天即为典型代表。
《塔窟东来》读后感(三):读书与行路
我跟C老师说,如今才发现,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缺一不可。
感慨何来呢?
看塔窟东来这本书,讲佛教如何传入中国并影响了中国的建筑、雕刻、绘画艺术,同时中国的匠师们也用中国式特色改良了印度佛教建筑和符号。比如印度早期的佛教礼拜对象是一种叫窣堵波的佛塔,其半圆形的覆钵、其上的方形宝匣和层层的相轮象征佛教的宇宙。
典型窣堵波——印度桑奇大塔,图片来自网络但是中国人不大能接受这么个实心大圆球,于是在佛塔中国化的过程中,半圆球被中国式楼阁所替代,唯保留并放大了顶部的宝匣和相轮,形成中国人熟悉的佛塔样式。
中国式佛塔,图片来自网络当然还有一些佛塔保留了与窣堵波接近的样式,比如北京白塔寺的白塔。
白塔寺白塔,图片来自网络以上是大致的背景知识。
书中讲到,中国汉地佛教建筑肇始于东汉,当时东汉明帝派使者去天竺取经,使者回来后在洛阳西门外建了白马寺。所以白马寺大概是中国最古老的佛教寺庙。
看到这里我想起2011年去洛阳玩的时候我去过白马寺,当时除了被那24尊空心佛像震撼到之外竟没留下什么特殊的记忆,于是我开始翻当时去洛阳拍的照片,试图唤起有关白马寺的记忆。但是我发现了这个:
白马寺旁白的一个异域风情建筑,拍摄于2011年我去,我定睛一看,尼玛这不就是印度窣堵波吗!
当时只觉得为啥白马寺旁白猛然出现一处异域风情建筑,诡异的很,还以为当地政府规划又抽什么风了,于是拍了下来。如今才找到答案,当时真是孤陋寡闻矣!
(我把这件事讲给当时一道去洛阳的mengmeng听,她说我真是个严谨的摩羯座!)
你看,不读万卷书,只行万里路,就容易变成睁眼瞎。
以前“玩”过很多地方,是真的玩,要么奔着或壮美或旖旎的自然风光,要么冲着或雄浑或炫丽的人文建筑,多半是为了一饱眼福或者拍照好看,还停留在初级的感官刺激。对于人文建筑,往往是打卡游,常觉得无聊。然而这许多以往过眼烟云的建筑,回头看却发现了不一样的滋味。
对罗马建筑也是一样,读完万神殿堂之后重翻照片,又有了不一样的领悟。
年轻的时候我们呼啸飞驰,游荡四方,用眼睛感受世界。成熟后,或许该多用心来感受这世界了吧,尤其是古建筑,历经岁月沧桑,大多已经没有了华丽的外表,如若不仔细聆听,怕是感受不到他们的美。他们的美,自然不在于眼前看到的有形形象,更在于穿过这一活生生的形象,一幅千百年前的壮阔图卷在眼前徐徐展开。千古朝代更迭,帝王宫室终埋荒冢,王侯将相俱成云烟,唯有艺术永恒,美是永恒。
To go list:
1、北京 真觉寺、银川塔林、天宁寺塔
2、山西 五台山(佛光寺、南禅寺)、云冈石窟、应县木塔
《塔窟东来》读后感(四):佛教传入
《塔窟东来》勾勒的是一副佛教西从印度沿着丝绸之路向着东方传入中国的盛大画面。佛教传入,不仅影响了思想和精神层面,也对中国建筑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中西建筑相互融合,迸发出新的激情。书本历史从东汉末年跨度到唐代,阐述了佛教建筑从进入到本土化的演变过程。
一、三国两晋南北朝 1、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将汉献帝软禁许昌。220AD,曹丕自立为王,改国号为魏,魏蜀吴三国鼎立。三国时期总共45年。
2、魏先灭蜀,265AD司马家建立西晋,后灭吴,全国统一。
3、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五胡入侵。317AD西晋臣民逃亡江南建立东晋,南北方隔江而治,西晋统一51年。
4、长江以南从317AD之后经历东晋、宋、齐、梁、陈,每个朝代都不到一百年。
5、长江以北五胡乱华之后由北魏于386AD统一。北魏统一148年,时间较长。后分裂为东魏、西魏。北齐取代东魏,北周取代西魏后灭北齐、灭陈。
6、581AD北周杨坚建立隋。
7、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220AD-581AD),相当于古罗马帝国的中后期(27BC-476AD)
二、古印度历史时期
1、332BC-185BC,孔雀王朝,顶峰为阿育王时期。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时期(476BC-221BC)-秦(221BC-206BC)-西汉初年(206BC-8AD)。
2、200BC-200AD,入侵时期,最主要的是贵霜帝国,受到希腊和波斯的影响,产生“犍陀罗艺术”。相当于中国的两汉时期(221BC-220AD)。
3、320AD-540AD,笈多王朝,产生“笈多艺术”。相当于中国的南北朝时期。
三、印度原型
孔雀王朝是古印度第一个统一的王朝,其中阿育王享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阿育王戎马一生,晚年放下屠刀皈依佛教,开始在印度大兴佛家,广盖寺庙。
1、窣堵波
最早的印度佛塔名叫窣(su)堵波,象征释迦牟尼的坟冢。早起佛教反偶像崇拜,都以窣堵波作为参拜对象。窣堵波为半球形“覆钵”,内土外砖,实心,上有“宝匣”和“相轮”。相轮象征圣树,宝匣象征围栏,象征着宇宙之轴,外部有带有雕刻的围栏和塔门。佛塔均由窣堵波演变而来。
2、支提和毗诃罗
支提是礼拜场所,内含窣堵波,像是一个负的巴西利卡;毗诃罗是僧人居住的地方。
3、佛像
1)犍陀罗佛像
早期印度佛教反偶像崇拜,只参拜窣堵波。贵霜王朝开始建造佛像,以希腊太阳神阿波罗为原型,建造犍陀罗佛像,有以下几个特征:波浪式卷发、希腊鼻、半闭眼、朴素的光环、罗马式披风,面部祥和、平静。犍陀罗艺术中“迦毕式样式”的佛像较有特色,光环中带有火焰,佛像特别刻板有力。
2)笈多式佛像
笈多时期的佛像比之犍陀罗佛像的印欧混血更加印度本土化,有以下几个特征:印度式螺发、希腊鼻、印度脸、更低垂的眼帘、颈部三折、整体更加肉感、光环中有莲花等花团锦簇(体现佛祖的冥想世界)。笈多式佛像可分为“湿身佛像”和“裸体佛像”,前者衣裳如出水般透明,后者衣裳薄如蝉翼。
4、西方极乐世界的其他人物
1)药叉和药叉女
药叉和药叉女是印度民间信仰中的自然之神和生殖之神,源于印度的生殖崇拜。在佛经中,他们是佛祖的护法之一。孔武有力的药叉后演变成佛教护法金刚、天王。药叉女是印度女性的典范,“三屈式”。
2)菩萨
菩萨是佛教中重要的神,男子,为普渡众生而推迟自己进入涅槃的时间,更富有人情味。
3)飞天
四、佛塔东传
1、阁楼式佛塔
东汉初期白马寺的建造,标志着中国佛教之始,而立塔是传教最为重要的一步。自早期窣堵波之后,印度佛塔朝着加高台基和增加相轮的趋势发展。西汉汉武帝时期崇尚求仙,“仙人号楼居”导致中国有大量的阁楼,即重楼。传入中国以后,在东汉至三国时期,佛塔完成了中国本土化,即将佛塔与阁楼相结合,产生了阁楼式佛塔,保留了顶部的宝匣和相轮,称为“塔刹”。阁楼与佛塔的区别即在于塔刹,“塔不在高,有刹则灵”。
南北朝之前佛塔楼层较低,之后出现七级以上佛塔。北魏永宁寺塔为九级木塔,高约133米,为世界上出现过的最高的木质结构佛塔。另外,永宁寺塔还开创了塔可登顶览胜的先河。
2、密檐式佛塔
与永宁寺同一时期的嵩岳寺塔为砖塔,是现存最古老的佛塔,密檐式。
3、其它
阁楼式和密檐式佛塔为中国最主要的佛塔样式。其它比较著名的有白塔寺(元代出自尼泊尔设计)、金刚宝塔等。
五、云冈石窟
中国石窟传入稍晚于佛塔,大约于东汉末年,沿着丝绸之路河西走廊传入中原。
云冈石窟建于北魏(386AD-534AD)时期。北魏佛教依赖于王权,将开国帝王比作如来降世。云冈石窟是在佛教被北魏政权打压后复法的背景下兴建的,是皇家祈福的国家工程。云冈石窟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昙曜五窟”,用五尊大佛象征开国五帝;第二期为迁都洛阳之前,是石窟汉化的关键时期;第三期为迁都之后。
1、大佛窟
云冈一期全是大佛窟,昙曜五窟是开国五帝的个人纪念碑,形象高大宏伟。传入中国的大佛有迦毕式样式、笈多湿身佛等,但有几个特征明显与印度佛像不同:素发而非螺发、唇上隐约有胡须、有眼珠。
2、佛殿窟
云冈佛殿为石制的仿木质结构建筑,有前廊、后室、通道等。雕刻仍有印度的异域风情,但也有中国木质结构建筑中常有的雕花、屋檐等设计。云冈二期至三期的佛像更加汉化,不仅尺寸上不如之前宏伟,而且佛像表情由肃穆转向恬静,身材由魁梧转向清秀,衣着由印度装转向汉服。
3、塔庙窟或中心柱窟
塔庙窟是对支提窟的翻译,将中心窣堵波翻译成中心柱,又汉化成阁楼塔,只是塔顶无刹,与顶相连寓意宇宙之轴。
六、敦煌绘壁
敦煌石窟始凿于东晋时期,有僧人修禅与祈福两方面的作用,后世俗化僧房较少保留。
1、塔庙窟
莫高窟的塔庙窟均为中心方柱窟,没有将中心柱雕成塔的做法,凿于北魏中后期。在中心方柱中间安置大佛龛,与殿前人字坡相结合是进一步汉化的表现,为方便聚集礼佛和绕柱参拜。
隋大兴敦煌,隋晚期中心方柱退居次要地位,而北朝时期佛塔占有参拜的主导地位。中心塔柱由礼拜塔变为礼拜塔上佛龛中的佛像,再到直接礼拜佛像的过程,到唐中期之后,中心塔柱基本绝迹,在壁前立塑像群。
2、佛殿窟
莫高窟的佛殿窟大多为覆斗顶窟,与云冈石窟的平顶不同。中间平顶为斗四天花,象征窗户,让原本昏暗的石窟仿佛出现光亮;四周斜坡模仿“帐”的设计,用流苏等图案装饰,让原本坚硬的石头产生柔软的视觉效果。唐以前的覆斗顶窟采用三壁三龛;之后只保留正壁一大龛,左右两墙画上“经变画”,即根据佛经及想象绘成的画,随即产生了辉煌的敦煌壁画。
3、大佛窟
北朝盛行大佛,尤其是北魏时期的“昙曜五窟”,之后佛像逐渐汉化,一改庄严宏伟的态势,偏向清秀之风。然而,隋唐造大佛的风气更盛、尺寸更大,例如四川的乐山大佛。
莫高窟最为著名的大佛窟为北大像窟与南大像窟,先后开凿于武则天时期(695AD)及开元时期(721AD)。前者稍大于后者,两者气势恢宏,高大巍峨。
敦煌石窟经历了由礼佛到参拜,由塔到佛,由建筑到壁画的过程,最终到唐代繁盛时期,已完成了以佛和绘画为主要基调的成就。
4、菩萨
敦煌早期菩萨如印度原型多为男子,而隋唐后的菩萨越加女性化。在一铺佛像纵队(一佛二弟子二协侍菩萨二天王金刚)中更显柔美。尤其是敦煌石质坚硬,多采用木骨泥塑法。变换多端的木头形状让菩萨的体态更多变、表情更含情。
5、飞天
1)印度飞天
主要在佛像背光上方两侧成对出现,表现的是佛说法时天人散花的景象。印度飞天体态丰腴,经常半裸或者全裸出现,展现男欢女爱的场景。
2)中亚、西域飞天
飞天的面貌更趋西域化,印度化特征减少。仍然成对出现,经常含情脉脉,眉目传情。
3)云冈石窟飞天
早期飞天印度化特征教明显,后汉化。首先,飞天不再是成对出现在佛祖身边,可单独或者成群出现,尤其是出现了飞天绕莲的题材。其次,飞天穿上了汉服,不在裸露,也不体现男女之情的色彩。最后,飞天体态清秀、乘风飞舞。
3)龙门石窟飞天
龙门飞天进一步汉化,体态更加清瘦秀丽,吴带当风之感油然而生。这时的飞天已与中国的天仙融为一体。
4)敦煌石窟飞天
早期飞天仍然有印度特点,较为粗犷、沉重。隋朝飞天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体现飞天的轻盈与乘风之感。轻盈是用浮雕或者线描壁画来规避飞天的体积感,乘风是用衣带等服装来体现飘逸的速度感。隋朝飞天的速度感把飞天壁画推向了新的高度。唐朝飞天则不讲究速度,而进一步展现飞天悠然自得、翩然起舞之感。
由于印度对生殖以及情欲的崇拜,印度的佛教体现的是一种“色即是空”的哲学理念。佛祖向世人传达面对尘世中无尽的爱欲仍然无动于衷的悲天悯人的之感。而中国传统思想“乐而不淫”,因此在佛教汉化过程中把艳情味去掉,更加着重于极乐世界的华美。佛祖向世人传达的是人们对佛祖净土的向往。
《塔窟东来》读后感(五):想逛明白那些石窟和佛塔啥的,可以从这本书开始
这本书只是个开始
你可以按照作者的参考文献目录
一直读下去……
王南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青年教师,他与读库合作出版的“建筑史诗”系列让人爱不释手。
书本不厚,但他能用巧妙的串引、明快的例证和洗练的语言把某一类型的建筑特征和变迁史说得清晰明了,让人心服口服。我读到那些曾去过的地方,更涌起相见恨晚之感。
《塔窟东来》是我读过的这系列第四本。前三本讲西方建筑,这本则讲印度佛教建筑千百年来被中国引进、翻译和再造的过程。全书框架异常清晰,读之忘俗,宛如隔空听讲,一堂堂课下来,只感心内无比喜悦充实——可见阅读可以超越时空限制,让人一次次幸运遇上“明师”。
01.佛塔与石窟寺:窣堵波、支提和毗诃罗
作者首先从印度现存的、可以考证的两种建筑,佛塔与石窟寺入手,讲述其缘起与遗存,也从时间角度梳理其风格承袭与流变。
窣堵波(梵文stupa,玄奘音译)即佛塔,其外形是一个倒扣的半球形(覆钵)、一个立方体(宝匣)和三重伞盖(相轮)的结合。内部实心,封藏着佛舍利容器。外部砌筑砖石,信徒可顺时针绕塔礼佛。
具有代表性的窣堵波之一有桑奇大塔(圆形基座),这是一个不断被修建的建筑群,纵跨阿育王时代、巽伽王朝和早期安达罗王朝,也即中国的战国时期至东汉时期;
桑奇大塔代表之二是犍陀罗窣堵波(方形基座),受古希腊和波斯的影响,具有混血特点,能见出科林斯壁柱和希腊神庙样式的运用,典型建筑是位于塔克西拉的西尔卡普城址中的双头鹰窣堵波基座遗址。犍陀罗窣堵波出现于贵霜王朝(公元1-3世纪,由曾游牧于河西走廊的大月氏贵霜翕侯部落建立),也即中国的东汉、三国和西晋时期。正在这个时期,佛塔样式开始流入中国,犍陀罗窣堵波也成为中国佛塔的基本原型。
西尔卡普城址中的双头鹰窣堵波基座遗址支提(chaitya)是佛教礼拜场所,包括窣堵波、讲堂或佛殿;毗诃罗(vihara)是僧人居住的僧房、精舍或寺院。岁月流逝,这两者的木结构在印度已不存在,现在可考的只有仿木结构的岩凿石窟,相应地分为支提窟和毗诃罗窟两大类。
支提窟也被称为“塔庙窟”,类似于古罗马的多功能集会大厅巴西利卡或基督教早期教堂结构,王南叫它“负的巴西利卡”,因为建筑主体不是在平地上做“加法”修建,而是在岩石内做“减法”凿刻而成。支提窟前端是矩形,尽头是半圆形,靠后的中央区立着一座小型窣堵波,代表建筑有位于印度西部的巴贾石窟和卡尔利石窟。
巴贾石窟卡尔利石窟西方的巴西利卡建筑结构毗诃罗窟是印度僧人修行的地方,早期崇尚苦修,因而十分简朴。通常是方形平面,中央大厅,周围设方形小室。后期逐渐变得装饰华丽,其代表有阿旃陀石窟,已初具佛殿功能。
阿旃陀石窟的后壁中央开龛设像,两侧列柱雕刻华美。02.造像艺术
佛塔与石窟是印度佛教的容器,其内容则是各色精美的造像艺术——印度造像艺术对中国佛教具有深远影响,其中以犍陀罗佛像和笈多式佛像为最。
犍陀罗佛像和佛塔一样,从贵霜王朝开始盛行。这个阶段是古印度繁荣时期,作为丝绸之路的中间站,对外融合度高,与地中海地区已有往来,其佛像雕刻融入了古希腊罗马的技法。书中提到印度对这种雕刻技法进行了本土化翻译,分为精美版(犍陀罗式)和拙朴版(如迦毕试样式)。好玩的是,中国在引入印度造像艺术时,再次对其进行翻译,也创建出自己的特色。
犍陀罗佛迦毕试样式立像,现藏于巴基斯坦白沙瓦博物馆。笈多佛像兴盛于笈多王朝,也即中国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这是印度古典黄金时代,与中国的交流最多,从而对中国石窟与佛像制造产生重要影响。
笈多佛像分为马图拉样式(湿衣佛像)和萨尔纳特样式(裸体佛像),区别在于雕刻手法。前者衣服犹如古印度人洗浴出水,衣服贴身;后者衣服薄如蝉翼似有似无,和古印度人裸体习俗有关。中国造像主要吸取了马图拉样式的特点,后来渐渐本土化,和造像所处的具体时代融合,体现出当时人民生活与服装的特征。
笈多时期马图拉样式佛立像,衣纹薄如蝉翼,似有似无。现藏于印度北方邦马图拉政府博物馆。笈多时期萨尔纳特样式佛立像,身体不加修饰与遮掩。现藏于印度北方邦萨尔纳特考古博物馆。03.塔窟如何向东来?
学习中国历史,我们知道,从西汉起,张骞使西域,通过河西走廊,打通了丝绸之路,带来西域各国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其中,“天竺”就是中国对古印度的称谓。东汉汉明帝派使者前去天竺求佛法,使者走到了今天的阿富汗,引带居于此地的天竺僧人入朝;晋朝时高僧法显漫漫西行,终于到达天竺国,他游历多年,饱修佛学,至暮年回国传道;唐朝时玄奘偷渡西行,历经劫难到达天竺取经,写下《大唐西域记》,带回若干佛经。为弘扬佛法,他不仅四处讲经,还率众多弟子将经书翻译成汉语——后来他成为《西游记》里最帅的唐僧,也是我们童年时代的“国民男神”。
玄奘负笈图古中国和古印度之间的交流,史料累牍,包含经济、文化、宗教、建筑、音乐、雕刻艺术等等方面。其中,佛教的实物载体建筑、雕刻、绘画等最易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接受。从造价的角度看,也只有通过统治阶层的命令,并以举国之力才可能实现这些宏大的建造。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佛塔、佛寺或佛像,少不了皇家身影。他们或敕造,或捐助,或供养,更或与陵墓修建相结合,以求千秋身后。纵观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路径,其兴衰也与当时统治者对待宗教的态度息息相关。
下图为明内府绘制《丝路山水地图》,其中也少不了佛塔身影。建议横屏观看↓↓↓
04.浮图千尺,汉地的佛教建筑特色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书中引用此句说明当时佛寺盛况。小时候背这首诗,我脑海里会浮现出雨中纷飞,寺庙中烟雾缭绕的景象,实在形象。南北朝是我国历来佛教最兴盛的时期,国际化与全国化的最大表现可能就是建造佛教场所。当时大兴土木,涌现出无数寺庙,雕出数不清的佛像,到唐代依然保存完好,才入了唐代诗人杜牧的诗行。
在写到这“四百八十寺”时,杜牧并举了的“楼台”,折射出中国对印度佛寺的本土化过程。楼阁,是中国本土重要的建筑形式,兴起于西汉,与中国古代求仙思想有关。印度的窣堵波与中国楼阁相结合,创新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的新样式,也就是楼阁式佛塔,也称为“塔刹”。
多少楼台烟雨中梁思成先生对窣堵波与中国楼阁的结合做了一张图文并茂的思维导图,王南在本书中也有引用,非常直观。楼阁式佛塔是古代中国人对印度窣堵波最精彩的建筑翻译,史书记载是在汉献帝初年时期,由丹阳人笮融首创。现在散落在中国各地的佛寺、石窟中都能看出这种创见与和谐,可以平行对比印度佛寺的,便是大同云冈石窟,作者也专辟一章进行了讲解。
《历代佛塔型类演变图》(梁思成绘制)楼阁式佛塔中最壮观的,是史书记载被大火毁于一旦的永宁寺塔。王南提到,根据郦道元《水经注》的记载,这座九层佛塔的塔基尺寸在35.7-41.3米之间(吻合考古发现的38.2米),由此推论其塔高为133.7米,约为中国现存最高木塔应县木塔(塔高67.3米)的两倍。
洛阳永宁寺塔复原图山西应县木塔剖面图(梁思成绘制)中国也有一种说不清楚来历的现存砖塔,代表建筑是河南登封嵩岳寺塔。其特别之处在于外形像春笋或玉米,造型属于单层密檐式——它不像楼阁式佛塔那样,每层具有完整的立柱、横梁、斗拱、屋檐,修建时层层收进,直到攒尖屋顶,而是只有一层塔身具有完整的上述结构,上面各层的屋檐密密相叠,只象征性地留出一小段“塔身”。作者善于用音乐譬喻建筑,他描述楼阁式佛塔是均匀节拍,而密檐式佛塔是一个长拍加一串短拍子,很是形象啊。
河南嵩岳寺密檐式佛塔楼阁式佛塔和密檐式佛塔之外,中国的佛塔样式还有喇嘛塔和金刚座宝塔。
喇嘛塔是元代时由尼泊尔大匠阿尼哥传入中国,北京著名地标白塔寺(妙应寺)是其中佼佼者,寺内也有阿尼哥的雕塑和相关史料展厅,还有佛像展厅,有兴趣不妨去观摩一番。
北京妙应寺白塔金刚座宝塔的典型代表现存于北京真觉寺。位于白石桥附近,规模不大,但极具代表性,王南的学术研究突破正是从这里开始的——通过这座塔的启发,他发现了中国古代建筑设计的重要“密码”,方圆做图比例的广泛应用(发表于《建筑史》2017年第二期,知网可购买下载)。
北京真觉寺的金刚宝座塔05.敦煌:塔窟、佛像、绘壁与极乐世界
讲石窟寺,本书最重要的举证是云冈石窟。而讲佛像,以及由之简化和演变而成的绘壁,则离不开敦煌。
读《敦煌绘壁》一章,你可感受到作者饱含的热情,敦煌之奇、之珍、之琳琅,哪怕很多珍宝早被侵略者洗掠至海外,现存的洞窟、佛像和绘壁依然令人称奇,怎么说也说不完。
敦煌莫高窟石窟密集,也被称为“千佛洞”敦煌规模庞大,也具有石窟寺的建筑特征,更重要的特征是其大规模的佛像与绘壁留存。由于干燥的外部条件,千年来,古代工匠采用自然颜料、以高超工艺造型和绘制的佛像、绘壁至今栩栩如生。
书中提到,敦煌石窟因跨越朝代建造,因而直观地体现出中国对印度佛教吸收的运动轨迹。从早期以僧人禅修为主功能的简朴石窟,到后期世俗造像祈福兴起而造就的佛殿窟,其中国化风格越来越明显,印度风格越来越淡去。
敦煌石窟群中的塔庙窟从北魏中后期开始,塔庙窟流行。脱胎于窣堵波的中心塔柱逐渐和中国木结构风格结合,在塔庙窟中的塔柱前加建前廊或前堂,成为带双坡顶或人字坡顶的空间,天花上则结合木质斗拱与彩绘假椽,形成一种全新样式。塔柱也有汉化特点:结合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阙”,形成“阙形龛”,内置佛像,这种格局和形制能满足当时信徒围绕中心柱礼佛的需求。
倒塔状中心柱窟短暂的隋朝造窟事业兴盛,涌现出类型丰富的石窟,其中造型最新颖的要数倒塔状中心塔柱。隋朝晚期出现中心塔方柱窟,其柱子向进深内退为次要位置,相应地佛龛空间变大,这种窟型被视为向佛殿窟过渡的类型。它实现了空间局限的突破,也让靠窟底背壁塑造高大佛像成为可能。
演变至佛殿窟阶段,佛像塑在窟底直接在窟底塑造佛像,也是印度佛教建筑中国化的重要表现:从礼拜佛塔变成礼拜佛塔佛龛中的佛像,再到直接礼拜佛像。到了唐代,敦煌石窟中,佛殿窟完全取代了中心塔窟,也意味着窣堵波痕迹的消失。
敦煌佛殿窟多为覆斗顶,中央为斗四天花敦煌的佛殿窟大多是覆斗顶,像一个倒扣的升斗。当时对覆斗顶窟的艺术处理是“斗四天花”,就是大小不等的正方形,相互呈45°角环环相套的造型,这种西域特色的图案在敦煌石窟中完成了与中国传统家具“帐”的结合,被绘上华盖、垂幔和流苏,坚硬的石壁显得柔软轻盈,宛若天宫楼阁。
莫高窟102窟:观无量寿经变唐代以后,佛殿窟的墙壁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拘泥于三面墙壁均设佛龛,而只保留底壁的佛像,左右两壁逐渐成为绘壁,以丰富的颜色与笔触绘制经壁画,描绘西方极乐世界,成为惊艳后世的敦煌壁画群。
除了塔庙窟、佛殿窟,敦煌石窟中还有大佛窟和涅槃窟。前面提到,佛像成为被膜拜的对象正是佛教本土化的体现之一,而大佛的出现则和隋唐盛世的经济能力息息相关。
敦煌大佛窟中著名的北大像即使到了今天,中华大地上大佛遗迹也随处可见。著名的有乐山大佛、云岗大佛、龙门石窟、荣县大佛、麦积山大佛等等。敦煌莫高窟的北大像窟开凿于唐代武则天时期,据说反映了武则天本人的面貌,对于这种传说,王南在书中总结得特别精彩——“不在于是否像武则天,而在于其宏伟的尺度、精妙的雕凿所反映出的庄严沉静、岿然天地之间的气度。”
敦煌涅槃窟涅槃窟内凿塑卧佛,绕卧佛展列巨型群塑,周壁绘制巨型壁画,显示着盛唐的磅礴气度。无论是雕塑,还是壁画中的人物,表情上都呈现出对佛祖涅槃的悲伤,作者认为这种情绪的表现形式有点像西方“哀悼基督”的题材。仔细对比,的确想像,或许因为人类力量与情感都是相通的吧,当艺术与宗教结合时,这种共通性也是一种佐证,是历史平行发展的默契呼应。
在写到敦煌飞天时,作者下笔更是恣意畅快,大概因为飞天这种形式本身具有轻盈与快乐,美妙与诗性的原因。唐朝的丰盛成就了飞天艺术的高妙,敦煌壁画中,飞天形象是最深入人心的艺术表现。直到今天,也给各类艺术领域带来无数灵感,从绘画,到音乐,到舞蹈,到时装,无所不及。
飞天的印度原型药叉和药叉女阿富汗巴米扬石窟内原有飞天,其形象肉感。遗憾的是2001年,这些壁画和巴米扬大佛一起被塔利班炸毁。新疆克孜尔石窟内飞天,有着丰满的形象。飞天的印度原型是药叉和药叉女,梵语为“密荼那”(mithuna),在印度意涵更重于欢爱亲昵的色情男女,突出人间情欲;传播至中亚和古代西域地区的飞天表达欲望的程度比印度更甚。敦煌石窟中的主要飞天形象,用流行话说,可谓“性冷淡”版,少了艳情,多了仙气。
敦煌石窟内北凉时期的飞天,男女性征明显,欢愉之情跃然壁上。北魏时期的飞天,依然能看出肉欲感。隋代时期的飞天,身形愈加轻盈,飞翔之姿动态分明。初唐时期,凭栏眺望的伎乐天,神色悠然自得。盛唐时期,敦煌飞天显得翩翩自在,体量感降至最低,达到乘风之境。从肉欲到冷淡的演变,证明敦煌壁画创作也是一个动态过程——早期受西域影响,肉欲感比较明显,后期则彻底汉化,融汇成中原风格的飘飘若仙。通过画中弹奏乐器的动作与动态身姿,我们能感受到速度与音乐感,加上流云、飘带、裙摆等等飘逸因素的烘托,让飞天们更加翩然自在,达到“乘风”之境,真正在轻舞飞扬。
这种飞扬,也是中国佛教区别于印度佛教的重要因素。
印度文化有生殖崇拜与男根崇拜的传统,在佛像及相关艺术造型中更重爱欲,表艳情,通过人间生动与佛陀悲悯形成强烈对比,是一种极致渲染手法。黑塞曾根据佛陀的传说,在小说《悉达多》中描写悉达多王子迷失与得道的过程,也曾突出其声色犬马、爱欲横流阶段,正是经历过这种“迷失”的极致,才带来后来的“解脱”、苦修与忘我。
中国儒家文化倡导”讲礼仪,知廉耻“,道家文化则崇尚素简,向往修仙得道,儒释道相互融合影响,我猜还得结合农耕文化与宗法生活让人习得的耻感。所以我们为佛陀、菩萨和飞天们穿上衣服,削减其体量,营造脱离人间俗常的幻像。
本质上,印度佛教传达面对人间放纵时,佛陀的克制,是舍弃与解脱之美;而中国佛教,描绘佛国净土,彼岸极乐,是向往与升华之美。
这就是我推荐这本书的原因——能够引人深思并理解至此。庆幸我们的时代可以让王南这样的象牙塔内学者,突破学术论文的域场,成为面向更广阔的学科科普达人。正是他们用严谨的态度、轻松的方式写就好书,引领大众读者感动于建筑,爱上建筑,以及建筑所代表的人类文明精髓。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