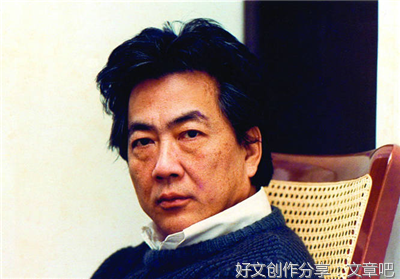《我的弟弟康雄》读后感100字
《我的弟弟康雄》是一本由陳映真著作,洪範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NT$ 250,页数:2001-10-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的弟弟康雄》精选点评:
●〈我的弟弟康雄〉、〈加略人猶大的故事〉、〈將軍族〉三篇可以說是「前革命時期的後革命心境」寫照。
●第一册小说集,年轻时的作品,但他估计是唯一一位能把五四之生命力——以一种带着新鲜清纯的视线的可贵形式,写国家民族最复杂深沉的感性——化在小说中的作家。比郁达夫还多出一点那说不清道不明的幽微,直追鲁迅。
●開始於 Jun 23, 2011 結束於 Jun 30, 2011
●《将军族》优秀
●TAT对不起 一篇都不喜欢要我怎么给你回信 再见吧QD
●都是些卑微的人的悲哀的故事,悲悯温柔的笔触一如陈映真。
●永善 映真....父母善良的愿望
●讀的第一本陳映真
●想写一篇评论,乱糟糟没写出来,很懊恼
《我的弟弟康雄》读后感(一):我的弟弟康雄
《我的弟弟康雄》写一个富于理想与爱心的青年,在乌托邦里幻想着建立许多贫民窟、医院和孤儿院,但他的理想却在个人道德的清教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激烈矛盾中破灭了,最后他选择了自杀。整个故事以重归于世俗生活的“姐姐”的口吻讲出,使小说整体蒙上了悲哀、忏悔、反思的色调,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最近几年总是在某些书籍里或由自己喜欢的学者口中不停提到陈映真的《我的弟弟康雄》,昨天终于一口气看完,解我心愿。不到14页的小短篇值得反复看。
准备看他的《将军族》。
《我的弟弟康雄》读后感(二):欲—情—爱
在1961~1964年的几篇小说中,多次出现了外省男子与本省女子的角色,人物的关系背后事实上也是两个不同社会、两段历史的种种纠葛。陈映真在《后街》中说,1962年他到军中服役,军队里下层外省老士官传奇和悲悯的命运震动了他的情感,让他深入体会了“内战和民族分裂的历史对于大陆农民出身的老士官们残酷的拨弄”。这个时间点让我注意到,发表于1961的《猫他们的祖母》和发表于1963、1964年的《文书》和《将军族》,对外省男性形象的刻画确有不同,外省男子与本省女子之间的关系也有区别。一年的军中经历和对对岸民众生命经验的更深了解,或许让陈映真的情感和思考都产生了变化。
在《猫它们的祖母》中,这名年轻的外省少尉,少时投军,孤苦一身,又没有学历,常被当地人看不起,然而陈映真也刻画了他的精明、狡诈、自私与残忍。这不是一个可爱的、令人同情的人物形象,战争经历给予他的是一种特有的冷酷,或许因为见证过那些死亡和绝望,黑暗的力量便在心中生根。现有的生活看似平和安定,“官儿也升了,老婆也有了,还赚了间房子呢”,但过去一直流淌在他的血液中,扰动着他的心绪,交织进他当下和未来的生活。在小说中看不到他对娟子的爱意,他对娟子的忧愁感到心烦,又说她“完完全全地在他的掌握之中了”。他的欲望时常来自于重新忆起炮火中无常的恐惧,必须通过女性的身体、通过激烈的交合才能重新把握住生命在那一时刻的实在,而在每一夜强烈的、刻意的性的表现中他所感受到的是征服和残杀的快乐(是与死亡联接在一起的欲望,下沉的、黑暗的,而不是情爱,上升的、光明的)。
联系到后面几篇小说,那些退伍的外省老兵多爱寻欢渔色(包括遇到珠美和小瘦丫头之前的安某和三角脸),我想可能多出于这样的心理。童年的创伤经验、战争经历,来台之后受到的轻视与排斥,或事业的落魄,都影响了他们对待女性和性的态度,这或许是他们在无常、失意的生活中所能找到的唯一安慰,然而他们的苦难却还难以生长出那种柔软的爱人的力量,所以常常只能唤起他们的战争经验,比如表现为如同征服、残杀的性心理。
在这一篇中,娟子的命运也是充满坎坷苦难的,她是被母亲遗弃的私生女,有一个瘐死外岛的政治犯舅舅,他为丈夫所吸引也并非因为爱,而是一种混合着恐惧的神秘的性吸引(“古巴比伦淫神的少女牺牲”,“被投落于那火烧的洞窟”)。她被欲望攫住,与外省男子结合,而饱受坊间舆论的恶评。我隐约觉得这是否意味着当时台湾社会对大陆的态度,当官方和社会舆论普遍将大陆描述为恐怖的、恶魔般、水深火热的,但是它对另一些人却产生了神秘的吸引乃至于赴汤蹈火。但将这种吸引以性欲现身,又似乎有些说不通。
在《文书》中,陈映真塑造了一个更为复杂深厚的外省男子形象,安某。他的几段生命经验铺展出来的却是两岸极为宏大的历史叙事:军阀混战的荒谬和不义,乡土中国的蒙昧残忍,抗日战争,以及到台湾之后经历的白色恐怖。我想,安某的经验呈现的正是陈映真所说的“内战和民族分裂的历史对于大陆农民出身的老士官们残酷的拨弄”。安某与妻子的相遇唤起他的怜惜与爱情,使他似乎终于可以步入平和、幸福的世俗生活,但在这一刻他却发现可能正是自己枪杀了他所爱的妻子的哥哥。被枪杀的少年纯洁又平和,但作为宪兵队员的执行者他又岂是真正凶狠残忍的杀人犯呢?施害者毋宁也是历史的受害者。荒谬、残酷的历史以鼠色的猫的面目一次又一次出来扰乱着他的生活——于是他终于精神失常了。但在这样吊诡错综残酷的历史中,其实又有谁能出来轻易指证谁是罪人呢?(所以我想台湾当下很多对二二八的讨论毋宁只是肤浅的喧闹罢)
《将军族》的情节和形式都更为简单,但是却更有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三角脸和小瘦丫头,一个老迈一个青春,一个来自东北,一个来自台东,一个由于战争背井离乡来到台湾,从此与家人遥遥相隔,一个受贫苦的生活所迫被家人卖到花莲,受尽屈辱。纵然他们的社会背景迥异,却在各自不同却又相似的苦难经历中产生了互相的同情和悲悯。“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正是在一个极为静谧美好的夜晚,在月亮底下,两个没有了家的人产生了经验和心灵的相通。这种感情绝非源自欲望,也超越了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一种广泛的、超越性的人道之爱,而这种人道之爱仿佛能跨过历史和现实生活的苦难,所以他们的赴死是充满了尊严的,“就像两位大将军”;死亡也并不悲凄,而更是一种最后的平和与完满吧。
我想或许正是62年的军中经历让他对外省老兵有了更多同情的理解,所以《猫它们的祖母》中的少尉与《文书》和《将军族》中的外省人呈现出不同的形象,也承载着更多历史的复杂性。而在这三篇小说中,男女之间由欲到情到爱的关系,也有一种递进或者说上升,仿佛可以听到陈映真面对历史和历史中的人物更深的喟叹,或许同时也寄托了他的一种希冀——以人道之爱是否最终能让历史和社会的伤痛得以化解呢?
《我的弟弟康雄》读后感(三):细读|陈映真《我的弟弟康雄》的主角是谁?
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作者:嘻嘻wency(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638844286/
导读:陈映真的小说值得细细品味,我的笔写不出其美妙的百分之一。但是做一个尝试也是略表对其的心意。 公众号的次篇就是《我的弟弟康雄》这篇小说的原文,没看过小说的可以去看看~还是那句,期待更多的交流。
虽然知道没有绝对纯洁的读者,但依旧想做一个尽量“纯”文本内部的思考,所以并没有去查陈映真的太多背景知识,试图就文本本身谈文本。
1.叙述了什么?
我们拿到一个文学作品时,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问题便是,这个作品讲了什么?
但其实要回答“叙述了什么?”这个问题是比较困难的。一旦作品形成,它就脱离了素材(故事),而成了有叙述策略的情节。也许在叙述策略的安排下,我们会忽略了更重要的故事。比如说《简·爱》,罗切斯特的妻子被自然而然地忽略了。但是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巨著《阁楼上的疯女人》重读了这部作品,阅读出文本中那个疯女人有不可忽略的意义。
回到《我的弟弟康雄》这个小说上来,它所叙述的故事也因此微妙了起来。百度上的简介理所当然地把弟弟康雄当成了主角,把它的故事作为核心故事来理解,因此《我的弟弟康雄》就是叙述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青年如何由于其肤浅的人道主义精神而走向幻灭和死亡的故事。这种阐释方式自然也没有错,在小说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对应的理据去证明:
在我看来,这种阐释方式没有错,但是又是有些可惜的,它忽略了一些更有意思的东西。
因为它忽略了叙述者“我”的存在。小说至少有两个主要的叙述时空体:a.“我”的弟弟康雄的成长经历b.“我”的心路历程。除此外也掺和着“我”的父亲、画家、“我”的丈夫等次级故事。当我们把叙述者“我”也纳入思考研究的范围中来时,小说的内涵便更加复杂了。
叙述者“我”作为弟弟康雄故事的旁观者,却深深切入了故事内部去。“我”并没有选择直接转述弟弟康雄的日记,而是不断地做自己的分析和概括,甚至于在描述弟弟的时候还不时加入自己的故事。
即如果我们换一个观察的对象,把目光投向叙述者“我”身上,会发现更有趣的故事。“我”是一个有着几分秀丽姿色的穷人家的女儿。在处女时代受弟弟影响,对理想主义产生了迷恋,对有钱人产生厌恶。但是这种迷恋在遭遇了弟弟的自杀后破灭,在不久我便嫁给了有钱人。
但是嫁给有钱人并不是“我”的妥协,“我”更将嫁给有钱人视为最后一次反叛,视为一种殉道行为。为什么?“我”才是那个看破了宗教和空想社会主义两重虚伪的面具的人。这次行动是双重的背叛,双重的否定。
弟弟康雄仿佛是父亲的复制,在信奉空想社会主义而不成后转向宗教,在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个意识薄弱,行动力欠缺的无能儿后自杀。而父亲更是撕破了他纯粹理想主义的面具,他说到“人应该尽力摆脱贫苦这一恶鬼,一如人应努力摆脱犯罪一样。”“我”不无反讽地说道,“他毕生凭着奋勉和学识都没有摆脱的贫苦,终于在他的第二代只借着几分秀丽的姿色就得到了。”在这里还有自欺欺人的隐瞒——“对方是有名望的虔诚的宗教家庭。”父亲借宗教的面具遮掩了其对财富的渴望。
但是“我”的内心依旧有不甘心之处,“我”不停的质问自己,“富裕”果真让我丧失了一些细致的人生了吗?贫苦确实让“我”变得龌龊、卑鄙了吗?对于“那些少女时代从未弄明白的社会思想和现代艺术”,对于“那个挂在十字架的男体”,“我”始终不能抛弃对其的恐惧和向往。
作品呈现出“我”这般的困惑,将其与“我”对弟弟的回忆和描述糅合在一起,隐藏了“我”的性格。
本文认为,“我”对康雄的回忆和阐释应该被理解为“我”的另一面,作为“我”内心焦灼不安,无法自洽的逻辑困境的表征。“我”才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
再回到开头那句,“当我是一个少女的时候,我写日记,也写信。”是否觉得有些似曾相识?“我”和弟弟走过同样的路,内心彷徨空虚的姐姐借重读弟弟的日记来寻求身份认同。叙述者在两重叙事时空体间的徘徊,显现出内心的一种徘徊逃避,希望借“我的弟弟康雄”的故事框架来逃避自己现如今的精神困境。
·2.结尾的悖论
结尾时,姐姐利用已有的财富权势帮助父亲实现了在大学里教古典哲学的梦想,也试图给弟弟修一个豪华的墓园,从而终于完成了自我价值观和处事逻辑的圆满,也就消解了自己内心的困惑。
当然当我对文本做了这样的阐释后,一个更深的问题自然是,作者为何这么做?隐含作者究竟表达了什么?叙述者对文本的叙述也是由作者完成的,它反映的是作者的所思所想。
这个问题或许需要结合陈映真更多的资料,也需要
当然,这部小说可以挖出更多更有意思的含义,是一部阐释空间很大的作品。不同知识背景和问题关怀的读者进入,会碰撞出不同的火花。期待您的思考。
《我的弟弟康雄》读后感(四):除了自杀,没有出路
【陈映真小说中的小知识分子,便是怀着这种无救赎的、自我破灭的惨苦的悲哀,逼视着新的历史时期的黎明。在一个历史底转型期,市镇小知识分子的唯一救赎之道,便是在介入的实践行程中,艰苦地做自我的革新,同他们无限依恋的旧世界作毅然的决绝,从而投入一个更新的时代。】
【他从梦想中的遍地红旗和现实中的恐惧和绝望间巨大的矛盾,塑造了一些总是怀抱着暧昧的理想,却终至纷纷挫伤自戕而至崩萎的人物,避开了他自己最深的内在严重的绝望和自毁。而于是他变得喜悦开朗了。】
陈映真的写作似乎都能看作是对自我的探寻、反省,上述引文是一对一的自我审视,而在小说中,这种内倾性格更紧张地旋转起来,不仅钻入懦弱者怯于直面的人心的深处,也力图牵连出整个时代的脉络。
——他必是怯懦、苦闷的,之后勇敢,于是知道那是什么,也知道如何走过。
陈映真对自身的反省使得阅读陈映真也成为了一个探寻自我的过程。小知识分子的这种探寻在孤身一人时常常难以彻底(按陈映真对radical一词的解释)进行,他对这类人的软弱、妥协等种种不彻底性的再现令人战栗。
《乡村的教师》中,从战场不可思议归来的吴锦翔获得小学教师职位后重燃了“小知识分子的热情”。然而终于他感到了悲哀:“他的知识变成了一种艺术,他的思索变成了一种美学,他的社会主义变成了文学,而他的爱国情热,却只不过是一种家族的、(中国式的!)血缘的感情罢了。”“他的懒、他的对于母亲的依赖、他的空想的性格、改革的热情,对于他只不过是他的梦中的英雄主义的一部分罢了。”(p38)这种反省不见得是错误的,但滑向了虚无、颓丧之后使得他“如今只是一个懒惰的有良心的人”(p40)然而破灭的理想仍在挣扎,不断刺痛他,终于自杀。
——自杀,是与旧我的决绝分别,是重生的关口。
——反省,对反省的反省。
《苹果树》中大学生林武治寄身于贫民区,在底层人丑陋、空洞的生活之间,他过着“颓然的懒惰的生活”。“他无须为生活劳力,也便因此得以逃避大部分的狰狞的压力了”。(p142)对于底层人,陈映真既能同情,也能正视他们身上的缺陷与丑恶,并进而指出,有些没有堕入此一境地的人可能只是因为不必承受生活的压力,满足于做一个寄食者。而这种人是无力(也无资格)批判他人的。与疯人相似,他们都逃避/隔绝于真实生活之外。而他一日强奸了邻居的疯女人,性的体验使他感到“许多这一向自己所藉以存在的支架,都像炎阳下的冰雪一般的销蚀着”。“这全个生命的抱拥所揭去的不止是他的童贞,而是整个的过去和历史中的某一条锁链。”(p151)他向她诉说梦境和秘密,“他感受到仿佛一个教徒在告解着自己的秘密的负罪时那种安慰人的感伤”。(p152)反省和忏悔具有安慰的功能,而对于犯下的罪,这于事无补。况且他在行动上如此无力,几乎不能说是反省,只是一种另类角度的辩解和借口。女人死去,林武治被逮捕。他浪漫幻想中的苹果树只是一棵茄冬。
——你在死路歌唱,天使的队伍吹响号角,带你回到纯洁。
《将军族》是无疑是蜕变的标志。没有小知识分子,两个人一个是落魄的外省老兵,一个是逃离被贩卖命运的穷苦女孩。“狂嫖滥赌的单身汉”没料到竟是“真好的人”,将全部家当送给女孩还钱。然而并不能息事,仍然被卖,玷污了身体,弄瞎了左眼。“然而我一点也没有怨恨,我早已决定这一生不论怎样也要活下来再见你一面。还钱是其次,我要告诉你我终于领会了。”领会了什么呢?人性中有真正的善良、纯洁;命运不可逃脱的破败;破败中仍不止息的爱与善良。“此生此世,仿佛有一股力量把我们推向悲惨、羞耻和破败……”这股力量阻止他们在此生结合。“下一辈子罢。那时我们都像婴儿那么干净。”(p201)命运的蛮力下他们仍能选择以将军的姿态死去,保持“滑稽中的威严”。以大笑作必胜的反抗,那股力量可以破坏他们,也可以成就他们的胜利。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我的弟弟康雄》读后感(五):《我的弟弟康雄》:踽踽独行的理想主义者
写在前面:
在开始小说评论之前,我想简单谈谈我的小说批评观。对于小说批评,我主要接受20世纪结构主义的思潮及其文论:关注文本、文学系统自身的价值或规律,将文学作品视为独立自足、自成一体的艺术品。所以在批评的过程中重视文本,“一切从文本出发”,在一定程度上较少地关注作品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地关联。呈现在文本上的,大多是通过阐述文学作品的艺术手法或形式、读者接受等理论,来分析文本内容。虽然此篇小说也具有比较突出的叙事方法和语言特色,但是针对陈映真,针对小说《我的弟弟康雄》,我想主要通过非常传统的“文学的外部研究”(韦勒克),也即 “时代、环境、种族”三要素(丹纳《艺术哲学》)来尝试批评《我的弟弟康雄》,这对我来说,并不是特别熟悉甚至有些困难,但是,对于《我的弟弟康雄》这篇小说,它的作者陈映真及其所处的时代是绕不过去的。
1950-60年代,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压抑成为台湾社会生活的主要特征。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以及1949年的国民党退守台湾等事件,使得情治机关无所不在,且对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进行大肃清,从而带来低气压的社会氛围。对青年人,尤其是那些敏感于时代创痛的青年人来说,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的压抑和文化上的保守是难以忍受的。而青年的陈映真,在其父亲的书架上,有幸阅读并继承了30年代鲁迅等左翼文学作家的作品和思想。正如陈映真关于自己写作母题的阐述:“第一个母题是描写一个人怀抱某种理想,受到挫折,郁郁而终,莫名其妙地死掉,如《我的弟弟康雄》等。这个母题的形成,是由于我二十多岁时,鲁迅等人的作品影响了我的思想,也影响了我一生的命运。”
《我的弟弟康雄》是陈映真于1959年,在上淡江英专(现今的淡江大学)时写作的。二十多岁的青年大学生的生活,总是交织着理想主义的美好与现实世界的惨淡,而《我的弟弟康雄》正是这一矛盾交织的产物。小说主要是通过两条线来穿梭全文,一是康雄姐姐叙说:受康雄弟弟影响,自己由“虚无者”走向“反叛者”的经历;二是通过康雄三本日记中部分文字的穿插来展示:康雄这一“少年虚无者”如何一步步崩溃于他的乌托邦之中的。当然,其间还有对父亲、小画家的文字描述。其间,弥漫着一股永难解开的忧郁情结,和与时代相衬的颓废和无奈的情绪。
通过文本的细致阅读,我们可以看到在理想破灭后,一众的人是走向虚无者的路线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耽于“虚无”的。例如:“我的可怜的父亲,独学而未成名的社会思想者转向宗教已有六年之久”;“我的远远的小画家也因贫困休学,而竟至于卖身给广告社了”。
而“我”,即康雄的姐姐,在面对虚无时,是与“耽于虚无者”是不同的,“我”是遂于行动的,但是这种行动是“反叛”的,而非“反抗”,是“虚无”的反叛者,是烈士。但这种反叛是疯狂的,是具有牺牲精神的,是“宁可玉碎,不为瓦全”的:在弟弟死后的四个月后,用一种近乎“报复”式的反抗方式,嫁给了富足的丈夫,希望为弟弟修建一座豪华的墓园,来使自己安心地“耽溺于膏梁的生活”。
在具体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那个时代众多青年者在理想的破灭中,不得不走向虚无主义,却疲于抗争的时代特征。即使有反抗,也仅仅是反叛式的或自戕式的,而完全找不到理想主义出路的一种所谓的反抗。从中可见,当时所弥漫的颓废与无奈的忧愁情绪深入到每一个青年人的内心里。
陈映真一生所创作的小说中,并未回避政治与社会特征,都以一种深度的思考和批判性来触及并反映不同时代的众多问题。1983年陈映真在临离开爱荷华大学时,写给香港作家潘耀明这样一段话:“为了中国文学写作环境地民主、自由和解放;为了中国文学创作品赏地丰富、提高和纵深;让我们谦卑而坚定地做出我们应作的贡献。”可见,陈映真一辈子都是理想主义者,并且一直践行着这一理想。这条通向理想的路上没有“父亲”,没有“小画家”,没有“我”,当然,也没有“康雄”,但是曾经有他们。而陈映真先生用其实际行动,向我们践行了一个真正踽踽独行的理想主义者形象。
对于《我的弟弟康雄》,三毛曾经说过: “这篇小说看了一百遍以上,每遍读都哭。”什么样的文学是好文学?什么样的小说是好小说?我想,他能借生活中或者社会中的一个虚拟的小人物,来真实地反映一个时代青年人对与政治、对于社会,所潜藏的苦闷与忧愁,让当时的或不同时代的读者,或联系自身,或感同身受,声泪俱下。这便是好文学,这便是好小说。而陈映真先生的小说——《我的弟弟康雄》正是如此,这一小说的创作,不仅凸显了作品与时代,与历史的真实性关系,且涵盖了作家真实的思绪与想法,符合文学的历史标准。
作者· 長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