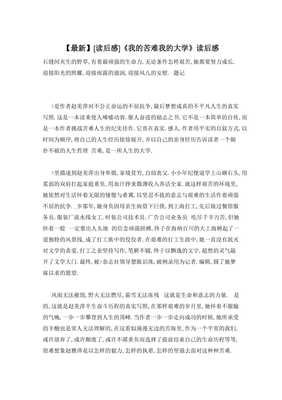局部:我的大学读后感精选
《局部:我的大学》是一本由陈丹青著作,理想国 | 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18.00,页数:27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局部:我的大学》读后感(一):《局部·我的大学》书评
《局部·我的大学》是谢梦茜导演陈丹青讲述的《局部》第二季的文字讲稿,节目是动态影像和音乐的并置,而书将陈丹青的观点明明白白的落实了下来。节目和书的标题偷自高尔基的《我的大学》,高尔基书里的人物小学没读完便四处流浪,日后称俄罗斯的江湖是他的大学,陈丹青说自己没有上过大学,大都会博物馆就是他的大学,至今仍没有毕业。陈丹青一再强调的是他不是在讲述美术史,他只是分享自己的观看经验,这是艺术史很少教给我们的。
普鲁斯特说:“真正的发现之旅并非有了新的景观而是有了新的目光。”以下我引用第一季里提到的“我们永远在谈论艺术的所谓“思想”、“主题”、“手法”,很少追究“观看”,我们总是说:啊,画得多好啊!可是绘画的核心机密不全在画法,画史的每次突破,其实起于观看:莫奈看见了逆光,梵高看见了向日葵,塞尚看见了物体的边缘”陈丹青身为一个画家,他更了解一幅作品如何去引导观众的目光,他不去定义一幅艺术品的地位,他只是将他的他的观看之道娓娓道来。
本雅明从形而上的角度解释了原作和复制品的差异在于灵晕的消散,而陈丹青则从画家的实践中点明了看复制品永远欣赏不到油画中最美的部分---凝结层。所以说有条件的能看原作就去看原作,原作的视觉感受是复制品带不来的。总之,《局部》这档节目和陈丹青的文稿适合反复观看和阅读,尤其是积累了一定的观看经验和知识之后。戈达尔说电影不是站台,它是公交车。同样,伟大的艺术永远召唤着人们的感受,它不会提供一个唯一的解释,作为观赏者,我们能做的就是多看多感受了。
《局部:我的大学》读后感(二):艺术顶顶要紧的,是……
首发于「正在读」微信公众号
撰文 | 梦元
编辑 | 静姝
当我亲身站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内,被几千年以来人类艺术的珍宝所包围,才真实地感受到了那种冲击力。精神上的震撼所带来的晕眩几乎是生理性的,时间、空间消弭了,意识想要挣脱出肉身的束缚,与美融为一体。我几乎同时体会到了优美与崇高,这是艺术给我最直观的感受。
有人认为艺术是有门槛的、需要学习的;有人认为艺术是专属于某个圈层的,是「更低级」的需求满足后才能追求的奢侈。然而,在经历了这样的震撼之后,我相信艺术应该是普遍的、平等的。它诉诸人的感官和直觉,必然有可能在每个人的心底引起共鸣。
诚如陈丹青所说,「艺术顶顶要紧的,不是知识,不是熟练,而是直觉,是本能,是骚动,是崭新的感受力,直白地说,其实,是可贵的无知」。
陈丹青与看理想合作的艺术类视频节目《局部》迄今已播出三季。在这部如诗般精致隽永的片子中,陈丹青从18岁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说到意大利前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对于死亡的描绘;他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就是他的大学,他没有从这里毕业,所以30余年后仍心心念念来此拍片;他前往意大利探寻无名工匠的湿壁画作品,揣摩他们的创作状态……
艺术本属小众领域,《局部》团队投入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实地拍摄、精良制作,去讲述这些「无用」的知识,不知在现在人看来,是不是「吃力不讨好」。片子中,陈丹青站在画作前,倾身细看局部,连连赞叹;而对于《局部》这部作品,我也想连连赞叹——好啊,真好!
将艺术与大众隔开的,是所谓「知识壁垒」。人们容易认为艺术是应该系统学习的,若非熟稔种种流派、历史、画家,断无法走入艺术殿堂。这种观念是外行人的「误解」也好,是业内人自行筑造的「壁垒」也罢,总之,在我看来,都脱离了艺术的本质。
艺术是人所造,我们也是作为人去欣赏。所谓艺术史背景、艺术鉴赏方法,不过是附着其上,辅助我们去感受美、理解人。陈丹青在《局部》中所为我们呈现的,是「博物馆中的艺术」而非「学院里的艺术」。前者是具备公共性、普遍性的,而后者则自限于一个小群体。
《局部》对于艺术的讲述是流动的。它没有框架,只有感受。因此,古今中外,融会贯通,艺术经验与个人经验彼此重叠、呼应,延伸出一个自成一体的宇宙。
于是,看到西方绘画中描绘的地狱之蛇,陈丹青能想到在乌镇所见那条「美丽透顶的小青蛇,蜿蜒屈伸,缓缓移过宾馆的大理石地面」;谈到塞尚、高更和梵高,他又亲切又怜爱地说,「后印象派三位大师都是愚笨的家伙」;而看到西方艺术作品中的墓园和死亡,能对比出中国的绘画传统是《千里江山图》,而不是《死亡的胜利》。
陈丹青像是一个老友,看到好东西,心里澎湃了,藏不住了,于是硬要拉你说一说。艺术作品流传千年所蔓延生长的生命力,就是在此间发生。不是在论文里,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博物馆里,在分享的话语里,在人世间敏感的心灵里。我不禁想,在《局部》中所发生的,一如上世纪90年代在木心家讨论文学的客厅中所发生的,一如陈丹青与木心在纽约逛美术馆,两个忘年好友之间所发生的。
陈丹青有一双锐利的眼睛,「看人如看画」,又「看画如看人」。在凤凰网的一个视频采访中,他与记者坐在江南石桥上,迎面走来一个老大爷,陈丹青停下对话,目光追随着他,感叹——「嗬,好一个罗汉脸!」而在他和《局部》团队拍摄的特集《线条的盛宴——山西北朝墓室壁画巡礼》里,他站在墓室中,眼神被黏在壁画上,想象绘画的工匠怀着怎样的心情画下这些本应「永不见天日」的杰作。
人活于世,总要有一点痴迷,才算有点意思。在《局部》中,在手边这套三卷本《局部》视频讲稿的文字里,我品出了点意思。我无法随时飞去纽约、伦敦、意大利,观看那些美妙的艺术原作,但谢天谢地,有人为我看过,还毫无保留地与我分享。
于是,艺术也发生在这里,在每一个你能体会到它的当下。
《局部:我的大学》读后感(三):《局部:我的大学》摘
1.到了19世纪,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自觉偏离规范,进入20世纪,偏离规范成为常态,因为再好的规范也会僵化,会过时,丧失魅力,甚至令人讨厌。
2.我怀着矛盾的心情,爱这幅画,就像我怀着矛盾爱列宾与苏里科夫,因为勒帕热既是绘画的高手,又是描绘情感与内心的高手。《圣女贞德》既画出了村姑的质朴,又画出了神圣感,而花园中暮色四合、草木有情的神秘感,更是动人,以至我觉得这种神秘感就是画家短命的原因,勒帕热在36岁就死了。
3.所以认清艺术,总要两三代人才会醒来,而这种昏睡和醒来,不会停止。
4.巴比松画派的世界,亘古如斯,每棵树相信大自然永恒。今日欧洲的自然仍然壮丽妩媚,柯罗和米勒没有了,他们是描绘欧洲千年农耕图景的最后一代人。最后补充几句:被承认的艺术,进美术馆的艺术,都是过时的规范,失效的规范,轮到偏离甚且背叛印象派的规范,就是毕加索、马蒂斯那代人。但毕加索、马蒂斯开创的规范,今天也早就过时了。
5.熊先生生于民初的大变局,和他那代人一样,折服西洋文化,对各地老庙的历代雕塑,视为当然,视而不见。日后到巴黎,几位法国大雕刻家用法国收藏的魏晋唐宋雕刻,开导他:这是何等高超的艺术,这才渐渐使他拜服。晚年,他成为中国古典雕刻的研究者和辩护士。
6.鸦片战争后,中国不断西化,再也不是辽代时期的中国。梁思成也好,熊秉明也好,包括我自己,都是景仰西洋的艺术,跟从西洋的大师,可是到了美国、法国,这才越来越晓得自己祖宗的伟大,而且是一种不可追寻的伟大。
7.意大利不同地区的地方流派,有北方的哥特艺术影响,有东方的拜占庭艺术影响,大量画家并不遵循透视法,那是“三杰”和提香之外,另一个伟大的意大利,占了文艺复兴绘画的大半,无数小镇教堂布满这样的壁毯和梦境。所以,透视法之外还有许多绘画手段,另有一种古老的美感,譬如平面性,装饰性,图案分割之美,造型天真拙朴……
8.今年3月,我为《局部》第二季来这里做功课,每个馆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到底讲哪件作品呢?忽然,我就停下来,看见了保罗——注意,忽然停下来,忽然有幅好画被你看进去了,这就是惊喜。证明什么呢?证明我此前有眼无珠。还证明什么呢——看画没有道理,用不上道理。
9.最后再讲几句祭坛画。迪·保罗的两幅画,原先是锡耶纳圣多明我教堂祭坛底座的一部分。大家必须想象:500年前的祭坛非常昏暗,只有蜡烛光,教民看不清,也不许走近细看,那时,人们去教堂不是为欣赏艺术,而是宗教崇拜。许多高高在上的雕刻、绘画,几百年间从不让你看清楚,你看不清楚的事物,才有神圣感。
10.时代变了,宗教崇拜减弱,不少教堂老旧毁坏,祭坛画于是出售,变成单幅,配上镜框,被美术馆的灯光照亮,给人细看。照法国艺术史家达尼埃尔·阿拉斯的说法,这样一种脱离教堂语境的展示方式,是“文化在舞台上的亮相”,属于现代人的文化崇拜,具体说,是美术馆崇拜,展览崇拜。
11.我们常说文如其人,画如其人,这话,只能信一半。
12.他画鞭打基督的暴徒,动作也很对,为了捆紧耶稣,还用脚顶着柱子借力气,我一看,就知道他精通怎样制服人。他画砍头的那幅很著名,我的感触倒不在砍头,而是西洋人喜欢安静地在展厅里欣赏杀头的画面,以为美。
13.所以每次走出回顾展厅,我会神志恍惚,觉得和这个人诀别。就算再来一次,又一次,最后,还是诀别。
14.世人形容绘画是镜像,映照存在与真实,其实呢,绘画是永恒的谜,遮没画家的一切,你不可能因为这幅画而了解画家,除了他的才能。
15.“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不见我。”这是南齐书法家张融的名言。他所谓“古人”,指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后人并称“二王”,他的意思是说,你们别讲我没有二王笔法,要可惜二王没见到我的笔法。
16.我不想说,我不信任外国人谈论中国画。我想说,在纽约这间屋子里认识以董其昌为象征的中国山水画,是我出国后的重要经验。扩大说:出国为了什么,就为看清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文化。缩小了说:但凡热爱中国古典绘画者,仅仅观赏本土收藏,是严重残缺的眼界。
17.马奈看不起同行,他说:“我画画是有依据的。”他说委拉斯开兹是“画家中的画家”,结果,他自己也成了画家中的画家,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得非常懂,才能看出痛痒。他会不会心里想:好可惜啊,好可惜!委拉斯开兹见不到我的画!
18.2001年我头一次去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朝拜委拉斯开兹,没想到,正赶上马奈大回顾展,为了腾挪空间,特意重新布置所有委拉斯开兹的画。记得博物馆门口排长队,绕了好几圈。我跟着排队,心里好感动——马奈早已作古,可是后人安排他和委拉斯开兹见面了。
19.说来可怜,我青年时代哪知道董大爷多么重要,那会儿什么画册都没有,更别提真迹的展览。现如今,年度拍卖每次都有董其昌,有些比这次陈列的董其昌还要好,只是藏家稀罕,大部分画家不稀罕。
20.人类做事,年代越早,越是神乎其神,越是郑重其事,何况那件事有关人类自己的脸。
21.木心曾说:年代更替,艺术的第一重价值自行消退,进入第二重价值。什么价值呢?艺术的价值。
22.没去欧洲前,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我的天堂,后来一次次去欧洲巡视,哪怕远未看遍,纽约收藏可就比下去了,欧洲家底实在富厚,美国人有钱,你就买吧,但重头大戏都在家。
23.鲁宾斯坦演奏无数次肖邦,每场一次性过,他心里清楚,某次若有神助,再无法重现,另几次各有瑕疵,再无法收回了。
24.艺术,尤其是现代艺术,取决于直觉和本能,本能、直觉,无法言说,也无法求证。可是挑衅之后,却连毕加索、马蒂斯也难以判断自己做的事。当初马奈遭遇的羞辱,就是挑衅者自己无从判断,并为之深受折磨的故事。
25.艺术与大众永远存在一道鸿沟。
26.如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天天涌进数以万计的大众,如果现代艺术博物馆允许拍摄,争睹《亚威农少女》的观众会比这里还多,还拥挤——相比一百年前的“大众”,今日的观众真的进步了,看懂了吗?我不知道,但“大众”恐怕愿意相信:一幅挂在美术馆的画总归是好的,而大众崇拜有名的事物。
《局部:我的大学》读后感(四):好书推荐|妩媚的暴徒·卡拉瓦乔——陈丹青《我的大学》
你好呀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 陈丹青《局部》系列视频讲稿 我的大学 陈丹青说:“美术馆是我的大学,而我至今尚未毕业。” 而这也正是一本围绕着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开的美术史书籍。
Part.1
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里,卡拉瓦乔的收藏只有两件,但正好是他绘画生涯的一头一尾:《乐师们》画于1597年,时年26岁;《圣彼得的否认》画于1610年,当年他就死了,得寿38岁。
要论卡拉瓦乔那可是出了名的暴烈,他性格暴躁、孤傲寡合、狂放不羁,很难与人相处,动辄寻衅斗殴,犯过命案,上过法庭,在1610年又一次犯事逃亡,结果害了热病死在了路上。而他不仅会打架、会逃亡,还很会狡辩,当法官要求他交代犯罪过程,他居然当庭大谈特谈自己的艺术,不知有没有留下庭审记录,不然也是一篇难得的宏论。
我们常说文如其人、画如其人,但这话只能信一半。
在15、16世纪,有很多暴力血腥的场面,但是要论画暴力,卡拉瓦乔当仁不让。他画了大量《圣经》里血腥而暴力的场面,比如鞭打基督的教徒,暴力细节都画得十分细致可信,为了捆紧耶稣,教徒还用脚顶着柱子借力。
这一副《大卫手提戈利亚的头》也十分的出名,而我的感触倒不在砍头,而是西洋人喜欢安静地在展厅里欣赏杀头的画面,并且以为美。
说来也奇怪,挣扎垂死,战场上的尸体个个惨不忍睹,可偏偏古希腊、古罗马的雕刻偏偏把《垂死的高卢人》、《死去的加拉太人》等塑造得个个姿态优美,好像特地选好了动作才去赴死一般。而行刑的画面就更多了:耶稣钉十字架、圣彼得倒钉十字架、圣塞巴斯蒂安身上插满利剑赤膊受绑、圣洁的圣芭芭拉跪着双手合十背对着背后举起刀的屠夫,等等。
这是卡拉瓦乔所谓的画如其人的一面,但是他还有沉静、绵密而严谨的另一面,画风异常妩媚,文艺复兴三百年很少有画家像他画得那般秀美,尤其当他描绘起十五六岁的美少年。
同样是同性恋,达芬奇似乎从来没有描绘过他所爱的人;米开朗琪罗更多是描绘偏向阳刚的、力量的、肌肉的男性激情。但从来没有人像卡拉瓦乔一般如痴如醉地、毫无保留地画出心中对于娈童的爱慕。
他的这类画,有一种此前的绘画从不曾显示的功能:谁要是不理解同性恋,在这幅画中,可能会传染到同性恋的目光。
而在这一副《乐师们》中,左角的男孩是爱神丘比特;右面的男孩背影抛弃了文艺复兴惯常的模式,画出了少年尚未充分发育的稚气的背,上面落满了画家爱慕的凝视;正面的男孩简直美到雌雄同体,画面定格在他即将启唇歌唱的一瞬,比少女更加的迷人。
这分明是一副爱到发疯的图画,而更迷人之处是这幅画本身就像是一个美少年,像一个初发育的面孔,刚刚爱上了一个人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会画出这般令人痴迷的画面。26岁的卡拉瓦乔忍不住将自己也画了进去,置于右二,跟美少年挤在一起,隐埋在阴影之中。
而对于卡拉瓦乔来说他的深刻影响在于,文艺复兴的漫长模式被他终结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写实主义”就在他的手里半自觉的萌发了。
他的题材虽然仍是《圣经》故事,但他将圣母、耶稣、使徒和天使都画出了人间的真实感,而这在当时是一件勇敢而微妙的事情。之所以说他勇敢,是因为他画得太像世俗之人,订件难以通过;而说他微妙,是他画的草民生动可信,却仍然沐浴着神的光芒。
而他的创造性的贡献更是在于他强调了昏暗与聚光的对比,按照英国画家大卫·霍克尼的说法,卡拉瓦乔在16世纪就发明了好莱坞式的打光模式。
在卡拉瓦乔之前,提香和丁托列托多少丰富了宗教绘画的空间感,到了他,画中的主要人物被一束光照亮成为了新的风格。从15世纪主要由蛋彩画绘制的平面感,到巴洛克绘画的纵深感,中间有一位天才的过渡,而这位天才,就是卡拉瓦乔。
罗伯特·休斯曾说:“除了普桑之外,把任何17世纪画家的表面刮擦一下,就会现出卡拉瓦乔的痕迹。”可以说,几乎全部巴洛克绘画都是卡拉瓦乔的无数变体。他又说,“没有他画笔下卑微、平凡的人物在黑暗中重叠但在圣礼的光明照耀下能美化变形的那种感觉,伦勃朗还能画出什么来?”
他说的没有错,伦勃朗的聚光风格只是拓展了卡拉瓦乔的手法,而法国画家拉图尔甚至走得更远,他的每幅画在发展到了都只剩下了蜡烛光,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最后,欢迎关注公众号“盐巴书影”)
《局部:我的大学》读后感(五):陈丹青《局部(二):我的大学》:重叠的时间
图文版(原创):https://www.douban.com/note/797346091/
时隔两年多,又续读陈丹青的《局部》,第二季是围绕大都会美术馆的馆藏作品,从印象派到毕加索,从勃鲁盖尔到卡拉瓦乔,陈丹青说“美术馆收藏的就是重重叠叠的时间”,而这本书就像把美术史上的角落与细节,延展摊平,重叠相映,展现在读者面前。相比第一部来说,结构显得散乱,可能是因为馆藏太过于丰富,难以归结到某种清晰明确的体系。
大都会美术馆在著名的曼哈顿第五大道,向北是古根海姆博物馆,向南是小型的弗里克收藏馆,再向南就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这里是美国文化艺术的集中地。《局部》节目组为了拍摄,向博物馆申请了三个晚上的时间,万籁俱寂时与展出的艺术作品独处,可以说是非常羡慕陈老师了!
关于叛逆
“叛逆”是这本书贯穿始终的主题,或是说“偏离规范”。
所谓规范,褒义的说法,就是中规中矩;贬义的说法,就是陈陈相因。某阶段,某时期,艺术家总会自觉自愿遵从一套规矩,完善一种大美学、大风范,久而久之,就出现所谓经典、楷模、权威。
用王朔的话讲,就是“行活儿”。偏离规范的天才,用独特的灵气,打破传统,甚至打破自我:例如擅长宫廷画的委拉斯凯兹,将目光转向侏儒真实的脸庞;例如晚年不得志的伦勃朗,在自画像中表达了一种摄人心魄的诚实之美。
最经典的叛逆来自印象派:19世纪红遍巴黎的学院沙龙画家,技艺卓群、风光无两,例如梅索尼埃气势恢宏的军史画《1807年弗里德兰战役》,勒帕热生动又富于同情的《垛草》和《圣女贞德》,如今只能作为沙龙画的少数代表,占据次要的墙面了。
盛极一时的沙龙画家卡巴内尔,因《维纳斯的诞生》深受拿破仑三世的喜爱,画中漂亮的维纳斯像一块奶油蛋糕,枕着海浪醒来:这是19世纪绘画借古代神话展现的世俗fantasy。同时期的马奈、库尔贝却因为反叛而被边缘、被羞辱。陈丹青花了整整两篇写马奈,可见心中地位:“杜尚谈起20世纪头几年青年画家热衷谈论的前辈,不是塞尚,而是马奈,他说,没有马奈就没有现代绘画。现代绘画不再关心画什么,而是怎么样画,就是享受绘画和媒材本身的快感。”
马奈的现代性首先体现在油画的凝结层:这是媒介的质地美。在他描绘男性裸体的《死去的基督和天使》中,层层覆盖描绘基督的肉体,100多年后弗洛伊德更为稠密的多遍覆盖,就有马奈的影响。
在此之前,《凝结层的魅力》讲一位安静的画家维米尔:“他画中的一面墙,半扇窗,一把椅子,一块挂毯,全是沉默的神迹,凝固为物质感。”记得一位朋友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观察:“维米尔的光,总是从左侧照进窗子。”仔细看过他的画,发现还真是这样布光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花边女工》是他的重要作品,而陈丹青选《熟睡的女仆》,原因在于女仆面前的毛毯:一针一线,一撇一捺,铺陈为稠密的凝结层,绵密叠加,构成不可复制的“质地美”,而画家在其中,物我两忘,超凡入定了。用现代心理学的话讲,达到了“心流状态”。维米尔的凝结层是不自知的,委拉斯凯兹晚年画的《戴钢盔的男子》也彰显出笔势挥洒的才气,到了马奈,则是有意识地制造了一场凝结层的盛宴。
另一个反叛的例子是毕加索,与马蒂斯同被斯坦因家族支持,却暗自较劲,不肯服输。从斯坦因肖像到亚威农少女,毕加索创造了一种非欧洲绘画的平面感,融合了塞尚切割形体的方式,从此走向了现代艺术最重要的突破:立体主义。
马蒂斯说过:“艺术与大众永远存在一道鸿沟。”为什么?艺术家的反叛,不仅在于反叛对立的艺术形式,因循守旧的传统,也在于反叛大众所代表的一成不变的、乏味的美学。陈丹青说:“古代艺术属于宗教、皇族、贵族,没有大众的份;现代艺术的初衷也没想到大众,相反,是对想象中的大众的持续加码挑衅。”
除此之外,还有艺术家对自我的偏离和反叛。陈丹青讲到勃鲁盖尔的《收割者》:“这是他绝无仅有的一次例外,他从人山人海嘈杂喧哗的画面忽然溜出来,画他眼前的麦田。”我自己是很爱勃鲁盖尔的,看他的画,仔细观察每一个生动鲜活的画中人,我甚至会不自觉笑出声来。中国最早引入的西方艺术就是农民绘画,例如巴比松画派的米勒和柯罗,《晚钟》这种灰蒙蒙、苦兮兮的作品,在我读书的时候,都是作为西方美术的经典之作。后来我才知道,我们不曾接触其他画作,是它们的“政治不正确”:要么涉及基督教神学,要么是文艺复兴、巴洛克时期的大胆裸体,要么则是印象派描绘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于是米勒们成了唯一选择。
同样是画农民,勃鲁盖尔不显出半点“苦相”,簇拥熙攘、土头土脑,留下无数生猛的画面:乡村的豪饮,酒席的醉汉,醉后的狂欢与舞蹈,拄着拐杖的瞎子一个牵一个,或是像这幅《收割者》,午休的农民叉着腿在树下打鼾,全然一副呆相,组成的画面又一派生机勃勃。所以陈丹青说,勃鲁盖尔若生在20世纪,一定是调度大场面的电影导演。
关于矛盾
这里要讲我私心最爱的画家了:卡拉瓦乔。第一次接触卡拉瓦乔,是2016年读蒋勋的《写给大家的西方美术史》,至今仍然记得看到少女朱迪斯持剑割人头颅、鲜血四射喷溅的摄人心魄的画面;还有手提着巨怪歌利亚头颅的少年大卫,而那颗血淋淋的头,正是卡拉瓦乔自己的自画像!十足的暴力美学。而他的另一幅自画像,则藏在《乐师们》的美少年的背后,这个系列里,《酒神》《捧果篮的男孩》,白皙的皮肤,微启的双唇,凝结着爱欲的眼眸,这是卡拉瓦乔妩媚的另一面。
他的暴力是真实的,因为他打架、杀人、与人决斗、历经逃亡,是个名副其实的暴徒;他的妩媚也是真实的,因为他画中浸透的对美少年的爱欲,正是一个同性恋画家爱的发昏的内心欲望。他还画受难的基督,市井的骗子,油滑的赌徒,在戏剧化的张力背后,卡拉瓦乔在主张某种真实:邪恶是真实的,欺骗是真实的,残酷是真实的,绘画原本就不只是天使、维纳斯,而是更加广阔的人间。这让我体会到某种勇敢,某种不屑伪装的诚实。
除了这种“写实性”以外,卡拉瓦乔对光的运用也是开创性的。大卫·霍克尼认为他在16世纪就发明了好莱坞的打光模式:画中主要人物被一束聚光照亮,成为一种新的风格。每次看伦勃朗的《夜巡》,我都从中看到卡拉瓦乔的影子,正如罗伯特·休斯评价:“没有卡拉瓦乔笔下卑微、平凡的人物在黑暗中重叠但在圣礼的光明照耀下能美化变形的那种感觉,伦勃朗还能画出什么来?”从15世纪主要由蛋彩画绘制的平面感,到巴洛克油画的纵深感,中间有一位天才的过渡,这个天才,就是卡拉瓦乔。
接下来一位矛盾综合体是法国艺术史的先驱普桑:优雅的暴行。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尼德兰、德国绘画人才辈出,但法国实在乏善可陈。到了17世纪,普桑去罗马呆了几十年,追寻古希腊美学。在他的经典作品《掠夺萨宾女人》中,描绘的内容是战争、杀戮、嘶吼、绝望、兵戎相见,但每个角落都是克制的、冷静的、处处斟酌——陈丹青称他是“绘画的修辞学家”。在普桑身上,彰显出一种优雅的“法国性”,与凡尔赛宫,蒙田和帕斯卡,精致的奶酪、红酒与牡蛎,一脉相承。
《草稿与正稿》讲的是生与熟的矛盾,很多大师的草稿虎虎生气、松爽迷人,一本正经到了正稿,却只剩下刻意模仿的匠气,没了精气神儿。“第一次动手画,你是在空白的布上寻找那幅画,感觉是新鲜的、机警的、锐利的。到了复制,那幅画已经在那儿,一路描绘,只是核对加工的过程,全画的生气,画着画着,不知不觉没了。”
关于他乡
易县罗汉是让我最为感动的一期。他们出自辽代的不知名的工匠之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逼真写实,似乎遥承秦陵兵俑,技法采用唐三彩的烧窑、上釉,而这16尊罗汉雕像后,中国雕刻艺术的“写实主义”,似乎陡然消失了。
1912年德国人帕金斯到河北易县考察,将16尊罗汉雕像全部买走,运输途中若干损毁,仅存11件散落在西方各大博物馆,大都会美术馆藏有两件,中国境内却一件也没有了。陈丹青认为,这两尊雕像咄咄逼人的神态,足可比拟文艺复兴的大雕刻家多纳泰罗。“那种宗教的深沉感、自在感,那种自认为把握真理的确信,那种不容辩驳的信仰的傲慢!”
另一个流于他乡的例子是乔万尼·保罗的两幅祭坛画,与文艺复兴以来的绘画传统大为不同:没有透视法,没有消失点,没有进大远小,甚至没有阴影,画得非常天真,又神秘,像一场梦境。所以,透视法之外还有许多绘画手段,另有一种古老的美感,譬如平面性、装饰性、图案分割之美、造型天真拙朴……近现代艺术的先驱塞尚、毕加索,又是将平面性发挥到极致的艺术形式了,所谓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古典的一种复归。
《离开寺庙的药师图》也是中国艺术,原位于陕西洪洞县广胜寺的《药师经变图》,当地政府为筹款救庙,将壁画出售,价格1600大洋。四大幅广胜寺壁画被纽约药商赛克勒买下,几百块重新拼起,放在大都会美术馆展出。中国壁画发于汉代,魏晋唐宋达于辉煌,敦煌是极致代表。唐代寺庙几近毁失,除了地下墓葬和洞窟的壁画,地面上仅五台山佛光寺是现存唯一遗迹。想到我2018年到西安,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看到几幅大的墓葬壁画,其中最喜欢的是章怀太子壁画,场面弘大,人物逼真,我在当时的日记里写:“唐人有趣、格局大,目中壁画不是惨兮兮的墓志铭,而是放眼去画狩猎、马球、外交盛会。”元代壁画则以广胜寺《药师经变图》与现存中国境内的山西永乐宫壁画为最绝,也许是同一群艺术家所创作的。
大都会美术馆的中国馆,最别致的几幅是五代《乞巧图》,文徵明《拙政园图诗》,王原祁《辋川图》,传为五代董源的《溪岸图》,煌煌长卷,勾勒出中国古代美术的气象。陈丹青提到一个有趣的观察和体悟:人往往在出国以后,才更了解自己的国家和文化。“爱国得有个爱法,要是爱得入骨,你得出国开眼界。”这是实在话。我以前有位40几岁的同事,对中国文化如数家珍,行事做派也像文人君子,落落有方,也是在国外工作、生活七八年后,愈发体悟传统文化的精妙,而日渐融入日常生活。
关于时间
大卫·霍克尼有本书叫作《图画史》,其中有个段子,一位导演对转行电影的美术学生说:“别放弃美术馆,别不看画,画不会动也不会说,但绘画更持久。”霍克尼认为,好画不但容纳时间,而且创造时间,画出后,为时间所拥有,跟着时间走。法国美术史家达尼埃尔·阿拉斯更是用“错时论”来看待一切绘画,他说,所有绘画都容纳着错综复杂的时间感。
大都会美术馆中有一幅明人仿宋的《胡笳十八拍》长卷,就生动体现着中国古人的时间观:文姬离家,途径荒漠,野营、明月、大雁,最后汉军迎蔡夫人归汉,“当时怨来归又恨”,十八段画面讲述了蔡文姬的一生,好像一部电影。
另一种“时间感”,来自于对画家画画时憨傻痴呆之状的想象:仿佛画作就是画家一个生命片段的凝结。我大学时读梵高写给弟弟提奥的手稿文集,总看到那些恣意挥洒的速写背后,是梵高一人呆坐、孤独无可倾诉,却不能不画的生命时光。
摄影出现之前,郑重其事的肖像画,也是人类妄图留下时间的努力。盛装打扮的贵族,或超脱潇洒,或优雅端庄,或目光炯炯,如今他们的名字与血缘已经不重要,但画作凝固的当时当刻,却成为某种包含历史时间刻度的美感和价值。
联想到自己写手帐,其实也是一种对抗时间的方式。某一天走进个人馆藏的时间刻度,扯出一段回忆,应该会很有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