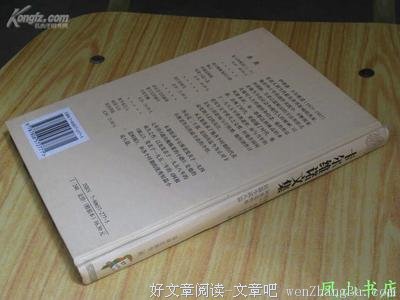《通向蜘蛛巢的小径》经典读后感10篇
《通向蜘蛛巢的小径》是一本由[意] 伊塔洛·卡尔维诺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8.00元,页数:17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不得不说,写得真好。
也许只有真正有童心的人才能写得这么好。柔软,一尘不染。
来看一下卡尔维诺的简介吧,1923年10月15日生于古巴,1985年9月19日在滨海别墅猝然离世,而与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父母都是热带植物学家,“我的家庭中只有科学研究是受尊重的。我是败类,是家里唯一从事文学的人。
少年时光里写满书本、漫画、电影。他梦想成为戏剧家高中毕业后却进入大学农艺系,随后从文学院毕业。1947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从此致力于开发小说叙述艺术的无限可能。
卡尔维诺在这篇小说里描写了一个过早进入成人世界的孩子。一个渴望得到关注但是却卑微的孩子。
他也有他的世界。成人进入他的世界里也变得可爱了。是因为单纯么?
当卡尔维诺写道,“他想法西斯分子可以顺着樱桃核追上他。但是世上除了红狼之外没人这么机灵会想到此。对,如果皮恩扔下樱桃核就行了!转过一道墙。皮恩吃一粒樱桃,在老榨油机房吃一粒,过了枇杷树又吃一粒。这样可以一直走到蜘蛛巢小路。但是还没有走到水沟旁,樱桃已经吃完了,皮恩明白,红狼永远找不到他了。”觉得那好像是在说自己。
这是皮恩自己跟自己的游戏。他没有和成人一起的游戏。也没有和同龄孩子一起的游戏。他只能自己给自己游戏。这看起来多么悲哀。然而这个故事不悲哀。因为,竟然有那么一些成人,进入他的游戏中来了。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兴奋的事情么?
皮恩也该因此骄傲了吧。
为什么,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谁愿意参与我们的游戏。而当我们长大,却也没有谁愿意重温童年的游戏?
这本书,也许可以给那些所有希望做一场梦回到童年,温习一场童年游戏的人看。
《通向蜘蛛巢的小径》读后感(二):有关皮恩与战争
第一次读卡尔维诺,还是在高中语文书上的一片《牲畜林》,虽然答题分析时要说揭露了法西斯的恶行、战争的残酷什么的,但其实影响最深刻的还是童话中人物动物淳朴自然。 《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也是这样,但纯真中带着更多的现实与残酷。
首先,皮恩是一个小男孩,他淘气,爱对所有人开玩笑,他大胆,偷走德国士兵的枪,又把它藏在蜘蛛巢里。另一方面,因为战争,他过早地接触到了成人的世界,那里有太多的虚伪、肮脏、、背叛、恶毒,混在一群大人之中,你会情不自禁地渴望一种认同感,一种被承认的感觉,所以他用童声大声恶毒地开着每个人的玩笑,他可以毫不露怯地讲出一段段成人笑话,他可以肆无忌惮地骂着每一个人。
战争是最暴露和改写人性的地方。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善恶都似一面明镜般的被照射出来。我们小时候,对成人的世界感到好奇,但总像是带着一层面纱,直到慢慢长大,它才慢慢明了。对皮恩来说的成人世界更像是一个荒谬的笑话,透过他清澈的眼睛所看到的一切都可以用来攻击他人,好像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但他终究还是个孩子,就像《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一样,鄙视大人的一切虚伪,有时又迫于夹在他们之中生活。
因此,当皮恩、德利拖、表兄、曼奇诺这样一支部队组建起来的时候,我感到十分惊奇。这些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目标,都不知道自己要对抗的到底是什么。战争是什么,是别人打你的时候,你要换回去。没有绝对的对错,只关乎你到底站了那边的队,而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在历史的场合中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战争是什么,是在外部的一切千疮百孔以后还要挣扎着活下去。
“在这里是正确的,在哪里就是错误的,在这里解决了某个事情,在哪里就破强化压迫。压在德利拖身上的负担,压在我们所有人,你,我,身上的负担,我们身上具有的古老疯狂都发泄在射击上,发泄在被打死的敌人上,这和使法西斯分子射击的疯狂是一样的,这疯狂是他们用纯化和解放的同样希望去杀人。于是,就有了历史。”
《通向蜘蛛巢的小径》读后感(三):通向蜘蛛巢的坑
非常吃力的读完,发现对于卡尔维诺理解的战争我还是不太能很好的理解。
所以先占个坑,把不太理解的位置给标记一下。日后再慢慢去理解。可能是我对于战争的理解还达不到卡的那种深度吧。
对于吉姆政委的对白和独白。我也认为这是作者在进行一个比较集中的想要对战争进行正面探讨的地方,并且大部分认同这种观点。但是,我不明白作者为什么要借助这样一个人物之口来说出。吉姆政委从一出场,经过了简单的身份介绍后就开始与指挥官对话。然后就是大段大段的说出他对于战争的理解。所以在我看来这个人物是个非常不立体的,身份和外貌的简单描述并不能唤起我对这个人物的认同感。而这一节的出场以及其话语的内容使得这个人物显然的成为了小说的主要角色之一。当然之前的文章也是在从侧面来讲这么一个东西,这里的作用只是相对直白的表达。但是为什么不让吉姆这个人物出场时间多一点之后再来一步一步的讲述与分析呢?在这么重要的角色身上为什么不多花些笔墨呢?
其二,我觉得小说的视角选取的非常巧妙。把视角局限在皮恩这个孩子身上。这种视角是使得本文的故事性强了很多。但是,也是从吉姆出场开始,这一节视角似乎忽然变成了全局式。类似于玩游戏时突然开了地图全亮。本来刻意营造出的黑呼呼的神秘感在这里一下子变没了。本来我猜想是不是皮恩偷偷的跟在他们后面听到的两人对话。但是文中似乎并无提及。并且后面吉姆的内心独白也很明显的证实了这些并不是通过皮恩来了解到的东西。那么,作者刻意在此处改变视角意义何在?
第三,我知道这个讨论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作者也刻意留了不少值得猜测琢磨的地方。不过我还是想讨论一下,结尾处的枪声是不是表兄杀了皮恩的姐姐?
第四,没理解筑巢的蜘蛛到底象征了什么?
小说页数不多,却断断续续花了近一个月时间才读完。情节也不大能连得上。所以此文只是一个坑。经过思考和重读之后再来填吧。
如果你对于我的疑惑有任何想说的,请赐教,不胜感激。
《通向蜘蛛巢的小径》读后感(四):欲望战争与少年梦
我们应该如何定义这本书?战争、革命,这本书上贴着众多的标签,但又无法完全概括这样的内容。由战争展开情节,却又跳脱出战争,触及地表之下更深层的矛盾冲突,而在所有的污秽里,却开出了一朵摇曳的白色小花。
构筑战争世界是政治还是主义,还是所谓的哲学理想?恐怕归根究底也逃不过人的欲望。所谓战争,也不过是群体欲望的对撞。
皮恩闯入了这个世界,以一个孩子的身份见证了这场成人的战争,窥探着成人的欲望纠葛。他的愿望是拥有一把自己的枪,逃离被成人当作玩物的命运,逃离被当作妓女弟弟的命运。他不知道什么是革命,亦不知道每个人之间的不同欲望代表着什么,只是在唏嘘,觉得这里有所不同。他在这里并未寻找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朋友,却最终与生活和人性达成妥协,找到那个并不完美的,伟大的朋友。
皮恩在他姐姐——一个妓女——的照顾下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这也就造就了开头时一个言语粗鲁下流的顽童形象。那个环境中的人们也并不排斥他,把这样一个顽童当做了玩物,让皮恩给他们唱歌,跟他插科打诨。在这些人的簇拥中,皮恩产生了逃离念头,他不想被当做顽童,这些大人眼中的玩味和欲望让他恐惧与厌烦,他想找到一个真正的朋友,能与他分享蜘蛛巢的秘密。但他不愿离开,不想这样在人们的笑声里离去,也从没想过自己可以去哪里。作者在第一章中,就是以这样的角度来定位皮恩的:一个生活的不在编者。
这一切在他得到那把枪开始改变。皮恩在众人的怂恿下,从水兵的裤子中偷来了那把枪。他完成了一个让众人赞叹的英雄情节,也因此被投入了监牢,受到拷打。在监狱里中结识了红狼,那个大名鼎鼎的游击英雄。红狼有英雄故事,有坚毅的性格,有太多皮恩所不知道的知识,完全符合皮恩梦想里那种伟大朋友的形象。然而红狼所关注的只有他的事业,也是把皮恩当做孩子的一个普通大人。并且在最后丢下皮恩自己逃跑,口口声声说,为了事业的荣耀。这种近乎于完美的人反而无法让皮恩接受,这种“没有缺憾”是人性美的消磨,反而是种更让人叹惋的缺憾。
这种缺憾就如同中世纪中泯灭人性的教义,只是改头换面,在现代的种种终极理想里变成了道德高标。整个故事里的这种伟大反而在那些所谓“流氓”的衬托下变成了《绿鹅》(》十日谈》)中可笑的父亲。卡尔维诺用自己的笔向那种种理想发起反抗,正如薄伽丘所做的,用墨水和纸张为人性求得福祉。
卡尔维诺在他的自序中写道:“你们想要'社会主义英雄'吗?'革命的浪漫主义'吗?我给你们写一个游击队员的故事,书中谁也不是英雄,谁也没有阶级觉悟。我给你们表现边缘人物的世界,那些流氓无产者!”
这在他那个时代是种争论与反思,战后青年人的迷茫,不断上升的犯罪率让人们忧心,卡尔维诺反思战争中人类的欲望和命运,又批判和反击那些把参与战争者丑陋化和神化的论断,构筑起这样一个故事。
我想卡尔维诺所玩的游戏就是现实主义作家对于一个时代乌托邦的调笑与思考,无论被追捧的乌托邦有多么伟大与圣洁,他都是被那些最不堪的人建立的,无所不用其极。就像那个笑话中一样,伟大都用鲜血和皮鞭建立的,而和其中所有的哀嚎,大可忽略不计。
但或许因祸得福,皮恩阴差阳错的加入了德利托支队,在这里继续寻找梦想,纵使他们依旧把他当做小孩子。这里有他梦寐以求的战争,但也依旧有着孤独感和不屑,然而就是在这里,皮恩观察到人性在一种不完美中达到和谐。
这本书所表现的并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主义运动,反而是在战争背景下人性的粉墨登场。在这场革命中不乏真正的军人、自我发现与迷茫的哲学家,也存在有着坚定意念的“革命党”,然而这场战争的推动者,仍然是那些什么都不知道的市井平民。
皮恩所的追求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不是大人的,也不是小孩子的。他,或者说整个小队参加战争的理由虽各有不同但都不是为了革命,表兄为了背叛他的妻子,皮恩为了不被人说成是妓女的弟弟。
然而归根究底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带着仇恨向欲望射击,向自己的恐惧不满开炮,都是对失意的泄愤。在这场战争里,至少在这个支队中,像是“主义”这样的精神追求全然被淡化,人们是在最原始本能的驱使下走向了战争。
或许那个厨师是为了什么主义,可是他从不参加战斗,连饭也做不好,他坚持的主义不过是对这些“市井无赖”的炫示,以突显自己的身份,来遮掩自己的懦弱和妻子不忠的羞耻。厨师和支队政委所宣讲的主义,对于这些整日与虱子搏斗的人们真的有什么意义吗?
作者用虱子粉象征着主义:旅部有虱子粉,这个支队没有,旅部知道了就答应给他们带来虱子粉,这就是主义。也就是说,所谓的主义也不过是一包虱子粉罢了,有它要打下去没有它依然要活下去,并且人们还在怀疑它的效用:是只能把虱子熏晕还是能杀死他们或者他们的卵?讽刺意味的是,那个说把主义解释为虱子粉的支队政委身上仍然有虱子,他的梦想——回到城市重新成为白铁工人——也最终在他死后变成泡影。
卡尔维诺所说的主义毫无疑问的象征的是一种群体追求,让我们不禁要反思与询问:群体所追求的精神意义又究竟是什么?而在战争中的人群所真正追求的,又是什么呢?
作者安排了一个释疑的角色——政委吉姆,他在战争中观察着这些游击队员的行为,揣度他们的心理,在战争背景下窥测着人性;而卡尔维诺则是通过皮恩窥测一场战争,一个少年的梦想在与人性欲望的冲突下成长,这便是这场战争的意义。
有些人放弃了土地放弃了奶牛投身战争为了他们的祖国,有些人则是为了他们的奶牛、土地和工作来保卫祖国,还有一些人则为了他们的财产而留了下来,站到革命的对立面。所有人都是因为原始的本能而战斗:为了生活,或者为了更好地生活。在这其中的德利托支队则是一个特例,是所有矛盾的集合体。他们之中有流氓、宪兵、小偷、流浪汉。这些市井无赖,所谓的“流氓无产者”并没有什么追求,连对于土地和工作的欲望也没有,他们的战争是种最原始的泄愤,以至于他们将子弹射向自己人或者打向“黑色旅”并没有什么区别。
卡尔维诺想传达给我们的,就在于此。战争本身由人的欲望所推动,然而在其中卷入更多的则是无目的的人群,为了战争而战争。最该有所谴责的,就是战争本身。而在这场无目的的战争中,德利托支队的众人遭受命运的折磨,却在一种有缺憾的性格(或者说恶劣的性格)中完成了人生的价值塑造。这也让皮恩最终明白人性的缺憾往往是人类固有的弱点,最终向那些意大利的先辈一样对人性妥协,这,则是皮恩真正地成长所在。
这部小说的情节大多是灰暗的,但作者用一个顽童的视角来窥探成人的世界,让这段看起来肮脏虚伪的时间蒙上好奇明亮的光彩。成长是少年人的梦想,在这个顽童的视线里,一切都不那么尽如人意,但也有很多有趣新奇的东西,在这个最底层的环境里开始自己的追寻。
“一切都应发生在一个顽童和流浪汉的环境中,以一个孩子的眼睛来观察。我虚构了一个写在游击战争边缘的故事,与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无关,却传递了它的色彩、节奏、辛酸的味道……”
皮恩作为大人世界里的一个孩子很伤心,永远是孩子,被大人当作好玩的东西和讨厌的东西来对待。不能使用他们神秘和有刺激的东西,武器和女人,永远不能参加他们的游戏。但是,皮恩有一天会长大,可以对大家很坏,报复那些对他不好的人。皮恩现在就愿意成为大人,或者不是大人,但照样令人佩服或令人惧怕。做某些杰出的举动,成为孩子,同时又是大人的头领……同时,他发现自己对那些计划的热情是假的,预想的。发现他的幻想肯定永远不能实现,他继续是个迷途的、到处漂泊的可怜孩子。在这个充斥着欲望和纠葛的成人世界里,皮恩是个异类;他永远只能抱着纯洁的梦想睡去,永远无法找到自己的乌托邦。
皮恩最终选择了妥协,将藏匿枪支的蜘蛛巢指给表兄看,也最终跟着表兄回到了支队,他知道了大人总有欲望,表兄是伟大的朋友,但也是个有着种种毛病的朋友,他最终明白了这一点,也真正完成了成长。
相比之下,《炼金术士》中圣地亚哥的命运反而更容易让人所接受:他经历了种种磨难,最终也得到了财宝和爱情,这是一种向往中的成长,而卡尔维诺笔下的皮恩经历的更贴近于生活本身,一种现实的成长。在这个昏暗的背景下,皮恩的追求更多了一种精神意义,一种对于人类人性的发现与妥协。
人性中总会存在着弱点,但正是这些弱点成为了人们最常顾影自怜的地方,如果没有这些缺憾,也就不会有什么文艺复兴,更无从谈起由此引发的人类对于文学与文明的探讨。卡尔维诺在自序中写道,“有些人不明不白地参加了斗争,也推动了人类的解放”正是这些人,用自身性格与命运的弱点完成了对于战争,对于欲望的反抗。
皮恩固然没有追寻到自己完美的朋友,却找到了一个能够分享秘密,一个真正能理解自己的人。他向这个充满瑕疵的社会妥协,也象征着人类在几千年间对于命运的抗争与探讨,对于人性的反抗与回归在最后达到了一种平衡。并非十全十美,却依旧是社会的珍宝。
正如雨果所感慨的那样,革命的绝对价值之上,必然有一个人道的绝对价值;卡尔维诺则告诉我们,在人类的梦想和欲求之上,有一个人性的绝对价值。每一个人在这种人性上都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找到一种亲近感,而这种对于人性的回归,最终将诞生文明。
卡尔维诺用自己的笔完成了对那个时代诋毁者的反击和对当局的控诉,在战后青年人的迷茫与诉求中找到了一条明路,给当时混乱的社会开出一剂救世良方。欲望的战争固然会使文明衰颓崩塌,但造就这一切的人依旧会存在,那些并不完美的人性依旧存在。人性存在的地方,文明便会在那里重生。
“快,把火柴扔进去!”皮恩说,“看蜘蛛出不出来。”
“为什么,可怜的小动物?”表兄说,“你没看见它们已经遭到很多损失了吗?”
“你说,表兄,你相信它们能重新筑巢吗?”
“如果让它们安静,我想会的。”表兄说。
《通向蜘蛛巢的小径》读后感(五):晨读卡尔维诺
卡尔维诺的语言不知道怎么形容,政委的话就是卡尔维诺的独白,关于共产主义,关于革命,那只是一群人为了各自不同的欲求的结合,到革命胜利了,大家各取所需。
谁在乎革命者的理想,革命者不需要理想。革命者是成人世界的东西,他需要武器和女人,武器可以完成身外的革命,女人可以解决体内的革命。
“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关于意大利的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知之甚少,我试图从蜘蛛巢的故事寻找那场战争的隐喻,是关于暴力与性的暗示。从一个孩子眼中看到的世界,远比置身于这个世界中的成年人更加清晰。成人世界的隐喻到了孩子眼里便是寓言,他们可以从寓言中得到他们想要的快乐和悲伤,而成年人只能获得那些没用的警示,因为他们下次还是会卷入到另一场战争之中,可以说这是成人世界的劣根性。
蜘蛛巢还在么,曾经的宁静还在么?那些人都是平静的,我们试图寻找平静的隐喻,那是一种向往吧,一种不属于自己的向往,因为别人都是平静的,只有自己不是。或许它指的是没有战争的生活,可这个世界上哪有这样的生活?或许这只是一个幻想。
通向蜘蛛巢的小径是沉重的,但是阅读是欢欣的,因为我会记得,在那个山间的早晨,和朋友们一起朗读卡尔维诺。
《通向蜘蛛巢的小径》读后感(六):道德的多义性
如今,当我再次用是否有道德去评价一个人的时候,我会立马问自己,我所使用的是哪种道德评价系统?
假如从基督教的道德观来看待,全世界那些不信教的人都是不道德的;
假如从一夫一妻制的道德观来评价,伊斯兰教国家的人都是不道德的;
假如从不允许近亲结婚的角度来看,林黛玉和贾宝玉也是不道德的,而在现实生活中娶了表妹的曹雪芹更是不道德;如果必须遵守法律,不能随意造反杀人,水浒英雄都不道德;
如果尊重自由恋爱,买卖婚姻为不道德,那潘金莲和西门庆在杀死武大郎之前的行为就算得上是遵循道德,武大郎才是不道德;
自由平等是道德时,整个的奴隶制、封建时代都不道德;
这个列表将会很长很长,我只是想说,道德真的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老子认为道和德是最重要的东西,但他所认为的道德是大道,是天道,是自然之道,并非我们今天所说的纲常伦理。
因此,我们能说皮恩的姐姐不道德?还是德里克不道德?就是那个叛徒,我们也无法去界定他是否道德。
就像卡尔维诺在序言中写到的,选择墨索里尼还是游击队,许多人都是出于无意识。难道所谓的站对了位置就是道德,选择了成功的一方就是道德,在历史上青史留名就是道德的吗?
那得看我们如何去界定道德了。
《通向蜘蛛巢的小径》读后感(七):通向蜘蛛巢的小径
强迫症,导致我没有写完一篇所谓的读后感无法接下一本书的任务。现在,我来摆脱我无法摆脱的烟云。
没有见过那么长 关于政治。然而他的第一本小说就是二战过后的反思。他说,他进行双线挑衅。
试想一下,若是某个中国作家,试图写抗日抗美或者写十年内战的小说,并且以儿童的视野写,那写出来的是什么样子的?我能想象出的文本是一个儿童力量的逐渐成熟和政治觉悟的成长……有谁会和卡老一样用一群流氓来解构战争?尤其是那一幕:一边伺机和火头军的妻子做爱的指挥员(或者已在灌木丛做爱)和一边是山头围攻德国军队的队伍。以不道德得性爱遮住了战斗的场面,间或的一两句还没有开战来给予战争一个小缝隙。将欲望和性爱无限的放大。战争的严肃性被瓦解,变得荒诞。
有人反对卡老安排的吉姆表达政治意识的那一段话。可是,我却觉得那是小说的内涵体现。当你有一个能够戳破整个形势的观点但是对大局情节的推动却没有用时,你会怎么样?我会选择献上它,尽管可能不符合整体风格。那也是作家的一种割舍啊,表达出来后,他变得更加贫穷。这种偏执,我理解。而那一段对话恰好让我这种没有多大政治觉悟的P民能够了解当时的队伍成员的战斗真正意图。吉姆的自白,很冷静又很迷茫,一个迷失在战争中的自我。
战争,在皮恩的眼里,是游戏,只是赌注是生命而已。行进的军队在他眼里,是阳光制造的幻象,P38的枪支是为了炫耀和保护自己,用暴力来抵抗暴力。投入黑色旅或者加波的区别在于哪者更有趣。他搞不懂大人的反复无常和虚伪,可以再黑色旅和加波之间随意转换角色,而对他来说,一就是一。他也想真正的进入游戏中,并且为了生存认真的玩耍。只是他不是大人,无法进入那个复杂黑暗的世界。他不知道武器和性真正以为什么,但是他想拥有它,就像墙强迫自己喝酒抽烟一样。仿佛它是进入大人世界关卡的通行证。皮恩以一种天真的眼光看待战争,他从来不知道有没有战争有什么区别,因他一生下来就是战争。所以他搞怪的在红狼写标语时写下CWL……他渴望展示自己的力量,炫耀自己的装备,展示自己的强大,以得到尊重和征服感。一路寻求有资格进入蜘蛛巢的真正朋友。他看重承诺,他热爱自然,崇拜力量。
但他是以一种毫无怜悯的讽刺的眼光看着一切人的。德利托、吉里雅、曼齐诺、米歇尔、丽娜……用笑话无情的戳破他们的弱点,揭露出他们的弱点和黑暗面。而这些因着欲望、愤怒的热情而革命的无知的人,推动了历史。像皮恩这样的人,暗地里是被排斥的,因为看得太清楚。早熟而明理的皮恩,找不到伙伴,无法被认同、被重视。
皮恩是孤独的,很孤独,在那样的时代和那一群人中间。局外人一样的存在。找不到依靠和目标。最后,皮恩还是找到了表兄。一个厌恶女人为战争武器所累的有温柔手掌的人。那是一种亲情,对皮恩来说。他们手牵着手,在黑夜中行走。
卡尔维诺对死亡、战争和暴力的描写,很冷静。笔墨不多,有的只有渲染。描写监狱里的挨打,没有恐怖之感,甚至让皮恩将它们和姐姐的打骂联系在一起。
而为什么那么爱鹰的曼齐诺会因几句愤怒的话而亲手杀死鹰?我一直不理解,猎鹰应该是他的一部分的,应该是这样的。战争和人性的冲突吧。也许。
最后,蜘蛛巢的小径是什么?蜘蛛巢代表什么?蜘蛛巢让我想起了卵巢,一个温暖隐秘的母体。那个是少见的纯真和平的地方,尽管时不时也受着皮恩的暴力对待,但它无疑是皮恩的精神慰藉之处。只有有资格的人才可以和皮恩通向蜘蛛巢的小径。它被佩莱捣毁过,一种精神方面的因暴力而受到的倾塌。我这么自我解释。有点浅显,原谅我的无知。
《通向蜘蛛巢的小径》读后感(八):通向蜘蛛巢的小径
这是卡尔维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小说。与《看不见的城市》相比,《通向蜘蛛巢的小径》的确有所不同。在形式上,它没有《看》那样精巧的复式结构,也没有使用那种细腻精美的语言;叙事基本按时间顺序进行(只有一些插叙的片段)。它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描绘了一系列相对鲜明的人物形象。
对于这部小说,作家必然会倾注特殊的感情,也更多地进行了反观。这些反思和追溯反映在1964年新版的自叙中(第一版出版于1947年10月),而其中关于创作和其他方面的思考,对于读者来说也许比小说本身更有价值。
作者自序中提到小说创作的过程,其中说到在写作这部小说之前,他曾经用第一人称撰写过一系列回忆游击队生活的短文,但往往走向奇怪的方向;而当他跳出自我的视角,以“客观”的角度去写一个故事时,却意外地顺畅自如,也受到了读者的认同。卡尔维诺由此感悟:“小说写得越客观匿名,就越是我的”。
对此,我的理解是:作者越是想把自己的经历、观念塞进小说中,就越可能因为自我意识和情感的过多参与而使写作失去控制。作者可能会因此而可以将叙事引至某个方向,或是讲角色塑造成某种特定的样子。这样的作品可能会变成一种强加给读者的意识形态,甚至变成作者的自说自话。而如果作者能够放下这种状态,转而“客观”地讲述,将自己隐匿在故事背后,则可以更加冷静(也许这就是c大一再提及的“冷静”?)地成为那个难以察觉同时也无处不在的“操控摄像机的人”,作者和读者都可以由此获得更大的自由。
此外,作家也真诚地提醒人们,“永远不要开始写第一本书”。因为有了第一本书,作家将陷入“自我定义”的桎梏,此后的写作将是对这些自我定义的不断重复和加深。而真正宝贵的不是那些经过筛选、加工并已固话的文字,而是那些活跃在记忆中的生动、鲜活甚至面目模糊的事物。
书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主人公皮恩的塑造和对历史与战争的思考。
皮恩是一个处于两个世界夹缝中的人物——在孩子们的眼中,混迹于大人中间的皮恩无疑是一个异类;而对于成年人来说,他则只是个假装早熟的孩子。两个世界对他而言都有难以消除的距离和陌生感,而他心中唯一的圣地则是那条蜘蛛筑巢的小径。那是他收藏秘密、发泄悲伤、寻找安全的地方,仿佛是心灵的角落、母亲的怀抱。虽然最后,小径的墙壁被推到、蜘蛛巢被摧毁,但正如“表兄”和皮恩期待的那样,经过漫长的历程,蜘蛛们会重新筑起巢来,小径也会恢复如初。正如和平将会到来,伤痕将会愈合,心灵也将会重新获得一个平静、安宁的秘密之所。
对历史和战争的思考藉由政委吉姆之口说出来。那一段长长的对话(实际上更像是吉姆的独白)也是我十分喜欢的部分。那些德利托支队的无名战士们,没有谁是为了崇高的理想而战,他们自己都算不上高尚的人,但他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所有琐碎不堪的小事,都构成了历史。我们自己也经历过(或者说离得很近)相似的历史,这些思考也许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去反观自己历史中的那些人和事。
最后想说的是小说中体现出来的童话笔调。作者自己也在序言中提到了它,但并没有详细讨论。也许日后读过卡尔维诺的更多作品后,我会对它有更好的理解。这里只记下一个问题提醒自己思考:到底是哪些要素形成了这种童话笔调?我们又是如何感知到这种色彩的呢?
《通向蜘蛛巢的小径》读后感(九):卡氏主流的一面
有深入阅读卡尔维诺的愿望,因此买了其处女作《蛛巢小径》,如其前言所说,此书的意境独特性比起后作的宇宙奇趣和祖先三部曲显然乏味得多,比起带有卡氏独特标签的奇幻作品,更像是通常意义上——我们甚至要加上一个无比主流的标签,即“爱国主义”——的小说作品。如果把人物名字,所处背景置换一下,此书的情节与一些国产电视剧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如同自己对此书之前的预期一样,蛛巢小径展现了卡尔维诺较主流、较与现实世界步调一致的一面——热血而粗野的少年皮恩,契合了战后意大利人渴望表达的心理诉求。本人当然与二战硝烟尚未散尽的历史氛围相距甚远,但想想大体也能理解,彼时的人们的确需要“倾诉”。卡氏在书的末尾为皮恩安排的未来是有着自由主义倾向的,但又在其身边设置了粗壮给人安全感的“表哥”作陪,又让人感觉这一自由主义并不彻底,至少其内心深处仍渴望着庇护——想想当然也可以理解,但是抛弃这些背景,个人更喜欢的,还是那个更奇幻更变化自如的卡尔维诺;正如比起作为纪实文学作者和杂文作者的春树君,个人还是更喜欢那个写小说的,用文字玩着多变有趣游戏的春树君。
《通向蜘蛛巢的小径》读后感(十):只在与青春最巧合的那一刻(摘自本书序言)
是帕韦泽第一个向我谈起我作品中的童话笔调,在这之前我尚未意识到这一点,从那以后我开始注意并尽量确认它的定义。我的文学道路开始显现出来,现在我发现,一切元素都已包含在那最初的开始。
到头来,第一本书或许是最有分量,或许你只要写那一本就够了。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有巨大的冲劲,表现你自己的机会只有一次。这个唯一的机会可以让你打开心结,表达自己,但这个机会稍纵即逝。可能诗歌只有在你一生中与青春最巧合的那一刻才能完成。过了那一刻,不管你已经表现还是没有表现,事情就已成定局,作者做的只能是模仿别人,或者模仿自己,他甚至都不能说出真实的,不可替代的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