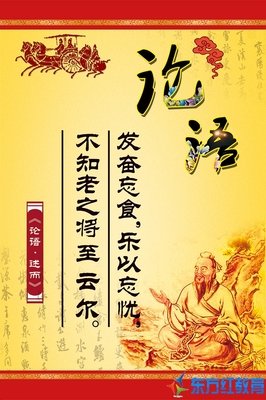《珍物》读后感10篇
《珍物》是一本由《生活月刊》编著 / 李宗盛 / 谭盾 / 林怀民 / 阮义忠 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元,页数:42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珍物》读后感(一):玩物不丧志
上海译文出的这本书叫《珍物》。听这书名,就知道所讲的大概就是一些为人所珍视所收藏的物件。我是个从来不藏也藏不住东西的人,走一路丢一路。倒从未以此为憾,只是羡慕那些能珍藏东西的人。比如我的好友旭东老师。
提到《珍物》时,他说了这样一番话:
四百年前,文震亨写了一本《长物志》。一些朋友在我书房看到的时候,总是会说:“这么精致的生活,等我有了钱,我也去买一些这么高雅的东西来”。
他们说的话,我是不相信的。一个没有惜物之心,一个没有留驻自己过往历史的习惯的人,难以理解身边的长物是自己世界的另外一部分。
我的书房里至今还有我三十年前写了一半的情书,因为那时我是多么想向心爱的人表达,却惶惑不安。我留下了不单单是那两张信纸,我留下了我青春的惶惑。
我书房里,仔细找找,应当是能够找到我初一用的第一个日记本,可能只是记了两三天,其他的都是空白。至少,在往后的几十年,我天天写日记。当年那个小毛孩子,多么担心日记被父母看到,然后受到严厉批评。
至于阳台上的晒衣架,是我结婚时,自己在木匠旁边捡废木做的。用了三十年,现在看起来简单得可笑。而那时,每一根能用的,我都制成了可晾晒一生的衣架。
我不像我一个姓梁的朋友,什么都扔掉,他身边真的是身无长物。我就一直没想明白,他急匆匆的往前赶,前面到底有什么呢?
非常欣赏旭东老师这样能留得住物件的人,他的每个物件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我也写过日记,却走一路丢一路。大概和旭东老师口中那个什么都扔掉、急匆匆往前赶的姓梁的朋友是一类。但据我所知,旭东老师这位姓梁的朋友,也就是和我写米锅诗的文谋老师,绝不是这样的人。他就连2012年与朋友们斗过的诗,还保留的好好的。而我真真正正是个没有惜物之心,也没有留驻自己过往历史的习惯的人。我对待生活和生活中各类物件的态度,用一个词概括就是“挥霍”。
若把这归结于性格使然,我便能免于反思。可听了旭东老师那一番话,我突然有了反思的自觉。在提倡摒弃多欲不为物役的全民断舍离时代,还要不要收藏?——收藏以往的日记,收藏几十年前亲手做的衣架,收藏年轻时写了一半的情书。
我想,还是要的。生活,既要身外无物,又要别有长物。正如周作人所说,“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
曾经的日记、衣架、写了一半的情书,放到现在,应该算不得什么日用必需品了,但作为无用的物件,给人的是必需品所给不了的愉悦。
身无多余之物,是一种轻快的生活姿态,而别有长物,则是生活情趣。
身无长物者,如东晋人王恭,《世说新语》记载:
王恭从会稽还,王大看之。见其坐六尺簟,因语恭:“ 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既举所坐者送之。既无余席,便坐荐。后大闻之,甚惊,曰:“吾本谓卿多,故求耳。” 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
王大看到从会稽归来的王恭坐着六尺簟,就开口求一席。王恭当时没说什么,后来就把自己坐的六尺簟送给了王大,自己坐在草垫上。王大得知,很惊讶,说:“我本来以为你有多余的,我才要的。”王恭说:“您不了解我,我这个人没有多余的东西。无论什么东西,送了人,自己就没有了。”
后人常以身无长物指代一个人贫穷。我看这故事里的王恭倒也没有呈现出贫穷迹象,没有六尺簟,就坐草垫上,未尝不可。六尺簟有六尺簟的好,草垫有草垫的好。
翻看旭东老师所提晚明文震亨《长物志》所记,未见什么奇珍异宝,全是常目所见之物。但每一物都颇有些讲究,都带有生活的情味。
比如书桌。
中心取阔大,四周镶边,阔仅半寸许,足稍矮而细,则其制自古。凡狭长混角诸俗式,俱不可用,漆者尤俗。
说的是,书桌桌面要阔大,四周镶边半寸左右,桌腿要稍矮一些细一些。这样的规格,自然古朴。凡是狭长圆角的庸俗样式,都不能用,上漆的尤其庸俗。
听这番分析,现今世上能摆脱庸俗的书桌恐怕不多。
北宋苏易简说自己“退食之室,图书在焉,笔砚纸墨,余无长物。”虽无长物,但笔砚纸墨作为他日用不可斯须而阙者也必求精良好用,还要耐看讲究。这不只是对器物品质的讲究,更多的,是对生活品质的在意。这些在意恰恰就体现在对器物的讲究上。
王夫之在《周易外传》中说:“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固其诚然者也。”器有载道之用,难怪苏易简在《文房四谱》中记载,唐代书法家柳公权为司封员外时,穆宗问他:“笔何者书善?” 对曰:“用笔在心正,心正则书正。”上改容,知其笔谏。
古人对室庐、花木、水石、禽鱼、蔬果、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香茗等都有一番讲究。这是我们今人所不能比的。因此,我对那些知晓物件背后故事的人,总是充满了佩服。
就像旭东老师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的:
在向现代拼命奔跑的这些年代。我们是以一种撕裂的方法,残酷的割除我们的传统,不单单的习俗、礼仪,还有我们的村庄。即便你今天回到家乡,那代表村庄历史的所有建筑、道路,都已经可能的荒草萋萋,而许多怪异的村庄结构,在村庄中心的牛栏,会让你嗟叹不已。
不能一味奔跑,我们也要珍藏些什么。
《珍物》读后感(二):如此隔离又息息相关
记得快毕业的时候,我们听张新颖老师讲过一只豆彩碗的故事。1950年,沈从文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和思想改造,休息日回家,端详着书架上的豆彩碗,联想起自己的文学命运,生出万千感慨。这个“稚弱中见健康”的豆彩碗,是沈从文生命中的珍物,手工艺者将受压抑的痛苦,和柔情,和热爱转化为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也是如此;十五年,经历了多少炮火和饥饿、恐怖与疲劳,多少人事都在摧毁与重建之中,而这个小碗始终陪伴左右,“由北而南,在昆明过了八年,由南而东,过苏州住了三年,又由苏州转北京,搁倒这个鸡翅木书架上,相对无言。”张老师将沉没于沈从文日记里的点滴感触剪辑成一首名为《豆彩碗》的诗。课堂上又有多少人亲眼见过这只豆彩碗呢?然而它从此成为我们眼前手边的温柔幻影。记得那首诗里写:一切生命存在都如此隔离,又如此息息相关,如此息息相关还是十分隔离。这是怎么回事?
读《珍物》,再次体会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息息相关”。书里有一篇,作家于坚讲述他的珍物陶罐。这个普通的印度水罐,他在旧德里的一个垃圾堆旁拾得,经过三个海关捧回昆明。读来不禁莞尔,于坚的陶罐与沈从文的豆彩碗,隔着时空遥遥呼应。物的背后,都有一位懂得识别故事的人:“我早就看见过这些水罐,红陶的,表面刻着古代传下来的波斯风格的花纹。需要多少时间,才做到这种形状。在其最初泥巴被捏制之日,也许曾经是某位工匠心目中的最美。作者匿名。它已经超越了美,成为一个物件,敞开在生活中”。
当代中国文艺界一百位富有个性和卓有成就的艺术大师,回望生命中最为珍贵的记忆和物品。一篇篇珍物纪录为我们呈现众生百态、万象流转的生活世界。现代人表面上为之追寻的、奋斗的、劳心的世界是热热闹闹的,而心底真正的牵挂与渴望却隐而不宣,甚至连自己也不甚了解。一件件珍物的梳理,像在重建一个日常世界。将早已存在于你生命中最真实的日常生活当作一份礼物重新送到你面前。
全书分成五辑——唤醒:时空隐语;印刻:光阴迭变;传承:家的秘密;追寻:光耀生命;灵犀:人生旅伴。它们记录了不同领域的艺术工作者的珍物故事,有着不同的探索重点,又由一条线索串起,这条线索便是时间,像《虫师》里隐秘而闪耀的光河,将一百篇珍物故事串联成沿岸风景,无数扇窗户打开,可见闪烁着斑斓星光的生命记忆。我们在时间里会游离不定,会成长、会衰老也会疲惫。此时狂热的事物,走过一段岁月再回望,回忆会慢慢客观,记忆里的“我”似乎也成为客体。人不由自己掌控,而物忠实得多;人会为自己找借口,而物更真实地表达。将当下瞬间的幽幽万古之情凝入珍物,才真正是时间的琥珀。
还有一类珍物,很粗粝,也不特别具有日常性,然而其中寄予更广阔的时空。物与人,相互陪伴,又各自放生。吕永中的珍物是汉瓦,“雨水沿瓦面缓缓倾泻,挟带着浮尘瓦砾,又回归土地”;叶放的珍物是一块玉化石,“原本是一棵树,遇到自然灾害埋在地下,经千万年后变成石头,木头的纹理仍清晰可见。流出的树胶,转变成了玉,交缠其上”;又一山人的珍物是拾荒而得的垃圾,如洋娃娃的手臂、银色蛋挞锡纸捏的鱼、荷叶饭余下的叶……它们被赋予飘零的诗性。“这些物件经历拥有失去,又再裹挟浮尘,在路途与人相遇,人生百态的气韵皆隐匿在这形态不一的细微处”。黄怒波的珍物是海螺石,它是一种海洋类古生物化石,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中,从远古海洋跃入陆地最高峰。海螺石伴随黄怒波艰苦的登山岁月,也启发了他的生死哲学:“生命在时间中消亡,残骸却在地质变迁中永存于灰岩或页岩中”。他说,“真正步过峥嵘之途,才懂得什么是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东西。”这一类珍物,当它们流转到主人的生命中时,已经拥有了很老很老的灵魂。人未必是物的主导,物也牵引着不同时空的人。
我也有过一个收藏盒,收藏着一些细碎的过往,大多是书信与卡片。记得刚上大学的圣诞节,斗胆和朋友在冬夜里走很远的路去庆祝。走完一条空旷的北方大道,龙湖大桥寒风呼呼的。一路都很荒凉,终于在大桥尽头,出现一家小饭馆,这家饭馆做过路生意,客源稀少。当时进去,店内没其他客人。我们欢欣鼓舞地饱餐一顿,要了一瓶白酒,酒未喝过半,阔气地塞回给老板,说下次来继续。再路过那里,饭馆已经拆了大半,只剩下几堵残墙与废墟。带了点凭吊的心情,我从那片废墟里拾回一块石头,它本身没什么特别,模样嶙峋,捧在掌心,五指刚好能够微微蜷起。接下来毕业、读研、工作,居住地点来来回回,这块石头很长时间被我保存在收藏盒里,因它的加入,盒盖一直关不拢,像半张开的嘴想要说话。又不知哪一次迁徙时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断舍离之心,将这块石头丢弃了。盒子从此闭拢,瞬间沉寂下来。直到翻起这本书,我莫名牵挂起那块石头的命运,它原本和友辈们在一处,可惜被半吊子主人妄自拾起,无才可去补苍天。我前两年重回故地,拆掉的饭馆早已翻新,如今已是迎来送往的热门餐饮地了。当年躺在残墙边的石头们应该还留在原地,只有那一块属于我又不属于我的,还有着它未尽的征途,说不定在参与某次造山运动呢,在经历它新的造化与新的相遇。
《珍物》读后感(三):2017.11.6图书馆借到
又读一次,在早班动车上。开篇王澍的《钟繇字帖》就很喜欢,写了他的练字经历。
许多有历史感的小物件,更多是好奇它的来历。比如纪晓岚的笔筒,底下刻着“一生伴我”,比如羊头瓦房,看起来就爱不释手,比如光绪年间武岩茶,装着的木箱子就显示出了年代。
阮仪三老师收藏的新制蠡壳窗,不知道杭州孩儿巷九十八号古宅有没有保护下来。释宗舜买下的民国手抄《华严经》,只有序言和题字留了下来,二十七册经书消失了,但态度超然,“出家人,东西丢了就丢了,不必念念叨叨的。事情因缘而现,因缘而逝,缘聚缘散都有定数。”
单锋剑则讲了北京混混消失的规矩,和消逝的年代。
《珍物》读后感(四):物中有忆
那本书里写了三毛自己的一件件小收藏品,没有太珍贵的古物,但每一件都有来历,都有故事。那时三毛的文笔已臻化境,所有的藏品,所有的故事,都平平写来,没有传奇的味道。但总留有韵味,淡而弥长。所以直到今日还记得这本书,以及书里写到的好些物件。
看到这本《珍物》,又让我想起了当年那本《我的宝贝》。那是三毛一个人的宝贝、一个人的回忆,而本书则是许多人——看目录里的那些名字,有作家、演员、歌手、舞者、设计师——每个人的一件珍物,每个人的一个故事。物未必珍,但回忆总是带着的牵绊,牵绊着不再回返的往日时光。
《珍物》读后感(五):最珍贵的是文化与人心
什么是珍物?按照字面理解,应该就是珍贵的物品。那么,珍贵的物品是否等同于值钱的东西,比如黄金钻石、香车宝马、别墅地产、古玩字画,等等,如果从金钱和商品价值的角度去衡量,不能说不对。但我相信,绝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会认同这种珍物观。即便是稍有教养的引车卖浆者流,可能也会说:黄金有价,情义无价。因此,所谓珍物,就人文与文化的层面而言,应该是与我们的生活过发生紧密的联系、甚至决定和改变了我们的人生道路;记载了某个特定年代的情感记忆与历史风云,映照了社会发展与生活变革的私人物品。也许其微如草芥,但对特定的人物而言,却具有无尚的价值。上海译文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珍物》一书,所记录的百位名人各自不同的珍物故事,就给人以这方面的启迪。
中国现代历史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有一段世界近现代史上少有的礼崩乐坏、文化沉沦、人性蒙垢的岁月,不堪回首,发人深省。中国美院院长、画家许江的父亲是名教师,却在1960年代就被剥夺了上讲台的权利,即便如此,他仍然异常认真地坚持编写讲义,梦想着有朝一日重上讲台,解疑释惑,授课育人。然而,“文革”爆发,他的讲义一半被炒走,一半被一位青年教师拿去。父亲不甘心,写信给那位远在福州的青年教师,想把讲义要回来,因为讲义就是他的生命。学者陈嘉映文革中没有读到什么书,但求知的火苗从未在心中熄灭,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走进旧书店,发现了当时在别的地方根本看不到、或者被禁止的原版外国经典作家文集——《歌德选集》、《席勒全集》、《托尔斯泰全集》、《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等等,他欣喜若狂,倾囊相购。然后就背着设法弄到的德语教科书和几本原版诗集,踏上了去内蒙草原插队落户的艰难旅程,也在坎坷的岁月中迈开了日后成为一名哲学家的第一步。诗人严力“文革”中在北京第二机床厂当学徒,与同宿舍的印尼归侨郑振信结为好友。两人某个晚上在宿舍中抽烟喝酒,酒酣耳热、放怀畅言之际,郑振信信手画下了一张在当时堪称惊世骇俗、在今天看来具有印象派画风的水彩画,大胆表达了那个特殊年代的年轻人对爱情的渴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可见,无论政治如何高压,环境如何悲摧,人性的光芒依然会顽强地闪耀,它们或表现为对文化的坚守,或表现为对知识的渴求,或表现为对情爱的憧憬。这也是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历经五千年风雨而不倒,生生不息、浴火重生的关键所在。
中国文化传统的博大精深、灿烂多姿,还表现在它对一代代人的滋养和哺育,而且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大概就是李泽厚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化具有“实用理性思维”特征的体现吧。本书中不少篇章即是这方面的生动记述。著名建筑设计师王澍从他收藏的一本钟繇字帖引开去,讲起他小时候在唐山大地震的防震棚里苦练书法,每天走三小时的路去西安碑林博物馆默读唐碑,以及对书法精神的领悟如何影响到他日后的建筑设计;台湾《汉声》杂志创刊人黄永松在贵州山村看中了一位老太太的蜡染围裙,老太太从舍不得到同意卖给他,但剪下了一小块,尤其是她的话“我把身体给你,灵魂留下来”给他带来无比的心灵震撼;建筑师张波在洛阳搜集到了一块汉代的羊头瓦当,精美绝伦,珍贵自不待言,既让他一下子感到自己与两千年文化历史精神上的联系,又体会到了尘封久远的年代那特有的富足、优雅的生活气息。饶是种种,揭示给我们的是,中华文化传统几千年来润物细无声地培育了中国人特有的审美观,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如何不使之断裂,传承、弘扬、革新、光大,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并且重视的问题
书中,百位名人讲述和回忆的每一件珍物都配有精良的摄影图片,光影细节的真实呈现之间,举凡金宇澄的史密斯船钟,樊锦诗的姐姐手织毛衣,陈丹燕的新天鹅堡木雕,张军的海燕牌旧收音机,欧阳江河的孤岛碟片,都能让我们依稀触摸到光阴流过岁月那隐含的记忆的深度、文化的维度、情感的温度。图文并茂,相映成辉,“珍物”的定义由此跃然而出,不言自明。
(此系本人原创作品,未经授权或许可,不得转载,否则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
《珍物》读后感(六):珍物,是有用心活过的证明
有幸来过世上,在时间与空间里容下一个小小的个体,又在这小小的个体的生命过程里始终夹带着一件重要的物件。珍物,是用心活过的证明。
建筑师马岩松的珍爱之物是下过雨的胡同里随处可见的苔藓,因为“有一种很生活的感觉”;作家金宇澄的珍爱之物挂在他家客厅,发条一上,就开始走,滴滴答答声里,回到当年在钟表厂里的日子,师傅搬进一支东德“船钟”,世上有这样一种物事,“即使船身历经超级风浪颠簸,摆轮一直保持水平运作,相当稳定”;历史学者葛剑雄的珍物是一本名为《中国人口发展史》的书,那是他的第一本书,特别之处在于,这是他用四通电子打字机写成的,那时是1988年。……一百位文艺中人的珍物,正如序言作者李宗盛所说“没有一样是世俗见解所谓的价值高的东西”。灯光下看是人物小传,是你所知道或不知道的谈资或别裁。关了灯,捡拾,回想,是我们都曾经历过的失去与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