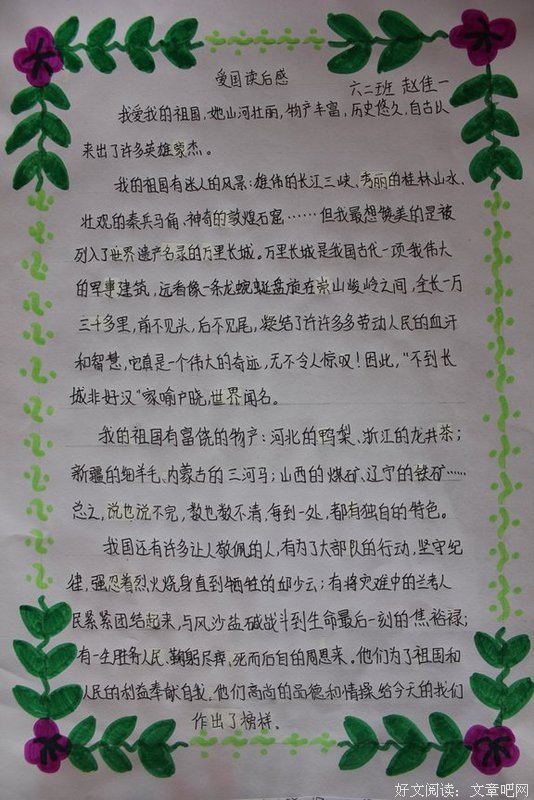《从今以后我叫丁》读后感10篇
《从今以后我叫丁》是一本由阿纳托尔·盖斯丹著作,33.00元出版的2012-9图书,本书定价:211,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从今以后我叫丁》读后感(一):一个法国传教士眼里的中国人
1923年:电话线已经架好,但因为没有钱,所以并没有利用。人民的民族自尊心非常强烈,不愿意追在外国人后面借钱,也不愿意让他们管理线路,索性就把它人在一边不管,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1928年:今年是中国的“1789”年,一切都将动荡不安。犹如我们居住在另外一个国家。我们将不再有同样的自由,革命者憎恨我们,很有可能,不到五年我们就会被赶出中国。
1929年:全中国各地,或者说,几乎是全中国,都在打仗。
1930年:欧洲报纸可能没有讲,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占上风。他们占领了中国南方四省的大部分地区。江西、广东、湖南和湖北。和别处一样,他们强烈反对宗教,烧毁教堂,抓捕传教士,迫害基督教徒。
1933年:中国的领导人非常聪明,自知不可以与经过充分准备的强敌硬斗,但又要不丢面子。受gcd人鼓动的大学生则不惜任何代价要求抗战。我们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看来要避免战争似乎是很难的。
1935年:许多人逃荒去了满洲里,到日本人修建的铁路上做工。 日本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别的地方到处生意下降时,而他们的营业额在上升。这是由于劳动力太廉价了,没有人能与他们竞争。现在,日本人把中国紧紧地勒在他们的网子里。
1948年: 我要十分认真地说,极有可能在二十年之后,中国人会像现在的美国人一样对我们发号施令。他们拥有一切:广大的人民群众,大川江河。我们的塞纳河与之相比,就成了一条小河。他们还有丰富的煤矿和铁矿。目前,他们所缺少的是团结和组织。而现在,则是中国人第一次团结起来走向正规。
1954年:我们这里对神职人员给以很多的自由。
《从今以后我叫丁》读后感(二):学习汉语的吐槽很有爱
一位属猴的法国神父,虚岁三十七开始学习汉语,我也默默的试了试“自始至终”这个词,何止是考察外国人啊,念标准了那妥妥就是普通话最标准模式。
关于这个词,神父的描述是:必须巧妙地把舌头贴在上腭才行,并让人听到某种摩擦音。这有点儿像妈妈呼唤小猫咪,最后的“终”字,要想发音完美则要利用鼻子的上半部位,像是感冒时的鼻音。。。。。。可爱的神父!
浓烈的感情并不定会短时间内爆发才会有感染力。书信中对于母亲的去世,描写总是不多,但是母亲过世后的节日信里情不自禁第一个想问候依然是母亲。没有过多悲伤和眼泪的字眼,合上书却想流泪:最亲近的人离开,影响的也许就是以后全部的人生
《从今以后我叫丁》读后感(三):一个神奇的法国人
首先是在网易读书频道看到的贺卫方老师、雷颐老师做的一个关于这本书以及20世纪来华传教士的一个访谈后才关注的这本书。两位老师谈到的书中的内容引起了我对这位“中国最后一位传教士”的好奇,看了书以后,确实有两位老师所言的问题,涉及到的“大事”太少,而更多的是一些温馨的家人间的亲情和风土人情的描述。
如果从史学的角度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我读后,却有一种意外的惊喜。人说,文如其人,看了这100多封信,我面前的丁是一个很纯粹、随遇而安、会从周身的人与物中得到乐趣,用现在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能自洽的人。离别、陌生环境、物质生活的极度匮乏、年老、死亡,等等,都不能成为他乐观生活的障碍,甚至他从中找到乐趣(这里用找到并不合适,因为他不是找,不是发现,而是这些乐趣像空气和水一样围绕着他,在他周遭自然流淌)。旅途30多天即使晕船也会在颠簸的餐桌上写下沿岸的美丽风光和不同国度人物“素描”,红海沿岸的人如何个个都是“大说客”,向客人兜售商品。谈到母亲从法国给寄来的包裹,他快乐地分配各种物品各做何用,甚至捆包裹的绳子也要派上用场,因为,这是亲爱的妈妈寄来的。他欣喜地描述孩子们在院子里洗头、编辫子的场景(有照片为证)。冬季工人们挖冰,他会细心地询问这一周工作工人得到的工资,并与法国工人工资、物价进行对比。夏季的北方,炎热无比,他幽默地形容:我们日夜都在淌汗,就像小黄瓜泡在了醋里。讲到中国人的幽默,医生兼开棺材铺,医不好病不收钱,但可以卖棺材,所以,无论怎样都挣钱。这样的描述比比皆是,令人时时欣慰,时时感叹,又时时哑然失笑。如果这是一篇写于当代的作品,我们也许不觉得什么,可是它写于将近100年前,作者是从欧洲精致、富裕生活中一下子到中国落后、贫困、肮脏的环境下,没有落差,无须准备,好像无缝对接。真令人惊奇和感叹!如果这不是一个对自己的未来有全部的把握和预期,准备好了迎接一切的人怎能做到?
他从来没有惶恐,也从来没有后悔之类的情感,只是接受,欣然地接受,全身心地拥抱这一切。即使我们说这是一个宗教人士的奉献也不能全然解释这一切。作者从34岁来到中国,88岁高龄去世,晚年很像一个中国乡绅,很多与学生合影的照片,白胡子,着长袍,总是给镜头右侧脸……真是一个神奇的法国人!
《从今以后我叫丁》读后感(四):一点分享
塞得港这座城市像是从苏伊士峡谷中神奇地开凿出来的,全城都是码头和锚地,住着将近四万居民。这座城市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新奇,以至我一整天在这里散步,都不会感到乏味。我们意识到已经到了埃及,到了非洲大陆,看到了全新的风俗。孩子们那件简单的上衣一直垂到膝盖,男人戴一顶红色的帽子,是平顶圆锥形并且带穗的,周围还缠上一条花花绿绿的并不干净的头巾。大部分男人穿着一件白色或蓝色的薄布衬衣,常常是颜色杂乱,红白不分明。也有很多男人穿一件小外套,却配上一条短裤。妇女们则戴着黑色遮头巾,还用一块紫色的织物吊在眼睛下面,一直超过她们的下巴,一种装饰着螺旋形流苏的木块遮掩着她们的鼻子。你们可以想象,这全套的装束有多么奇特,是不是令人发笑?
我还看到,一头骡子在拉着一辆有轨车。检票员是个年轻人,他穿着一件垂到脚跟的白色衬衣,一个黑色的售票袋斜挎在他的肚子上。远处有无数个黑人孩子会把你团团围住,他们带着刷子和鞋油。你只要一伸脚,他们就会给你擦鞋。我们说:“不需要。”他们回答:“先生,没多少钱。”
那么多的阿拉伯人带着他们的商品大举进入到船上。有扇子商人、书商、卖卡片的、卖珍珠项链的、卖地毯的。他们把甲板摆得满满的,用不可思议的大嗓门儿吹嘘着自己的商品。船上的男人们挥挥手打发走了他们,而在女士们那里,他们可以得到赚钱的机会。同一个小商人问了我一百多次买不买他的明信片。
※ ※ ※
早上有条好消息,左船舷处出现了岛屿!所有乘客立刻奔过来看。的确,我们看到有个小岛在我们视线里,远看只有手绢那么大,绿油油的!要知道,这是从马赛出发以来,我们第一次看到绿色。小小的岛屿上耸立着椰子树,长长的树干,树顶上还飘着一缕缕清烟,这说明岛上有人家!整个岛屿被树木覆盖和遮掩着,但看得见有灯塔矗立在绿岛中央。这突然出现的美景让我们消愁解闷,成了各式交谈的主题。
昨天,我未能讲完在科伦坡游览的见闻。今天接着写,大厅里只有我一个人,船在左右摇摆,晃得很厉害。这里的房屋、居民、习惯,都和我迄今所见的不一样,我对这一切都感兴趣。这座城市的欧式大楼大多是赭石色的,因为白色会炫目伤眼。道路用当地红色碎石铺就,人们穿的衣服很鲜艳,到处是红色。在东方的强烈的阳光下,这一切混杂在一起,给人极强烈的印象。
科伦坡是座很奇怪的城市,房子都是紧紧地挨着的,寸土寸金,中间大片的空地上种着棕榈树。还有一个大湖泊,沿着湖边有许多茁壮的树木。从有轨电车上可以瞥见当地人在湖里洗澡,远处有一排破旧的房屋没有楼层,房门都敞开着。一些小货摊摆在门前的街上,也有特别小的商铺。到处挂着一簇簇香蕉,还有瓶装苏打水在陈列着。男理发师在给客人剃头,人们就蹲在自己商品的中,滔滔不绝地吆喝着。真难以相信,当地人都是大说客。
我们在青枝绿叶覆盖着的美丽的小岛间穿行,时而也沿着突兀的峭壁前进。初升的骄阳辉煌壮丽,阳光照耀着天边的云彩,红彤彤的,有些云朵酷似一缕缕融化的黄金在流淌。汽艇在绵延开阔的泊位间穿梭前行,总之,这里景色壮丽。远处,广阔无垠的港口深处,大轮船在进进出出。我们到码头了,登岸了!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这个东方民族,我以为走到了东方的尽头。因为在我看来,新加坡其实就是一个中国的城市。
※ ※ ※
新加坡传教团神父的精心安排使我们非常感动。多亏为我们提供了专用的小车,我们才能立即浏览这座城市。我们经过了中国街区,看到了不同于我们的穿戴人们,以及他们头上的尖顶帽和后边的长辫子,这绝对就是天国天国,西方人过去对封建时代中国的称呼,也称中国人为天国居民。--译注的居民啦。到处是商店,门前有许多铭文题词和广告海报,全都使用中文。这里的人们好像都在干活,没有人闲着。
今天我们游览了香港。这座城市里的路都建在陡坡上,走起来极不方便。我们几乎不是在走路,而是在不断地爬坡、下坡。科伦坡的人力车在这里不见了。于是,我们只能乘缆车,让它载着我们,顺着陡坡将我们带到了令人发抖的丘陵高地。香港就是在这块丘陵上建立起来的。在半路上,我们看到一队队工人在运沙、运砖或是灰浆。这儿的房屋就是这么建造起来的,一切都是靠人们肩挑手提。
我们终于登上了山顶,阵阵凉风扑面而来,站在五百米高处,面前的风景极美。游人说:在这里可以了望到世界。往远处看,诸多的岩石像山脉一样拔地而起。这是一个杂乱无章,但又非常稀奇古怪的小岛。
这座城市有25万居民。我们从山上清楚地看到了植物园,也看到了法国领事馆。我们沿着令人发晕的陡坡走下来,参观了植物园,游览了最大的商业街。
商店里摆满货品,琳琅满目,东西丰富但缺少情调。我们又到了菜市场,人们所能想到的食品,在这儿都能找到:肥母鸡、兔子、鹌鹑、鲜肉,一串串葡萄,还有长得和法国不一样的梨、菠萝、香蕉、柚子、石榴、荔枝,几乎什么都有。我还需要很长的篇幅才能把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化妆品和水果的种类写给您。
※ ※ ※
亲爱的母亲:
我已经到达中国了!四名神父在上海码头上等候并迎接我。他们帮我提箱子,替我照看行李,总之我什么都不用管。我感觉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他们带我来到驻地。中国人都看着我,看到我头戴帽子身着黑色的教披,表情有点惊奇。因为这儿的神父们穿的都是华服。顺便告诉你们,那华服很好看又很方便,以后我再给您详细地描述吧。
在驻地,大家为我们开了欢迎会,热情接待我们。我收到了我的上级、贝克尔神父的一封信。他向我表示欢迎,并指定了我的中国名字。一般来说,在中国名字里,总是设法保留欧洲姓名的一个音节。
我的名字是这样的:
丁(家姓),鸣(响声),盛(昌盛,繁荣),(鸣盛是我的名字)
从此,在中国,我的名字叫丁鸣盛,字:盛赋
午饭时,给我们上了啤酒,非常好喝,可以和里尔的任何一种啤酒相比。还有米饭和其他食品,愿意的话,可以吃面包,都很好吃。这里驻地的房子已经建好了,家具很简单,墙是用石灰浆刷白的。这房子很大,足够宽敞。外国神父们贪婪地向我询问着他们国家的消息,也问了我们很多关于法国的事情。
晚饭后,我们参观了一个中国堂区的教堂,那是个很老的教堂,曾被改造成塔楼,后来又改回教堂。路上我们经过了一些拥挤的街区,有些街上的摊位和对面摊位之间的距离十分狭窄,庞大的人流在那些死胡同里走动,异常拥挤。看到这种状况,我只能和里尔空地上的集市比较了。
负重的劳工们在人群中用“噢!呵!”的喊声互相提醒着,用力地喘息着。这里的某些气味最令人难受。怎么说呢,老实的中国人民,他们没有卫生间。我们看见那些端庄的妇女就在您眼前清洗。哎呀,还在您鼻子底下冲洗便盆!但这也无所谓,会适应的。我们还看见,到处都有很大的中国字,用黑色的或是金黄色的写成。
昨天早上,我在驻地五点钟起床,并很快整理好了床铺。床铺很简单,一个小床垫上铺着床单。睡觉时,这里也不像在法国那样把被子的一端紧紧裹在床垫下,而是把被子放在自己脚下向里面叠一下,再拉到身上将左右两边裹紧。我还学习用中国的方式洗漱,也就是用热水洗漱。前一天晚上,有人给我送来一个大白铁盒子,里边有个容器是装满热水的。铁盒里有个盛水的容器,那周围裹满着糠屑,是用来防止热水变凉的。你们可能想不到,这铁盒子里的水到转天还是热的。
※ ※ ※
我来继续叙述星期六这一天的见闻。我们在街上遇见了一大队人,他们头上戴着礼帽,上面镶着红丝条,服装颜色也很鲜艳,以红色为主。大多数是两个人一伍一起走,有的背着装酒菜的盒子,有的抬着桌子,还有人举着铭文字牌。原来这些人组成的队伍是专门给人送礼的!那个被送礼的人或者是位有名望的人,或者是做了什么好事的人。这支队伍很长,足有120人。我们听说,一般来说,收礼的人总是高兴地收下某些礼物,把其他的留给赠与人。
※ ※ ※
我在一家客栈里给您写信。这个小客栈的顶棚、墙和地面都是泥土建造的,房顶是由三根木头撑着的草帘。从客栈的大门进去,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大院子,四面都有房子但没有上下层。我们的三辆大车停在院子里,六头骡子在吃着草拌豆子,六名车夫在喝茶。我趁此时间给您写信。我们已经跑了四个半小时。我们似乎走的不是大路,而是压出两道车辙的乡间曲径。我们在车上晃晃荡荡,坑坑洼洼造成的颠簸很容易让人在陆地上有晕船的感觉。我看到远处一块巴掌大的平川,乡村里的几个小房子挤在一堆儿。再远远望去,小土岗上飞着几只麻雀,又有几只鸽子从那里飞起,小黑猪自由自在地在村子的街道上溜达。年轻人背着一竿长秤和沉重的大包袱在赶路,默默地奔向大城市。人们好奇地看着我们,一语不发。天寒地冻,而奇怪的是,到将近十点钟时,升高的太阳又变的暖融融的,好似阳春四月,很多中国人在晒太阳。
您看,当地的文明和习俗在紧随着我们:我们刚走进客栈的院子,两个店伙计就迎上来,他们递烟,送糖果、花生和柿子。我谢绝了,然后坐到桌前准备吃饭。饭菜虽不那么丰盛,但我的食欲仍然很好。我还看到这个旅店的招牌上写着:《穆斯林客栈》。
※ ※ ※
我继续用铅笔来描绘昨天的事情。这里的人们为了主教和我们的到来,忙得有点儿颠三倒四的。我写完短信,坐到桌旁,有人就给我们送来茶水。红色的泥砂壶,三个瓷碗,还有三个茶托,每个人还另外有个吃饭的碟子。最后又上来八、九个小盘,都是做好的菜:有油煎小鲤鱼、肉糜、凉的淹白菜片、茄子泥、几片夹心鸽肉。还有其他菜肴,但我忘记了菜名。所有的菜都摆在桌子上,让人感到有很多的东西要吃。然后有人给你送来一大碗汤,是粘稠的,汤里有一多半是小小的扁豆和面条。喝完汤,晚饭就算结束了。您会理解,对我们欧洲人来说,吃过肉和菜再喝汤是很困难的。我们往往只是沾沾嘴皮,而留下大半碗没有喝。
※ ※ ※
比起上午来,这会儿我们路过的村庄多了一些。我们看到的砖房不多,然而建造得还相当不错。房屋不分上下层,但是漂亮的屋顶优美地挺立在高处。砖是浅棕色的,挺好看,表面也比我们法国的砖光滑。用石灰浆描在墙面上很细的黑色的线条是那么的整齐。不同大小的墙砖交错着砌在一起,经过精心的计算,形成了既简单又好看的图案。
※ ※ ※
现在是冬季,中国人往往没什么事做。于是,他们十人或十五人凑在一起,在一排排房子前面晒太阳。男人们穿着蓝色的、宽大的棉布裤褂。妇女的穿着方式和男人一样,只是服装样式丰富些。有钱人家女人穿的颜色尤其显眼,上衣下垂到小腿,并且左右两侧在下边开叉。小孩子们的衣服颜色鲜艳,例如:袖子是浅绿色、裤子绛紫色、坎肩是蓝色的,整个看起来颜色搭配得很怪。
田野上,所有的牲畜都自由自在,骡子、小牛、猪、驴子都在地里溜达。到夕阳西下时,这些牲口又老老实实地回到它们的饲养棚里。只有绵羊是由人们成群放牧着。这里村庄之间没有树木,只是村庄周围有几行树,多数是些梨树和枣树。葡萄的成长情况和咱们那儿一样,不过到了冬天,人们会把葡萄架全部埋在土里。村庄里除了果树之外,再没有别的了,看不到柳树和小榆木。因此,当你看到果树时,你们可以说:啊!这儿一定有个村庄。
人们常常还会看到一些用泥巴盖着的锥形大土堆,那里面其实是一堆高粱杆,是人们冬天当作燃料用的。所以要用泥土盖起来,是为了防止坏人纵火。
※ ※ ※
一天晚上,我们穿过平川和村庄,一直走到六点半。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我们把车停在一家客栈的院子里,那里已经有八辆大车了。于是,我们立刻掉进了赶车人和客栈伙计们的喧闹声中。有人告诉了我们吃饭和睡觉的地方。在室内一个方块地上,有两张大桌子和两个又高又窄的木板凳。屋子的墙是用泥草抹的,屋顶的木梁黑乎乎的。这就是我们的饭堂和里面的全部家具。另一房间通过一个开口和这个地方连接。因为没有安装屋门,我就把这个开口叫作门洞。里间屋里有一个砖砌的很大的炕,高0。5米,占了房间的三分之一。您可以躺在那上面,打开席子,铺上被褥,这就是一张现成的床。
※ ※ ※
您会说没有房门的房间会冷吧?不冷。我们把所有的衣服都盖在了身上,这样既暖和了,同时还保证透气。您问屋子里有光亮吗?有一盏油灯,因为这里缺少玻璃,油灯会生成更多的烟。但是黑油烟没有毒。这里也没有玻璃窗,人们不了解玻璃这种东西,所以糊窗户的油纸会很有生意。
※ ※ ※
我两点钟就起床了。五个赶大车的人在门前大声嚷嚷,询问是否马上出发。天还黑着,很冷,不过我穿的很多。坐在车上,用厚硬的被子堵在车棚前面。这一路没什么特别的,只是路很长。从凌晨三点走到中午十二点半,一直走在沿运河的路上。这条大运河连接着北京和南京,是为了给北方各省运送大米才开凿出来的。为了不妨碍船只通过,河上不准许修桥。因此,过河的牲畜、人和车不得不乘摆渡。人们趁机拍打一下身上和鞋底的泥土,喝点儿茶水。看起来,这地方是个重镇,我们过河时看到两名专区公署的士兵在那里吹小号。在这个很少见到西方人的地方,我们听到了熟悉的曲子《爸爸,今天是你的节日》,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又走进一家客栈,这一家比前面的那几家客栈小很多。客栈老板的家人和朋友都出来了,他们都想看看西方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怎么吃饭。吃饭时,他们给我们上了鸡蛋、鸡和鱼,尽管感觉油腻,但还是很好的一餐午饭。
饭后我们很快起身,高兴地坐上车又出发了。大家都知道,我们晚上要住宿在范家圪瘩的寓所,为此还要走一个半小时。路上,我用目光在天边搜寻。突然,我瞥见在一丛树林后,在一个钟楼上,也许是在一个有雕刻图案的人字形屋顶上,发现有一个小小的十字架。我为此十分地高兴,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北方看到天主教堂。
……
《从今以后我叫丁》读后感(五):超越时空的善与美
1907年10月7日,年轻英俊的34岁法国教士阿纳托尔.盖斯丹 (丁神父)放弃了他在比利时的教师职业,在他父母位于法国北方小城里尔的故居告别了众亲人,于10月13日在南方的马赛港登上“太平洋号”邮轮。海上行程一万七千公里,历经 33 天,于1907年11月15日到达中国上海。从此,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54年的传教生活。
从煌煌青年,到老耄,漫长的半个世纪,远离故土,远离亲人,从欧洲精致的生活,一下子到20世纪初贫穷、落后的中国农村,这种巨大的反差是他始终要面对的,尤其是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很详细具体地描述如何从最初的学习汉语,接触质朴的中国北方老百姓,到与他的“教民”融为一体,和他们吃同样的饭,穿中国式的袍子,拱手作揖,虚寒问暖;如何刚刚来到乡亲们中间闻到奇怪的味道,自我劝说:会习惯的,到看到孩子们因不经常洗澡脖子上的黑黑的泥痕露出的无奈的微笑;如何从最初看到的一张张相似无表情的脸,到后来真切感受到这张张脸孔后面的真诚、友善和信仰。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丁神父在八十多高龄时写给他的亲人的信中说:我现在真是中国人的胃了,冬天喜欢吃白菜和豆腐。此刻映入我们眼前的是这样一幅画面,一位身材高大的白须老者,安然地坐在冬日阳光照耀的屋子里的炕桌旁,如果不是他的高鼻碧眼,我们以为这是一位年迈的中国乡绅。简单、整洁的房间弥漫着一种宁静、祥和的气息,这是一种历尽沧桑后陶然自得的泰然。
这个画面不过是他进入八十岁,渐渐减少了工作后的一种状态,在这些书信里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他在中国华北地区很多贫穷的地方传教时,经历的艰难岁月:冬天住在没糊窗户纸的房子里,风吹进来,就像睡在外面,白天,靠在屋里踏步取暖。雨季,一头瘦弱的毛驴载着他在没膝深的水里艰难地行走,有时不得不徒步趟着水走几公里。夏天的华北,持续高温无雨,他幽默地描述到:“我们日夜在淌汗,就像小黄瓜泡在了醋里。”玉米面饼子、冷咖啡,水煮白菜,偶尔乡亲们给他吃上一顿有几块肥肉或几个肉丸子的饭,他会从心里说:这已经很好了。
他说,对一个传教士来说,上天堂是不需要豪华车的。
20世纪初的华北大平原上,少树缺雨,他在一篇篇日记里,记述着与当地百姓一样的焦虑和企盼,每天都在祈祷,快下雨吧,再不下雨老百姓都会没饭吃的!他在任丘待了很多年,与那个美丽的地方感情很深。在1932年9月23日的信中写到:“一次灾害蹂躏了我那可爱的任丘。本来,因为天气对庄稼很有利,热又潮湿,今年的收成被看好......在收割的前夕,大水吞没了那么好的庄稼。你们可以想象到,穷苦的人民有多失望啊!他们看着幼小的儿女们,自言自语道:‘这个冬天,我们给孩子们吃什么呀?”
他接纳他们的孩子,用从法国筹来的少量的钱办学校,他看到那些因缺食而黄瘦的孩子们在学校里2周就大变了样而欣喜;他也记述了他的教民们如何地爱他,几位赶了一百多里路来的教民,看到他咳嗽,说:神父冷,所以咳嗽。十几天后,他们送来了厚厚的棉被。在他进入人生的最后阶段,他写给家人的信中这样描述:他(主教赵振生)对我像一个宠爱孩子的爸爸。
我们在搜索丁神父词条时看到一篇记述丁神父的文章,其中讲到,一天中午,年已70多岁的丁神父路过某村,村民请他去家里吃中饭,神父说,吃过了。村民回去告诉烧火的老婆,老婆责骂他,这个时候,神父去哪里吃?快去追。村民追了一圈没有发现,想,神父70多岁的人了,不可能走这么快,正往家里走,发现神父在一处没有屋顶的破房子下在啃干饼子。村民又痛又气,说,您这是为什么呀?我们再穷也有您吃的呀!
每每看到这里,我都会落泪,这种水乳交融,是心与心的交流与碰撞。今天我们抱怨人与人之间冷漠,人们更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不考虑他人,难道物质丰富了人却更吝啬了?我们扪心自问:自己要多少才是够?拥有多少才能分给别人一些?物质上贫穷的人精神上也可以富足,物质匮乏的人也可以给与。互助互爱,是人类最可宝贵的品质,今天的我们更应好好珍惜。我们也欣慰地感叹,生活在一个世纪前的丁神父给了我们一个样本:不论生活在什么年代,在怎样一个环境下,他/她的善与美都是可以超越国度、超越时空光照后人、启迪后人的。
丁神父是独子,他的母亲和姐姐姐夫们非常爱他。临别的时刻到了,“大家聚在母亲的房子里说些别的事情,就是为了不流泪。”一封封跨越太平洋,行程一万多里,历时一个多月才能到达的信,传递着亲情和温暖。一代代,从与母亲、姐姐姐夫们的通信,到与从未见过面的外甥、外甥女的通信,亲人间血脉相连,是万重山水、几千、上万个日夜所阻挡不了的。亲人的容貌模糊了,但离别时候亲人的话语永远不会忘记;母亲去世了,我们还是她的孩子,她对我们的爱永远牢记。
丁神父在油灯下写下一篇篇日记时,不会想到你我此刻坐在书桌前捧读他写于一个、大半个世纪前的东西,所以,他的文字是真诚、质朴和毫无造作的,这也是任何今天的作家乡野采风、闭门修为、电脑前苦思所不能得到的。我们翻捡陈案,译者尺牍劳形,还原给我们一个世纪前的美文与情思,作为今人,我们读它,了解那个时期的历史、人文,满足我们对知识、信息的渴求,我们更能越过这些文字,去叹谓人类如何在艰难、匮乏的物质生活年代互相理解和扶持,走过属于他们的一生;去赞美亲人间血缘的纽带不因时空阻隔而灭失,相反,靠着回忆、祈祷和尺素传情,跨越半个多世纪而历久弥新。“让回忆与祈祷把我们聚集在一起吧。你们看,这一切都过的那么快!生活不过是一部较长的电影,而我们都是电影中的演员和观众,重要的是演好自己的角色。”
1961年,丁神父在中国辞世。他是留在中国并在中国辞世的最后一位外国神父。在他生病期间曾经精心照料过他的那些中国人,将他安葬在张庄教堂附近的山中墓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