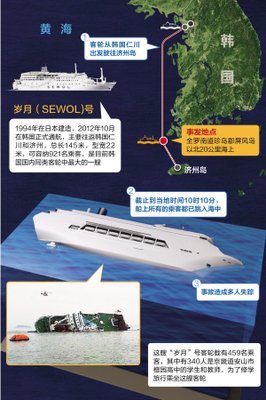《石榴的颜色》影评10篇
《石榴的颜色》是一部由谢尔盖·帕拉杰诺夫执导,索菲柯·齐阿乌列里 / Melkon Aleksanyan / Vilen Galstyan主演的一部传记 / 剧情 / 音乐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虽然对亚美尼亚还有这位诗人都没有了解,不过电影所流露的诗意,正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一种精神,我想说的是,即是这个世界不要一位诗人,也至少需要这种“诗意”,诗人、导演、音乐……正是这种精神的不同体现。
《石榴的颜色》影评(二):二维的电影
看电影往往不是个消遣,在无所事事睡觉前看上几眼,感觉至少缺乏尊重。什么东西都拉上梦的解析也未免太老土了吧。
在他的电影里人们都不说话,好象所有的都是无声的,都是聋子,哑巴。就像绘画一样,人们默默地相互注视着。在那些宗教浮雕中,圣母从来不和耶稣说话就像和天使们一样。他的电影更接近于绘画,他创造的是二维的世界,那看不到的第三维是靠心灵来传达的吧。
《石榴的颜色》影评(三):影像诗
苏联电影史拥有极为悠久的诗意传统,而两位同时代的集大成者―塔克夫斯基与帕拉杰诺夫却分别发展出了极端分裂的两种风格,与塔氏电影世界中蕴意神秘的流动诗意相比,帕拉杰诺夫表现了他独具个人化的静止风格,无镜头运动、少对白、平稳的构图、大胆先锋的色彩与达达主义式物象的并置,宗教主题与诗性的杂合辉映,他试图将片段的诗意进行拼贴,运用象征与隐喻的方式来还原诗文本难以具体括写的广泛意涵.
……
《石榴的颜色》影评(四):绝美的祭礼
在诗人的梦境里,吟游是一种最诗意的常态。而《石榴的颜色》便是这样一场关于吟游的梦境。作为谢尔盖•帕拉杰诺夫穷尽其身的诗电影杰作,本片无疑是前苏联光影圣殿中的一场绝美祭礼。在年幼懵懂的儿时梦境里,帕拉杰诺夫一次次将作为少年的自己投掷进须臾的光影洪流,那一刻,少年附首贴耳,倾听大地的诗句。时隔多年,他将诗人的时空与自己的梦境奇妙缔结,终于拍出这一部《石榴的颜色》。影片中,借助诗人之口,帕拉杰诺夫道出了艺术的真谛:一个诗人也许会死,但是他的缪斯不死。
《石榴的颜色》影评(五):这个电影very gay!
very gay是一种赞美!从心底的赞美!老实说,如果一个艺术家创作的作品不能获得gay的青睐,那么他就可以收拾收拾行囊准备退休了。
这部电影拍摄于1967年。在那个时代能拍出来如此惊艳的作品,真的是令人震惊。因为这部电影关于隐含的意味太深,如果不是对亚美利亚历史与文化背景了解的话,很难理解它的意味。但单纯唯美主义的画面就已足够了!真的是大师的作品。
顺便说一下,这个导演曾因为同性恋而被苏联当局在1948年判处5年徒刑,但关押3个月后就被释放了。
《石榴的颜色》影评(六):瞎几把乱扯
这就是电影语言。 小时候调皮的诗人有一个快乐的童年,神父给他文字书籍的熏陶;各种家庭节日仪式让他感到欣喜和好奇,这是一个无忧无虑的男孩纸。到了青年,他该结婚了,但是他却娶得是一个不爱他的女孩纸,然后他爹娘还去世了,不但如此,他妻子还弃他而去跟别的男淫跑了。他心灰意冷,人生已无留恋,他干脆就出家了。在修道院里,他敬爱的主教也去世了。人到中年的他,继续在修道院里清心寡欲,拒绝各种诱惑。最后在耄耋之年,他开始回忆自己的一生,那和父母度过的欢乐的童年。到死的时候,他才放下了他的妻子——他心爱的女人。她随他一起入土。
老娘只能帮你们到这里。
《石榴的颜色》影评(七):亚美尼亚式的“呼愁”与“规驯”
#电影笔记#
《石榴的颜色》是一部细思极恐的电影,它讲亚美尼亚的“呼愁”,民族式的悲壮和无能为力,全片没有一句台词,叙事推进全靠符号,若想理解须迈向诗的意境。导演帕拉杰诺夫是个意象选择的天才,象征丰收的水果也用作杀戮,无论是残忍又艳丽的石榴,还是有着宗教“圣血”意味的葡萄。
每一工种的人都在画面里各司其职,面无表情地劳作、纺织、战争、洗礼,机械循环往复,却又是如此仪式化。他们像木偶吗?可是却没有提线,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不需要任何压迫和惩罚,人们都已经是乖乖自我规驯的个体。所以,这是一个时代的安稳祥和吗,还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式的莫大悲哀?
《石榴的颜色》影评(八):有人说没有完全看懂,反正我是完全看不懂
看的很郁闷,戈达尔,大卫林奇,一些超现实主义的片算的上难以看懂了,但是大致也能知道看啥,但是这片到底看啥东西,非常的诡异。
内心戏!电影是用形象来表现的,最难表现的就是内心戏,会走两个极端,一种是平庸的类似戏剧的表现,用大段大段内心独白来说明;一种就是类似这片的表达形式,完全抛弃了电影的手法。很多地方换场剪接的也很跳越,突然出现一人或者消失一个人,打光也很平,没有景深,大段大段定位,演员面无表情,默片式样的字幕卡。
难道是导演故意抛弃了电影的表现手法,来凸显绘画中构图和色彩的表现。
--------------------------------------------------------------------
反正看了很多其他人的评论发现,“诗”这个字,已经成为一些人,不能表达自己意思的万能字了。
《石榴的颜色》影评(九):20110205
情节的推动用了两条线,明线的时间顺序使暗线存在的用意变得晦昧,暗线从“水”到“火”最后来到“土”的变化很有古希腊哲学的味道。水的特质是其自身的可塑性,它充斥了诗人的童年,导演费了很多笔墨去描绘曝书、沐浴以及清洗毯子,流淌的水布满了画面。火的特质更多的是其对外部的影响,它在诗人成年之时来到影片。字幕明示的流俗意义上的时间顺序很容易使观影者忽略“你是火”这一画外音,笔者亦注意到电影进行到此时画面中方出现红色。结合其游吟诗人的身份,导演要表达的是他在这一阶段的传道。最后一个“土”的环节是最难理解的,对应在流俗时间观上是诗人的老年。年老的诗人时时回忆起童年往事,此时非常有意思的一幕是石榴被碾出了红色的汁水,红色的汁水流淌着渗入了土地,同时电影进行到诗人的老年之后开始出现大片的黑色,笔者遂推断暗线的最后一环是“土”。“石榴的颜色”暗含的意义是诗人童年“水的特质”与成年“火的特质”在老年合二为一并且融入到“土的特质”中去,从时间观上可以理解为诗人在经历了“水”的童年、“火”的中年后来到“土”的老年并且迎来死亡,这里倒又有了宗教里“一体意识”的味道。
《石榴的颜色》影评(十):终于见识到闷片了
就是《石榴的颜色》,绝对是睡前的催眠片。
前几天每天凌晨睡前读一本催眠的书,作者把苏联5,60年代导演人才辈出的分成莫斯
科派和南方派,然后把Sergei Parajanov和老塔并列,打压倒雁南飞,士兵之歌这类的。
ergei比老塔惨的是他在政治风向一变得时候就被当局监禁了5年,其中一向莫须有的罪名
是同性恋。很搞。不过也难怪,他的片子被当局看来太邪教了,老塔至少还有个Ivan's
childhood挡箭牌。
片子的最后还是他的一个访谈录。。看上去像是解冻后西方记者搞得。
讲了一些基辅工作室(南方派)还有莫斯科电影学院的事情,不得不感叹只有计划经济
搞出这样的导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