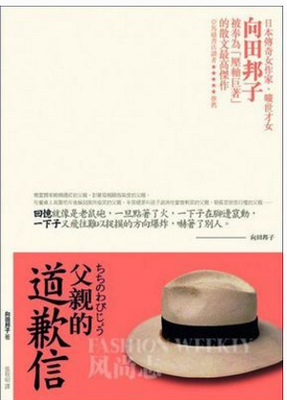天真随笔 || 我称父亲为矮爷
又一个罕见的天寒地冻。
而十年前的那场雪还盘踞在胸中,我顽强地躲避和堵塞它,竭力克服它带来的透心彻骨的寒冷和悲凉。十年之后,当我尝试面对那惨痛的记忆时,就下来了这场雪,历久弥坚,丝毫没有融化的迹象,但我不再感到那么尖利那么残酷。洁白的冰雪层层叠叠,仿佛是灵魂的伤口正在艰难结痂。我相信,这场雪是来自天国的信物,矮爷在催促和鼓励我,向前看,朝前走。
1
在我眼里,矮爷是个了不起的人。
我曾经是把矮爷和毛主席相提并论的。有一天,应该是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之后的某一天,我们江渡大队的基干民兵、社员群众和红小兵统统集中在小学操场上开会。我平生第一次参加如此盛大的集会,也平生第一次听矮爷作为魏书记发表讲话。看到矮爷站在台上的大红横幅下,我心里真是无比自豪和庄严,可是当矮爷一开口“社员同志们——”,我感到错愕,那声音好陌生,好遥远,特别是那种显得高亢的声调让我心下狐疑。后来我终于释怀,因为我听见了喇叭里的毛主席讲话的声音,听起来也是那么的高亢并且遥远。这使我更加坚信世界上只有两个伟大人物,一个毛主席住在北京,一个矮爷是我们家的,是我爸。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总是和毛主席在一起,被挂在家家户户的墙上,但我一直以为,这些长着奇怪的胡子和头发、真正凸眉凹眼的人都是毛主席的帮手或跟班什么的。我当时觉得矮爷了不起,肯定不是因为他是大队书记,因为他是被我们队里的人硬拉回来的,本来他在公安县三砖瓦厂做厂长,干得好好的,而他之所以会去砖瓦厂工作,“还不是他们把他赶走的!”我姆妈说,“现在大队里搞不好了,又叫他来捡烂摊子!”
那时我们江渡大队一生产队的牛屋旁边住了两个老太太,一个瘦小弯曲、满脸皱纹的是五保户张家婆,还有一个高大挺拔、满头华发、面如满月、眼如朗星的老太太,我们喊她付家婆,讲一口湖南话。人们都说付家婆是叛徒、特务,还有人传言,说听到她夜晚说梦话,喊饶命,甚至模仿她的口音,怪腔怪调地喊“打不得了——打不得啰——打不得呀……”。基干民兵们觉得这些就是她当叛徒的铁证,再开斗争会的时候,真的拉上了她。也许他们觉得老是斗一个四类分子桑自彬,再加一个赵地主,不过瘾,斗一斗这个当过叛徒和特务还很有架子的老太婆,也许更有味。但她并没有真的挨斗,只有那一回她站在了台上,在一溜四五个“地富反坏右”的边上,虽然也是弯腰垂首,但个头真高!不仅比其他挨斗的人,也比那些高举拳头喊打倒的干将们也高出了一个脑袋,并且她那抿着的嘴唇和白净的面容,似乎透出某种威严,让民兵连长、排长都有点失措,台下的社员也不给劲,批斗大会也就草草收场。
那时,我们家刚搬了新屋,我几乎每天都看见付家婆。她天天都去大队部,所以天天都要经过我家门口,我很喜欢看她那与众不同的样子,她也经常和我说一两句话,但我大多听不懂,听得懂的现在还记得,一句是批评“妹坨子呃,辫搭子梳歪咯”,还有一句是夸奖“妹坨子有蛮乖嘞,背得聒多语录啊”。一个暖和的上午,付家婆路过我们家时看见矮爷站在门口,她就过来了,很是恭敬肃然,说,她刚刚学习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想跟矮爷汇报一下学习心得。矮爷赶忙躬身还礼,说您家的水平我们哪里赶得到,我们要向您老人家学习才则是啊!有一回,我姆妈照例数了十个鸡蛋给我,要我去大队部换五角钱回来。刚走到大队部供销社,就看见付家婆从店里出来,用手绢包着刚买的几个鸡蛋。我估计我一到家就把这事告诉我姆妈了,因为不久之后,付家婆到我们家,硬要给姆妈五角钱,说是买鸡蛋的钱,不然她就把鸡蛋还回来。原来是我姆妈给她送了鸡蛋。几年之后,落实政策,付家婆要回长沙了,她儿子来接她时专门到我家来辞谢。我看到的是一个黑红脸膛的汉子,一件白衬衣硬挺挺的没有一丝折痕,说的是一口普通话。记得姆妈事后还跟我们说笑,说付家婆这个儿子不晓得到底是打铁的还是教书的!付家婆走时送给我们一大堆物什,说是做纪念,我印象最深的一样是一顶比簸箕还大的斗笠。多年以后,矮爷被调到乡卫生院工作——据说这是组织上照顾他的体弱多病——付家婆又托人辗转捎给他一个陶瓷暖壶。记忆里那个壶像一只超大的白色的胖头鱼。由此我断定,她对矮爷是相当感念的。
2
当年,我常常暗自着急,因为我姆妈好像专门要跟基干民兵对着干,对那些“四类”“五类”分子那么好。现在想来她也并不是故意的,扶持弱者是她和矮爷一贯的为人之道。当然,由于家道败落,她从幼年起就受人冷眼、吃尽苦头,这使她很容易和“四类”“五类”分子惺惺相惜,只是她的行为实在是给她自己和矮爷带来很多麻烦。除了付家婆,我们队里还有一个地主婆周家婆,也常来我家。我记忆里的周家婆总是拄着拐棍,颤巍巍地挪动小脚,她的头还不停地摆动,似乎每走一步都有跌倒的危险。她经常到我家来一坐半天,不停地说话,脑袋不停地摇摆,红红的嘴唇也不停地颤抖,也许只有我姆妈肯听她诉说,并且总给她冲甜水喝——如果没有糖就往开水里加半粒糖精。姆妈跟这些人来往密切,就有人说魏书记包庇坏人;也有人说干部家属的觉悟这么差,应该比旁人多扒点工分。我姆妈不理这一套。有一回的斗争大会盛况空前,姆妈看见主斗的人把捆人的麻绳先用水打湿,就十分气愤,絮叨着回家来了。不想她前脚进门,基干民兵后脚就跟来了,是因为捆人的绳子不够用了,来借绳子。我姆妈当然不借。不借他们就要自己找,不让他们找,基干民兵排长就说我姆妈“仗势”,自然是仗魏书记的势。我看见姆妈勃然大怒,满脸通红,捶胸挠头,恨不得要拼命又不知道怎么做的样子,只有喝他们走。民兵走后,姆妈余怒未消,从不说脏话的她一边骂他们是狗日的们,一边恨恨地数落起矮爷来,说:老子是说不该住这个狗×地方的!“这个狗×地方”就是在江渡大队一生产队的新街,我们是新街第一家,紧挨着生产队的大礼堂。姆妈说矮爷“抢积极”。当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公社规划了新的集中的居民点,但社员同志们的觉悟都停留在“搬一回家等于过一遍火”的水平上,没人愿意响应号召。矮爷是大队书记,显然得带头,所以我们是第一家建新房的,自然就建在大礼堂的隔壁了。那时,大礼堂天天开会,有的会矮爷也来参加,但斗争会从来都是基干民兵的兴致高、劲头大,社员群众有些是爱看看热闹,如果不是怕被扒工分,其实大家多半是懒得捧场的。矮爷从来就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斗争会。这也是有原因的。姆妈告诉我,搞“四清”的时候矮爷因为爷爷的“历史不清”挨了斗,后来又不晓得怎么又成了“保皇派”,被斗得更狠,架土飞机,站板凳头,他是实在过不得了才调去的砖瓦厂。记得他再次回到江渡大队时,有好些人一直送他到家里,帮忙运回了两脚箱告别留念的礼物,一脚箱是塑料封皮的笔记本,还有一脚箱的香烟!我还记得,当我们翻看那些笔记本上的题词签名时,特别是翻看晒在大簸箕里的那些新华、圆球、春耕等牌子的香烟时,心里的那个自豪感……(情感文章大全 www.wenzhangba.com)
3
矮爷让我自豪,我也那么想给他争光。这在别人看来未必不是套话,对我却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我六岁的那个夏天,矮爷用自行车驮着我到他此时工作的砖瓦厂去玩,一路上我都在引吭高歌。当时时兴的革命样板戏唱段,在矮爷的鼓励和提示下,我唱了十三段,后来矮爷说我唱了十七八段,显然是为了给我赚面子。矮爷交代我,到了砖瓦厂,别人叫我唱歌就得像现在一样好好唱哦,我说好哦;矮爷说,在人前要大方出众一点,我说好哦;又说,还要学着讲点礼性,我说好哦;又教我要怎么叫叔叔伯伯,白天干什么晚上干什么,我统统满口答应——好哦好哦好哦。后来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我在砖瓦厂待了四天,除了矮爷,没有跟别人说过一句话。有人给我梳头,有人给我送瓜,有人陪我乘凉,还有人请我们吃饭,我是横竖不开口的。终于可以回家了,一坐上矮爷的自行车后座,矮爷说,我的嘴巴又成了“豆渣罐”,响个不停。我这种极端乖张的性格不光扫大家的兴,显然也让矮爷颜面大失。
那时,我老觉得人们在捉弄我或者准备捉弄我,所以我是如此地警觉和戒备,一看到人们脸上的笑意不对我的胃口,就绝不再理睬他们。我最气恨的是大人们经常说我是“捡来的孩子”,捡就捡吧,但他们捡我的地方又那么不体面!起先,家里人说的还挺浪漫,口径也一致,我是矮爷挖藕挖出来的,对此我还可以做出得意洋洋的样子。后来终于招架不住了,那些一个比一个腌臜老丑的老太太,影伯妈、九伯妈、胖姑妈、莲姨妈等等,都声称她们捡过我:在鸭棚,在肥堆,在猪屋,在茅厕……最叫人不能忍受的是在路上的牛粪里!!!有时矮爷在场,见玩笑开得过分了,就说,听她们瞎扯!这么聪明的伢,天上也捡不到的。本来,我一直在抗着,拼命地装作满不在乎、藐视一切的样子。如果没有人来声援和解围,我会一直这样装下去,可是矮爷一当救兵,却使我满腹冤屈一下子溃堤,山洪爆发般哭将起来。我的被人编排还不止这些。记得那时我经常一个人跑出去野,总是碰到那位只有一只手的田家爹爹,他身后常跟着一群小孩,许多难听的歌谣都是他们传唱开来的,“一二三四五,山上打老虎。老三来时发,天真就来煮,屁——”,什么意思?没人知道,他们看到我就这样唱,有时远远地冲我狂喊那个长长的“屁——”。有时,田家爹爹还领着他们一起怪叫“喇嘛天真,阿弥陀福”,也没有人知道什么意思,但只要田家爹爹念一声,那几个混蛋就再三再四地喊得越来越起劲。还有的时候,他们中一个人领头,唱诵道:“高鼻子,夼额角,凸眉凹眼是哪个?”其他人随即高声附和:“是天真!”我只能狠狠瞪他们一眼然后跑回家,或者钻进芦苇丛里躲起来。有时,我刚一钻进芦苇丛中,就听到令人头皮发麻的咯吱声,是蛇在吃蛤蟆!又慌里慌张蹿了出来。还有其他一些更丑恶的外号,其实也并不针对我一个人,但我认准了人们都是在跟我过不去。比如有个说法叫“三姐麻金怪,四姐逗人爱”,无论谁说到这一句,我都觉得是在讽刺我,马上跟他翻脸。如果是家里人说的,我就会撒泼耍赖,强迫他们承认我是“四姐”。矮爷取的外号就不一样了,拽得很:“非洲朋友”。虽然我是家里皮肤最黑的家伙,但这个外号让我感到自己与众不同,洋气,用现在的话说还很酷。我还记得矮爷给一位远房堂侄叫应成的起的外号:“魏饭来”。因为每当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就来到我们家,在门口站着,然后就在我们家吃饭。当时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最有趣的外号了。
矮爷的风趣,还表现在编歌上,兴致一来,打油诗就脱口而出。我记得的最近一首即兴打油诗是给我外甥唐兄的。那是一九九五年寒假,矮爷带着唐兄去他四爷家,并等他的三爷我从武汉归来然后大家一起回公安。我到的当晚,唐兄吃多了橙子,又兴奋,尿了床,这使他在不到两岁的表妹面前大失身份。本来我们家的人,小时多瘦弱,尿床尿到十岁也不罕见,但毕竟出门做客的时候不多,出门做客而尿床的情形就更少了。为了替唐兄挽回面子 ,我们一致责怪四爷家的橙子太好吃了,矮爷就是在这个时候口占一首的。以前人们从公安到沙市、到武汉都是走水路,所以戏称尿床为“赶沙市”;如果一泡尿得太多的话就是“下武汉”了。我没有实地考察唐兄在表妹家的床垫上画的地图到底有多大,记得打油诗押的是“橙”的韵,以及跟我有关的几句:“坐车到沙市,换船下武汉,接了三爷赶回程”。
4
当然,我也有让矮爷脸上有光的时候。刚搬到杨厂,俺们姐妹仨就名声大振,因为学习成绩总是班里的第一。不光考第一,而且经常把第二名落得远远的。有一天,我在路上又碰到李校长,我经常碰到他,他也经常跟我说同样的话,没想到这一回他用的是正儿八经的腔调,还故意板着一张脸:我已经给你爸爸说好了,要解剖麻雀,把你的脑袋打开看看里头长的是么东西……没多久,我就听见矮爷把这话转述给一个夸我聪明的叔叔听。我想,矮爷这是为我骄傲呢。只是,从那以后,我的所作所为皆乏善可陈,矮爷对我也就操心的多了,引以自豪的时候少了。勉强可以一说的是我上大学的头一学年,过完寒假返校,矮爷和我一起到武汉,一则送我上学,也顺便找找曾住我们家的知青,看看能否做成一笔赚钱的生意,敷补家用。学校招待所没有房间了,矮爷就在我们班的男生宿舍住了一晚。第二天对我说起来,他似乎感觉蛮好的。他说,有七八个同学围着他坐,陪他说话说到转钟了。又说某某话太多,一看就是个滑头;某某话太少,并且还“说不转”,是个憨头子;还又说道,那个当班长的小魏不错,说话一句是一句,蛮沉稳,只怕有二十大几了吧。随着年岁的增加,这个断语使这个小魏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做一个文明人是一定得修边幅,顾脸面的——那时的小魏还不满十八。
的确,一生生计艰难的矮爷,一直在竭力维护他和他的孩子们的体面和尊严。而我呢,直到现在还时常回味和向往着小时候的那个情形,明明是兴冲冲地揣着奖状往家里奔,可是在把它交给矮爷的时候却偏要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现在,我很难再领到奖状了。即使当我领到时,我又到哪里去找矮爷呢?
在那些更遥远的初秋的傍晚,生产队的稻场上堆满了圆锥形的谷堆,谷堆外围用石灰画着做记号的圆圈。矮爷一手牵着天真的妹妹,一手牵着天真,在白线外面绕着那些谷堆慢慢走。凉风习习,炊烟袅袅,薄雾弥漫。当我望向远处的田野,看到了那宁静祥和的雾霭里的奇异景象:有三个洁白的人影在并排走着,中间高,两边低,越走越高,越走越远,直至融入天际。多年以来,这个景象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想,矮爷现在就在那至高的安谧之所,注视我们,保佑我们。
2008年1月
插图来自网络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我们
真无观:与他者比邻而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