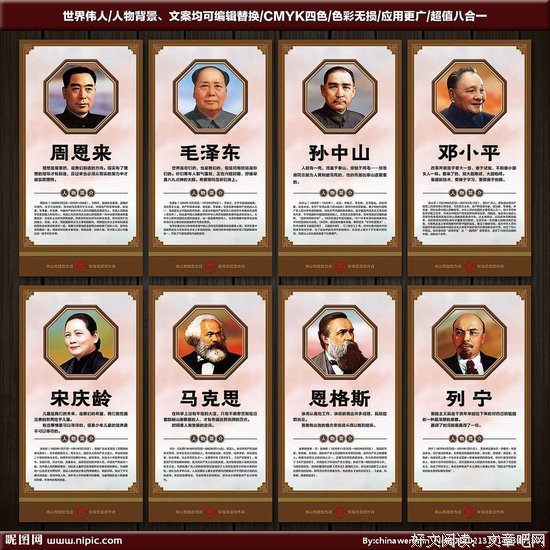梁文的名人名言
●凡干一事,我总是习惯后退一步,想想自己到底在做什么,然后再稍稍追溯一下这件事的源流,看看它和周遭环境的关系。于是我写书评时论,就不免粗糙考据书评与时论的由来;后来在电视台做节目,自然得思考电视与社会的关系。好听点讲,这叫做自觉反省;说难听点,这是不专心干活。一个人在骑自行车的时候要是太过自觉,心里老是想着双腿发力如何带动齿轮运转的力学问题,他多半会摔得很惨。 ----梁文道《味道·味觉现象》
●曾几何时,外科医生在西方的地位就和一个理发师一样,是等而下之的低级工作。事实上,替人施行外科手术和替人理发的,往往就是同一个人。当时的外科大夫流行放血,遇到各种大小病症,一律穿孔放血,好让病人的坏血流失,减轻症状。他们必备的工具之一是一根木棍,作用是缠着一块白布以绞紧病人放血处附近的肢体,以防病人失血过多。今天的理发店总爱以一管会转动的红白条纹灯做标志,它的原型正是那根棍子,白色代表缠绕在棍子与病人身上的白布,红色则是喷洒在上头的血迹。 ----梁文道《味道·第一宗罪》
●他和那个时代的许多日本文人一样,一方面非常尊崇中国古典文化,另一方面则慨叹中国的衰落沉沦。他说:“对晚近的中国人来说,喝茶不过是喝个味道,与任何特定的人生理念并无关联。”因为“长久以来的苦难,已经夺走了他们探索生命意义的热情”,所以虽然中国人的茶仍然散发香气,却“再也不见唐时的浪漫或宋时的礼仪了”。言下之意,反倒是日本继承了真正的华夏文化;他们就连制茶的方式也和宋朝一样是抹茶。“礼失而求诸野”,这也是今天不少中国人去过日本之后的感受。他们会认同冈仓天心的想法,觉得唐宋的建筑、礼仪乃至于一切传说中的高尚品味,全都保留在日本那里了。尽管他们会嫌茶道太过仪式化,也许还有点做作;可是茶室中的摆设与气氛却不断提醒他们: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古代的中国。 ----梁文道《味道·第一宗罪》
●假如食物注定要被人吃掉,假如食物真的是一种艺术,那么我们欣赏这种艺术的唯一方式就是毁灭它。只有透过吃的动作,我们才能完整的体验食物之美,才能领会食物作为一种艺术的精髓,可是吃的动作同时也就是一种破坏,吞没与消化,食物一生的高潮在于他的死亡,不消灭食物,我们就无从欣赏食物,饮食艺术乃是一种关于毁灭和败亡的残酷的黑色艺术,最美的刹那,就是崩解朽坏的一刻。 ----梁文道《味道·味觉现象》
●首先,苦是一种成熟的品味,小孩少儿不能轻尝,所以我几乎没见过有孩子是爱吃苦瓜的。
只有经历过了人间百味,酸咸尝遍,你才能体会苦瓜的清凉。盛夏时分,一盘冰镇苦瓜的消暑功效甚至比得上红艳艳的甜西瓜,一放入口,直如醍醐灌顶,沁人心脾。中国人爱吃苦在这个意义上非但不是贬损,反而是个褒扬,这表示历史够悠久的这个民族沧桑见尽,什么滋味都试过,这才晓得细品苦中真味,成了全世界最能欣赏苦瓜的国度。
大陆游客开放游宝岛以来,最受欢迎的景点莫过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而故宫博物院内又有三宝是他们万万不能错过的,并且按照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以菜名将之合称为“酸菜白肉锅”。 ----梁文道《味道·味觉现象》
●梁文道就说过,如果一辈子只读你读得懂的书,那你其实没读过书。真正严格意义上的阅读总是困难的。你读完一本很困难的书,你不能说自己都懂了,但是你的深度被拓展了。
不要总让自己那么舒服。舒服意味着你原地踏步。舒服意味着你没有进步。
●大陆的“庙口”渐渐走味,香港的“庙口”根本不存在,只有台湾还保留了这套庶民的善美风俗,而且东西真的好吃。吃新竹的贡丸米粉,没有比新竹城隍庙更好的所在了;其他地方亦然。有一趟我在台南,朋友说晚上要带我们吃海鲜,我以为一定是要到海滨河口了,没想到下了车竟是市区里的一座庙。夜凉似水,小城灯静,我们坐在贴地极近的低矮板凳上,前面是一行小卖车展示鱼获,背后则是庙门两侧的红灯笼(上书大字“肃静”)。烹调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白水湛湛煮熟的海产,一人一小碟酱油蘸料。但看附近桌子零落三四张,食客不出十来人,大家吃得也慢话声也低,我居然意外地感受到了一股神圣。 ----梁文道《味道·第一宗罪》
●正是一套系统而艰深的科学知识。你不懂医学,没有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就不可能做得成外科手术。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想象,或许未来有一天,你没有学过生理学与化学,不知道温度对感官的影响机制,不晓得苦味的构成方式,你就没有资格入厨做菜。 ----梁文道《味道·第一宗罪》
●「深入挖掘了人类的“怨恨”(ressentiment)心理,他的说法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现代中国的阿Q心态。依照舍勒,怨恨是一种对他人不满的情绪反应,这种情绪是种潜藏心中隐忍未发的怒意,毒蛇般地折磨和扭曲了一个人的正常心智与价值观。所以要隐忍不发,是因为有这种情绪的人根本没有发泄报复的能力。这种怨恨的由来有二,一是受到他人的侮辱,二是嫉妒他人拥有的东西,觉得那东西本该为己所有。可是他人的地位比自己高,实力比自己强;我不只没法抢夺他拥有的一切,没法改变我和他的差距,甚至连对之发作都不敢。这时就会出现“价值位移”(value shifts)的现象了,意思是颠倒价值常规,把自己得不到的说成是不好的 ...」 ----梁文道《常识》
●醉酒是不懂饮食艺术的表现,因为餐桌上的艺术“是很文明的,一切讲究节制,为的是更完美的人际沟通。喝酒可以放松神经使人健谈,促进桌上的气氛,但绝对不能让人变成野兽”。所以一个人要是自己吃自己喝,除了只是满足很动物的食欲之外,又还有什么意义呢? ----梁文道《味道·第一宗罪》
●进入茶室的时机。客人要先在外头的“待合”里静心稍息,培养品茶的情绪。直到主人召唤,才按照顺序鱼贯入室。这个过程必须尽量安静,以不发出任何声音为妙。所以最讲究的主人会用最静谧的方法通知客人时候到了,那就是点香。闻到空气中开始飘来一股似有若无的清香,客人便知这是主人的信号。他们觉得,这个状态实在是太美了,除了檀香与海潮般的沸水声外,一切沉静,乃东方特有的优雅情调。 ----梁文道《味道·第一宗罪》
●读书是要你重回人间,而不是逃离。 ----梁文道
●”东方”是西方人发明出来的。”“西餐”就算不是中国人发明出来的东西,也是种文化碰撞的结果。在西方人那边,他们征服的地方越多,见识过的东西越是奇异,就越容易回过头来寻找自己与别人不同的特点,以及欧洲和各国之间彼此相似的地方。遇到了其他文化的食物,他们才有机会渐渐了解自己吃的western food。而在中国人这边,西餐就和“西方”一样含混。对我们的祖先来说,红须绿眼的都是鬼佬,但凡使用刀叉的都叫西餐。例如中国第一家西餐厅、原址广州沙面的太平馆,大家只知道在那里吃的是“番菜”,当年有谁计较它到底是哪个“番”呢? ----梁文道《味道·第一宗罪》
●日本料理的精髓(或者狡诈),一切以食材为主,怎样最能让它保持原味就怎么做,只要东西好,尽量不加工地把它完整呈现出来,竟然就成一道独立的菜肴了。 ----梁文道《味道·味觉现象》
●中国文化是最“工业化”的一种文化,一切花样变化都不出几项基本元素的组合。看似繁杂的汉字,全可化约在“仓颉”输入法的几种笔画之内;青铜器上迂回的花纹也不外数种根本要件的拼凑。但这么简单的元素却能化生天下万物,有创意的厨师自能在里头精细微妙地制造差异;犹如兵马俑虽然成千上万,个个大小相当,但走近一看才发觉原来每个兵俑的表情都不一样。 ----梁文道《味道·第一宗罪》
●所谓"感人",指的可能就是作品足够抽象足够普遍,使得每个人都能轻易代入;同时它还得有个人化或拟个人化的腔调,令听者代入之余还觉得它是独一无二的;不只恰到好处地传达了自己的感情,且似根本为己而设为己而造。 ----梁文道《我执》
●他们认为人类这种杂食动物比其他禽兽麻烦的地方,在于常常要为什么东西能吃而担心。熊猫没有这个问题,它专啃竹子,哪怕你给它一盘炒笋尖,我也敢保证它掉头就走。人就不同了,什么都想试,但又怕中毒,总在好奇与恐惧之间来回犹豫。我们有习惯的食物,可以使我们吃得放心,吃得温暖;但同样的东西吃多了很苦闷,心里就老想尝点新鲜的。这该如何是好? ----梁文道《味道·第一宗罪》
●好厨师起点或有不同,但爱的终点是一样的 ----梁文道《味道·第一宗罪》
●所有的人际往来,莫非一种应答关系,有呼召遂有响应,送礼就期待回礼,寄了一封信之后就等着回信的到来。 ----梁文道《我执》
●时代变了,现在机遇比以前更多,但代价更高,人们变懒了,不愿意读书不愿意思考。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来的。当代人不读书,根本不是有没有时间的问题,而是一个选择什么的问题。 ----梁文道
●零食有两种,一种是晒晒太阳的时候,消遣永日。得用手细致地东剥西弄,不怕费一点工夫才尝那一口短暂的滋味。这种零食必须有格调有味道,例如菱角,例如现烤乌鱼子,因为它可能是一整个下午唯一不让人发呆的提神丹。
另一种零嘴正好相反,要甘于当配角,口味单调,同时又能引人上瘾,无意识地一口接着一口地吞。例如看球时吃的锡纸包装薯片,或者电影院必备的爆米花,它们实在是很平凡的东西,没有变化只有重复,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是注定要停不了地一直吃下去,直到整包淀粉消耗殆尽,犹如我们不得不过但又乏味庸碌的人生。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和偶尔一场的好电影,就是这可怜生命的小小高潮了。在这样的高潮时刻,平凡的零食恰好对比出高潮的难能可贵,同时又提醒了我们那个乏味生活的存在。 ----梁文道《味道·第一宗罪》
●看狮子,每回饱餐之后都要倒头大睡;又或者牛羊,醒着的时候必须把大部分时间耗在反刍上。因为它们不懂得把肉和草煮熟了吃,所以才要花工夫慢慢消化食物。而且任何常吃沙拉的人都明白,同样分量的蔬菜,生吃要比熟食慢多了;一捆菜就算看起来不少,丢进热水一烫往往也只能装满一小碟而已。 ----梁文道《味道·第一宗罪》
●就说江苏一带,上海城隍庙、南京夫子庙、苏州玄妙观,这些地名几乎等同某种小吃的流派了,过去要找地道好小吃,非去这些庙前的空间不可。我还说得苏州玄妙观前面的“观前路”,什么五香排骨、酱螺蛳、鸭血汤、玫瑰糕、梅花糕、酒酿饼……这一路吃下来,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苏州的“香甜软糯”了。可惜时代变了,那一带的地价太高,小吃做不住,反而开了麦当劳。 ----梁文道《味道·第一宗罪》
●怀旧是种无人可以避免的病,人类历史有多长,这种病就存在了有多久。它不是记忆,它是一种对待记忆的方式。它总是让过去比现在美妙,有时候还会创造出一个不曾存在的过去。 ----梁文道《味道·味觉现象》
●失根兰花?说来也怪,娘惹本就是漂流、抵岸、生根再繁衍的茂密雨林。谁又能保证有一天它不会北移大陆,生出香港、潮州甚至北京的异种呢?无根,于是处处有根。 ----梁文道《味道·第一宗罪》
●家乡漂洋过海抵达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气候、风土和周遭的声音与气味都不一样了,往往是老家的食物可以延续记忆,使生活稍显安定,使自我身份仍然在时空裂变中维持一统。移民的食物还会顺便带来一连串的链条,比如说专从老家运来家乡才有的原料的小贸易商,比如说专门售卖这类食材和比较花工夫制造的吃食小店,又比如说一整套围绕着这些原乡食物打转的年节仪式和社群,最后还有用原乡饮食聚集乡亲的食肆跟会所。许久之后,当这一切遍地开花,成了异乡中别具异国风味的消费场景 ----梁文道《味道·第一宗罪》
●此外也有些人学得太快,知道Fusion是潮流就搞Fusion,晓得室内设计是话题就不惜大老远搬来一座古宅做噱头。“品牌形象”正是近年大陆商界的关键词,一时之间人人都以为品牌无非形象,仿佛LV起家靠的就是广告,完全用不着任何手艺传统做根底。这样子搞下来又怎能不是形象大过内容,公关大于实质呢? ----梁文道《味道·第一宗罪》
●但凡山珍海味等神话食品,都有不凡的出身。例如燕窝,要工人冒生命危险爬上悬崖采集;白松露则要夜晚秘密地用狗去寻找(一条合格的狗,其价码可能比采燕窝的工人生命还高)。但松露更神秘之处,是所谓的“焦土现象”,也就是它附近的植物会因其生长而干枯,直径范围可达十多二十米,直如被雷劈过一般,留下一圈烧焦的土地,至今无人能够给出科学的解释。所以我们在吃松露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些使它增值的背景故事,正是它们造就了神话,使它昂贵,也使它更美味。 ----梁文道《味道·味觉现象》
●水果当然是树上熟为美,其中又以荔枝为最,所以香港才会有这许多“荔枝团”专门去广东果园现采现吃。而江太史家更胜一筹的地方在于他们讲究到了时辰,露水乍现,就要及时取用,差一分都不行。
读明人徐渤的《荔枝谱》,方知这是由来已久的古法:“当盛夏时,乘晓入林中,带露摘下,浸以冷泉,则壳脆肉寒,色香味俱不变。嚼之,消如降雪,甘若醍醐,沁心入脾,蠲渴补髓,啖可至数百颗。”徐渤还说,要是怕吃得太多肚胀,可以略略点盐,有消滞之效。 ----梁文道《味道·味觉现象》
●京都洛北有间叫做“大德寺”的佛寺(港人熟悉的“一休和尚”便做过它的住持),它后门的小路上便有家开了一千多年的小食肆。没错,它真是家代代相承的千年老店,不只几乎与京都同岁,甚至可能是世上现存最长寿的食肆。他们家只卖一样东西,那便是用竹签串起来蘸酱烤着吃的日式小年糕。尽管独沽一味,尽管看似简单,可他们一家人还是全力以赴,老奶奶还是严肃盯着年纪也不少的女儿,生怕她调控炭火的动作不对。曾经有客人和店东聊天,一边嚼着年糕一边随便指了指马路对面说:“对面那家年糕铺也很古老了,也是家名店呀。”老板先是赞同说是,然后又带着一副好像要说人坏话的神情悄声补充:“可是他们前阵子换手了。”“哦!真的吗?什么时候?”老板继续放低音量,说:“两百年前。” ----梁文道《味道·第一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