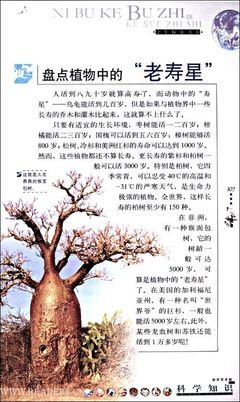世界史前史的读后感10篇
《世界史前史》是一本由布赖恩•费根(Brian Fagan)著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4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世界史前史》读后感(一):消逝的文明
今天,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还保留着完全未被现代文明染指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在亚马逊盆地深处,在新几内亚高地,还有一些族群尚未与工业文明形成持久的接触。这些社会处于被灭绝的危险当中,就像在工业文明的血盆大口之下,雨林遭到砍伐,环境被破坏得面目全非一样。但是,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和企图,250万年前发祥于非洲的古代世界已经消失得几近被遗忘,以至于就目前这个程度而言,我们也只能从现代科学研究中对其窥探一二。
《世界史前史》读后感(二):对人类起源的探究由来已久,《世界史前史》就为读者解答了这样的疑问和困惑。
对人类起源的探究由来已久,《世界史前史》就为读者解答了这样的疑问和困惑。
世界史前史权威学者布赖恩•费根以其科学的视角和完善的理论生动地讲述了史前人类活动与发展轨迹。本书结合考古学、生物学、生态学、地质学等多门学科,甚至遗传学与心理学,探索人类的起源、流徙,以及农业生产的出现,以至国家的形成,带领读者进行了一次跨越长达 250万年的时空之旅。
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向读者简洁地介绍了历史、文化、空间和时间的基本概念,并系统概括了人类史前时代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概述解释人类及其他灵长目动物的起源和科学研究方法。其中涉及最富争议的现代人的迁移路径问题。在这一点上,作者赞成“非洲迁徙理论”。第三部分着重讨论了古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农业的起源及其与现代世界的关系。最后一部分,针对西亚、非洲、南亚、东南亚和东亚和美洲的古代文明进行了广泛讨论。
《世界史前史》读后感(三):四大文明古国的谬误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这样的判断,已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所推翻,事实证明,文明古国绝非四大,即使硬性规定出四个,中国也不在其中。
国人很少知道,世界最早的农业诞生在中亚,较中国早数千年,这有偶然性的因素,人类常用的食物中,绝大多数产生在这里,相比之下,原产于中国的只有几种。小麦产自中亚,大米则产自东南亚,斯基泰人带来了马和马车,今天我们在中原所见到的绝大多数家禽与家畜,它们的祖先都是舶来的。根据目前的考古成果,一些主食在朝鲜可能出现得比中国还早。
人类的诞生,是一个集体事件,不同文明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脉络。然而,在相当时期,考古成了一件为国争光的面子工程,很多国家都试图挖掘出自己很古的证据,日本一位学者甚至不惜去自己制造古物。然而,古真的是荣誉吗?文明发端早,与文明的发展成果,真的具有决定性的逻辑联系?
事实上,历史是存在“蛙跳效应”的,后发文明往往居上,先发文明因为后来的衰败而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例子,数不胜数。一个文明的光荣在于它与时俱进,能根据当下的需要而调整自己,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相反,那些固步自封、只想以实力示人的大帝国,往往难以长久维系。
本书是美国大学的一本教科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全球最新的考古成果,材料之新颖,梳理之细密,令人耳目一新。人类从蒙昧到文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回望这个过程的艰难,可以拓展我们视野,可以满足我们无法遏制的对过去的好奇心。
总之,对于有一定知识的现代人,“四大文明古国”已是过时的说法,应予剔除,否则难免贻笑大方。
《世界史前史》读后感(四):生态环境与文明的兴衰
随着大众旅游和探险的兴起,人们开始注意玛雅文明、吴哥窟、复活节岛文明的离奇衰落,大众媒体也不断靠它们来引起话题。学者们其实也感兴趣,考古学教授布莱恩•费根的作品《世界史前史》和《大暖化》在谈述上述文明的考古史时,旗帜鲜明地指出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了上述文明的衰亡,而生态环境的恶化跟人的活动不无关系。如果你人云亦云地批评其为“环境决定论”,的确有些落入俗套,因为环境对于历史进程和人类文明的影响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真正的见识有时其实就是剑走偏锋的。
美洲地区玛雅文明处于远离江河湖泊的地区,当地的降雨量也颇少。为了维持城市的运转,他们修建大型的蓄水工程,发展汲取地下水的技术。甚至在城市的设计过程中,他们已经充分考虑了收集雨水的功能。总之,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希望掌控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世纪暖期促发的持续干旱,人口增加导致的过渡开垦,给本就恶劣的生存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他们热衷修建大型的祭祀建筑,毫无节制地祭祀天神,消耗了大量的资源,更是加重了文明的危机。在人口较少,资源相对丰富的时代,人们在遭遇特大干旱时还可以通过迁徙来抵御灾难。不过,随着人口越来越多,避无可避,大规模战争成为争夺资源的重要手段,文明的危机愈演愈烈。
与此相反,东南亚的吴哥王朝身处热带,雨水充沛,但是也不免“在沉默中死亡”。无独有偶,吴哥王朝跟玛雅文明一样热衷于修建大型祭祀建筑和精细灌溉工程。风调雨顺的时候,贵族凭借着在祭祀典礼和灌溉工程中树立起的权威,顺利地统治着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和奴隶。文明运转顺利,他们对于祖先和神祗的祭祀更加虔诚与奢侈。象征极权的吴哥窟,工程浩大,供养着成千上万不事耕作的神职人员,也消耗了大量的资源。中世纪暖期临近,极端气候侵袭,时而洪水滔天,时而极度干旱,远远超过精细灌溉工程能够承受的极限。河道淤积,水利工程失修,战争频仍,人们被迫疏散到小型城镇和乡村,人口过百万的城市被遗弃在热带雨林中。
玛雅和吴哥窟的故事讲述的是大型文明的覆灭。而太平洋上复活节岛文明的衰落揭示的是小型聚落的悲剧。西方探险家到达这个岛屿时,岛上有1000多根气势恢宏的巨大祭祀石像,但是岛上却人口稀少,树木奇缺。考古学家异常疑惑,慢慢才发现原因。岛屿居民为了表达对神祗的虔诚,建造大型雕像,砍伐了大量的树木来运输石像。对于资源极度有限的岛屿文明来说,种植、捕鱼、房屋建筑本来就需要大量木材。无节制地砍伐加速了区域内生产增长极限的提前到来: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农业生产遭受重创。为了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部落居民的冲突异常剧烈,导致大量人口的直接死亡,发展就此止步。
数种古代复杂文明的崩溃很大程度上跟“气候和社会原因导致生产增长极限的出现”有关。无独有偶,今日的人类文明,繁荣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但是人口超过70亿人口,全球变暖,地壳中蕴藏的能源日益减少,人们日益鄙视作为生存基础的农业生产。危机四伏之际,布莱恩的《世界史前史》、《大暖化》讲述文明兴衰,让后工业时代的读者感受到一丝冷意。尚有热心的读者,其实可以去读读另外一些作者的作品,比如张光直、陈星灿等。
《世界史前史》读后感(五):后记
我们这趟穿越史前史的时空隧道之旅在现代化的门槛前戛然而止。它伴随着大发现时代的开始而终结,这个时代见证了欧洲的探险家们离开家园,航行到了从未去过的远方,去寻找黄金和香料来侍奉上帝,或仅仅是为了满足心中难以遏制的巨大的好奇。
西欧诞生于3000年前。几千年来,西欧始终是远离亚洲的一个偏僻的地理概念,处于近东和地中海地区各个文明和帝国的边缘。25个世纪以前,欧洲变成了一个有着自己的意识和认同的西方半岛,诞生自希腊文明的这种意识在更晚近时欧洲人对德国人(Huns)、土耳其人(Turks)和摩尔人(Moors)的胜利中得以进一步的成熟。这是一块深受个人与国家同样重要这一信条驱使的天主教的飞地。个人主义意识和探险意识的增长导致对外部世界的强烈好奇。在广袤无垠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西方那无尽的海平面之外是否还有遥远的土地?
在14世纪二、三十年代,绰号“航海家亨利”(Henry the Navigator)的葡萄牙王子组织了一场向欧洲以南探险的年度航海,并深入到赤道地区。他的船队沿着非洲西海岸向南进发,并在1433年绕过西方的大海角 。然后,在1488年,巴塞洛缪•迪亚士(Bartolemeu Diaz)绕过了非洲的南端。他与科伊科伊人(Khoe Khoe)进行了接触,这个简单的牧牛民族其实也只是赶着他们的牛群漫无目的的四处游荡。他们在西方人眼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似乎有着比世界上其他民族更原始的风俗。几个世纪以来,科伊科伊人都被视为半猿半人的,在那条“存在之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上处于最低的一环。在欧洲人于1652年定居好望角仅70年后,科伊科伊人就消失了,入侵的白人农民摧毁了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
1497年,瓦斯科•达•迦马(Vasco da Gama)追随迪亚士的步伐,沿非洲的东海岸航行到了现在的肯尼亚,然后循着信风(tread wind)到达了印度。借此,欧洲人便发现了直通南亚和东南亚丰富的黄金和香料市场的替代路线。他们沿着古老的海上运输线航行,这些航线将非洲那似乎无穷无尽的黄金、白银和奴隶输出,与对这些货品贪得无厌的市场连接在了一起。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非洲同时遭到了来自欧洲诸国和伊斯兰世界两方面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财富的剥削。迅速发展起来的国际奴隶贸易使沿海广大地区人口出现锐减。欧洲探险家们直到19世纪才渗透到非洲内陆,那时非洲已经成为巨大而繁复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
就在迪亚士和达•迦马探索非洲海岸的同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也于1492年向西对“印度”进行了探险。他以为自己来到了亚洲的门口,但实际上,他发现的是一个遍布着各种千奇百怪的动植物和美洲印第安人社会的新世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墨西哥和秘鲁这样伟大的文明在西班牙征服者面前迅速地土崩瓦解,与此同时,凡欧洲人所到之处,天花等一些外来疾病的蔓延在历经几个世代之后便使美洲土著人口急剧减少。
随着好望角和美洲大陆的发现,掀开了人类史前历史的最后一章,这是一场错综复杂而旷日持久的碰撞和争锋,一方是日益发达精细的西方文明,一方则是遍布世界各地的大量的非西方社会。类似的剧情一再上演。一小撮欧洲探险家来了,就像詹姆斯•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到了塔希提和新西兰,法国航海家马利翁•杜•弗莱(Marion du Fresne)到了塔斯马尼亚岛和澳大利亚。第一次相遇总是带着万花筒般令人目眩神迷而转瞬即逝的好奇,有时这种着迷甚至到了惊人的地步,并经常饱含充满浪漫色彩的刺激和兴奋。有时也会动武,一方掷矛枪,一方开火枪。但有时则是友好的物质交换,用皮毛换取一些廉价的玻璃珠或者其他什么小玩意儿。尽管如此,就双方来说,几乎可以说是完全陌生的。
有时,当地人会认为这些神秘的访客是神,就像赫尔南•科尔蒂斯站在特诺奇蒂特兰城门前阿兹特克统治者蒙特苏马(Moctezuma)所认为的那样。新西兰一位年长的毛利(Maori)酋长曾对19世纪一位官员说,祭司告诉他这些远道而来的白人实际上是眼睛长在后脑勺上的灵魂,这显然与库克船长的划桨人面向船尾有关。但是很快,不管这些陌生人出现在哪儿,事实都证明他们不仅不是神,而且是百分之百的人——富于侵略性,好战,而且贪得无厌。
最初的接触总是短暂的。但是很快,大批的欧洲人涌入进来,从事兽皮贸易,整修补给他们的船只,或者寻找黄金。然后传教士来了,试图为异教徒改宗换教,拯救他们的灵魂。澳大利亚成为囚犯的流放地,其中大多数脱逃后四处虐杀澳大利亚原住民。在许多地方,继第一批探险者之后,殖民者潮水般涌入。他们通常是一无所有而渴望土地的欧洲农民,希望在非洲内陆,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在新西兰或者塔斯马尼亚肥沃的土地上寻求更好的生活。
这些人都是些永久居民,他们带着铁器和火器去寻找新的家园和草木繁盛的土地。他们与当地人争夺良田,他们见人杀人遇鬼杀鬼,有时甚至赶尽杀绝,或经常通过卑劣的手段——土地出售和非法贸易获得大型的农庄。当地人几乎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他们的土地,那些即使没有千年,至少也在许多个世纪里为他们的家族合法拥有的地盘。他们并没有多少选择,只能撤退到偏远的边缘地带,在那里继续保持着先前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点点影子,如果他们能侥幸存活下来的话。唯一的选择是让自己接受新入侵者的同化,但即使这样他们也几乎还是生活在边缘,通常被雇佣做农工或家仆。
19世纪晚期的工业革命使得西方文明戏剧性地加速了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这次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个催化剂,它创造了不仅靠人类的头脑驱动,同时也靠化石燃料推动的工业社会。它激发了对各种原材料的疯狂的需求,创造出大轮船和铁路,并引发了史无前例的移民潮,人们从欧洲移民到北美,从亚洲移民到太平洋和北美。近年来大规模的人口变动为大大小小的非西方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今天,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还保留着完全未被现代文明染指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在亚马逊盆地深处,在新几内亚高地,还有一些族群尚未与工业文明形成持久的接触。这些社会处于被灭绝的危险当中,就像在工业文明的血盆大口之下,雨林遭到砍伐,环境被破坏得面目全非一样。但是,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和企图,250万年前发祥于非洲的古代世界已经消失得几近被遗忘,以至于就目前这个程度而言,我们也只能从现代科学研究中对其窥探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