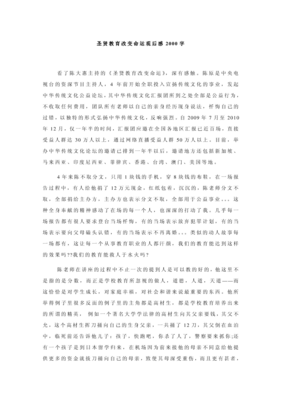《小镇》经典观后感1000字
《小镇》是一部由努里·比格·锡兰执导,Cihat Bütün / 伊敏·托普拉克 / Fatma Ceylan主演的一部剧情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零散的小镇景观里包涵了时间与气候的变化,孩童视角丰富地记录了主体叙述外的无用景象,雨雪丛林万物都显露小镇的生气。那些超越孩童认知的长辈叙述里是对国家历史与自我经历的回顾,小孩只以逝者坟墓方位来辨别地理方向。导演给了未来的几种可能,又一一否定,“你不是已经学会了如何离开这块土地吗”
●两段 神秘自然 像躺在古老的时光身边 听爸爸妈妈 还有他们的爸爸妈妈 讲从前的传说和真人真事 你并不十分明白 但却沉浸其中 在深夜密林的篝火边 你枕着草丛 梦在游乐场里迷路 你透过玻璃窗户 外面大雪纷飞 你看见她穿过玉米地 看见她的手伸进溪水 好像会发生什么 好像不会 如同当年漂在头顶的羽毛
●锡兰。绝美的摄影艺术,每一个镜头底下都蕴藏着无声的语言。惆怅的情感,不安的心潮,怀疑的神态,通过一个家族三代人的谈话全部流露。在土耳其的乡村社会里,也经历着传统与现代的对抗,经验主义与科学文明的对抗,现代技术与纯态自然的对抗。所有的人都一样,如此留恋这个世界,虽然,它是无趣的。
●电影看了有一段时间了 回忆这部电影 依然是满满的孩童时光浮现 抒情是种病 但不得不记录 破旧的课堂 放学后伙伴们的嬉耍和回家穿过树林里的美好 母亲温暖的怀抱 影像之前只剩一些残存画面 影像之后 就如同儿时故乡的一阵风 把记忆和味道一点一点吹回我面前 老家的那些人 事 物 又这样一点点跃然当下
●锡兰你把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拍出来吧!
●黑白印象自由别味之处,电影中的一家三代人围着火做活夜谈和我小时候一样,其他地方也有不少相似之处,几个人的谈话还是能够咀嚼一下的,影片的摄影在黑白映像下显得很不错,淡淡悠长的感觉富有诗意,让我想起塔尔科夫斯基
●五月碧云天前传。早期的芥兰一直在试图描绘自己故乡小镇的众生相。他把社会议题藏在角色中,关注的重点仍然是人。人的情绪,人的状态,人的行为。人构成了这个社会意义上的故乡。从这个意义上讲,芥兰影片当中的物也都是有生命的。植物、动物,甚至是环境,都被芥兰赋予了人性。(又或者说是和人具有同样的功能而交织在一起)。流浪的狗,死睡的猫,挣扎的乌龟。他们和真正的“人”一起成为了这个环境的构成要素。这样的思路和很多处理类似题材的中国导演是完全相反的。(他们喜欢让环境和社会分离出来,成为所谓的客体)
《小镇》观后感(一):值得反复看
优秀导演的处女作总是值得拿来反复看,那是他的起点。顺着拍的年代,你会发现他对电影的思考和理解。
锡兰最大的特点是可以将琐碎的生活拍的趣味盎然。这部电影我更喜欢前半部分。这其实也是一个很难一句话说明白的电影。剧作课上会讲到不能用一句话概括出来的故事不是一个好故事~~也许这句话没错,电影不一定就是在讲故事。
“在8岁时,快放暑假的一个下午,我走在斑驳的树荫下回家。然后我停下抬头看着头顶树叶,缝隙间的阳光。我记得那个下午,空气中的味道,漂浮在空中的尘埃,阳光照在身上的感觉,脚下的鞋……”这不是什么故事,但很能感动人。
艺术同科学一样,向人们揭示的是人们未曾发现的东西。情感,一种情感体验。就像数学试图向人解释“负二的平方”这样一个概念~艺术也一样,那是一种试图让人去理解的东西。
忘了“故事”吧……我觉得那是误入歧途!
《小镇》观后感(二):离开了故乡,才认识了故乡
锡兰的处女作,非常个人的一部电影,通过自己从母亲那听说的故事表达对故乡的思念。
前面部分我还蛮喜欢,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跳跃着童年的记忆,尤其是载着孩子们的旋转飞轮在头顶飞驰的画面,像是一种久违的欢乐萦绕脑海。
原来锡兰从一开始就喜欢运用自然的声音,把它们放大来烘托气氛。
后半部分的野外"围炉"夜话内容,历史,战争,工作,让我开始迷糊,如同那个依偎在母亲怀里的少年,昏昏入睡。不过,小孩子入睡这段处理的真好,大人们的讨论声随着入睡的深度越深渐渐消失,经历一段噩梦,又回到还未结束的讨论声中,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害怕一个人回屋子里睡觉,就硬撑着在大人们的聊天声中昏昏入睡。
叔侄俩的争吵,关于故乡的意义,在我和小孩子的意识里都是陌生的,因为我还没有过对故乡的思念之感。
小青年走上离开家乡去往城市的背影,略显沉重,厚厚的背井离乡之愁,只有在离开故乡多年后才会切身感受到。
《小镇》观后感(三):关于锡兰家乡记忆的动态照片集
《小镇》(Kasaba)是Ceylan导演非常个人化的处女作电影,其中融合了很多他对家乡的私人记忆。 对于在中国城市中长大的我来说,土耳其小镇的风情都是新鲜的,但由于黑白的影调、悠长的固定镜头以及散文式的叙事,中途看得我几度昏昏欲睡。不过,其中堂哥的心境却与我有几分契合:不想一辈子待在家乡,总想出去闯荡一番。 另外,让我记忆深刻的是,Ceylan导演用一个画面就把堂哥的孤独表现得淋漓尽致:堂哥抬头看着坐在空中飞人上的人们,欢声笑语地不断掠过自己的头顶,他边看边抽起了烟。
这种意蕴十足的固定镜头,就像Ceylan导演拍下的动态照片,而《小镇》便是他关于家乡记忆的动态照片集。
《小镇》观后感(四):远在他乡的故乡——贾樟柯谈锡兰(转载)
远在他乡的故乡——贾樟柯谈锡兰
1998年,我带着《小武》去参加柏林影展青年论坛。那年我已经二十八岁了,这是我第一次出席国际电影节,也是我的首次欧洲之行。
一个人从北京搭乘汉莎航空的航班出发,起飞后不久大多数乘客就都睡着了。机舱里异常安静,我却睁大眼睛不肯入眠,脑子里不时闪过法斯宾德或文德思镜头下的柏林,近十个小时的航程我是在冥想中度过的,一会儿柏林、一会儿北京、一会儿我的故乡汾阳。
多年之后我想,我之所以到现在还热爱所有的远行,一定跟故乡曾经的封闭有关。而所有远行,最终都能帮助自己理解故乡。的确,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
那时候两德统一还未满八年,人们习惯上还把目的地称为“西柏林”。可我偏偏对“东柏林”感兴趣,放下行李拿上一张酒店的地址卡,我便在暮色中坐一辆公共汽车出发了。
每到陌生之地,我都喜欢这样漫无目的地游荡,喜欢在偶然中遭遇一座城市,公共汽车从动物园附近出发,穿过城市向东而行,没有跟当地人说一句话,车窗外的建筑像是能告诉我一切。西边的马路基本上呈放射状分布,路边建筑的设计也表现出开放的状态。可一到东边,横平竖直的街道和平板的办公大楼就似曾相识了,国营体制的感觉毫不掩饰地经由建筑表现出来。
我下了公共汽车,遥望西柏林方向,远处大厦上奔驰汽车的广告在夜幕中旋转闪烁。那时,我脑子里冒出一个词:资本主义的柏林。这里的观众能理解社会主义的汾阳?我问自己。《小武》拍摄于我的老家汾阳,那里尘土飞扬、城外的军营每天军号阵阵。电影的世界是真奇妙,再过两天,我就要将故乡的风景人物,放映给异乡人看了。
98年的柏林电影节还有一个导演,也用电影把他的故乡带到了柏林。这部电影叫《小镇》,导演是来自土耳其的锡兰。锡兰1959年出生在伊斯坦布尔,他是在当兵期间看了波兰斯基的自传,开始爱上电影的,他常自编自导自演,和他的妻子一起出现在自己的电影中。
在看《小镇》之前,我从来没机会知道土耳其的小镇会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那里的人们怎样生活的。
坐到电影院里,灯光暗下、银幕闪亮的时候,才知道《小镇》是一部黑白电影。电影开始于一场漫天大雪,原来土耳其小镇上的孩子们跟我一样,只有天气的变化才能给一成不变的生活带来新鲜感。这时,银幕上一个孩子穿过山峦去上学,他进入教室,把雪打湿的鞋子脱下来,烤在火上。火炉温暖,窗外寒冷,这不就是我小学时冬天的记忆吗?接着,孩子脱下他的袜子,挂在火炉上,袜子上的水滴,掉在火炉之上,“吱吱”蒸发的声音,一点一点滴在心头。
我不喜欢跟踪电影的情节,我看电影最大的乐趣,是看导演描绘的诗意氛围,没有诗意的电影对我来说才是沉闷的电影。锡兰的《小镇》是一部用电影语言超越语言的电影:不用听懂对白看懂字幕,仅仅通过电影画面,已经能够理解导演的世界。
记得在黑泽明导演生前,侯孝贤去拜访他,黑泽明问自己的助手: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侯孝贤的电影吗?他的助手用哲学命题来解释,黑泽明摇摇头说:不是,我在他的电影里,能看到尘土。
锡兰导演呢?在他的电影里,能看到天气。雪后的寒冷,自雪地上玩耍的孩子们身体里散发出的热气,被雪冻得麻木的双脚,袜子上掉下来的水和炙热的火炉相碰撞冒出来的蒸汽……都是这部电影的诗句。
锡兰在《小镇》中拍了很多微观世界的镜头:小动物、一草一木的细节、纹路、肌理。我们从未这样专注而细心地凝视过那些与我们共存于这个世界的生命。透过锡兰的摄影机,我们看到自己内心的粗糙,以及逐渐丧失的耐心。
锡兰营造的声音世界也让我迷醉,他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里将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声音提取出来,加以夸张,给我们熟悉的陌生感。水滴在火炉上被炙烤蒸发的声音,大自然里面动物的鸣叫声,远处隐隐约约人的喊叫声……鸟啼虫叫,风声雷鸣,这些原本被我们在日常中忽视的声音,在影片中被提炼出来。它们帮我打开了记忆之门,让我想起已经淡忘的岁月。
通过锡兰的电影,会发现我们还有一个故乡远在他乡,它也解答了我的疑惑:在资本主义的柏林一定有人看懂了我的《小武》,他们在我的电影里同样可以遭遇乡愁。
努里•比格•锡兰简介
土耳其著名导演。从Bosphorus大学毕业后,锡兰在伊斯坦布尔的Mimar
inan大学学习了两年电影制作。1995年执导短片《Koza》入围当年的戛纳电影节短片竞赛单元。他的剧情长片处女作《小城》(Kasaba)在1998年的柏林电影节上获得“青年导演论坛”最佳影片奖。2000年他的第二部作品《五月碧云天》(Nuages de mai)首次入围柏林电影节正式竞赛单元。2003年他执导的《远方》(Uzak)在戛纳电影节上一举夺下评审团大奖和最佳男演员两项大奖。证明了他作为艺术电影导演的地位,成为21世纪欧洲影坛炙手可热的新锐导演。今年最新力作《气候》(Iklimler)再度入围戛纳电影节正式竞赛单元。2008年,在第61届戛纳电影节上,努里•比格•锡兰凭借新作《三只猴子》(Three Monkeys) 获得最佳导演奖。其后凭此片还获得第二届亚太电影大奖最佳导演奖。2009年第62届戛纳电影节担任评委。
(原文载于《中国周刊》)
《小镇》观后感(五):童年的小镇与锡兰的乡愁
不知道土耳其怎么划分,凭个人印象,小城与小镇还是有着本质区别,再小的城也是县城,再大的镇却只能是乡镇。听上去,《小城岁月》是比《小镇》舒服且文雅,看完后却发觉片名只能选择后者。树林与田野的连接相交,变幻的晨曦暮霭,加上稀疏散落的房屋,实在构不成一个小城。结合锡兰的自传文字,那么它就只能是个小镇。影片带有田园牧歌的天然风格,乡村故土的亲切与贴近。其中又不能不掺杂着锡兰大量的自我回忆和个人经历在里面,通过作品流露出的个人气质,在《小镇》里展现无遗。
开头,冬天雪景。小孩子们捉弄疯子。疯子摔了一跤,站起来又摔一次。孩子们笑了,他也露出笑容。
《小镇》大约分成不太明显的三段或四段,冬天早晨的课堂,小女孩(姐姐)在学校。春夏之交的中午到下午,小女孩和弟弟在归家路上。再到晚上,他们跟全家篝火露宿。夏秋季节的清晨,小女孩来到了河边。看上去故事只发生在一天,由几个不同场景组成,但时间变化的实际跨度却远比一天来得长。《小镇》里的时空跳跃、季节更迭没有特别说明,造成真假难辨的错觉。观众可能还会困惑于一家人的安排设置,人物来历如小女孩的堂叔也欠缺交代。
直观地划分,《小镇》前半部分对白很少,构图优美,适合欣赏。后半部分对话太多,喋喋不休,理应让不少人入眠。锡兰这部黑白处女作有着日后作品的很多影子:人物周围存在的各种不同声响,有大有小,鸟叫虫鸣,风声雷响,音效相当丰富,单独捕捉后的放大更是引人入胜。由于预算问题,它们在灵活变换的程度上可能还不如后来《气候》里那般运用自如,却有独到之处。
教室里,迟到的小男孩脱下在雪地弄湿的袜子,挂到炉子上烘干。落下的水滴掉在烫热的铁板上,化为水蒸汽嗤嗤作响。小女孩由于午餐便当的事,自尊心被刺伤在自愧落泪。她注意到黑板和老师以外的一切,比如那片飞在教室里头的鸭绒毛。个人的主观体验被慢慢放大,形成一种迷幻的、带有童年记忆的游离效果。老师让不同的学生朗读课文,小孩子们都很认真听话。不过跟我们同龄时一样,要么拽长了尾音,情感饱满,过于夸张;要么逐字照念,有气无力,读得没啥感情。看上去,电影里的他们属于后一类型。
中年男老师不时驻足窗前,隔着玻璃,看着对面山坡上的积雪。镜头变焦,一下子就清扫了之前伊朗儿童电影的残旧错觉。比起伊朗人,锡兰还是有着个人专属的美学体系。出色的导演对于真实距离和窗框构图都着独特的表现力,称得上所见略同。隔着玻璃窗户的几组镜头,在《远方》和《气候》等片里都有出色表现。
第二段故事有了林中的风,一阵阵的风吹起,跑到姐弟俩人身边。他们忙着摘枝头李子,穿过树枝的阳光在地上投下了色块分明的阴影,明暗来回游走变化。时间流动迟缓,不为周围人察觉。整段的场面调度和视听语言都十分出色,游乐场里的叫喊声,音乐的高低变化,时有时无,像极转晕了头的人们,又是一旁人物百无聊赖的真实体验。空镜和特写镜头在这一段被多次运用,苍蝇侵犯着驴子的眼睛;一番争论后,火光下爷爷额头的皱纹、眼睛、耳部,父亲和堂叔因为据理争执表现出的不同神情,不耐烦或小沉默。
到了林间,一家人围坐在野外生起的篝火边上,夜幕下火光摇曳,简直有些难以想象的美好。篝火,夜晚的风,大人们的话,到后来的咳嗽,狗叫,放诸于我,找到一个契机圆了心中所往。孩子们把时间用在了长大后记不起来的顽皮事上,也会一直记得曾经捉弄过的疯子,出于人类本性里的欺凌弱小,他们捉弄的小动物,有时候也变成童年的梦魇。
影片在这一大段插入两段非现实的画面,一是小男孩在爷爷的一战故事里入睡,不管伊拉克和印度在何方。讲故事的声音再一次高低变化起伏,小男孩做了个噩梦,梦见母亲从窗台摔下。堂叔用牢骚表达着自己的不满,对其他人的讲话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他发表异见,讲起自己一人去当兵:路边松树的味道,眼前的黄土路,变得真实起来。
曾在《刺杀神枪侠》里费尽心思地讲解了听故事的体验,这里出现一个相似的场景。昏昏入睡或者说本来就是希望你安详入睡,它就存在于《小镇》的第三段中。听爷爷和父亲们的故事,这是真实不可替换的体验,但对于小孩子来说,长辈所说的东西太深奥,无法理解。小孩子会想是什么,会问为什么,却很难理清大人们自己都搞不清楚的事情。这是他们的幸福,不需体味世事的单纯。
借助爷爷等人口中的讲述,现下的时间被拉长,进入穿越几十年光阴的另外一个空间。讲述的时间超越了影片的时间,这部分的片长占用也是最长,也是锡兰小时候的独特记忆。锡兰的魅力在于不掩饰对小镇的认同与归属,里面包含着父亲带来的宝贵记忆财富,他所持有的不仅是一种尊敬加关爱。小镇给他成长带来的欢乐太多,它的变化与消逝,看在一个经历者的眼里,只会驱使他记得更深。这是怀旧情结的积累爆发,也是感性主义的培育。虽然没有外力的介入,锡兰成长后离开小镇。但小镇生活的美好却伴随着男孩的长大,在不可逆中的时间流动中催促着他去重拾,加以再现。
一条到处觅食的狗,一名路边静坐的老汉,寥寥几个画面,这就是锡兰记忆中的小镇和故乡。换作许多人,这样的情景人物也是亲近的,它们出现在每个人的记忆中又略有不同,有斑点的狗,抽烟、瞌睡乃至发愣的老汉。他们注定应该出现在成长过程中属于他们的合适位置上。你费尽心思去寻找记忆中不应忘记和错失的记忆,却不知这狗和老汉其实已是完整的解释。【080509】
http://ent.163.com/08/0930/20/4N49LAB400031NJO.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