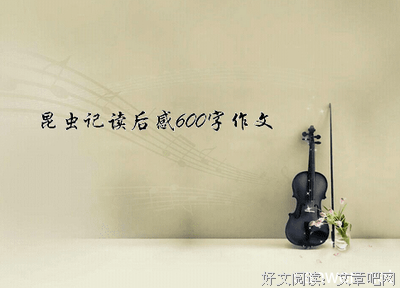《译者的尴尬》读后感1000字
《译者的尴尬》是一本由傅雷 等 著 / 郭凤岭 编著作,金城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3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老一辈的翻译家的翻译心路,看完很是感慨,现在认真搞文学翻译的没多少人了
●翻译有一段时间会上瘾,不知道别人翻译时有没有自虐的感觉,有段时间喜欢自虐,回想起来有点恐怖,反正很难,归咎于资质会不会把问题简单许多。
●虽然编者不是业内的,挑的这些文章,也算给翻译家办聚会了,热闹,有日语西语的。只叹:谁给文字工作者加薪!
●#2013088#
●这本书收录多位译者的感悟与思考,读完受益匪浅,感慨万端,恭敬与钦佩之情溢于言表。有人赞誉译者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想来当之无愧。 封面的话让我久久回味:“ 忠贞亦或是背叛,都无法回避这个时代的尴尬;是坚守孤独与清贫,还是一同媚俗和狂欢?”我想,这也是每一个潜心创作者的尴尬。
●这本书常常提醒我译者的生存困境,哪怕遇到糟糕的翻译作品也要宽容一些对待。可是现今大多数译者不是外语掌握的不好,而是中文素养太差,这点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原谅。
●肃然起敬!
《译者的尴尬》读后感(一):这书出的正是时候
巧合的是女翻译家马爱农正为维权与中国妇女的组织-全国妇联直辖的中国妇女出版社打被盗版官司。马爱农受到的是双重的侵犯:既来自文化出版单位的蛮横无耻盗版,又是来自本该保护女性的妇联组织,压力山大。这个时候出版社无耻推诿,妇联也不出来表态保护,这样的尴尬局面居然在一个文明古国和号称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伟大的国家里发生,是斯文与道德的悲剧,也是妇联组织的耻辱。而这一切都集中在一个女翻译家身上,标志这这个时代的芜杂肮脏。翻译家本就清高,却要在一个把法律当装潢的时代靠自己微薄的力量与恶人抗争,这个文明古国自己难道不尴尬吗?
《译者的尴尬》读后感(二):一锅大杂烩
整本书形成了一个略显散乱的总集,体裁上有约稿,有的看似书序,还有副刊议论杂文。内容上,更是涵盖个人履历回忆录、方法论、经验谈乃至一些牢骚话。由于每一篇文字的作者都不同,不能全在封面上体现,于是就简化为傅雷等。这可能是出版社夺人眼球的做法,毕竟傅雷先生是知名度最高的译家之一,好似翻译界的灯塔。书名也是从这些文章标题中挑出来的,并不是傅雷的那篇,可能那篇标题过于普通,书名却一定要选得有些特点,能给人带来遐思。
由于选文渠道众多,这些文章原本便是面向不同的读者,有些浅显,有些更偏重理论,有些谈得泛泛,有些以点及面,比较具体,读的时候有不小的落差。《翻译为什么重要?》一篇译自英文,略显粗糙,有个别句子读着费解,还有一些语句原文痕迹过重,这样的译文出现在一本探讨翻译的文集中实在遗憾。
有几篇给我的印象较深。朱光潜的《谈翻译》是能给初学者很大启发的一篇,方法论不过于理论化,用不晦涩的语言一针见血地指出常容易被忽视的问题。黄灿然的《给未来的译者》里提到的几点也非常中肯。几篇谈大家翻译历程的自述和访谈中,王永年的比较有趣,这是因为他有别致的生活态度,其余人的多少有些大同小异。单论趣味性,除了南桥的两篇辛辣诙谐,百看不厌,京不特的《漫谈翻译者的工作》也有让人捧腹的生动例证。这些都是文章自身的优点,非编辑之功。如果在编排时不是按时间断代,而是以体裁区分,可能阅读体验能有所改善。
《译者的尴尬》读后感(三):摘录
你能看到咄咄逼人、狂放不羁的作家和诗人,但从来看不到这样的翻译家,因为他们内心十分平静谦卑,仅仅把翻译当作一项介于学术和文学之间的严肃事情来做而已,并不认为头顶上那个“家”有多少光环,因为他们明白,如果自己翻译得好,成就大多归于原作者,如果翻译得不好,则是自己失职。—黑马
是的,翻译一位我们所喜欢的作家的作品,在我们既是一种献身也是一种享受。我们真的常常会忘记自我,变成作者的代言人或替身,将他所思所想、所经历的苦和乐再思想一次、经历一次,以致忘记了自己周围的现实,忘记了流逝的时间,忘记了工作的劳累。—杨武能
文学翻译家还必须爱自己翻译的作品和作家。但这种爱不应是痴迷的爱,神魂颠倒的爱,就像热恋者之间那样;而应是敬爱,是冷静的有分寸的爱,就像一位艺术鉴赏家之于艺术珍奇,抑或忠实的仆从之于贤明的主人。— 杨武能
尽管译者的名气难比作家,而地位又不及学者,还要面对这么多委屈和难题,翻译仍是最从容、最精细、最亲切的读书之道,不但所读皆为杰作,而且成绩指日可待。在翻译一部名著的几个月甚至几年之间,幸福的译者得与一个宏美的灵魂朝夕相对,按其脉搏,听其心跳,亲炙其阔论高谈,真正是一大特权。—余光中
作家的责任,在勇往直前,尽量发挥一种语文之长,到其极限。译者的责任,在调和两种语文的特色:既要照顾原文,保其精神,还其面目,也要照顾译文,不但劝其委婉迎合原文,还要防其在原文压力之下太受委屈,甚至面目全非。—余光中
英国诗人兼评论家柯勒律治曾说诗是“最妥当的字眼放在最妥当的位置”。如果译者也有相当的机会,来妥择字眼并妥排次序,则翻译这件事也可以视为某种程度的创作了。何况译文风格的庄谐、语言的雅俗等等,译者仍可衡情度理、自作取舍。其成王败寇的后果,当然也得自己承担。—余光中
“灵妃顾我笑,粲然启玉齿。”郭璞的游仙诗句呈现了多么生动诱人的表情。如果译成“灵妃看我笑,明亮露白牙”,说的还是那件事,但已面目全非了。……文言译为白话,已经大走其样,一国文字要译成他国文字,可见更难。—余光中
回想往日,少年气盛,提起翻译,多少有些自负。可是年齿加长,越来我越心虚。翻译何尝容易,某些译文,自己校勘出来的错误,远在热诚的读者指出来的数倍以上。—李健吾
创作如若是艺术,翻译在某一意义上最后同样也是艺术。我说的是文学作品的翻译。译者在这里从事的,不是机械地介绍作品的内容,而是企图把原作应有的全部生命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出来。最好的翻译总是通过译者个人的存在而凝成果实的。在凝的时候,首先却要结合着爱。—李健吾
然而翻译的困难,实在不下于创作,或且难过创作。第一,要翻译一部作品,先须明了作者的思想:还不够,更须真能领会到原作艺术上的美妙;还不够,更须自己走入原作中,和书中人物一同哭,一同笑。已经这样彻底咀嚼了原作了,于是第二,尚须译者自己具有表达原作的一副笔墨。—茅盾
《译者的尴尬》读后感(四):编后记
这本书最初在约稿的时候叫做《译者的任务》,与本雅明那篇著名的文章同名。但是在编辑的过程中,我被这些文章透出的情绪所感染。我突然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受,我说不清那是一种怎样的感受,更找不到一个比“尴尬”更合适的词来表达。读者现在看到的这本《译者的尴尬》,其实是编者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一厢情愿的自我认同。对于一个编辑而言,从技术上说,这是不对的,但从情感上说,其实挺难跳出来的。
书里收了南桥的《翻译和养猪经济效益对比分析》。一篇自嘲、讽刺又幽默的文章,很早之前就看过,很为方先生真诚的自我剖析所动。他说:“我翻译完一本书很得意,立刻就送给各个亲戚朋友,还有夫人,恳求夫人拜读,请朋友斧正。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拜读,也没有一个人斧正、指正、雅正。朋友看睡着了。夫人成天上网看巩俐章子怡,就是不肯看我的呕心沥血之作。”看了这段话,我想感同身受的不只是译者,一个写作的人,一个编书的人,可能都有过类似的经历。甚至这可能是当今时代跟文字打交道的人,所共有的尴尬。
这个年代只要是从事跟文学扯得上关系的文字工作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做下去,靠的无不是理想的支撑。但其实说到底,写书、译书、做书,跟养猪并不能分出个高低贵贱。除非你真的不用吃猪肉。可就算你真的不吃猪肉,别人还是不看你的书,你又能怎样呢?
没有人会为你的理想买单,无论是写书、译书还是做书,其实你都没有理由让别人一定去看你的书,就像养猪的人没有理由让别人一定去买他的猪肉,除非他的猪肉比别人的猪肉天然无公害。把书写好译好做好,也自然有人来看。无论做什么,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平常心。要做到黑马在《说说这悲摧的翻译事业》中所说的那样:“你必须要承受得住实际生活中亲友和故交及进取的同事们对你的忽略甚至轻蔑……别太强调自己的翻译家形象,人家说你没混好也别受伤……但自己内心要坚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坚持自己的梦想。”
这么一想,也就不尴尬了。但这时而尴尬时而不尴尬的状态,不还是一种尴尬吗?就像我们在分析别人的问题时可以做到客观公正,而一旦事情到了自己头上,我们却怎么都跳不出来了。我把自己编的书送给亲朋好友,不管我再怎么假装我不在乎他们看或者不看,当我确信他们压根就没翻过的时候,我还是没法做到一点都不失落。我倒是希望他们“看睡着了”,那至少说明他们看过。
写书、译书、做书,其实都是一种自我的表达,这种表达无不诉求关注,否则也就不需要表达了。译者的尴尬,首先是技术层面的:意译和直译,或者说“漂亮”与“贞洁”,也就是信达雅三者的平衡。其次是本质上的:对“翻译的可能”的思考,对翻译行为的意义的思考,进而是对实现译者自我价值的质疑。这两个层面的尴尬,最终都归到一个根本的问题:翻译是什么?而这个问题究竟有没有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重要的是思考,像袁筱一在《为了一种可能的翻译?》中那样思考:“译者是什么呢?他的所有意义或许就是提供或为读者欢迎或为读者拒绝——但无一例外都是“失败”——的翻译尝试和翻译结果。
这本书也仅仅是一个尝试。
编者
2013年8月9日
《译者的尴尬》读后感(五):译者“尴尬”有不同
《译者的尴尬》是一本讨论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生态的书,同时又是其中一位作者写的专题讨论文的标题。我借着这个由头,想在两个层面上简介此书内容。
此书的缘由好像是一次邀文,编者邀请各位在翻译方面已经小有(或大有)文名的译者(译家)对翻译这件事(工作/事业)发表感想,然后又从古人堆儿里扒出来一些专讲翻译的旧文,一共49篇,编在一起,结果就是这本书。我很庆幸码这段文字的时候想到了“生态”这个词儿,因为此书真的是一个“杂”字了得,涉及到了翻译这个行当的方方面面。
一个是时间跨度很大。第一篇鲁迅已经是百多年前的人物,最后几篇则是1970年代生人,四十多岁正当年——貌似此书就是按照出生年月排序的,除了最后一位没有出生年份。这么长的时间轴线上,翻译的本意,翻译的内容,翻译的方法,翻译者的自我感受,肯定有了很大变化,所以读着这些文字,不禁有穿越之感。比如,鲁迅讲翻译文字就是要有一些隔的感觉,要通过这个载体,扩展中文原有的狭窄。而村上春树的译者,则讲到日本对他翻译的一种指责,认为是帝国主义。
另一个是话题非常多元。从美学上、传播学上讨论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关系,自然是其中的应有之义。从翻译的态度、方法技巧等方面讨论如何用功,当然也是很自然的话题。除此之外还有两类篇目:一些篇目将翻译与人生交织起来,讲自己一生与某国文学(比如俄国文学)、某位作家(比如普希金或托尔斯泰)甚至某部作品(比如《叶甫盖尼.奥涅金》)结缘,成就了自己,甚至拯救了自己;另有一些篇目以戏谑口吻抱怨翻译如何被轻视(读者只认作家忽略译者)、被冤枉(书好看是作家的功劳,不好看是译者的问题),以及在实际利益上被剥削(译作不属于科研成果,稿酬低到地板价)等等。你可以看到,有的译者是因为对作家和书充满热爱才翻译,为此特别投入;有些则纯粹就是职业行为,需要什么就翻译什么,但也并不意味着不负责任。
我自己读过不少译本书,看到这些此前熟悉的译者大名出现,蛮高兴的。一些书虽然没有读过,但也听说过,看到对译者的介绍,“原来此书是他翻译的啊”,感觉也很亲切。看到这些人写那些柴米油盐的,还挺有趣,但也会有点失落,原以为他们不食人间烟火呢!看到另外一些篇目中显示的翻译与人生之间的各种纠葛,也忍不住扼腕叹息一番,个人这一份才华放在国家的跌宕起伏之中,真是无法掌控的脆弱啊!
说到翻译的本论问题,无外乎如何处理原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在直译到意译之间寻求解决办法。倒是那一篇专论《译者的尴尬》中说了一些与其他人不同的话。他把翻译分为技术、文学、思想三类,分别对应不同的原理:以技术为主导的翻译与语言学原理有关,例如语际转换的规律;以文学为主导的翻译与文艺学原理有关,比如风格、神韵等;以思想为主导的翻译与解释学原理有关,包含着诠释的因素,与思维和语言的关系有关。他还说,翻译意味着思想的转渡要依赖语言的转换而实现,真正的翻译首先要将思想从陌生的语词剥离开,然后用本己的语词重新装扮起来。所以,翻译之难在于,一方面是思想是否可以转渡,另一方面则是语言是否有能力支持思想的转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先要对思想有深刻的理解,为此可能要对思想做再构,对思想再做思考,甚至会比原作者更好地理解该思想,更好地表达该思想。在此意义上看翻译,所谓信达雅应该有重新给予定义:信,是思想的再构,要再思考一次,尽可能如实把握;达,是语言的重述,用自己的语言尽可能如实地、甚至更通达地表述原作的意义;雅,是风格的复制,尽可能如实地再现原有的风格,无论原作是雅是俗,是晦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