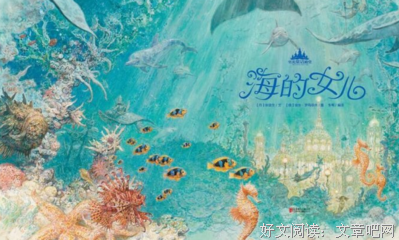女宾读后感1000字
《女宾》是一本由(法)波伏瓦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0.00,页数:2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有个人物表就好了,否则我还能给高点分。结局既骇人又在情理之中。可惜阅读过程太痛苦。
●弗朗索瓦丝完全成为可怜的附庸,无限退出自己成全对方的自大虚荣。怎么会有这样两个人如此热衷于用精神分析解析一个人的种种举止乃至陷入进可鄙的状态,多么像《登堂入室》啊。谨慎的人被自大的人操控,三个愚蠢的人,三个都活该,谨慎的那个最痛苦。
●重读了一遍
●不过是为了体面而失了体面
●大部头小说,有五百多页,每页字小行密,去年军训之前开始看的,军训结束才看完……除了被认为是一部存在主义小说外,小说表现和思考了「open relationship 」的真实的现实的困境也是不能被忽略的。要看到,嫉妒与占有,既是社会历史建构出来的,也是人的本能,作为人类情感状态的一种探索,开放式关系前景似乎很黯淡。其他的,好像没什么了。
●哲学家的洞见,用在小说上,既是优点,也是缺点,优点是准确,缺点是囿于准确。作者的用心高度概括在引言黑格尔的那句话里“每个意识追求另一个意识的死亡”。透过三人关系的复杂博弈,可以更好的看到其中的情感纠结,但“二生三,三生万物”,两人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如果仅仅认为本书是作者的自怨自艾,那就真辜负作者的良苦用心了。
●好
●they just talk all the time and do nothing
●几年前读过。从文学角度来说,这部小说人物有点脸谱化。但它作为存在主义演绎的工具来说,也情有可原。对存在主义的思想,它多处都有容易理解而又精彩的诠释,比如开篇弗朗索瓦丝穿过走廊去街上透透风,走过的那段路,她的想法和感受。高度关注自我,自我与外界的关系,并从中感受自己的存在。最后,弗朗索瓦丝选择自杀,使整个小说的格调从一出庸俗的三角恋,瞬间变成为自由和存在而抗争的斗士。批判,超越,这是其意义所在。现实中的波伏娃也由此获得了重生。
一直对波伏娃和萨特的爱情充满好奇,也从一开始就直到波伏娃在这份感情中的抓狂和失望。后来听说《女宾》是她的自传小说,她在书中把萨特的情人写死了,遂买来看看——那个时候我也在经历不好的事情。最近看完这本书,唏嘘不已。
面对皮埃尔反反复复与她人的爱情,佛朗索瓦斯一直在等、在忍——痛苦地等他们分手。这次是“三重奏”。三人无论是共同出现在酒吧、伊丽莎白家,还是聚会,甚至佛朗索瓦斯的病房里,皮埃尔和格扎维埃尔都“肆无忌惮”地或互递暧昧的眼神,或打情骂俏,或闹情人间的矛盾;单独与皮埃尔相处,他对格扎维埃尔失魂落魄的上心表露无遗;单独与格扎维埃尔相处,她对佛与皮的爱情的嫉恨满满——可见每个女人都有独占欲……她甚至还要安慰他们俩、帮他们和好!她的心多少次失望地震颤了一下,她多少次觉得自己从巴黎的中心被流放到了世界的尽头,她面临多少次崩溃……佛朗索瓦斯难过得那么隐忍和克制,无声无息,却总令我为之心痛得不能自已。
在工作中,佛朗索瓦斯是出色的、优秀的。皮埃尔是她的好搭档。如同伟大的波伏娃也有个好搭档——萨特。他们互相引路、指导,也互相成就。
书中,佛朗索瓦斯亲手杀死了她情人的情人,我猜现实中的波伏娃应该也对她情人的情人恨之入骨吧,但在现实中她怎会去杀了她们呢?她和情人是有约定的呀!
书中,她爱上了热尔贝。这是否对应着多年后的现实中向她求婚、送她戒指的那个美国爱人呢?——她还把戒指带入了坟墓呢!
(1943年写《女宾》,1949年内奥松求婚)
据说波伏娃也不一定是真正爱内奥松,她爱的大概只是萨特缺少的那部分。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她是选择能给她一生安稳的人?还是能互相成就的皮埃尔?
强大、伟大如波伏娃,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不喑俗世如格扎维埃尔,也想独占所爱之人~
何况平凡如我。
书中有很多精彩片段,我很喜欢。
大道上,秋雨未停
夜阑人寂,我侧耳细听
那心声多么凄婉
沉重的脚步声伴你而行
在他手指间溜过去的所有年华在他看来仅仅是一段匆匆而过的、无意义的时光,但是却构成了他独一无二的生活,他将永远不会经历任何其他的生活。
“我的情况是存在盲目的执着精神。”皮埃尔说,他笑了笑。“你知道蜜蜂吗,当人们在它们巢房深处挖一个大洞时,它们会带着同样幸福的心情继续往里吐蜂蜜:这有点像我的形象。”
《女宾》读后感(二):《女宾》的困扰,萨特和波伏娃如何破解?
《女宾》的故事来源太具体了,以至于我们都会很自然的想到这就是波伏娃和萨特真实关系的写照。
这样想不能说不对,但我想作者的意图应该远不止于此。
故事中的情绪是真实的,作者的困扰应该也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自然会认为三个人的关系是没有出路的困局,言下之意,常规的二人之间的关系才是正常的、和谐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并没有这么说!
先回到小说。
故事中作者困扰于这种关系没有出路,并且以自杀的极端方式获得解脱。同时,故事中的皮埃尔,就算不是猥琐,至少不是正面的,字里行间,看不出弗朗索瓦丝深爱他的理由。
但相反的是,现实中,作者和萨特一起走到了最后。
毋庸置疑,萨特一定也看了这部小说,他也一定会通过小说,看到波伏娃的困扰。问题是现实中,萨特和波伏娃是如何获得和解的?
先绕个弯,我们看一下通常作者都是如何通过小说表达自己的。
一般情形下,作者通过小说提出问题、表达困扰,这困扰有或没有答案,并不是他们的重点。多数情况是,至少在写作的时候,没有答案。不幸的是,很多作者最终也没有找到答案,甚至自我沦陷,这样的作家不胜枚举,文章也往往杜鹃啼血、字字珠玑。比如海子、太宰治。
还有如歌德,通过《少年维特的烦恼》给自己爱而不得的热恋一个交代,然后就放下困扰,开始新的生活。可是歌德走出来了,读者却没有走出来,那些读了《少年维特的烦恼》而自杀的少年留下了多少的唏嘘。
还有种作者后来找到了答案,或者其实在写作的时候就有了答案,这种作者往往理性大于感性,比如加缪,比如波伏娃,这是哲学家的高明之处,但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小说的感性,这或许就是有人说他们不是一流小说家的症结所在吧。
那么,波伏娃的答案是什么呢?
其实,引言黑格尔的那句话因为太有力量了,所以在我读小说的时候,通篇都印在我的脑海里,这或许就是问题的关键:“每个意识追求另一个意识的死亡”。
这和萨特“他人即地狱”的说法如出一辙。
波伏娃的困扰、挣扎,指向萨特,但仍在萨特思想的统摄之下,看到这句话,看到自己权力意志的绽放,我想萨特内心应该是在微笑的。
哲学家们太清醒了,“认识生活的真相之后仍然热爱生活”这种事,只有极富理性的人才做得到。对存在主义哲学家来说,“生活的真相”是什么?荒谬、徒劳、无意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他人即地狱。
既然这是生活的真相,生活于其中的人,怎能不受其困扰,怎能不痛苦呢?
有人会认为有些哲学家太悲观了,因为他们说出的真相总是显得如此的丑恶。比如叔本华、尼采。其实,或许不是悲观,而是深刻。能直面生活的丑恶,痛苦清醒的生活,是需要勇气和力量的,对他们来说,无所谓悲观、乐观,只是事实如此、无可回避而已。
对波伏娃来说,人与人关系的本质就是“每个意识追求另一个意识的死亡”。三人之间的关系如此,两人之间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周围两人之间关系的无奈和仇恨难道少了么?
既然如此,三人还是两人并非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人与人相处中,把“每个意识追求另一个意识的死亡”作为真相来认识、接受。
萨特不是圣人、波伏娃也不是圣人,都是人啊人!自私的群居动物。
所以,我们也无需太过悲悯,因为本性让我们痛苦,如此而已。我们能做的或许是,约束一些本性、保留一些本性;给别人一些温暖,也保持自己的独立。
《女宾》读后感(三):不速之客——波伏娃与《女宾》
我怀疑读者如果无法自行想象朗索瓦丝和皮埃尔就是波伏娃和萨特的化身,便很难对这部小说产生浓厚的兴趣。因为波伏娃似乎没有心思对人物进行较为立体的塑造,而只是让他们在时间中不断变幻着,唯一不间断清醒着的,就是弗朗索瓦丝或者波伏娃本人的意识,这种意识笼罩了整部小说,使它罩上了令人不快的主观阴影。
我奇怪的是,为什么弗朗索瓦丝会认为自己喜爱格扎维埃尔。她把格视为一个天真可爱的小东西,没有认真对待,对她的想法感到无足轻重,却又把她放在自己身边,似乎将自己视为一个庇护者,带有深深的自恋。然而纵观全书,无论是叙述者弗朗索瓦丝还是波伏娃本人,似乎都并没有真正刻画出、也就未必真正了解格扎维埃尔,而且,她们并没有真正的兴趣去了解这个女孩,也缺乏与其深入的沟通,实际上,在小说中,弗朗索瓦丝一直没能与格扎维埃尔进行真正的沟通,她能看见的只是她年轻光鲜的外貌上无数细微的差别变化,以及她似乎总是为了激怒别人而故意做出的言行,她从未进入格扎维埃尔的内心。
但我们几乎走遍了弗朗索瓦丝的内心,就像走进小说开篇的剧场——那个“硕大的空心薄壳结构”的内部,而这个壳子里的事物之所以能够具备意义,只是因为弗朗索瓦丝的喃喃自语触及了它们,也正因如此,我们几乎获得不到弗视角之外的感官。少部分以伊丽莎白和热尔贝视角的叙述因而显得新鲜,但这些叙述太快地又转回弗那喃喃自语的内心。弗朗索瓦丝几乎不与别人进行真正的对话,面对外界,她“几乎永远不去费心表述自己的思想”,为何如此?因为她完全活在自己思维的世界中,她无法真正地从客观角度理解他人,而是用许多的自我判断,将一个又一个人物在她心中的面貌向我们呈现出来,这让这些人似乎不过是她多种意识的化身。我们几乎无法将弗朗索瓦丝与波伏娃的意识相互区别开来,距离感的缺失,让这部作品更多地使用观察的手法,而并不是结构化的体察,因为流于表面,所以扑朔迷离。
甚至连其灵魂伴侣皮埃尔,也并不能和弗朗索瓦丝进行真正的沟通交流,她甚至不用去交流,因为皮埃尔的而一言一行仿佛都是出于她自身,因而不能让她从麻木的自我意识之流中伸出头来,只有当他谈论起格扎维埃尔,把注意力放在弗朗索瓦丝无法触及的区域,成为他自身时,她才如大梦初醒,却又感到从与他的同一意识体中分离的痛苦。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她所希望的,因为她似乎处于一种理应幸福却感觉不到幸福的麻木状态之中,她一厢情愿地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一个为她而永恒不变的人:“皮埃尔的名字永不可能激起痛苦……和皮埃尔永远不可能产生任何误会以及任何难以挽回的局面。假如有一天她试图自寻烦恼,他将能完全理解她,因而幸福又会回到她身边。”但是,她又“寻求欲望,寻求遗憾”,烦恼于自己“已经置身于一种一目了然的、无感情起伏的幸福之中。”
可以认为,正是在皮埃尔和格扎维埃尔及其他女人的感情纠缠中,弗朗索瓦丝才能感受到梦境与现实那道相对清晰的边缘,感受到自己的爱情之存在。但这种状态同时也是弗朗索瓦丝无力承受的,令人恐惧的是,在这种所谓的同一体之下,她已经放弃了自我,用“我们”去代替“我”,换句话说,她已经不习惯拥有自我了。因此,她又要马上呼唤皮埃尔给予的绝对化的爱情,来回到自己的安全地带——另外一个人意识的庇护之下,而并非如书前摘录的黑格尔所言“每个意识追求另一个意识的死亡”。
相比之下,虹影的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则显得意外的明快。在其中人物从不喃喃自语,她不断地和周围的人发生斗争,没有在自我中纠缠而一事无成的黯然,而是不断的行动。弗朗索瓦丝一直在思索,但几乎从不行动,争执都是周围的人引发的,她只期待某种永恒的平静安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她在现实面前是温驯的,她只是等待事情发生,从不引发,也不回应,她让自己处于梦境般的被动与模糊之中。
无论发生在弗、皮、格这个三人游戏中的结果和过程究竟如何,格扎维埃尔的存在对于弗朗索瓦丝来说始终是无足轻重的,这根本不是如她自己所描述的那样一个平等的三人游戏,在这之中,只有她和皮埃尔的关系才是永恒不变的,那第三个人无非只是游戏所需要的结盟,在游戏结束时也需要随时解约,但她和皮埃尔是不可以解约的,这是她随时希望确认的那一点。在书中,皮埃尔也被描述得非常理想化,他完全认同自己和弗朗索瓦丝的这种联盟,并真切地在弗每一个需求的时刻确认这种关系,然而他的行动却往往指向与这种真诚态度相反的方向。
伊丽莎白和克洛德的婚外不伦之恋,在书中只是作为一种补充形式,缺乏被描述的意义。这样的恋爱在波伏娃眼里永远没有终点,不像是她和萨特不证自明的爱情中具有的主导性,伊丽莎白像一个没人愿意理睬的可怜虫。尽管她具有艺术家的高超品位和自己谋生的双手,但这一切怎么能与轻轻松松、身着华服出场的弗朗索瓦丝相比呢?伊丽莎白的衣服即便合身,也只是穿旧了的,她为了指甲油懊恼,她发觉吸引弗朗索瓦丝和皮埃尔深度注意的格扎维埃尔不过是个不值一提的小姑娘,然而比起格扎维埃尔,她更不被波伏娃喜爱,即便弗朗索瓦丝给了她少许怜悯,劝格扎维埃尔不要蔑视她。
弗朗索瓦丝本来希望格扎维埃尔成为自己和皮埃尔之间的小玩具,但她发现自己对这个玩具根本没有兴趣。于是三角关系变成了四角关系,她也需要一个自己的情人,好让皮埃尔感到对等的痛苦,于是她选择了热尔贝。热尔贝这个人物的存在感比格扎维埃尔还要微弱,他仿佛只是为了成全弗朗索瓦丝的自恋而出现,对弗无甚深入接触却一往情深的爱恋,能够突出弗与其他庸俗女人的区别,弗朗索瓦丝甚至通过他间接地击败了格扎维埃尔,因为波伏娃让格扎维埃尔只对热尔贝一见钟情,甚至献上了自己一直坚守的贞操,但热尔贝却毫无保留地选择了弗朗索瓦丝。每次,和热尔贝在一起的弗朗索瓦丝,都像是她自己希望的那个独立自由的女人,而不是和皮埃尔在一起时候那个软弱无力的嫉妒者,然而弗朗索瓦丝却不能在这个关系里感受到单纯的快乐,因为她只希望利用热尔贝,作为她那份永恒爱情祭坛上的羔羊。
最后,波伏娃选择让弗朗索瓦丝开煤气杀死格扎维埃尔,这并不是一个很阴暗的结局,对于作家来说,让角色死亡简直是最唾手可得的简便途径。弗朗索瓦丝没有在事实上杀死格扎维埃尔或者自己,“不是她便是我”,无论二者谁消失都没有区别,都可以让那个悲观的自己、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被轻易卸下,让死亡干干净净地解开一切淤积缠结的关系,回到不必思考、充满安宁的初地。而似乎作为主题的“女宾”,从来只是偶然造访的一位不速之客,是印证了一段理想化爱情,又必须被驱逐的对象。
《女宾》读后感(四):萨特是渣男吗?
波伏娃的处女作《女宾》常被看作是她的自传式小说,在这本书里面非常详细的记录了她与萨特,和加入他们的奥尔加,三人之间真实的情感纠葛。
关于买《女宾》这本书,还有一段小小的“历史”。它是我在2017年去台湾的时候买的,当时行程的最后一天,我们去到台北最大的一个书店,楼上楼下逛了几圈,买了一堆文创产品。挑来挑去不太习惯竖版繁体字,于是无奈之下就挑了这本从大陆运过去的简体字版本的《女宾》。
回来之后看到一半,被字里行间的痛苦情绪折磨得崩溃,数次想把它卖掉,但是又想到毕竟这么远背回来不容易,于是又默默放回去,搁置到今天书页都有些发黄了。
前阵子整理东西又想起这本书,于是又再次拿起来,这回花了三天时间,从头到尾仔仔细细,逐字逐句地又看了一遍,觉得这本书真是不负声望。除了他们的爱情之外,还让我们看到书中人面对人生鲜活又矛盾的人性。
走在前面的艺术家们
看完这本书之后,上网找了好多关于这本书的评论,发现大家都各自把自己的观点套在了这本书的人物上面。有一篇文章完全把波伏娃当成了“受害者”,换句话说,波伏娃是与萨特关系里的弱势方,用今天的话或许就是被pua了。刚开始看那篇文章,觉得有理有据,心想确实就是这样啊。然而整本书看下来,又想到萨特与波伏娃此后的一生,觉得作者实是看扁了波伏娃,也看扁了萨特。
按照精神分析的理论,我们总是会看到我们自己想看到的东西,会在不自觉之间把自己的想法投射在别人的身上,所谓万物皆可投射。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把自己俗人的情感、认知投射在名人的身上,再寻找证据佐证自己的“偏见”。其实要理解他们的爱情,就得先放下我们心中既有的爱情道德观,放下我们心中的柴米油盐。
艺术家是走在人类前列的那一批,他们更勇敢,身体力行地试探人类关系的边界,努力帮助人类走出一条更加自由的路径。艺术家们不同于我们芸芸众生,他们专注于务虚。尤其是萨特和波伏娃这种青史留名的大人物,他们和我们,更加不同。
爱情是否真的容得下第三人?
在小说中,波伏娃和萨特的名字分别是弗朗索瓦丝和皮埃尔,第三人格扎维埃尔是从小镇鲁昂来到巴黎的年轻小姑娘。故事的情节非常简单,三人试图建立互相热爱的爱情“三重奏”,但遗憾的是,在三人拉拉扯扯的关系中,充满了嫉妒和猜疑,最终饱受折磨的弗朗索瓦丝打开了煤气开关,结束了这一切。
皮埃尔在书中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戏剧导演,他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演员。故事里面他们正在排一个《尤乌利斯. 恺撒》的戏剧,而皮埃尔既是导演,同时也是演恺撒的演员。皮埃尔的形象正如恺撒大帝,他的才华,他的魅力,可统摄一切。他的存在赶走所有的虚无,让所有的庸常瞬间有了意义。他反对一切的规则和束缚,他是自由的。
而格扎维埃尔是一个情绪无常,看不惯一切的年轻女孩。她就像许多年轻时候的人一样,内心总是涌动着一些情绪,时而自卑、时而自负,急于寻找自我、确定自己。她当然是有生命力的,或许正是她这一股莽撞的、单纯的、狡黠的、无知的、尖锐的劲儿,引起了皮埃尔的注意。她在面对弗朗索瓦丝的时候,“那张孩子般的、无戒备的脸上会毫无顾忌地显现厌恶、快乐、温柔的表情”。而在皮埃尔的面前,“她意识到自己是个女人,脸庞上准确无误地表露出她所想表露的细微感情:信任或保留”。
书中的弗朗索瓦丝是矛盾的,她试图维持三人的平衡,她极力否认和掩饰自己在其中流露出的嫉妒情绪。她努力去爱格扎维埃尔,安抚她,抓住每一个幸福的感觉。但事与愿违,她的感受是真实的,痛苦是真实的,她最终无法欺骗自己。她徘徊在和皮埃尔既定的自由规则,与真实的内心感受之间。她虽然觉得深深的受伤,但对这段关系却没有任何反对的立场,她也是共谋者之一。她言不由衷,一边在内心体验着无边的失望和无尽的痛苦,一边在表面上拼命掩饰,用完全相反的温言软语来维护这表面的和平。她像是拼命披上一件明明正在滴水的衣服,她一边想知道自己能不能和湿衣服共存,一边又无法忍受这湿衣服带来的不适。她只好假装这衣服是干的。
在看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在不停的问弗朗索瓦丝一个问题,既然这么痛苦,为什么还要持续下去呢?为什么不能快刀斩情丝?转身离开不可以吗?
真实的波伏娃和萨特很早就没有了性关系,甚至他们一开始都没有从性上共同获得过愉悦。
社会心理学里面认为爱情是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激情状态下的爱情保鲜期只有18到30个月。
波伏娃和萨特之间的关系,不是性,不是短暂的激情,更像是一种纯粹精神意义上的共振。
书中当弗朗索瓦丝和皮埃尔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细微的感受放在显微镜下细细揣摩。他们释放自己敏感的触角,互相交流每一种思想,每一种看法,让它们彼此拥抱。我们普通人会常常觉得孤独,源于自己不被理解,自己的想法找不到伴侣,但为了过日子,我们不会细究自己的每一个感受,会得过且过,会难得糊涂,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萨特与波伏娃,他们的每一个想法都能在彼此身上找到伴侣。情人如流水,这样的伴侣却是人间难得。
他们的关系本身也是一种权力的博弈。
这本书在写之前,萨特已经在巴黎的文艺圈名声大振,而彼时的波伏娃活在萨特的才华阴影里,没有身份。她在书中写“他是她的知己,如同她了解自己一样,但同时他也是不可知的。”她和萨特的自由关系在刚开始的时候是单方面的,她被动的参与。在小说里弗朗索瓦丝也是忠贞的,她说自己不是一个沉迷肉欲的人。一直到了小说的最后,她才终于直面自己的情欲。
然而再伟大的艺术家也是人,爱情总是自私的。俗世的占有,与精神的灵性时时刻刻发生着惨烈的战斗。面对进击的格扎维埃尔,热恋中的皮埃尔,弗朗索瓦丝觉得自己被孤立了,“她原地呆立,与他、与众人疏远了,与己也无联系。她被遗弃,却从中领悟到真正的孤寂感。”
这场爱情的实验,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在阅读中看到多元文化和价值
波伏娃在这本书里安放了自己的所有不适,此书的出版也让她在存在主义领域获得了声誉和地位。她的这次写作,让自己得到了解脱,但是对于我这样的读者来说,看这本书的时候却是经历了一些小小的挑战。
书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好好过日子的,他们昼伏夜出,整天泡在咖啡馆、酒吧里,有人安然地插足别人的婚姻、有人公然劈腿、有人毫无负担地在异性和同性之间游刃有余。当时的我生活在保守,退缩的价值观念里面,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沉浸于各种爱而不得,为什么他们都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去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其实现在想来,当一个人的三观特别容易被震碎的时候,在批判之前反而要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是否是自己的边界过于狭窄,容不下更多元的文化与价值。
就拿格扎维埃尔来说,在她之前,剧场中的许多女孩都曾经和皮埃尔发生过一些肉体关系,她们不重要。只有她是不同的,恰恰是她的不同,带给了弗朗索瓦丝无尽的伤害。但她是错的吗?弗朗索瓦丝在书中几乎穷尽了所有词汇来描述自己的矛盾情感,她给格扎维埃尔和这段关系留下了许多的余地。她深知,她们的本性让她们无法相爱,但狩猎者的本能又让她们彼此猜忌。三人行是困难的,或许萨特想象中的稳定关系只能存在于他的理想世界里。
萨特是否是渣男?
当许多评论把波伏娃当作受害者的时候,萨特自然就站到了对立面。但是以一个“渣”字形容萨特是不公平的,因为他在这个规则里面并没有执行双标。他是公平的,小说的最后,弗朗索瓦丝把自己和热尔贝睡一夜的事情,写信告诉了他,他真心地送上了祝福。他对自由的追求一直一以贯之,他不想束缚自己,也不想束缚别人。是波伏娃选择了萨特。
我在想为什么许多评论文章枉顾这些细节,总是偏执地要把萨特当作一个渣男呢?或许是在我们的文化语境里面,“受害者”是一个有利的位置,占据着道德高地。在两性关系中,只要给对方冠一个渣字,似乎就站稳了这个位置,也就逃脱了反思成长的责任。其实复杂的人性哪有一个渣字这么简单?
现在有一个说法是,有一些女生似乎有“吸渣”体质。在她们真实的经历里面,总是上一个“渣男”带来的泪痕还没有干,下一个“渣男”已经在来的路上了。为什么陷在这样的循环里面无法自拔?或许可以尝试放弃受害者的位置,把自己主动放在两性天平的两端,才能获得成长和真正的幸福吧。
《女宾》读后感(五):波伏娃的女性主义拓荒史
波伏娃,百度百科上是这么介绍她的:西蒙娜·德·波伏娃,法国著名哲学家,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萨特的终身伴侣。法国总统希拉克曾在一次演讲中评价说:“她介入文学,代表了某种思想运动。在一个时期标志着我们社会的特点。她的无可置疑的才华,使她成为一个在法国文学史上最有地位的作家。”这是后人对已经拥有盛名的前人的赞誉——说实话,赞誉总是最不费力气的事情,而波伏娃本人绝不止于赞誉——作为一个女人,波在哲学领域,文学领域和女权主义领域皆是当时时代的翘楚,她的女权理论名作《第二性》揭示了“女人非天生而是被造成的”这一真理;对上述理论的小说版演绎《女宾》,则从实践角度探讨了男女两性关系——确切的说是人与人之间的性'爱关系的可能性。《第二性》在论述女性发展和存在现状等一系列问题时,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波伏娃引用的主要论据都来源于小说,比如劳伦斯,司汤达,柯莱特等人的小说。当然,艺术来源于现实,小说也是。所以拿来引用无可置疑。但我们能否从这一特点中看到另一个事实呢?即,波伏娃作为一个开拓者,她在思想领域中的披荆斩棘是非常艰难的——除了散碎的有关女性的集体无意识的记忆,小说家对女性的描写等等这些不成体系的资料,她从前人那里得到的唯一成体系的理论性的助益看起来仅仅来自于弗洛伊德。
这种艰难也同时反映在她的个人的成长史中,对此,在最接近她的生活的《女宾》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读这部小说,有助于我们从她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一角度,更立体的理解她的思想和作品。无论一个作家写作时多么晦涩,都无法隐藏他的世界观,价值观。一个人的作品,就是她个人的历史。《第二性》中波伏娃也说,生存不是城市案卷里记载的抽象命运,而是富有肉感的未来。波伏娃的生存,是一场艰难而丰富的拓荒史。也许我们沿着她曾走过的路再走一遍,会尽可能的接近风起云涌的二战时代后的波伏娃。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是以革命为主题的年代。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在第三世界国家兴起。而伴随着大环境的变革,社会风气也会相对宽松,由此,社会中的劣等性别——这只是个尊重事实的称呼——女性,便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波伏娃也生活在这个时代。如果试着摸索波伏娃女性主义拓荒史,往时间的纵深处眺望,你可以看到浓墨重彩的三个点,自我经历,《第二性》(存在主义)和《女宾》。而在横向上品味,有两个关键词:女性,人性。《女宾》作为小说最易理解,或许我们可以立足于此,勾勒出波伏娃的脚步所及。
《女宾》中有两个女主角,弗朗索瓦丝和格扎维埃尔——为了方便我们简称为弗朗和格扎。弗朗,法国典型的女性知识分子,现实中对应的是波伏娃本人。长的一般,靠脸吃饭基本无望,平时也不打扮,只专注于写作和话剧,有一个灵魂伴侣皮埃尔——现实中对应的是萨特。弗朗属于典型的有脑无色(请注意,弗朗因关注其他而忽略了自己的容貌,她本身如果打扮也很美,这一点小说有有所提及)。本来弗朗和皮埃尔这一对才华男女在巴黎的咖啡馆、剧场过着思想充实,生活忙碌的日子,也算是神仙眷侣。但是——现实生活总喜欢给人时不时来一个“但是”——格扎出现了,打破了这一平衡。
格扎,我们常见的那种漂亮无脑的女人。在《第二性》中,波伏娃毫不留情揭露说:“所谓的女性气质,就是显得软弱,无用和温顺。”格扎就是这样一个颇具“女性气质”的人。《女宾》中对这个角色的设定,可谓是用心良苦。格扎被设定为一种女性的代表人物,她很漂亮,其容貌到底有多美,小说中没有具体细致的描写,但是她一连吸引了弗朗、皮埃尔和热尔贝三人,除了容貌我实在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在起作用。当然,只有容貌还是不够的,她身上还有一种难以克服的掩盖在叛逆之下的懦弱。一开始,所有人都会被她吸引,她的天真让人喜爱,但彻底的叛逆的态度又容易让人产生不适感。她企图否定一切,而这否定似乎只是为了她的懦弱无为做背书。在读小说时,我会想,如果格扎按照弗朗说的去做些什么,比如学着演戏剧,会怎样?但下一秒我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她不会的,这不会发生。因为她的存在就是不做(do nothing,just being),只无止境的消耗自己,和身边的人。
格扎作为一个被塑造的女性,天生就具有占有和独享的强烈欲望,这欲望几乎与她的生命混为一体,合二为一。弗朗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女人,她有强大的世界观,重视概念且理性,重视道德、友情和爱情。她的存在,也是道德的存在,她是一个自我构建完全的人。而皮埃尔在这段三人关系中更像一个过客,他有才华,不愿被束缚,他的才华迷倒了格扎,他用无意义的概念约束着弗朗,他乘兴而来,兴尽而归,剩下两个自始至终都在挣扎的女人。波伏娃用冷酷的笔触,向我们揭示了这段现实中为人所称道的三人关系,其实从一开始所有当事人的姿态都南辕北辙。
弗朗在人的欲望和已经构建完成的自我之间挣扎,一开始她服从自我,以强大道德感约束自我,乐于在与皮埃尔和格扎的三人关系中表现的积极快乐,用以掩盖那些无处不在的刺痛——这也许只是现实中波伏娃在与萨特、奥尔嘉关系里的无数次刺痛的缩影。后来,她在欲望的驱使以及格扎的伤害下,她倒向了欲望。跟热尔贝上床,与皮埃尔私相往来,背着格扎传递诉说爱意的信件——这对格扎是致命的,因为格扎的命,她的存在就在皮埃尔或热尔贝身上(或者任何一个出现在她生命且完全属于她的男人)。当他们集体背叛她时,她的自我就变成彻底的虚无和自我厌恶。她像一张白纸,只是这白纸不是用来写字或者画画,而是生来为了燃烧成灰烬。她成了灰烬。
《女宾》的“宾”这个词,是指客体。那么,女人这个客体,所指向的主体是谁呢?是男人,还是整个客观世界?也许都有。我们无法探知格扎的过去,她好像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姑娘。我们只知道她来自鲁昂的乡下。在鲁昂,在巴黎,在法国,在欧洲以至于世界各地,都有千千万万个像格扎一样的姑娘。在这些地方每天都有可能发生的事实是,无数个皮埃尔让无数个格扎爱上自己,当她有背叛行为又抛弃了她。格扎是皮埃尔骄傲自大的男权的牺牲品。格扎没有为此自杀,但她的某种内核已经毁灭。(这种内核是什么呢?是人性的本源,还是对未知世界的热情?亦或是《第二性》中所说的“主体”的地位?)
而弗朗觉得她要为此负责。她的道德感让她做不到袖手旁观,或者置身事外。弗朗最后的死亡,恰恰是被道德杀死。她的自杀不是偶然,而是早就在那里等待着她的。她终于做了有违道德但顺从自己心意的事情,可是她的内心不安。在小说的后半段,我们可以读到一种倦怠感。这是小说中的弗朗,她一直在求死。她的良心在谴责她,她转身去自己房间打开煤气的片段,看似仓促,其实也许,她在心里已经练习了千百遍。当生无所据,死就成了最适合的命运。她主动选择了自己的命运。
格扎和弗朗对应的是女性性格中两个极端:极度懦弱和极度理性。但结局却超出了人们的日常所见:本该自杀的没有自杀,无需自杀的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一讽刺性胜过悲剧性的结局,是对男权社会最深刻的鞭笞和控诉——作为一个女人,无论你是被创造的还是自我创造的(部分的),懦弱的亦或理性的,都逃脱不了男权的罗网。
同时,小说探及了人性的阴暗面。皮埃尔的自私和占有欲,格扎的嫉妒和愤怒,弗朗的撒开手和背信弃义。这段三角恋最是丑陋不堪。可,仅仅是这段关系么?不,波伏娃指出了整个人类的劣根性。波伏娃在《第二性》最后,描述了一幅男女皆在一种女性解放后的新型关系中自由徜徉的美好画面。现实生活的实践,却并不因波伏娃的个人的期许和意志而有任何进步。而在小说的最后,波伏娃选择了死亡。有人说,波伏娃在《女宾》中杀死了弗朗,所以她在现实生活中能够生存下来。但我更愿意把这理解为一种殉道的倾向。所有的伟大开拓者同时也是殉道者。她主动选择的死亡有力回击了自以为是的男权社会,引导人们思考,惊醒人们去改变,这才是其价值所在。
备注:本文所说的“道德”并非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道德,而是指波伏娃以存在主义为指导的弗朗,她的存在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