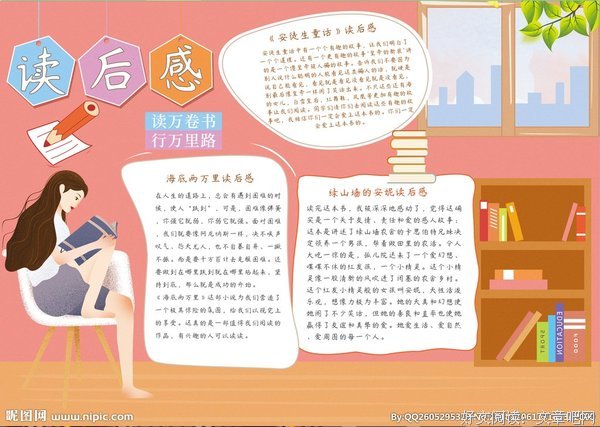《明代的社会与国家》经典读后感有感
《明代的社会与国家》是一本由[加] 卜正民著作,黄山书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页数:32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卜正名真帅啊~他又出了一本新书《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分析问题丝丝入扣,文笔也很好。
●国家对地方管控程度:*北方水稻、地图、藏书楼、书籍审查*、度牒
●讲了半天等于什么也没讲的书,中国自古县以下士绅自治,这难道也算特色?西人治中国史,最强项的还是清史,尤其近代部分,其他都隔靴搔痒的很
●比“那些事”还是耐读的
●除了写明末清初华北种植水稻的论文有趣外,其他的总感觉温吞水,没有深入问题。
●很多问题浅尝辄止
●还是改成四星吧……
●今天讀到陳時龍關於明代書院在地方志中記載位置的論文,文末引用卜正民關於寺廟興廢與國家關係,覺得奇怪,所引用并沒有強烈的必要。後驚覺,原來是《明代國家與社會》的譯者。卜此書,老師推薦為明代研究入門書。啊,試圖往明代文學靠攏而實在被影響成歷史研究的尷尬。
《明代的社会与国家》读后感(一):“社会与国家”or“官治与乡约”?
中国久已有之的地方乡绅的桑梓情怀在本书中有了个新鲜但逼格平平、感觉似乎又未尽其义的名称“社会制造”,文中又时时出现将定语置于主句之后的英语语法,大概暴露了本书译者的中文水平没有那么高,所以做不到信达雅,这降低了本书中文版的学术价值。本书的英文书名《明代的中国官治》被扩展为《明代的社会与国家》就是译者试图更贴近原义而不得的败笔了。
在维基百科词条The Chinese State in Ming Society中有这样的描述:The book is an "account of events and issues that engaged the members of local elites in Ming society and of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se elites and the state,"...Brook argues that the model of despotic government fails to account for the complex interactions between individuals, groups, communities, society and state in this period. Instead he proposes that by 1500 the Chinese had a remarkably developed system of governance, surpassing that of the European monarchs of the time, and that the developments were not the result of the isolated actions of the state, but rather of a complex interface and interaction, including local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tate such as magistrates and local networks of the elite class of gentry.[1] According to Ellen Soulliere in her review, Brook argues that "society had the [enduring] ability to constrain, limit and sometimes redirect the authority of the state, without challenging its most basic claim to be the source of all legitimate authority."据此来看,似乎翻译为“官治”(the state)和“乡约”或“乡绅之治”(local elites)要更为贴切一点。
这样一来,本书的论点就没有那么新颖了。官方自上而下的权力延伸到一县之治后戛然而止,地方乡绅填补了县丞和草民之间的空隙,一方面成为国家治理的帮办,一方面又成为地方社区的领袖和代言人,官府和乡绅之间自然产生了权力进退和频繁互动。这是已经广为接受的定论,无需再多饶舌。而从引言来看,似乎西人一直大而化之地将中国的传统治理模式认定为专治,而不曾留意到最底层的乡绅阶层。因此本书的价值大概在于有理有据地例证了这一公理,又将其介绍给西人而已。
此外,卜氏在书中对中国这一传统悠久的治理模式大加赞扬,认为胜过同期的西方宪政。考明代中国之强盛,所言当不谬也。
《明代的社会与国家》读后感(二):关于第二章所用材料的疑问
因课程原因只细读了第二章《叶春及的方志图》,其文主要叙述了明中叶士人叶春及在任福建泉州府惠安县知县时组织编写了一本基于实际统计数据的《惠安政书》,其中的数幅地图因与当时绝大多数方志的会意式、不讲求精确的地图大相径庭而显示出其重要的研究价值。只因想找史料细读,稍微核对一下便发现不少可问之处。
1. p71 :“我所使用的版本,是现存东京东洋文库的孤本,1672年叶春及《石洞集》重印本。”
按:叶春及《石洞集》收入四库全书集部,其总目提要曰:“次载《惠安政书》十二篇,其官惠安知县时作,共五卷。”篇目和卷数都与作者所用之版本无异,大概查阅了一下,这个版本也是有图的。惠安政书》东洋文库的单行本在1980年已经被傅衣凌带回,1987年经惠安县志办公室整理点校出版。作者另叶春及其事迹附见《明史•艾穆传》(卷二百二十九列传第一百十七),也不知为何作者言《明史》未载叶春及。
2. p73:罗洪先《广舆图》首次出版于1555年。这部地图册很为人称道,并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的世纪至少重印过五版(1558年、1561年、1566年、1572年、1579年)。
按:王庸先生在《中国地图史纲》的记载与此甚异,其言:“按《广舆图》的胡松、韩君恩及钱岱诸序,此图最先在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由胡松刊行;五年后韩君恩有为翻刻;到万历中,钱岱再次翻刻。现在北京图书馆藏本是初刻刊行本……”所查中国古籍善本目录导航系统亦不见1555和1558两个版本,或藏之海外,大陆不见?作者此段有注,行文所据小川琢治《支那历史地理》(p59-62,版本待查)和傅吾康《明代史籍汇考》(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8.1.3,手头有的同学可以帮忙查一下。
3. 此章多讨论到中国传统地图的问题,大部分基础观点都征引自日人小川琢治的《支那历史地理》,据查小川先生生于1870年卒于1941年,所著三本关于中国地理学的作品均出版于1935年之前(见维基百科http://ja.wikipedia.org/wiki/%E5%B0%8F%E5%B7%9D%E7%90%A2%E6%B2%BB),此后关于中国古代地图之研究尚有1958年出版的王庸之《中国地图史纲》,王庸先生长期在北京图书馆特藏部工作,此书亦精于文献考订,为经典之作,由第二点可知作者不知此书。如是因出版之时大陆尚闭塞,尚情由可原。可此章亦未参考作为芝加哥大学《世界地图史》项目的《中国地图学史》(“Cartography in China”,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ume Two, Book Two: 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 , ed. by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而作者此章曾于1994年发表过(据p67注),此番收入由又有编订,何不吸收最新之研究成果?
4.今日又检出一疑问处p85 注释【35】 称《肇庆府志》又称《儋州志》,因儋州是肇庆古称。
按肇庆古称为端州,查万历《儋州志》所记非肇庆,即今天的儋州市,在海南岛。两者读音相似,不知是否为翻译失误?
=======================
如此一例,大概可知所谓西方汉学家之桂冠,也不是很靠得住。后之学者慎之,慎之。
《明代的社会与国家》读后感(三):超越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思维,摆脱专制主义的刻板印象
看到这个书名,很多人应该能联想到这样的评价:“中国古代没有社会”,“强国家,弱社会”,“没有宪制意义上的国家”,对此卜正民做出了相当激烈的批评。他认为此类观点都是流行于冷战时期的“东方专制主义”和“欧洲中心论”之遗毒,而魏特夫的理论又可以上溯米留可夫、克柳切夫斯基,再到黑格尔、孟德斯鸠、霍布斯、洛克乃至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列这么多名字不是为了增强说服力,而是为了指出这是一种多么陈腐的观念。
将”国家“和”社会“视为对立的两极概念,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抽象模型,但也仅此而已。深入的研究应该抛弃这种习惯,而更多的探讨这两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具体到明代,就是说皇帝远非近代西方思想家想象的那样“无所不能的专制”,而是受到很多限制的。即便是洪武那样接近无所不能的皇帝,其制度设计最终也要被来自社会的反弹所消磨,从而达成新的平衡。
作者从乡治、土地、书籍、宗教四个方面阐展开论述,其中个人评价最高的是第三章《江南的圩田及其税收》,同时也是最切合主题的。通过这一章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被后世归纳为“一条鞭法”的改革,是怎样自下而上的在张居正之前的一百年中逐步发展起来的,面对超出洪武制度预想的社会变化,地方官们是怎样“努力地重新组织国家赋税在地方上的接口”。
当然在此之前最好先读前两章。第一章写作时间较早,内容也比较基础,好处在于相对全面,把明代县以下的组织分为“四套班子”:基于土地的赋税单位,乡-都-图,基于户口的赋税单位,区-里-甲,治安单位保-党-甲,以及公共教育单位,约。这四套班子逐渐趋于合体,最终成为清代的图甲制。可以看出,即便是洪武时代,乡治机构都远远达不到“整齐划一”的理想专制主义状态,何况后来的演变也绝非政府所能控制的。第二章的地图,可以视为对第一章的补充,另外略述了明清以来地图学的发展,认为叶春及的网格法与中国古代很多大加宣扬的科技成就一样,并未在当时带来什么影响。
第四章讲明清两代北方的水稻种植,其失败原因除了技术的、自然的“不可抗力”之外,社会的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不过以此来论证“国家不够强大”总还是牵强了一些。
第五章讲明代的地方藏书楼,但是给我的感觉是作者对思想史不够熟悉,把丘濬这个堪称保守的理学家和众多阳明心学追随者放到一个筐里,强行构建出知识分子和国家的对立,似乎国家刻印发放那么多儒家经典只是为了让人远观而并不想教化士子,未免太离谱了。
第六章关于明清两代的书籍审查制度,是最差劲的一章。作者明明认识到了清代统治者的特殊性,还坚持认为“乾隆时期满清统治稳固,所以不可能是为了合法性而兴文字狱”,并且还引用盖博坚的观点:文字狱闹得沸沸扬扬主要是由于汉人官僚的互相报复,而满洲贵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居然是“阻止猜疑的升级”,简直是搞笑。在他看来,乾隆真正要审查的不是思想,而是书籍的印刷与流通。但是文中提到的“不识字者罪轻”,“书商无罪”恰恰能反驳这一猜测。逻辑本就不通,更何况他所列举的案例既不全面,复有多处理解错误,完全无法支撑其结论。关于天启六年刘铎的诗扇案,作者完全把史料理解错了,此案从头到尾与书籍没有任何关系,原文所谓“图书”指的是印章,“制书”指的是诏书。《曹溪通志》被禁是因为钱谦益,但是作者却另外找了一个理由尚可喜,人家明明是大清忠臣怎么就敏感了?
第七章和第八章,标题里都是佛教,但是实际上道教也包括在内。槽点也很多,作者认为洪武后期对佛教的打压是空前绝后的,三武一宗表示不服。所谓打压,不如说是控制,而洪武时代对儒家的控制丝毫不见得弱于佛教。对售卖度牒制度的辩护也很无力,它诚然不会让普通百姓直接变成僧人,但是毫无疑问能间接导致赋税人口的流失。作者自己也说了,这是一种透支。另外还谈到了地方士绅对佛教的支持,并将其与地方自治联系起来。问题是在这个环节中关键的是士绅而不是佛教。参考李天纲《金泽》。关于清初北方士绅在地方志中对佛教的排斥,也应该更多的放到思想史的环境下考察。
翻译总体质量相当不错,没有很拗口的句子,而且可以看出译者作为明史专业人士也经过了细致的考证,有所修正和补充。不过有一点想不通的是作者以辞海为标准来纠正原书中关于历史人物生卒年的记载,恐怕不够专业,至少许论这个就是把对的改成错的了。
《明代的社会与国家》读后感(四):社会与国家的互动
中国是个专制主义的国家,从黑格尔那里就已经下了这个定论了,魏特夫为此而专门写了本书,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从最近几十年的状况来看,这个结论下得还不算离谱,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符合专制的定义。有问题的是魏特夫的东方二字,不过,如果前苏联也能称得上东方的话,其实叫东方也没什么关系。但如果以专制主义来指代整个中国历史的政制,恐怕就值得认真讨论了。
加拿大历史学家,也是中国明史专家的卜正民的《明代的社会与国家》就对魏特夫的观点进行了质疑。《明代的社会与国家》并非一本专著,而是卜正民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合集。这些论文有着内在的联系,正好论述的是此书需要阐明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卜正民先生对这些已经发表过的论文进行了改写,让其内在联系更为紧密,并在加了一个导言,讲了一个南昌墓地案的故事,还加了最后一章的结论,使整部专著显得更为完整和严谨。该书共有四个部分:空间、田野、书籍和寺庙,每一部分分为两章,分别讨论了乡治、方志图、圩田税收、北方水稻种植、藏书楼、书籍检查、佛教及地方志中对于寺观的记载八个方面的问题。从题目来看,讨论的问题很杂,涉及的面也很广,乍看之下似乎也缺乏紧密的联系。其实细读全书,作者所讨论的问题其实也很单一,即明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全书的四个部分,即是作者观察这种关系的四个角度。
说实在的,作者的观察角度不算多,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这样一个大问题,光从这几个方面去分析,虽能得出一样的结论,但毕竟缺少更多的观测点,其中很多方面应该是非常重要的角度,可惜作者并未涉及,给这本书的论述,打了不小的折扣。这是该书不足之处。此书优胜之处则在于作者对于地方志的研究,在书末作者列出了他所参考的地方志,我粗略地数了一下,除去相同地方不同年份的方志外,他共参考了217种地方志,分布于十二个省份。在书中他亦大量地引用了这些方志的资料,作者在书中的两章,还专门讨论了地方志。因此作者曾在导言中如此说:“假如不是某些方志恰巧涉及明代社会与国家这一论题,就不会有本书的问世了。”暂且不论作者对于某些论题的研究是否存在问题,光是他所参考如此之多的地方志,也够让我们的历史学者汗颜了。我不是学习或研究历史的,所读此方面的书仅靠兴趣,但在我的印象中,一本书参考了200多种地方志,好象并不多。我一直认为,地方志是历史研究的富矿,但史学界似乎重视不够。虽然我们也有不少关于地方志的论文及专著问世,专于一方一志的偏多,缺乏对比的研究,未将其中的资料,纳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论题里。最后点还是点,未能由无数的点而构成一个时代的面。卜正民先生的这部著作,我认为是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卜正民在书中探讨了国家这一概念。在西方学术界在谈到中国历史时,对于国家这个词的使用很是慎重,认为中国实行的是一种专制统治,不是由组织和法律原则来统治的,与欧洲的国家根本不是一回事。说实在的,这种说法有些似是而非,甚至可以说是可笑。以一个地方的术语去套另外一种不同体系的东西,肯定会得出这样的荒谬结论。如果要在两者之间进行比较的话,首先我们得厘清什么是国家这个概念,而不是以西方既有的国家概念来界定已有的东西。这样的讨论只能说是书生之见,对于问题的探讨毫无益处,只能陷于概念之中。卜正民先生对西方学术界的此种讨论也不以为然,但他的结论我却并不同意。他认为西方关于国家概念中的许多东西,其实中国是早已有之。中国的国家发展是超前的。这样的说法我就觉得有些过了。其实我很赞赏他在书中所强调的一点,即在明代,国家有能力对全国进行监管,但顽强的社会力量可以塑造甚至阻碍国家政策。专制的统治虽然强大,触角亦伸及到社会各个方面,来自金字塔顶端的命令能够迅速地得到贯彻,但它必然借助社会的力量,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也不得不改样。
其实,我一直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专制统治虽然一直存在并且强大,但在中国的广大乡村,社会是存在的,而且起着很大的作用。国家的权力很难深入到社会的末端,深入到社会的肌理之中。来自国家的力量在不时地侵入个人的生活,而基层的生活却也在以其固有的惯性在抵御着这种侵蚀。在中国以前各朝代,乡绅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他们其实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模样,所以尽管中国时代不断地更替,也万变不离其宗。即使如蒙元及满清这样的异族政权,依然不得不造就这样的社会。与西方大多数国家不一样,他们的统治依赖于数目并不庞大的家族。而中国则是依赖于士绅,这些士绅没有家族的传统,他们来自于广大的民间,只有文化传统的承袭,通过科举致仕。他们在中国乡村拥有极其强大的影响力,也决定着当地社会的生态。专制的统治得通过他们来执行,而当地民间的传统又左右着他们的行动。因此国家与社会在古代的中国是互动的,社会是完整并且起着作用的。
中国专制统治最强大的应该只是最近的数十年,它的强大在于这种来自国家的力量,已经彻底地摧毁了社会,国家的触角已经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之中,任何组织及个人都变成了国家权力链条中的一环。这样的结果就是在当下的中国,原本鲜活而蓬勃的社会不复存在,社会的肌理也已经腐烂,民间社会不再有活力,在这种社会里能起作用的就只能是国家的权力了。与中国同样情形的,还有前苏联。但中国与俄罗斯,却是来自完全不同传统的文化,而这种专制的思想之源,却是来源于欧洲。因此,将专制冠以东方之名,就有些张冠李戴了。
《明代的社会与国家》读后感(五):许亿:和尚出身的朱元璋为什么要与和尚为难。
有些皇帝当和尚是初衷,如梁武帝。
有些皇帝当和尚是出身,如明太祖。
明太祖朱皇帝元璋还在朱和尚重八的时候,显然日子过得很苦,但因为有个和尚的身份,也算在乱世中有了糊口的本钱。乱世流离,冷暖自知。在朱重八从事革命事业之前,应该感受到佛教对于这样一个失孤小孩的照料,点滴在心,念念不忘。
在战争的年代,朱重八还很有效的利用了佛教信仰网络来动员其追随者跟他一起战斗。而朱元璋本人,却不至于将他的信仰一直保持虔诚下去。
佛教对于皇帝对此世相万千有无深刻的启蒙。我们不得而知。朱皇帝元璋日后从政,并非全无善念,但杀戮之心之烈也不大像一个佛徒。
元朝末年,战争连连。寺庙被焚毁,十余二三。但信仰的网络倒是未被摧毁。在苦难的民间,越是艰苦的环境,越是坚定人们的信念。
朱元璋从中受益,他的部队所向披靡,最终获得政权。所以他也懂得感恩。
他登基的开始十年。命令朝廷向寺院捐赠。并出资修缮寺庙。他还赏赐给寺庙许多免税的土地。甚至让僧人参与他的朝廷事务。派他们作为外交使节出使。还任命和尚做王府的顾问。
也许皇帝那段时间,也确实比较闲在,他还将全国几乎所有的高僧一一请到首都聊天。战后的国家,满目疮痍。于是他让高僧们齐聚南京的寺庙里,超度那些战乱中丧生的亡魂。接连两年的广荐法华会,成为唐朝以来高僧规模最大的盛会。
皇帝似乎无比的信任佛教,使之几乎成为官方宗教的样子。寺庙不但可以不受拘束的打理自身的事务,还可以从国家那里拿到丰厚的补助。皇帝登基十年,对于佛教几乎不插手,唯一做的重要事情,就是颁布法令,恢复过去的度牒制度——和尚去京城僧録司领取度牒,登记自己的 身份,而有司只是将这些身份造册,然后复印下来送到各个寺庙,以便寺庙方及时方便的确定每个游方僧人的身份。
国家只是帮忙做了身份管理而已,而和尚剃度这件事,依旧由寺庙自己执行。简单的说,国家没有把手伸到寺庙当中去,皇帝乐见寺庙保持相对独立的状态。
但好光景不长,这年,发生了胡惟庸案件。有人说胡惟庸是中国最后一个实至名归的相国。此后,中国再无丞相。所以此案意义重大。
胡惟庸案说起来扑朔迷离,实际上,就是帝权向相权开战而已。胡案连累到几万人受到牵连,对这个国家也起到了非常微妙的变化。皇帝说,以后我们不再设立丞相职位,后代也不许立,有谁提出建议的话,就将他凌迟,将他全家处死。皇帝也是人,当时的口气非常草根,他的旨意狀似发出毒咒,像一个怨妇。
有传说,胡惟庸请皇帝到他们家看西洋景(他们家挖出了一个有异像的喷泉),出宫的时候,据说皇帝的马惊了,被一个名叫云奇的太监拉住。皇帝这才惊觉胡家的上空阴云密布。派人勘查,发现胡家埋伏着甲兵。才确定胡惟庸谋反。那个名叫云奇的太监,在史书上查无实据。但明朝后来的皇帝,深度依赖太监也是不争的事实。
皇帝恨的是一个职位而不是一个人。怎么说呢,皇帝并非睡不着觉怪床歪而已,他也算懂得总结客观规律,懂得从根子上找问题。因为不是人出问题,而是制度出问题。
至于制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就不要难为皇帝的判断力了。只能说,我们大致看出朱皇帝元璋的办事风格。揪出萝卜带出泥,揪萝卜的力道,决定了泥能带出多少。朱皇帝元璋是此中高手,他办的案子,没有不牵连广泛的。他的土地上,处处深坑,以致人们忘了里面只是种了萝卜而已。
所以此案不久,佛教的好日子也跟着到头了,虽然找不出两者间的牵连,但也不怎么奇怪。宛如看出丞相制度对于帝权的掣肘,皇帝也看出佛教对于这个政权稳定的某些隐患。这距离皇帝登基以来已经有了十年的光景。他对着那些昔日欢喜的僧人们露出了鄙夷的神色。然后,开始出手了。
首先,他将他对于全国的寺庙进行登记,然后将佛教的所有教派分为“禅,讲,教”三派。禅派清修,讲派学习,教派呢,就负责深入民间向人们布道和举办仪式(丧礼)。各司其职,各安本分。
将信仰以官僚体制化进行简单的分类,虽不足以得到合适的学术解释。但越简单的分类,越有利于官方的管理,而跨教义分歧的分类,使不同意见的僧人们不得把精力浪费于内斗——总之使这些懒散和尚不再自由自在。再然后,可以按照国家的意志,帮助皇帝进行道德的宣讲,强化意识形态。皇帝此举可谓一石数鸟。
接着,皇帝命令向所有县以上的寺院派出会计,也就是所谓“砧基道人”。这些人负责寺庙的财务管理,保护寺庙土地不被买卖。并负责寺庙的外联事务,比如与地方官员联系,交涉寺庙的赋税问题。
当然皇帝并非关心寺庙的财务状况,而是通过设立此职,以确保僧人们有条件呆在寺庙里,不用出去抛头露面到处化缘。皇帝希望将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有所隔离。虽然事实证明,这个通过行政命令试图保留土地不被买卖的方式,在明代这个商业化很充分的社会里,显得意义不是很大。
再接着,皇帝发布了“百日谕令”,要求在一百天内,强行推动寺庙的合并。将所有的小型寺庙合并到大寺庙中,看起来是强强联合,做大做强,事实上,不过无非借此手段大量淘汰掉寺庙。并获取寺庙房屋以用他途,此举超过了历史上大多数行政干涉佛教的力度,这场运动,当时就使寺庙数量减少了四分之三。
尽管效果明显,皇帝意犹未尽。1394年,洪武皇帝对于佛教最后一次干预,他颁布《避趋条例》,规定僧人不许化缘,不得与士绅联系,不得与官员俗人为朋,不得接受未成年人为沙弥。僧人们必须住在规定的寺庙之中,不要乱出门。
也在这一年,《金陵梵刹志》记录了皇帝说的这句话,他说,迩年以来踵佛道者,未见智人,但见奸邪无籍之徒,避患难以偷生,更名易姓,潜入法门。
与23年之前,皇帝对于僧人的嘉许“若僧善达祖风者,演大乘以觉听,谈因缘以化愚”。比较起来,已是深深的失望。当然,这何止于一个前辈僧人对于后辈堕落的恼羞成怒。
皇帝看到的,当然不止于部分僧人的堕落,更大的可能,是对于国家治理指导与制度的认识发生了改变。犹如革命者发现革命理论并不能维护一个正常社会之稳定。当朱皇帝元璋意识到对于这些昔日同道的嘉许以及放任,并不能有帮助他的政权保持发展时候,做出改变使多么顺其自然的事情。
尤其是在他为了为了后代清理执政道路,对那些居功的老革命同事痛下杀手之际,忽然意识到,掌握舆论工作的重要性,试想,那些游方和尚在市井巷陌对于无知民众的碎嘴该是多么讨厌。他们又如何将这些宫廷杀戮的血腥事件添油加醋的描述扩撒到民间去。
更何况这些闲的蛋疼的僧人们,穷极无聊,未必不生异端。假如让他们与老百姓紧密结合,妖言惑众怎么办。
即便是得道高僧,他们在宣扬善念的时候,假如不进行合理的引导,任由百姓将其与皇帝对于革命老臣狀似忘恩负义的政治行为联系在一起。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所以,朝廷要注重理论引导工作,而宣讲的和尚,更要掌握住宣传部门的主旋律定调。假如放任自流,想想都是多么危险的事情。
所以皇帝下决心管理佛教的其中关键,还在于国家意志,与僧人对这俗世所能施加的公共权威的冲突。当然,朱皇帝元璋的手段想来粗暴,看似雷厉风行,当时也颇见成效,但是后果就不值得检验了。
略举两例,一是,洪武皇帝去世,他报以期待的孙儿建文帝的政权很快被燕王朱棣篡夺,而辅助朱棣的,就是一个和尚,名叫姚广孝。
一是,朱元璋恢复的度牒制度,到明成祖朱棣时代更是加强管理,但很快,也就100多年的时候,景泰皇帝为了增加一点国家收入,开始对度牒进行买卖。意识形态终于让步于财政收入。意义也就被消解了。
历史证明,堵住不同声音的嘴,就以为彰显自己的正确。只不过粗暴拒绝别人提醒你的善意而已。
当然,历史也证明,历史这玩意,基本没有前车之鉴,但往往存在重蹈覆辙。
本文 取材(加拿大)卜正明著《明代的社会与国家》
—————————————————————————————————
许亿频道
公共号:xuyi_bpz
生活且慢,待我说三道四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