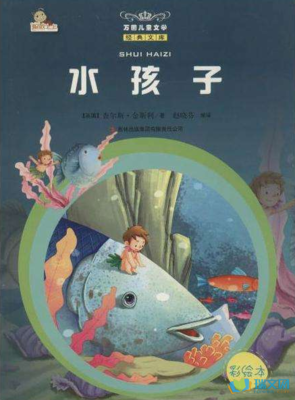记忆经典读后感有感
《记忆》是一本由[美] 埃里克·沃格林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8,页数:5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记忆》精选点评:
●基本上看不懂
●这是一本哲思的书,不是“哲学”书。
●理论素养普遍孱弱的国内文科界往往把记忆、书写、空间之类当作救命稻草,或者搞几个华夏、中国的大毡帽装装逼,共同的症状都是不读书,缺乏常识,智商低下!
●盛赞译者!优秀的翻译。 内容重要程度:13章.何为政治实在?12章.时间中的永恒存在.3章.论意识理论。 13章花了很多内容,处理实在问题。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做哲学?为了再现实在!”《自传性反思》一话真正含义和重量所在。 阅读时需要带着具体生活的感受来理解,很多疑问能得到澄清。 如果有一些历史研究、古典哲学、基督教神学、心灵哲学的阅读基础会更佳!
●第2 4 6 7 12 13值得特別關注
●1.第3、12、13章是意识政治理论最集中精彩的论述。博丹、柏格森、詹姆斯、加缪是与他同生共死的现代哲人,他对语言畸变的诊断接近后期维特根斯坦。盎格鲁—美利坚的常识文化是当今世界的擎天柱,但缺乏智思(noesis)之维。 2.批评胡塞尔:目的论式历史哲学是进步哲学,丧失了康德的谨慎;未把握到作为笛卡尔式沉思之核心的超越体验;把意识流动不恰当地抬高为本源性体验。 3.“意识之均衡”洞见的结论:不存在永恒真理,存在永恒真理的源泉;确定的都不是永恒真理,永恒真理都是不确定的。这类似“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4.沃格林思想最迷人的部分恐怕是其“超越体验”,他以《奥义书》练习冥想。要澄清秩序的历史,“灵魂”是核心枢纽。他有神秘主义色彩,被误认为反灵知的灵知主义者。柏、亚和奥古斯丁的洞见依然构成背景场域。
●个人倒是很不理解沃格林为何认为那些写下了“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云云之诏书的蒙古官吏心中必有一套世界帝国的理念框架,仿佛从亚历山大到帖木儿,成为世界的征服者与拥有一个天下帝国的概念成了充要条件。不如举一个今日的例子以资参照,官样文章或者说红头文件的专业写手不可谓不是运用政治话语的大师,然而他们对这次词汇的真切含义不甚了了,更遑论其心中有一个天下帝国的秩序概念。当一种话语沦为文本范例的时候,它的本意与旨求往往也被淡化和遗忘了,而诏书中这些套话与范式本来就是长期文化传承的结果,蜕变为一种不必问为什么、也无法回答为什么的惯例,从这种无意识的辞令中建构一个统摄东西方的政治秩序框架,恐怕本质上就是一种迷思吧。 译者把“哈拉和林”翻成“喀喇昆仑”,文中说了是汗庭所在,自己不觉得违和吗
●译文可信,流畅
●https://athenacool.wordpress.com/2017/12/07/%e8%ae%b0%e5%bf%86%ef%bc%9a%e4%b8%80%e5%8f%a5%e8%af%9d%e4%b9%a6%e8%af%84/
●译者可以的,年轻有为。
《记忆》读后感(一):感谢读者的鼓励、批评和指正
《记忆》出了快三年了,这几年中,译者一方面得到了许多读者的鼓励,一方面也从各种渠道得到读者(以豆瓣网友为多)的批评和指正,一并致以感谢。这部书稿还有许多问题:知识错误,字的错误、标点失误,些许术语译名现在看来不妥等等。
其中,知识错误一个最大的硬伤,就是将“哈拉和林”译为“喀喇昆仑”,我对蒙古史隔膜,当时没有认真核查,以至于出了这样大的低级错误(多谢宿景祥先生,另外还有一位不知名豆瓣网友指正)。另外,最后一文中“公民神学”也直接误作“公民宗教”,也是自己校对时太粗心。
术语方面,比如把希腊文的nomos译为律法,这个旧约的风格的词不合适,还是礼法更好。
记得当年译者着急把第一稿发给出版社,后来自己核查后的第二稿发过去时,出版社已经按照第一稿做好了清样,责编老师的细致校改之后,仍然有许多错误逃过了。这些错误,都是译者知识、态度方面的不足造成的,无可推诿,译者谨向读者们致歉。经一些学友的建议,我会将现在出现的错误在书上改正后,联系出版社,以求再版时能改正,以为补救。
《记忆》读后感(二):回转与记忆
“回转”意味着:沉迷世界,转离世界并转向超越,再回头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quot;记忆"意味着:眼睛看到世界,眼睛的视力让人回忆视力的原因,世界让人回忆世界的原因,记忆,在根本的意义上,不是记忆时间中的先前,而是对人和世界之原因/根基的记忆。
沃格林的政治科学在原则上是柏拉图式的:神是尺度、灵魂的转向、真实的层级、灵魂是社会场域中显亮的中心、爱欲正义死亡、哲人是精神领域的“王”、记忆(求索根基)。
第一编的2-4章是理解成熟时期沃格林哲思的钥匙,喜爱沃格林的学友不可不熟读深玩。
43年左右。在精神上,沃格林经历/经验了一个回转,或者说,回转行动首先是灵魂中的经验到的实在;2-4章的这些文字,是这个回转行动在智识层面的表达,它成了一种知识的实在(即充分的象征形式)。
对于一个已经有了回转意识或开始回转的人来说,沃格林在这里展示的分析有如金圣叹所说的:直剜心肝刽子手。
论胡塞尔:应先仔细阅读沃格林对胡塞尔和笛卡尔关系的分析,然后才能更好理解他前面那些针对胡塞尔历史和社会观点发表的那些断言。这个分析指出了笛卡尔的意识分析的缺陷(心理学的“自我”溜进了“先验自我”,对神的理性“证明”),胡塞尔的外科手术式偏离(刨除了笛卡尔理性证明的“神”,却忽视了笛卡尔的“神”来源于沉思经验本身,而非“证明”。这个偏离,胡塞尔还自以为是对笛卡尔缺陷的克服),诊断的标准是奥古斯丁(和柏拉图)那种健全的意识分析(对心思的思想、心思、朝向神的灵)。超越/神 来自思想者的沉思过程本身,而不是来自于命题和逻辑演算(也不是来自于“我”的意志力的投射和创造,因为“我”尚需一个根基):在边际经验中,有限和无限、缺陷和完美被同时给予,神/超越不是人的对象,却是经验的真实!沉思,意味着对神/神性根基的回忆,通过anima animi,人能回忆起神,就好比苏格拉底在Politeia中说,人通过nous观看善的“本相”。获得了神/超越,哲思方获得了一个确定的阿基米德点。这个阿基米德点不是“我”,而是“神/超越”。再以超越来度量人和世界,人和世界获得了一个全新的位置。所以,在一个获得了神的人眼里,世界变得更透明。这就是episteme——知识、科学。
沉迷世界(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转离世界转向超越(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回头看世界(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论意识理论:胡塞尔批判的一个自然结果,本篇包含对各种意识分析(尤其是胡塞尔)的检讨,重获了健全的意识,由此重获了一个更充分的存在论框架(恢复了意识的健全性,即指向超越指向神性根基的灵。神、人、世界、社会在这个存在论框架中得到了落实)。这是沃格林脱离胡塞尔势力范围、回归古典哲学、基督教哲人源始意识/经验分析的最重要篇章。
记忆:既是对幼年的事件的记忆,更是对推动一个人哲思之“事件”的记忆,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没有一个绝对的哲思起点,只有具体的意识受到根基的推动,并进行哲思时,哲思才是现实的。想搞一个绝对的、一劳永逸的奠基,这是梦话。这切合后面引用的奥古斯丁:开始渴爱者,开始出离。渴爱/爱欲是发生在每个具体的人身上的事件,别指望一种外在于人本身的,命题构成的终极真理,因为真理有待于具体的人的实现。所以,形而上学可以完蛋,但哲思不会终结,因为只要有人,便会有对超越/神的爱,便会有哲思。
这三篇奠定了沃格林之后言说的基础。如果读不懂这几篇,就去妄论《秩序与历史》和之后的其他著述,是毫无用处的。因为沃格林的存在论、哲学人学,在文献层面只能在这里找到成熟根源。我们读《秩序与历史》,第一句便是:“神、人、世界、社会构成了一个原初的存在共同体”,有人说,沃格林应该为自己的“神”提供存在论证明,有人甚至认为这是教条论中的神性实体,这可能就是译者所谓的“矮人看戏”了。
不能忘记,这三篇都是沉思文本,它们也需要读者相似的努力。
《记忆》读后感(三):由ousia引发的现代性
在What is Political Reality?(《何为政治实在?》)一文中,沃格林通过追溯ousia一词的变迁考察了现代性。如果说现代性引发了“神性的内在化”,怪谁?在这篇文章中,沃格林觉得亚里士多德难咎其责。
据沃格林分析,由于亚里士多德不仅对各种being进行了分类,而且用ousia来总称所有的being,这就带来了麻烦:因为being包括了“在世之物”(things-in-the-world),所以ousia一词就容易被窄化为世间的某种事物。而在亚氏的语境下,它显然指涉的是各种being,不仅仅有thing,还有transcendent being/divine nous。后世人们把ousia彻底当成了思辨的对象(后世ousia这个词惯常被翻译成substance),也就出现了教条主义的各种争论:关于灵魂——它的存在、前存在与后存在,关于神的存在及其证据,关于世界在时间之中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等等。在沃格林看来,这显然是comprehending reality(总括性实在,它包括神、人、世界与社会)萎缩的现象。因此,考察一下ousia/substance一词的历史,就可以对这个过程有个了解。
ousia(现代常常译为substance):
在希腊语境下,ousia(本体)来源于einai(to be)/ousa.
而亚里士多德则把being分为不同的种类,ousia在第一种意义——终极实在——上来说是being,ousia是支撑其他beings的终极主体。在《形而上学》中,他又将ousia细分为形式(form)、质料(matter)以及两者的合成体。
如果说“本体就是主体”,那么显然质料(matter)是更重要的本体,然而,亚氏又说,评判何者更重要的标准应该是“这一个”(tode ti),所以形式是更重要的本体。
在亚氏的语境下,“本体”(ousia)有两层意思:1. 终极的基质,它不是用来表述其他任何东西的一个谓词;2. 它是每一种事物的形状或形式,从而与universal相关联。
Descartes的substance(实体):
笛卡尔对实体的定义是:一个不依赖于其他任何东西而自身存在的东西。严格意义上的实体是上帝;但存在被造的实体:心灵与物体。心灵是思维的东西(res cogitans),而物体是广延的东西(res extensa)。它们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实体,并且本质二者不相关,因为思想没有广延,而广延不能思想。这就是笛卡尔著名的“心物二元论”。
由此可以更好地理解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句话表明,【思想的主体】和【反思的主体】是同一个主体,【主体就是实体】。“故”表示的不是两个实体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心物二元论”里已经指出它们之间没有联系),而是【本质】和【实体】之间的必然联系;“故”也不表示从已知到未知的推理,“我思”是该实体的本质;“我在”是该实体的存在。笛卡尔要表明,人们只能通过实体的本质来认识实体:从自我的思想活动——这一自我的本质中,人们认识到了自我的必然存在。
inoza的substance(实体):
斯宾诺莎关于实体的定义是:在自身内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这个定义是从认识论角度做出的,因为它强调实体是“通过自身而被认识”;但同时也具有很强的本体论内涵:因为实体在斯宾诺莎那里是“在自身内”,它是自因(因自身而存在,不需要外在原因,同时也意味着不会因外在原因而不存在,所以“存在乃是实体的本性”)、无限的(不受限制)、唯一的(不存在另一实体)、不可分割的整体(一切存在和认识都包含于其内)。可以说,对于斯宾诺莎而言,实体=神=自然,这反映了其一神论、人与自然预定和谐的观念(接近泛神论)。同时,由于斯宾诺莎的“实体”是唯一的,因此他的主张就是与笛卡尔的二元论截然相反的“一元论”:思想与广延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实体,而是同一实体的两种属性,因为这个唯一的实体可以表现出多种属性;并且斯宾诺莎还认为,思想与广延具有一一对应关系。
与笛卡尔的区别在于,斯宾诺莎并不是从“完满性”来论证上帝存在的(笛卡尔是这样做的),而是从“充足理由”原则来进行论证的,即:凡物之存在或不存在必有其所以存在或不存在的原因或理由。既然神(上帝)乃是唯一的实体,因此是自因,那么就没有任何原因可以使得神不存在,所以神是必然存在的。这种论证的含义是,它显示了斯宾诺莎对唯意志论、唯名论、同时也是超越世间的人格神的否定,因为如果强调神的意志,那么在终极意义上,神的无限意志是“原因”的反面,因为神的意志总是可以超越甚至否定一切“充足理由”或因果必然法则。
Leibniz的substance(实体):
莱布尼茨的实体就是“单子”(monad)。实体是组成世界的最小单元,它无穷多(所以莱布尼茨是多元论)。莱布尼茨是反原子论的,因为原子论认为有形的原子是真正的实体,而莱布尼茨认为只有不可分的单纯实体(物质实体因为有广延,乃是可再分的)才是“真正的原子”。单子(实体)是没有部分的(是不可分的)、没有广延的(所以不是物质实体)、不受外部影响的(预定的和谐)、能动的(因为物质是惰性的,它不是物质的)。最高级的单子(实体)具有理性灵魂,只存在于人的自我意识之中,理性是:精神、统觉(apperception)(相当于“我思”,因为能够以“自我”为思维对象,能够进行反思)。
题外话:entity常常也被译为实体,它源自拉丁文ens,与thing、object相关。从词源上来说,ousia更应被译为entity。但这个词含义较substance更为宽泛。
《记忆》读后感(四):第三编“意识之秩序”:《何为政治实在?》教学大纲
一、科学与实在
1.什么是逻辑学意义上的“基本原理”(fundamentals),为什么本文要转向对实在(reality)的追问(393.1-2)
2.数学公理化分析不适用于政治科学与实在的关系,不适合的原因(394.2-3)
3.政治科学与政治实在的关系的若干特征(395.2-5)
1)社会的自我(非智性)阐释早于智性阐释而出现;
2)在智性阐释出现之后,社会的自我阐释仍居于主导地位;
3)智思(noesis)永远与社会的自我阐释处于互相阐释的张力关系中。
4.“科学—对象”模式的缺陷,“科学”作为意识形态(396.2-397.2)
5.为何要引入“智性阐释”这个表达(397.3-4)
二、对根基之意识
1.政治实在的张力源于求索根基之人的意识,这种求索的经验可以有多种表达,但根基具有唯一性(398.2-399.2)
2.把古典哲学当成澄清意识本身的起点——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例(399.3-402.1)
它的基本结构:渴求(位置)+牵引(方向)
1)亚里士多德表达寻求根基的不安感的语汇:arche(根基),aporon(困惑),thaumanzon(惊异),kineitai(推动)等
2)亚里士多德用“nous”表达“根基的牵引”这一运动的方向性,沃格林代之以“ratio”(智性)
3)“参与”(metalepsis)——神圣nous与属人nous之间的关系
3.神话渗透进智性诠释,其重大意义在于,神话作为原初的宇宙体验,使得对事物统一性的体验在智性诠释中得以保留(402.2-404.1)
4.进一步考察亚里士多德的metalepsis: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之前就有了某种表达灵性体验的象征形式(404.2-409.1)
插曲:智思(noesis)导致的对象化问题
各种参与的经验可归于“参与”这个“属”之下,其中包括哲人之参与,但参与来自哲人之参与,所以它既是属又是种(既有参与性又有意向性);哲人之参与相比其它类型的参与,达到意识的最大显亮;显亮程度的实质是真理之差别,“参与”本身并不能被对象化,我们不可能绝对“客观”地看待参与;个人意识的历史场域创生社会的历史场域。
5.对参与之逻各斯的三种诠释维度:智性(ratio),显亮(luminosity),过程(process)(409.2-415.1)
6.亚里士多德作为历史哲人(415.2-416.1)
在意识中的时间性之流这个维度中,智思将自身确立为真理之在场;历史由意识所建构;历史时间对应着对根基之渴求这个内在于意识的维度;历史场域总是关涉普遍人类;各类象征形式的对等性;对属于过去的各种象征的爱意反顾(Liebende Rückwendung)。
7.我们时代的智性诠释在哪个点(“实在之丧失”)上与亚里士多德的分析分道扬镳(416.2-421)
亚里士多德语汇在方面的缺陷:没有区分各类存在模式(事物类的实在与神性存在、神性存在与意识性存在);这种技术层面上的缺陷推动亚里士多德后学发展为教条论形而上学——起点是ousia这一象征形式
Ousia相当于aletheia,形式与质料、灵魂、政制和神圣nous都可归于ousia之下,当ousia与原初体验之实在性脱离关系(被知识对象化)后,我们便丧失了超越性的实在与内在于世的实在
8.我们可以做的:进一步殊显存在之态(422.1-424.1)
在整体性的存在之域中,人凭借意识这种参与性实在,以形成实在图景的方式去描述作为实在的参与之诸端点(他人、社会、世界、神)
形成实在之图景,这是一种感性的方式,关于实在的象征必须是含混的,因为并不存在意识的阿基米德点。这种象征在语言层面上含混,但在智性层面并不含混。
9.进一步澄清象征在语言和智性层面的复杂形势,避免两种误解(424.2-427.1)
第一,实在是恒常的,存在实在图景的真理坡度,但如果忘记图景只是个譬喻,就会忽视意识的参与性,产生各种次级哲学现象;第二,实在又不是恒常的,因为某些殊显性的意识会误以为产生了新天新地和新人,以为人类通过自身行动可以改天换地。
10.由此引出对误导性的实在图景的分析:对象化问题的起源在于意识的意向性(427.2-434.1)
意识在筹划图景时拥有某种自由维度,并非随便什么态度就可以实现实在形式(Realitätsform)与实在内容(Realitätsgehalt)之间的贴合,唯有承受重负的意识才能做到这一点;撙节科学与反对体系化图景;次级实在
11.Periagoge——转向谁?转向生存分析,以生存张力这种实在重新填补到实在形式中,以加缪为例(434.2-438.1)
12.总结(438.2-440.1)
六组关键词:智性(ratio),显亮性(luminosity),真理的坡度,实在视景(Realitätperspektive),意向性,实在形式/实在内容/实在之丧失
两个阶段:古典智思(classical noesis),现代智思(modern noesis)
古典智思没有充分地区分参与(体验)与参与之诸端点(象征形式)这两个实在之域,这正是我们要继续做的。
三、言语引得与类型概念
1.回顾“意识是非对象性实在”的基本观点(440.2)
2.言语引得(language indices)(441.2)
3.智思的洞见(442.2-444)
言语引得就是智思的象征,智思的象征来自智性洞见;智思使得世界的本己结构向科学探究开放
3.类型概念(445.1-451.1)
对历史场域进行类型化;类型概念与引得的关系;“对象”的三种意义,意识的单独实在性;历史场域之结构反映实在之结构;历史意识并非某种意识把自己开显为大全意识,否则就偏离到灵知主义;对象性的两个维度在构造类型概念的过程中互相渗透
四、知识实在中的各种张力
1.从实在转向知识(451.2-454.1)
什么是智性知识;智性知识在参与知识的实在中的地位;参与知识的实在在历史层面的丰富性(信望爱);ratio具有对各式秩序知识的批判功能
2.参与知识场域之张力的三个主要阶段(454.2-457.1)
古希腊阶段;犹太-基督教阶段(教条论神学);教条论形而上学与意识形态
3.教条战问题的几个层次(457.2-464.1)
意识形态教条论表达的是反抗,它不可能成为智思的出发点;以反抗这一历史行为作为指针,实行转向;向前教条论的知识实在前进,加缪与神话;当前对前教条论的知识实在的争取运动缺乏它自己的中心;考古学的作用
4.古典哲学的智思与神秘论与教条战之间的关系(464.2-474.1)
亚里士多德的智思,阿奎那的偏离,启蒙知识分子的反抗,直到海德格尔;神秘论回归智思的两次尝试:博丹和柏格森;博丹论宽容
五、具体的意识
1.人的复合本性(synthetic nature)(474.2-475.2)
对生存张力的意识+躯体生存
2.意识之具体性(475.3-483)
当前政治理论的病态图景;忽略躯体存在的乌托邦式象征;忽略参与意识的各种契约论;具体的人的具体意识,是唯一能体验到的意识;具体意识的社会场域的多样性;汤因比的文明型社会;比文明社会更为广大的权力组织场域:作为文化人类场域的“天下”;历史普遍性场域的“人类”;普遍人类(universal humanity);具体的人的生存秩序在历史这个阐释场域得到阐释;时间中的永恒存在,指的是历史普遍场域对根基之永恒性的参与
六、智思之功能
1.总结:总体勾勒智性阐释的结构(484.1-485.1)
2.古典智思领域对政治实在的探究的三大特点(485.2)
3.“人这个存在之域”,两大实事线条(486.2-488.3)
4.对两条实事线条模型的违背(488.4-490.1)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基本原理的追问
5.“常识洞见”(490.2-494)
比起常识洞见,智思洞见的高级并非来自其一般性特征,而是其更高的显亮性;苏格兰学派;文明的社会人必须拥有常识;作为智性避难所常识现象,常识哲学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