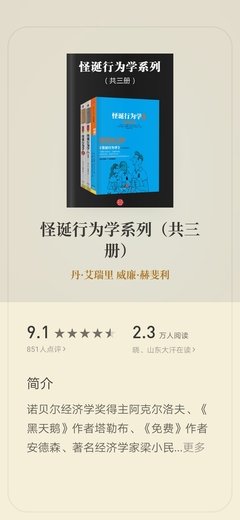非理性的人读后感摘抄
《非理性的人》是一本由[美] 威廉·巴雷特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 32开图书,本书定价:27.00元,页数:33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非理性的人》精选点评:
●海德格尔诠释的好
●新教育实验网络师范学院哲学课程选用教材,必读。
●读不太懂,得多了解更多的西方哲学才行!我深度不够,半途而废了。
●书很好,对存在主义的介绍很全面。但却让我觉得始终停留在生活的表面,有一次要突破边缘了,却异常恐惧,边缘的外面一片漆黑,我不知道这位作者要带我走向何处,也不知道这片陌生领域要如何开垦。什么能够在一片未知中指引我呢?还是逻辑与理性吧。
●从高二读到了现在,我的想法,立场,一变再变。 极具启发意义的存在主义读本。 人何以为人,何以为自我。 总之就是更加想去读萨特和海德格尔,但是哪来的时间,哪来的底气去读。
●智慧所在 “理性的人”和“非理性的人”合成 客观扼要
●挺好一本导读(又开始问自己咋现在才看),通俗易懂,行文流畅。but看目录时对《存在主义大师》那一编期望值极其高,结果中途嫌弃了好几次讲得太文艺太啰嗦了差点打算跳过去不看惹orz
●谈论起尼采来真好笑,“爬上屋顶发出尖叫格外容易惹是生非”。我觉得尼采真的是很陀式的人物,很像是会在陀的小说里出现的角色。读到海德格尔,我认为他对存在的解释以及寻到的出路——“感谢和回忆的行为”,思想它感谢它,以感激的心情铭记它,比起尼采的“权力意志”我可能更喜欢一点。真的是一本很棒的书,了解存在主义的绝佳的书,不过翻译有些生涩。
●西方哲学 存在主义
●写的很棒!而且用并不是特别晦涩难懂的语言,来向你解释几位存在主义哲学大家的思想的。
《非理性的人》读后感(一):为何回到中世纪?
原著文笔流畅,翻译也还不坏(没有与另一译本对校过),偶有失误,如把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译为《声音与疯狂》(?),也不算致命。
段德智教授如今在武大领导一帮人翻译《神学大全》,还没动工,台湾的多米尼克(多明我)会神父集三十年之功给翻出来了。神父们基本上通拉丁文,还参考众多欧洲语言译本,而武大的课题组似乎是打算从英文翻中文的。
我好奇的是,当年翻译这种存在主义著作的人,怎么兴趣就转到阿奎那去了,难道是因为书中不停地提到阿奎那,作为中世纪的高峰与代言人(据说海德格尔就是以研究阿奎那为名,弄了笔奖学金)。段先生给刘素民《托马斯·阿奎那的自然法思想研究》写的序言,值得一读。
《非理性的人》读后感(二):没读懂的读后感就像非理性的理性人
书断断续续读了一个月,笔记摘了大好几页,仍然没弄懂海德格尔讨论的存在议题…看书的前四分之一的时候很兴奋,从进入存在主义大师的介绍开始看的一头雾水了,只好硬着头皮读下去,收获了一些知识和印象,但对存在主义母题的实质内容含混不清。基于这样的读书体验,完全没法对全书内容作完整而准确的回顾(更别说评价),大概是读的还不够认真,或者真没有读哲学类书籍的天赋。
首先关于存在,虚无是可能性,存在也是可能性,看不到虚无也理解不了存在。面对这种存在的有限性,西方哲学家和东方哲学家的反应路径很不同,道家和佛教的虚可以幻化成一种悲悯后的平静安乐,而西方哲学家从帕斯卡尔开始,对存在本性下的最终判断中是一种恐惧和绝望的情绪。这种绝望产生于发现不了自我存在的真理,又不肯放弃怀疑,只能像大卫休谟一般到弹子房的真实世界中暂时性的消除这种焦虑感。海德格尔似乎提供了情绪上的路径,即承认这种有限性。这里很喜欢作者举的复仇女神的例子,“完整的人若没有诸如死亡、焦虑、罪过、恐惧、颤抖以及绝望之类很煞风景的事,也就不再完整了。”对那些人生的阴暗面的认识与和解是面对自己生命的重要一步,当复仇女神得到尊重以后,她会放下制裁。
其次是如何理解存在。作者在附录中总结道:“人只要搞逻辑,他就倾向于忘掉存在,然而,如果他恰巧要搞逻辑,就首先必须存在。”我们用于理解的最基本的工具——语言和逻辑,似乎在这里已不足够。如何理解置先于语言的存在,海德格尔提出了现象学的路径。现象学打破主客体二元论,海德格尔又进一步提出除了言语理解存在的特性外,还有心情和领会两种存在情态,这其中根本的心情是焦虑,如果没有这种心情,人就只会“漫无目标地漂泊进虚幻不实的拉普特王国。”
这里的拉普特王国是由格列佛游记延伸出的一个充满抽象的理性世界,拉普特人热衷抽象却毫无灵魂,常常在谈话中陷入深奥的逻辑沉思而忽视面前的人。存在主义所反对的正是这样一种忽略人类实在性的抽象形式,而这些抽象形式充斥在现代世界中,在高科技的网络漫游下愈加弥漫开来。
在获得了一些对海德格尔存在的粗浅印象后,再提出“存在主义是什么,为什么存在?”这样的问题好像很傻,但如若得不到语言上的明确回答,存在始终似是一个莫比乌斯环一样不知从何观测。即便如此,在听了翻电之后,仍然觉得海德格尔的这个比喻无比贴近我对存在的感受:它,像是照在林中空地的那一片光。
《非理性的人》读后感(三):非非理性
突然发现很多非理性主义者既狡猾又懒惰。他们狡猾如怀疑论者,无论对方提出一个什么观点,无论这个观点的论据有多么充分,非理性主义者总可以一言反驳之——理性是站不住脚的。他们同时又懒惰,不愿意彻底思考一个问题,而总是或者求助于古代,或者求助于感情。
我曾经很喜欢尼采,他作品的美在我人生的某一阶段有重大的意义,而直到现在,我也仅把尼采看作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哲学家。至于尼采的理论方面,如果不被其大气磅礴的语言所迷惑,其实是有不少漏洞的,例如我认为“永恒重现”这个理论就是一个倒退。很多哲学家在描述自己理论时,并不致力于把此理论清晰明白地告诉读者,反而或者用重言式,或者用比喻来掩盖结论的缺陷。我一直以为,只要一个理论逻辑上是融贯的,则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人都可以理解它。当然,这并非说明尼采的理论没有意义,至少对于我来说,它缺少严格哲学的意义,但具有美学的意义,而这又与我对许多东方哲学的看法是相同的。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好”的哲学?我认为恰恰应该是本书作者所极力反对的“分析哲学”。作者开篇就对分析哲学加以斥责,放佛这是一群学院哲学家卖弄技巧的玩意儿。接着作者反对了对“存在”概念化地思考,但是却并没有提出一种合适的对“存在”的思考方式。作者也许会说,对存在的思考就是我们活着所感觉到的东西,但这种说法就跟“我感觉到我是自由的,从而存在自由意志”一样站不住脚。那么既然抛弃了概念化的存在描述,存在主义者要说明他们的存在理论,便不得不借助于诗化地描绘了,而这恰恰是极佳的逃避手段。
作者为了说明科学哲学的虚妄以及不得不破产的命运,列举了数学中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物理中的测不准原理等。然而我认为这并没有达到作者的目的,这只能作为任何理论都有其局限性的归纳论证,而不是因为发现了例如数学中有某个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反驳的神秘定理就使得整个数学大厦倒塌了。虽然这些反例宣告了人类试图用科学解决一切问题野心的失败,但却加深了人类对科学基础的理解,从而促进其提出更加完善的理论,例如罗素悖论就促进了公理化集合论的发展。
也许作者觉得分析哲学家的工作太琐碎、太不值一提了,好像就是在那玩弄几个符号,讨论某几个词的意义。罗素极富创造力、为了解决本体论承诺的摹状词理论,被作者形容为“一个喜剧演员的把式”,却对这思维的突破视而不见。至于将“存在”看作二阶谓词从而避免通常“某某存在”这种说法,对作者而言,更是胡言乱语。虽然分析哲学定义的“存在”理论尚有许多不甚满意的地方,却绝不是逻辑的障眼法。我认为哲学应该从小处着手,虽然有时候显得不那么迷人,甚至琐碎,却是避免逻辑上前后矛盾的好方法。
当然,如果你是个非理性主义者,我上面所说的,算是白说了。
《非理性的人》读后感(四):非理性的人摘抄
人类理性乃是人这种动物长久的历史建构,人的精神根须还伸展下去打到其原始的土壤
宗教、社会形式、科学以及艺术都是人借以存在的样式
理性事物与非理性事物的性质(界限)是容许怀疑的
我们知道一个事物是以不知道某些别的事物为代价的,我们并不能够同时认知一切事物
哥德尔表明数学包含着不可解决的问题,因此决不能使之成为一个完全的体系
人的因素超出机器,数字像人的任何生活一样永远是未完成的
(理性的最终形态-数字的沉没)
理性是有一种办法来说明不以它本身派生出来的东西,这就是把它归为虚无-----爱弥尔·梅耶松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又都是现实的-----黑格尔
我存在:而我存在这个事实作为一种实在是如此非使人相信不可,它又如此包容一切,以致我的任何一个心理概念都不能明显地把它再现出来;但它显然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实,没有它我的所有概念都将是空洞无效的
我自己的存在对我完全不是思辨问题,而是一种我个人热情介入的实在。我并不是在心灵这面镜子里找到这种存在的影子,我是在生活里遭遇它;它就是我的生活,一股无形地环绕着我的整个心灵镜子奔腾不息的“流”
而在这样一种紧急关头,他们便会对基尔凯戈尔所说的“伦理悬置”有所体验……选择实在相互敌对的两个善之间进行;一个人无论如何也都必定要作一些恶,而且最后的结果甚至我们自己的动机,都不是我们能看得清楚的。在这样一种情势下,一个人面对自我实在太恐怖了,多数人都会惊恐不已,尽力随便找一条适用的普遍规范躲避起来,只要它能挽救他们免于选择自己的使命就行。很不幸,在许多情况下,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种普遍的规范……这样,这个人就只能靠自己摸索挣扎,自己作出决定,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绝望归根到底,绝不是对于外在事物,而始终是对于我们自己的……不可容忍的损失其实不是它本身不可容忍;我们不能容忍的,是由于被剥夺了一件外在事物,我们就赤裸裸地站着,看见了自我无法忍受的深渊就在我们的脚下张着大口
在东方的宗教和哲学传统中,从来没有说真理基本上属于理性;大师识别他的门徒是否已经醒悟,根据的是他的举止表现,他已经成为哪一种人,而不是听他如何引经据典推理论辩。这类真理不是理性的真理而是整个人的真理。严格地讲,主观真理不是我所拥有的真理,而是我所示的真理
无可否认,权力欲和怨恨这两者在历史上一直是道德家严肃面孔背后阴影的一部分
现在,对当代人来说,他的最高价值已经失去了价值;为了取代这些最高价值,尼采能够提供的唯一价值就是:力量
我们从来没有像德国占领期间这样自由过。从说话权利起,我们已经失去了一切权利。每天我们当面受辱,又不得不忍气吞声。随便找个什么借口,例如说我们是工人、犹太人或政治犯,就把我们成批地驱逐出国。广告牌上、报纸上、银幕上。我们到处都看得到我们自己枯燥可厌的、我们的镇压者想要我们去接受的图像。然后,正是由于这一切,我们才是自由的。由于纳粹毒液渗透进我们的思想,每一个正确的思想都成了一项战利品。由于近乎全能的警察机构企图迫使我们闭口不言,使得我们讲的每个词都有宣布基本原则的价值。由于我们遭人搜捕,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庄严献身的份量
沉没的共和国 萨特
人的自由就是说“不”,而这意味他是那虚无赖以产生的存在
人的存在的极端不安全和偶然性是他命里注定的;因为舍此他就不成其为人而只是一个物,从而也不会具有人类超越其既定处境的能力
在佛学中承认我们自身虚无意在引导人去奋力追求神圣和悲天悯人--------因为这种承认到头来会使我们认识到,没有任何东西支撑我们,从而使我们相互亲爱,一如同在一条救生筏上的幸存者,只有当他们觉悟到大洋无边无际,也没有营救船开来,才能相互怜悯和同情
自我的虚无正是行为意志的基础:如果这泡是空的并且终将破灭,这样,除了使这个泡拖长些时间的活力和激情外,还能留给我们些什么呢?
《非理性的人》读后感(五):【书摘】非理性的人
基尔凯戈尔曾讲到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对自己的生命心不在焉的人,直到他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一觉醒来发觉自己已经死了,才知道他自己的存在。这个故事今天讲来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我们时代的文明终究掌握了一些武器,凭借这些武器,可以轻而易举地使它自身陷入基尔凯戈尔故事主人公的命运:我们可能明早醒来发觉自己死了,却从来不曾触及我们自己的存在之根。
现代社会已经把哲学贬黜到完全无关紧要的地位,而哲学本身对此竟也欣然接受。
法国的存在主义在巴黎,是一种狂放不羁的酵素;它把由它的年轻信徒们以汇聚夜总会、跳美国爵士舞、留奇特发型、穿奇装异服等形式造成的时尚作为哲学的装饰。所有这一切都成了想要报道大战和德军占领期间巴黎生活的美国记者们的新闻题材。再者,存在主义还是一种文学运动,它的领袖人物——让·保罗·萨特、阿尔伯特·加缪(2)、西蒙·德·波伏瓦(3)都是才华横溢、大受欢迎的作家。
法国的存在主义在巴黎,是一种狂放不羁的酵素;它把由它的年轻信徒们以汇聚夜总会、跳美国爵士舞、留奇特发型、穿奇装异服等形式造成的时尚作为哲学的装饰。所有这一切都成了想要报道大战和德军占领期间巴黎生活的美国记者们的新闻题材。再者,存在主义还是一种文学运动,它的领袖人物——让·保罗·萨特、阿尔伯特·加缪(2)、西蒙·德·波伏瓦(3)都是才华横溢、大受欢迎的作家。
法国存在主义,作为一种时尚,就像去年的时髦一样现在已经消逝了。诚然,它的领袖人物依然十分活跃:萨特和西蒙·德·波伏瓦依然出类拔萃地多产,虽然就萨特来说,我们感到他至少已经差不多发表完了他的全部看法,因而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相当完全地掌握了他的要旨。阿尔伯特·加缪在他们合演的三重唱中最为敏锐,虽然很久以前就脱离了这个存在主义团体,但却还在继续探究原本属于存在主义深为关注的论题。作为新闻和轰动,这个运动已经完全寂灭了;然而,它却给欧洲最近十年几乎所有的作品和思想都打上了它的烙印。在严酷的冷战年代,
存在主义的主要论题,对英美哲学超然的庄重态度来说,恰恰是某种丑闻似的令人反感的东西。诸如焦虑、死亡、伪造自我与本真自我之间的冲突、民众的无个性、对上帝之死的体验等问题,几乎都不是分析哲学的论题。然而,它们却是人生的课题:人确实要死,人确实终生在本真与伪造自我的需求间奋斗挣扎,而且我们也确实生活在一个神经过敏性焦虑增长得很不相称的时代,就连那些以为自然科学技术可以解决所有人类问题的人,也开始把“心理健康”列在我们公众问题的首位。
萨特思想的直接源头是德国人:马丁·海德格尔(1889— )与卡尔·雅斯贝斯(1883— ),(5)以及作为其方法论直接源头的德国伟大现象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1859—1938)。严格地讲,只有海德格尔与雅斯贝斯才称得上本世纪存在主义的创始人:他们给它打上了决定性的烙印,给予存在主义诸问题以新的更加贴切的表达方式,而且还一般地构建了一种所有别的存在主义者的思想无不环绕其旋转的思维模式。海德格尔与雅斯贝斯两人的哲学都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德国哲学在本世纪初期的气氛由于探求一种新的“哲学人类学”——一种对人的新的解释——而活跃起来。哲学人类学由于所有研究人的特殊学科知识的遽增而成为必要。虽然一般人不把马克思·舍勒(6)(1874—1928)列为“存在主义者”,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特别提到他。这是因为他对于来自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新的具体资料很敏感,然而最为重要的,是因为他入木三分地领悟了下面这个事实,即现代人就其内在本质而言,已经变得成问题了。舍勒与海德格尔都极大地受惠于胡塞尔,而后者同存在主义的关系却极其含混和矛盾。就气质而言,胡塞尔在现代哲学家中是位卓越的反现代主义者。他是古典理性主义的热情倡导者,他的惟一的和崇高的目标,就是把人的理性建立在比过去更为恰当和更为全面的基础上。可是,由于执着于哲学必须摈弃先入之见,才能注意到实际具体的经验材料,胡塞尔就使哲学的大门突然向丰富的存在内容敞开,
无论基尔凯戈尔或尼采都不是学院派哲学家;尼采,虽然曾在瑞士巴塞尔大学当希腊语言学教授达七年之久,但他最根本的哲学思考却发生在他离开大学及其严肃的学者圈子之后。基尔凯戈尔从未担任过学院教席。他们两人的哲学都没有发展出一套体系;事实上,他们两人都嘲笑体系的创造者,甚至否认构建哲学体系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他们创造了极其丰富的、远远超前他们时代、只有下一个世纪的人才理解得了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