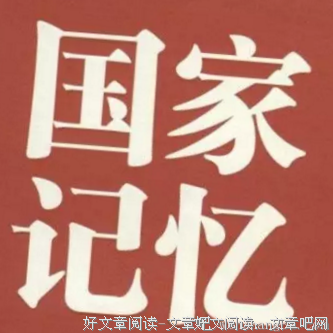《说吧,记忆》读后感精选
《说吧,记忆》是一本由[美]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2.00,页数:39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说吧,记忆》精选点评:
●整部回忆传记像蝴蝶翅膀的纹路,不断旁逸,又互相连接,绽开一个无比精彩的生命。而回忆的视角又有如蝴蝶的拟态,虚构与真实的辩证。嗷总之是很好看了
●《记住,现在》这是狂喜,而在狂喜后面的是别的什么,难以说清楚。就像是拥进了我所爱的一切东西的片刻的真空。一种和太阳及岩石的一体感。一阵对有关的不论什么人的感激而生的激动——对擅长以对位法安排人类命运的天才,或者对纵容一个幸运的凡人的温柔的幽灵。
●从此知道怎么制作蝴蝶标本,不过翻译水平欠火候,也跟纳博科夫随兴所至拗一连串高端词汇有关系。
●18年阳历新年读完的第一本书是他,莫名有些欢欣。他让我更多地肯定自己,离自己的感受再近一点。随着肯定自我的努力,我终于可以欣赏这些以前可能读不进的文字了,为自己的阅读品味高兴。
●丰富而又奇特的人生经历,细致无比的记忆,世间有对过往有如此深刻,让人惊叹不已。
●蝴蝶,人,雨与树与无数的空间,最重要的是时间,所有都值得复活,像蝌蚪们顶着大脑袋和高频率摇摆着纤细的小尾巴,在错落的重构的图像里窜动。
●读时代文艺版。在想车氏、左拉某些作品完全没有血肉、文学性。纳氏反之,然只血肉文艺又不足至巅峰。嗜好仍在《群魔》类别上。最高文艺的秘密,如同纳氏捕捉了一生的蝴蝶,我还没有找到。
●那个仙风道骨的小说理论与创作老师说,这是他看过最美的传记。 老师说的很对。 当我看见了它,就再也不可能看不见它了。
●有套平装本,这套精装只选了喜欢的《说吧,记忆》和《普宁》两本买。
●自传。
《说吧,记忆》读后感(一):End of the line
“他们是一支自觉的军队,他们的存在将对世界知识者的良心构成永久性的冲击。…康菲诺称他们的特征中贯穿着对于祖国土地燃烧般的情感。…乌斯宾斯基把提升起来的涵盖这一切的精神称作’土地——人民性’。”
我喜欢林贤治先生在《沉思与反抗》中对于俄国知识分子毫无保留的赞美。在自传《说吧,记忆》中,纳博科夫映现出一个天生贵种的知识分子形象,天真却疏离,顽固却妥帖。
人们爱一遍遍重复,因而纳博科夫这一类人的stereotype往往与亡国奴或温柔的幻想家脱不了干系。但书中篇幅最多的,是他瑰丽的童年与金黄色的青壮年,苦难的阴影在他的鹅毛笔尖下轻描淡写地留在纸张上。于是,我只记得他缓慢无声地行走在西伯利亚的泥泞平原里,假装自己是一条熊皮毯子,双眼里只有奇异美妙的磷翅目昆虫。
噢,这个糟老头是多么地爱蝴蝶啊。他的生命之光,他的欲念之火,他的罪恶,他的灵魂——他追逐的只有蝴蝶吗,我们却不得而知。但他和他的珍宝确确实实地留在了我们的视界里。俄国知识分子,那些殉道者、播种者、纵火者…我看到,当其他那些顺着时间的河流而下时,纳博科夫独留岸上。
《说吧,记忆》读后感(二):如果纳博科夫懂中文,定会派一群大黄蜂去上海译文的门口。
就序言的翻译而言,时代文艺出版社的版本更像一本文学书。就序言的翻译而言,时代文艺出版社的版本更像一本文学书。就序言的翻译而言,时代文艺出版社的版本更像一本文学书。就序言的翻译而言,时代文艺出版社的版本更像一本文学书。就序言的翻译而言,时代文艺出版社的版本更像一本文学书。就序言的翻译而言,时代文艺出版社的版本更像一本文学书。就序言的翻译而言,时代文艺出版社的版本更像一本文学书。就序言的翻译而言,时代文艺出版社的版本更像一本文学书。就序言的翻译而言,时代文艺出版社的版本更像一本文学书。
《说吧,记忆》读后感(三):在没有了国属之后
20世纪文明的倒退和进步都绕不开和一个命题的关系:流亡。当然,这是一个现象性的结果,是明显具有深层意识根源的大国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在民众生活中广泛施加的一种影响。是的,包裹了多种因素的可能最初还披裹着明艳的进步革命色彩的、但终究因凝聚了尖锐沙砾而沉滞阴暗的历史,在这一延续几十年的时间段中,被粉碎成了无数颗粒抛洒向万千人的心灵,成为伤痛,或者阴影,或镶嵌在一个个个体生命里,用个体不同的存在方式进行了又一次的追忆加反思式的创作呈现。
流亡对生活的影响和对创作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这其间必然会涉及旧有社会地位所带来身份感在新境况中的调整、与他人关系的定位、对过往社会的评价,涉及到不同语境中交流和理解的困境,最重要的是还有一种不知道该指向谁但又无法消除的抗争。开头说到的文明的进步就和流亡带来的人才和知识的交融有关,这中间,流亡最大的承载地是美国,美国也因此在20世纪中后期成为最有力量的世界中心。不过这种承载并不能消融流亡者在心理在灵魂上的伤痛与困境。或者说,美国之所以可以借力发展,恰恰是因为它并不带有关注灵魂伤痛和困境的感性,它只是给予了一片安全的空与静,让流亡者有一个时空可以反刍记忆、舔舐伤痛。
这是一种阴郁的色调,没有强大的支撑不足以维持这种与命运抗争的体面。纳博科夫是深厚的,流亡前的20年生活给了他在以后颠沛流离的岁月中得以释放温情、保持尊严、维持生存的爱、品性与学识,在流亡中得以从容前行,而不是沉溺过往。
白先勇也有《最后的贵族》来展示流亡,那是属于另一个大陆风云变幻后的故事。不由的想到当年到台湾的大陆人,又是怎么样来包裹和呈现当日的剧变带来的变故和震撼。对此没有研究,也许不善或也不志于言情达意的中国人将所有的浓情都化成了余光中的那枚乡愁,把历史的厚重都变成了清浅的吟诵。
不知道是刻意还是无意,《说吧,记忆》的封面上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名字前面并没有标上国属,他自己也在书中少有的表达了对办理身份证明之类的官僚文件的厌恶。可能,在生命的前20年过后,在太多的流亡岁月中,那个名字前面的国属已经彻底的成了一种通关密语,于他自己,已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他的国属,留在了他生命前20年的那个时空。
《说吧,记忆》读后感(四):万千离愁凭谁诉——纳博科夫与《说吧,记忆》
文 / 韵竹
在许多读者看来,纳博科夫不是个讨喜的人。他有张毒舌嘴,骨子里骄傲至极,看不上这个也看不上那个。从康拉德、海明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历史上那些鼎鼎大名的文豪,无一不被他数落过。他的作品多数曲高和寡,属典型的学院派风格。如小说《微暗的火》居然有近百页注释,文学典故从希腊罗马神话到乔伊斯无所不包,此等天书,怕是想要存心捉弄读者。然而《说吧,记忆》则不同。它所展现的纳博科夫,给人以另一种感觉:温暖且略带伤感。
这是一本自传性回忆录,由十二章独立的散文集结而成。纳博科夫在其中追溯自己的成长、教育和文字生涯,其中不乏动人篇章,如写父母,写亲朋,写家庭教师和初恋。某些方面他像极了普鲁斯特:擅捕细节和瞬间感受,字里行间融合色彩、声音和气味,把“通感”形式运用到了极致。单凭这一点,也不可否认纳氏具有一流作家的才华禀赋,纵使他为弥补经验世界的局限,在其它作品中屡屡捣鼓各类生僻知识。
所谓“经验世界的局限”,指的是他虽身处动荡年代,总体上却过得安稳。回顾纳氏生平,他出身俄国贵族,幼年丰衣足食,过着公子哥的生活。父亲为法学家和政治家,博闻强识、才华横溢。受家学熏陶,纳氏自小习得俄、英、法三语,青年时代又入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可谓百分百精英教育。日后辗转赴美,任教于多所名牌学府,在象牙塔度过二十多年。晚年重回欧洲,定居瑞士直至逝世。作为高级知识分子,他一生志趣仅限阅读、写作、捕捉蝴蝶和研究标本,其间虽历经战火,颠沛流离,却能免受牢狱之灾,得以安稳读书而不问政治,这不得不说是流亡作家中的幸运儿。
既然如此,作为写作者的纳博科夫,所谓“难以言说的痛苦”又在何处?这还得从他的跨文化背景说起。纳氏自小接受英文教育,但作为非母语者,完完全全用英文创作,确是一件非比寻常的难事。在《说吧,记忆》的后半段,他坦言学生时代用英文写诗的焦虑。为提高英文水平,他穷其一生斟酌词句、创新文体,如此极端做法,或是为填补内心作为“异乡人”的不安,希冀为英美主流文坛接纳。《说吧,记忆》属这类跨文化书写的典型。有趣的是,作品第五章用法文书写,其余各章皆用英文写成,后又译为俄文,经补充修改,再度译回英文集结成书。可以说,纳氏的人生经验,经过多次重述与再重述,已然成为一个杂糅体。语言文字经由这种跨文化过滤,加上作者本人又偏爱英美法文学传统,其作品风格不免趋于英法的精巧细致,而远离俄罗斯的粗粝深沉。《洛丽塔》、《普宁》是如此,《说吧,记忆》亦是如此。
然而,相较“融入”之苦痛,纳博科夫更大的恐惧,则是在异国文化影响下逐渐“丧失或讹用了从母国俄罗斯抢救出的唯一东西——她的语言”。因政治体制变革和时局动荡,他深知自己无法重归故土,遂发奋书写俄文,企图紧紧抓住母国文化在自身血液里的一息残存。此种状态下,追忆或写作俨然成为一种抵抗主体危机的方式,以弥合当下与往昔、现实与梦境之间的巨大鸿沟。
及至书末,有关流亡生活,纳博科夫如是说:“我们,流亡者们,虽然使用他们(异族人)精巧的装置,给他们爱开玩笑的人鼓掌,采摘他们路旁的李子和苹果,但我们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像在自己人当中的那种极富人情味的交流。有时候,似乎是我们无视他们;但是偶尔,而且还是相当经常地,那个我们借此平静展示自己伤心事的幽灵般的世界,会产生一种可怕的动乱,使我们明白谁是无形的囚徒,而谁又是真正的主人。”诚然,流亡者游离于母国和他国边界,与异族人和母国同胞都存有隔膜和疏离。作为边缘群体,纵有千般愁绪、万重伤悲,也难以找人诉说。这本《记忆》之书,或道出了他们共同的心声。
注:引文参考王家湘译《说吧,记忆》,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
原文刊载于2017年6月12日《文艺报》第六版“外国文艺”
链接: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0612/c405174-293322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