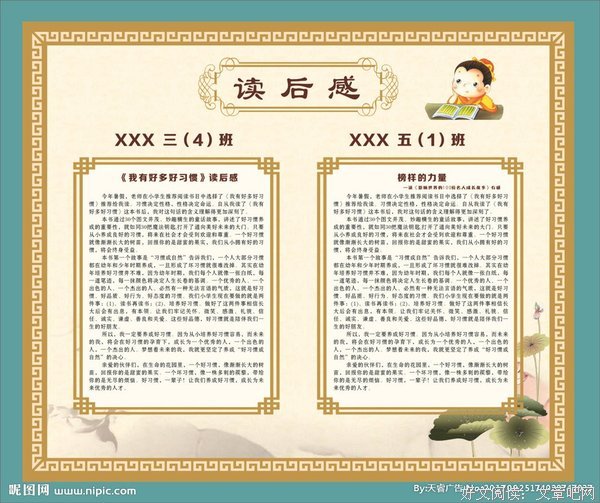《National Geographic》读后感1000字
《National Geographic》是一本由著作,出版的图书,本书定价:,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National Geographic》读后感(一):透过谁的眼睛在看?
我们看到的一定是真实么?如果这样理解是否意味我们放弃了脑子的解读和判断?母螳螂在交配后吃掉了自己的老公,这和我们通常理解的婚姻不同,我该给这样的事情贴上什么样的标签呢?恐怖?不人道?自然法则?本应如此!
照片很美,但多少有些怀疑下面的说明文字。同时也担心自己的理解能力。
毕竟世界太大了,我们不知道不了解的也太多了,就好像没法向我家鱼缸里面的金鱼解释什么是交强险和利息税。
不过你能说金鱼不是在努力观察这世界并希望对世界有更多的理解么?
向努力了解和理解世界的鱼儿们致敬!!!
《National Geographic》读后感(二):very good
《National Geographic》读后感(三):National Geographic--透明的天空*生活馆
透明的天空*生活馆
出售全新National Geographic(美国国家地理),即可单本出售也可成套出售。极具收藏价值。
单本杂志:80年代至90年代,每本15元/本;
单年套装:1982年至1994年,240元/12本;
多年套装:1964年至2005年,共504本。
以上皆为全新正本,是生日馈赠及收藏的极好选择!
联系方式:
联系人:戴小姐
电话:010-81422635
邮箱:crystalskypark@yahoo.com.cn
MSN:followingme803@hotmail.com
《National Geographic》读后感(四):《国家地理》
《National Geographic》读后感(五):诚实的杂志。
如果你生在发达地区你就无法得知落后地区的现状,这就是中国的现状,这也是为何国家地理始终无法获得大陆中文版的原因,对立场的坚持。同时也是我力荐此杂志的原因,当然我早就没有订阅杂志的习惯了,因为我只选择喜欢的期刊主题,而好的主题在任何杂志都是可遇而不可求。
其实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当代的中国都是一个充满了故事与变革的时代,如果中国有一本杂志能真正的塌塌实实去关注中国最普通人群并诚实的报道它时,我会力捧它并订购全期,但很显然,不会有,而即便是我们只是出于对于对被牺牲人群的尊重,这种愿望也变的苛刻。直到它变为一个空洞的历史名词并无人知晓,留下的只有官而堂之的可喜报道,和无人知晓的被牺牲的群体。
可惜的是大多的历史都是这样。
《National Geographic》读后感(六):世界石油 World Oil
y Paul Roberts(June,2008)
WAUMAN译
面临人类对石油需求的不断增长,全球石油产量的极限已逐步逼近。
沙特石油地质学家Sadad I. Al Husseini 在2000年公布了一个惊人的发现。Husseini是沙特国有石油公司Saudi Aramco的开采与生产总监,他对于业界关于石油产量的乐观预测一直持怀疑态度。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他开始研究全球250个高产油田的生产数据,计算每个油田的剩余原油量和耗竭的速度,汇总石油巨头在未来几十年将要开发的新油田。当把两组数据进行比较时,他发现很多石油专家“不是曲解了世界石油储量与石油产量,就是模糊了二者的关系”。
主流预测显示,石油产量呈稳步增长态势,与全球需求量的增长基本一致。而Husseini的计算表明,产量实际上从2004年起就已经趋于稳定。值得警惕的是,这种产量上的稳定水平最多能维持15年,之后常规石油的生产量将开始“逐步不可逆的下降”。
从Saudi Aramco,这个全球石油储备量最大的企业——大约2600亿桶,世界已知原油储量的1/5——而且一直对外宣称石油将在数十年内保持稳定供应的巨头,得到这个预测结果是出乎人们意料的。实际上,根据业内人士消息,沙特石油大臣Ali al-Naimi并不赞同Husseini的看法,Husseini已在2004年从沙特石油公司退休。但如果他的计算正确,严重依赖廉价石油的当今世界,从国防、交通到食品生产,将面临巨大的调整。
Husseini并不是提出世界石油产量极限的第一人。经过数十年的研究,石油地质学家得出结论:当世界原油储备的开采量达到一半时,保持稳定产量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进而不可能实现。世界原油日产量从1900年的不到100万桶飙升到8500万桶,总有停止增长的一天。不管人类是否准备充分,后石油时代逐步来临——美国和其他石油进口大国将不惜代价谋取石油资源,衰退和战争可能会是未来世界的主旋律。
关于预测石油最高产量的争议很多——不是有人认为石油将永不枯竭,而是没有人知道地下还有多少油、我们离转折点有多近。所谓的石油悲观者认为最高产量已经逐步逼近,甚至已经来临,正如Husseini相信的,转折点已经潜伏在日产量的波动中。这或许也能解释油价逐步上涨,今年已经突破了100美元大关。
很多业内人士仍然在为当今的高油价辩解,技术上的瓶颈、亚洲石油需求量的迅猛增长、美元走跌都是有力的证据。“人们对石油的需求将在石油枯竭之前终结”,英国石油的首席经济学家在年初的一个会议上宣称。但是其他的乐观派已开始动摇。不仅油价屡创新高,更棘手的是,不像之前的价格峰值总会带来产量的激增,这次的原油产量并没有明显变化。高油价会鼓励石油企业增加技术研发投资,启动开采难度大的油田作业。例如上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之后油价猛涨,最终导致石油产量增长。但是过去的几年中,尽管油价稳步提升,全球传统石油日产量维持在8500万桶左右,正好是Husseini预测的转折点。
如此惊人的变化使得骄傲自大的石油产业开始紧张。去年秋季,在世界能源组织宣布石油需求量在2030年将再增长1/3之后(即1.16亿桶),几个石油公司的总裁公开表示了对维持产量的怀疑。在伦敦的一个业内座谈会上,法国石油巨头道达尔的总裁Christophe de Margerie宣布“乐观情况”的最大日产量为1亿桶,也就是说,全球石油需求量将在2020年超过产量。壳牌的首席执行官Jeroen van der Veer在今年1月预计,“在2015年后,容易开采油气田的产量将难以与需求量同步”。
当然,像de Margerie和van der Veer这样的老油子不会谈及地质学意义上的最高产量。他们认为,地平面之上的政治经济因素,而不是地下的地质学因素,才是提升产量的最大障碍。备受战争困扰的伊拉克拥有巨大的石油储备,但由于动乱其产量不足沙特的1/5。在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外国石油企业面临种种法律限制,无法全力投入油田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有没有油”,前美国国务院石油专家Edward Morse(现任莱曼兄弟的市场顾问)说,“而是如何克服生产的政治障碍”。
但是,石油乐观派也承认,地质学上的极限已经迫近。以油田发现率为例,石油在没被发现之前是没法开采的,但是自1960年以来,新发现的石油量就开始逐年下降。尽管科技突飞猛进,包括辅助企业发现深层石油的电脑地层成像技术。发现率下降的一个原因是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大多数容易企及的大家伙——所谓的“大象”——已经在数十年前就被发现了,剩下的油田都不会很大。不仅是大油田的发现难度增加,而且必须要发现更多的油田来维持产量。去年11月,业界巨头为巴西海岸Tupi油田的发现而欣喜若狂,它是7年来人类发现的最大油田。殊不知Tupi总计80亿桶的储量还不及1948年发现的沙特Ghawar油田的1/15(在发现之初其储量达1200亿桶)。
小油田的运行费用要比大油田高得多。“世界上小型油田不计其数”,休斯敦投资银行家Matt Simmons说:“问题是你需要不计其数的钻探设备去开采它们”。投资的不等性促使石油企业更偏爱大油田——这也是大油田占到世界原油产量1/3强的原因。不幸的是,绝大多数大型油田都是在数十年前发现的,产量已经接近其峰值,或者已经开始下降。北海、阿拉斯加北坡等产油地区的原油产量都开始一落千丈。
世界范围内,现有油田的产量每年下降8%,石油企业要维持现有产量就必须从新的油田中生产700万桶用于补给,若要满足1.5%的年需求增长量,源自新油田的产量还要更多。但是,随着油田规模下降、成本上升、政治壁垒,发现新的产量将会越来越困难。很多大型石油企业,包括壳牌和墨西哥的国有企业Pemex,销售量已经超过了其新发现的储量。
随着现有油田的产量逼近极限,世界原油需求的不断增长,供求矛盾将进一步加大。ConocoPhillips的首席执行官James Mulva认为,到2010年大约40%的石油会来自目前尚未开采的油田(或尚未发现),到2030年几乎所有的石油都会来自目前尚未运行的基地,他对石油储量深表忧虑。在去年秋季在纽约的一个会议上,他预计全球石油日产量的极限在1亿桶左右——与道达尔总裁的数据是一致的。“原因是”,Mulva说:“哪里还有油?”
无论产量极限是多少,有一个预言是可靠的:廉价石油的时代已经终结。如果历史有什么前车之鉴,世界将不再安宁。上世纪70年代,当阿拉伯世界对美国实施石油封锁,美国的政客为保证石油供应,甚至谋划武力夺取中东油田。
当然,华盛顿驳回了武装行动,但是此类紧张气氛可能再次出现。因为沙特和其他欧佩克成员控制了全球75%的石油储备,他们的产量转折点会滞后于其他产油国,这赋予了他们更大的定价权和世界经济话语权。产量极限也意味着,随着人口增长,人均可支配的汽油、煤油、柴油都要显著下降,如果这对于能源密集型经济,以美国为例,是个坏消息,那么对于依靠石油燃料煮饭、照明和灌溉的发展中国家将是灾难性的。
Husseini为世界对此做出的消极反应而忧虑。节油汽车、替代能源(如生物质能源)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石油枯竭所带来的影响,但更大的挑战是让这个油荒的社会学会减少需求。目前,关于改变能源密集型生活方式的讨论还不被重视,但是随着石油枯竭的那天无情接近,“它终会被摆上议事日程”Husseini说。
《National Geographic》读后感(七):明日之路
eter Hessler
艾小柯 译
两年时间里,我常常去浙江看工厂城怎样在耕地中从无到有的诞生。每次我都租一辆车,沿一条崭新的公路开向明日新城。一般说来我能自由开上六个月而不用担心地方机构,直到我开始收到超速罚单——每张20美元,每次出行三到四张。它们都是被自动照相机照下来的,通常都在限速神秘下降而毫无标识的地段。我在全省的工厂城都收到过罚单:以生产胸罩著称的金华;产人造革的丽水;纽扣与拉链之乡的桥头。
富航租车公司(Prosperous Automobile Rental Company)会把罚款从我的押金里扣除。“罚款是警察的好业务啊,”租车行老板告诉我。后来我听说警察们自己出钱投资了这些自动相机,可以利润分成。车行老板让我记住那些相机的位置,但我从来都做不到——每次我周密计划以便还车时油箱刚好用完就够难的了。这是富航租车公车的商业策略:每辆租出去的车油箱里都只有很少的汽油,刚刚够开到最近的加油站。如果我还车的时候车里还剩下哪怕只有一加仑油,那这一加仑也会被吸出来卖掉——在激烈竞争的中国市场上不能放弃任何可能的利润。
以描述马塞诸塞州Lowell镇早期工业时代著称的诗人John Greenleaf Whittier曾写过这样的句子:“城市破茧而出,如同阿拉伯神话中的魔宫,就在一夜之间。”今天,中国这些工厂城也如同春笋般隔夜而出。人的力量势不可挡:天不怕地不怕的创业者们,步履如飞的建筑工人,年轻的移民。几乎所有的人都因为过去的伤痛记忆而变得更为坚强;大多数家庭还忘不了毛泽东时期的艰苦岁月。而与此同时,大多数中国人也都亲身经历了近年来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常常是大幅度的显著提高。这样的组合——过去的挣扎加上今天的机遇——创造出了一种独一无二积极向上的人民。很难想象这世上会有第二个地方,人们会比中国人更乐意工作。
个人和机构的短视代表了中国所面临的一种基本挑战。另一个问题是人口。不过从某个角度上看,这也是力量:中国的十三亿人口中,72%在16岁到64岁之间。现代历史中这个国家还从未拥有过如此巨大比例的劳动力人口,他们从乡村向城市的迁徙,使中国变成了全世界的厂房。1978年,当邓小平决定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之时,城市人口只有一亿七千两百万。现在城市人口数量已经增加到五亿七千七百万——超过人口总数的40%。社会学家预测,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60%。每年大概都有一千万人从农村迁入城市,为中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
中国人自身都求知若渴。在中国的工厂城里,前期建筑刚刚结束,机器才开始轰鸣,私人教育课程就遍地开花了:英文课,打字课,技术课。在浙江我遇到了罗守云,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完全是个文盲;有段时间他把薪水的几乎四分之一都花在了夜校上。现在他成了一名技师,工资足够让他进入中产阶层。还有一个年轻人学习阿拉伯语以便给中东来的买家当翻译。一名只有初中一年级学历的流水线工人给我看他晚上读的书:哈佛MBA管理技能培训教程。“我还不够成熟,”他说,“我这样的年轻人需要引导,这本书正合适。”
可在中国,新城市仅仅意味着商业机会:工厂,建筑材料供给和手机店。地方政府只关注利润,而共产党一贯不鼓励民间团体,即使这样的团体可能已在他国被证明有益于社会。其实这可能才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的人权挑战。西方喜欢关注那些戏剧化的问题——不同政见者,言论控制——但实际上缺乏制度保障才是影响大多数中国人的问题。工人们只能自己维护自己的权益:没有独立工会,没有自由媒体,社区团体凤毛麟角。通过顽强的意志力,许多工人也能成功,但因此而造成的资源浪费却也是惊人的。改革开放让中国解放了规模巨大的人口,下一步该是学习如何尊重财富的时候了。
在浙江,我开车穿过了六座附属于滩坑水电站大坝的新城。五万多人迁移后,新建的大坝将会为这一地区的工厂们提供电力。目前的能源短缺使水坝建设在全中国掀起了高潮,同时大量人口迁移至新社区,这个过程也会经历类似的发展阶段:建筑材料销售,手机店,遍布垃圾的街道。不过这些地方总有警察的踪影,以防民众因为对拆迁不满而闹事,而且宣传横幅到处都是:今天献出滩坑,明天造福后代。在浙江,如果党的宣传条幅突然开始赞扬长效思维,这变化很难不让人不心存疑虑。
几乎当前中国的一切都让人对环境问题无法乐观,其特色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巨大的人口,薄弱的中央政府,不得不通过不断发展来筹集资金的地方政府。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在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十大城市中,中国已经占了四个。中国的问题越来越成为世界的问题。中国已成为世界主要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国,而汽车潮在中国才刚刚兴起;中国的石油消费量目前仅占世界总量的不到10%。可能让人乐观的一点是,中国与世界已不再可能彼此忽略。若要控制这些问题,合作至关重要。任何发达国家在批评中国之前最好先仔细照照镜子。中国通过制造业满足海外的消费需求而崛起,普通中国人的物质追求也和我们完全一样。美国人批评中国的环境记录就如同吸毒者责备贩毒者一样荒谬。
在滩坑大坝迁徙区之一的石帆,一家人邀请我与他们一起在新公寓中吃了第一顿饭。这位父亲是个还算成功的商人,他很自豪的向我展示了他装修后的家。那里遍布时尚用品:卡拉OK机、45寸电视、头板装有电话的床。但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客厅照明系统。一个巨大的水晶吊灯装有三十多个灯泡,一排排的吊顶蓝灯用以仿真天空,还有嵌在凹槽里的红灯(主人说“它们使人温暖”)。所有的灯都可以遥控开关。
2008年5月中国专刊 结语
《National Geographic》读后感(八):苦水 Bitter Waters
rook Larmer
黄河,中国北方的生命线,在污染和过度利用的双重压力下,潜伏着重重危机。
这里已经数月滴水未降,空气中弥漫着来自远方沙漠的黄尘。当黄河流经这片北中国的荒原时,地平线上却意外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态——绿宝石般的稻田,金灿灿的向日葵,茂密的玉米、小麦和枸杞——在恶劣的环境中生长着。
但是,这片人间天堂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扩张的城市、工厂和农场正在逐渐耗尽黄河的水资源,尚存的水域也受到了严重的污染。沈学祥指着灌溉渠旁的一个排污口,血红色的污染物正滚滚流出,将原本土黄的水体染成了明亮的紫色。“这里以前有鱼有虾”,他心疼得说:“现在却连灌溉都不能用了,我家养的两头山羊,喝了沟里的水不到一天就死了”。
在中国,黄河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对于中国人,其地位相当于埃及人眼中的尼罗河:文明的摇篮、辉煌历史的象征、令人敬畏的自然之力。黄河发源自海拔14000英尺的青藏高原,滋养了大西北的平原地区,中华民族的祖先在这里耕作灌溉,生产瓷器和火药,历经改朝换代。今天,中国的母亲河正在死去——水质污染、泥沙沉积、不当的水利工程——在入海口只剩下几缕毫无生气地水带。步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黄河已经多次断流。
这条传奇之河的泯灭是一个悲剧,其影响力不仅限于流域内的1.5亿人口。黄河的困境也暴露出了中国经济神话的阴暗面,环境污染已经造成了水源短缺。
长久以来,中国人将水视为宝贵的资源——在一个水量等同于美国的国度,人口却是美国的5倍。在干燥的北方,当地人用15%的水资源养活了占中国一半的人口,水的短缺尤其严重。历史上的过度耕种已经让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变得极其脆弱,近年来全球变暖更加速了冰川退化,使得黄河水量减少,土地沙化严重。
但是,与3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比起来,自然力量对中国水危机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与中国经济增长相对应,环境的恶化触目惊心。在努力成为超级大国的征途上,中国不仅耗尽了河流、湖泊的水资源,对环境造成的不可逆转损害更是达到了世界银行指出的“危及子孙后代生存的灾难性后果”。
如果上述的说法让人觉得危言耸听,我们看看黄河盆地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断蔓延的沙漠已经在黄河谷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沙碗,粮食减产、生态恶化并使得数万“环境难民”流离失所。各类有毒物质流入黄河——目前黄河50%的水域被认定为生物学的死亡地带——造成沿岸居民的癌症发生率、出生缺陷率、水携疾病发生率飚升。由环境污染引起的群众抗议在2005年就有51000起,极有可能转化为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正如温家宝总理指出的,清洁水源的匮乏将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
在一坐海拔接近5000米的高山上,一个双颊通红、镶着金牙的西藏牧人遥望着这片圣地。眼前的景象美不胜收:牦牛和绵羊漫步在远处的茫茫草地,山边流过一股清澈的细流,这就是黄河的源头。“这里是我们的圣地”,这个39岁的女人、4个孩子的母亲珥娜卓玛回忆起起家族放养过的600只羊和150头牦牛,“现在都没了,干旱改变了一切”。
实际上,环境恶化的苗头在几年之前就出现了,高原湖泊逐渐干涸,草地慢慢变为荒原。为了保证牲畜的粮草,卓玛一家不得不踏上寻找草场的马拉松式征途。中国科学家将干旱归咎于全球气候变暖和过度放牧,但是卓玛并不这么认为,“是外来的汉人,他们在神山里开采金矿,在黄河源头的圣湖中捕鱼,触怒了天神。面对牛羊的成群死去,卓玛和她的丈夫选择了由政府提供的安置计划,卖掉了所有剩余的牲畜,搬进了位于玛多(音译)的安置小区,在这里,他们每年能得到1000美元的补助。牧人已非牧人,游牧生活从此划上了句点。
中国的水危机源自世界屋脊,三条著名的河流(黄河、长江、湄公河/雅鲁藏布江)都发源于其藏高原的冰川和地下水。实际上,来自青藏高原的水占到了黄河水量的一半。但是,逐渐变热变干的气候已经危及到高原脆弱的生态系统。根据中国气象局的研究数据,这一地区的气温一直在上升,在本世纪末还可能会上升3-5度。截至目前,仅仅在青海省的玛多县就有超过3000个湖泊彻底消失,不断逼近的沙漠正对其余的1000多个湖泊虎视眈眈。冰川的退化率达到了每年7%,消融的冰水能在短期内增加河流的水量,但是科学家相信,其远期影响对于黄河来说是致命的。
为了拯救这条母亲河,中国政府启动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工降雨计划。在盛夏时分,大量的飞机和高射炮铆足了劲,向黄河源头的云层中发射碘化银晶体,将水汽凝结成雨滴。在玛多,整夜的炮火作业使得卓玛一家彻夜难眠,和当地的大多数藏民一样,他们认为这些噪音将进一步引起神明的愤怒。
卓玛始终对于已经消逝的游牧生活不能释怀。对于藏人,一个家族的财富是以牛羊的数量来衡量的,而现在,只有她身上的饰品还见证着昔日的辉煌:三个银戒指,一串宝石项链,还有她的两颗金牙。卓玛整天无事可做,她的丈夫租了一辆拖拉机在当地跑运输,生意好时候的每天能挣到3美元。就在不久之前,卓玛家还能天天吃上肉,现在只能靠面条和炸油条度日。“我们只能去适应”,卓玛说:“还有什么办法?”。从安置房里,她仍然能够依稀看到黄河的源头,但是她与这条河流、那片土地之间的联系已一去不返了。
“干什么的?”保安厉声问道。“没啥”,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妇女回答。在靠近这家纸浆厂的同时,她揣紧了手中的秘密武器——一个便携式全球定位仪。意识到自己并没有离开保安的视线,江林(音译),一个51岁下岗女工屏住了呼吸,迅速的掏出GPS仪,锁定了这个纸浆厂的地理坐标。
尽管兰州以身为黄河流域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城市而自豪,在全球范围更引人注目的是其严重的污染。万幸的是当地民间环保组织已经开始行动,这可能是拯救黄河的唯一出路。上世纪90年代中期,草根环保组织在中国还是屈指可数,而今天已经出现了包括“绿驼铃”在内的几千个团体。江林的25岁儿子,赵忠(音译)于2004年成立了这个组织,旨在保护兰州和黄河的环境。目前,“绿驼铃”只有5个雇员,在一个美国NGO太平洋环境的资助下举步维艰。江林说:“绿驼铃是丝绸之路上的驼铃,它象征着生命,给每个听到驼铃声的人带来希望”。
终于,北京已经开始倾听来自这些草根组织的声音。经历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30年后,政府逐步意识到为此付出的环境代价。环境恶化的影响是复杂的,在经济方面,世界银行认为环境污染每年给中国GDP带来了5.8个百分点的损失,在社会方面,成千上万的环境投诉已经让政府应接不暇。为此,北京已经出台了雄心勃勃的总量减排计划,要在2010年之前将水资源消耗量降低30%,水污染物排放量减少10%。
回到绿驼铃的办公室,江林强调了组织与当地政府融洽的关系。“政府也在努力的控制偷排漏排”,她说。在办公室的墙角,摆着一排装满各色工业废水的塑料瓶——均因为经费紧张无法进行分析。利用有限的资源,绿驼铃还招募志愿者开展了黄河兰州段生态调查。他们最重要,也是最秘密的任务是公开那些邪恶的排污者。“我觉得自己像一个侦探”,江林笑道:“但是普通人必须要参与进来,污染影响到每一个人”。
从兰州往东西北走200英里,黄河在此进入了宁夏广袤的荒原,在这里暴露出比环境污染更加严重的问题:水危机。中国以占世界7%的淡水资源养育了20%的人口。但在连年干旱的宁夏,这一问题尤其突出。历史上,黄河曾经是宁夏的救星,而今天其水量则少的可怜。在银川,曾经磅礴的黄河已经变成了一条小溪流。当地人把缺水归咎于少雨,但最大的根源来自上游对于黄河水源的滥用:不断扩张的农场、工厂和城市都消耗着大量的淡水。
经济的快速增长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毁于它所造成的水危机。中国的660个主要城市中有400个缺水,其中有超过100个城市严重缺水(北京其实也长期缺水,引黄入京水利工程在奥运期间将暂时解决水源问题)。在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中国社会,农村,以及生活在农村的7.38亿农民,成了水危机的牺牲品。
尽管孙宝城的沙地上还有些荒芜,但他看着邻居们绿油油的玉米地,心里还是充满了希望:“如果我们不走,可能活不到今天。”母亲河又一次拯救了人类。但是面临日益降低的水位线,试想:将来,还有可能利用黄河水创造绿洲吗?
毛泽东语录中有这么一段:牺牲一家人,拯救万家人。这句话对于王阳西(音译)来说还是记忆犹新的。就像历朝历代的君王,毛泽东对于治理黄河兴趣浓厚。黄河被称作是“中国之殇”,在滋养生命的同时也因为频繁改道而屡次酿成大祸。1957年,三门峡工程正式上马,包括王阳西在内的40万人响应政府号召移民搬迁。按照毛的语录,他们是在做出高尚的牺牲。“当时我们非常自豪”,83岁的王阳西说:“而现在却只剩后悔”。
自从4000多年前夏朝的首领大禹开始疏通水道、征服自然起,民间就流传下了“得黄河者得天下”的谚语。老爷子深受其影响,并在实际中发挥到了极致。高达350英尺的三门峡水坝正是他“人定胜天”理论的集中体现,这同时也是一个不计后果盲目行动的经典案例。三门峡大坝将黄河下游的1/3变成了“全国最大的灌溉渠”,但因为缺乏远期考虑,工程对黄河上游的负面影响是灾难性的。工程师并没有考虑到黄河巨大的携沙量(超过密西西比河的三倍),泥沙调控的失误致使三门峡水坝造成的水灾比它预防的还多,造成的人员伤亡也是如此。最终,政府被迫在水坝上游兴建另一座大坝,以纠正它的错误。三门峡的一个设计者甚至建议干脆把坝炸了完事。
跟毛的红宝书不同,三门峡水坝不仅仅是历史的遗迹。目前,中国大型水坝的数量占到了全球总量的一半——这是美国的3倍——而且建设仍在继续。黄河上已经有20个大坝,在2030年之前还要建成另外18个。民间对筑坝的反对已经开始明朗化,特别是在移民超过100万的三峡水坝开工之后。知名环保人士马俊(音译)认为在黄河上筑坝弊大于利,水坝会放大污染和过度用水的效应,“为什么老是要去改变自然、征服自然,而不是学着和谐共存呢?”
答案是简单的——北京仍然渴求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使得千万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理性,甚至其生存也在于持续的增长。目前,中国的领导层对于生态保护和资源节约仍然停留在敷衍、做秀的阶段。政府并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将水资源提到一个合理的价格——这个举动将淘汰大量的耗水企业——而是开工了另一个浩大工程:南水北调。这项耗资620亿美元的运河系统每年将在黄河的两段输入12万亿加仑的长江水。毫无疑问,和三门峡一样,南水北调也源自毛的水利梦想。
肖家店(音译)位于距黄河入海口200英里处的一条支流旁,千百年来这里风调雨顺。但是,曾经的生命之源现在却成了毒水。没有人愿意提起笼罩在村子上的厄运,但农民肖四柱(音译)胸前那一道疤痕却证明了一切。那是医生切除他癌变的食道肿瘤时留下的伤口,一边啃着未烤透的面包(这是他唯一能吃的几种食品之一),一边回忆起之前的好日子,“20年前,上游冒出了很多皮革加工厂、纸浆厂,他们把废水废渣都往河里倒”,以前他经常在河里钓鱼、游泳,“现在都不愿意靠近,水又脏又臭,还有厚厚的泡子,恶心死人”。
另一个他不愿去的地儿是村子外的白桦林,那里埋葬着70多民因癌症去世的村民。在过去的5年中,全村1300人有70多人死于食道癌或者胃癌,在临近的16个村镇中还有接近1000人受害。山东知名的肿瘤学家余宝发(音译)在考察东平县后称其为中国的“癌症之都”,这里食道癌的发病率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25倍。
疾病频发成了肖家店村民的一个魔咒,使他们生活在恐惧和羞耻之中。恐惧是显而易见的:去年,村里又有16个人被诊断为癌症;羞耻就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尽管官员告诉村民疾病是由于受污染的饮用水源引起的,很多居民仍然相信癌症源自“气虚”,这又是脾气暴躁、品行不佳的代名词。
就像大多数患者,肖四柱在确诊之后的一年沉默寡言,甚至很长一段时间讳疾忌医。巨额的医疗费掏空了他的家底,肿瘤也使得他只能发出轻微的呻吟。尽管如此,现在肖四柱是村子里少数几个能坦然面对的人,“如果我们不说,没有人来管这些事”,他吃力的说。政府最近在11英里外开辟的新的饮用水源,同时派驻了医疗队。肖认为,如果不是两年前一个村民向媒体披露了此事,政府可能永远也不会注意到肖家店。
几个月之后,河边的白桦林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坟堆。坟头并没有墓碑,只有几棵竹子飘摇在微风中。肖四柱还是来了,加入了那些死于癌症的邻居、朋友的行列。这是一个残酷的讽刺,他们的长眠之地居然面对这将他们吞噬的河流。
要拯救肖四柱已经太迟,但是征求黄河还有一线希望。中国的领导已经意识到面临的困境,高呼要建设“生态文明”,每年将拨出巨额资金用于环境保护。但是,未来同样掌握在普通人手中——就像赵忠,和他勇敢的母亲江林这样的积极分子。还记得那家江林跟踪调查的兰州纸浆厂?在其信息公之于众后,立刻就同其他30多家非法排污企业一起,被政府关闭了。
“一个人的影响是有限的”,赵忠说:“但是一旦与其他人的力量联合在一起,会变得无穷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