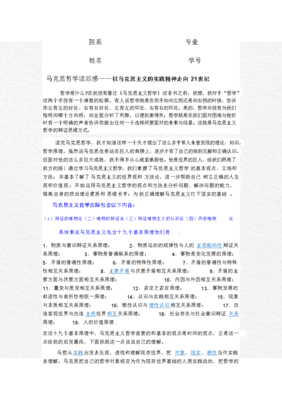政治自由主义读后感精选
《政治自由主义》是一本由(美)约翰・罗尔斯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80,页数:64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政治自由主义》精选点评:
●应该看原版,翻译得相当晦涩
●终于跟着读书会的小伙伴一起读完了。罗尔斯从人人具有的道德能力入手,论证出人的基本权利,以及基本权利的优先性,进而产生公正的正义原则、宪法、社会基本结构、法律和法院判决,并在此过程中与社会中已经存在的各种完备性学说之间保持一个礼貌的距离,对自由主义的辩护非常有力
●不推荐阅读、
●需要再读一遍。
● @2008-04-15 12:59:31
●我就想问一句,翻译的人自己有没有读懂原著?比如在原著412页,译著第436页,译者将大量的autonomy翻译成自律,看的云里雾里。翻译成自主性似乎更明了。
●并非每个人都有伯林般天赋异禀的洞见,但负责任的学者可以用二十年的学力来支撑起同等地位的观点。罗尔斯不是人们今天口口声声呼唤的那种“有很大的想法”的思想家,事实上他们也根本不知道自己期待的“思想家”到底该是什么样。罗尔斯是极端严谨的政治哲学家,他仅仅不遗余力陈述自己的看法和佐证,他不是克尔凯郭尔或者伯林,而是康德是黑格尔。
●很不好意思地写读了,如果这么囫囵吞枣的也算的话,唉。
●哎。。。
●戴元光教授指定书目。
《政治自由主义》读后感(一):罗尔斯的契约论
一
罗尔斯所设计的政体,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一种扩展了的契约论。霍布斯的契约论,以人和人之间充满敌对和伤害,所以过集体生活的话,就必须有一个强力来压服。他的这个前提是错的。洛克以人类为上帝的子民为前提,推论出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对上帝有交代为中心,并认为政权是人们集中起来进行商议所做出的一种协议契约。洛克以为逻辑上应该如此因此历史上也应如此。自然,洛克的这个前提和推论也都是有问题的。卢梭的契约论体现了一种平民精神,即使是集体层面,也把给予个体以平等,把集体当作是平等个体的集合。但是他走火入魔,把政治问题或政治生活当作个体的全部,要求个体把自己完全交给整体,完全牺牲个体性而和集体融为一体,构造出一种错误的“我为集体,集体为我”,“我即集体,集体即我”的假象,所以被眼睛雪亮的群众看出来带有极权主义强制色彩。
罗尔斯的契约论,首先是寻求正义,而不是功利。霍布斯的契约论显然是为了让人们能够不相互伤害地生活在一起,目标是很低的,而且也是一种低级“利益”。罗尔斯一再强调基本自由作为首要的“好处”,必须有一种任何其他价值不可僭越的优先性。正如哈特对罗尔斯的一句总结,罗尔斯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出对自由的爱,高于任何其他“好处”,比如社会的繁荣和进步。其次,罗尔斯把公共政治领域和私人领域分开。卢梭或许忘记了私人领域,又或者,他仅仅停留在了所谓“古代自由”的这种状态下,即是说,在生活相对简单的古代,人们仅仅有一种公共的政治生活,私人生活领域非常狭窄。在这种情况下,就如亚里士多德,把政治生活理所当然看作人生最重要的内容。但是现代不一样,现代世界的丰富性使得生活中,个人的私人领域甚至在个人生活中占有更大的内容,比如经济、文化、娱乐生活。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一种“我不关心政治”这种奇怪态度的出现。罗尔斯的契约,仅仅针对人们的公共合作社会活动。为了达成一种大家都任何的契约,或说一种公共遵守的行事原则,罗尔斯祭出了他的“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正如罗尔斯一再强调的,这不是历史上发生的事实,而只是一种假设。
二
罗尔斯的原初状态,把所有人都“归零”,剥掉了每个人的社会和自然属性;不仅如此,他还设置一个无知大幕,让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未来发展会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每个人,只要有理性并且按照理性,都会接受他的所谓justice as fairness的合作协定,因为他的这个协定,给每个人足够的保障。其一,罗尔斯认为,没有其他的理论,能够有他的这个“公平的公正”理论的效果。他说,历史上出现的一些理论,无论是宗教、哲学还是道德理论,都不能赢得所有人的赞同。所以,不能找这样一种完整的包括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完备理论来作为让所有人都接受,也不能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构成一种美好社会。基督教已经分裂了,其他宗教不幸,理性主义的密尔的个人主义和康德的道德完善论都不行。其二,罗尔斯认为,自由社会下,自然发展出各种持有不同三观论的群体,这种“多元性”是必然并且会长存的现象。任何一种这样的理论,如果作为社会组建的基础,那么必然会构成对其他群体的压制。所以,要获得一种平等、公正的共识,就需要放弃这些理论,而另外寻找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理论。其三,罗尔斯认为他的理论,是一种即使不是最好也是更好的选择。一则,他的理论符合“重合的一致同意”,不偏向、不批判任何一种学说,因此具有“公正无偏”的立场。这是因为,他的理论仅仅关注公共的政治范围,仅约束公共活动,而不干涉个人的信仰和追求。二则,人们根据理性,能够达到、理解和接纳这种“一致同意”,不仅因为这种公平公正的原则保证了每个人都能够从这种社会公共合作方式中获益,而且这种政体还确保了每个人都能够去追求公共领域之外个人的生活信仰和理想。
罗尔斯的理论中包含了两种基本的原则,其一是确保个人基本的自由。如言论自由、良心自由、移居自由;其二是社会存在的经济或政治不平等,应以能够最大促进最劣势群体的利益为准。一方面,罗尔斯的这个理论就是一个集体生活方面的一个基本框架,用于兼容任何“理性”的完备学说。能够在让人们相互合作,共同促进社会进步的情况下,每个人都能够去实现自己的潜能,以及自己的信仰。另一昂面,罗尔斯认为这些基本的原则仅构成宪法,宽泛地保障人们的基本自由和权利,至于具体的事务,则留给立法来确定。
三
如果天堂有网络,我希望能给罗尔斯发封邮件,来跟他探讨的我几个困惑。我相信他不会拒绝,毕竟他甚至专门写了一篇文来回答哈贝马斯,而这个哈贝马斯看上去就像德里达这类作家一样,喜欢用修辞来探讨学问。洛克在《人类里结论》中曾说,Figurative speech就是一种the abuse of words,他说:“机智和想象,要比干枯的真理和实在的知识易于动人听闻……如果仅仅追求快乐而不是知识和进步,这些figurative speech而成的装饰或不是什么问题。修辞学的一切技术,和演说术中所发明的一切技巧,都只能暗示错误的观念,都只能够打动人的感情,都只能够迷惑人的判断,因此,它们完全是一种欺骗”。罗尔斯在回答哈贝马斯的说法时,对于哈贝马斯“在市民社会中重新点燃原初状态激进民主的灰烬”这一类说法,常常表示“我不清楚”,“我不明白”,“它包含着某些令人疑惑的陈述,而我怕我没有理解他的意思”。 或许正如罗尔斯自己所说,对于这类不诚实的叙述,或者没有反驳的必要。毕竟,“garbage in, garbage out”。
我认为罗尔斯没有搞清楚“理性”的问题。正如哈特对罗尔斯的分析,罗尔斯常常要求,甚至默认,人们有一种从理性上能够得到的逻辑上的美德,而不仅仅是一种直觉上的道德。这是因为,我相信罗尔斯自己也意识到了,直觉上的道德是有问题的。我相信正是因为这个问题的困扰,导致罗尔斯提出了无知之幕下的原初状态,通过剥离人们的“属性”,使得人们相互达成一种假设的等同状态。这实际上变成了一种“程序正义”,而不是“实质正义”。所谓程序正义,就是说,给出一种程序,任何人,只要采用这种程序,都会达到一种公正。罗尔斯提到“分蛋糕”的例子。如何在一群素不相识的自私的人中间合理分蛋糕?正确答案是让切蛋糕的人切完蛋糕后,最后一个取。通过这种程序,这个人就不会切给别人小块,给自己留大块。他的最佳策略是,所有切出来的蛋糕块一样大小,这样能保证自己获益最大。实际上,无论哈贝马斯还是罗尔斯都没有注意到,实际上这是一种博弈。回过头来看,罗尔斯的假设,实际上在设置一个博弈之局。如果大家都一样的起始条件,没有人知道自己将来会是怎样,那么就进入了一种赌局。你可能是多数派,也可能是少数派。你可能是天赋异禀,你可能是资质平庸。你可能生而平穷,你可能生来富贵。罗尔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能够接受这样一种协定,即确保最基本的保障,因为自己也可能是少数派,所以会禁止多数派欺压少数派;因为自己可能生而贫穷,所以会同意或要求社会上的优势者割舍一些利益给劣势者。问题在于,他这实际上是假设了人们都是risk aversion的人格气质倾向,然而或许并非人人都是如此,所以他的这种实际上想实现“程序正义”的假设也是有问题的。
通过博弈性策略做局,就如分蛋糕的例子,如果能够实现公平正义,那么对人类来说,实际上无比适用。所以,我相信密尔、康德和罗尔斯,都会同意这一点。但实际上,这一点非常难以实现。这是因为,自然发展,从来都是一种博弈,但是自然的发展,从来只是达成一种力量的均衡,而不是形成一种“正义”的均衡。自然是一种适者生存的进化,是不讲道德的;正义是一种道德判断,而只有在人类身上,才有这种“道德”的追求。所以,人类的历史从野蛮到文明的发展,实际上是人类自身随着知识的积累和理性认识的提升,所逐渐要求和构建出来的结果。对于人类社会,即使是要构建一种“博弈”的情景,实际上也需要有价值判断先行。比如说贡斯当以及其他很多人所不断提到的通过分散权力来达成对权力的限制,比如说波普尔所提到的民主的选举、短任期制度是作为一种防止坏人执掌权力而非选择最优秀的人作为领袖,都是一种程序性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修宪延长任期的做法,都是反文明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做出价值判断是一种必然。做价值判断的问题在于,谁的价值?如何判断?
罗尔斯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大众理性。我认为他的这种方式,或许不如哈贝马斯的公共讨论。当然,罗尔斯实际上也说交给公共讨论,并且也说实际上是理性上通过讨论不断完善的过程。但是他的视角是错的,他牢牢盯住了“大众共识”,所以他希望有一种简单的、容易为大众理性所理解和认可的一种公平正义,作为一套方案来构建社会。密尔实际上在《论自由》里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人类的理性有限。所以,一方面,没有谁的观念能够保证是对的,所以不能让某一个人的观念成为真理,压制其他观念;另一方面,由于大家的理性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最好就是采用一种集思广益的做法,让个人都发挥自己的想法,这样人类随着自身的知识逐渐积累和提高。罗尔斯为了达成一致,实际上迁就了这种大众理性,所以他还认为,大众理性达成的一致带有历史性,即不同时代,可能有不同的结论。这样,罗尔斯实际上就是一种务实派的态度,不寻求真正的真理,仅仅为了能够在实践上可行。
罗尔斯不仅没有寻找一种完备性的三观理论来支持公平正义理论,甚至还有要和任何这种完备性的学说摆脱干系的意思。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正如哈特所分析的,罗尔斯不得不默认了他的民众带有一种政治美德。罗尔斯不断强调民众的两种道德能力,其中就包括一种人们愿意和其他人合作,大家都从中得到好处的一种“正义感”。因为没有完备理论支撑,所以罗尔斯不得不放弃了“理性”,转而寻求“感觉”,即正义感和道德感。但是,遗憾的是,这种他认为通过在秩序良好的社会里熏陶,人们逐渐发展出来的正义感,只能说是一种脆弱的基础。这或许也使得他的整个观念,变得基础薄弱。
《政治自由主义》读后感(二):美利坚意识形态
这篇文章讨论的问题是以下三本书中涉及过的: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
本文将讨论两种意识形态,这两种意识形态在美国都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其一是“多元文化”,其二是将美国将基督教与民主制连接起来的公民宗教。分别可视作是左派和右派的。本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谈意识形态与“多元”结构的内在关系,第二部分谈意识形态与历史终结论,第三部分谈冷战结束后(尤其是911后)的美国与世界。
1. “多元”作为现代诸意识形态的结构特征
一切意识形态都必然拥有的一般特征,即过度修辞。如“私产神圣”是一个意识形态口号,然而在主张私产“神圣”的人内部,也没有任何正常人会对统一征税感到奇怪。意识形态的过度修辞是为了塑造某种幻觉,用幻觉驱使我们去实现某个比这个幻觉小得多的目标。例如当美国国父们说“不自由毋宁死”时,他们说的是何种具体的“自由”呢?其实是“无代表不纳税”。意识形态的原理不是以“科学育儿”的方法让学步的婴儿去学步,而是让学步婴儿去追天上的鸟儿,以驱使婴儿有站起来的欲望。
然而修辞的语义永远在漂移中,它不像日常语言那样具备稳定性。修辞中的美好幻觉毕竟不可能在法律规则上实现。这表现为:意识形态一方面要求权力,同时却恐惧并排斥着“现实性”的恐怖。原因是意识形态家们心中清楚,若真的在政治暴力上“认真”贯彻了此意识形态,才是大败。意识形态渴望的不是成功,而是小败:所谓“小败”就是一边保障意识形态的修辞尚未被全部实现,使人们尚且对它“实现后的美好”心存希望,同时恰恰已实现了它的真正的、被隐藏起来的目的,毕竟编造意识形态起初就不是为了追天上的鸟,也不是为了让私产“神圣”;而是为了让婴儿学走路,让私产的权界和赏罚规则清晰化。
然而意识形态的这一特征,会引发很多问题。那些学会了走路,却仍追不到鸟儿的孩子会不会哭呢?那些私产权界和法律规则已经清晰的人,会不会根据“自然权利”的意识形态做出过度的主张呢(例如从洛克的劳动价值论到马克思,从诺齐克到柯亨)?因此,在意识形态宣传必须在实践上克服它的理论悖谬:它必须被当做幻象,人们必须尽可能对自己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宣传的真正目的心知肚明——
——“liberty”这个词之所以可以在美国、法国革命中被使用,不是因为革命之前的美国和法国缺乏liberty这个修辞,而是因为缺乏合理的政治装置。这才是这一宣传的真正目的。在不缺乏该政治装置的英国本土,慷慨激昂的意识形态口号被休谟、斯密、边沁的更具体的哲学、经济学和法学取代,被渐进的工业/交通革命、市场一体化、规则一体化取代。意识形态修辞是过度的,这注定它无法静态地生存;无法着眼于当下、无法着力于当下,它必须依赖对未来的许诺和继续扩张的空间(这一点很重要)。
这一特征注定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倘若不疯狂的话)都只是在相互对冲关系中。颠簸的时代浪潮与宗派主义的狂热冲突是意识形态的生命力源泉。因为当它们的信徒冷静下来思考时,他们也并不曾真正地相信,如果其意识形态所主张的政治被一丝不苟地执行,世界会更好。他们心里都暗暗明白:该意识形态若真的完全支配世界,反而是末日。因此它只有伪善(法利赛人)或伪恶(大话王子)。
意识形态的伪善(法利赛人)体现在将遵守意识形态的习俗准则等同为“道德”的:只要我自己的手没有沾血,哪怕因此生灵涂炭,我也是道德的。这是掌握了现实权力的人,在有能力改变世界时,所采取的一种规避责任的谎言。
意识形态的伪恶(大话王子)的缘起与掌握权力的伪善者相反,是意识形态信奉者在知道这一意识形态不可能掌握权力时放出来的大话。因为反正多元世界已成现实,反正自己不可能全赢,所以说大话也无所谓。意识形态宣传家知道要撒谎,就得撒弥天大谎,因为人只会对弥天大谎上瘾。
请注意:我不否认那些说大话的“宣传家”能起到推动历史的作用,但这种推动的后果不仅不是以他们的意志所欲望的,甚至其后果不是他们能想象到的。越是这样的大话也越会激起反感,激起反作用力。毕竟人海之中有契合某修辞的心理需要的人很少,因此当你吸纳了一个信徒,往往已经刺激出了更多嘲笑者或反对者和反向的意识形态修辞。在社会总合力上往往面临正反相抵的局面。大话宣传能改变历史,却无力如其所愿地推动历史,它的真正作用是将人群分割成一个一个内部互相影响的小圈子小宗派,互不相容,变乱口音。此即“多元他者”的起源。“多元他者”并不是某些“渴望多元化”的人造成的(那些所谓“渴望多元文化”的人是不够真诚的,他们中的多数其实只是不满主流文化而已),“多元”文化中的每一种文化的信徒脑海里,都上演着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文化大一统的好梦。正是从各种小宗派的激烈竞争中才诞生了“多元他者”。若询问这些诸多宗派的意识形态信徒,他们都会异口同声地谴责这个多元的、缺乏相互理解的世界,并将原因归咎于竞争对手:你们若都改宗了,多元乱象不都消除了么?
这样的局面正是凌驾其上的当权者乐于看到的:即便不知道什么叫“认真对待权利”,人们也会发现小圈子里的组织原则无法应用到人口过亿的陌生人社会,“意识形态相近”的周末聚会组织原则无法应用于商业和财产,所以诸相互对立、抵消的寄居在诸小圈子里的意识形态,都其实已经放弃了挑战、取代现行秩序的野心。相反若不存在小圈子,陌生人们就必须放弃意识形态修辞而转为日常语言和理性考量。任何无法得到辩护的、明显荒谬而痛苦的政治规则都会暴露于聚光灯下,整个社会就会不可阻挡地越来越民主化。
在古典世界,由于优势意识形态是被普遍信仰的,他们只需要采取法利赛人的模式就可维持稳定。而古代世界中的那些大话王子,都是信奉某种劣势意识形态的人,其意识形态如果不说出荒唐的大话就无法维持。古代的权力装置是自上而下的天命神授,所以不需要大话王子的宣传。
在印刷术普及后,全球网络实现前(1500-2000)的现代史上,大话王子比法利赛人更占宣传优势。在这段时期,法利赛人的死水已被打破,全球信息尚未汇聚成大洋,地域的局限、信息的闭塞使得大话型意识形态凝结成了一个一个的“教派”与“民族”。然而大话王子们一旦掌握权力,要么变成和法利赛人一样的虚伪,要么就将大话付诸实践,成为罗伯斯庇尔式的人物。
古典世界中的意识形态为政治服务,政治权力并不需要反过来耗费巨大的成本维护意识形态,这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尚未被戳破,尚未被揭露为意识形态的前提上的。而在现代世界,政治必须反过来为意识形态服务。“皇帝的新装”被嘲笑之后,皇帝唯一的选择,是在其禁卫军也参与到对他的嘲笑之前,用暴力机器维护他的新装。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大多数人都渐渐知道:大话只不过是意识形态,所以人们决定(至少在寻找到一套更精确的词汇从事政治之前)暂且默许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正是对意识形态虚伪性的默许,区分了成熟的英美现代民主与那种更“诚实”地不顾一切执行意识形态命令的疯狂政权。(在此“诚实”不是一个褒义词,参见:http://www.douban.com/note/350999081/ )
因此后现代的意识形态模式就诞生了:它承认自己说的不过是谎言而已,它承认怂的正当性并以机智自夸。古典的法利赛人说“太初有言”;在这一稳定秩序消失后,现代的大话王子说:“我的(私人)语言是真理”;当私人语言被现代人抛弃后,后现代的人开始说:“人们‘需要’高贵的谎言,我要说谎了,你要相信哦。”
然而意识形态如何保持住虚伪呢?任何意识形态团体,都有愈演愈烈、丧失界限、走向疯狂的倾向。此类团体常以某种似是而非的修辞为始,经“解释学”的“理解”,渐变成某种荒谬的修辞,在外人看来其语言犹如疯癫,他们自己却浑然不觉。因此若要维持意识形态的虚伪(安全),必须有一种能够同时既能满足、又能维持意识形态的叶公好龙的虚伪欲望的模式。然而这是极为困难的,正如恋爱的结果不是分手就是结婚,意识形态幻觉的结果不是破灭为现实就是实现为现实,两种结局都将导向幻觉的消亡。我们很难设想一个永远的恋爱。然而政治与恋爱不同,它可以依靠一种模式来同时既满足意识形态,又维持它们,即“多元主义”——
(其实历史上曾出现过“多元主义”的恋爱,也达到了同样的效果:既维持住了众多的追求者,令他们为自己服务;又不完全倒向其中一者,以至让其他人心灰意冷。这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的策略。)
——“多元主义”本身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更是一种诸意识形态的持续共存模式。它依靠差异燃起火焰。多元化确保了诸意识形态之间不会相互吞噬,令其持续竞争。凡试图保存意识形态者皆偏爱“社区”,无论是左派每逢诘难就开始呓语的“community”,还是右派喜欢的美国农村,因为community是意识形态唯一能转化为政治力量的场所。罗尔斯所谓reasonable和unreasonable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划分是虚伪的:合理的和疯狂的意识形态之间没有界限,因为哪怕在小圈子内看似合理的意识形态,一旦走出去被毫无保留地、原教旨地执行,也是疯狂的。真正能遮盖这一界限的虚假性,骗过很多人的,恰恰是他的所谓“多元文化重叠共识”的当代现实模式,正是多元性保障了没有一种意识形态能够大获全胜,也就赐予了每一种意识形态夸口“如果全世界人都信仰XX,将如何如何美好”的自欺,这种自欺赐予诸意识形态宣传家们以虚假希望,在现实中遭遇无数“异教徒”和“他者”的挫败面前燃起更高的热忱。然而事实上,即便看起来reasonable的意识形态,不过是败者的光荣。
2. 世界历史的黑夜与白昼
霍布斯、斯宾诺莎、法律实证主义的现代政治要诀在于“国家”只是外部装置,斩断一切政教联系(斩断政教联系在历史上只是幻觉,只在20世纪语言学转向后展示出实现的可能,但这不是本文的主题)。而“后现代”却是这样的一种时代:意识形态被堂而皇之地承认为心理的。人们公开承认:塑造偶像只是因为在心理上需要偶像。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变得模糊:不再仅是如现代思想家说的那样,意识形态单向地服务于现实利益,充当它的借口和旗帜。当人们醉梦于意识形态时,这种醉梦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维持这种醉梦状态就成为了政治决策的一大关键。后现代主义者一直“后”着,“后后”着,“后后后”着。而将这种“一直后着”维持下去、维持意识形态不消亡的唯一办法,是承认“多元”,以彼此的相互对立将将诸意识形态维持在黎明的地平线上:你看得到那曙光,却永远到不了。
在每一个宗派主义的意识形态小圈子里,信徒们都相信自己身处新时代的朝霞,可是他们无一例外都畏惧正午。
将普世民主维持在地平线上不让它升起:既不要白昼,也不要黑夜。在民主制仅被局限于地球上少数几个国家的一百年前,将现实的政治民主和某种意识形态幻觉捆绑,是一种良好的策略。在任何意识形态的萌芽和上升期,这种策略都是几乎没有副作用的,修辞幻觉提供的只有希望,没有绝望。然而当现实的民主已经在大半地盘稳占上风,意识形态的民主就会预见到它自身的未来危机:现实的普世民主实现后“民主”这个词也将消失,它将消失在“政治”这个词中。人们将遗忘“民主”这个词,因为民主政治只是规则和装置(如何令优势者中没有人权力大到能安全地违反规则,令无权者不至困窘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令遵守规则对一切人都是最利己的选择),如此而已。
与“民主意识形态”在普世政治民主建立后就会消失的命运相反,君主主义作为前现代意识形态,它渴望彻底的黑夜。专制权力最无法忍受“半个世界的民主与半个世界的专制共处”的局面。在这种泾渭分明、界限清晰的共存中它必将失败,因为在这种局面下,呈现为启蒙学对神棍学在社会组织、经济效率、意识形态真诚度等所有方面的完胜。民主的意识形态是现代型,专制的意识形态是古典型。现代型意识形态是大话王子,例如地上天国;古典型意识形态是法利赛人,例如君权神授。古典型意识形态的“大话”是放在死后/彼岸世界的,因此不担心大话被实现之后的幻想破灭,也不存在“胜利之后呢?”“属于何人之胜利?”等问题——这类问题是仅属于被现代意识形态纠缠的人。全世界若都是专制国家,专制的意识形态骗局不会被戳破,而能得到更好的掩饰。皇帝不能容忍有人戳破他的新装,也不能在这类戳破者(哪怕只有一个小孩)面前露出丝毫软弱,因此要求的是绝对的黑夜。
那么有谁盼望绝对的白昼(普世民主的现实实现)呢?只有两种人:
第一,非意识形态地思维政治,将国家仅当作装置和规则的人,他们对国家毫无热爱。任何“国家”只不过是用来实现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工具。他们的政治思想本身就是绝对的白昼;“民主”这个词对他们而言本来就不重要,重要的是“think politically”,政治地思维。当大多数人都政治地思维,而非意识形态地思维时,当大多数人以实在的法律规则和日常语言思维,而非用“主义”思维,并将那些无法写入实证法的神棍词汇视作无意义的废话时,民主就是所剩唯一的可能性。
第二,美国民主信仰者,他们尚未意识到自己所信奉的是“美国意识形态”而非政治民主,被这种意识形态幻觉所骗,被诱入理想的牺牲。
然而当普世民主实现后,后一种人会转入虚无。如果这种意识形态的信仰者的智力足以在普世民主到来前就预见这一点,他们的唯一可能即是成为西方衰落论的悲观主义者,甚至(以直接或间接的修辞)反对将民主普世化。
意识形态将道德呈现为固化的道德准则,要么是“我是好的,所以你是坏的”,要么是“你是坏的,所以我是好的”。无论今天的美国意识形态是哪一种(其实两者皆有),都不能适应普世民主完成之后的那种缺乏对立面的价值,即“让我们具体地判断诸事的好坏”。如果这种不适症达到一定的程度,历史终结的幻觉就会在普世民主后变成文明冲突:为了维持这种“好/坏”的意识形态对立,诸文明(包括美国人)会强化自身的文化,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强化本身又会损伤民主的外在制度,将历史拖入下一个循环。因此强化美国意识形态,看起来是支持这一民主普世化运动的,但实际上这种意识形态越强,它在推广民主的初期助力就越大,但在越是逼近普世民主最后门槛时候,它对民主的阻力也会越大。
如果将民主视作一种仅仅基于人类生活的基本形式(霍布斯:political man as talking wolves,作为 “有语言的狼” 的 “政治人”)而生的政治学原理,那么它根本不需要对立面。但如果将 “民主” 绑定在某个意识形态上,认为美国 “文化” “公民宗教” 是 “民主” 的最明亮的光源,那么它就必须维持敌我的区分,因为倘若不存在这种层级差异,那么美国的文化也将与民主的政治装置分离。“敌/我” 二元区分并不是政治的概念,而是意识形态政治的概念。“决断” 也不是政治的概念,政治的概念只有一个又一个殊别而具体的好坏判断。施密特不是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哲学家,他的所谓 “政治的现实性”,完全是建立在意识形态政治的历史条件上的(他所回应的也正是德国史上意识形态最严重的时代的问题)。真正政治的基础二元概念是 “赞同/反对”,而非 “敌/我”。一切政治都必然有赞同和反对,我们无法设想一个没有赞同和反对、不作价值评价的政治。但只有沉湎于对想象的共同体的人才总是在政治中寻找 “敌/我”。
只要今天拥有美国国籍的人类(不是“美国人”)仍寄托于意识形态的“理想”,那么对于他们而言,普世民主的实现就是一次理想的牺牲。在这一牺牲中最大的祭品将是那些信奉它的人。为阻止这一牺牲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以功利主义、法律实证主义取代意识形态,要么中止普世民主进程。前者是彻底现代的,即“非意识形态”的政治(它同时取消了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后者是后现代的:意识形态本身在后现代被计算入“现实利益”的一部分。如果“美国人”认为美国无法丢掉意识形态存在,那么逻辑结果就是:为意识形态续命就是为美国续命。现代意识形态是诉诸狂热信仰,例如德国人力图将德国“Kultur”凌驾于一切之上。后现代意识形态却意识到自身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它要求克制,深谙与其他的意识形态井水不犯河水、偶尔发表些只触及皮毛的相互谩骂才是生存之道。单以外在表现论,这种叶公好龙式的虚伪,无法区别于传统的法利赛式伪善,奥巴马以各种陈腐规则为借口,绝不以实质行动推动民主。延缓民主,也就延长了美国的意识形态生存。
3. 意识形态史的终结VS意识形态(文明)冲突论
美国推广自由民主政治装置的动力,不仅出自美国人对独裁压迫下人民的善意(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同时也是出自对意识形态的信念。小布什政府的举措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热忱,他不会这样做。小布什是属于那种“大话王子”类型的现代君主。这样的现代君主的特征在于他们真诚地信奉某种意识形态:不仅放出大话“邪恶轴心”,而且还为之付出实实在在的努力。小布什信仰普世民主是好的,但他从不思考一种意识形态的普世胜利(也就是消灭了一切对立面),对寄生在普世民主的政治装置上的意识形态而言意味着什么。
奥巴马以及美国左派的“多元模式”与其说是一种反西方的意识形态,不如说只要不是真诚地(如法国左派那样)信奉多元主义竟到了支持伊斯兰的地步,令政治装置濒临危险,而仅仅是利用“多元”让诸意识形态谁也无法大获全胜,那么它就会形成最有利于西方的格局:一方面,在西方中心主义已经事实上被安全地确立的国家,它让诸意识形态不陷入原教旨。另一方面,多元模式若被曲解为相对主义,就尽可以将发展中国家维持在积弱地位。
小布什所卷起的“第四波民主化”令奥巴马惊恐。在这个意义上,奥巴马(无论他自己是否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但这不重要)是比小布什更深谙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的君主:他是意识形态的维持者而非其信徒,也只有本身不信仰它的人,才有力量充当意识形态的维持者(对于意识形态修辞的编造者而言也是一样的:诗人要做的是超拔诗外,维持情感的程度与形式,而非狂热地投入)。奥巴马们隐隐预见到:当普世民主的太阳爬上正午,也就是“人”的意识形态阴影最短的时刻,习惯了将政治与“信仰”捆绑在一起的美国人将失去信仰的对象。民主将是彻底政治的,成为“每个人暴力力量差不多”这一生物学事实的现实结论,“人”也将被迫迎来最后一个定义:从动物到自我超越者之间的绳索(这是现代“人”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定义)。
我们不必低估了自己的时代:人类从未如今天这样接近民主的正午,即意识形态阴影最短的时刻。伊丽莎白一世曾以比莎剧更动情的演说词巩固力量,而21世纪两位美国总统用稍微含糊的修辞说“邪恶轴心”或“别做傻事”时,都遭到了激烈批判。你能想象今天的美国总统说出“Let tyrants fear!”这样的台词吗?哦,不,这太莎士比亚了,太夸张了,而我们生在一个对任何过分的夸张都会困窘脸红的时代。这是讲究用词精确的时代,在对精确性和确定性的追求背后,浮现出一种更成熟的、更冷峻而不可战胜的力量,这种力量强大并自信到了不需要以任何夸张的形式出现。我们已经将从伊丽莎白一世到丘吉尔、希特勒、马丁路德金这些演说家的时代抛在了身后。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以为上演《理查二世》能有助于谋反,纳粹推崇《科里奥兰纳斯》,而美国占领军会禁演这部“反民主”的戏剧。然而在今天的任何正常国家,对意识形态魔力的信奉或恐惧都只会遭人耻笑。互联网二十年对意识形态的祛魅和削弱,比自霍布斯、斯宾诺莎以降三百年都要有效(1850-1950正是意识形态狂欢的巅峰)。世界语(英语)和全球互联网的普及意味着修辞所需的特定“场所”的消失,如果说工业之于艺术意味着对艺术之“光晕”的剥离,那么完全开放的网络之于基于修辞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祛魅更是摧毁性的。
(换言之:意识形态宣传家们仍是可以在英语水平低下、网络技术封闭的地区有所作为的。这是众神的黄昏中的最后余晖了。)
让我们回到主题。只有民主装置尚未普及的世界才需要美国,只有当普世民主仍只是理念和口号,人们尚无法具体地想象那样一个世界时,这个将“自由”、“平等”、“民主”等词汇视作公民宗教(而不仅是政治装置)的国家才能不迷失方向。是美国人自身尚未做好迎接意识形态热寂与世界历史终结的准备。罗马和美国的类比已经太多,倘若普世民主真的统一人类了,美国人(这次不是外邦人,因为已经没有外邦人了)自己来到自由女神像下自言自语:你往何处去呢?对于意识形态地思维政治的人而言,自由女神像首先是自由与非自由的意识形态边界,然后才是美国人和异邦人的政治边界;而意识形态边界的消失,必然使得政治边界归于规则边界,而丧失“意义”,丧失诗性和神性。
致力于普世民主和历史终结的人,其实根本不在乎普世化以何种旗号进行。无论意识形态家们怎样试图把政治装置染上他们的私人价值观,待到全球民主实现之后,只需一代人时间就只可能剩下一种政治哲学,即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历史的自然速度是“代”。1790年代的英国是潘恩还是伯克占上风根本不重要,因为到了1825年后反正一定是边沁时代。意识形态只可能在动荡的、被称为“发生史(Geschichte)”的时代用丧失边界的巨词宣布宏大许诺、终极答案,这段历史过去了就会沉寂。只有在乱世的烟尘中意识形态修辞家的“思想”才会有短暂的力量。换言之:历史终结论者、全球民主论者的站队也只有一个标准:无条件支持世界语(英语)教育、全球互联网、日常语言政治、法律实证主义,反对“文化”殊别论和多元“他者”。只要维持住前者对后者的优势,剩下的交给时间去做就可以了。
这也反过来说明:将其生活世界的“意义”置于政治之外,将政治规则完全视作装置并放弃从意识形态中推导出政治规则的努力,对于能够不怀怨恨、不怀嫉妒地真诚地做一个自由主义者是多么必要。但可惜的是,往往越是在政治哲学、政治思想上倾注了大量心力者,越会有从中提炼出某些深刻意义、高妙道术的心理渴望。普通人都知道:暴力和规则都只是保障利益的工具,只有当知识分子走火入魔、变为意识形态家后才会从中寻觅“意义”。然而自由主义的最强力量恰恰在于它的“无招”(我想再次强调它与维特根斯坦的相通),放弃这一无招去追求意识形态,只会陷自己的努力(一方面要普世民主,一方面恐惧普世民主之后意识形态稀释)于自相矛盾、相减相抵的境地,最终收获的也只能是内心的矛盾、犹豫与畏怯——
——冷战胜利时刻的福山版“历史终结论”无疑标记出了该意识形态的最高潮,此后它越来越弱。当全世界只剩下最后一两个大国尚未民主化时,美国/民主意识形态竟然弱到了最低点。在民主制刚刚腾飞的时代,它裹挟着18世纪美国国父们的一大堆各种各样的思想,混合成一种大型“民主意识形态”或“美国意识形态”。(这两个词大致相当:想想从托克维尔到二战之前“美国式”、“美国化的”这两个形容词对欧洲人而言意味着什么)。这种意识形态“话语”为民主的推广提供了强大的助力。然而所谓“理性的狡计”却一次次利用了它:意识形态想自我推广,可实际上能够被推广的却只是民主的装置和规则;意识形态渴望肯定美国文化,然而击倒一个又一个独裁者却只是在否定对手。哪怕在美国的政治殖民最成功的典范,如日本,其文化也并没有美国化,今天的英国人、欧洲人谈及美国人时仍如百年前那样傲慢不屑。战争的胜利、政治制度的复制移植不能带来意识形态和文化胜利。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开放社会,文化扩张只遵循审美原则。新保守主义文化在互联网会被迅速消解稀释,在小圈子之外没有扩张的可能性(想想conservapedia和wikipedia的差距,就会明白“日常语言”在互联网这个完全开放社会中的压倒性优势)。执着于“文化”者在每一次政治胜利之后迎来的都是意识形态失败。
任何力量的历史位置都不会由其自身意志所定,这就是黑格尔所谓“理性的狡计”。旧枷锁的打破意味着新力量的整合。以美国的经济军事力量,推行全球民主、打破专制不是难事,但等到中国完全民主之后50年,日本、台湾、韩国、菲律宾还会倒向美国那一边吗?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敌人的消失并不意味着胜利。只有那些甘愿舍弃自己的祖国归属感,并渴望遨游于更广阔世界的美国人,能够欣然离去并接受美国时代的谢幕。
在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的24年后冷战时代之后,历史终结论已经冷却,“多元”主义乃至“文化”宽容甚嚣尘上。美国人已经开始洞见“理性的狡计”,他有何理由傻乎乎地跳进去呢?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口号是“Don’t do stupid stuff.”至此可以发现美国的强调多元“文化”宽容的左派,和强调美国价值的右派,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共谋(他们自己并未意识到,但这不重要):正是“多元”世界、“文化”宽容抑制了“美国价值”的过度自信与美国的过度扩张倾向,保护了美国价值不会溶解于全球民主之中。美国右派与左派表面上看似水火不容,但当右派批判左派的“文化多元”这个丧失界限的意识形态大词时,却做不到如启蒙主义或功利主义者那样决绝彻底不留余地,因为“文化”这个兴起于19世纪德国的、丧失界限的、涵盖一切却又什么都没说的词汇,同样是右派赖以编造神话的(伪)根基。
对19世纪德国人和今天的中国人而言,“文化”是政治不如人意时聊以自慰的避难所;对信息全球化时代的西方人而言,“多元文化”是退缩进小圈子的意识形态家的避难所,无论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在现实的民主规则可能普世实现的前夜,对美国意识形态的依恋已成为恐惧民主装置的理由:当我们将“民主”视作人类这个个体暴力力量差不多大(霍布斯说明了这一点,枪支保障了这一点)的物种的“政治”的先验语法,我们渴望的是胜利之后的平静而生气勃勃的、清晰的日常语言写成的法律规则下的生活;而任何以法律维持“文化”的企图,都必须牺牲权界的清晰性,以至于无法适用于人口众多的陌生人社会,因为任何清晰的规则(即便伊斯兰教法也不例外,如果它清晰起来的话)都是实证法学规则。然而,美国意识形态渴望的却是全世界承认它的神圣律法、与邪恶帝国对峙的旗帜和胜利时刻的炫目光荣;他们不明白,写就现代世界的已不是宗教律法或英雄史诗,而是日常生活颂歌。
我们身处的时代史无前例:1991年底苏联崩溃,1993年克林顿启动信息高速公路,同年欧盟诞生。这一连串的事件标志着十九世纪思想家们所谈论的“生活世界的普遍关联”已经从国家规模跃迁到了全球规模,即人类的最高规模。这一时代“之后”将没有更远的地缘目标可供意识形态家去征服,意识形态的浪潮不会涌向更远的边界,只会调转浪头形成回潮。无论后现代的“多元他者”还是保守派“小国寡民”都视全球化为眼中钉,但任何脱离全球化的国家都等于自愿被制裁。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墙之者亡。若说19世纪法律改革将诸习惯法整合到了国家的统一规则中,消去了诸地域、诸阶层的诸规则间的参差矛盾,在法律语言上改写成了实证法;那么当今政治格局必然挑战将国内法/国际法二分的“威斯特法利亚二重奏”,要求铸造全球规模的可通约(不是“普遍”)政治规则。(尽管从理论上说,经济全球化的边界应当就是政治规则可通约化的边界。然而有些政治规则无法通约到日常语言中去的国家仍加入了全球化:这种不稳定的黑市交易以牺牲安全为代价,后果如何且看今后。)
正如任何现代国家的民主化都经过了两个过程:首先封建诸侯地方割据被削弱,然后最高统治者本身要么受制于越来越民主、具体、细碎的规则,最终被架空;要么不甘于这种命运,最终触发革命。无论是力量上的还是规则上的大整合都没有在“国家”这一级别停止下来:两次世界大战让“诸神之争”偃旗息鼓,冷战结束标志着神/魔二元对立结束,而全球民主之后将是一神教向无神论的转变:一个所有国家都是民主国家的世界,也将是一个美国走下神坛的世界。倘若美国真的统一了世界性的民主秩序,也必然会日渐被规则所束缚而丧失优势。无论是否故意,“文化多元”和“文化他者”实质上形成了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拖延和缓冲。“历史的终结”必然意味着意识形态(政治诗学)的热寂与巴别塔的诞生,意识形态为求生存也必然会为阻止这一进程而拼命“变乱口音”,发明出更多元的“他者”。反过来说:我们时代的政治哲学能否完成其“语言学转向”,来克制这种变乱口音的逆流,事关的绝不仅仅是象牙塔内的事情。
4. 结语
任何普世主义意识形态,当它逼近其普世政治目标,就反而会犹豫。意识形态对现实性的恐惧必然会将“普世”蜕变为“多元共识”,它能提供的助力也会骤然减少,甚至变成阻力。意识形态越是在切近原始部落的历史阶段就越提供助力,越是逼近全球化,世界越是呈现为复杂精密的规则,它的弊端就越明显。当今时代要求更强健有力的精神:普世民主的最后一步,只可能由无涉意识形态的“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去跨越。从烧掉赎罪券、拆毁偶像开始,现代人就走上了漫长的意识形态批判之路。普世民主政治装置要求更超越,同时恰恰也是更日常的精神(那些“看山不是山”的意识形态癖患者无法理解,为何最超越的精神恰恰是最日常的):将一切政治力量视作工具和装置,绝不对它抱有执念。若将普世民主和意识形态捆绑,为保全后者得出的策略反而可能是牺牲前者,在确保民主力量稳占上风之后养敌自重止步不前。承担世界历史命运的国民必须有世界公民的心胸和气度,必须健壮到足以扬弃自己的祖国;唯有如此,历史的大潮才能够不激起同样强大的回潮,逐渐退入日常生活的细碎涟漪。真正的强大不属于凯旋而归的罗马人,他们执着于图腾和“意义”所唤起的“荣耀”,当扩张的热望刚走到尽头,衰败的历史就已开始。美国人如果要避免相同的命运,就必须强大到能够在凯旋时刻以冷淡的眼神看着自己(犹如哈姆雷特看着Yorick的头骨),在自省和自嘲中坦然平静、不怀悲观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All glory is fleeting.
《政治自由主义》读后感(三):读《政治自由主义》
罗尔斯七八十年代的论文集。感觉翻译得很别扭,这种建构性的书还是应该看原版的。
4 政治自由主义假定,处于政治的目的,合乎理性的然而却是互不相容的完备性学说之多元性,乃是立宪民主政体之自由制度框架内人类理性实践的正常结果。政治自由主义还假设,一种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并不拒斥民主政体的根本。
这种合乎理性却又互不相容之完备性学说的多元性事实--即理性多元论事实--表明,在《正义论》中我使用的公平正义之秩序良好社会的理念是不现实的。这是因为,它与在最佳可预见条件下实现自身的原则不一致。
9 现代和古代的区别的讨论,对我而言很重要。
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政治观念的观点与许多完备性学说的观点之间的二元论,不是那种起源于哲学的二元论。相反,它起源于具有理性多元论特征的民主政治文化的特殊本性。我相信,这种特殊本性说明了(至少在很大范围内)政治哲学在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相比较)的不同问题。为说明这一点,我陈述了一种推测--我只敢这么说--一种有关历史情景的推测,这些历史情景分别说明了古代和现代的特殊问题。
当道德哲学开始时,比如说发轫于苏格拉底时,古代宗教曾经是一种平民的公共社会实践宗教,是平民用以庆祝节日和公共庆典的仪式。而且,这些平民宗教文化并不是建立在像《圣经》、《古兰经》和印度教的《吠陀经》那样的圣典基础之上的。古希腊人颂扬荷马,《荷马史诗》是他们教育的一个基本部分,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却从来就不是圣典经文。一个人只要按预期的方式参与其中,认识到各种得体的礼节,那么,他所相信的具体细节就无所轻重。实际上,他只是在做或做过他想做的事而已,而作为一个值得信赖的社会成员,他随时都准备听从召唤,履行他作为一个好公民的平民义务,如,参加陪审团出庭作证,或出海征战。这不是基督教意义上的救赎宗教,而且也没有任何惠施神恩的僧侣阶层;确实,在古典文化中,不朽和永生救赎的理念并不占中心地位。
所以,古希腊的道德哲学原本肇始于城邦之平民宗教的历史情景和文化情景内部。在这一情景中,荷马史诗及其中所诵的诸神和英雄占有中心地位。这种宗教不包括任何与通过荷马史诗的诸神和英雄所表达的最高善理论相左的其他最高善理念。那些英雄都出身贵族望门,他们公开追逐功名,争权夺利,猎取社会地位和声誉。他们并非对家庭、朋友和仆从的善莫不关心,而只是这些要求占较次要地位而已。至于神,从道德上讲,他们与英雄并无殊异,只是由于不朽,他们的生活要相对幸福和安稳些罢了。
所以,古希腊哲学在摒弃以过去武士阶层之生活方式为代表的荷马史诗式理想的过程中,不得不为自身创造出人生至善的理念,即,能为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公民们所接受的理念。道德哲学从来就只是自由娴熟的理性功夫。它不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更不是建立在启示基础之上。因为平民宗教既不是它的指南,也不是它的敌手。道德哲学所关注的焦点,是作为一种引人向善的、合理追求我们真实幸福的至善理念,而她所谈论的问题,乃是平民宗教基本上悬而未答的问题。(这段对于希腊0古代宗教的概述可以作为理解先秦时代的思想的重要参照)
。。。到现代的三次发展,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导致的宗教多元论乃至各种多元论,并在十八世纪末形成一种恒常的文化特征。第二次发展是现代国家及其中央行政管理的发展。第三次是发轫于十七世纪的现代科学发展。。。。
对于中世纪宗教的五点概括。不可以忽略宗教战争的因素,宗教分裂的结果使得旧的秩序崩溃。
。。。因此,政治自由主义(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的历史起源,乃是宗教改革及其后果,其间伴随着十六、十七世纪围绕着宗教宽容所展开的漫长争论。类似于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现代理解正始于那个时期。正如黑格尔所看到的那样,多元论使宗教自由成为可能,而这当然不是路德和加尔文的本意所在。诚然,诸多其他争论也具有关键意义,诸如,那些围绕着通过适当的立宪原则来保护基本权利和自由,以限制绝对君主的权力所展开的争论就十分重要。(罗尔斯意识到了正义论过于集中在近代伦理思想跌得梳理方面的缺失,从而力图从思想史角度来解决)
13 的确,自由宪政的成功是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可能性的发现而出现的:这是一种理性和谐而又稳定多元的社会可能性。在具有自由制度的各社会中成功而和平地实现宽容之前,人们无从了解这种可能性。。。。通过持续的维护正义社会和自由制度的努力,使得排除异端的信念的不断削弱。
。。。政治自由主义的问题是:一个由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他们因各种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到的学说而产生了深刻的分化--所组成的稳定而公正的社会之长治久安如何可能?这是一个政治的争议问题,而不是一个关于至善的问题。对现代人来说,这种善被认为是包含在他们的宗教之中,而由于他们的深刻分化,他们认为公正可行的社会之根本条件却不在其中。这样一来,如何理解这些条件便成了这一阶段的中心问题。这一问题部分在于:在自由、平等、然而却又因深刻的学说冲突而发生分化的公民之间,进行社会合作的公平项目是什么?如果确有可能建立一种必不可少的政治观念,那么,该政治观念的结构和内容又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古代产生的时候,并不是个正义问题。古代世界原本就没有过各种救赎主义的、信条化的和扩张主义的宗教之间的冲突。这是一种新的历史经验现象,一种通过宗教改革才得以实现的可能性。(是否可以通过类似宗教改革的形式将这个国家引向宽容?)当然,基督教已经使民族征服成为可能,这种征服不仅是为了异族的领土和财富,为了统治和支配他们,而且也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灵魂。宗教改革使这一可能性转向了它自身。
15 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问题都首先产生于神学之中。在我们通常所研究的著作家中,休谟和康德均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认肯这三个问题中的第二个选择。他们相信,道德秩序以某种方式源于人性(或作为理性;或作为情感)本身,源于社会的生活条件。他们还认为,我们该怎样做的知识或意识对每个具有正常理性和良知的人来说,都可以直接获得。最后,他们以为,我们是如此构成的,以致我们生来就有充足的动机引导我们按我们应当做的去做而无须外在的胁迫和利诱。的确,休谟和康德同那种认为只有少数人能够获得道德知识、而所有的或大多数的人须得凭借这些制裁才能做正当之事的观点相距甚远。(注意他们的观点的力量 ,与精英主义的对立)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信念属于我归之为的完备性自由主义,它与政治自由主义相对立。(尽管有些令人吃惊,但罗尔斯指出了另一路径)
25 对于那些认肯某一基于宗教权威(譬如说,教会或《圣经》)的宗教学说的人来说,如何可能让他们也坚持一种支持正义民主政体的合乎理性的政治观念?。。。我坚持认为,这些学说仅仅把民主政体当作一种临时协定来加以接受是不够的。相反,它们必须把这一民主政体作为社会各成员达成一种合乎理性的重叠共识之政体来接受才行。(注意这与柏拉图所主张的政体的不同,罗尔斯基于的是现代多元化背景下的整体)
。。。。。。政治自由主义的问题,是为一种立宪民主政体制定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在这种立宪民主政体中,人们可以自由地认可各种合乎理性的学说之多样性存在,包括宗教的和非宗教的;自由主义的和非自由主义的;因而他们可以自由地生活在这一政体中,并逐步理解该政体的美德。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政治自由主义并不想取代各种完备性的学说,包括宗教的和非宗教的完备性学说,但它有意与宗教和非宗教的完备性学说都保持区别,而且希望这两种完备性学说都能接受它。
。。。古代人的中心问题是善的学说,而现代人的中心问题是正义观念。。。。(罗尔斯实际上讲的是救赎之后达成共识的问题)
34 它所做的,最多也只是提出一种独立的自由主义政治观念,该政治观念并不反对各完备性学说自身的基本理由,也不排除形成一种具有正当理性的重叠共识之可能性。
36 社会统一的基础。
49 对一般哲学问题的争论,不可能成为政治学的日常材料,但这并不会使这些问题成为无意义的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些问题之答案的思考,将塑造我们对政治文化的基本态度和我们的政治行为。假如我们姑且把不可能有正义而良序的民主社会当作共同的知识假定下来的话,那么,我们态度的品德和基调就将影响到这一知识。魏玛立宪政体失败的原因之一,乃是德国的传统精英都不支持其宪法,或是不愿意合作使其生效。他们不再相信有可能建立一种像样的自由议会政体。时机错过了。。。
50 本世纪的多场战争以其极短的残暴和不断增长的破坏性--在希特勒的种族灭绝的狂热罪行中达到顶峰--以一种尖锐的方式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政治关系是否必须只受权力和强制的支配?(注意这个关键问题,以及提问的方式)
4 关于自由与平等的双重要求的对峙理念--即那种与洛克相联系的传统和那种与卢梭相联系的传统之间的冲突--来加以思考,与洛克相联系的传统更强调贡斯当所讲的“现代人的自由”,如思想自由和良心自由、某些基本的个人权利和财产权利、以及法律规则;而与卢梭相联系的传统则更强调贡斯当所讲的“古代人的自由”,如平等的政治自由和公共生活的价值。
10 这也就是说,该政治观念将是政治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实际上,这也进行了最基础的建构,即为了一个社会的现实,必须倡导一种务实的、政治的主流观念)
12 我不讨论如何才能制定出一部民族法(在《万民法》一书中得到展开)
罗尔斯应该是典型的提出问题的那种人物。他总是试图通过提出问题来解决困境,而解题的过程则相对简明。
38 只有靠压迫性地使用国家的权利,人们对某一种完备性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的持续共享性理解才得以维持下去。(这一点可以找出很多例证,而且往往在追寻完备性的整全感过程中,共同体需要强大的压迫手段来维持统一性)
与罗尔斯的分析过程相比,国内绝大多数的文章都极不严谨,甚至可以说是危险的。大概这也是没有基础的体现。
56 没有一个确定的公共世界,理性的理念就会成为空中楼阁,而我们就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诉求于合理性理念,尽管理性总是约束着人对人像狼一样相互刺杀(拉丁语“foro interno”)的现象(用霍布斯的话说)。
66 针对怀疑论证的防御。
82 (罗尔斯对于政治价值和伦理价值区分的重要性)在此我要强调指出,充分自律是由公民获得的:它是一种政治价值,而不是一种伦理价值。
可以看出耶和华-柯亨对于罗尔斯的重要启发。
Joshua Cohen is Goldberg Professor of Humanities at MIT and his original essay on Rawls appeared in
Classics of Political and Moral Theory, ed. Stephen Cahn. The following may be considered a brief,
introductory synopsis of the penetrating essay.
A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t Harvard for many years, John Rawls died in November of 2002. He is
recognized as having revived the classical liberal tradition of Western, democratic ideals. Traditional
liberal theories of economics and justice, as represented by John Locke and Adam Smith had come
into disfavor of egalitarians who saw “legal rights and liberties” giving preference to the rich as over
against the poor and ordinary workers. Classical liberals condemned the paternalism and sacrifice of
rights made in hopes of a utopian future or happy welfare state.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1971) sought to bridge the chasm between Friedrich von Hayek’s classical
liberalism and Karl Marx’ s socialistic egalitarianism. Cohen explains:
(Rawls) proposed a conception of justice—he called it “justice as fairness”—that was committed in
equal measure to the individual rights we associate with classical liberalism, and to egalitarian ideal of
fair distribution conventionally associated with socialist and radical democratic traditions. Justice as
fairness, he said, aims to effect a “reconciliation of liberty and equality.”
Although his views did not win widespread support in American politics, his work prompted a
remarkable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lsewhere (A Theory of
Justice)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more than 20 languages), and has provided the foundation for all
ubsequent discussion about fundamental questions of social justice.
Cohen proceeds to explain the two principles that underlie Rawls theory of justice.
The first principle—of equal basic liberties—says that each citizen has a right to the most extensive
ystem of equal basic personal and political liberties compatible with a similar system of liberties for
others…. A person’s chances to hold office and exercise political influence should be independent of
ocioeconomic position. Citizens with motivation and ability to play an active political role should not
e disadvantaged by a lack of personal wealth.
Rawl’s second principle of justice restricts the extent of social and economic inequalities. It requires,
first, that jobs and positions of responsibility—which often carry unequal rewards—must be open to
everyone under conditions of fa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The demand of fair equality is that people
who are equally talented and motivated must have equal chances to attain desirable positions,
regardless of their social background. Access to well-compensated, rewarding work should not depend
on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people happen to have been raised.
Those disadvantaged by race and poverty immediately see the difficulty in working this out. So many
things—from birth to daycare, to private school, to Ivy League, to contacts in the Big Boy Network—
redetermine who will get the large slices of the pie in the end. Rawls was not only committed to
address such disparity, but the inequality of natural talents themselves. In short, we might say that
those with great athletic, musical, surgical or managerial skill should not be entitled to salaries
extraordinarily greater than most workers.
To address this concern (Cohen continues), Rawls proposes what he calls the “difference principle,”
which requires that we maximize the economic expectations of the least advantaged members of
ociety. This striking principle requires that we limit the extent to which some people are richer than
others just because they happen, though no doing of their own, to have been born with a scarce
talent—say, the hand-eye coordination of a great hitter or an unusual mathematical gift.
Justice as fairness does not require flat equality: a surgeon might legitimately be paid more than a
teacher because the higher income compensates for expensive training and education; income
equalities might also be used as incentives to encourage lawyers or venture capitalists to take on
tasks they would otherwise decline. But justice commands that such inequalities work to the greatest
enefit of those who are least well-off.
Attacks from libertarians and communitarians led to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1993) dealing more
deeply and specifically with problems of religious, moral and philosophical pluralism. His Law of
eoples (1999) dealt with issues of global justice. In both these books people are brought together
from different traditions, with different values and ideas of justice through his concept and process of
initial contract. This is an important idea for Rawls. He asks all to imagine themselves behind a veil of
ignorance… before experiencing life at all. There we are to consider what principles of justice would
e fair to us no matter how we are born and raised. There are no class or ethnic lines behind this veil
of ignorance. Without knowing what may lie ahead, we imagine principles of justice that would be fair
in all cases.
Underlying Rawls theory seem to be presuppositions about human autonomy, the need for human
community, the repository of human decency, and the notion of a common good.
This is an inadequate summary of Cohen’s fine article; and a less adequate introduction to work of
John Rawls. If you are serious about justice in your society, you might want to read these books. This
article is philosophical; remember that John Rawls was a philosopher. Cohen concludes his article with
this paragraph:
Inevitably, philosophy will be criticized by the Aristophaneses of this world—not to mention the
Machievellis—for keeping its head in the clouds, or buried in the sand. John Rawls was aware of this
concern, and, in one of his final essays, acknowledged that his work might seem “abstract and
unwordly” to some readers. But, he concluded, “I do not apologize for that.”
很有兴趣的是罗尔斯的建构社会体系的政治路径,与先秦思想中的相通之处,即放弃形而上的建构办法。
104 康德的道德建构主义与公平正义的政治建构主义之间的差别。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依托康德进行建构的基础上,对于自己的理论进行了进一步发展。实际上,他所谓的完备性理论是基于一定限定条件的,即相对于任何一个普通人而言所能通过教育习得的,而非绝对的完备的意思。
106 根本的问题是,公平正义把某些政治的根本理念作为组织性的理念来使用。超验理想主义和其他诸如此类的形上学说在政治的根本理念的组织和解释中不起任何作用。。。。(可以参考其对康德的意图的概括)康德的目的难以简单描述。但我相信他把哲学的作用看成了正式的辩护(apologia):即对理性信仰的辩护。这不是较为古老的表明信仰与理性的相容性问题,而是通过理性本身来表明理性--理论的和实践的--之一贯性和统一性问题,是我们将怎样把理性视之为最终的诉讼法庭、看作惟一有能力解决所有关于理性自身权威的范围和限度的问题。康德试图在前两个《批判》中,通过道德法则为我们的自然知识和我们对自由的知识辩护;他也想找到一种构想自然法则和道德自由的方式,以便使这两种方式能够相容。他把哲学看作是一种辩护的观点,否认了任何削弱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一贯性和统一基础的学说;所以,他反对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因为这些主义会导致自然法则与到的自由互不相容的结果。康德变换了证据的负担:理性的确认根置于哲学反思必须由之开始的日常(健全的)人类理性的思想和实践。只有当这种思想和实践与理性自身产生矛盾时,理性才需要辩护。(辩护饶有趣味,让人想起了苏格拉底的申辩,辩护应该说是面对矛盾时不得不为的一种努力)
127 就政治的目的而言,对于解释的有限需求。
在第二编中,处理的如重叠共识之类的问题,都属于技术上的问答式操作,基本上都比较轻松。
176 必须有根本立法来保证良心的自由和普遍的思想自由,而不仅仅是政治言论和政治思想的自由。同样,也必须有立法来确保结社的自由和移居自由;除此之外,还要求有各种维度来确保全体公民的基本需求能够得到满足,以便他们能够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
195 罗尔斯对于四个变量的处理方法。(1)道德上和智力上能力与技艺的变量;(2)体力能力和技艺的变量,包括疾病的影响和天赋才能方面和偶然因素;(3)公民善观念上的变量(理性多元论的事实);以及(4)兴趣与偏好的变量--尽管后者较为浅显。
218 比较重要的几条脚注。
但是,就我的理解而言,政治自由主义的确与市民人道主义有着根本的对立。因为,作为一种亚里士多德主义,后者有时被陈述为这样一种观点。。。
注:有时候,人们把马基雅弗里《君主论》中的观点看作是古典共和主义的解释。见昆汀-斯金纳著:《马基雅弗里》,特别是第三章。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可能是一个更切合于我们立场的例子。
注:对市民人道主义的这种解释取自查尔斯-泰勒的《哲学论集》(剑桥:剑桥大学出版,1985),第2卷,第334页之后。泰勒讨论了康德,并把这种观点归诸于卢梭,但请注意,康德并不会接受这一观点。以此理解,正如汉娜-阿伦特那样从悲观主义的意义上来表达的话,一种市民人道主义还是很有力量的。(她认为,这种市民人道主义是古希腊人表达出来。)阿伦特主张,在政治中获得最佳实现的自由与世界性乃是仅有的将人生从无终止的自然循环中拯救出来并使之具有生活意义的价值。见她的《人生状况》一书(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8)。我所依据的是乔治-凯特伯对阿伦特有关政治之首要性观点的理解性研究,见凯伯特等:《汉娜-阿伦特:政治学、良心、罪恶》(托望达:罗曼与阿兰赫尔德,1984),第一章。
(政治自由主义可以很好的抵御在完备性理论的遮蔽下的精英倾向)
250 在讨论作为公共理性的最高法院判决时,罗尔斯着重强调了不应基于一般道德判断,二是应该诉求于政治价值,从而避免了福柯笔下的理性的暴政。
罗尔斯这本书里面涉及的著作和事例要远远超过《正义论》,这也为利用其理论来论证具体问题提供了方便。
265 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诉求于正当宪法所表达出来的那些政治价值,而废奴主义者却不是这样。注:因此,金能够且常常是诉求于《教育部棕色手册》,诉求于最高法庭一九五四年的决议,该决议指出,种族隔离不符合宪法。在金看来,“正义的法律是人制定的、与道德法则或上帝法律一致的法典。而不正义的法律则是与道德法则不和谐的法律。用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话说,不正义的法律乃是没有永恒法和自然法根基的人类法律。任何能提高人格的法律都是正义的。而任何让人格堕落的法律都是不正义的。一切种族隔离的法令之所以都不正义,是因为种族隔离曲解了人的灵魂,损害了人的人格。”在接下来的的一段里,还有更具体的定义:“不正义的法律是多数人迫害少数人、且他们自身无所约束的法典。这是差别创造法律。。。。。。而正义的法律则是多数人迫使少数人遵循他们愿意遵循法律本身的法典。这是同一创造法律。”再接下来的一段还谈到:“不正义的法律是迫害少数人的法典,而少数人在制定或创造这一法律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因为他们并没有不受钳制的投票选举权。”很显然,宗教学说是金观点的基础,而这些宗教学说在他的诉求中都是很重要的。然而,这些观点是以一般性的语词表达出来的,而且它们都充分证实了宪法的价值,符合公共理性。
362 去除煽动诽谤罪的重要意义。(而这个重要判决的重要性离很多人的理解还很远)
431 让我们说,美国宪法史上三个最具有革新精神的时期是一七八七至一七九一年的宪法缔造时期、宪法重建时期和罗斯福新政时期。
566 【为译者所做的导读文章】在新自由主义内部,罗尔斯的《正义论》刚刚发表,立刻遭到了其哈佛哲学同事诺齐克的严厉批评。诺齐克认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严重背离了现代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即“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它的要害在于,罗尔斯对所谓“差异原则”和社会公平秩序的腔调,不可避免地要求牺牲个人的天赋权利,而这种牺牲是现代自由主义精神所不能容忍的代价。
在外部,当代共同体主义者们更是群起攻之,其势方兴未艾。。。。在《正义论》发表十年后,麦金太尔发表了《追寻美德》,该书被视为当代美国伦理学的又一部扛鼎之作。在是书中,麦氏对染未能像哈贝马斯所期待的那样把论战的矛头公开指向罗尔斯,但是他仍然含蓄地指出了罗尔斯的个人主义权利政治学和尼采式的“强力意志政治学”的同质性,并认为,处于“无公度性”道德冲突之中的现代社会和现代人不得不在这种尼采式的权利伦理或法则伦理与亚里士多德式的共同善伦理或美德伦理之间作出抉择,而真正合理的选择只能是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麦氏的批评立场是传统文化的、新历史主义的。与他共享这一理论立场的还有当代著名的黑格尔主义者查尔斯-泰勒。
571 他要将其正义论伦理学改铸成一种政治哲学,用他的话说,就是从康德式的“道德建构主义”走向“政治建构主义”。
《政治自由主义》读后感(四):罗尔斯 《政治自由主义(1993)》摘要索引
【按语扔了吧: 本摘要仅供索引备查之用。简单地说,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由于接受了合理多元论或合理分歧的观念,Rawls将《正义论》中的公平正义观从一种哲学性整全学说收缩铸改为一种(适合于宪政民主社会的)政治观念。这一改变主要借助重叠共识和公共理由等概念辨识出来,但根本性的观念却是“政治价值压倒(override)可能冲突的非政治价值【145-6】”这一政治优先的思想。适应这一改变,Rawls在合理的多元论与一般多元论(pluralism as such)所作的区分是一个重要问题;有一个遗憾是中心的迁移并没有让Rawls放弃对公平正义观念的严格辩护,虽然在“平装本导论”中对正义观念家族的问题有所论述。
从哲学上讲,Rawls的政治优先的观念是决断式的,缺乏理性说服力的。Habermas批评说Rawls仍然表达了形而上学观念;Raz的自律或许仍是Rawls实际上的立场;Larmore对黑格尔式的历史理性的强调或许是对Rawls政治优先观念的更好解释。我个人现在就倾向于认为后期Rawls的政治哲学是一种黑格尔化的康德伦理学,唯有这样才能糅合正义的普遍性和历史偶然性。另外,Rawls的论著一如既往地厚密严谨,真正的大家风范。】
“导论” 《正义论》没有区分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页3,下同】而且卷3中稳定性的解释与整体不不协。【3】TJ中的不现实:所有公民都把公平正义作为整全学说接受的。合理而不兼容的理性多元论是民主社会特征,表明TJ中的公平正义理念不现实,其稳定性解释必须重来。在PL中公平正义一开始就被描述为政治的正义观念,并带来诸多改变。稳定性问题在政治哲学而非道德哲学中受重视。
L所涉问题:“深刻分化的公民之稳定而公正的社会如何可能长期存在。”【5】政治自由主义接受reasonable pluralism,并无启蒙谋划的雄心,而仅仅制定政治的正义观念。【6】它区分证明的公共基础和非公共基础;谈及政治的正义观念的reasonable而非true;建立在实践理性原则之上,政治建构主义【8】
政治观念与整全学说的二元论源自民主政治文化的合理多元论。Rawls勾勒或猜测了一段自希腊至善(highest good)道德哲学以来的历史:“政治自由主义的历史起源,乃是宗教改革及其后果。…多元论使宗教自由成为可能。”【12】“自由宪政的成功是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可能性之发现而出现的:一种理性和谐而又稳定的多元社会的可能性。”【13】宗教改革中的冲突的新颖之处在于将不容妥协的超验因素引入善观念,出路只有力竭或让位于平等的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政治自由主义把不可调和的潜在冲突牢记在心。【14】)Hume和Kant都开出独立于教会之外的整全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则本身不关注道德哲学的普遍问题,其主旨是“在深刻的学说冲突毫无解决前景的条件下,公正而自由的社会如何可能?”【16】,力图对各整全学说公正无偏(impartiality)。【16】
解释为何TJ强调了宗教改革和宽容而不是种族和性别。TJ是个人主义、公私的区分等批评源于没理解到原初状态是代表装置。TJ可延展。文章遭受批评后又补充freestanding view、区分simple & reasonable pluralism、区分reasonable和rational.1992.10
“平装本导论”提供阅读指南。PL之目的:a、理解公平正义的良序社会如何适应合理多元论,又如何为政治的正义观念所调节(1、2、3、5)。b、理解包含诸多合理政治观念的自由社会的合理unity基础何在。(4、6)1.PL并没有足够明确地确认其谈论的哲学问题:认同权威式宗教学说的人会认可政治的正义观念么?导论谈过,古今是善的学说与正义的观念的对比。【26,正义在于其范围狭隘,限于公共领域】Modus vivendi还是overlapping consensus。2.TJ卷3的稳定性论证与合理多元论不符,因为在那里公平正义是整全学说。而政治的正义观念能从Modus vivendi发展为overlapping consensus.3.公平正义被重述为free-standing的政治的正义观念(也是道德观念)。理想:社会合作系统中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之间合理的合作条款,相互性(reciprocity)标准。【31】政治自律vs道德自律(不能满足需要reasonable的相互性标准)。个人vs公民(基本结构内部;自由而平等)。相互性标准产生自由主义的合法性原则。【33】4.合理的重叠共识。a源自合理的多元论,freestanding的正义观念 被视为交叠共识;b不证明共识围绕一个政治的正义观念形成。存在着诸多合乎理性的自由主义政治正义观念的家族之争.【35】自由社会的条件包含:权利、自由和机会的规定,自由的优先性、各种措施保障运用权利和机会的手段。而公平正义最满足这些条件【35】,但任何满足相互性标准和承认判断负担的观念都行。社会unity的基础:基本结构受自由主义正义观念的规导、整全学说认可正义观念、宪法危机可依正义观念来裁决。5.public reason.区分公共领域和背景文化。理念是公民在满足相互性标准的正义概念框架内讨论宪政和正义问题。相互性刻画政治关系的本性。广义的公共理由:只要由正义概念给出的公共理由也支持该论点,合理的学说也能被引入公共理由。公共理由不限于公平正义,而是由正义观念家族规定,并非不变。【40】有时不同政治观念之间的疏远是正常的,这时投票的结果被认为是合理的。【44】6. 适于目的的手段也需要满足相互性标准,防止过度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唯意志自由论仅仅捍卫形式自由,公平正义依据5条件来补足:选举公费和政策信息公开、机会均等、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公平、社会作为最后雇主、医疗保健。7.必须预设正义社会是可能的,而人类具有一种道德本性(moral nature)。【50,这立场完全是整全康德主义式的嘛,见《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它(自由)只是被视为理性在一个存在者里面的必要预设。…但是,在依照自然法则的规定终止的地方,一切说明也就终止了;剩下的只有捍卫。”(467)】
卷1 政治自由主义:基本原理
“讲1 基本理念”考虑最适当的正义观念(1)和宽容的基石(2)—>多元的正义社会如何可能?
一. 两个基本问题。公平正义在洛克和卢梭传统的分歧中做了评判。这一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念的三个条件or特点。公平正义借助社会的理念来组成(政治的)正义观念,是政治一致的基石,“政治自由主义将宽容原则运用到哲学本身。”【9】宗教学说让位于立宪原则,政治自由主义寻找无恃的正义观念,“是政治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10】二、政治的正义观念的理念。正义观念含三个特征a.适用于基本结构的道德观念;b.是无恃的观点、是module;c. 内容隐含在公共政治文化的基本理念中,(区别于作为背景文化的整全学说)。【14】这些基本ideas包括:作为长期的公平合作体系的社会理念(organizing idea)、作为自由平等个人的公民理念和良序社会理念。(此外还有辅助性的原初状态理念和基本结构理念) “这些理念可以被精心阐释为一种能够获得重叠共识支持的政治的正义观念。”【15】三、作为公平合作系统的社会理念。三个要素:公认规则引导的合作;公平合作条款和相互性;各参与方合理利益。相互性介于impartiality和互利之间,对应于strains of commitment. 这里解释公民即自由而平等的个人,“个人凭借其两种道德能力(正义感和善观念的能力【形成、修正和合理追求一种人的合理利益或善观念的能力】)和理性能力(判断能力、思想能力、推理能力)而成为自由的。…又使每一个个人成为平等的。”【19,对康德自主理念的一个经验诠释】四、原初状态的理念。原初状态仅仅是一种代表装置,“作为公共反思和自我澄清的手段来发挥作用的。”【26】是mediating idea。 五、政治的个人观念。拒绝个人的形而上学的假设。自由的三个方面:a.公民在具有善观念的能力上是自由的。(公共认同与道德认同)b.公民视自己为各种有效要求的自证之源(self-authenticating sources of valid claims)。c.公民能够对自己的各种目的负责。总结:公平正义从社会理念来解决实现自由与平等的正义观念的问题。六. 良序社会的理念。良序社会中:人人接受相同的正义原则【36太强,为何不是正义家族】、基本结构满足正义原则、公民具有正义感。高度理想;合理的多元论事实、压迫性事实、政体需要多数公民支持、(4直觉性理念的存在、5.合理分歧的事实)。因此正义观念限于政治领域。【39】七、良序社会非community或association。区别于联合体:社会是完全而封闭的;而共同体受整全学说支配。八、关于各种抽象观念的使用。深刻的冲突导致抽象的工作。
“讲2:公民的能力及其表现(powers of citizens and their representation)”
一、合理的与理性的(the reasonable & the rational)。溯源Kant的纯粹实践理性和经验实践理性的区分。The reasonable的第1方面:若他人亦同样,愿意提出和遵守作为公平合作条款的原则和标准(相互性);而the rational则适用于单一或联合的行为的主体之确认目标和手段,缺乏道德敏感性。the reasonable与the rational不能互推,而是互相补充,“分别与正义感的能力和善概念的能力相联系着。”【54】也不能证明不能从the rational推出the reasonable;the reasonable是公共的,而the rational则不是公共的。二、判断的负担(the burdens of judgment)。The reasonable的第2方面:承认判断负担。合理分歧(reasonable disagreement),而判断负担就是合理分歧的根源。三种判断:rational, reasonable, theoretical判断及其负担。这些负担包含:证据复杂、权重、概念困难、总体经验多样、不同的规范性考虑、社会空间的限制性。判断的负担导致合理分歧这第5个事实。三、合理的整全学说。合理的整全学说是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实践,并源出某种思想传统。个人并不认肯相同的整全学说,而用政治权力去压制合理的整全学说的做法是不合理的。“being reasonable并不是一个认识论的理念(尽管它具有认识的因素)。相反,它是一个包含着公共理由的民主公民的理想。”【65】两点评论:a.判断的负担不从怀疑论开始;b.一般多元论(pluralism as such)和合理多元论两种事实的重要区分。前者中包含种种不合理的整全学说,也赋予了遏制战争和疾病等防护正义的任务。【67,这一区分在Rawls体系中关系重大,近乎文明与野蛮的界分】四、公共性条件(publicity condition)及其三个层次。1.公共正义观念的接受;2.相关的一般信念的一致(得到共享的探究方法和推理形式的支持);3.公共正义观念的充分证明。三个层次都满足就是“充分的公共性条件”。【71】五、理性的自律:人为的而非政治的(rational autonomy: artificial not political)。理性的自律是在原初状态这一纯程序正义情形中由参与方的慎思塑造出来的。含两方面:正义原则是作为理性慎思之结果而被接受;利益(三高阶:善观念、正义感、决定性的善观念)引导公民代表的思考。Artificial指理性技巧。引入Primary goods来充实形式化的高阶利益。六、充分的自律(full autonomy):政治的而非伦理的。由原初状态的结构性方面塑造,公民在其公共生活中才成为充分自律的,“它是一种政治价值。”【82】原初状态的公平:诉诸平等理念【83】七、个人道德动机的基础。一些能力(正义感和善观念的能力、判断和推理的能力、整全学说的能力、正常合作的能力)构成平等。【86】公民的4特征:a相互性的条款接受;b合理分歧;c想成为正常的社会成员(self-respect的基石);d.合理的道德心理学。说明a和b涉及的道德感受性区分三种欲望:依赖对象的欲望、依赖原则的欲望(reasonable & rational)、依赖观念(conception)的欲望(最重要)。这样,“可能动机的类别就开阔了。”【90】合理的道德心理学的内容。八、道德心理学:哲学的而非心理学的。这种道德心理学“表达某种政治的个人观念和公民理想。”【92】非自然科学,而这里自然心理学是permissive(容许的)。立宪政体的政治哲学是自律的:正义观是规范性的思想,不需要在自然科学意义上解释。【93】
“讲3: 政治建构主义(political constructivism)”与康德的道德建构主义和道德实在论的直觉主义对照,“政治建构主义为政治自由主义提供了一种合适的客观性观念(conception of objectivity)。”【94】正义原则可以被描述为某种建构程序的结果,这一程序体现了实践理性的要求。【94】
一、建构主义观念的理念。理性直觉主义的4个特征:道德第一原理是对独立的道德秩序的真实陈述;由理论理性认知;缺少充分的个人观念;真理趋近观。政治建构主义的四个特征:正义原则是建构程序的结果;基于实践理性;复杂的个人和社会观念来使建构具有一种结构或形式;规定了the reasonable的理念,在其内没有真理的概念。【99,constructivism这个词选得有点怪的,或许恰好只最适用于政治学说,就道德哲学而言,对应的是道义论或自律学说】建构主义与理性直觉主义并不矛盾;两者都依赖反思平衡的理念。诉诸建构主义,公民找到大家都可接受的原则,而不必求诸于Kant或Mill的整全学说。二、康德的道德建构主义。与Kant比:Kant是整全的道德观点;两种自律:表现型和构成型。Kant是构成性自律(constitutive autonomy),“价值秩序…须通过实践理性的活动本身才得以构成。”【105】Kant是一种更深的、超验的理想主义;康德的个人和社会观念基于transcendental idealism;公平正义仅在揭示正义证成的公共基础,而Kant哲学则是对合理信念(理性之一贯性和统一性)的正式辩护。【106】三、公平正义作为一种建构论观点。建构出正义观念的内容;原初状态是laid out而非建构的,公民和良序社会的理念嵌入建构程序中。“并不是所有的一切都是被建构的;我们必须有某些由之开始的东西。”【110】叔本华对Kant的批评。四、社会观念和个人观念的作用。社会和个人观念“是实践理性的观念”【113】,刻画着运用理性的行为主体的特征。五、三种客观性观念。客观性的5+1要素:确立思想的公共框架;判断的目的是真的或合理的;规定一种理由的秩序;区分客观的和偶然的观点;解释一致的判断;能够解释分歧。 理性的直觉论的客观性取决于独立的道德秩序,它会批评建构论没有恰当的真理观念,但建构论不需要申认或否认这种真理观; 道德建构论的判断满足理性和合理性标准或绝对律令程序;总是从某处出发的观点。【122】六、独立于因果知识观之外的客观性(objectivity independent of the causal view of knowledge)。一种因果知识观批评前述3种客观性。Rawls认同Kant存在不同的客观性的观念,因此上述批评无效。七、从政治上讲,客观理由何时存在?政治理由是客观的,如果在良好条件下,人们最后认可政治确信或大大缩小了差异,即确信是reasonable。【126】八、政治建构论的范围。限定在具有政治领域特征的政治价值之内。政治建构论对更深刻的真理要求保持沉没,reasonableness是其正确性标准。【135】在政治中,reasonableness比truth更合适。【137】
卷2 政治自由主义:三个主要理念
“讲4: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的理念”引入与正义观念相辅相成的另一个基本理念重叠共识,并与modus vivendi区分。
一、政治自由主义如何可能?正义问题上最深刻的区分:多元论正义和一元论正义。政治关系的两特征:封闭性的,“生入其中,死出其外”【143】;强制性的公共权力。这就产生了权威的合法性问题。自由主义的合法性原则说:政治权力的运用必须符合共同人类理性接受的原则和理想所认可的宪法。【145】政治自由主义根本的两点:constitutional essentials和basic justice问题应尽可能只诉诸政治价值;政治价值压倒(override)可能冲突的非政治价值。【145-6,这是最重要的观念(freestanding view源于此),但也仅仅是reasonable的,其实缺乏根本性的论证,重叠共识似乎仅仅是次要的部分了】问题表达为“我们如何才能认肯我们的整全学说,然而却又坚持认为利用国家权力来获取所有人对这一学说的忠诚是不合理的呢?”【147】答案分两个部分:1、政治价值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基本框架和合作的条款,是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的惟一依据,不能轻易僭越。2、历史表明,多元的整全价值与特殊的政治价值领域相互一致或无冲突(重叠共识)。二、稳定性问题。两个问题:个人能否获得正义感(诉诸2.7道德心理学);正义能否成为重叠共识的核心(诉诸重叠共识理念)。公平正义以公共证明的方式获得稳定性。三、重叠共识的三个特征。不是屈从非理性(unreason),而是服从合理多元论的事实;正义是自恃的论点,是Module.1(异议).重叠共识不是modus vivendi。Rawls借助一个模型,其中三种整全观点构成共识:Locke式的宗教、Kant或Mill的整全自由道德、多元论的。重叠共识不是modus vivendi:正义是道德观念;是在道德基石上被认肯的;具有稳定性,认肯的人不会撤回支持。共识的深度和广度。四、重叠共识不是冷漠的或怀疑论的。2(异议).重叠共识不是真理怀疑论。“通过回避各种整全学说,我们力图绕过宗教和哲学之最深刻的争论,以便有某种发现稳定的重叠共识之基础的希望。”【161】“最终可能不得不申认至少是我们的整全宗教学说或哲学学说的某些方面。…但只限于认为哲学整全的观点对于达成政治共识的目的来说是需要的或有用的。”【162-3】尽可能的限制。把宽容运用于哲学中。五、政治观念不必是整全的。3(异议).如模型中第三种观点一样,政治观是多元论的更重要的一部分。宽容、让步、合理性(reasonableness)和公平感等是“巨大的公共善、构成了社会政治资本的一部分。”【167】并且与基本的整全价值并非不相容。六、达成宪法共识的步骤。4(异议).并非乌托邦式的。描述出重叠共识产生的两阶段:宪法共识到重叠共识。宪法共识只包括民主政府的政治程序。【169】开始只作为临时妥协接受;整全学说的弹性/非充分整全性具有特殊意义。[169]稳定的宪法共识的三个要求(权利和自由的优先、公共理由、政治美德)。七、达成重叠共识的步骤。基本政治权利和自由等;重叠共识的焦点是一种正义观念或一类自由主义观念。交叠共识的深度(系统阐释正义观念、社会观念和公民观念)、广度(纯政治和程序性的宪法共识太狭窄,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等、满足基本需求的措施)、具体范围(自由观念的差别)。从临时协议到宪法共识再到重叠共识,关键是整全学说的非充分。八、观念与学说:如何联系?一个例子中共识由4种观点组成:洛克式的信仰自由;康德的自律理想:演绎性的;边沁和西季威克的功利主义近似的关系;多元论:平衡式的。总结:共识并非妥协,而是基于理由体系,非野蛮力量或非理性影响。政治哲学发挥着康德曾赋予哲学的普遍作用。【183】
“讲5:正当的优先性与善的理念(the priority of right and ideas of the Good)”正当与善是相互补充的,“正义设定了限制,而善表明了意义所在。”【185】 在公平正义中,“正当的优先性意味着,政治的正义原则给各种可允许的生活方式强加了种种限制,任何追求僭越这些限制的行为都是没有价值的。”【184】一、政治观念是如何限制善观念的。PL为政治和社会生活提供正义观念,它所包含的善理念必须是政治性的理念。这一限制通过正当的优先性表达出来,“可允许的善观念必须尊重该政治正义观念的限制。”【187】二、作为理性的善(goodness as rationality)。五种善理念:理性的善;首要善;可允许的整全的善;政治美德;良序社会的善。理性的善:按照理性的生活计划安排追求和资源,以敏感的方式在一生中追求善观念。正义观念必须“把人类生活以及基本的人类需求和目的的实现当做善,并将rationality视为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188】作为理性的善不足以规定特殊的政治观点,却提供了部分框架以确认首要善目录。三、首要善与人际比较(primary goods and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s)。首要善是为了解决共享的或可比较的善的实践性政治问题:在公民的可允许的善中确认部分的相似性。首要善的目录:基本的权利和自由;迁徙自由和职业选择;结构制度中的权力、特权和责任;收入和财富;social basis of self-respect。“在引入首要善的想法背后,是想找到一种实际的进行人际比较的公共基础。”【193】设定公民具有充分参与合作所需要的道德能力、智力能力和体力能力,而首要善是根据这些能力的假设来评估的。四种变量:道德、智力的变量、体力和技艺的变量(疾病和偶然因素)、善观念的变量、兴趣和偏好的变量。【195】公民为其偏好负责。四、作为公民需要的首要善。首要善不能作为富宁的尺度,而是规定正义问题的需要,这些需要是政治观念范围内的建构。【200】首要善是责任的社会分工的内容。五、可允许的善观念与政治美德。中立性理念。程序中立性(公平正义非程序中立)和目的中立性。Raz的目的中立性三种定义:平等机会;不得袒护或促进任何整全学说;不得支持除非补偿。【205】公平正义这样满足neutrality:制度和政策不是设计用来偏袒任何特殊整全学说的;把后果或影响的中立性作为非现实的东西排除掉。【206】PL仍然可以鼓励某些政治美德:公民美德、宽容、理性和公平感。六、公平正义对善观念公平吗?国家将不有意袒护任何特殊整全观点。袒护或压制某些整全学说这样的社会影响是任何正义观都无法避免的。“任何社会都无法在其自身内囊括所有生活方式。”【209】“在伟大的善中间,有一些是完全无法共存的。…没有无缺陷的社会世界。”【210】 七、政治社会的善(the good of political society)。公平正义不是private society制度。公民共享具有高度优先性的正义目的。良序社会在两方面是善的:对个人来说是善(运用两种道德能力为善;确保享有正义、尊重和自尊);是社会善(如民主制度乃是一种伟大的社会善)。PL与古典共和主义具有亲和性,却对公民人道主义(civil humanism,如Arendt)对立,在后者中“参与民主政治被看成善生活中占据特权地位。”【219】八、公平正义是complete。公平正义使用的善理念是政治性的;正当的优先性。
“讲6:公共理由的理念”“公共理由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理由,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由。”【225】
一、公共理由的问题与论坛。公共理由是正义观的一部分,是公民的理由,只限于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问题。应用于public forum,法庭是典范。二、公共理由与民主公民的理想。拒绝诉诸真理,公民理念对公民们施加了一种对根本性问题相互解释的公民义务。排斥把投票视为私事,让人想起《社会契约论》。三、非公共理由。很多种,属于背影文化,也是社会性的。各联合体(法庭、科学社团、教会)的非公共理由。【234】四、公共理由的内容。通过正义观念系统陈述出来:基本的权利、自由和机会;及其优先性;适用所有目标的手段。正义观是政治性的:适用于基本结构、不依赖整全学说、按隐含于公共政治文化中的根本性政治理念论证的。政治观含两部分:正义原则和探究指南(推理原理和证据规则);因此政治的价值也含两种:正义的价值和公共理由的价值。【238】公民对最合适的政治观念有分歧。【241】五、宪法根本(constitutional essentials)的理念。两种宪法根本:政府结构和政治运行的原则;平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正义的两种原则中:规定权利和自由的正义原则属于宪法根本,调节分配正义问题的原则却不是宪法根本,而是基本正义的问题。【242】要区分基本自由等宪法根本的原则和控制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原则相区别。六、最高法庭作为公共理性的范例。“公共理由乃是其最高法庭的理由。”【244】立宪主义的5个原则:制宪权和日常权力的区分;高级法和普通法的区分;宪政是人民自我统治理想在高级法中的表现;权利法案的宪法确定宪法根本;最终权力由对人民负责的三个权力分支共同掌管。七、公共理由的明显困难。多种合理的答案;投票的真诚性;确定何时公共理由解决了一个问题。八、公共理由的限制。排斥性论点与包容性论点(基于整全学说的理由)。这些限制的适当变化,取决于各种历史和社会条件。【267】
卷3 制度框架(institutional framework)
“讲7:作为主题的基本结构”
一、正义的第一主题。基本结构(宪法、财产形式、经济组织、家庭等)是第一主题。本文分析其理由。二、通过适当的顺序达成统一。Rawls对比了公平正义与功利主义(缺乏社会形式内部的区分,276)。“基本的统一性由下述理念提供的:即自由而平等的个人将根据他们对这类组织化原则的需要…”【278】三、自由意志论(libertarianism)对基本结构没有派给任何特别角色。这里是批Nozick,“这种学说…认为国家仅仅和其他私人性联合体一样。”【280】政治忠诚是私人性的契约责任,“根本不是一种社会契约论。”【281】libertarianism没有基本结构的位置。四、背景正义(background justice)的重要性。基本结构的制度确保正义的背景条件。五、基本结构如何影响个体。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人之所是;限制着人们的抱负和希望;…正义论调节产生于偶然性的不平等。“康德式的契约学说集中关注于这些基本结构上的不平等,它坚信,这些不平等是最根本的。”【287】六、作为虚构的和非历史的原始契约。【288基本结构影响契约条件,乖乖的话】七、原初契约的独特特征。特殊契约与原初契约的区分。八、人的关系的社会本性。正义原则的内容反映了人的关系的社会本性:差异原则不区分成员之物和尚未成成员之物;正义原则规导着资格或权利;各派被看为自由而平等的道德人。九、基本结构的理想形式。“正义两原则为基本结构具体规定了一种理性形式。”【301,在PL中Rawls的部分目标仍然是为公平正义的具体形式辩护,这约束了Rawls在正义家族观念上的展开?】也需要调整。十、对黑格尔批评的回答。Rawls的正义观与康德的超验唯心论分离出来,并自觉可欲,但需要表明不会遭受Hegel唯心论对契约论传统的那种攻击。Hegel说契约论把国家与私人联合体混为一团,没有认识到人类的社会属性。但前面对基本结构和节3对Nozick的批评表明,Rawls免于黑格尔的批评。
“讲8 基本自由及其优先性” 回应Hart的批评(两gap:基本自由及其优先性的说明;基本自由相互调整的标准),勾勒自由及其优先性如何建立在自由而平等的公民观念之上。【308】
一、公平正义的初始目的。初始目的是要表明:公平正义比功利主义学说、完善论或直觉论更好的对民主社会中的自由和平等的理解。【310】基本自由的清单的两种方式:历史的;对两种道德人格能力实践的条件说明。 二、基本自由的独特地位。基本自由“具有一种绝对的分量。”【312】只能因其它最基本自由被限制,而不能因公共善或完善论价值而限制;区分限制和规导;对基本自由清单的限定;并非所有条件下,而是合理有利条件下要求优先性。三、个人与社会合作的观念。为了解释基本自由及其优先性(第一裂缝),Rawls引入个人和社会合作的观念。两种道德能力是正义社会平等成员的必要充分条件。四、原初状态。将个人和社会合作观念与正义原则联系起来。各派只是rational自律,而reasonable由外部强加。首要善(5种)是两种道德能力的条件。接下来考察几种不同的基本自由说明其优先性。 五、自由的优先性1:第二种道德能力。考察良心自由与善观念的能力。3个根据:a这里的多元的善观念是non-negotiable非协商性的;b善观念的能力是形成、修正和合理追求某一种决定性善观念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充分发展和实践(尤其是修正善观念的能力)被看做是达到个人善的手段;c深思熟虑的认肯也是决定性善观念的一部分。【332】这样善观念的能力成了决定性善观念的本质部分。六、自由的优先性2:第一种道德能力。正义感的能力,在此(原初状态中)只被视为个人之善的手段。3个根据:(这里的推理都还原到了善观念上)a.1(重大利益)正义的合作体系对每个人形成善观念的重大益处/a2(较大稳定性)两原则是最稳定的正义(“无条件地关注我们的善的正义理念,…以认肯我们的人格为根基”【336】);b.自尊受到鼓励和支持:自信(道德能力的发展,受到基本自由的支持)和对自身可靠的价值感(这需要支持的公共性和普遍的认肯)。“我们的自信和价值感都依赖于他人对我所表现出来的尊重和互惠性(For our sense of our own value, as well as our self-confidence, depends on the respect and mutuality shown us by others)。”【338】c.良序社会,洪堡“诸社会联合体的社会性联合…通过正义两原则而很好组织起来的民主社会,对每一个公民来说,可能比那种凭他们自己的策略来建立社会或使他们局限于较小联合体的个体之决定性善观念要完备得多。”【339】更完备,极大扩展和维持每个个人的决定性的善。才能互补使许多形式成为可能/超过个人生活所能成就的/正义感能将相互性作为内容。正义原则必须与公民观念相连,而且包含相互性观念。【341】七、基本自由不仅仅是形式的。一种批评意见:基本自由可能仅仅是纯形式的。Rawls区分了基本自由与自由的价值。“我们不把这些障碍(无知、贫困以及物质手段的缺乏)看作是限制人的基本自由的障碍,而是把它们看作是影响自由价值的东西,即影响个人利用其自由的东西。”【345,这只是一种讲法吧?自由的缺乏和较少的自由价值之间有区别么?】而差异原则能弥补那些拥有较少自由价值的人。Rawls主张保证各种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这是一个自然的焦点。【348】拒绝更广泛的保证:非理性、多余、造成分化。之所以保证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因为对建立公平的立法、政治过程平等开放极为根本。【350】八、一个完全适当的基本自由体系。Hart所言第二gap.自由体系不是最大化什么,而是对实践两种道德能力(两种基本情况)是根本性的社会条件的保证。在反对最大化时(不能有最大化的一贯的观念),Rawls将决定性善(determinate conception of the good)与两种道德能力并置起来:因为两种道德能力不是个人道德能力的全部【353】九、诸自由如何结成一个连贯体系(scheme)。一种自由之意义大小在于其在两种道德能力的实践中的角色。宪法不是建立在正义原则基础上,而是公共文化中的个人和社会合作观念之上。【359】rational从属于reasonable。十、自由政治言论(free political speech)。举例说明基本自由如何得到调整的。相互限制与自我限制。主要问题涉及颠覆性主张(subversive advocacy)。这里是自由言论与革命暴力关联的地方。“在一立宪民主社会里颠覆性主张的合法性。”【365】抵抗和革命何时才是正当的,这“是最深刻的政治问题之一。”【366】civil disobedience。抵抗和革命仅在反对法律的意义上才是犯罪,然而,某种法律已经丧失了合法性。“受保护与不受保护的政治言论之间引出的界限,并不在于颠覆性主张本身,而是在于当颠覆性主张既直接煽动人们非法使用暴力,又可能导致这种结果的时候。”【368】十一、明显而当下危险的规则(the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rule)。这里Rawls批评了Holmes的明显而当下危险的规则,需要区分宪法危机和紧急情况,搁置自由政治言论必须在存在宪法危机时才进行。【375】 十二、维护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具有优先性的是自由家族。政治言论自由的三个条件:“第一,对言论内容不做任何限制”【379】;制度安排以均等方式影响所有政治集团;合理设计各种政治言论规则。因此政治言论自由也必须regulated以确保其公平价值。十三、与正义第二原则相联系的(非基本的)自由。讨论广告,“广告权…并非不可剥夺的,这一点与基本自由相对。”【387】“基本自由的优先性意味着,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个人群体、甚至全体公民,都不能以…多数派的欲望,或压倒性的偏好为由,来否认这些基本自由。”【387】第二原则从属于第一原则。十四、公平正义的作用。公平正义解决最近政治史在自由与平等上的僵局。【390】公平正义“力图将一种特殊的自由和平等的理解与一种特殊的个人观念联系起来。…这种个人观念乃是一种政治和社会之正义观念的一部分。”【391】
“讲9:答哈贝马斯”
一、两个主要差异。1.哈氏为整全学说,而Rawls是政治观念。2、理想辩谈和原初状态。在注解中Rawls对政治自由主义没有被更早提出感到踌躇。【396】“核心理念是,政治自由主义只在政治的范畴内运作,任凭哲学自然发展。”【397】Habermas的交往理论则给出了理论理性&实践理性的普遍解释,他用一种程序化的理性取代柏拉图式的本质理念。Rawls认为哈氏的学说“乃是一种宽泛的黑格尔意义上的逻辑学说。”【401】哈氏自认更适度,因为是procedural的学说。哈氏认为Rawls的个人观念和政治建构主义仍然表达了先验和形而上学的观念。【403】原初状态提供的是reasonable,而理想辨谈中的共识则保证真理的有效性。公共领域不同于公共理由。【注解中提到宽泛的反思平衡是fully inter-subjective,完全是哈贝马斯式样的】二、重叠共识和证成。哈氏问:1重叠共识中的学说为自恃的观念额外提供什么证明?2、reasonable是什么含义? Rawls回答说政治观念有三种证明:Pro tanto justification(政治观念是complete,能对几乎所有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问题都提供合情理的回答);充分证明(既有政治观念又有整全学说的公民自己将政治观念作为module融入整全学说);公共证明(所有reasonable成员都将共享的政治观念融入各种完备学说,证成了政治观念。这里整全学说只起间接作用。):这里重叠共识与广义的反思平衡结合,而正是广义的反思平衡为政治观念给出了最好的证成。【412】公共证明与重叠共识、稳定性和合法性一起。Rawls区分两种共识:日常的利益化的共识;合理的交叠共识(reasonable overlapping consensus,先有freestanding view)。合情理的交叠共识植根于各联合体的品格之中,是民主政体的政治社会学的基本事实。有正当理由的稳定性也是公共证成的一部分(充分证成)。民主合法性(宪法原则而不是所有问题上的一致)的条件得到满足。Reasonable consensus是被设定的。【413-8】关于reasonable, Rawls坚持回避真理问题。【419】三、现代人的自由与人民意志。哈氏认为原初状态的两阶段导致现代人的自由的优先。Rawls要否认。自由优先是原初状态中的选择,”不需要表现出一种对大众主权的外在强制。”【430,我觉得回到根本Kant观念,Habermas的判断是准确的,道德人的身份预先施加了约束】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并不优先于Habermas所谓的意志形成。哈氏则判断Rawls的现代人的自由是一种自然法,从而给人民意志施加了限制。【432】 四、自由的根基(the roots of liberties)。哈氏说私人自律和公共自律之间存在不可消解的竞争,现代人的权利是道德权利从而约束多数民主。哈氏认为自由主义存在两难:人权无法外在地强加给公共自律。 Rawls否认政治自律和私人自律是无法消解的竞争,两者是共源的具有平等价值。两种自由或自律都由公平正义建构,有内在的联系。【446】哈氏似乎有共和主义的倾向。【447】这不对。五、程序性正义与实质性正义。Rawls自辩实质性正义,也批评哈氏并非程序性正义。讨论和质疑了哈氏惯用更弱的legitimacy和程序合法性观念。【455-8】六、结语。遗留了宪政民主与大众民主的协调问题。感激Habermas家族内部式的挑战。【462,个人觉得哈贝马斯认为Rawls的个人观念和政治建构主义仍然表达了先验和形而上学的观念的判断更准确,Rawls的政治自由主义最终依赖于Kant的哲学观念。虽然交锋中我判断Habermas占据上风,但这无损于这样一个事实:Kantian Rawls的根本性结论是正确的,甚至比Habermas的要好。】
江绪林 2014年12月28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