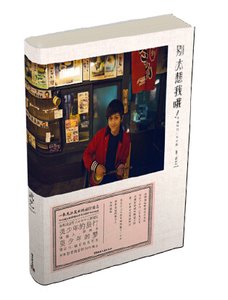《随遇而安》读后感摘抄
《随遇而安》是一本由[美] 安妮·普鲁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页数:2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随遇而安》读后感(一):化不开的忧伤
读完《随遇而安》那晚,只觉得有股忧伤在弥漫。想来若你读过本书,定会牢牢记住“怀俄明州”。它位于美国西部,《断背山》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生活于此的人们,和生活在别处的人们又有何分别呢,不同的只是环境,人性其实相通。
作者安妮·普鲁曾提过,怀俄明州让她感到亢奋,那里无垠的大地能解放人的思绪和视野。然而此处虽空旷,不属拥挤之地,却也实在蛮荒,以致于久居此地的人们,日常生活里免不得充斥着乏味和无趣。
每每提及美国西部,人们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西部牛仔,并想当然的认为他们骑在马上游走四方的状态很man。至于事实如何?很遗憾地讲,这种神化牛仔的想象,在普鲁笔下已被消解。你可读读《那些古老的牛仔歌曲》一篇,心中便有了数。
阿尔奇和罗斯在婚前是蛮和睦的一对,尽管如此,他们仍难逃婚后平淡如水,枯燥无味的日常。为了赚更多钱,阿尔奇择了份新工作,夫妻俩不得不面临离别。别后的两人都不顺遂,罗斯孤立无援,孩子惨死;阿尔奇日夜辛苦的劳作,费尽心力,最后却在病中被解雇。
牛仔们度日的方式没那么多浪漫色彩,有的是饥饿和困倦,以及干不完的活计。阿尔奇和罗斯到底没有重逢,这种凄凉的分别和日复一日的辛酸劳作,使得西部牛仔留给人们的印象,逐渐完整起来。普鲁笔下的牛仔,不会令人产生对驰骋的快感的向往,反而会为他们的孤寂而神伤。
恶略的气候和生态环境,是西部让人望而生畏的原因之一。假如西部种满三齿蒿,会是怎样一种境况?读到《三尺蒿小弟》时我心里想。这篇小说的题目有意思,所谓“小弟”,实则指的是植物。它就像猫或狗,是一个孤独女人精神上的陪伴。
小说里有两种忧伤,首先是人物本身,米兹帕·弗觉得这丛三尺蒿就像孩子,她日夜将其牵挂。在她看来,三尺蒿无论何时都举着双臂,仿佛在迎接她,像孩子似的索要拥抱。哪怕它已经残废,仍举起一只臂。读到此,读者朋友或许会感到内心酸涩,因这是米兹帕的精神投影所致,她渴求的温暖的关怀和拥抱,于现实生活里无人可依,只得借近旁的植物抒情。
其次,忧伤的来源不可排除作者对西部生态的担忧。原本,无论怀俄明的经济繁荣或萧条,三尺蒿所在地都不会被影响到,因为人们很难走向这遥远的地方。然而随着能源公司来此开采,情况便有所不同起来。这丛愈发茂盛的三尺蒿,逐渐成为稀罕物。人们开始注意到它的存在,它与周边景致如此格格不入,好像它不该属于植被稀少之地。读者可试着猜想它的命运,怕是活不长。
离开此地的米兹帕是否又在寻找别的寄托?普鲁笔下的人物,仿佛都在寻找某个出口,来慰藉自我的孤独。印象极深是《有家的男人》里,福肯布罗克先生的自言自语。他渴望能被人倾听,听他讲曾经的故事。
也许即使没有人,只有台录音机,他照旧能滔滔不绝,他需要的是自我诉说的机会。那些话,那些往事,藏在心里许久,时不时地提醒他不可忘记。最终,他讲述了一个悲伤的故事,与父亲有关,是一件刺心之事。尽管如此,他仍说:“我爱我父亲”。
这种情绪很矛盾,一方面父亲给了他一个家,让福肯布罗克成为有家的男人;另一方面,父亲在外面有多个家,他有几个孩子,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家。福肯布罗克对父亲的爱是专一的,而父亲未必如此。
类似破碎的情感在《驴的证词》里也有,卡特林并未停止对马克的思念,她本想忘记他,却发现遗忘是如此难。走到半途时,卡特林遭遇到不幸,腿被石头压住,动弹不得。她在恶劣的气候里苦熬,多个小时过去,却不见救援者出现。
在没读到结尾前,可能读者会觉得诧异,既然是《驴的证词》,怎么全篇没有驴出现?你先别急,耐心继续读。读到结局便会知晓,所谓的“驴”其实是卡特林。被困多时,她的“手和胳膊变成了黑灰色的皮革,像一种苔藓”,骄阳将她炙烤,“阳光热得吓人”,她在临死前呼唤的还是“马克”。
普鲁写的悲剧,悲的很彻底,属于没机会更改的悔恨,或难以愈合的伤痕。她每篇小说的构思很巧妙,比如《我一直热爱这地方》的开篇,作者写了一个魔王,正在回地狱的路上。这个魔王有意思,来人间参观,而后取人间精华,去人间糟粕,完善地狱。
读者将跟随魔王的视角,遇见一些熟悉面孔。此时竟有种分不清人间和地狱的错觉,尽管那句“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得抛弃希望”,令人不寒而栗,但仔细读下来,倒也没感到绝望,反而有几分轻松。
读完最后一篇小说,可能你会思考《随遇而安》这一书名被确定的缘由,因为这些短篇丝毫不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感觉。或许这恰恰是作者想表达的,生活如此,总有波折,我们预料不到未来,不如随遇而安。普鲁的小说适合重读,第一遍通常体会不到深意。她书写的忧伤难化掉,因而在感受这些故事时,切记不可浮于表面。
《随遇而安》读后感(二):游牧之地的拓荒岁月:他们生于“恶土”,他们“随遇而安”
《随遇而安》是安妮·普鲁“怀俄明故事”系列之三,另外两部分别是《断背山》和《恶土》,前者因为一部同名影片早已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后者与《随遇而安》一起,于202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继2020年出版安妮·普鲁长篇小说《树民》之后,对其文学作品的又一次隆重推介。这对熟悉、喜欢安妮·普鲁的读者朋友们来说,不啻为一场文学解渴的及时雨。
《随遇而安》延续了安妮·普鲁描写怀俄明地区故事的一贯风格,她笔下的怀俄明是一片地广人稀的荒野,物质条件极端匮,普通人过着贫穷落后的生活。除了几乎一无所有的穷人,还有掌握有一定社会权利的政客,拥有一大片土地的牧场主,以及他们成群的奶牛或马。与之交相辉映的是,新兴产业在这片土地上的野蛮生长。
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怀俄明人,明显受到了荒野、风沙、孤独与寂寞的“滋养”,大多数人尤其是没有经济或政治地位的人,生活举步维艰、跌跌撞撞,他们生活粗放,性格粗粝,思想粗放,少数心理细腻的人,也会在无边的原野中变得无处安放,到头来唯有将自己包括自己的思想变得像这片土地一样博大而粗犷才宣告结束。
在这部由9个短篇小说集成的作品中,安妮·普鲁以细腻之笔,描绘了荒原与山谷之间游牧之地的普通人生。《那些古老的牛仔歌曲》讲述了一对年轻夫妻的故事。丈夫为了挣钱远离家乡,远离怀孕的妻子。结果,丈夫因为得了肺炎被解雇,返乡途中遭遇暴风雪,与护送自己的工友双双冻死在路边的一个小木屋;而在这之前,他年轻的妻子已经因为难产而死去,同时死去的还有刚刚出生还没脱离胎衣、呼吸一口新鲜空气的婴儿。而她醉醺醺的父亲来打听她的近况时,甚至没有下马来敲一下门,只是在马背上喊了几声,没有得到回应就返回了。他不想下马的唯一原因就是怕下了马而上不去了。
悲惨的命运,悲惨的人生,肆虐的风雪,掩埋了两个年轻人的希望。
同样悲惨的故事在《壕沟里的驽马》中再次上演。有一对老人,他们的女儿十五岁就怀了孕,生了孩子当天就不知所踪。对女儿的不满与怨恨转移到了这个无辜的外孙女身上,孩子在缺乏爱的环境中长大。她临近毕业前辍了学,嫁给了一个像比利小子的同学。草率的婚姻没能持续很久,在协议离婚之际丈夫参了军,而已经有了身孕的她在生了孩子之后也当了一名战地护士。最后,丈夫在战争中身负重伤而亡,她也在边境检查时遭遇炸弹失去了一条胳膊。而他们的孩子,那个被曾外祖父母宠爱的孩子,因为一场意外也永远地失去了。
这难道就是这片游牧之地对他们艰辛付出的回报吗?这些人的苦在作者看来是值得同情的,值得回忆并深刻缅怀的。他们虽然生活艰难,但始终有一颗不甘的心,虽然社会并没有善待他们,让他们残缺了身体,甚至失去了生命,失去了挚爱,但这种生活的苦难必将成为未来幸福的基石。他们是路边的小草,顽强地生存着。
相比之下,作者对另一部分人的描述就不那么客气了。只不过她没有直接表达,而是让地狱之主魔王出场。在本部作品中,有2篇以魔王为主人公。在《我一直热爱这个地方》,魔王试图将他的统治王国——地狱进行创新改造,打造一个他心目中更加完美的领地。这里面住满了烟草说客、公司高管,电影制片商、婚姻骗子、吸毒者、牧场主,还有C国税务局的工作人员。怎么改造,具体细节尚在筹划之中,但最终目标是要让下地狱的人更痛苦。他甚至听从了秘书的建议,计划在九层地狱之外再加一层,建造第十层地狱,这一层主要用来容纳M国商人。不过这个主意能否付诸实施,还不确定。因为他认为:
“从长远来看,很可能不需要进行扩建;因为所有的人几乎都必然会罚入地狱。”
“无须他动手,地球本身就会成为另一个地狱。”
而在另一篇《沼泽地的不幸》中,魔王则回想起了曾经也是天使的过去,他让魔鬼造了一只翼手龙,袭击了一群生物学家。而这场不成功“造龙”运动和“袭击”行动,让其中之一的熊类学家认清了一个世间真相:
“世上到处是魔鬼,就像色拉里面的油炸面包丁一样。”
哪里是地狱,哪里是天堂?谁是魔鬼,谁又是上帝?似乎没有人能弄得清楚,也许只有曾经是天使的魔王,还有那个经历过“上帝死了”的熊类学家才知道真相。
不管是开拓还是毁灭,这片神奇的土地既给予了一部分人生存的机会,也夺走了另一部分人生存的希望。《三齿蒿小弟》本来是一对不孕夫妇的精神寄托,谁料却成了与百慕大三角海域一样神秘、夺人性命于无形的怪异之物,看似荒诞的描述,折射出现代工业在无序发展中“吃人”的真相。《驴的证词》讲述了一对情侣分手之后,女人赌气独自去探索早已被封闭的“杰德小道”的故事。从最初的“她并不想马克”,到“马克本来是会来这儿的”,又到“还有对马克的思念”,女人越来越深入秘境,对男友马克的思念就越来越深,后来“她后悔同马克发生争论”,尤其是在自己遇险渴望营救时,甚至想到“要是马克同她在一起”,更是幻想“如果马克回到活动房”。但是,所有的幻想,在这人迹罕至的森林里就显得那样不切实际。
与《树民》这个大部头相比,《随遇而安》短小精悍,既没有贯穿数百年的历史纵横感,也没有多达七代人的命运沉浮,但就人物命运的刻画来讲,后者一样细致入微、入木三分。这些西部牛仔们的生命,就像风暴中的沙子被裹挟着,时而漂浮于天空,时而陷落入泥淖。他们就是人间的一粒尘埃,卑微的生命,卑微地活着,但同时也不甘地倔强。而安妮·普鲁的细腻文笔在这些短篇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叹为观止之笔随处可见,“寂静像一条雨水泛滥的河流,充斥在这个房间的四壁,笼罩在他们的头顶上。”有没有瞬间被寂静笼罩在自己头顶的感觉?
环境与命运,时代与人生。安妮·普鲁用笔画勾勒出了这片游牧之地,用文字描述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荒凉,阴冷空旷,麻木,成为当地人暗色的生活基调。虽然到处都是“魔鬼”,但他们依然不屈地活着。
他们生于“恶土”,他们“随遇而安”。
《随遇而安》读后感(三):后拓荒时代的荒蛮西部——读安妮·普鲁短篇小说集《随遇而安》
安妮·普鲁可以算得上美国当代文坛最为引人瞩目的作家之一,她的美国西部故事曾一度被搬上大银幕,最为著名则是李安导演的《断背山》。在这些西部故事中,安妮·普鲁以她冷峻、狂野的笔触塑造了一系列或粗粝或细腻的人物形象,拥有极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独特的观察角度。《随遇而安》是安妮·普鲁著名的“怀俄明故事”系列的第三部,一共收录了九篇短篇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20年11月首次引进出版。在这部以怀俄明州为背景的书里,安妮·普鲁更加关注了在二十世纪浪潮迭起之间西部小人物的生存与追求,在后拓荒时代思考荒蛮西部的历史与未来。
美国西部拓荒时代历时一个多世纪,从18世纪末开始,历经整个19世纪,直到20世纪初叶才逐渐结束。在这长达百余年的拓荒历程中,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淘金者或失业者来到这片有待开发的土地上,修建房屋和牧场,种植玉米小麦,建立起了美国西部独特的经济体系,并在随后的工业生产中促进了美国近代知识与工业革命。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其著作《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中称“一部美国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西进史。”安妮·普鲁出生于1935年,在她成长的岁月里,美国西部开始进入后拓荒时代。往日发生在这片土地上各种各样或可歌可泣、或阴险毒辣、或骇人听闻、或愁断情肠的故事都已成为了历史,成了美国好莱坞至今兴盛不衰的西部题材电影的素材,让观众在手持六响左轮手枪的西部牛仔身上想象西部。然而安妮·普鲁并没有沉溺于那些已经过去的遥远想象,在她看来,与其关注不切实际的西部牛仔,后拓荒时代下依旧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人更具有书写意义。
拓荒时代与后拓荒时代下的美国西部都拥有着同一特点,那就是荒蛮。这既是恶劣的自然条件所带来的,同样也是西部拓荒者在面对他者时所保持的态度与内心荒芜的空间。因为生存的艰难,死亡和财富被端放在了天平的两端。就如书中所说:“有的人确实如此。但更多的人走得不远,很快被遗忘了。”人们不得不在其中挣扎。安妮·普鲁的写作常常被人评论为陌生化写作,这是因为美国西部独特的异域色彩还有其写作主题的迷离。在后拓荒时代,人们依旧需要理解一匹野马的价值,一滩洼水的四周,一公顷土地的范围,这些和越来越发展的东部城市充满隔阂。可东部仍然在影响着西部。淘金者和失业者将目光转向了东部。人们明白西部巨大的油气与矿产,也知道一个矿工的工资是任何一个牧场主都无法承担的。拓荒时代与后拓荒时代的分裂让身处两个时代的经历者无所适从。有人恪守着西部男性至上的准则,崇拜力量,却在不加防护的工地失事,只因防护是“娘们儿”的事。也有人结束在西部的故事,走入城市,却因缺少基本的技能,只能艰难度日。西部在崩塌,沙子、汽车旅馆、围猎、人们在重塑自己的生活。
在《随遇而安》中,安妮·普鲁十分重视人物内心感受的刻画,她用或密或疏的笔触,将人物的一举一动所代表的意义都显露了出来。如在《壕沟里的驽马》中志愿者格洛斯勃太太劝说达科塔去见一见曾经将怀有身孕的她抛弃而如今躺在病床上的丈夫萨施,并尝试是否可以唤醒他。达科塔像一般人一样表示了拒绝。可在进一步的劝说中,作者并不开始关注劝说者说的什么,而是开始描写达科塔所闻到的气味和她所观察的女人的手型以及戒指。最后达科塔答应了这一请求。这一处理并不会感到突兀,反而更加让人理解达科塔最为在意的是被爱的滋味。一丁点温暖的味道便会让她的心变得柔软,这当然也是她悲剧因素的所在。又或者在《那些古老的牛仔歌曲》中罗斯在小屋中独自产子并遭遇难产,作者写道:“她没有哭,心中充满着一种本能的愤怒。她不去看那具小尸体。”而当罗斯想要用床单裹起自己的孩子时,却又想到“她觉得,损失那条床单是另一桩悲剧。”所有的人类文明在这一刻显得如此虚伪,一个女人如同野兽一般在荒无人烟的小屋中产子难产,并死去。而在此之前,命运一环接着一环的让人一步步迈入深渊,让人感受到深切的绝望。安妮·普鲁的内心刻画以及人物举动的反应描写将荒蛮世界中的挣扎表现得入木三分。
安妮·普鲁在《随遇而安》中描写了大量的死亡。不同于西部电影中的快意恩仇,在这本书中,死亡是拖沓的、无助的、甚至是无意义的。出现死亡最密集的是《那些古老的牛仔歌曲》。在这一篇中,罗斯难产而死,阿尔奇和辛克冻死在木屋中,还有那个自杀的老光棍哈普·达夫特。老光棍是在对罗伯特·多尔甘夫人的眷恋与意淫中死去的。除了他,其他三人都在尽力地活着。可事情的无解之处就在于,怀孕的罗斯需要丈夫阿尔奇的照顾,而阿尔奇需要去很远的地方工作,生活需要钱。罗斯也可以不需要阿尔奇的照顾,可是她并不愿过早回到自己早已厌烦的父母米勒夫妇身旁。厌烦米勒夫妇也没关系,阿尔奇委托了朋友汤姆·阿克勒,可他们并没有见面,写的便条被风吹跑了。而米勒夫妇在出门看病时,生命也流逝着,最终葬身在外。罗斯只能在简陋的小木屋里,看着早产儿的尸体,流血而死。而阿尔奇本可以去看罗斯,可他又遇到了牧场主不收结婚雇工的规定,没有空闲。在罗斯死去时,他正在发高烧。辛克在送他回家时,遭遇了连续十二天的暴雪,两人永远留在了那个避宿的路边小木屋。蛮荒西部如同泥沼,生命如《分水岭》中被围猎的野马,无处可逃。
安妮·普鲁对于时间线的把握在这部书中得到了体现,一个故事往往要涉及到几代人的经历。就如书中雷·福肯布罗克老人所想的那样:“他也许一生只是个牧场主人,但是他经历的事情不少。”《有家的男人》采取回忆叙事的手法,通过福肯布罗克老人的回忆拼凑出各类不同人物的形象,这些形象是残缺的又是鲜明的。老人在讲述过去的故事的同时总是在对比现在。而现在的代表则是他的孙女贝思。老人最终说出了自己父亲有四个家庭的秘密,这是老人最为羞耻的事情,可贝思却想着她竟然有那么多的亲戚。这种价值观的碰撞,是时间带来的。在《三齿蒿小弟》这篇,掌握时间的并不是人类,三齿蒿丛成了主角。从比尔和米兹帕夫妇到到跨国沼气开发公司的矿工,再到发生在三齿蒿丛下的凶杀案。时间跨度几十年。三齿蒿小弟还站在那儿,并会一直保持着朝天的姿势。《壕沟里的驽马》则以重现的方式,将未成年生育孩子的悲剧在母女两代人身上书写两次。保持着一个又一个循环。挖掘上代人的恩怨,并在下一代中隐现,让人感到时间的复杂与罪恶的静止。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九篇故事中,有两篇是连续的,分别是《我一直热爱这地方》和《沼泽地的不幸》。塑造了地狱里的魔王这一形象,通过他的所作所为和所言,深深地讽刺了刻板的官僚体系与虚张声势的当代艺术。时不时来一个反讽和自以为是,十分幽默。如“杜安,与加拿大税务局相比,美国国内收入署是幼稚的娃娃。地球上没有一个机构像加拿大税务局那么顽固、官僚化、专权、假惺惺、敲竹杠、打官腔、深不可测、吃人不眨眼。”又如维柳玛斯·马利诺斯卡斯的露天游乐场是他的主意。让人忍不住捧腹大笑。这也同样是西部世界中人们常见的调侃。
安妮·普鲁这本《随遇而安》英文原名为《Fine Just The Way It Is》,直译过来为“好吧,就这样”或者“这样就好”。译作“随遇而安”,可以说是恰如其分。后拓荒时代下的荒蛮西部上,一代代的人或出生、或死去、或离开、或回来,大家都在“随遇而安”。
《随遇而安》读后感(四):所谓的“随遇而安”,不过是面对命运无情的捉弄而无能为力
人类征服蛮荒之地的过程中,注定要有传奇出现,作家需要这样的环境,来安放他们笔下的那些不羁的灵魂,怀俄明州就是安妮·普鲁笔下人物的栖息地。
关于怀俄明州的故事,安妮·普鲁写了很多,《随遇而安》就是“怀俄明故事”系列之三,书中收录了短篇小说九篇,在她的笔下,那些“拓荒者”在这片土地上上演一出出悲喜剧。
作为美国当代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给与了安妮·普鲁这样的评价:普鲁用狂暴、紧凑、娴熟的笔法将人物一路推到悬崖边缘,想要越过边界。
的确,读安妮·普鲁的文字,需要有一个强劲有力的心脏,阅读的感觉就像书中《一个血迹斑斑、滑溜溜的大碗》中的那群野牛,他们原本优哉优哉走入往年要进入的熟悉的水草地,突然一群人跳出来,牛群开始惊慌失措,沿着赶牛人设置好路线一路狂奔,路途中人不时有埋伏好的赶牛人出现,让受惊的它们更加无目的的狂奔,直到悬崖,然后义无反顾地跳下去,血肉模糊。
文字的冲击力带给你的“震撼”,如同粗粝的岩石与狂暴的野牛摩擦声,让你沉浸其中不能自拔,而故事透出来的宿命感又带给你满怀忧伤。
初涉社会,不少意气风发的青年都会吼上一嗓子:“我命由我不由天!”当经过了跌跌撞撞的人生之后,会用历尽沧桑的声音哼上一句:“万般都是命,半点不由人。”
安妮·普鲁的作品中的宿命感处处可见,在《那些古老的牛仔歌曲》中,16岁的孤儿阿尔奇娶了十四岁的罗斯,他们用全部的钱购买了土地,一点点构建自己的“爱巢”,对未来充满希望,但仍旧被现实与死亡打败。
为了生计,阿尔奇去别的牧场打工,罗斯怀着孩子宁愿一个人呆在小家坚守,也不愿意回到有酒鬼父亲、长期因病卧床的母亲身边,最终因难产生下死婴,自己也大出血而死。
阿尔奇也是一样,农场主不需要结了婚的雇工,为了挣到钱他隐瞒自己的婚史,也不能与罗斯联系,最后因为赶牛受冻而引发肺炎,和同伴死在求医的路上。
另一个故事《壕沟里的驽马》,也是一个与命运抗争最后被命运打败的而故事。
达科塔一出生就被十五岁的母亲遗弃,外公外婆不得已接手这个“烫手的山芋”,窘迫的生活、外公外婆的冷漠让她的生活充满了忧伤。为了逃离,她高中没毕业就和臆想中的男孩萨施结了婚。
但婚姻、爱人与她的想象相差太远,于是,她提出离婚,在没有办理离婚手续的情况下,萨施离家参军,达科塔这时发现自己怀孕,并因此丢了了收入菲薄的工作。
无奈之下,她接受外公外婆的意见,生下儿子之后也去了军队,日子眼看好了起来,自己的收入也可让儿子得到最好的照顾,外公外婆把没有给过达科塔的爱都倾注在儿子身上。
可不幸还是降临了,她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炸掉一条胳膊,十八个月的儿子从车上掉下来被车轮碾死,在医院里,她又得知萨施也被炸掉双腿,这还不是最惨的,萨施的父母说他们并没有离婚,所以达科塔依旧有照顾萨施的义务……
面对这些结局,只能用“宿命”来注解,他们的童年、甚至是一出生都是不幸的,所以以后生活无论怎么努力,也一样败在命运手里,败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永远也翻不了身。
小人物的人生被命运紧紧攥住,为所欲为,而全人类的命运、地球的命运呢?安妮·普鲁早就想好了答案。
本书中的两篇“神话”,是关于地狱魔王的,地狱里关着十恶不赦的人,魔王的工作就是想方设法惩罚这些的“恶人”。
“为了容纳日益增长的大坏蛋,其中主要是M国商人,增加了第十地狱。”“无需他动手,地球本身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地狱。”“残酷无情的技术文明让他们跌跌撞撞地走向末日。”安妮·普鲁无时无刻不在透露这样的讯息:坏人越来越多,人类正在将自己赖以生存的地球变成地狱,甚至用人类所谓的“文明“毁灭地球。
为了征服与掠夺,人类对旷野资源无尽的开发,对野生动物残忍的猎杀。在《分水岭》这篇文章中,海伦的父亲兄弟喜欢捡拾鸟蛋,最终一个去掏鸟蛋的兄弟,被狂暴的的鸟啄烂了眼睛与脑袋;海伦的姐夫芬克捕捉野马为生,他们把野马卖给饲养场作为饲料,海伦的丈夫海在生计困难的时候也参加了捉马的队伍,最终死于野马蹄下……
你争来的,最后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