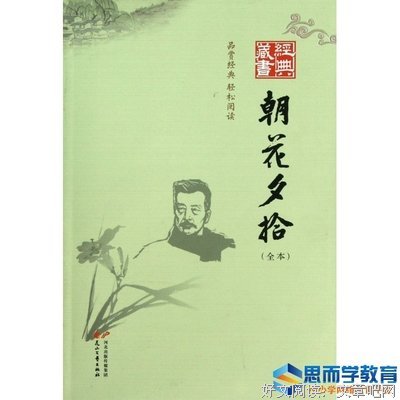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读后感摘抄
《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是一本由[美]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著作,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2.00元,页数:47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读后感(一):告诉我该怎么做,才能更多的喜欢你一点——我最挚爱的作家
首先得说,DFW是我最喜欢的作家,所以在这篇书评里写下的一切要么是我因为过度喜爱而写出的优点罗列,要么是就是因为我真的过度喜爱这个作家而又在他写的这本散文集里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沮丧,这才写出来的气愤与讽刺的话语
《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读后感(二):网球迷+文青+思考者必读书
最初了解威廉 福斯特来源于比尔 盖茨推荐“String theory”(弦理论)。作为十多年网球资深球迷,打了近十年网球,一直想写一点关于网球的文章,无奈文笔不够。 福斯特被称作“历史上最佳网球作家”,“天才作家”。然而这位天才2008年已经牺牲了,和林肯公园主唱一样..
我也在抽空翻译福斯特的一篇经典网球文章,“Federer: both flesh and not”(费德勒:半人半神) 。太tm难翻译了!
《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读后感(三):天才的作品
简直想打超五星。先讲丑话:校对有问题(一页中相同的人名都能搞错)翻译一般(当然翻译这种语句想必很难很难)装帧一般(把外面浮夸的封皮拿了倒是合心意)
但隔着语言的山头,仍能看到华莱士写作的魅力以及他本人的魅力。游记,人物倾述,文化批评,他都能轻巧驾驭,并时不时让我大笑,或是兴致勃勃地去查找他所提及的一切。他可以说是个天才,对于文学、哲学、数学、网球,都有精深的造诣和独特的个人体会。他说话的方式则带着一种可爱的灵巧和坦率。
太喜欢了,以至于觉得有必要要啃下原文。可以说是刚读完一遍就想立马再读一遍的书了!
(查了他本人的资料才觉得,他的死亡正是他在本书最后一篇短文中所论述的“作者之死” 华莱士本人应该是不会喜欢那些金光闪闪的标签吧
(以及,是时候恶补哲学了,不能到了大三连高中买的Said还看不懂吧...
《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读后感(四):短评放不下
读华莱士体验很棒。艰难,但很棒。有点伍迪艾伦式的自言自语絮絮叨叨,吐起槽来没完没了,其间不乏讽刺和辛辣,但其实并不针砭时弊,只是作者本人太聪明太敏锐太有洞察力了,能看到许多常人看不到的东西,脑洞也够大,写着写着就控制不住地很幽默,我也只好边读边笑,边用铅笔画着那些金句。 畅游加勒比那篇就想,哪艘游轮要是碰到他这么个极品神经质也真是倒了大霉了哈哈哈。博览会这篇满满对东西部存在差异和价值差异的观察与讨论,关于性骚扰的不同态度尤其值得玩味。二十多年后的2017和18,性骚扰犹存,并且终于被推到了聚光灯下,但其实站出来的也都还是东西海岸那一小撮人而已,这一点没有任何改变。但感觉出华莱士对东海岸的道德优越感以及个人与政治高到病态扭曲的相关度都是持批判态度的。看他对自己从小生长的中西部代表之一伊利诺伊的描写,想起刚刚看过不久的电影sweet home Alabama,里面也都是纽约的社会精英和老南方红脖子们之间的尖锐矛盾。在我们生活的国度其实也有一定代入感,北上广和外省。最近这两年每次回到家乡,这感觉就太强烈了。
《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读后感(五):《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看透一切的聪明
文/夏月
如果你拿着杂志社提供的钱,免费做游轮游玩,回来只需向杂志社交一篇稿子,你的心情是怎样的?大多数人都感觉是中了大奖,自然欢快愉悦、毫无负担地登上游轮,开启豪华之旅,而后写一篇热情洋溢的游记。这只能是普通人的故事,却不是华莱士的,在华莱士的游记中你会读到别样的东西。
《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这部文集收录了华莱士1992年至1996年期间创作的七篇非虚构散文,其中同名散文《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和《远离几乎已经被远离的一切事》都是作者应杂志社的邀请写的游记。华莱士笔下的游记可不是用有优美的语言来描述美景和享受,他脑洞复杂,太过常人的聪明,以一种非常人的眼光来观察世界。他善于用文字游戏,在文学创作中夹杂着数学、哲学等各种概念,还伴随着长长的注释。通读华莱士的文章,感觉其语言是琐碎、片段,充满意念性的,似乎反常态,但仔细一琢磨却觉得华莱士说得好有道理啊,在絮絮叨叨中处处都有闪光点。当他站在游轮上,看到夹板上的人群,“每个人的拖鞋敲击着码头,产生了一种社会语言学的效应,对象由游轮变成了游客”“高层游客开始流通货币,体验经验”,他的旅行是站在人群外的,异常的冷静和孤独。
华莱士出生于美国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哲学老师,母亲是英语老师,从小受到的系统教育,使华莱士具有很高的哲学、文学素养,而这些影响也体现于自己的作品中。在《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这部文集中,除了应邀的游记外,还收录了华莱士关于电视、网球、大卫·林奇的电影等诸多内容的其他文章。对于大众电视,华莱士是反感的,在《众目窥一:电视和美国小说》中,他说自己不是“唯一一个对电视抱有仇恨态度的人”,电视是“窥视”人们生活的一种手段,而且是以观众为受众目标的模拟,是“一场盛大的幻想”。
华莱士于2008年在家中自杀,之前他一直患有抑郁症,并长期服用药物。在普通人的眼里,华莱士是一个抑郁症患者,而在华莱士的眼里,那些普通人又何尝不是无趣之人呢?也许正是他有着看透了一切的聪明,才选择远离这本该远离的一切事吧。读华莱士的文章,会颠覆一个正常人的思维和感官,不信,你可以试试看。
。
《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读后感(六):《所谓好玩的事 我再也不做了》读后小感
看完这本书,我想说:华莱士的书,我再也不想看了。倒不是他写得不好,相反,写得相当地好。可以看出,作者对文字和数据的处理手法异于常人,不愧是天才。
回到我自己本身吧,主要是被好玩的题目吸引,结果把自己给坑苦了。
可能是中文转译的原因,大段大段的长句长文,很多时候阅读时候有一种紧迫感。
不可否认,很多比喻和见解还是很深刻的,尤其是写到美国五十年代电视文化和大卫林奇的电影分析,但大多数时候,我是在遭罪的。就阅读体验来说。
这本收录了7篇经典文章的非虚构作品,出自美国天才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之手。
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
远离几乎已经被远离的一切事物
旋风谷的衍生运动
网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伊斯的职业艺术性堪称有关选择、自由、局限、愉悦、怪诞,以及人类完整性的典范
众目窥一:电视和美国小说
不动声色的大卫·林奇
天花乱坠
从标题就可以看出,这是一部光怪陆离的作品集,难怪他会喜欢大卫林奇,感觉这两人的风格很像。
神神叨叨,琐碎冗长,阴暗晦涩。
整本书透露出一种讯息:一个人太过着急于表达自己的看法时多少会有点抓不住重心,唯美主义所能容纳的信息量又太少了,从这点上来说,需要体谅一下这位天才作家。
一个对自己局限性认知过于清楚的人,容易陷于自身对于沉闷现实的焦虑恐惧和疏离。
所谓天才,都是短命的。华莱士9岁得抑郁,46岁自杀身亡。多么短暂抑郁的一生。
总体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奇特的阅读经历。就像看大卫林奇的《穆赫兰道》,未必是我所有认知范围内最精彩的,但绝对是最独特的。
摘录最初吸引我买此书的一段话:
“你有多久没有这样无所事事过了?我清楚地记得,我已经好久没有这样过了。自从我的每个需求只能借助身外某物提供的必然选择才能得到满足——甚至连这种选择都没过问、了解过我要什么——之后,我就没有这样过了。此刻,我也像游轮一样漂浮着,身下的液体很咸,很暖,但不像海水的程度那样深,如果我能意识到我想要什么,我敢保证我不会惧怕任何东西,并因此度过一段真正美好的时光。我还会给每个人寄去一张明信片,希望他们也能来这里。”
想哭,有没有?
《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读后感(七):资深玩家的毒鸡汤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实在是个鬼才。虽然文集名为《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却也不得不承认,他才是地道的玩家。豪华游轮旅行、伊利诺伊博览会,都变成他品味人性的旅程了,“人类的处境就是作家的猎物”。网球大赛、大卫·林奇的电影、后现代文学的专业解说,都是冰山一角,哪比得上他以小说作为大学毕业论文、深深迷恋实验性写作叫人钦羡啊!
世界上有趣的事太多,这么会玩的华莱士为什么说不玩了呢?同名篇目《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玩了》写满答案。虽是一趟精彩的七天七夜豪华游轮旅,华莱士也看到了种种可供享乐或是体现用心的细节,偏偏忍不住要吐槽。倘若这是华莱士的乐趣,那么随行者(或读者)可没法视其为安稳的休闲之旅了。
华莱士从砌得雪白的游轮谈到资本和工业的加尔文主义,从及时递上的热毛巾联想到“善意的副本”(模仿声音),从离开房间犹被田螺姑娘清扫过,扯到“他们惯着你,其实证明他们并不想看到你”。华莱士煞有介事地提及他的“科学试验”:“田螺姑娘”会在他离开房间多久以后进去打扫呢?他掐表发现,外出29分钟时无人打扫,外出31分钟已然打扫干净,其中短暂的时间差简直是魔法,又与前文加尔文主义相映成趣。可是玩到这种程度,华莱士只证明了“人至察则无徒”,他洞悉一切、口若悬河,当我们有机会反驳的时候,倒觉得他说的也没错。就像一个玩了百遍过山车的人,哪个地方转弯、何时倒退、何时俯冲都能如数家珍,寂寞多过乐趣吧。
华莱士牌毒鸡汤,有时还真该一饮而尽。他既能轻而易举直击问题本质,又能理解此中人的心境。譬如,花跟睡觉一样长的时间去做一件事后我们认为不好的事情,是不是该三思?看电视就是这样,人均每日看电视达六小时,大多数人浑然不觉。再想想其他“乐趣很小、危害很大”的事情,也攻破了意志力的防线,说是上瘾不如说是惯性。又如,华莱士观察欢乐谷的游乐项目,沉浸其中的男女乐而忘返,焉知走光、露怯、丢魂的丑态百出?相比之下,他倒对大善大恶没那么纠结,认为邪恶也是一股发人深省的力量。
正因为同时看到了正面的光鲜快乐和背面的丑陋虚无,我们只能一边点头赞同作者的字字珠玑,一边感慨“还能不能愉快地玩耍了”。做看客是轻松的,置身事外又不可得,难怪华莱士放言“再也不做了”呢。好比他那一夜爆红的演讲(后整理出版《生命中最简单又最困难的事》),看客把它当鸡汤干了,可华莱士终究循此走进了死胡同:做一个目光如炬、妙笔生花的资深玩家太累了。
——丁酉年读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
《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读后感(八):结束玩笑
知道华莱士是从《旅行终点》开始的,知道《旅行终点》是由卷老师开始的,那部电影改编自《无尽的玩笑》,据看原版的朋友说是一本脚注非常繁杂的书,以至于到现在都还未出版。 看《旅行终点》的时候我还截了一段话,是这样的: “因你已看穿这一切均不过是幻梦,你比旁人糟糕太多,因你已经该死的无法正常过活。” 那是我很消沉的一段日子,或者说是闲的消沉,一种平凡的消沉,满脑子都是万青十万嬉皮的那几句歌词。 “敌视现实,虚构远方,东张西望,一无所长。” 我看这本书的时候也是浑浑噩噩的,大抵华莱士就不是一个引人入胜的人吧,每一篇文章都像是一间充满碎碎念的屋子,在里面听说了很多东西,但走出来什么也记不住。他的文字是琐碎的,自说自话,他的形容是非常细腻但绝不拗口的,可以说是很直白,带有译制体的魅力。仿佛看到一个毫无活力的青年人,碎碎念的像个60岁的奇怪老头,像电影里面那些喜欢背着包埋着头戴着眼镜的小年轻,颓唐颓唐颓唐。 这让我想到了我非常喜欢的伍迪艾伦,但相反的,伍迪艾伦非常浪漫,极度理想化,华莱士的碎碎念是厌世的,而伍迪艾伦则是小资中产,不羁,没有自我,伍迪艾伦重享受,既然万事无意义,不如先随便活一下。华莱士则不是,也许华莱士会觉得,万物皆是幻觉,活着仿佛就是死去。虽然看待世界的方式是一样的,却走向了两极,这两种处事方式也恰好是我生活的两个阶段,而人总是容易在许多观点里循环往复。 活着的尽头是什么呢,绝不是死亡吧,大概是感到虚无的那一刻。 我想,大部分人都曾经感到虚无,被无意识的意识包围的时候,往前往后没有出口,也无法想通,人在时间的暗长的甬道里,放弃挣扎。但即使这样,也没有很多人因为感到了活着无意义就去奔向死亡。因为即使是幻觉,这幻觉让人兴奋的因素也太多了,比如金钱、比如爱,虽然我们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过是幻梦里的道具,但还是常常深陷其中,忘记要死去。 还有人对自己独特性的高瞻,总以为自己是特别的,人有太多奇奇怪怪又难以抗拒的欲望了。《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的后面谈到了大卫林奇,这曾经是我最喜欢的一位导演。那个时候迷恋cult电影,迷恋不知所谓的黑暗、虚幻、长镜头,诡谲的情节画面细节。虽然从电影里看到了某些东西,但我现在更怀疑我看到的只是我自己,电影就像面镜子,导演想表达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或许,导演也不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 但他不需要去探究自己表达的东西,电影被抛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千百万种人生了,而无论电影的逻辑有多么混乱情节有多么荒诞,都不需要被在意,因为无论是谁的一生,商人或工人、总统或平民,都是毫无逻辑的一片狼藉,或许这么说别人的人生太武断和绝情了,但再是一帆风顺的人,也会时常觉得手里握不住想要的东西吧。 可无论怎么样,这一生还是要接着过下去,就像那本《无尽的玩笑》的书名一样,可能终其一生就是一场玩笑,为了自我保护我们和别人开玩笑,为了活的少一些痛感我们对自己开玩笑,华莱士不过早早结束了这个玩笑,而我们继续着,乐此不疲。
《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读后感(九):我大概是快乐的吧
《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是美国天才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非虚构类作品集,书中收录了他的游记、评论以及随笔类的文字。其实,华莱士的文字并不容易界定类别,别人眼中快乐的“吃喝玩乐”经历,到了他的笔下却往往变成了“痛苦的记忆”。
从这本书书名就能略微窥见华莱士的特点。书名取自首篇文章,其实它本是某杂志向他约定的豪华游轮体验文字,杂志社为其定好船票,并预付了稿费。这并不是游轮业主的约稿,而是出于杂志社第三方观察目的,而且按常理来说,如此“盛情”之下,多少也应该会让体验者下笔“手软”。而华莱士却似乎毫不“领情”,他的体验总结正如题目一样——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
似乎有些奇怪,豪华游轮,海上旅行,周到服务……这些在外人看来是享受,在作者眼中却成了漫长的“放逐”之旅。他不是被繁华放逐,而是被放逐于繁华,在所谓繁华与舒适之中,他仍旧孤独、敏感。而在《远离几乎已经被远离的一切事物》这篇本该是关于农业博览会的记叙中,华莱士仍然还是那个心事重重的人,博览会上的各种喧嚣、气味似乎要将他吞没,各种展出和娱乐项目则在他的笔下全然不见精彩,只看见他如苦行僧一般缓慢前行。
这并非是华莱士过于脆弱,反倒显出他的诚实:游轮上的人们逃离日常生活,来到陌生人中,经历那些平日里不常或不曾有的体验,他们又何尝不是孤独的呢?他们寻求自由,实则是将自己“困”于船上,就像购买了“海上监狱”套餐;他们渴望交流与尊重,但完美的服务让人像流水线上的产品,无暇他顾,相互接触也不过流于形式。博览会上的一切是热闹的,但同时也是混乱繁杂的,忽视了客观事实而只以预设的结论去观察博览会显然是不诚实的。
此外,在书中还有华莱士对电视、电影、美国小说的评论,然而这些文字也总给人一种“消极”的感觉,他似乎总能自然地看到“月球的背面”。(当然,月球的背面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人们忘记了或者不愿提及。)由此,可能有人会将华莱士看作天生的悲观主义者。的确,他仿佛对快乐(甚至更多)持有怀疑态度,总会敏锐地捕捉到不相符的信息,用惊人长度的注解去否定自己,否定那些想当然的结果,但细致去看可以发现,他并不是怀疑其存在,而是怀疑人们趋之若鹜的并非快乐。
所以,他并不是悲观主义者,而是细心的、传统的人。我们无法判断这是否与他的抑郁症有关,但可以肯定的是,具有这种能够细细分辨事物的特性并不轻松,就像听力范围覆盖了“次声”“超声”的人,这样的超群能力使他获知甚多,也使他的夜晚更不安宁,同时,他对于这些信息的反馈也自然与众不同,无法匆匆得出结论,至少无法得到浑然无知者的结论。
2008年9月12日,才华横溢同时又饱受抑郁症折磨的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在家中自缢身亡,年仅46岁。文坛失去了一位奇才,世界也失去了一台极为灵敏的雷达,人们再也无法看到他去体验那些所谓好玩的事,无法看到他出自真诚却让人莞尔以及耳目一新的见解。
再细细翻阅大卫·华莱士的作品,想到以他的狡黠与忠实,他或许想把这句传递给我们琢磨:我大概是快乐的吧。
《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读后感(十):隐藏于偏执外衣下的孤独与自由
文/R郭郭
《所谓好玩的是,我再也不做了》是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一本非虚构经典文本,这本书收录了华莱士从1990年到1996年之间的七篇散文,两篇最不像游记的旅行日志,两篇与网球有关的科普大全,两篇关于影视的文学评论,最后一篇文如其题《天花乱坠》。如果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记者用纪实的手法所书写的论述性散文的话,那可观性就会大打折扣,但这本书带给你的不只是这些,你不仅能看到相对客观的叙事描写,还能够欣赏到除此之外作者基于这些客观之上的带着些对于哲学和人生的思考,这本书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在索然无味和无聊透顶当中,风趣、诙谐,还带点黑色幽默,每一篇都会让你回味无穷。惊讶于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对于物品的描述详尽到极致,无论是尺寸、品牌、品质等方面,在读者面前呈现了一种几近完全的具象,即使没有见过的人,也能够第一时间跟随作者的叙述想象物品的样貌,可能是记者的职业病,华莱士的身边总是带着纸笔记录所看到的一切,并如实报道。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想他是唯一一个将数学理论化为优美几何图像来欣赏的网球种子选手,若不是在青春期的一场锦标赛中的失利,或许我们今天就少了一位文坛鬼才。华莱士就像蛰伏在大众之中的一个普通人一样,但是建立在客观和幽默之上的叙事手法就能让他独树一帜。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是个幽默感十足的人,这本《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一书中,在与书名同题的文章里,他用“癫痫发作”来比喻孩子们们对于游乐场的喜爱,从“渡轮排队”这件事也能联系到奥斯维辛的纳粹份子,如果说这是一种黑色幽默的话,我觉得还不是最贴切的赞誉,辛辣地讽刺可能才能够说明他的用意。华莱士是一个集荒诞和怪异的想法于一身的作者,若不是记者的身份作祟,我必然会觉得这是一个患有“生活妄想症”和“半广场恐惧症”(华莱士自己标榜的)的介于天才与疯子之间的不正常人类。
在大卫·福斯特·华莱士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他作为一名作者的偏执,这里的偏执不是指刁钻古怪的脾性,而是华莱士作为一名作者对于事物的表象之下探索事物内在联系的一种严谨和极致的态度,这绝不是一种诋毁,而是由衷的赞美之言,在这本《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当中,《旋风谷的衍生运动》以及《众目窥一:电视和美国小说》这两个篇章将这种偏执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严肃的文字不是一种游戏,而是发自内心深沉而又冷静的思考,将这份思考不失毫厘地准确表述,我想这是华莱士最具魅力的地方。
如若偏执是缘由认真而又极致的态度,那么隐藏于偏执之中的那一份孤独就是守护这份态度的真挚表现,这种孤独不是标榜特立独行的怪异,而是将这一份偏执的冲动执行到底的坚持,保留客观的刻印,在此基础上坚守对于文字的忠实,我们在这其中还能嗅到一点自由的味道。弗吉尼亚·伍尔夫曾说“自由精神才是书籍圣殿里的生命气息”,华莱士在这本书中为我们实践了这句话。无论受邀于游轮公司还是采访于博览会现场,甚至去好莱坞大导演的家中,华莱士在文中都没有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写作就仅仅是写作,不受任何外力因素的限制,在写作上的这一点自由就让我觉得特别具有独立精神。
他的偏执、他的孤独和他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认真、极致、忠实、谦逊,也是我们在他身上能够看到的美好品质,我想作为一名写作者,他身上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学习,若不是他于2008年就离开了我们,我其实特别期待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如何看待现代互联网和美国小说之间的关联,或许这又能变成一篇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