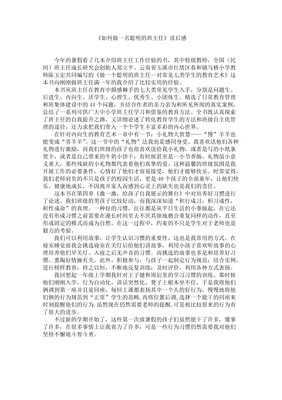《马桥词典》的读后感大全
《马桥词典》是一本由韩少功著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5,页数:40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马桥词典》精选点评:
●《马桥词典》真的太牛了,以词典的形式从日常用词、文化上进行虚拟,再用创造的词汇和文化习俗讲述马桥发生的故事,每一个在词典中出现的词再运用的时候,对人物的描写和故事的叙述就会比准确更准确,因为还有哪样的词能比与人物在同一文化环境下而创造出来的更无比准确呢?笔力和敢言也是非常牛!
●以这样的形式从湖南方言中挖掘出如此多的内涵,令读者感到耳目一新,也令我等湖南人觉得甚为亲切。这本书让我真正看到方言的魅力,它折射出的不仅是一城一地的生活习惯,更涵盖了这座土地上人们的全部物质精神文化和意识形态。
●读完才知道,我们对很多词的理解,还跟肤浅。
●沉醉其中……
●为了写论文又读了一个版本 莫名开心
●万玉那一段读得让人想哭(┯_┯)
●韩少功和他的《马桥词典》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是独树一帜的,它制造了一种全新的文学定义和小说书写模式,当然拓展了当代文学的面向,尤其注重了以一种“凌驾”的视角谈论了语言及意义层面的哲学问题,对言和象的探寻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对处在封闭困难生存重压下的人格裂变做了详尽的描绘。但这不能掩盖作品内容本身在永恒性上的憾缺——比如,小说中姑且称之为“民俗学读本”的部分的刻画,是远胜于其“作者文本”部分的。在新批评越来越强调“文学”的自发性、可解性、丰富性而否认作者的操控与过度议论时(甚至插入了科学话术),韩少功显然没有过于超前的认识。
●文学化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作品见多了,文学化的语言人类学作品还是第一次见。而且对语言的理解,是见功力的。
●第三次拿起此书,终于看下去了。几年前看书是看连贯的故事情节,而现在,在经过西方文论的洗礼后,终于关注点可以放在语言上了。甚至可以说语言构造了这个世界,韩的创造性尝试无法归到九十年代的任何一个派别去。
●从某种意义上说,较之静态语言,编撰者更重视动态语言;较之抽象义,编撰者更重视具体义;较之规范性,编撰者更重视实用性。这样一种非公共化或逆公共化的语言总结,对于公共化语言成典,也许是必要的一种补充。
《马桥词典》读后感(一):马桥词典
当乡土的呜咽再无法升起半个月亮亦驮不住失意的黄昏,那些苍老的语言与记忆又该何处保留?而当我看完韩少功的这本《马桥词典》,我想,像这样,为乡土与方言立传立典,确实成为一种好办法。《马桥词典》,顾名思义,将马桥这个地区(虚构)的方言与人物入典,以期许保留马桥的人文风俗。虽是小典,以故事记叙入文,却莫名拥有大典没有的气势,像一卷收不尽的羊皮地图,即便到了末尾,还留有余音,作册千秋。这本书一共收录了115个词条,以笔画数量作序,其中不少词条新颖大胆,从思想的背面赋予词语新意,闪现着马桥人民的睿智光辉。(247字)
《马桥词典》读后感(二):语言,就是一部活生生的生活史
真正奇书,相见恨晚。。。我觉得应该拿黑格尔哲学奖~~~
语言和文字,是有一种魔力的。。。成也语言,败也语言;人之为高等动物,就在于会运用语言。
书中人物的性格和生活,鲜活明亮,特点突出,各各不同,引人入胜。但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作者成功描绘了一个完整的闭环乡村社群的生活状态,给在如今的大城市物欲生活中迷失和颓唐的人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的风景。
人的社会化,是一件很复杂很精妙的事情,而语言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的自然农村生活,自有文明以来,已经传承了有上万年了吧。即使农村物质生活匮乏(大概主要是因为资源有限、人口增殖),农村的精神生活、集体生活、邻里关系、社会结构等等等等,仍有多处值得学习和深思的地方,仍有巨大的营养价值可以汲取。
马桥人的哲学,颇有些辩证主义的味道。比如说“醒”指愚蠢,“觉”(qo)指聪明,“梦”指神明;不思进取、消极颓废叫做神仙;男子十八岁和女子十六岁以前叫做“贵生”,男子三十六岁和女子三十二岁以前叫“满生”,再往后就是“贱生”了,不值价了;“怜相”是漂亮;男人叫作“蛮子”;科学”意味着懒惰和嫌恶;等等。
在马桥,时间是静止的。传统的农业社会生活,一成不变,周而复始,轮回不休。
盐早因为地主家成份出生,吃尽了苦头,没有人搭理,最后竟然成了个哑巴。盐早的父亲茂公太自私,当过汉奸和地主,为人刻薄,跟乡民关系恶劣,祸及子孙,可叹可悲。人啊,还是不能脱离社会而生存。
万玉是顶顶好的人,因为少年不幸成了阉人,老婆不亲,小孩不养,好跟女人打成一片。村里面好多人欠他工钱,最后却死于贫穷。死后才真相大白,女人为她悲哀,男人也觉得错怪了他。
丐帮头头戴世清和他的女儿铁香,都是既有个性的人。丐亦有道。还有就是,人不能轻易的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否则身体上或者精神上一定会出问题。铁香跟三耳朵私奔,三耳朵是马桥村的弃儿,然后却重义气、明是非;虽然最后做匪双双身死,但马桥村关于铁香的传说,证明了村里还是有些人对她有种莫名的敬佩和同情的。
“黑相公”牟继生,作为知青,跟当地人起了文化冲突。当地人认为跟他借个种、生两个壮娃,没啥大不了;知青却觉得根本无法接受。然后他也中了语言的蛊,回城之后也没好起来。
兆青七八个娃崽,生活很艰难,因此也迸发出顽强的生命力,也很懂得爱惜物力人力。只是太抠门,结局悬案一桩。本义虽然嘴巴上不满他娃崽太多,但是估计全村人心里对他都是羡慕嫉妒的要死。
马鸣是个神仙府里的神仙,也就是个流浪汉。但是他对自由的追求,对村人单调无望的生存方式的鄙视,对文字知识科学的执着,仍然证明他是个活生生的人。也许在外面更大的世界里,会有属于他的位置吧。
当然,马桥也有藏污纳垢、封建落后、冥玩不灵的地方,乡村和农民的劣根性和落后、愚昧,勿庸赘言。但我们也要明白,我们不能用旁观者的态度来要求当事人去如何生活。那样的话,马桥就不成其为马桥了,马桥就是另外一个无聊的市镇了。我们这些习惯了现代化的城里人的生活的人,是否还要多从马桥人身上学到人做人处事的本源性、人格性、善良性、责任性、等等的品质呢。因为毕竟在那样一个闭环熟人社会里,人是无法伪装和掩饰的,也不能装作对别人无动于衷、不闻不问、心安理得。。。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故事是灵魂的血肉。人类的生活,永远离不开听故事和讲故事。
《马桥词典》读后感(三):愿每一片乡土都有一部词典
《马桥词典》是一部可以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
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是一部亲切而让人激动的词典体小说。韩先生以上山下乡时期自己所在的位于湖南汨罗县马桥村的公社为背景,从这段本身并不愉悦的经历里创造了一部意义非凡的作品。通过这部词典,作者为马桥的也为大家的文化,历史,语言留下了印记,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世界的工具。虽然韩先生自己开玩笑说有的书店店员错误地把它放在词典类别里,但这应该不算错。正如作者自己意图的那样,马桥词典是公共话语言词典的一种补充。它实质还是一部词典,一部为马桥这个小村寨编撰的词典。在词典中,作者也对仅流传于马桥的词和不限于马桥的词做了区分。
《马桥词典》里收录了115个词汇,以词汇而窥马桥。如果说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说的是村落经济,吴毅的《小镇喧嚣—— 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谈的是政治,《马桥词典》则是一个综合体。作者利用这一个个,一串串词,呈现给读者马桥村这个四十来户人家的小社会里的各个层面,包括人情往来,生产娱乐方式,哲学态度,性别关系,等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者通过一个村寨里的具体的词汇来体现语言与事实的复杂关系,与生命过程的复杂关系。比如,女性的社会地位就可以从关于女性的词汇里一窥一二。
在马桥,不存在女性词。与女性相关的亲系称谓也是完全男名化,在男性称谓的前面冠以一个“小”字。比如,“小哥”意指姐姐,“小”弟意指妹妹。这种规则与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之类的古训不谋而合。作者怀疑这种女性词完全取消的情况与当地妇女的行为方式有着密切关联。据作者观察,马桥妇女们习惯于粗门大嗓,为梳妆打扮而羞愧万分,羞于承认自己的女性特征。
作为中国本土小说,相比于西方小说,《马桥词典》的画面感很强。一个小小的词汇,与之想对应的情境会立马浮现于脑海,整个故事发生地的面貌也能一一清晰得架构起来。同时也建议湖南的或者是说湘语的读者们在阅读的时候把词条用自己的本地话读出来,然后对比这个词在本地话里的意思与马桥词典里的解释。可能你会发现他们的意思尤其的相似。这时,你一定会为韩先生这个外地人对这些词语的精准理解而惊讶,转而欣喜若狂。尤其时当你读到“醒”,“流逝”,“宝气”,“呀哇嘴巴”,“渠”,等时。当然词典里也有一些你也从来没听过的或许已经消失了的词。
普通话的普及,不断威胁着方言的生命力。话说,我的侄子侄女们已经不会讲我们当地的宝盖话了。他们不知道很多我熟知的词汇。而我也在逐渐忘却这些原本熟悉的词语。我们太慕新了,太想脱掉自己身上的土气,以至于忘了自己是谁。可能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但是还是希望至少能把这些方言留在博物馆里。同时也希望出版社能多出版一些方言词典。多媒体已经非常便利,希望我们的方言可以通过语音与影像的方式保留下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不会因自己的出生地而自卑了。让会说方言成为一件值得炫耀的事。
俗语说,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我们寻常百姓虽如蝼蚁,但同时也在塑造我们自己的语言,我们的生活环境与社会,我们自己的历史。然而我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会化作泥土。我们塑造的世界也随之消失,没有任何记录。而马桥的人与语言被记录了下来,向历史证明了他们的存在,多么幸运啊!
因此,愿每一片乡土都有一部词典,也愿每一个人都有一部自己的词典。
《马桥词典》读后感(四):马桥词典词典
2017年10月,这书甫一重印,便在Pageone发现了它,封面设计太优秀了。读的书不多,甚至连韩少功都是通过高中做语文试卷上的现代文阅读某段《山南水别》才认识的。
由于是湖南人,我很容易在书中发现熟悉的词汇和语言,亲切感十足。除了塑造志煌、本义、盐早一个个深刻而有趣的角色(及其故事)之外,本书对语言的关注、认识,拔高了这篇小说(虽然的确很像是真实故事)的意义,成为了生活词典之上的语言词典。部分令人印象深刻的话语如下:
语言看来并不是绝对客观的、中性的、价值缺位的。语言空间在某种观念的引力之下,总是要发生扭曲。女人无名化的现象,让人不难了解到这里女人们的地位和处境,不难理解她们为何总是把胸束得平平的,把腿夹得紧紧的……对女人的身份深感恐慌或惭愧。正是体会到了这一点,执政者总是重视文件和会议的。文件和会议是保证权利运行的一个个枢纽,也是强化话份的最佳方式。文山会海几乎是官僚们不可或缺并且激情真正所在的生存方式。即便是空话连篇的会议,即便是没有丝毫实际效用的会议,也往往会得到他们本能的欢喜。道理很简单,只有在这种时候,才会设置主席台和听众席,明确区分等级,使人们清醒意识到自己话份的多寡有无。权势者的话语才可以通过众多耳朵、记录本、扩音器等等,得到强制性的传播扩散。也只有在这种氛围里,权势者可以沉浸在自己所熟悉的语言里,感受到权利正在得到这种语言的滋润、哺育、充实和安全保护。他们瞪大眼睛,只是对马克思著作里(这本书再版时删去了“马克思著作里”六个字,嘻嘻)一切听不太懂的语言恼怒,感到他们的话份正在受到潜在的威胁和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主义艺术声势浩大,抽象画、荒诞剧、意识流小说和超现实主义诗歌惊世骇俗,嬉皮运动、女权运动,还有摇滚乐等等异生的文化现象也随之而来。有意思的是,这些新现象出现时差不多—一都被视之为邪恶的政治陰谋。资产阶级的报纸攻击毕加索的抽象画是“苏联企图颠覆西方民主 社会的罪恶伎俩”,“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宣传”,而摇滚歌手“猫王”爱尔维斯和“披头士”代表人物列农,被教会和国会议员们疑为“共产党的地下特工”,目的是“要败坏青年一代,使他们在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未战先败”——他们的音乐在美军驻欧基地一直是禁品。在另一方面,任何红色政权也做着差不多同样的事情,现代艺术无论雅俗,几十年来也一律遭到官方的批判,官方文件和大学教科书将其定性为——“和平演变的先锋”,“西方国家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的精神毒品 ”等等。这些性语词无疑是人类性感粗糙化、公式化、虚伪化、鬼鬼祟祟化的结果。两性交流过程中涌动和激荡,来自身体深处的细微颤动和闪烁,相互征服又相互救助的焦灼、顽强、同情及惊喜,暗道上的艰难探索和巅峰上暴风骤雨似的寂灭之境迷醉之境飘滑之境(活跃于各不相同的具体部位、具体过程)……这一切一直隐匿在语言无能达到和深入的盲区。 一块语言空白,就是人类认识自身的一次放弃、一个败绩,也标示出某种巨大的危险所在。语言是人与世界的联结,中断或者失去了这个联结,人就几乎失去了对世界的控制。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完全可以有理由说,语言就是控制力。一个复杂的化学实验室,对于化学专家来说,不过是一块熟悉的菜园子;对于毫无化学知识的人来说,则不啻于危险无处不在的可怕雷区。一座繁华的城市,对于本地市民来说,是无比方便和无比亲切的故土,但对于毫无城市经验的乡下来人而言,无异于处处隐藏着敌意或障碍的荆天棘地,让他们总是摆脱不了莫名的惶恐。其中的原因十分简单:一个难以言说的世界,就是不可控制的世界。人并不怕展示自己的身体。在洗澡堂、体检室、游泳场甚至西方某些国家的裸泳海滩,人们没有感到什么不自在也没有畏惧。人只有在性交的时候才感到关闭窗帘和房门的必要,像一只只企图钻进地洞的老鼠。形成这种差别当然有很多原因。在我看来,其中一直被忽略的原因,是人们对洗澡、体检、游泳一类活动有充分的语言把握,也就有了对自己和他人的有效控制,足以运作自己的理智。只有当人们脱下裤子,面对性的无限深广的语言盲区时,不安全感才会在不由自主的迷惑和茫然中萌生,人才会下意识地躲入巢穴。他们在害怕什么。与其说他们害怕公众礼教的舆论,毋宁说他们在下意识里更害怕自己,害怕自己在性的无名化暗夜里迷失。他们一旦脱下裤子就同样会有焦灼、紧张、惶乱、心悸、血压升高、多疑和被窥视幻想,如同他们投入了一心向往的巴黎或纽约,但要把寓所的门窗紧紧关闭。语言迷狂是一种文明病,是语言最常见的险境。指出这一点,并不妨碍我每天呼吸着语言,吸吮着语言,在语言的海洋里毕其终生,被一个个词语引人新的思维和感觉。一次次对那次辽宁之行的回想,只是使我多一点对语言的警:一旦语言僵固下来,一旦语言不再成为寻求真理的工具而被当作了真理本身,一旦言语者脸上露出自我独尊自我独宠的劲头,表现出无情讨伐异类的语言迷狂。当然,还有非常细腻的描写:
散发:准确、生动、细腻地透示出一个过程。生命结束了,就是聚合成这个生命的各种元素分散和溃散了。比如血肉腐烂成泥土和流水,蒸腾为空气和云雾。或者被虫豸噬咬,成为他们的秋鸣;被根系吸收,成为阳光下的绿草地和五彩花瓣,直至成为巨大辽阔的无形。我们凝视万物纷纭生生不息的野地时,我们触摸到各种细微的声音和各种稀薄的气味,在黄昏时略略有些清凉和潮湿的金色氤氲里浮游,在某棵老枫树下徘徊。我们知道这里寓含着生命,无数前人的生命。这就很像熊培云所描述过的,乡村的魅力就在于生人与死人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生命的周而复始在一个村落里体现得明显。我知道这颗泪珠只属于远方。远方的人,被时间与空间相隔,常常在记忆的滤洗下变得亲切、动人、美丽,成为我们魂牵梦绕的五彩幻影。一旦他们逼近,一旦他们成为眼前的“渠”,情况就很不一样了。他们很可能成为一种暗淡而乏味的陌生,被完全不同的经历,完全不同的兴趣和话语,密不透风坚不可破地层层包藏,与我无话可说——正像我可能也在他们的目光里面目全非,与他们的记忆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