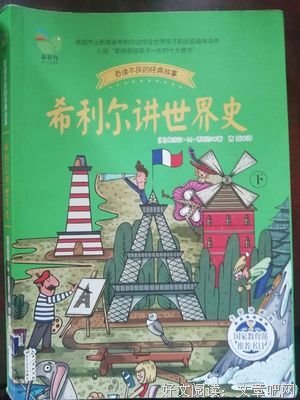《10½章世界史》的读后感大全
《10½章世界史》是一本由[英] 朱利安·巴恩斯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页数:33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10½章世界史》读后感(一):宝藏
异彩纷呈,立意广阔。《偷渡客》从木蠹的角度反人类中心主义;《不速之客》以阿拉伯人的立场反白人中心主义;《宗教战争》为木蠹申辩——文学史上难得的人类为昆虫发言;《幸存者》是我最爱的一篇,一个受家暴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对婚姻心灰意冷,幻想出核战争,带着猫咪离家出走,故事虽然残忍,但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边缘群体的人文关怀;《海难》让我想起《The Open Boat》和《蝇王》,节奏很快,平铺直叙人性的阴暗面,叛乱、食人肉、吃屎喝尿、谋杀,应有尽有;《山岳》和《阿勒计划》相互呼应,阿曼达在寻找诺亚方舟的途中感受到上帝的召唤,自愿在能看到月亮的山谷中结束自己的生命,她的尸首被同样受到上帝召唤的前宇航员斯派克误认为是诺亚的尸骨;《三个简单的故事》分别讲了一个男人乔装为女性从泰坦尼克号逃生、约拿被鲸鱼生吞、二战时满载着犹太人的轮船被各国拒绝的故事;《逆流而上》揭示了男人从恳求到翻脸的转变是多么迅速;《插曲》写了作者自己的恋爱观:爱情并不能让你幸福,只是开启了你感知幸福的能力;《梦》幻想了天堂的样子(地狱并不存在)——就算让一个人想怎么活就怎么活,TA也会有厌倦想死的一天。每个短篇的人物、情节、背景、立意都迥然不同,甚至文体也大相径庭,但共享了“方舟”这一条主线,诺亚方舟、木蠹、“洁净与不洁净”、上帝等意象贯穿全书。作者解构历史,揭露单一叙述的荒谬,但又带着人文主义的温情,不会陷入虚无主义。BTW,钻石公主号的遭遇又是一个完美契合这本小说的素材,希望巴恩斯能再补上一章。
《10½章世界史》读后感(二):巴恩斯这个木蠹就是苏格拉底——雅典人的牛虻
历史在记录时不可避免地会遗漏一些细节或者虚构某些情节,从而简化事件和人物,最终可能会误导后人对某一段历史的评价。巴恩斯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编造出故事来掩盖我们不知道或者不能接受的事实;我们保留一些事情真相,围绕这些事实编织新的故事。我们的恐慌和痛苦只有靠安慰性的编造功夫缓解;我们称之为历史”,这一点在故事中不断地重现。
《偷渡客》以木蠹的口吻来回忆诺亚方舟那段历史,大洪水中保留世间万物的诺亚在它眼里就是个粗暴的酒鬼;
《不速之客》涉及1985年“阿基列 劳罗”游轮被恐怖分子劫持事件,借恐怖分子之口批评某些历史被掩埋;
《宗教战争》则以法庭诉状信件回忆1520年路德被教皇开除教籍事件,讽刺的是最后的法律判决书竟然被白蚁所啃噬;
《幸存者》将1986年切诺贝利核电站泄漏和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两个事件联系起来,各自都陷入了所谓的幻觉当中;
《海难》前半介绍1816年梅杜萨战舰沉没的历史事件,后半讲解几年后的《梅杜萨之筏》画作如何一点点去掉历史的细节;
《山岳》,《三个简单的故事》,《逆流而上》,《阿勒计划》和《梦》则相对虚构,但也一直呼应着“虚构的历史”这一主题。
木蠹讽刺但也悲怜地说:“你们这一族也不太会说真话。你们老是健忘,或者假装健忘。法拉第和他的方舟失踪了,又谁提起过?我知道这样视而不见可能有它好的一面:不去理会坏事可以活得更轻松些。可是,不理会坏事,到头来你们就以为坏事从来就没发生过。一有坏事出现,你们就大吃一惊。枪炮杀人,金钱腐蚀,冬天下雪,你们都大惊小怪。唉,这样天真幼稚会很讨人喜欢,但也会有灭顶之灾。”在一点上,巴恩斯这个木蠹就是苏格拉底——雅典人的牛虻。
:就文笔而言,《宗教战争》最有趣味也最反讽;就主题而言,《海难》最直接表明巴恩斯的观点。
《10½章世界史》读后感(三):诺亚方舟为何驶出了艺术史?
香港作家西西的短篇小说集《胡子有脸》中收录了一篇《图特碑记》,以史官为叙述者,虚构了一位古埃及帝王的一生,从部落兴起、结盟,到讨伐征战,再到王朝覆灭,全文不过两万字,读来却好像是《史记》或《权力的游戏》中遗漏的一章,有一种宏大而无奈的史诗感。可惜篇幅太短,总觉得不过瘾,一直想找一本虚构的世界史来看,所以当初一见到这个书名,就毫不犹豫地买了。
全书由十个暗藏脉络的故事和一篇作者以第一人称夹叙夹议的插曲组成,令人失望的是第一个故事和最后一个故事,前者虚构了诺亚方舟上的一只混上船的蠹虫,后者则想象了一个任何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的天堂。可能是由于架空了历史,又缺乏细节,这两篇读来总觉得有些尴尬——作者似乎有心玩“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虚构游戏,却由于缺乏说服力,读者只觉得太假,无法进入作者设想中的语境,双方都很努力,像一对过分执着又缺乏缘分的情侣。
不过第一个蠹鱼重述诺亚方舟的故事似乎不可或缺,后面的每个故事都与方舟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是洪水退去,诺亚和他的动物们繁衍出的各地子民,他们的故事不断重复着毁灭与得救的主题。在《海难》一篇,作者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西方经典艺术作品中,为何少有人描绘那艘以歌斐木打造的巨型方舟?
在中世纪教堂的壁画、柱头和镶嵌画里,我们很容易发现对诺亚方舟具体而微的描述,一直到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教堂,“方舟第一次失去了构图上的突出位置,一直推到画面的后部”,前景是各种没能进入方舟、注定被撇下等死的动物。象征得救的方舟自此开始淡出艺术史,画家们越来越集中地表现被抛弃者,而不是被拯救者,在普桑的《洪水》里,方舟已消失无踪。
《10½章世界史》读后感(四):小说家药丸①:脑力开发过度
朱利安·巴恩斯的写作向来很有趣。这种禀赋实则继承自英国文学的光荣传统:挖苦调侃,看似一本正经,实则玩世不恭;故而,“毒舌”多出于此传统。此中也可见英人之“虚伪”,内在的小算盘小心思与外表的绅士风度实相分离。就书名“10½章世界史”来看,巴恩斯的目的是通过小说戏拟世界史。至于庞杂的世界史如何通过几章小说写成,看过的读者自有认知。此不赘述,想谈谈本书的写法。这是我尤来有兴趣的。
我曾今设想过一本小说,是通过设计多个叙述者完成的。非多视角叙事,比如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而是借助对多个叙事腔调的模拟,来瓦解一本小说因完整声音贯通所形成的整一性。也许会是很普通的不同片段之拼接,但也有可能因此碰撞出具有丰富意涵的复调小说。前者,看起来已经被巴恩斯实践了。
这10½章的文字,每一章都可谓模拟了不同叙述者可能发出的声音。《偷渡客》中那只虫子的声音,为我们展示了与《创世纪》中“诺亚方舟”不一样的故事,阅读的趣味正来源于此,我们因为可以通过这些细碎的感觉和思索生成为虫子,进而获得现实中不能拥有的感知能力。其它几篇,则由人称变化(第三人称、第二人称),结构形式(诉讼文件、书信等),体裁(传说、寓言等)这些不同变种而完成,每一章的叙述者均相异。
有人也许以为,这只是一种司空见怪的后现代小说“拼贴”的手法,但我们若能以叙述声音的角度去观看,巴恩斯的创作实有其独特之处。”拼贴“之机械,往往得之于形式上的考量,比如《尤利西斯》文本背后贯穿始终的那个叙述者;而巴恩斯显然拥有更多天赋,比如模拟人之外的其它物种之发声,各类人种的说话方式等等,全书因而不再有预先设定的统一叙述者作为基础,而是令小说真正以不同的片段来回击”世界史“这一主题。
这是巴恩斯的野心,也反映出其”聪明“。一个脑力过于强盛的小说家,其危险就在于过于热衷地卖弄其创作技法,而这正是我们要对这本小说的作者提出的批评。小说家的脑力一旦开发过度,或来不及用心力来平衡,将导致一类“叙述机器”的诞生。在波拉尼奥的小说中,我们已不再能辨明到底是作为人的波拉尼奥在写作,还是那台机器。
巴恩斯也有此困境。当其用高智商调侃、挖苦历史文明,与读者玩着阅读游戏之时,稍有不慎便有玩得过火之嫌疑,因而有将文本硬化为石头之危险。我们有责任为我们的小说家指出明路,给他推荐几位前辈(或同辈),来均衡两股力量的交锋。这种义不容辞的任务只能马上履行:他们是普鲁斯特、纳博科夫、约翰·班维尔、科尔姆·托宾等;并祝愿巴恩斯尽早能骑马快行。
《10½章世界史》读后感(五):掉入历史的罅隙
看了《终结的感觉》后觉得想再多了解下朱利安·巴恩斯的历史观,于是又撸了《 10½章世界史》,原来是个短篇小说集,一章一景,但前后各章都有呼应,每个故事题材体裁手法各异,但都互为亲戚,用流行音乐的话讲有点像“概念专辑”。这样的小说初看起来还是很好玩,也适合目前低头一族的“碎片化阅读”。因为没啥宏大的叙事、庞杂的情节人物、深刻的意义这类玩意。虽说探讨的主题是严肃的,但形式的轻盈的,角度是刁钻的,行文叙事是偏门的。 不过撸了一段时间后,作为三俗观众,还是觉得有点缺乏那种畅快的阅读感,因为写法的不断变化,需要你不停适应作者的新花样,有些花样非常抓人(比如《宗教战争》里的动物代理人在宗教法庭上的辩词、《海难》从对遇难者的心理侧写笔锋一转到对名画的细致分析),有些则一开始难以进入(比如《阿勒计划》因为充斥着英国人想当然中的“美国人很庸俗浅薄”的diss味进而让行文也变得乏味起来)。有时看得很high,有时又昏昏欲睡几乎想弃,好在坚持撸完还是觉得充满回味。
作者本人似乎有深厚的历史学术素养,但其对历史的态度显然不是什么“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那个½章《插曲》里,作者坦诚了历史观:
历史并不是发生了的事情。历史只是历史学家对我们说的一套。有程式,有计划,有运动,有扩张,有民主的进程;是织锦挂毯,是一连串事件,是繁复的记述,互相关联,可作解释。一个好故事接着另一个好故事。先是国王和主教们,加上台下神灵凑几分热闹,接下去是各种思想观念的行进和一场场群众运动,再往下是局部小事件,意义并不小,但始终都是互相关联,进步,也就是说,这个导致这个,因为这个而发生了这个。我们是历史的解读者,历史的受害者,我们审视历史程式,为的是发现给人以希望的结论,找到前进的路径。我们紧抱住历史不放,把历史当做一系列沙龙绘画,一段段谈话,其中的参与者可以通过我们的再想象轻而易举地回到生活中来,但历史向来更像是多种媒体的拼贴,涂油彩用的是粉刷滚筒,而不是驼毛笔。世界历史?不过是一些回荡在黑暗中的声音;炫耀几个世纪而后淡去的形象;故事,有时似乎重复的老故事;奇怪的联系,牵强附会。我们躺在当今的病床上(如今我们有这么好的洁净床单),每天的新闻点点滴滴不断注入我们的手臂。我们以为自己知道自己是谁,虽然我们不完全知道我们为什么在此,或者我们还要被迫待上多久。我们在绷带缠缚的前途未卜中烦恼翻腾——我们是否心甘情愿做病人?与此同时,我们虚构编造。我们编造出故事来掩盖我们不知道或者不能接受的事实;我们保留一些事情真相,围绕这些事实编织新的故事。我们的恐慌和痛苦只有靠安慰性的编造功夫缓解;我们称之为历史。以上看似一些轻巧的漂亮话,但人家多年专业学术研究的心声与一般瓜众的吐嘈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在这种前提下审视这部小说集,这10来个故事看上去也就是“保留一些事情真相,围绕这些事实编织新的故事”,一些充满“恐慌、痛苦和安慰”的故事。
《10½章世界史》读后感(六):故事新编
《偷渡者》---诺亚方舟。 上帝挑中诺亚一家(包括家畜飞禽走兽)逃离大洪水。然后,在这场逃离中,一些动物并不以此为幸运,他们开始另一场逃离,逃离方舟逃离上帝。
这是政治寓言。政客们牙尖嘴利老谋深算,连环陷阱一个接一个,帮闲吃里扒外抽血吸髓,有人打着政府的名誉借机生利捞钱捞名;有人看破玄机愤然离场,更多是傻傻分不清丝瓜藤和肉豆须的散户,被面前吊着的永远也吃不到的红萝卜牵着步步惊心。“诺亚方舟”从头至尾就是上帝的一场阴谋。海选搞得煞有其事,最强联姻配得轰轰烈烈,打着各路明星走着星光大道,人马蜂拥而至,再来一次花儿与少年,老少通吃,小鲜肉PK花样姐姐,满足几多老男人小女人的幻想,最后一招奔跑吧XX把孩子牢牢拴在荧屏前。娱乐嘛,博全民一笑即可,才发现,真正笑得开怀的不是屌丝,一集一百万,看,笑也是有代价的。所以最先上不了方舟的,就是清醒者和糊涂虫。
上帝选人是有技术的,这个技术就是虔诚,不要能力,不要精明,只要常汇报够虔诚。所以诺亚被选中。虽然他没有航海技能。“风暴来临他就犯傻”“他只会诈唬和祈祷”,而被诺亚选中带上方舟的动物,不过是“从此想吃我们哪一个全由他挑”。他是上帝的全权代表,所以他可以仅凭喜好就认定鸽子代言“和平”,虽然真相是乌鸦带回的橄榄枝。他喜欢恭顺的良品动物(猪羊鸡),这样即使离开方舟也可以吃他们一代又一代。我是猪“天生没有报复”,所以活该被欺负。
短短31页,堪比《动物农场》的短篇。最后巴恩斯写到“身为木蠹,不是我们的错”。
《不速之客》像富兰克林修斯提这样的,是巴恩斯讽刺的一类人。新闻播报员,他们既是政府的传声筒,又身兼娱乐主持,总之,“说”而优则“书”,四处演讲,顺便打击一下娱乐圈。接下去故事出乎意料。
旅行,遭遇劫匪,生死选择。
弗兰克林不是利他主义者,他只是别无选择。
在这场生死博弈中,富兰克林终于做了一回“英雄”,只是在公众看来正相反,就好比在屈辱条约的签订人,永远被历史深深钉牢在卖国贼的耻辱柱,世世不得翻身。在那种情形,需要替罪羊。富兰克林到底成了帮凶。他至少救过她(情人),此事过后,她再也没有同他讲一句话。“舍己为人就是这样,少不了被误解”。
《幸存者》有一种长大,就是你最虔诚的信仰某一天被最残酷的方式粉碎。
这种伤不被同情,没有道友,别人笑你太天真。他们不知道你曾有多真诚的信仰过。
她一直执着的找一个答案,而生活给她的不过是嘲笑“政治是男人的事,你不懂别乱讲”“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他们要小孩掏钱去看鱼”“连鱼都被剥削利用,然后污染中毒”“我们一定要看事物的真相,我们不能在依靠虚构,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
《海滩》对于那场海难,我们的认知仅仅停留在那幅画《梅杜萨之筏》,对于学过画画的,看到的是完美的躯体,凝重的表情,特有的落暮的色泽,娴熟的技巧,还有画里面汹涌的感情,至于画面外那个故事,到成了陪衬。
对于学法律的,只看见诉讼的可能与人性的道德之间成败的较量。而非黑白的证明。人性不可假设。那个事故是一场诉讼教材。
在小说家眼里,根据幸存者的描述,加以加工,多些惊悚多些想象,只要博读者眼球,真相重不重要又有什么关系。那场事故早已成为人们饭后的谈资,而真相就像绝望时飞来的白蝴蝶,惨白,无趣。
原来,人们只喜欢围观,围观一场灾难。
《山岳》生,身不由己;死,亦身不由己。佛格森不相信上帝,临终却要走一遍虔诚的仪式,因为笃信上帝的女儿怕父亲入不了天堂。佛格森小姐始终坚信能找到证据来超度父亲的亡灵,带着女仆,一路追寻神山的踪迹。只是受到惩罚的却是自己。佛格森小姐坚信上帝,却依旧不能选择死(按自己的意愿死),这一点,父女殊途同归。
巴恩斯用自己的语言重新演绎了历史上最著名的事件。考据已经不重要,原本就是旧瓶装新酒。渗透了现实的历史。
《10½章世界史》读后感(七):《10 1/2章世界史》: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文/吴情
每次说到英国著名小说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很多读者或者评论家脑中头一个跃出的词便是“聪明”。殊不知,聪明人往往尖刻刁钻,恃才傲物者大有人在。好在巴恩斯克服或者说避免了这一点,代之以英国绅士的优雅与从容。不过,优雅从容之外,巴恩斯,其讽刺才华也堪称卓越。
巴恩斯从不自我重复,《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 Parrot)、《柠檬桌子》(The Lemon Table)、《终结的感觉》(The Sense of Ending)、《英格兰,英格兰》(England, England)、《脉搏》(Pulse),《10 1/2章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 1/2 Chapters),巴恩斯总是在书写新的主题,总能呈现出新的结构、新的风格,让读者眼前一亮。
《10 1/2章世界史》从体裁上看应为长篇小说,只是与读者通常熟悉的长篇小说有所不同,其中的十个章节可以独立成篇,还包括半篇(?“插曲”)随笔性质的作品。十个故事外加半篇随笔,虽然都可以独立成篇,但在情节上存在一定的联系。比如,第一章“偷渡客”中的木蠹,其后代成为第三章“宗教战争”中的被告,第六章“山岳”中父亲在弥留之际时,听到的虫类交配声。一部世界史?巴恩斯似乎颇有雄心。从史前到现代,漫长的历史,一部译成中文也不过十九万字——英文原文也就更短的小说,如何能够为读者绘制一副世界史的大致样貌?更何况,这是部小说,而不是导论性质的历史读物。巴恩斯,未免太过狂妄了吧?
第一章“偷渡客”以一只藏在诺亚方舟中的木蠹口吻,讲述了它在大洪水时期的艰难生活,为现代读者剥离了《圣经》对人类老祖诺亚的美化,还原了他的真实面貌——嗜血、残忍、麻木、粗鄙。第二章“不速之客”则书写的是一次恐怖分子的杀人事件,恐怖主义,这一为现代人诟病的威胁,如何挑战了人心的良善,毕竟,如果暂时只将其视为一种极端的状态?可以看出,威胁生命时,利己主义轻易战胜了哪怕最低要求的利他主义(在外人看来如此),自然而然。第三章“宗教战争”围绕的是一场宗教裁判,原告是村民,被告是木蠹。原告和被告的辩护理由都很充分,其根据宗教教义进行的观点交锋、对峙,似乎永没有结束之时。作为西方人道德来源之中很大一部分的宗教,是否常会这般将人类的生活置于类似的窘境?
第四章“幸存者”书写了核战争一触即发的特定历史时间内一个普通人内心的震颤与惊怖。在外人看来,她——一个“听到什么信什么的女孩子”,似乎有些魔怔,总在逃离身边一切;但在核战争的阴影下,一个人所能做的,难道不正是毫无目的地逃离吗?现代人的宿命吗?第五章“海难”则把笔触伸向了艺术品与一桩著名的海难事故。艺术品应当如何描绘灾难?是传达痛苦,还是把痛苦变成艺术让人欣赏膜拜?或者可以这样问,有灾难艺术品一说吗?灾难是苦涩的,就不应该成为在博物馆陈列的艺术品——美的(在审丑的习气未开之前)?第六章“山岳”讲述了一个教徒女儿为去世的非教徒的父亲远赴圣山,为他“超度”的故事。在超度之旅的结尾,女儿选择留在圣山独自接受最终的宿命——死亡。亲人之间的感情联系,由此融入了一种更为崇高的范畴。
第七章“三个简单的故事”呈现了三个与葬身鱼腹有关的故事,似呼应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阐释:历史经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第八章“逆流而上!”则书写了一个演员在丛林中的拍摄经历,以及他感情破裂的故事。从一开始,他就不断给对方写信,只是从未收到回信,或许,从一开始,一切都无法挽回,结局只会是“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插曲则是一系列关于爱情的真知灼见——也可以说是有趣的偏见,机智巧妙而又无法复述。第九章“阿勒计划”中,主角是一个登上了月球的宇航员。在月球上,他忽然间听见一句话:“去找诺亚的方舟。”回到地球上,他对这句话着魔,人生的意义集中在了寻找诺亚的方舟,为此,他苦心孤诣出一个“阿勒计划”。可等到去了阿勒山,找到的却是疑似诺亚的骸骨。他并不因此灰心丧气,第二次“阿勒计划”应运而生。第十章“梦”则写了一个住在宾馆中的人的梦与醒——他梦见自己醒来。他不断地梦见自己,“购物、高尔夫、做爱、会见名人、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永生不死”。真的是梦吗?现实之中,大多数人的生存,也不过如此。梦与醒之间,似乎并没有严格的界限。
这十个故事,外加半篇随笔,真的可以勾勒出一部世界史吗?可以,又不可以。宗教纷争、恐怖主义、核战争的阴影,这些毋宁是当下威胁人类生存根基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并且塑造着人类历史的进程。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在不断刷新着人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不过,世界史也包含一些进步因素,比如不断扩大的民主权利、文化多元主义、对边缘群体的宽容与理解。当然,说明这一点并非是苛责巴恩斯,毕竟,文学家关注的焦点是有限的。以文学的方式指出当代的弊病,追问一句: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或许是肯定世界之外,我们能做的头一件事。
如要转载,【豆邮】联系。
《10½章世界史》读后感(八):方舟之上
在圣经故事中,造物主耶和华为了惩罚充满罪恶的人类,降临了一场持续一年的大洪水。他嘱咐当时人类中唯一的善人挪亚用歌斐木建造一艘大船,带领他的家人,把各种活物分成“洁净”与“不洁”,分别带一公一母的登上方舟,以便在洪水退后繁衍生息。挪亚照做了,在洪水退后用洁净的动物祭祀耶和华,耶和华把管理万物的权利交付挪亚,并以彩虹立约,此后挪亚便在方舟停靠的地方建立一座葡萄园,继续着他们一家的生活。
不过,巴恩斯的方舟故事,却和圣经里讲述的大有不同。
依旧是上帝愤怒之下的洪水,依旧是躲避灾难的方舟,依旧是奉旨意造船的挪亚以及按规则上船的动物,不过和我们知道的那段历史完全不同了。
好吃懒做的无赖挪亚,用比赛挑选的方式选拔有资格上船的动物们,看上帝脸色行事,却暗中迫害,甚至吃掉那些优秀的“洁净”物种,在方舟上进行恐怖统治。而见证眼前这一切颠覆书中历史的,是一只本不允许出现在船上的偷渡客——木蠹。
方舟的故事,自洪水退去后仍在人类的历史中不断反复上演。上帝已经答应不再通过毁灭的方式惩罚人类,但挪亚的方舟并未从之后历史的长河中消失。
除了开篇以木蠹为主讲述的方舟故事以外,之后的这十几个故事并非是对那段历史按部就班的重复,甚至连主要情节也大相径庭。没有灭世之灾,没有传达神旨的挪亚,那艘用歌斐木打造出来方舟只在那次洪水中航行了一回,便永远停靠在阿勒山顶,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后面故事里出现的许多细节,却与那段历史微妙地重合了起来。无论是无形中存在于各处的方舟,还是洪水和上帝把万物进行的对立的分类,又或是偷渡上船的木蠹,停靠方舟的山顶,它们的存在反复地提醒着那段带有神话色彩的事件,仍在后续的历史中隐隐地重复上演。
“历史经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
尽管木蠹眼中的“方舟事件”本就没有圣经故事所描述的那样严肃,然而之后的故事里始终伴随着的“方舟事件”影子,让后续的历史如同闹剧一般,显得更为荒唐。
先说方舟。
挪亚的故事里,方舟是避难的港湾,也是噩梦的开始,之后所有的“历史”都抹不去方舟的影子。
被劫持的邮轮上,劫匪每隔一小时杀死两名乘客用以逼迫政府答应谈判的条件;因为教主坐上被木蠹蛀坏的椅子摔倒,在法庭上争执木蠹在洪水时到底有没有坐上方舟成为上帝承认且庇护的物种;凯思坐上丈夫的小船在海上漂泊,想要逃离切尔诺贝利核事件后扭曲的世界;“梅杜萨”号搁浅后船员在筏子上艰苦漂泊的过程,被籍里柯用浪漫壮烈的油画再次呈现出来;狂热的信徒阿曼达追寻方舟的遗迹;幸存于泰坦尼克事件的异装癖,从鲸鱼肚子里解救出来的水手,无处可去在轮船上漂泊的犹太人;在人迹罕至的丛林里拍摄传教士逆流而上为印第安人传教的演员;得到神谕去阿勒山寻找方舟的宇航员;在远离现实的天堂里尽情享乐的男人。
这些故事的发生地点都处于脱离陆地,或者说是远离世俗,脱离现实的位置。正因为远离陆地,发生的历史便有种脱离了真实的荒诞。比如《幸存者》凯思带着两只猫在海上漂泊,被自己的幻觉所折磨感觉皮肤被核污染的空气腐蚀而脱落,噩梦里她是被束缚住的精神病人,而叙述视角从第一人称到第三人称的来回切换,让读者很难分辨出到底凯思带着两只健康并生了一窝小猫的胖猫独自漂流是真,还是凯思因为和丈夫关系破裂而精神出问题被送到医院,身边跟着两只濒临饿死皮包骨头的猫是真。
这些历史里的“方舟”都是远离尘世的地方:海上的邮轮,架空在房梁上被木蠹蛀空的椅子,凯思的小船,梅杜萨的筏子,停靠方舟难以接近的山岳,远离世俗的丛林,得到神谕的月球,和梦一样永无止境的天堂。既然离开现实,便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历史”,人们不能证明,却又没有有力的观点否认它的存在,是虚假,又是真实。
再说分隔。
方舟上发生过的另外一件事,便是把“洁净”和“不洁净”的动物分隔开来,然而结局充满了讽刺意味,“洁净”的动物被当成食物或做成祭品,只有不顺从的和“不洁净”的自由地活了下来。《海难》中,虚伪狡诈的人登上了船上唯一的救生艇,切断了本应拖拽筏子的缆绳。筏子上剩下的150人,经历了几次叛乱后,剩下的存活者分食人肉充饥,把存活希望小的“不洁”者残忍地扔下大海。
再比如泰坦尼克上的异装癖,靠扮成女人的样子坐上救生艇顺利地活了下来,成为有名的幸存者。虚伪的骗子,惊慌懦弱的人都坐上了逃生的小艇,光鲜的活着,而真正具有美德的英雄却同那艘不幸的邮轮一起沉入了历史的泥淖。
似乎世间的一切都被荒诞地分割为两个对立的派别,而存活下来的往往又是被称为“不洁”,或者本身便是“不洁”的人。一如方舟历史开端处卑鄙的挪亚,争功的鸽子,而德高望重的独角兽被诬蔑,聪明的类人猿被谋杀,乌鸦因为被挪亚嫌恶而被鸽子夺取了本应有的荣光。“洁净”的动物被当做食物,“不洁”的木蠹则久久存活至今。生活的本意是适者生存,但所谓“适者”真是一些虚伪的劣质基因吗?
不过巴恩斯在这本书中用那1/2章告诉了读者避免世界被不断劣化的方法,那就是“爱情”。
“世界历史若没有爱就变得自高自大,野蛮残忍。”
巴恩斯的爱情并非特指某一种两人之间区别于对待他人的情感,而是纯粹的精神世界,是基于物质世界的对立面。尽管它无法传授,不见得利于生存,也并非必不可少,如同奢侈品一般难以得到,但爱情的纯真能使人们摆脱对绝对物质的追求。即便会令人失望,即便在多数时候会给人带来痛苦,爱情也拥有足够的力量把这个世界从永无止境的趋利避害向劣发展中拯救出来。
就像最后一章里的梦境,“我”不会疲倦地享受美食、购物、高尔夫、做爱、见名人,在这不会厌倦永生不死的新天堂里,尽管充满了不会厌腻的物质享受,尽管想要的一切都能拥有,却唯独没有爱情。在无底洞般的欲望漩涡中,“我”还是让自己从这个古老的梦中醒了过来。
或许方舟之上的事情至今还在反复上演,漂泊与虚幻之中的航船,分隔出各种各样截然对立的两方,爱情用纯真的力量努力从贪婪的堕落中挽救着世界。
又或许本就“不洁”的木蠹讲出的历史不可信任,挪亚还是虔诚善良的挪亚,方舟也是载着希望渡过苦厄的方舟,世界在彩虹的照耀下闪仍旧烁着美好灿烂的色彩。
《10½章世界史》读后感(九):一万个挪亚方舟故事
小说以对圣经旧约中挪亚方舟故事的解构开篇。故事以木蠹的口吻述说了挪亚的那次远航,可内里的细节完全不同于我们在经书中读到的。在木蠹的回忆里,挪亚是个酗酒的“自命不凡的老昏君”,一半时间讨好上帝,一半时间拿动物出气。在这些动物里,五分之一的动物灭绝是因为一条船失踪了,一部分动物灭绝是被“挪亚一伙”食用或者滥杀了,蜥蜴会变色乃是被人类吓得,宝石兽则因为含的老婆迷信宝石存在其中而消失……总的来看,《创世纪》里记载的这个神话在木蠹眼中完全是一出闹剧。
这出由神话演绎的闹剧,直接构成了我们理解与把握《10 1/2章世界史》的一条主线。读者接下来将会看到,它既为整部作品提供了事件的发生场域(方舟),也定下了此后一系列故事展开的叙事基调(“现在,我们要离开事实的港湾而进入谣言的公海。”P23)。如果将挪亚的故事称为历史性,那么解构则作为开放性存在。在两种特性的共在作用下,随时将被撕裂的张力与撕裂已成定局的混乱不可动摇地内在于文本,并且总是浮上水面与小说的主题(历史的不确定性)遥相呼应。
方舟故事中至少还包含了如下几个被巴恩斯反复演绎的关键语汇:譬如将畜类分为洁净与不洁净两类,在第一章《偷渡者》中它便被幽默地改写为可食用与不可食用,而后来干脆演化为:“对挪亚及其家人而言,我们就是水上餐厅。在方舟上,洁净不洁净对他们都是一回事”;譬如木蠹的因素(虽然是作者添附的,却也在此后不断出现);譬如方舟故事的灾难性内核。这些细节不断出现,有如螺旋一般扭结住了十个互不相干的故事。但尽管如此,它们一概无法取代方舟的主线地位。第一章中的挪亚方舟尚且还是挪亚方舟(这并非同义反复的废话),但已然不是旧约中那艘原本由义人挪亚带领的象征拯救的符号;相反,木蠹眼中的方舟倒更像是在预示着人类历史的荒诞本质。
自第二章起,挪亚方舟像是进入到万花筒,经历了一系列变形:在《不速之客》中,它是遭遇阿拉伯恐怖分子劫持的游轮,《宗教战争》中它是圣米歇尔教堂被木蠹侵蚀欲坠的主教座位,《幸存者》中它是被核恐惧驱赶到大海的女人的小船,《海难》中它是梅萨杜之筏(这一章最是复杂也尤为精彩),《山岳》与《阿勒计划》中它是狂信者求之不得的方舟残骸,《三个简单的故事》中它先后变换为泰坦尼克号、鲸鱼之腹以及二战中满载着寻求庇护的犹太人的圣路易斯号班轮,《逆流而上!》中它是纪录片的拍摄道具木筏……这样的安排也许会让读者想起克尔凯郭尔对亚伯拉罕献祭以撒故事的反复改写,几乎是如出一辙地陷入到疯狂的边缘。
以后现代小说的共相来看,《10 1/2章世界史》当之无愧。它的主题正是历史性与开放性两者的关系映衬:历史场域必然无法长久地钳制开放叙事,也必然最终让位于建基于此的后者。起于摹本的作伪(解释)而非起于官方定本的复述(阐明),所意欲的岂非质疑我们理解的那种真实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以讹传讹的终局,抑或:无力解释的因袭?此处无关虔敬是否,古老事件只有在与主体达成关联之后,只有在我们对其加以解释、赋予新意、打上签名的烙印之后,才可存在。
这就是后现代小说的假定。在戏谑不堪的文本后,古老事件重新获得实存,但并不单纯作为一场文字狂欢,而是——至少在巴恩斯笔下,我们能够识别出一种戏谑背后的严肃叙事传统和野心——古老事件重新获得实存,首先表现在它对事件能够脱离主体自存这一现代观念的否认。因此,后现代小说的叙事不是置身事外的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它开启了唤醒了我们对某一古老事件的认知,以及增进领会的可能。什么领会呢?暂且分为两方面来说:
第一点可称之为认识论意义的领会。依据巴瑞·班德斯塔的意见,挪亚方舟位于圣经太古故事(《创世纪》1-11章)的尾端。太古故事以水开始,以水结束。“上帝从混沌之水创造出一个能够居住的世界,后来又把这个世界推向洪水。 ”(《希伯来圣经导论》P42)朱利安·巴恩斯裁取的便是这后一个故事片段:义人挪亚带着后裔以及世上的动物历经洪水之劫,再现于新的世界。水代表着不可或缺的混沌,贯穿了太古故事,而它之所以不可或缺,乃因秩序正由混沌孕育。秩序虽然终结了混沌,混沌却是秩序必不可少的开端。
混沌既是开端,也是手段。秩序的再造总要依赖于混沌的灾难性(本书以《梦》作最后一章亦是题中之义)。从这一点来说,巴恩斯写这本小说不仅在题材上选择了方舟,也在叙事理念上无限贴近于(虽然是极端扭曲地贴近)旧约经文背后的结构。此一理路,便是作者根本没有想到要做一番正本清源的工夫,他所做的无非是针对隐匿在时间中的符号通过大量癫狂的互文程序从而将其推向混沌,亦使之再现于澄明之境:挪亚方舟的原初含义并不重要,但作者在赋予它新的解释之际,也就把握了此世的认识。所以说,方舟既是题材,也是结构。
第二点可称之为本体论意义的领会。我们读了《10 1/2章世界史》难免会疑惑:这些恐怖分子、狂信者、性别狂热人士、反犹之徒,甚至是那些逃离了德国在轮船上寻欢作乐的犹太人等等,为何在此之后既没有受到祝福,而在此之前也没有遭遇诅咒?尽管班德斯塔将后洪水时代人类不再被上帝全盘灭世与上帝知晓了恶是人类的深刻本性联系在一起,但也不要忘了,“耶和华上帝的创造故事,成就了一个涉及人类的欲望,个体的责任,因为悖逆而受到惩罚的永恒的道德传说。”(《希伯来圣经导论》P53)就中关键之处在于个人主动承担起的道德责任。
在《创世纪》第8章中,耶和华感念挪亚的虔敬,于是决定“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简而言之,挪亚促成了自亚当夏娃之后人神之间紧张以至分裂的关系和解。也就是说,如果依据经书的意思,小说中那些傲慢的人类没有被毁灭是因为人神和解了。但巴恩斯恐怕意不在此。有的读者可能会恼怒于这本书对《圣经》的篡改,然而在我看来,它恰恰是非常忠实的。即便是全书惟一一次的位移,也符合我们对《圣经》的整全理解:它出现在小说插曲一章。在这篇随笔中,主线方舟抽象为懵懂无知的童男处女寻求的应许之地——爱情。谓之位移,是指促成人神和解的核心由挪亚移至爱。不是诚与真,而是爱与真:
“爱情也是这样。我们必须信奉它,否则我们就完了。我们可能得不到它,或者我们可能得到它而发现它使得我们不幸福;我们还是必须信奉它。否则我们就只好向世界历史缴械投降,向别的什么人的真相缴械投降。”(P262)
尝有论者认为但丁《神曲》中最为生动的是《地狱篇》,最是乏味的为《天堂篇》。这个道理可能就是人们从来不缺少有关恶的想象——虽然这并不是说人类逃离善如同逃离灾疫,可难道不是这样么——一旦人们设想善的图景,想象力便迅速枯萎。我觉得这也能体现本书惟一的不足:插曲——作者提供的这条救赎之路——尽管很可能是行之有效的,但让人感觉乏味。在仅仅提供了某个温馨的场景过后,作者随即陷入到谈论爱的说教泥淖中。
他在《三个简单的故事》中借着谈起现代约拿,有过这样一段议论:“你可能不相信它,但实际情况是,这故事一讲再讲,又修改,又更新,搞得离我们更近了。”(P187)《福克纳传》的作者杰伊·帕里尼同样持此观点,他说:“想象力(vision)的本质在于修订(revision)”。我觉得这个观点对得上本书所有虚构部分,可恰恰在插曲一章里榫枘不合。有两种写法,其一是理解的想象力,其二是想象的理解力。对于前者,巴恩斯在虚构的十章做得足够出色,对于后者,它本应操持在非虚构的一章——如果将爱情理解为善,将受难理解为恶,那么善就比恶更需要想象——然而惟独在这里巴恩斯丢开了想象。尽管他依然毒舌(“我们对相爱者的沉湎应当适可而止,他们在追慕虚荣这方面可以赶上政客。”P238),抑或不改俏皮本色(“《爱情散文:苦干家手册》。要到木工专业书柜去找。”P239),甚至效仿罗兰·巴特在书中玩起了“我爱你”的语义学分析(P241),但在读者看来可能都不如那个半夜里依偎在一起的回忆感人,也不如仅有的几个想象来得具体实在。不妨略作一番比较:
——“听天由命的童男处女被告知,爱情是许诺之地,是一条两人借以逃脱洪水的方舟。也许是一条方舟,但却是一条流行食人肉的方舟,一条由某个花胡子昏老头掌管的方舟,这老头用歌斐木手杖敲你的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你扔下船去。”(P243)
——“夫妻相爱,但并不幸福。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说他们中有一个不是真正爱另一个;说他们相爱只到一定程度,还不充分?我不同意这个真正;我不同意这个充分。我一生已爱过两次(这在我看来够多的了),一次幸福,一次不幸福。正是那次不幸福的爱给了我最多有关爱情实质的启示——但不是在当时,而是在很多年之后。”(P244)
真知灼见总要在想象中被道出,而议论能够抵达的地方实在太少。可是尽管如此,瑕不掩瑜,作者的苦心毕竟能够理解,那就是他要为混沌的历史建立一条秩序基准(从这一点来说,他的旨趣倒不是后现代的);也惟有如此,我们得以把握上文提到的第二层本体论意义的领会:上帝与挪亚立的约发展成犹太人的律法,后来又经由保罗的总结归纳为爱人如己。因此,《10 1/2章世界史》中仅有的一次位移,本质上是作者将主动权移交给了人类:人类不再等待拯救的降临;人类必须为自己祝福。
在人们尚未遗忘索多玛与蛾摩拉这两座城的背景(立约之后)与命运(毁灭)之际,不正是爱成全了律法吗?巴恩斯的改写虽然像是在对方舟故事中的拯救做无限滞后的处理(《创世纪》中毕竟只用了三章上帝即平息了大雨和洪水),而文本的张力亦许正出于此一延宕。作者的用意,毋宁说是,惟有爱能唤醒了人类对己待人的本真体会。在巴恩斯看来,这才是人类在历史洪流中安身立命的关键。
2015年8月6日写成
(《文艺报》2016年3月16日)
《10½章世界史》读后感(十):重复与颠覆——浅析《10½章世界史》中的戏仿
戏仿手法自古有之并且受到越来越多的现代作家的青睐。本文从朱利安·巴恩斯的《10½章世界史》出发,试图将戏仿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作品的重要手法重新带入研究视野。
完整原文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PREP&filename=WGWD201803004&v=MjMxMjg3RGgxVDNxVHJXTTFGckNVUkxLZllPUnZGQ3ZrVnJ6TU1pcmNhckc0SDluTXJJOUZZSVI4ZVgxTHV4WVM=。由于原文较长,在此仅试图勾勒出论述框架与几个基本想法。
1984年巴恩斯凭借突破性之作《福楼拜的鹦鹉》跻身英国文坛一流作家之列。在此书中,巴恩斯展现出了他炉火纯青的小说创作手法,其中就包括戏仿手法,而他于1989年出版的《10½章世界史》(以下均简称《世界史》)可谓是戏仿传统的延续与发展。《世界史》不再按照传统的线性书写展开,而是平面化排列各章,初看之下并没有明显的联系,但是通过仔细阅读,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内藏玄机——作者通过戏仿重复了之前的文本与话语,同时又颠覆了它们。涉及本书中戏仿的研究一般强调其颠覆作用,并将其作为后现代主义对权力话语、逻格斯中心主义的重要解构手段附属于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中[1]。有部分研究者即便注意到了戏仿在构成本书过程中的重要性,也常常是从戏仿的对象入手,将其分为对政治、宗教、历史等具体方面的戏仿。以上这些研究都或多或少地缺少对戏仿本身特质的系统研究,有些甚至将戏仿和被戏仿的对象简单对立起来,当然也就不能揭示戏仿自身的矛盾性以及戏仿与后现代主义的密切关联。哈琴曾指出,戏仿是“后现代主义的完美表现形式”[2],而在这部小说中,不论从内容还是结构上来说,戏仿都是重要的构成基础。那些看似重复的文本和话语都蕴含着颠覆性,作者带领我们在重复与颠覆中,反思西方长久以来的观念,探索历史书写新方式。一 后现代视阈下的戏仿“戏仿(parody)”(或称“戏拟”)的概念由来已久。亚里士多德在《诗学》就使用了“parodia”[3],这个词可以被理解为即对史诗作品的滑稽的模仿和改写,可以说是戏仿的最初来源。戏仿在各个时代的作品中都被广泛地使用,从阿里斯托芬的《青蛙》、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斯特恩的《项狄传》其中都有它的影子,但是长久以来人们常将其拆分为“戏”和“仿”进行解释,将其简单地理解为“戏谑模仿”——“戏”常常带有贬抑或玩弄被戏仿文本并将其降至一个荒唐层面的意思,而“仿”则是不顾忌原创性地对被戏仿文本的模仿。到了后现代时期,著名理论家哈琴表示 “戏仿的全部意义在于对戏仿这个概念的重新界定”(后:36),也就是说只有重新认识戏仿的特质,才能够认识到这种手法在后现代主义时期的重大意义。哈琴认为,在文本中运用戏仿“等于恢复了与过去的对话”(后:32),它使得文本以既重复又颠覆的方式保持了“鲜明的历史性”(后:30)。戏仿在重复前文本的同时,不惮于表明与过去的差异,以一种“既使用又误用、既确立又颠覆常规,自觉显示其本身固有的矛盾和临时不定性”(后:31)的方式对过去的艺术展开带有批判、反讽性质的重读,既包含又质疑了戏仿的对象。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所有的文学艺术都与话语有关。“在阐明自己的同时,艺术作品也清楚展示了审美概念化的形成过程以及艺术的社会学状况”[4],所以戏仿并非是没有深度的、滑稽搞笑的手法,而是能够深入探究话语的本质、局限性和可能性的手法。一方面戏仿使得人们“直接面对审美与由外在意义构成的世界、与由(过去与现在的)社会意义系统(或者说由历史与政治)构成的话语世界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戏仿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型来绘制艺术与世界的边界。这一模型记载上述两者之内运行,又不完全在两者之内”(后:31),也就是说,戏仿能够在重复和颠覆过去的话语的过程中保持一个特别的姿态进行多元话语的建构,具有相似性与差异性、保守性与革命性共存的特点。后现代戏仿所面对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在重复与颠覆之中找到平衡点。斩不断的文本间联系、无孔不入的书写传统使得重复成为必然,但也正是在这些“影响的焦虑”之下,戏仿带入了颠覆性的文本和话语,尝试着进行新一轮的重构。同时,它又如后现代主义一样,以临时不定又自相矛盾的立场取代了预言家式的、约定俗成的姿态,不断揭示自身的矛盾性,调整自身的定位,使得它的重构姿态具有多元性,而不再重蹈中心主义的覆辙。二 戏仿与文本(一)被蛀蚀的权威文本《圣经·旧约》第一章《创世纪》代表了西方文化对于人类起源、发展的基本认识——人类的罪恶引起上帝的反感,使上帝意欲毁灭人类,但由于挪亚一家虔敬侍奉上帝,所以得到了上帝指引。挪亚一家提前建好方舟、收纳各种生灵,最终躲过了洪水,重新开始繁衍生息。在巴恩斯小说中,《圣经》中方舟故事的情节或关键词被不断重复,然而就是在对这些具体内容的重复中我们可以发现,看似忠于原文的内容实际上已经成为对源文本的戏仿。人所共知的“方舟”的形象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多次——遭遇劫持的游船、海上孤舟、梅杜萨之筏、泰坦尼克号、拍摄土著人的筏子等等不一而足。虽然这些对具体文本内容的戏仿有些零散,但却可以展现出作者对于以《圣经》为代表的权威文本的深入思考,同时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在传统延续的核心部分里传统中断了”(后:14)的后现代状态。按照《圣经》的叙述,挪亚的儿子们分别叫“闪”、“含”和“雅弗”,但木蠹对于雅弗的称呼始终是“名字以J打头的”[5],并且一直保持到章节结束。可见它有意识地与原来的话语保持距离,这也为戏仿文本的存在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个小虫首先对《圣经》中出现的具体时间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雨下了四十个日日夜夜,是吗?”,“大水淹没世界一百五十天,是吗?”(世:3),同样的数字曾经出现在《旧约·创世纪》的第七节——“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水势浩大,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6]。通过仔细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木蠹不仅引用了源文本《旧约·创世纪》中的具体数字,同时模仿了源文本“事件加具体时间”的句式。如果没有最后的反问和语境作为支撑,那么木蠹的两句表述完全就可以被看作是对于源文本的复述。作者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将戏仿文本带入一个看似熟悉的语境中,也正是由于这些看似重复却带着强烈嘲讽、否定语气的文本的存在,《圣经》内容的客观性、真实性变得值得怀疑,因而也就成了被戏仿的文本。[......](二)从模仿到戏仿后现代主义对文本的定义十分宽泛,绘画、话剧、书籍、电影等等有意义的文化产品都包含其中。小说第五章“海滩”围绕着画家籍里柯所绘的“梅达萨之筏”及其相关文本展开。根据历史文本记载,1816年梅杜萨号炮舰触角沉没,此后不到一年,作为幸存者的萨维尼和科里亚就出版了他们对这次航行的记录,1819年画家籍里柯完成画作“梅杜萨之筏”。从现实中灾难发生到围绕这场灾难创作的各种艺术作品出现,时间间隔之短令人咋舌,正如作者说的那样,“如何把灾难变成艺术?”,“如今这个过程是自动的”(世:129)。在本章中,作者就试图展示这个“自动的过程”——画家竭尽全力想要重复真实,殊不知重复内部其实蕴含着颠覆,创作的过程其实已经转化成了戏仿的过程。[......] 三 戏仿与话语 (一)话语模式的重复与颠覆[......](二)戏仿姿态下的多元话语建构尝试新的话语通过对之前话语的戏仿产生后,仍然可能成为更新的话语的戏仿对象,任何所谓的“正式授权”都不是永恒的。为了不使自身陷入一个质疑的循环,戏仿通过表现自身的矛盾性从而来消解新的宏大体系的切实建构。在小说中,作者通过木蠹的叙述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戏仿的姿态。木蠹曾经强调“我们没有任何过错”(世:5),原文中就将“我们”突出强调。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圣经》中指明人类有罪恶,但没有指明万物都有罪,所以木蠹将自己排除在外。木蠹觉得本身“全没有和上帝或挪亚订什么靠不住的协约。我们自己干。我们觉得自己成了崇高的一族”(世:28),当人类的信仰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受到挑战、日渐衰微的情况下,木蠹在重复又颠覆挪亚方舟的故事的同时,难道不也是在构建另一种一元的、因果的、线性的、有模式、有等级的“木蠹中心主义”话语吗?其实不然,戏仿其实给自己留足了“后路”,而这种后路通过自行暴露内部的矛盾性来形成。虽然木蠹多次强调自身话语的真实性,但同时也曾说过“我们要离开事实的港湾而进入谣言的公海”(世:23),并且声明不一定非要相信它的话,因为很多说法都是从其他船上的鸟儿们那里听来的,读者可以自己选择相信哪一种。也就是说,戏仿所强调的是可能性,所提供的是不偏袒的、有选择机会的平台,摆出的是留白的“姿态”,进而避免了自身再次陷入尴尬的境地。戏仿重复与颠覆的过程其实也是进行重组尝试的过程,但正如上文所述,戏仿以一个更平等的姿态提供了话语形成、互相作用的场所,这也意味着多元话语有了共存的机会。戏仿让处于边缘的群体能够在话语内部和话语对话,而不被其同化,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成了“中心之外”的话语的最佳表达方式,边缘的群体能够给出不同的历史书写方式,同时又不带任何一本正经的“理论”色彩。在戏仿的重复和颠覆两个特点的矛盾运动过程中,作者带领我们重新审视“受难-救赎”模式的本质,揭示建构多元话语世界的可能性和所面临的困境。[......]事实证明,后现代主义戏仿并不是轻浮、格调低下的,而是确实能让人洞察到事物的内在关联性的。作者通过戏仿打破了传统历史书写方式和传统观念,挖掘出潜藏着的话语,并对话语模式进行了重复和颠覆,积极地探索着一部新的“世界史”的模式,促使我们深入思索人类如今的生存状态和未来。四 结语本文从琳达·哈琴关于戏仿的论述出发,将戏仿在后现代时期的特征总结为重复又颠覆,并通过对巴恩斯的《世界史》中具体文本和整体结构的分析,试图将戏仿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手法重新带入研究视野。戏仿在重复《圣经》和艺术作品等文本的同时,对前文本的内容、语境进行了刻意改动,从而颠覆了文本的权威性和真实性,揭示出传统艺术创作目的与方式的矛盾。戏仿在重复过去的话语的同时,以敏锐的洞察力暴露出“受难-救赎”话语模式的不稳定性,从而颠覆了传统历史书写整体化、线性化要求,促使人们反思长久以来被话语建构的固有观念。同时,它还以一个更包容的姿态提供了多元话语形成、互相作用的场所,使得边缘话语能够与传统观念中的“权威话语”同台发声。虽然戏仿没有、也不可能帮助边缘话语彻底解决边缘话语所遭遇的尴尬现状,但它已经开始引起更多人对于边缘话语、对于历史书写方式的关注,所以还是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的。另外,本文只针对巴恩斯的一部作品进行了具体研究,而戏仿是被后现代作家、理论家们广泛运用的手法,所以必然有所疏漏。若本文能够抛砖引玉,让戏仿得到更多研究者的重视和讨论,本文的一大写作目的就算达到了。[1]参看李颖《论<10 1/2章世界历史>对现代文明的反思》,载《当代外国文学》2012年第1期,第76页。另参看罗小云《震荡的余波——巴恩斯小说<十卷半世界史>中的权力话语》,载《外语研究》2007年第3期,第98页。[2]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李杨、李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3]参看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8-40页。[4]Charles Russell, "The Context of the Concept"in Harry R. Garvin,ed. ,Romanticism, Modernism, Postmodernism,Lewisberg: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p.189。转引自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第33页。[5]朱利安·巴恩斯《10½章世界史》,林本椿、宋东升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4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6]《圣经》,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编,中国基督教协会,2009年,第6页。[7]玛格丽特·A·罗斯《戏仿:古代、现代与后现代》,王海萌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7页。[8]Shusha Guppy, “Julian Barnes, The Art of Fiction No. 165”, in The Paris Review, issue 157, 2000, https://www.theparisreview.org/interviews/562/julian-barnes-the-art-of-fiction-no-165-julian-barnes[9]伊哈布·哈桑《后现代转向》,刘象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