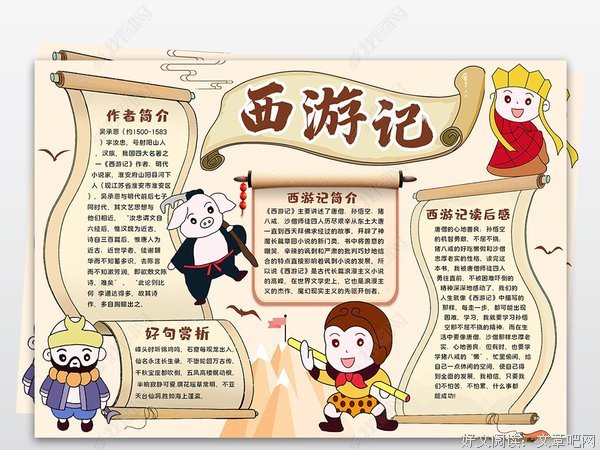失落的星阵经典读后感有感
《失落的星阵》是一本由[美] 尼尔·斯蒂芬森著作,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58元(全三册),页数:8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失落的星阵》读后感(一):揭秘网赌电子平台作假套路!
小编的后台每天都会收到很多留言,其中两类人的留言最多。一类是“杀猪盘”受害者,来这里讲述自己被骗的经过。另一类是自己或亲人陷入网赌,来寻求帮助。不过近期的一个留言,却引起了小编的注意:
看留言,应该是一对姐弟,在遭受同一个网赌平台的毒害。先和你谈恋爱,另一个是常规的推广办法,通过好友邀请的方式来进行。
虽然我们无法直接去把这些骗子给马上抓到(他们很多都在国外),但是觉得很有必要做点啥,最起码要说服这个粉丝的弟弟认清网赌的危害。于是,我们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开始扒这个网赌平台的内裤。
首先,我们按照粉丝姐姐提供的网址打开了这个网赌平台。
不得不说,现在的网赌平台做得越来越高大上了,也越来越敢吹牛逼了。
看看下面这个网站的主页,从设计上看风格简约、色彩鲜明,一个硕大的迪士尼米老鼠在为你述说整个网赌平台的使命:为人类建乐园。
仅仅看网站主页,并不能发现网赌平台真正的奥秘。在一不小心之下,我们无意间进入了网赌平台的管理后台。
《失落的星阵》读后感(二):感觉这次尼尔·斯蒂芬森翻车了
读完,感想很复杂,简单来说一说。
大家都知道NS是个考据狂,从《雪崩》到《编码宝典》到《七夏娃》到这本《失落的星阵》,都姚往里塞无穷无尽的细节和各种考据,属于那种喜欢的人爽翻天不喜欢的人根本读不下去那种,但是我觉得这次他是有点过分了。
一,生起一个平行宇宙的人类世界搞worldbuilding不是不行,这是奇幻作家喜欢的做法;但是近乎于刻意的编造出大量术语和名词来做世界构建,这完全是出于作者本人的恶趣味:因为这除了给读者和译者提升门槛之外没有任何用处。我们都知道“唧嘎”就是手机,作者也是把“唧嘎”作为手机来描写,那么从作者自己就喜欢玩弄的语言学角度,这无非是在一个同样的所指上去刻意代换能指,那么它叫做phone还是唧嘎还是手机还是shouji,对于文本本身的表达而言有什么区别吗?同样,“斯皮里”和“视频”,movie或者video又有什么区别呢?文中引入了大量类似的虚构的术语和名词,我没有看出除了恶整读者和译者之外有什么意义。
二,承接第一点,NS在小说里铺排了大量的人物对于宇宙学和形而上学观念的讨论(毋宁说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但是你一旦把那些在第一点里说的,刻意的为了提高门槛而提高门槛的虚构术语和词汇代换成普通的地球术语,那么这些观念讨论立刻就会变成很平常的,你可以在一万本其他宇宙学科普里能读到的那些内容。那我为什么不去读一些正儿八经的哲学书,而不是废了吧唧的在这本庸俗哲学科普里找剧情,就好比在一大盘重庆辣子鸡里找鸡肉一样。
三,我会感觉NS在这本小说里丧失了幽默感。他在《雪崩》或者《编码宝典》或者《七夏娃》里都有的那种幽默感在这本里几乎消失了,只剩下了那种非常急迫的对读者进行信息灌输的冲动,症状就是我在第二点里说的,整个小说大半内容都是这些很形而上的角色之间的对话。幽默感的另一个说法,就是“游刃有余”,这个你在他之前小说里都能感受得出来,他对于文本的把握是很松弛的,可以感受得到他在背后做了多少工作,但是他其实就露了一小手。这本不一样,特别满特别急迫。
四,我要吐槽这个外篇部分。还是那句话,你把里面装腔作势的虚构术语拿掉,这个外篇部分就是数学系入门课程101。第一个粉本讲几何学入门,第二个粉本其实就是数学分析里向量空间的重新定义(然后用了一个特别唬人的亥姆空间),第三个是讲拓扑学。所以问题来了:我为什么要来一个科幻小说的外篇里接受大学数学系入门课程教育啊?这恐怕是一个死宅自娱自乐的最高境界:你必须先理解他想要写什么,才能理解他写了什么。懂的人一看就懂而且觉得这些都是很浅显的玩意,不懂的人怎么都不会看得懂。
五,跟他之前的所有小说一样,都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人物塑造……里面的人都跟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说话风格也都类似,我想象就是NS自己的那种风格:带点亚斯伯格那意思,聪明理性,没有情绪起伏。你把所有的那些形而上的东西全拆开,情节也很简单。当然NS的小说的情节主线从来就不重要,要读的是他那些掰扯的奇奇怪怪的东西。问题是这次掰扯的东西我觉得没劲。
六,核心设定是“人脑是量子化的,可以在量子平行宇宙中选择可能的世界线”。说实话这个设定本身就有点俗套,况且还当做大梗直到最后一刻才抛出来。这个类似的设定用得好的推荐一个短篇叫做《魔法师和拉普拉斯妖》,比这个写得有趣多了。
七,大概就这些了。以后想到再说。
《失落的星阵》读后感(三):你以为的穿越,其实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
文|木之
在科幻剧作里,穿越时空拯救世界是常有的桥段,主角总是一本正经的说着看客们不懂的理论,再一本正经的将这些理论实践出来完成剧情上的结局。我们内心只能写个大大的“牛逼”然后将这一切调侃为“遇事不决,量子力学”。
可这样的穿越方式也引发了新问题:如果可实现,真的只存在我们生活的这一个世界吗?其他世界与我们的关系又是什么样的?
本书从另一个世界(书中前言所说,一个与地球相仿却不相同的世界)的角度来写我们所畅想的“第一类接触”。这里的主角不再是地球人,地球人所扮演的是被接触者。故事通过一系列的变故,展现了与“外星人”接触可能会出现的现实状况。
风险、预知、发现、新理论、新文明……成为了这个本来存有分歧的世界的主流论调。原本对立的学派现在开始合作,对立的政权开始共同治理社会……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一切都将要被重新审视。而我们知道一个新的时代要到来了。
异世界的访问,作者将它放到了量子力学的领域里解释其合理性。我们只能用我们的意识去观察已有确定的事物,然后提出假设并论证。可一些假设被已有的现实所限制时,又当如何去证明其正确性和错误性?就如同薛定谔的猫一样。这些受限于现实已有观察的假设,现在呈现出错误与正确的叠加状态,只有当新的发现出现,或新的现象出现时才能下定论其错误与正确性。这就成了本书展开想象的起点。
作者将书中的对立面设定的十分清晰便于理解,又不乏历史发展的合理性。在世界上存在着两大组织:世俗(这一组织更像现在的社会)和集修院(一个纯学者的象牙塔)这两个世界中也有着与我们相似的人、事、物。比如慕像者(神的信徒,唯心主义者)、理学者(知识分子)、伊塔人(IT人士)等等,其中也有着明显的不同。比方说:世俗世界里也会有理学者但与集修院里的理学者相比,世俗世界的理学者从事的大多是实践理学。也有像集修院里的理学者不能与伊塔人接触的社会规定。这样的世界有着我们的一些特点但也有着不相同的地方。同时在某些方面展现出比我们的世界更理想的状态,就好像是我们的历史,在某些特定的点向着更加“正确”的方向发展。该灭亡的种群或该被取缔的习俗都会通过一些方式存续下来。或许这也是一种比我们更高级的社会,充满着历史的正确性。
该书涉及了大部分的理论的问题和理论思想,却不难被人理解,相反通过阅读更能对一些理科理论有一定的了解。同时也能发现,穿越是一种解释方式,但其更是一种事件可能性的展现,这就要回到那只名猫的问题上,它是两种可能性的叠加状态,要么死要么活。而放到现实社会就是无数种可能性的叠加问题。这也成为本书故事发展的核心,有时可能会发现为什么故事同时进行着很多叙事线,这只是作者在展现它可能的叙事,而最终向哪种情况发生是一种随机状态。
对宇宙的探知是进入太空时代以来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也一直想要弄清楚的事。在探索中,在任何的实践中我们或许会犯错,会失败。但不要放弃与气馁,在打开箱子前,我们永远都是薛定谔的猫。同样的作者只是假设了“开箱”之后的一种结果,而另一种结果如何也是一个令人充满兴趣的问题。
PS:作为理科的小白,书中一些理论是我自己搜索以后的理解,如果举例有不正确的欢迎指正。一开始想写一个比较论点集中的书评,但觉得没有什么更好的辅助作用,所以改成了比较笼统的。
《失落的星阵》读后感(四):不光要翻译百科,还要翻译外星语?翻译太难了(笑哭)!
文:王方 (《失落的星阵》译者) 这绝对是我翻译工作中的一座星程碑。——外星语翻译 王方 我没开玩笑!哪个翻译会一边翻译一边解码(因为作者给作品加了密)? 一边翻译一边学习外星语(因为作者给笔下星球居民创造了小语种语言)? 一边翻译一边……哭(这句是玩笑)!
●包罗万象 理科生看得到量子力学、多宇宙论、核动力宇航船、轨道问题、基因编辑……文科生看得到认识论、语源学、语义学/句法学之争、后殖民文化论、反乌托邦,甚至还有一整部“哲学史”。 科幻作家尼尔·斯蒂芬森好作鸿篇巨制,算是一位十分高产的作者。1984年初出茅庐,12年后便以一部《钻石时代》(The Diamond Age,1995)夺得了当年的雨果奖。此后,创作的势头更是一发不可收拾,2009年又以新作《失落的星阵》(Anathem,2008)再度入围同一奖项。 他凭借地理学和理论物理学的教育背景踏入科幻小说创作领域,其著作在科学构想方面可谓一丝不苟,极富说服力,却又不乏奇绝瑰丽。斯蒂芬森擅长消化各种前沿的学术理论,将它们巧妙地融入作品设定,总是给读者带来眼前一亮的新鲜感受。 不仅如此,他也是一位“出格”的科幻作家,“贪婪”的触角甚至肆无忌惮地伸向了哲学、语言学、历史、宗教等诸多领域,并且皆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 《失落的星阵》便是这种野心的力证,理科生看得到量子力学、多宇宙论、核动力宇航船、轨道问题、基因编辑……文科生看得到认识论、语源学、语义学/句法学之争、后殖民文化论、反乌托邦,甚至还有一整部“哲学史”。可以说,这本书已经多元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甚至让人怀疑它到底能不能归入科幻小说的范畴。 当然,标准科幻的招牌元素在本书中有着十足的分量——自休·埃弗莱特在1957年提出量子力学多世界诠释论以来,多重世界和多重宇宙就成了科幻作家手中的法宝。 短短五六十年里,包含这一元素的科幻作品便已汗牛充栋,更有不少登上大小荧幕。作家们脑中的多宇宙模型可谓花样百出,比如因果域隔绝的视界平行宇宙,比如多世界并存的量子平行宇宙,再比如跟弦论有关的膜平行宇宙,但通常一个故事只会采用一种,《失落的星阵》却霸气十足地占了两种,也让这本书变得格外烧脑。 本故事发生的舞台是另一重宇宙里的一颗行星,有了外宇宙外星,必然有飞船,宇宙际穿越自然也少不了。不仅如此,斯蒂芬森还找来一票语言学家,专为这个星球上的居民打造了一套“外星”语言。 对于读者而言,外星语想必已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凡在银幕上看过《星球大战》(Star Wars)的都不会陌生:怪模怪样的外星人,非人的嗓音,听不懂的一串串音节,以及荧幕下方的一行地球语字幕。 但此类“外星语”的创造,不外乎是为了营造陌生感和距离感,让外星的设定更具有说服力而已,导演可绝不会难为观众们通过它去理解情节。 然而,本书的作者却不满足于小试牛刀的耍耍花腔。他所作的,是给这份文本加了一套密码,读者要用眼睛去识别陌生的书写,在里边搜索可能的语源,用头脑去拼凑它们的含义,必要时还得动手翻阅他附赠的“词典”。甚至合上书后,还要回味这些文字游戏的“妙趣”。
●诲人不倦 斯蒂芬森怀揣着满满的自信,不仅要把自己的设定暴露到每一个螺母,还要不厌其烦地给读者们上课,抛出一朵又一朵科技术语的蘑菇云,直到所有人都承认他是真正的行家。 硬科幻、密码,想必就是这本书给绝大部分读者留下的初步印象,但如果您以为烧脑和解谜就是此书的全部,可就低估了斯蒂芬森的“用心”。 看其他科幻作品时,可能很少有人会为自己不懂位形空间,不懂弦论,不懂量子物理而感到恼火,因为作者多半会巧妙地避开枯燥的核心理论阐述,以防自己的作品从招人喜爱的通俗文学变成惹人讨厌的理科教材,也避免在阐述的过程中暴露自己在科技理论方面的不足。 斯蒂芬森却怀揣着满满的自信,不仅要把自己的设定暴露到每一个螺母,还要不厌其烦地给读者们上课,抛出一朵又一朵科技术语的蘑菇云,直到所有人都承认他是真正的行家为止。 这方面《失落的星阵》的“变态”程度远超克里斯托弗·诺兰拍摄的《星际穿越》(Interstellar)。如果您幸运地拥有良好的理科知识背景,读到这些段落时,也许还有点儿温故知新的感觉;若非如此,又不甘心放弃的话,大概就只好不停地求助于各种百科,一边翻阅此书,一边龇牙咧嘴地吞下那些难以下咽的术语了。 另外,即便是擅长破译密码,精通科技理论,可以轻松破解本书的“外星话”和科幻原理,也不代表您的阅读体验会一马平川。 在科幻类作品中,向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艺术致敬的并不罕见,比如杰夫·范德米尔的《遗落的南境》(The Southern Reach Trilogy)、薇若妮卡·罗斯的《分歧者》(Divergent)…… 当然,这类作品通常不会在科技理论方面大掉书袋,哲学之类的元素也主要是为作品的文学性服务,因此通常会被贴上软科幻的标签。 欣赏这类作品时,读者不会为自己不熟悉康德,不了解胡塞尔,不清楚什么叫本体论、认识论,分不清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而读不懂核心情节;不会为搞不清哥特建筑每一个构建的名称而弄不清主人公身处何地。 是的,说到这里,诸位大概已经看出来了,《失落的星阵》还是一部无情碾压读者文化常识的“刑具”。这本书大概是活百科全书和考据派眼中的乐园。
●这要怎么翻译!!! 我也曾考虑,是否把这些“外星”词汇直接意译为它们的本义,比如把“speely”翻译成视频?但那就像是交给读者一本画满了答案的谜题游戏,想想都觉得失礼和讨厌。 在接到本书试译稿的时候,译者曾惊讶于出版方的慷慨,虽然试译的字数并不是很多,但发来的原文稿子却不是常见的一两页书影,而是十多页的一整段情节,这对于理解上下文实在是有极大的帮助。 但我只读了几段就开始气馁,一下子质疑起自己的阅读能力,一下子又质疑起手里的字典是不是不够全面。抱着如临大敌的心态,我搜索了大量关于这本书的资料,才发现原来还有一套专为它打造的《词典》,《词典》的后边还藏着一伙精通小语种的语言学家。 结果,为了一两千字的试译段落,脚注里几乎加上了同样字数的考据和译法说明。 本书故事发生的场景并非地球,而是一个叫作阿尔布赫的星球,此星球在诸多方面与地球相似。 发音提示:阿尔布赫(Arbre) 法语中意为树,词源为拉丁语的“Arbor”(树),与本书自创词汇树种师(Arbortect)同根。发音近于“阿尔布”(Arb)略带尾音。该发音可请教法国人。亦可掐去词尾读作“阿尔布”。 书中奥尔特语文化的词汇发展是建立在阿尔布赫星古代语言基础上的,我并没有使用对于地球读者来说毫无意义和内涵的奥尔特语词语,而是试着以地球上的古代语言为基础创造了一些词语。 其实我也曾考虑,是否把这些“外星”词汇直接意译为它们的本义,比如把“speely”翻译成视频?但那就像是交给读者一本画满了答案的谜题游戏,想想都觉得失礼和讨厌。 于是只好下了番功夫,狠狠地破解了一把幕后工作者的语言学游戏,拆词源,摸构词规律,查隐喻……这样便有了今天这个中文译本,夹杂着拗口的陌生词汇,还有让人轻易不敢念出声的异体字。 而这,就是广大英语读者在看到这本书原文时的感受。 举个例子: “Fraa”是什么?看起来有点儿像是“Fra”,怎么读?发音也和“Fra”一样吗?意思呢?就是“Fra”吗?《词典》告诉大家:这就是阿尔布赫版的“Fra”,意思也和地球上的“Fra”有点儿像,又不大一样,就好像是这个“Fra”后边多了一个“a”。 让我们来把上边这段完全汉化一下: “
《失落的星阵》读后感(五):特供版《失落的星阵》阅读指南
这是一篇等待了三年不断填充内容的编辑手札,终于能够突破漫长的时间和读者见面了。内心喜不自胜,毕竟,再等等,版权就要到期了。因此,率先感谢作者尼尔·斯蒂芬森的耐心等待,面对诸多问题都保持了极大的宽容,而这,是这本书能够出版的最强力支持。
这是例行公事的诉苦环节(我超真心的部分)。是的,每本书的出版过程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本小说算是创造了我个人出版筹备耗时最久的记录。历时3年多,它终于能和读者见面了。
论科幻小说设定细节之出众,不得不读的三个作家是弗诺·文奇、刘慈欣、尼尔·斯蒂芬森。这本正是出自尼尔·斯蒂芬森之手。按照外网的界定,《失落的星阵》算是一本太空歌剧的科幻小说,这个分类其实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作者庞大的脑洞和强大的执行力,以至于这本书的细节设定之多、之繁琐简直令人崩溃。
我最初接手这本书时,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翻译。小说原稿的艰深可以预期,但作者大胆设定了一个星球的独特语言,专门找了语言学家专程打造出一个阿尔布赫星语系。为了对应原书造词的特殊性和趣味性,译者尽可能用意译和音译相结合,把词汇表隐含的很多文化信息体现出来。同时需要说明的是,读者在阅读时可能遇到的异体字词汇。这主要源于原文中的自造词,如果单纯将作者设定的阿尔布赫星的词汇意译为一般词汇——比如把“speely”译作视频,把“Jeejah”译作手机,将失去原文造词的趣味性和文化性。译者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尽力保留译文中每一个小心思,争取还原这些词汇在英文原版中呈现出的陌生感、隐喻和双关性。因此,有些特殊的异体字,实际上就是为了和简体字作区分,请大家放心阅读。
词汇表的确认只是第一步,书中的建筑和哲学性的思辨,硬核的科学猜想,让翻译的时间延长了一倍不止。非常非常感谢译者王方用无比的耐心和超纲的严谨解决了很多专业性的问题,并最终给出了60多万字的译稿。在这个优秀稿件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了一轮轮的校改和审核,其中艰辛不胜枚举。2020年,稿件确认可以出版的当口,恰逢CIP的坎坷时代。最终在2021年,在出版社的大力协作下,它幸运地,得以和各位读者见面。
这本书国外首版是2008年出版的。作为一本就现在而言的老书,它却仿佛早早便预见到了今天的诸多社会现状。当然,科幻小说的预见性可以说是人们很喜欢的内容,而这本书的预见性在今日的一定程度上的体现,或者帮助我们见证了人类文明发展中,很多不可避过的必然之路。在这里,我只列出一个相对明晰的现状,更多的内容,等待读者阅读后自行感受。
首先,这个预见和反智主义有关系。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一词,是由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提出的。按照大众的看法,它大概是指:“对智力和知识分子的敌视和不信任。”反观2020年和2021年的美国社会,或许恰是这个词的延伸义的最好体现。不论是奇葩的喝消毒水对抗病毒,还是甚嚣尘上以至于矫枉过正的反抗运动,或许都在证明着理智、思考和冷静判断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这里反智中的“智”已经不是知识分子、学界精英等人,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思考的力量。而本书的故事,就建立在一个反智主义遍布社会的时代。
故事发生在一个已经有数千年文明发展的星球——阿尔布赫星,那里的居民在经历数次战争后,分化成了两个分支:被圈禁在集修院内的学者和在世俗政权领导下的普通人。集修院是作为战败方的学者们终生生活的地方,他们拒绝高科技和流行文化的侵蚀,以知识和思考为信仰,遵循传统的方式耕地、劳作,建立了一个仿如乌托邦的小社会。而集修院外的人们贫富差距悬殊,在世俗政权的渲染下,把知识和思考当作反叛,极度依赖着便利的科技和享乐的生活,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
先不说集修院中的生活。本书通过主人公的视角,借由一次特殊的节日——大隙节而展现除了集修院外的生活。院墙外的人们被各种多媒体设备便利和娱乐着自己的身心,也被它们蒙蔽着。看似便利的网络,却连想要搜索到真实可用的消息都很难,因为每一条真实信息都隐藏在数百上千条虚假信息之中,而每分每秒,虚假信息都会不断生成。人们普遍没有什么追求,在看似发达的技术中被圈养,沉浸在娱乐至死的生活中,受困于贫富差距巨大的阶级鸿沟,还被世俗政权通过各种手段监视着。知识不再能够改变他们的生活,有些希望孩子能够学习知识的人,只能在孩子幼时便把孩子送到集修院,期待孩子有机会能够进入。
上面提到的所有预见,影响每个人生活最多的大概就是网络和虚假信息。随着网络的发展,信息的真实有效性不断被质疑,并随着越来越多的假新闻而降低人们的信任度和敏感度。人们不再关注新闻的真假,而是简单从中收获片段式的快乐和虚假的肾上腺素飙升,用极端的语言发泄自己的情绪。真相显而易见成为最末端的牺牲品。回想鲍毓明事件引起的广泛社会轰动和最终让人大跌眼镜的真相,同样的事件正在不断发生。在大量虚假信息中,不信任、不关心的冷漠摧毁着人们的善意,也助长着构陷与伤害。在小说中,主人公面对早已无法辨认的外界社会的无奈,或者也是现实生活中,每个挣扎思考的人的无奈吧。
个人建议的阅读步骤:
1. 拆开本套书后,将词典单独放置。
2. 阅读作者序和译者序。便于大家理解这本书的基础设定,和译者对全书的很多设定的翻译考量。
3. 正式开始阅读内文,词典会成为你的好工具。清空你的大脑和固有印象,开始接受 阿尔布赫星的一切。你将会遇到用来调侃斯皮尔伯格的斯皮里(一种摄录机)……
4. 适当调节阅读时间,劳逸结合。毕竟,全书内容有点多。所以,不用三天读完。
5. 如果遇到思辨部分,不能理解,可以先略过,后续的故事会帮助你反向理解。
6. 全书读完后,请阅读我们特别邀请王存诚先生写的书评。在这里,你会明白这本书的理论支撑是什么。
7. 这个故事的结局,关于时间的节点与多重宇宙的选择,是非常有趣而新奇的(我个人最喜欢的部分),这部分建议仔细阅读哦。
这是翻译过程中和译者的沟通,有助于理解全书。
原文:前面说过,我们十年士用的是两座簇拥在一起的角堂,而非堂殿。最瘦的那座角堂里有一条旋梯,通向楼廊。楼廊是贴着高坛内壁的一圈拱廊,位于屏壁之上,尖顶高侧窗之下。
楼廊一头还有条通向敲钟点的小阶梯。珂尔德对此饶有兴趣。我看着她的视线沿敲钟绳向上,直望到主楼上方绳子隐没的地方。我敢说她不看到绳子另一头连着什么是不会罢休的。于是我们走到楼廊的另一头,开始攀登另一条阶梯。这条阶梯呈之字形,一直通到大院堂西南角楼的顶上。
问题:这一段怎么理解?楼廊到底是什么样的?
译者答:楼廊一词(triforium)本义为三拱廊,但在建筑发展过程中逐渐摆脱三的限制,从实际功能考察,主要是在大型室内空间中位于半腰高度的走廊,向内侧开放,外侧为实心墙壁。本书楼廊形制可参照布尔日主教座堂(A和B为楼廊),楼廊上方的高侧窗如A和B上方的长条花窗(布尔日是双层高侧窗,这不是所有建筑必须的,单层更常见),楼廊下方的屏壁可参照最底层的拱门结构。本书中所述角塔、角堂、主楼、飞扶拱的关系也可参照此图左图。
原文:再往上去就是飞扶垛的柱墩和角楼的尖顶了,大致和秩序督察总部的高度相当。尖顶不用梯子或登山器械是上不去的,楼梯则只能通到柱墩的顶部。到达柱墩顶部以后,尖顶之下是座镂空的石雕,刻着行星、卫星以及研究这些星星的早期宇宙学家,可谓整座集���院最精美的石雕之一。石雕的镂空处形成了一条供人行走的通道,通道的正中有座吊闸,这是一道可用摇柄升降的栅栏门。门后有一道在飞扶垛上凿出来的露天石阶,爬上去,就可以登上主楼。此刻吊闸正抬着,意味着我们还能继续上行。假如它落下的话,我们唯一可去的也就只有通往秩序督察庭的拱桥了。
问题:吊闸是怎样的,和电视剧里一样吗?飞扶垛是什么?
译者答:首先,原文中翻译成“尖顶不用梯子或登山器械是上不去的,楼梯则只能通到柱墩的顶部。到达柱墩顶部以后,尖顶之下是座镂空的石雕,”这部分和原著对比来说改动较大,一来将原本不详的方位说明具体化,二来修改了作者对雕塑部分的定义,修改依据见下图。
吊闸这部分的结构可以参照兰斯主教座堂的飞扶垛柱墩,不过图中的部件从上到下为:尖顶(pinnacle)→柱墩/镂空雕刻(pier/ carved statue);本书中角塔的部件从上到下为:尖顶→镂空雕刻→柱墩。作者对于镂空雕刻部分的描述使用了cupola / tower / walk-through statue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cupola是小圆顶,和哥特建筑很不搭,有可能是作者用错了词,tower是废话,因为整个角塔就是tower,所以这里译文只取镂空雕刻的意思,免得读者困惑。另外从视觉观感上,作者描述的石雕没有兰斯教堂的这么庞大,只可能占一层楼高度,是只能近距离观赏的,否则吊闸就得设在柱墩的底部,穿过吊闸也不可能登上飞扶垛顶部的阶梯。但这个细节大家无需较真,只有凭借误解才能获得如同兰斯教堂这样的美感。
原文:这镂空的墙壁是用手工雕刻的石块交织而成,组成的图案是泡沫状的分形(fractal foam)。她已经着了迷。我也忍不住地看着它们,想着自己为它们耗掉的时光,作为弟子,打扫这些石块和发条装置上的鸟粪全是分内之事……
问题:泡沫状的分形是什么样子的?
译者答:fractal foam纯粹是作者的创造,完全没有传统建筑来源,分形几何学是1967年由美籍数学家本华·曼德博(Benoit B. Mandelbrot)首先提出的,是研究无限复杂具备自相似结构的几何学。传统几何学的研究对象为整数维数,如,零维的点、一维的线、二维的面、三维的立体乃至四维的时空。分形几何学的研究对象为非负实数维数。哥特式建筑虽追求复杂,但未出传统几何学范畴,尤其追求规律与对称。分形美学在精神实质上与哥特美学相去甚远。此处在我看来相当诡异,比哥特与文艺复兴式杂交更加诡异。但估计一般读者会当成一个不好理解且无意义的词直接略过。没想好有无加注必要。若想对分形几何图像有直观印象,可参考下图。
原文:图莉亚是在十七年前被人在日纪门前发现的,当时她身上裹着报纸,躺在一个掀开盖子的啤酒冷却箱里。那时她的脐带蒂已经脱落,意味着她已经太大,被世俗世界影响得太深,所以千年士们已经无法接纳她了。而且起初她还生着病,于是就被安置在了独岁纪马特,毕竟从那里到公共医疗点更方便一些。在她六岁卒业穿越迷园之前,(据我想象)一直被居住在那座马特的市人的妻女们疼爱着。
问:马特不是住的阿佛特人吗?
编辑答:独岁纪马特却完全相反,把它建造出来就是为了威慑那些从外面来的人:每年有十天用来威慑墙外来的旅游团,剩下的时间用来威慑住在这儿的一年士,那些人发愿以后少说也要在这儿住上一年。
我们尽可能地还原了这个世界和这个故事。虽有不足,但确已尽力。希望各位读者可以耐心地读完它。或许,它不会成为大家最爱的一本书,但如果能为大家带来一点启示、联想,就很好了。
《失落的星阵》读后感(六):六步读懂这部硬核科幻史诗作品,到底硬在哪里?
文:王存诚(清华能源与动力工程系前教授) 美国作家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代表作《Anathem》,国内终于引进了。中文译名为《失落的星阵》,由酷威文化出品,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对当代外国文学涉猎极浅,对科幻作品更少拜读,之所以写这篇书评,是因为机缘巧合,在该书翻译期间,做了部分专业性的校对及审核工作,一瞥之下被惊艳到了(这是一本拿起来就很难放下的书),通读之下更是有很多心得想与人讨论、分享。 故事梗概——外星人版的“第一次接触” 《Anathem》英文原著2008年出版,《圣地牙哥联合论坛报》(San Diego Union-Tribune)对该书的评论很精准,那就是三好图书——好的历险故事,好的成长故事,好的第一次接触(first-contact)的故事。 “第一次接触”通常是指地球人类与外星来客的初次遭遇。而该书描写的,确切的说应该是外星人与相对于他们来说的外星来客的初次遭遇,而且这个外星来客里居然还有地球人。 故事发生的那颗行星叫阿尔布赫星,存在于与我们所在的宇宙分隔的另一个宇宙,它的发展程度要比地球先进几千年,虽然两个宇宙相互隔离,却受着相同物理规律的支配,因此它的历史和现实,包括其上“人类”的形体结构和思维方式都与地球十分接近。 但那里的信息(书中称之为given)却可以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在不同宇宙之间流动。 入侵阿尔布赫的外星(不光是外星,甚至是外宇宙)飞船,就是受到这种神秘信息的感召而来的。 在此之前,这艘飞船已去过四个不同宇宙,登陆过那里的行星,飞船上载的就是来自四个宇宙的居民(包括地球人),他们已经无法回到原来的宇宙,成了太空里的永久流浪者。 外星人来阿尔布赫的意图很明确,就是掠夺资源,供飞船维修和补给。他们带着杀伤力极强的热核武器和动能武器,巡弋在环绕阿尔布赫的轨道上,可想而知,会引起怎样的混乱和恐慌。 而阿尔布赫星居民大致分为两类——知识分子和世俗大众,其中知识精英阶层被称为阿佛特人,由于某些历史原因已经被隔离于世俗社会之外,过着苦行般的修道院生活。飞船来袭之际,世俗政权一边试图蒙蔽大众,一边重新把他们征召起来,以谋应对之策。 被征召者中,一批来自偏远小集修院埃德哈的阿佛特人成了主力军。小说第一主人公,年轻的伊拉斯玛修士也在其中,昵称拉兹。那时刚成年。 这些人既要经历身体的历险,独对强敌,长途跋涉穿越大陆以及最后乘火箭突袭外星飞船;也要经历思想的历险,前无古人的完成探索,从而获得对外星来客以至宇宙和意识本质的了解。而我们的少年,要通过重重考验,完成蜕变。 另外还有一条暗线,主人公是拉兹在集修院中的导师奥罗洛。当奥罗洛率先察觉外星飞船入侵的危险时,不惜违反戒律,采取激进手段对入侵者进行追踪,甚至试图与其展开“第一次接触”,结果被集修院革出教门。原著书名《Anathem》的含义之一就是“诅革”。 最终,奥罗洛在外星飞船发动袭击时为保护重要证物而献出生命,被尊为圣者。
文字游戏——从书名就开始了 原著书名Anathem是杜撰出来的一个英文词,一开头,作者就表明这个词是用“anthem(圣歌)”和“anathema(诅咒)”作的文字游戏。这两个词分别源自拉丁语和希腊语。 因此Anathem在该书不同语境里,分别代表两种含义。在这个世界举行庆典时,代表合唱的“祝歌”;在出现不安定因素时,则代表“诅革”,即将不遵守传统教义的异端分子以一种庄重而严厉的仪式革除出去。导师奥罗洛就遭到了“诅革”。 个人认为作者此举不纯粹是“文字游戏”,而是试图用这个词的两面性来表达一种思想——要维护一种传统和一种秩序,需要两种经常的仪式:一是持续歌颂传统,一是时刻警觉,随时驱除破坏秩序者。 矛盾且统一,作者用这个词作书名,反讽的意味不言而喻。但可惜的是,Anathem很难用对应的中文词汇醒豁地表达出原意。 现在这个译名《失落的星阵》,“星阵”原文为starhenge,是作者借鉴stonehenge(石阵)造出来的,指天文台(不过网上已有人用这个词来意指“文艺明星阵容”,与书名无关联),象征故事中的知识界,仅被允许保留最古老的科技设施,如果连它也“失落”了,“真正的智慧”就被逼上了绝境。 另外,英国顶尖科学刊物《自然》(Nature)杂志有为科幻作品(包括小说和电影)写评论的传统,2008年第456期上,伦敦大学学院UCL细胞生物学家(也写小说)珍妮佛·罗恩(Jennifer Rohn),为《Anathem》写了一篇书评,题目为《智能的囚徒》(Imprisoned by intelligence),着眼于这部作品反映的科学与社会的分裂,把作品对这种分裂可能导致的后果的预测,看作一项“思想实验”。《智能的囚徒》似乎也可以挪来用作中文译名。
类型标签——硬科幻无疑 该书到底属于什么类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当然,它是小说无疑,且属于流行(通俗)小说范畴。但却不因通俗而缺乏文学性,不因虚构而缺乏现实性,也不因幻想而缺乏科学性。甚至相当于展开了对人类认知以及可认知物本质的哲学探讨。 原著出版后,国外有人称其为科幻小说(SFF - Sci-Fi / Fantasy,Science Fiction & Fantasy),奇幻史诗(epic fantasy / epic-length fantasy),推想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传奇故事(narrative saga),理念小说(novel of ideas),或赛博朋克(cyberpunk)小说。另外还可以贴上“百科式科幻”“硬科幻”,“乌托邦”“反乌托邦”等标签。总之界定越多越广,越证明该书内容的丰富和复杂。 该书在对所构筑的虚幻世界中的事物进行描绘时,一直竭力保持细节的真实性,建筑物、机械的结构和尺寸,飞船的运行、操纵原理等,都纳入了具体的数理考量。 例如那座二十面体的外星飞船,是靠自转产生人工重力的,它的尺寸设计和自转速度恰好能产生近似于地球表面的重力,显然是经过仔细计算的。 作者甚至请人专为阿尔布赫人设计了一套语言,虽然并没有完整用在小说里(也足够难为翻译的了),认真态度可见一斑。 因此,说这部小说是“硬科幻”,还是比较准确的。 不过也有细心的读者在书中发现了若干错误,倒不是出在高深的量子力学方面,而是出在初等的几何问题上。阅读时不妨找找看。
科学解决——遇事不决,量子力学。解释不通,穿越时空 看见网上流行一句话“遇事不决,量子力学。解释不通,穿越时空”用以形容那些理论不过关的科幻作品,如何不负责任的推动剧情发展。 《失落的星阵》不这么玩。在该书的“致谢”中,作者就明确指出作品所依据的三个真实的学术和技术背景: (1)丹尼·希利斯及其“今日永存基金会”的合作者斯图尔特·布兰德与亚历山大·罗斯等人施行的“万年钟计划”。——这项计划现在仍在进行,该书作者也是参与者之一。 (2)源于泰勒斯,历经柏拉图、莱布尼兹、康德、哥德尔和胡塞尔的哲学传承。——西方哲学史的主要脉络以一种镜像的方式嵌入了该书历史叙述部分,而故事情节发展中涉及的人物、学派和理念,都有地球上西方哲学的影子。 (3)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猎户座计划”。——这是美国曾推行的一项研究计划,试图用小型核弹爆炸产生推力作为火箭动力,后因环境污染考量而停止。小说中外星飞船所用的推进技术由来于此。 作者没提的另一重要背景,就是他学习和研究过量子力学。 当代自然科学发展有个趋势,就是试图把描述微观量子世界的规律应用到宏观甚至巨观世界中去,例如用来研究宇宙和人类的意识。这部科幻作品就是在文学上对这种趋势做出反应。 量子力学的“多宇宙观”,构成了该书科学幻想内容的基本框架,书中还探讨了对意识的量子解释,但多少有些游离于情节的基本框架之外。 多宇宙设定其实也屡见不鲜了,例如著名的儿童科幻作品《时间的皱折》(A Wrinkle in Time),时空皱折就是某种类似于“缩地成寸”或“虫洞”之类的东西。成书时间是1962年,作者麦德琳·兰歌(Madeleine L'Engle)是受到爱因斯坦和普朗克科学理论的启发。而在《失落的星阵》写作期间,多宇宙观已进入科学与幻想交界的边缘地带。 目前主流多宇宙观有两种: (1)早在1957年,休·埃弗莱特(Hugh Everett)就在博士论文中发表了对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诠释”(MWI),作为对“薛定谔之猫”悖论的说明。当时并不为主流科学界所重视。 直到20世纪70年代,经布莱斯·德威特(Bryce S. DeWitt)的宣传,MWI才成为被广泛接受的量子力学解释之一。按照这种概念,我们周围同一时空中真实存在着多个“平行”或“重叠”的宇宙,但它们之间并不能相互沟通,而在人们进行“实验”或“测量”时,就实现了其中一个世界,或宇宙。 这有点难懂,举个例子,装着活猫和死猫的薛定谔盒子都是真实存在的。但当你打开看时,只能有一个状态被感知,也就是说你进入了其中一个宇宙,可能看到的是活猫。而你无法知道的是,在另一个宇宙里,或许正有另一个你,在同一时间,选择了另一个盒子,因此看到了死猫。 (2)1982年,霍金提出量子宇宙论,得出结论说,我们存在的这个宇宙是由一次大爆炸形成的一个有限无界的封闭宇宙。接着他又提出,同样的过程完全可能在我们的宇宙之外形成其他的宇宙,只是受到“视界”(由光速极限所限定的时空观测范围)的限制,这些不同的宇宙之间也是无法沟通的。 作者在书中把两种多宇宙观烩进了一锅。 在说到外星飞船的来历时,用的是霍金的分离宇宙概念,飞船通过超光速飞行实现了不同宇宙之间的穿越。而在故事结尾,阿尔布赫人登上飞船后,故事情节出现了歧异的平行叙述。 这是书中最易令人困惑的部分——千年士嘉德带着主人公拉兹同时进入了多个平行宇宙,在不同宇宙里的同一条飞船上,情节发展截然不同。 说个题外话,就像鲁迅评价《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那样,千年士嘉德也是“智近乎妖”的存在。而且嘉德更近乎妖一些,因为毕竟活了千年。这种同时穿越进几个平行宇宙的能力,千年士才有。 霍金曾提出疑问:不同的宇宙是否会有不同的宇宙常数,也就是说它们是否遵从相同的自然规律?他去世前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文仍是论述多宇宙的,不过这次他提出的模型似乎回答了自己的问题。 依照这个模型,大爆炸是唯一的,但爆炸后形成的物质按分形的模式向外扩散,不同的部分在一定的时空节点上内卷,从而形成各自的宇宙。这样形成的多宇宙,既然是同一来源,自然应该遵从相同的自然规律。 作者的设想似乎与此不谋而合。他用“有向无环图”构筑起一个成体系的多宇宙模型,每个宇宙在作者描述的“亥姆空间(位形坐标系)”中形成一条轨迹,小说主人公们就活动在这个多宇宙中的一条“世界轨迹”上。 作者这个模型的独特之处在于,不同的世界轨迹之间是可以发生接触和碰撞的。 首先,信息流(他用英语given来代表)可以向处于时间下游的其他宇宙传播,而原始的信息则有着唯一的共同来源,书中称为“叙莱亚理学世界”,也就是纯粹理念的世界,其中充满只有“圆”“三角形”等纯粹的数学理念。 这个理念世界处于最上游,所有宇宙都接受来自那里的信息,因此都遵循相同的自然规律,也就是都拥有相同的宇宙常数。甚至不同宇宙中的智慧生物都具有相近的结构和形状,他们之间通过共同的“信息”构成亲缘关系——这在书中是用“表亲(cousin)”一词来描绘的。 其次,有智慧的生物可以在不同宇宙之间穿越,该书情节就是这样展开的。 基于上述设定,《失落的星阵》中,来自不同宇宙的智慧生物可以通过语言翻译交流,几何学更成为他们的共同语言,外星飞船上醒目地标志着勾股弦定理证明图解,它与阿尔布赫人的几何知识是完全一致的,因此阿尔布赫人把外星来客称为“几何学家”。 多宇宙观本身并非幻想,至少已是某种科学假说。但该书中出现的涉及多宇宙及意识本质的诸多情节和论辩中,确实也包含着若干幻想的成分。 例如,故事里不同宇宙中的物质虽然对应相似,但在原子结构上却有细微的差异,以致激光具有不同的光谱,不同宇宙的“人类”不能呼吸其他宇宙中的空气,也不能消化彼此的食物。 不仅如此,改变物质原子结构已成为阿尔布赫星上很实用的高科技。更有甚者,千年士们可以通过修炼,改变自身的原子结构,从而延年益寿,并具有穿越平行宇宙,以至改变过去或未来的超能力。 这些情节,经作者以合乎逻辑的方式娓娓道来,还真能给人文学享受,也会诱发读者在科学层面的思考。
哲学思辩——每个存在都有对立面 作为一部科幻作品,该书对与科学相关的哲学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特地为阿尔布赫星上的知识体系造了一个词Theorics(中译本译为“理学”是合适的,但应区别于我国传统儒家的理学)。而且把是否钻研和精通“理学”作为在精神上区分精英界与世俗界的标志。 故事里的理学界,又因哲学观念不同分化,主要有两个对立的大派别——“普洛克会”和“哈利康会”。两派斗争构成该书情节发展的一条重要的哲学脉络,阅读时有必要加以厘清。 两派分别对应地球上西方哲学发展的两条脉络: 普洛克会对应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的“唯名论(bominalism)”和近代哲学中的“经验论(empiricism)”。 哈利康会则对应中世纪的“实在论(realism)”和近代的“唯理论(realism)”。 中世纪经院哲学主要与宗教相关,而近代哲学则主要与科学相关。两派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认为人们只能通过经验认识具体个别的事物,而后者则认为能够通过推理认识抽象普遍的理念。 作者在构建他的“多宇宙”模型时,是倾向于哈利康会的立场的,因为这个模型和故事情节都承认了“叙莱亚理学世界”和信息流(given)的真实存在。 有趣的是,在作者构筑的阿尔布赫世界中,社会由于哲学理念的不同发生了分歧。普洛克派的传人组成了“句法学会”(地球上的计算机在那里就叫作“句法机”),而哈利康派的传人则进入了“语义学会”。 在世俗界和宗教圈,人群则按信仰不同分裂为“慕像者”和“慕形者”。两派的修士,修炼到极致(千年士),则可能分别成为“雄辩士”和“咒士”,前者能改变过去,后者则能改变未来。这些“捉对厮杀”固然是剧情需要,也未尝不是我们这个现实世界的一幅漫画像。 也有人说,该书最大的对立面是科学与社会的分裂和对立,毋宁说它要揭示和批判的是社会自身的分裂,是精英界与世俗界的对立。
文学预演——悲观与光明的循环 该书哲学部分和科学部分是相辅相成的,作者用文学手段将之完美缝合。显示了非凡的勇气和驾驭能力。这一尝试基本上是成功的,不过有些过于繁冗的论辩,偶尔也会让读者溜号。 尼尔·斯蒂芬森曾在一次访谈中谈到“通俗小说(popular fiction,genre fiction)”和“文学小说(literary fiction)”的区别,大意是:前者的价值是由书籍市场的排行榜评定的,后者是靠文学界的同行评议。 所以这部作品理应是通俗和文学性兼备,一边获奖无数,榜单靠前。另一边,作者创造的阿尔布赫星世界,与诺奖得主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魔幻世界及莫言作品中的高密乡,在照映现实上异曲同工。 阿尔布赫星比地球先进了数千年,可以说是对地球未来面貌的一种预测。 那里科学高度先进,技术高度发达,却反而造成了毁灭性的恶果。甚至不得不把智能(智者)关进笼子。 那里已经实现了世界大同,没了国家疆界,但社会却因思想割裂。每个集群内部,又分化出更琐碎的阶层、族群、教派、学派…… 政治的肮脏膨胀、大佬的昏庸虚伪、学术权威的自以为是和专横、民众的愚昧、先知先觉者的无奈、年轻人的彷徨,无人幸免,也无一不是现实的映照。 如果这就是地球的未来,斯蒂芬森无疑是位悲观主义者。但他又给故事安了个好莱坞式的光明结局。 与外星入侵者达成和解,知识界与世俗界的隔墙被打破,主人公载誉归来,有情人终成眷属……阿尔布赫实现了第二次“大改组”,阿佛特人争取到同等地位,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在外星飞船践踏过的废墟上建起了世外桃源。 但作者毕竟是位现实主义者。于是最后一章开头,出现了这样的句子:人们正在给这片新开辟的殖民地建起一道围墙…… 黑暗与光明,本来就是此消彼长,也算基本保持了整部作品反乌托邦的主色吧。 其实,科学、哲学、文学的终极目的一样,就是影响、改变未来。写好哪一个都不容易,把三位融为一体就更不容易了——这也就是我被该书吸引的终极原因吧。 如果你也对该书有兴趣,可以看看维基百科(Wikipedia),上面能找到Anathema和作者Neal Stephenson的详细条目,而且出现了一个独特的Anathem Wiki网址。这个网站自2008年建立起,至今已收录200多个条目,包括情节、人物的“剧透”;对书中虚拟历史人物和新创词汇来源的索隐;以及对内容漏洞(包括情节错误和科学内容偏差)的揭发。均为读者自发。 当然,正如这个网址给出的敬告:如果读者要享受自己猜谜的乐趣,最好先别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