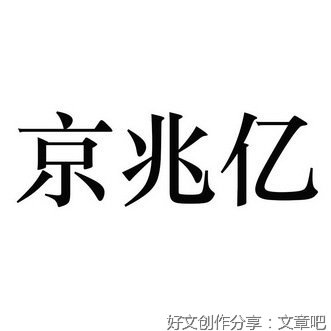《京兆集:半通斋诗选二编》读后感100字
《京兆集:半通斋诗选二编》是一本由刘炜评著作,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页数:347,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京兆集:半通斋诗选二编》读后感(一):半通斋主素描(转胡安顺教授评)
胡安顺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半通斋主者,商洛才子刘炜评也,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斋以“半通”名,而志在全通,是故于文学评论、诗文创作、戏曲说唱等皆有研习,所谓倜傥博物、触类多能矣。性好古,有节概,喜交游,疾恶俗,是是非非,颉颃傲世,常寻竹林纵歌之乐,每效阮籍穷途之哭。然畅饮而不至大醉,讥议而不失其度,谈谐而不在取容。歌主秦声,诗擅格律,文颇恣肆,友多名流。其为诗也,素有“挚情、正义、美境、丽辞”之自期。摛藻有别才,吐辞张心声。每见不平,必有慨发。嗟忧黎元,肠内恒热。怀抱风人之旨,或得意而忘时。年才逾不惑,而自撰墓表诗曰:“墓主生前号半通,皮囊昨夜赴虚空。痴狂一世多悲喜,毁誉由人爱恶中。”虽属滑稽戏谑之语也,亦足示其鼓腹行歌、卓尔不群之态。其诗炼句好用典,选字频取血,又显见其笔阵既列,风格已成,盖积学激情所致、时代使然也?抑或心有磊块,欲借古求通也?抑或意不在当今,拟藏之名山、求知音于后世也?昔人评仲晦、子美有云“许浑千首湿,杜甫一生愁”,余戏炜评诗曰“半通满纸血,典密使人愁”,未知可乎?
商州山人胡安顺于陕西师大菊香斋
庚子年六月十日
《京兆集:半通斋诗选二编》读后感(二):刘郎炜评诗印象(转方英文评)
方英文
(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才子”一词在中国,大抵指诗写得好,而且是旧体诗,格律合谱。以此才子标准高帽子,吊挂直升机,转遍今之长安城,我以为落到刘郎刘炜评头上,合适。
印象里的刘郎,有事必吟句,无聊亦别裁。如母鸡里的超凡劳模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日产一蛋么哥大哥大。光阴三十多年,其数累计,是否接近或业已超过史上最高产诗人陆游?得由刘郎自答读者。
刘郎的诗我爱读,原因是古奥多典,时遇生字头大——正好借机查阅辞书,增益学问。诗人取材宽广杂碎,庄子宇宙,杜甫春韭,只要来了感觉,一概入诗,且每成佳构。如此雅淫诵癖,难免为过诗瘾而无厘头、瞎胡闹。故统而观其诗,不无斑斓多姿、异彩竞秀。但其身份却决定了整体诗作的主色调:士子心一颗,情怀家国肠。
古来诗人往往一身毛病,却经常是真理在手的架势,可爱复可笑。回望百年中国人物,刘诗几乎一一梳理过,一番沙场秋点兵:或臧否以律绝,或慨叹于词曲。臆测他写诗时,心里是颇为自雄的:俺要像司马迁那样,不可缺席重要人与事;诗艺攀比杜子美,修辞上力求险绝而工稳。这般努力,意义甚大。不是说国学当务之急嘛,完美的格律诗最能表率国学噢!
刘族出过一个最高领导人刘邦,一辈子写了一首诗,仅三句,却传颂了两千多年。其后裔刘郎,目下尚难遴选某首比肩其祖。如此类比有点抬杠,概因不顾时空与各自平台也。主因是刘郎诗量太大了,拔萃起来费事。一个大托盘端出一颗珍珠,定然光彩四溢。一托盘全是珍珠,势必互吞其辉。
对于格律诗我一向神往,却始终不能创作。倒是很有幸,常被刘郎当作诗料,大概是被他写得最多的一个家伙吧!不由窃喜,如同汪伦被李白写了一句,便名扬千秋。
《京兆集:半通斋诗选二编》读后感(三):《京兆集》的善意和关怀(转孙尚勇教授评)
孙尚勇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从西安回到成都,三年倏忽而过。己亥春节前,炜评兄寄来《京兆集》稿本,希望我写一些感受。我多年从不曾认真写过旧体诗,偶尔酒后或受外物刺激,也会乱诌几句,但自知在这方面是个门外汉。炜评兄之所以要我“说几句”,大概主要出于两个方面考虑。第一,我们的确是“钟楼的朋友”。在西安十年,他待我如亲弟,每有提携批评;我待他像亲哥,时时找他喝酒求教。我们时而推心置腹,时而谑浪调笑。炜评兄不讳言自己的朋友有分层,曾打比方说,一些属于钟楼那块的,一些属于一环路的,二环三环的最多。记得一位同事并朋友大惑不解:为何孙尚勇来西安时间不长,却成了刘炜评的钟楼朋友呢?我想,生活中很多特别出色的人,是不需要朋友的,炜评兄和我则都需要,这或许是我们能成为钟楼朋友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京兆集》所收诗作的很大一部分,写于我在西安的十年间,因而直接或间接承载着我们之间的互动。若干吟章涉及的部分人和事,我不陌生甚或熟知,另一些则有我在其中。
古今受制于性情者,其往事甚多不堪回首的沉哀,其人却又屡屡执着于回望。故傲岸如李太白,清狂如杜子美,回首往事的诗篇,往往写者嘘唏,读者涕零。西安十年,在个人的小圈子里,我以嗜酒、狂妄和疯癫“著称”。故回到成都三年多,不得不稍稍远离酒狂等等,亦常常讳言往事。“悦读”《京兆集》,却让我不得不将往事翻开。
《京兆集》八百多首,写人之作最多,最见崇真扬善弘美旨趣。这方面的代表作,可推“素描”同窗三十八人的组诗。炜评兄之于世俗之人,就如他待我,有认同,有喜欢,也有嫌恶,然更多悲悯。即以其同窗和友朋而言,我认识的十多位,似乎都不如诗中所写般举止华美,被他所状写评说的,却多是这好那好,这当出于他内心的善意体恤。想炜评兄之所寓目,未必皆是美好的感受、正义的激扬,但他之所措笔,总是着意于“堪慰夙怀俱保真”“人间正道两心知”,这恰恰是当今需要格外提倡的人文情怀。
自鲁迅把他的投枪掷向普通中国人的国民性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的读书人,似乎都能从他的文字中,读出我们自身国民性的丑陋和残缺。但现实太骨感,处于不同年龄层次、不同位置的凡夫俗子如你我,既无可奈何地看着彼此,又各自带着无法逃脱的种种遗传,带着些许自信与自期,认真投入地奋斗着,顾不上找机会体验情感和美。“未惧命途多辗转,难言世道是炎凉。”我们大多数人已经属于不观察、不思索之辈,所谓学而不思者。我正是这样,走着走着,一回头,发现自己半死在路上。而今读《京兆集》,不禁为自己的经历过而感动万端,而泪流满面。
十年在西安和西北大学的经历,给予我的滋养很多,我在那里体验过的沉痛和飞扬、意得和绝望等,不少都既影影绰绰又真真切切显现于《京兆集》的字里行间。炜评兄热眼如烛照暗室,而每有温馨临拂于我,实是我不幸人生中之一大幸。
《京兆集》所收诗作佳美者尽有,然一些即兴率性之作,似欠缺更为细致精微的描摹,就中体物又大不如体人。我总以为大自然比人堪怜许多,愿炜评兄的诗眼诗心更多关切于山水草木,像少陵那样获得更多的自在,尤其在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