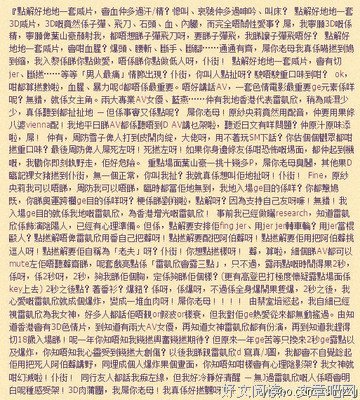专家之死读后感锦集
《专家之死》是一本由[美] 汤姆·尼科尔斯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页数:2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随着信息技术和教育的发展,人们可以平等而方便地获取越来越大量的信息。但是掌握信息是否就意味着掌握了知识,拥有了智慧,具备了在处理实际事务方面的资格、技能和权威?人们相信网络而不再相信事实,相信自己而不再相信更有可能掌握事实的他人。在一种盲目冲动的情绪中,人们拒绝知识的获取,理性的判断,和行动技能的提升,在自以为是的封闭空间里,在一种反智主义和平民主义相结合的非理性文化心态中,社会面临着涣散和分崩离析的严重危机。尼科尔斯的忠告是,专家依然是我们所需要的,而我们更需要的是理性思考的能力。这是健康社会运作和未来发展的前提。
●一个进步的社会与国家是需要专家的。
●书中的内容虽然是描写美国社会,但何尝不是现今很多国家的缩影,人人都认为自己的智商不比任何人低,自己的看法才是正确的"证实性偏见"布满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认为人人应该享受到一切的平等对待。无知的自满很容易使人拒绝一切反对观点和真理,只选择接受和自己一样立场的人和物。
《专家之死》读后感(一):让反对更理性
今天,距离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1962年出版《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已经过去了近60年,然而特朗普的当选和有可能的连任告诉我们:反智主义从未离开,不要高估了文明社会里的“智性”影响力。作者尼科尔斯从专家与平民的话语权争夺、人类思维陷阱导致的沟通困难、高等教育低质化、信息爆炸导致的信息匮乏以及新闻的娱乐至死等各维度剖析了“专家之死”的原因。
柏拉图笔下生而睿智、具有绝对正确的智识理念的金人毕竟是幻想。专家的倒下无论是过去时还是进行时,这从来不是一个新问题。如果反智是当前阶段的民主社会的副产品,人们仍然要对此有所警醒和节制,应该尽可能在善意下出发,在自我检省的氛围下运作,避免其扩大、失控,我们才能真正的守护文明。
尼科尔斯的著作就社会发展给反智主义带来的新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然而就核心问题的探讨而言,霍夫斯塔特的著作仍是振聋发聩的经典。
《专家之死》读后感(二):有驳没有立
想要结束反智主义的盛行,绝对不是简单粗暴的「请相信专家」就可以。我们需要好的教育,而书中有关教育的一章主要是对大学教育的抱怨,对大学教育存在的问题这一事实的重复描述对读者没有任何价值。
我们需要为下一代提供一个尊重科学的氛围,需要在教育中重视逻辑思维、统计思维、概率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等思维能里的培养,需要提高对认知能力的重视。在教育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不少教授坚持对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在互联网环和新闻媒体方面,我看到国内的(国外的看不到,哔~)少数优秀的媒体和自媒体在专业性报道和深度报道上做出的努力和成就,而且拥有不少的读者。我们需要有能力识别出这些媒体(或者说是信息源)。
在非专家群体中,也有很多不反智的民众。专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做的,是怎样让其他民众变得更接近这些不反智的民众,而不是批判和抱怨。更重要的是,面对社会困境,我们应该继续向前走,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而不是倒回去——维护专家的权威。
有驳有立才是一本好书。考虑到改变社会这个复杂系统的难度,以及解释和分析现状的必要性,这本书不应该只是受到批评,而是应该被仔细阅读。不过,在中文的特殊语境中,不带着怀疑眼光就去看这本书很可能是有害的。
对于已经阅读了这本书,或者通过其他的信息源意识到自身的反智行为的读者,大可不必担心,不用纠结和专家知识水平的差距。一点点基础的逻辑知识、基础的统计学知识,和一颗不甘于做一个「理直气壮的糊涂蛋」的心,就可以帮助自己告别反智。
《专家之死》读后感(三):据“教育商品化”谈一谈我们高等教育
今天的国内高等教育仍然活在公立教育的制度体系内部,并不如尼克尔斯描述的美国教育一般——学生成为高等教育行业的客户,但对比美国高等教育的输出结果,二者却是出奇的一致。我们的毕业生和美国的毕业生一样,经过了美妙的四年,自尊见长知识却鲜有长进,大学的经历没能养成批判性思维的习惯,却失去了继续学习的能力,学生面对复杂问题同样不知如何平衡。
按照尼克尔斯的逻辑:今天的美国有着大量的学生涌入大学,大学教育变得日益商品化正是拜学生与学校数量增长所赐,而顾客至上恰好是商品交易的基础体现。由此解释了为何美国高等教育变得“顾客至上”的道路。
回顾我们的教育,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二十年的时间,大学生数量不仅逐年增长且增速快于绝大部分国家,我们的高等教育发展经历了阶段性的飞跃,但问题同样显著。
首先,不同时代的大学生所代表的含义不尽相同,经历了高校扩招以及教育改革后的今天,大学生已经离我们眼中的“天之骄子”渐行渐远,所有人不愿承认但又不得不承认的是如今的大学生并不像过去一样可以证明她身上显著的“特质标签”,相反她只能证明你在对应的年纪完成了你应该接受的高等教育。而这正在不断损坏我们的学历价值,同样摧毁”大学“在人们心中的意义。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我们的大学掀起改名风潮:大专院校更名学院,学院更名大学,地方院校不再“偏居一隅”名号从市到省,传统行业院校不甘落伍,努力沾上时髦的标签,即使已经是重点大学的高等院校,也要努力附上“一流”大学的身份,08年—13年五年时间竟然有四百余所学校选择更名,急功近利的中国教育以此简单粗暴的方式吸引学生的选择进一步培养急功近利的学生,让人瞠目结舌。
吸引学生选择大学的方式当然不止更名一种,如今奇葩的方式更是层见叠出,清华大学”女神营销“的招生宣传,各个高校不断建设的’新’校区以及泛滥的大学排名等等。作为教育的输出方,面对日益增多的准大学生,却以千奇百怪的偏离教育的方式吸引着目标学生。我们的大学虽然算不上“顾客至上”,但却同样正在失去作为教育中心的主体地位。
二十年的时间我们的大学变成了文凭工厂,国内日益增重的”野鸡大学”比例是大学在今天日益变成文凭工厂的直接证明。野鸡大学虚高的学费与其对应与教育相差甚远的教育内容,恰恰是受到文凭文化的影响,在文凭文化主导下,大学成为学生接受培训而不是接受教育的场所,但不幸的是,文凭的价值在今天并不能代表学生接受了教育,他只能证明他按时支付了大学学费。
如今,大量学生涌入大学的同时我们的大学之路已然发生质的改变,曾经的凤毛麟角到今日的普通寻常,这也导致了大学毕业生的质量急剧下降,她们缺乏专业性,更要命的是她们缺乏该有的批判性思维。言听计从的孩子们让大学课堂变成了一言堂。而另一方面正如作者所言,大学生接受教育不足的同时却接受了过度的赞誉,一旦离开便要吃尽苦头。
想必留给中国高校和高校毕业生的难题并不比美国轻松,我们的高等教育在太多“学生”,太多“高校”,和太多“学历”的叠加效应下逐渐失去大学的教育使命。正如作者所叙述的那样我们已经不能再指望大学毕业生在生活中引领“理性辩论和讨论”,分辨“知识和感觉”。
如今,我们已经危机深重。
《专家之死》读后感(四):中国教育的镜子
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是不高的,作者可能本来就是想写一本针对大众的通俗性读物,让大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在里面涉及大量大众文化(电影、畅销书、互联网等)事件、公共政策事件等,他往往是简单介绍这些事例来论证他的观点,或是引用一些名人的话语,但没有怎么深入分析一个案例。 而且作者在美国这个民主社会,非常敢说自己认为的大实话,很有精英意识,挺不政治正确的。我草草阅读后,略微归纳了一些观点。
作者尼科尔斯首先指出了平民对专家权威和意见的不尊重与否定这一现象,然后在第二章对专家和平民的对立做了进一步的描述。
本书中,我会交替使用“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和“专家”这几个词,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指代那些掌握了特定技能或知识体系的人,并且在自己的人生中践行这一技能或把这一学科的知识当作终身职业的人。(p33)真正的专业知识,也就是其他人所信赖的那种知识,是教育、才能、经验和同行肯定的综合体,虽然无形,但可辨认。(p34)于是尼科尔斯开始进行因果分析,即为什么会有反智主义思潮?为什么平民反对专家的意见?第一,达克效应,“越愚蠢的人,越是会高估自己,不觉得自己无知”(p50);第二,证实性偏见;第三,民间传说、迷信和阴谋论;第四,刻板印象和一概而论;第五,不接受彼此在学识和能力上的差距,“你好我也好”。
第三章是我着重关注的“高等教育:顾客永远是对的”。尼科尔斯认为美国大学已经成为“多年假期套餐的商品,而不是与教育机构和教职员签订的一场求索知识教育的契约。大学的商品化,不仅严重破坏了学历的价值,也摧毁了大学在普通美国人心中的意义”。如今商品化的大学成为一个文凭工厂,提供的不再是教育,而是培训;美国本科大学迎合学生和家长的需求,有钱的家长过度保护孩子,学生现在可以不需要与室友共享空间,对教授发随意的电邮,这种不尊重老师权威的行为进而“美国流行的一种肯定和自我实现的文化”(p86)有关。
大学和学院具体做了什么事情强化学生是顾客的观念,降低对专业知识的尊重呢?第一,如今专业类的小学院纷纷开设名校才有实力开设的学科和课程,这会让学生对自己的能力产生误会;作者在这边比较反对的是课业负担变轻和学分标准变松,分数膨胀问题,这是就业市场、学生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共谋,但学校在其中这么做是不负责任的。第二,学校鼓励学生给老师测评。
作者特别指出了大学中一个悖论:“大学生一方面要求管理学校,另一方面又要求学校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他们。”
到第四章和第五章,作者都在阐述信息时代泛滥的假信息,他认为互联网助长了错误的信息的盛行,但却让大众自我感觉已经掌握了很多“事实”;新闻行业中“形式压倒内容,全力比拼速度,再加上现代大学盛行的偏见,一环扣一环造就了错误信息的三连胜。”作者认为年轻记者在大学中接受的新闻学教育是“均质化的过程”,他们“眼里只能看到自己认同的东西”。那么怎么办呢?记者应该尽可能多去了解所报道的领域的知识;专家在感觉被记者下圈套或是断章取义时学会严词拒绝,记者“还是会尊重和如实抱到你的观点”的;读者则要在看新闻时学会“谦恭虚己、混合吸收、少点儿偏激、多加辨别”。
到第五章结束时,作者已经列举了几个要为专家之死负责的因素:
我批评美国人的基础知识薄弱,批判自恋和偏激阻碍了他们学习新知,批评大学产业没有治愈无知,反而还成了帮凶,批判媒体认为自己的本职是娱乐大众,批评记者要么太懒,要么太嫩,总之没能做出正确的报道。于是到第六章,只剩下“专家”这个群体有待作者批判,比如同样会犯错,做出错误的判断、学术不端、没有预测成功。尼科尔斯指出,“真正的问题在于,专家应该在何时预测,又该如何预测,以及在专家出错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在结论部分,作者主要讨论的是如何处理专家和民众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崩塌,民主社会会停滞紊乱,陷入死亡螺旋,这一方面是因为民众文化水平下降、野蛮又固执,不信任不理解还去指责专家,另一方面是专家顾问和决策者之间的关系也会失败。作者认为现在专家在反抗民众对专业知识的攻击,这是一个好迹象。他主张民众应该接受教育以提高文化水平并具备公民道德,专家则要视自己为公仆而接受自己意见不被采纳。
《专家之死》读后感(五):“无专家时代”要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拉斐尔经典名作《雅典学院》你尊重知识吗?
对于这个问题,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会给予肯定的回答。然而,看看眼下的舆论场。不仅“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已经被污名化许久,连大部分专家,也被戏称为“砖家”,若是他在电视或者网络上抛头露面,更有可能被耻笑为不务正业。世人似乎得了一种怪病——一方面我们急于在各个领域发表个人见解,另一方面,我们又对这些专家不屑一顾。
反智主义为何会在当下如此流行?这是个多年来在舆论界备受热议的话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学者托马斯·尼科尔斯所著的《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一书,给了中国读者以救赎——通过该书,我们获知,原来对知识分子不服不忿不只是时下中国人独有的专利,而是一个蔓延全世界的普遍现象。
这种现象严重到什么程度?书中以两个例子进行说明。
书中提到了一项民意调查:2014年,俄罗斯与乌克兰发生冲突,美国是否应该军事介入。事实证明,只有不到1/6的人能在地图上正确指出乌克兰的地理位置,却有超过4/5的人满怀着军事热情表达着偏激的观点。热情与认知不成正比。
如果你认为这种基于无知的傲慢只在庸众中存在就错了,另一个例子提到了南非前总统塔博,此公在任期间坚持认为艾滋病是由于营养不良,拒绝听任何医疗专家的意见,并拒绝为患病人员提供医疗救助。其结果是在其执政期间,南非至少因治疗不当多死30多万人,并且有超过3.5万的艾滋病病毒阳性婴儿出生,艾滋病成泛滥趋势——正因为他打着鄙视专家的旗子,居然在卸任后获得了南非国内外不少人的“点赞”!
在全世界,一股反智主义的风潮已然崛起,人们在厌恶甚至恨不得消灭所有专家——这是《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一书为我们点明的恐怖现象。
那么为何会如此呢?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曾对知识分子下过一个定义:知识分子是“理念的处理者”。知识分子的工作始于理念,终于理念,就算将这些知识分子发明的理念应用于现实世界,对周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与知识分子无关,因他们并不对现实世界发生的后果负责。比如作为经济学家的亚当·斯密、哈耶克和凯恩斯并不从事商业活动,即便出现了经济危机,他们也可以依然高枕无忧,专著一本接一本地写,毫不顾忌有多少人为他们看似完美的理论经济模型失了业。由此看来,专家或者说知识分子,其实就是一种挺讨人嫌的存在。
在过去,人们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这种行为不得不忍。因为在信息时代之前,掌握知识的是少数派,而且时代越往前追溯,知识分子的比率就越低。知识的宝贵让人们不得不允许专家呆在“免责区”中空发议论。
然而,时代终究还是变了,二十世纪后半期,教育在全球普及,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不再占有知识的制高点,而对他们来说,最为致命的“杀手锏”莫过于互联网及其所带来的“知识液化”——知识不再像过去一样被锁在象牙塔中,而是摆在互联网上随手可得。当人们习惯于一遇到疑难问题就先打开手机“百度一下”时,无论对什么问题都试图将之复杂化的专家是不是显得更讨厌了呢?
专家在现代遭遇的另外一个打击,是他们与大众地位关系的改变。追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自人类文明史开端以来,越在古代,具有技术和知识的人群的地位就越高。在上古时代,识文断字者往往被视为能够通神的存在,而在中古时期,知识分子和专家群体跟社会的精英阶层(比如西方的神职人员、中国的士大夫)高度重合。到了现代,专家与普通公众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一书追问了读者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你把你身边的专家当作什么人?他是否跟给你送外卖的快递小哥一样,是你生活中的服务者呢?若果然如此,专家注定是个不合格的服务者,因为前文所述,专家不能为自己给公众的理论建议完全负责,而为服务负责,恰恰是现代商品社会对服务提供方的必然要求。
在《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中,尼科尔斯还分析了大众对专家不信任的其他原因,比如高等教育的商业化、沟通不畅、专家本身的原因。不过,这些都是尼科尔斯根据美国的现状做出的情境分析,并不太适合中国当下的现状。但尼尔科斯的一个判断无疑是精准的,专家无可避免地在走向衰亡。在不久的未来,人类也许要适应一个“无专家”时代,取而代之的只是那些不再以知识为傲的“知识从业人员”。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将要面临一场莫大的转型——如果你恰巧是一个爱知识并以具有知识为傲的人,这就是该书能为你透露的最有价值的信息。
------------
本文作者:王昱
2019年7月27日首发于齐鲁晚报
更多内容请阅读《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
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兴及其影响
作者:[美]托马斯·M.尼科尔斯
译者:舒琦
定价:58.00元
2019年3月
中信出版社·见识城邦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网络社会的“大数据”至上和数字媒体的“人性化”设计——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当代社会的人们似乎个个都是“高知”。
但是,未经鉴别的网络信息与真正的知识能否等同?高等教育文凭与理性思考能力是否一致?在一种自大、自恋、自我中心的盲目狂妄中,人们拒绝专业知识的获取,拒绝理性判断和行为能力的提升;在一种反智主义和平民主义相结合的文化心态中,社会面临着涣散和分崩离析的严重危机。
信息技术网络化!高等教育商业化!新闻媒体娱乐化!时代沉浸在对无知的崇拜中,专家已死!这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这是知识碎片化的时代——知识何在?听听一位专家写给其他专家和非专家的话。
-End-
见识城邦
中信出版集团社科人文品牌
为独立思考的人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