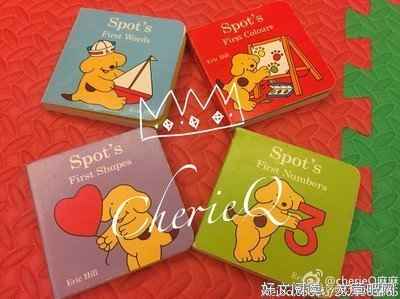《我们骑鲸而去》经典读后感有感
《我们骑鲸而去》是一本由孙频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页数:23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们骑鲸而去》读后感(一):我们骑鲸而去
实名表白孙频姐姐,我要把给80后作家的第一个五星献给这本书。其实《鲛在水中央》已经足够好了,这篇依然让人惊艳。
《我们骑鲸而去》像卡尔维诺的寓言,但要现实沉重很多,以岛屿和海洋铺展叙事,触及到许多可能,字数不多但具备长篇的分量,中后部一度有《蝇王》倾向,对自然辽阔的描写有菲利普·罗斯的势头。但终究还是写人的小说,所有可能都受到节制,落回人物形象身上,延续了《松林夜宴图》《光辉岁月》后对古怪零余人的偏爱,女人的故事更像是《白貘夜行》的《鲛在水中央》化,但她勇敢地使用莎士比亚做副本,对故事模糊化、人物偏拗化的处理,以及克制又充分,在节奏里恰到好处的描写,使小说摆脱了现实琐碎枯燥平庸的陷阱。比喻比以前少很多,依然有漂亮稀奇的名词,以及瞬间让人心悸的精准形容词。
如果说孙频早期还是张爱玲的弟子的话,《盐》,尤其是《我看过草叶葳蕤》对女性生活与身体的探索表现了作家更大的野心,在《松林夜宴图》之后更为温和开阔,《鲛在水中央》是近年难得一见的好小说。唯一槽点是,我还是觉得《天体之诗》《白貘夜行》用意明显略尬,《狮子的恩典》就要好很多。孙频的低调和作品的高质量,与同代许多作家形成巨大反差,她所偏爱的中篇小说似乎是现代汉语文学特有的文体,她在苏童老师和毕飞宇老师之后进行了很有个性的开拓,她已然是中文世界最好的作家之一。
《我们骑鲸而去》读后感(二):逃不开生命的本来——读孙频《我们骑鲸而去》
孙频的新作《我们骑鲸而去》让我想到了本雅明的话,每一个不能被现在关注而加以辨识的过去的形象都可能无可挽回地消失。 孤岛上的两男一女,事业不得志婚姻已破碎的小杨,曾经的艺术家老周,出狱之后被骗、失子的王文兰,他们无一例外地想逃开过去。这过去,便是压抑的个人历史。但这个避世的地方,哲学能解释清楚的观点,同样适用于这个狗会抑郁猪会自杀的岛屿。即便只有三个人,一样有明争暗斗,你争我夺,世俗纷争同样在这个小世界里活色生香地上演。 说到小世界,不得不提到老周的世界剧场,未必比古希腊的圆形剧场逊色。老周不止一次地提到“要用脑子,要活在自己身上”,想必是用了心的。三幕莎剧,四场岛屿戏,最后一出是留给自己的。老周从不谈论自己,每出戏,或多或少带着隐喻或暗示。哈姆莱特和霍拉旭说到了故事传承,麦克白对死亡的淡定,卡列班的好梦。岛屿故事中天堂庄园以血肉铸就的忠诚,族长和失败作家的生死探讨,饥饿中挣扎的船员以及六个工人的自相残杀。这一切暗合了三个被命运摧残的人的困顿,各自的较量,面临饥饿的状态,义无反顾的坚持。最后一场青年导演的戏,是终结,也是开始,如同苦难与幸福,不分仲伯。 他们要逃开的过去,虚虚实实,遮遮掩掩。但历史是否定不了,也躲避不开的。新的环境没有带来新的神话,却有着与过去惊人的相似。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人性。康德说过,如果我们抽掉我们直观的感性,因而抽掉我们所特有的表象方式,而谈论一般的物,则时间就不再是客观了。孙频笔下的时间是各种各样形状的,甚至是加剧了繁殖速度的一个种族。这也再次印证了本雅明的观点,时间肯定不是均质的、空洞的东西。 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的封面,女孩儿的长发如岛屿上的大片绿荫,整个人置身于海浪中如同命运的安排,眼睛微合,一只眼睛被鱼儿遮挡,另一只眼睛挤出一滴泪。但这滴泪终将汇聚在海浪中,被吞噬,被卷入,随波逐流,如芸芸众生。依靠岛屿力量获得的微弱心灵救赎,未能击败苟延残喘的历史生活。逃得出世外的纷争,却躲不过内心的困扰。 孙频的小说向生命的内里探索走近了一大步,虽然生命本身不是心理探究,也不单纯是我们所理解的岛外的种种世俗。只有在生命之中才能理解生命,无论是小杨的回归,老周的消失,还是留在岛上的王文兰。他们不再逃避,而是有所行为,进入了自己的生命轨道,真正为自己而活。只有生命本身才能进入生命。无论以什么面目呈现,哪怕他们的选择是乌托邦而不是一个确定的蓝图,此刻的他们,在意识领域中赢得了自己,活出了生命的本来。 历史让不可知的未来有了期待。
《我们骑鲸而去》读后感(三):在岛上寻找自我
《我们骑鲸而去》是孙频的中篇小说新作,故事的背景虽然只是在一座小岛上,发生的故事却很有深意,只有三个人在岛上生活,孙频的所有小说都有着曾经的记忆和痛感。
三个不同的人生经历的人来到孤悬荒废的小岛上生活,这座小岛没有四季,只有很热的夏季。其中的台词有:“这个小岛上只有我们三个人,好像全世界只剩下了我们三个人。我们成了这个世界的央。”在这样的一座岛上,难免会感到孤独、恐惧和害怕。这种孤独感使三个人有时间思考,还有对这些的反思,也许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在三个人都是在精神方面有创伤的人,中年女子王文兰杀死了家暴丈夫,坐了17年牢,出狱后,他的儿子却因为车祸去世了。这些打击换任何人都会垮掉,而王文兰在岛上却看到希望,她积极向上百折不挠的精神令人敬佩。老周莫名从小岛上消失不知所踪,令人若有所失,而我亦有所得。
在现代生活中,很多时候会使我们处于心中不安的状态里。城市的快节奏和职场的压力和人际关系的难处,感情生活的不如意。我们我们工作生活有压力,那也不妨经常在假期去晒太阳看书,过悠闲的生活,一位内心非常安定的人,心乱一切乱,心安一切安。不管是遇到什么事,亦复如是。什么荣华富贵,锦衣玉食都没有一颗安定的心重要。其实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看清楚事情的本质,把剪不断理还乱的烦恼放下,然后就会自由自在。 书中的文字优美,用悲悯的情怀关注人生,展现尘世的至善、大美,阐发人生哲理,文字或绮丽、或素朴,但都潋滟动人,闪烁着智慧的波光,荡漾着爱的温暖涟漪深受读者的喜欢。在悠闲生活的节奏之下,仿佛一切都变得那么美好。人生应该宠辱不惊,闲看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用一个平和的心态去面对这个世界,开开心心活好自己。两人每天都有令人新奇的新鲜事。作者用质朴的文笔讲述了活出自我、活出趣味的一个个故事。 虽然最后的结局是小杨的回归,老周的消失,留在岛上的王文兰。他们开始面对现实,不再逃避。总是想着干自己喜欢的,真正为自己而活。 读《我们骑鲸而去》后,就想找个像这个小岛一样的地方隐居起来,就像《瓦尔登湖》描写的那样,过几年属于自己的日子。
《我们骑鲸而去》读后感(四):我们如何“而去”? 如何能够“节花自如”?
何平/本文作者
中篇小说《我们骑鲸而去》涉及到的只是一座小岛三个人的偶遇。此种岛屿之书,实有还是异境,多为小说家言。一天可以转数圈的小岛曾经有十几个矿工的采矿业,说不上繁华,至多算一个小作坊,但这个小作坊给未来的岛民留下电力和通讯这两笔重要的遗产。老周,一个前导演;“我”,一个落魄潦倒的诗人,一个离婚的孤家寡人,谋得一份守矿的差事,寄希望于离群索居的写作,用以疗伤;王文兰,经历过失婚、丧子、杀人、坐牢、被骗巨款。三个人无一例外都是如散落海洋的小岛一样的零余人和失败者,却是不同命运的样本。如果算上王文兰高中热爱文学,三个人都有文艺生涯。无须奇怪这个岛上的“文艺团体”,也无须找出诸多案例来证明文艺家天生与岛屿的亲缘性。小说本身就是说谎的艺术,至少是虚构和想象的艺术。至少,文艺的濡染,在建构小说人和人、人和世界关系时可以触及到感觉的、抒情的和反思的各种晦暗、暧昧、难以言说的细枝末节。从小说的叙述角度,《我们骑鲸而去》虽然最终是通过“我”来完成全部叙述,但还是掺杂了老周和王文兰虚虚实实的往事与回想,这些不断被编织到“我”的叙述,扩张了“我”叙述的宽度、深度和效度。
孙频的小说几乎都关涉记忆和遗忘,伤痕和痛感以及对这些的反思和追责,她叙述的世界一向偏内在和内倾,只有赋予人物“文艺”性才有可能处理这么细致精微的内容,这是一个小说家的限度,也是其长处。限度不等于狭隘,好的小说应该自有一种扩张能力,读者可以在小说里从一个人去想象一类人、一群人、一个阶层人等,到达更辽阔更广大的地方。
作为零余人和来自欢腾闹热世界的溃败者,《我们骑鲸而去》不是过厌了锦衣玉食的现代生活而逃归荒野的所谓表演性的现代性叙事,也并非中产阶级鸡汤的灵修秘史。我们能看到的,他们是切切实实的活无可活的凋敝人生,如“我”,四十多岁了还是个小科员,在单位被人呼来喝去,老婆都说我没用。离婚后什么都归了老婆,房子也没了,又辞了职,就想找个地方躲一躲,躲开人类,写出一部《瓦尔登湖》那样的作品,但“我”更大的作用是叙事的视角。最值得注意的是王文兰这个人物,她的生命荒芜却向上,失败也跌宕起伏,屡败屡战百折不挠,代表一种最强悍的生命,即使已经沦落荒岛给富人可有可无的一个房产做个可有可无的看管,依然不妨碍她幻想在荒岛上开发旅游度假并且身体力行。她的生命在风尘仆仆中绽放微光,直至把灰烬攥出余温。孙频小说的女性往往都有从冷硬荒寒的世界不屈地拱出的力量和美的特质,王文兰也是这样的女性。至于老周在废弃岛屿度过的日常,真的如他所说“节花自如”?或者我们换个方式去看,一个有着敏感艺术之心的逃亡者,他所经历的孤独和恐惧,多少年,他是如何做到“节花自如”?他又有怎样的黑暗心史?与王文兰的喧哗和外张恰成对比的,老周的力和美是缄默的、内敛的。
放在当下中国小说里看,无需注水,《我们骑鲸而去》绝对是一个长篇小说的体量,但孙频却将它做成一个大中篇小说。这固然因为孙频对中篇小说文体的偏爱。事实上,同时代小说家里,能够像孙频这样持续地写出有质量的中篇小说的已经很少见了。把一个长篇小说的体量收缩成中篇小说,已然腾挪艰难。不惟如此,《我们骑鲸而去》还要回旋出大量的空间来安放小说中以戏剧片段方式呈现的副文本。我们当然可以说出许多副文本的好处和增益,比如复调、互文,比如意义的拓殖,但这些好处和增益都是需要以空间来换取的。但《我们骑鲸而去》,并不臃塞堆叠,反而因为副文本运用和调度得恰如其分,从而开放和延展了有限的空间。确实,我们所谈论的小说空间,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
可以看小说的第一副文本《哈姆雷特》最后一幕哈姆雷特临死前对霍拉旭的托付,“请你把我的行事的始末根由昭告世人,解除他们的疑惑。”“请你暂时牺牲一下天堂上的幸福,留在这一个冷酷的人间,替我传述我的故事吧。”孙频征用《哈姆雷特》这个片段不只是意蕴的彼此参证和召唤。在《哈姆雷特》,霍拉旭是故事的叙事者,而老周的故事最终也是由“我”来讲述。哈姆雷特和霍拉旭,老周和“我”,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老周的“世界剧场”演出的第一场剧就是《哈姆雷特》的这个片段,是不是暗示从老周遇到上岛的“我”开始就已经做好了弃世的准备?他也希望“我”有可能成为他的“哈姆雷特的霍拉旭”?小说的艺术某种程度上是时间的魔术师,借助时间的幻术,可以实现它的藏与显。就《我们骑鲸而去》而言,小说将这个戏剧片段提前,自然深意在焉,读者作为“被蒙蔽者”只有读完整个小说才能意识到其中的“深意”。
有意味的是,小说接下去老周为人偶的一段配音是哈姆雷特对霍拉旭的赞赏,却省略第一句“你就是我灵魂中选中的一个人”。如果我们意识到《哈姆雷特》这一句是和小说中所引用的部分本来连成一体的,那么,其实在“我”并未觉察(也许小说一直到最后“我”也没有能成为老周“灵魂中选中的一个人”)之时,老周已经自以为是地将“我”作为他“灵魂中选中的一个人”。人和人之不可相通,所托之人非所想,或者漫长的孤岛生活,老周去意已决,托无所托,只能一厢情愿地属意于“我”,这和小说整体的孤独感是相通的。作这样的判断并非是主观臆断,小说写道:“我们俩几乎每天都要见面,每天见了面他都是这般倾其所有,每天要请我喝椰子再请我喝茶,还要请我到他屋里,让那些木偶人为我表演《李尔王》《巴巴拉少校》《三姐妹》《暴风雨》,他对莎士比亚简直是热爱,总是夸赞莎士比亚如何伟大。”老周“倾其所有”的是物质,也是借莎士比亚戏剧而“倾其所有”的内心所藏。除了《哈姆雷特》,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和《暴风雨》也被接入小说的叙事,好像孙频熟谙了嵌入和弥合术,接入的副文本自然地汇入小说的叙事流,同时也发微、发明着小说的意义和结构。
我自然会猜测孙频为什么会选择莎士比亚这个并不冷门的剧作家接入小说作为小说的副文本,如果仅仅为了文本的炫技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当然首先是小说中的老周替孙频选择了莎士比亚。同样,这种选择的合理性只有在你读完小说之后,只有在你意识到老周的世界剧场最后那场木偶剧,关于导演甲乙的吊诡人生,其实是老周向“我”拉开的他自己的人生舞台的帷幕之后,才能理解“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节花自如”,此岸失去了意义,在彼岸的获得,没有什么可以终止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找不到”,无论是艺术、自由还是死亡。因此,莎士比亚戏剧里的人物只是老周如许害怕和恐惧的流年光阴中的无数个自己。仅有莎士比亚无法满足老周孤独一人奔驰的冥想,它要创造出不同的戏剧,这种创造是他对自己岛屿生活的扩张和扩容。老周成为孙频的“影子作者”,承载她对世界的思考。据此,《我们骑鲸而去》,老周世界剧场的人偶故事、老周和“作者孙频”,他们在小说中不断交换着形与影,暧昧着人生和戏剧、真实和虚构的界限,在扩张和扩容小说叙事空间的同时,也扩张和扩容了对世界的想象与思考。
需要指出的是,在一般研究的理解里,孙频是一个“抒情性”的小说家,这用来说她早期的小说也许成立,那是她内心淤积的倾诉期,甚至是宣泄期,她需要泥沙俱下地喷发。但至少从《我看过草叶葳蕤》(2016)开始,以及其后的《松林夜宴图》《光辉岁月》(2017)、《鲛在水中央》《天体之诗》(2019)等等,孙频的写作呈现诸多复杂的面向,除了内倾化的诗性,还有比如,如何认识社会学和小说结构学意义?如何控制小说的情绪和节奏?如何获得小说的历史感和纵深度?如何消化与自己生命等长的同时代?包括这部《我们骑鲸而去》等小说是如何对“荒”和“废”这些重要美学意象进行文学的转换和安置?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思想性或者说哲思,我们现在很少用来谈论小说,尤其是对年轻作家的小说,但这可能却是孙频最近这些年有意为之去尝试的。我们往往有一个假想的现实和人性的标尺可以拿过来衡量小说家的艺术世界,比如“人性”就是很多研究孙频小说的关键词。这当然不会错,但除了我们惯常和大而化之的思路,孙频的小说有没有其他讨论的空间?比如《松林夜宴图》,孙频自己就说过,她思考的是关于“艺术的权力和历史真相的关系”。具体到现在的《我们骑鲸而去》,孙频将三个不同的生命样本收缩到孤悬荒废的小岛上,在人类文明的尽头,在无涯际的时间里,勘探生命与存在的意义,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话题。时间和空间的计量单位变化之后,“这个小岛上只有我们三个人,好像全世界只剩下了我们三个人。我们成了这个世界的中央。”人的感受和思想变得越发敏感,但人并未因为敏感获得一种可以安放自身的纯粹的精神生活,相反更加陷身孤独、恐惧和害怕。事实上,这种孤独、恐惧和害怕也是因人而异的,在这个命题上,有一点被孙频揭了出来,为什么王文兰却比老周和“我”可以更加免于孤独、恐惧和害怕,而这种免于并非建立在我们想象的比物质更高的精神之上,相反是对物质的永不餍足。再有,有现代以来,我们往往会想象进化的现代滋生出内心的不安和精神的匮乏,所以要逃向荒野,而《我们骑鲸而去》写到的却是当我们向后撤退之后,固然在这岛上,时光倒流,文明消怠,宇宙的规律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更重要的是没有了人群里的种种扑朔迷离。在这岛上想起人类,竟有一种隔世的恍惚感。在这岛上,所有的历史都已经失效了,只有最原始的时间,我们像远古生物一样漫游其中,似乎又回到了时间的起点,一切文明的进化又得从头开始。“从头开始”不只是采集、渔猎、种植维持基本的物质生活,而且三个人的小型人类社会又开始重建现代交际生活。这意味着我们一直宣扬和假想的逃离和退回可以疗愈现代病可能是失效的。我们是不可能离开我们生焉在焉的当下此刻,所以,小说让“我”选择坦然地回归到“现代”,而不是退到远古蛮荒。
但可以预见的是《我们骑鲸而去》发表后,还会被谈到“人性”。小说家笔下在荒岛上萍水相逢的江湖儿女,亦是老周桌上“世界剧场”里的芸芸众生。亦可想象的,会有读者在“荒岛文学”的文学史谱系谈论《我们骑鲸而去》。这毫不意外,甚至小说的有一段副文本戏剧片段就来自荒岛文学的遥远鼻祖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但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这个名为“永生”的小岛有水有电,有通讯有补给有人类工业和建筑遗址。某种意义上,荒岛又不是荒岛文学的荒岛。我不知道孙频出于怎样的考量,节制了荒岛文学的奇观化,甚至荒岛文学发展到《蝇王》的寓言化也很少在她考虑的范围里。换句话说,《我们骑鲸而去》与世隔绝,却是在人间。还可能被拿来比附的是“骑鲸”。“骑鲸”的文学母题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但在中国古典文学里,“骑鲸”往往联系着“游仙”。孙频不会把她的岛写成蓬莱,自然老周的骑鲸远遁于她也不是虚无缥缈的游仙去了。而且“我们骑鲸而去”,“我们”是复数,小说里,鲸鱼关联的细节是生命的自由欢畅,那么,我们各自的骑鲸而去,或者老周的杳不知其所踪,或者王文兰的永不言弃,或者“我”重回“现代”,到底有多少是自由欢畅,有多少是“节花自如”,还是只是作者所寄予的人类一个最洒脱优美的背影?关于我们到底如何“而去”,又如何能够“节花自如”,她都将其深埋在文字之下。
《我们骑鲸而去》读后感(五):所有逃离皆为归来丨孙频专访
2020年过去了一半,“80后”作家孙频一如既往地“产出稳定”,在《十月》《收获》《花城》杂志上陆续发表新作。其中,《我们骑鲸而去》首发于《收获》长篇专号2020年春卷,本月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单行本。
这是一个发生在海上孤岛的故事。岛上有三个人:“我”,一个离了婚又辞了职的落魄诗人;老周,一个前导演、前演员;还有王文兰,一个经历了失婚、杀人、坐牢、丧子、被骗巨款的女人。
他们都亲近文学,也都是现代生活的失意者。三个迥然不同的存在,在小说呈现上“1+1+1>3”。岛上的人,从一个、两个变成三个,又在一次寒潮之后,从三个、两个变成一个。唯独不变的,是笼罩于小岛和人心之上的巨大的孤独。
这篇新作或许能给人们独特的感受。之所以把小说背景设置在一座远离人间的荒岛上,是因为它契合了孙频的部分心境。
“我是一个有避世感的人。我会产生这种感觉可能还是与个人的性格有关系,一个敏感细腻的人有时候容易产生逃离感。”孙频坦言,其实疫情对她的生活方式影响并不大,因为就是没有疫情的时候,她每天的生活也主要是面对自己。“人的本质就是这样,每个人其实都是一座孤岛。”
她的文字也总有一种岛屿的气质,没有繁复的烟火味,没有幽微的世态人情,更多着墨于人与自然,人与文明,人与心灵。写作十二年,孙频一直感谢小说——是小说让她在这个世上不至于太孤单,能找到一种愈合自己的方式。她甚至说,如果敏感也算一种命运的话,如今她已经坦然接受了敏感所能带给她的一切伤害与惊喜。
在王文兰之前,孙频写过很多让读者印象深刻的女性形象,比如《同体》中的冯一灯,《假面》里的王姝,《乩身》中的常勇、《自由故》中的吕明月。但近两年,孙频笔下的主人公有了更丰富的面貌。她的文字也不再那么激烈和决绝,有了更多的温和与诗意。她开始关注个体与时代的关系,对文明的深处和历史的不确定处有了更多的思考。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最后依然落在了繁复、幽深的人性。
“在《我们骑鲸而去》这篇小说中,我试着想突破创作地域、视野、性别、叙述方式等等,至于到底能突破什么,还是要由读者来评价。”近日,孙频就新作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澎湃新闻:因为一句“一个人在深山里废弃的矿上住了两年”,你写了《鲛在水中央》。因为一句“要攒多少钱才能够买一张票去澳大利亚”,你写了《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这次呢,因为什么,触动你写《我们骑鲸而去》?
孙频:你说得不错,我的每一篇小说里都埋着一个核,这个核就是很深地打动过我的那个点。这个点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件事,可能是一种目光,可能是一句话,它们一定都在暗处散发着光芒,在瞬间照亮过我。写《我们骑鲸而去》是因为我去了一座大洋上的小岛,一座很小的岛。我是一个在黄土高原、黄河流域长大的人,不管贫穷与否落后与否,那里都有古老的黄河文明给人们的精神垫底,你觉得你的身后还有几千年的文明。可是在这样一座小小的海岛上,我被极大地震撼了,不是被灿烂的人类文明所震撼,也不是被广袤的大海所震撼,而是被忽然退回到文明之始所震撼。在那岛上,你会觉得一切文明都还没有开始,你会觉得人类几百万年的进化皆成云烟,你会与人类的祖先——那些还没有来得及上岸的鱼类相遇。不知你是否相信,这是一种极其巨大的荒芜感与虚空感,巨大到了辉煌的地步。你会在瞬间觉得,连人类最畏惧的权力在这里都消失了。如此巨大的虚空会给人一种错觉,让人觉得这小岛是一个空荡荡的剧场,什么都可以上演,任何上岛的人都可以成为演员。几百万年进化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成为在这里上演的戏剧。在大洋深处,我感到了海岛那种生来与俱的剧场感。我为什么在小说里要把老周的桌子叫成是“世界剧场”呢?是因为海岛独特的封闭性和世外感,一切细小的东西在这里都会得到最大程度的放大,这使它最容易成为一座考验人性的实验场所。海岛与剧场之间这种隐秘的共生关系便是我写这篇小说的起因。
澎湃新闻:在具体创作中,“我”、老周和王文兰是怎么出来的?他们和荒岛文学中的经典人物有哪些不同?
孙频:我这篇小说虽然写的是与世隔绝的海岛,却并不属于荒岛文学,或者说,也不具备荒岛文学的元素。我只是把人间移植到了世外,人间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比如水、电、书籍、交流、娱乐、劳作、收获、交易、拉帮结派,甚至权力,在这世外的海岛上都能找得到。 这座海岛是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趣味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与桃花源、蓬莱岛、鹿门山有着相似的属性,都是适合避世隐居的地方。避世的原因各个不同,但却可以大致分出类型,一类是有着隐秘心史与黑暗过往的人,一类是遭遇过大变故而窥破红尘的人,一类是能量偏低,沉溺自我,在人群中总有消耗感或是在人群中没有归属感的人,一类是被时代和社会淘汰遗弃在一边的人,一类是厌弃社会与人类,渴望清洁与独善其身的人。 我安排这三个主人公登场之前,已经在心里对他们各自的性情与命运思量了很久,我想让三个独特的又是平凡的,退无可退的又是海阔天空的,黑暗的又是明亮的人,一一登上这个海岛。我最早想到的是王文兰这个人物。我想对她这样一个人来说,也许海岛是一个最适合她的去处,可以包容和吞噬她所有的苦难。然后我又想到了老周,一个已经等在那里的,在荒芜中从未放弃过灵魂的人,他和王文兰形成了两种可以交错的复调。最后,那个旁观者与那个自省者也该上场了,那就是“我”,一个带有诗人气质的落魄者或失败者,而在现实中,失败者又是如此之多,“我”不过是其中一个缩影。
澎湃新闻:比起老周和王文兰,“我”这样的人似乎更普遍。到故事最后,老周消失了,王文兰坚持留岛,“我”选择了离开。他们各自的出路,承载了你的哪些思考?
孙频:是的,这个小说中,三个人有三种不同的去向,老周骑鲸而去,消失在茫茫大海中。一个独自在海岛上避世隐居几十年的艺术家,连孤独都能忍受,却不堪忍受人性的缓慢丧失,不堪忍受人在饥饿状态下暴露出的动物性,所以他最终选择了死于饥饿、死于大海。而这种选择无疑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最后的风骨,也是一个艺术家对人性的捍卫。包括他固执地要“活在自己的脑子里”,既可以看成是一种避世,也可以看成是一种自救,也可以视为是一种高贵。王文兰一个人留在岛上,用“在大海深处建立一座王国”的梦幻作为自己的归宿是最适合她的,因为无论是她还是读者,都心知肚明她已经回不去了,她是一个被社会淘汰出来的个体,而社会从不因为哪个被淘汰的个体而产生怜悯,所以选择一种梦幻对她来说也算是慈悲的方式。而“我”,一个最普通不过的普通人,注定要在最后回归到人类社会,因为他在远离人的地方才开始理解人到底是什么,同时他也开始明白,他所选择的避世是无效的,他和老周和王文兰都不同,人群才是他最后的去处。
澎湃新闻:在今天,“避世”这类说法已不鲜见。尤其在这次,很多人说自己想去荒岛隔离,想找世外桃源。有意思的是,小说里的这座海上孤岛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孤岛,人在上面还是可以用手机、打电话、看朋友圈。这样的设定有什么特别的用意?
孙频:这个小说是在2019年写的,我把小说的背景设置在一座远离人间的荒岛上,是因为它契合了我的某一部分心境,也就是说,我也是一个有避世感的人。我会产生这种感觉可能还是与个人的性格有关系,一个敏感细腻的人有时候容易产生逃离感。人的能量有高有低,过了这么多年,我已经承认,在人群里,我属于那种能量偏低的人。这也使我经常在思考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也是我会对一座海岛情有独钟的原因,因为它可以寄托个体与人群关系的另外一种假设,可以承载我对人这个生物体做出的一些思考。另外,我觉得疫情期间所有的人本身就都是孤岛,既然已经身在孤岛,就没有必要再去找世外桃源了。走出孤岛后,人只会加倍地渴望拥抱人群,而不是再去荒岛隔离。
澎湃新闻:小说里有几处细节耐人寻味。一是“我”为了避开人来到岛上,结果发现岛上最可怕的事情是没有人可说话;二是“我”想逃避权力,但是发现在只有三个人的荒岛上依然有权力的存在;三是“我”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岛。这些细节让人去想——远离“现代”,我们真的就能过得更好吗?如果不能,到底怎么样才能过得好?或者退一步说,过得下去?这不是“逃离”第一次出现在你的作品中了。对于逃离的方向,逃离的意义,你现在有自己的答案吗?
孙频:你读得很认真。我想,但凡有过些文学情结且性格偏内敛的人,都会对梭罗的《瓦尔登湖》产生过些许向往,“我们这些新英格兰的居民过着现在这种卑微的生活,是因为我们的眼光无法穿透事物的表面,我们把表象看成了事物的本质。” 到底什么是事物的本质?“我”情愿来到一座与世隔绝的岛上,不妨可以理解成就是一种对本质的追寻。结果我的发现是,一,岛上最可怕的事情是没有人可说话,二,在一个只有三个人的荒岛上依然有着权力的存在;三,只有在人群中才有资格厌恶人。 减少孤独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比如,要承受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甚至相互倾轧,即使如此,又有谁可以真正地承受绝对的孤独?恐怕没有。我相信很多人都厌恶过权力,因为深受过权力的压迫与羞辱,但事实上,权力与人也是共生关系,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权力,哪怕全世界就只剩下了三个人,仍然有着权力的存在。如果想逃避人类文明中的这些无可回避的部分,那就必须变成绝对的孤独,又有谁可以真正地承受?恐怕没有。 那到底什么才算过得更好呢?这是一个根本无法有定论的问题,因为人的千姿百态,那就必定产生出千姿百态的生活和结局。比如老周就愿意活在自己的脑子里,他就愿意一个人守着莎士比亚,愿意守着一个“世界剧场”过了半生。王文兰就愿意在最没有希望的地方依然给自己种下希望,就愿意把一个单薄而强悍的背影留给世界。而“我”只能在游荡与漂泊中找到自己所要的真相。所有的逃离其实皆为归来,它们只是一个事物身上的阴面和阳面,而这阴阳之间又是互相流动的。
澎湃新闻:我对小说的题目《我们骑鲸而去》也很好奇。“骑鲸”这样的意象在中国古代就有。扬雄的《羽猎赋》里就提到过,杜甫在《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里也有“若逢李白骑鲸鱼”的句子,关于李白溺水而死的传说里,李白就是骑着鲸鱼溺死在浔阳的,这让“骑鲸”这一意象在中国古代既有隐遁的淡泊,又有游仙的欢喜,隐隐还有死亡的意味。 你在设计这样的意象时对它的古典意蕴是不是有意参考过?你小说里的“骑鲸”,更接近于这个意象的哪一方面意味?此外,“我们”是谁?要“去”哪里?
孙频:这篇小说里有几个涉及到鲸鱼的片段,每个关于鲸鱼的片段都代表着生命的自由与欢畅,比如鲸鱼一定要用跳出海面来表达它的快乐,比如鲸鱼在大海中孤独地遨游和歌唱。 而骑鲸也是从古到今人类所能为自己寄予的一种最优美的姿态,可以与高山流水,程门立雪,青松煮白石这些高洁出尘的意象相媲美,那么骑鲸者也一定是复杂而扑朔迷离的,如你所说,他身上既有中国古代隐士的高雅与淡泊,又有寻仙般的洒脱与自在,还有那种对赴死的通透与坚定。 在骑鲸这个意象里,生死是一体的,逃离与归来是一体的,高洁与自在也是一体的。所以,骑鲸二字其实寄予了我本人太多的愿望与渴望,我渴望在这样一个物质的,快节奏的,不再倾慕风骨的时代里,依然有着高洁的隐士,依然有着九死不悔的理想主义者,依然有着属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风骨,依然可以有人“采薇山阿,散发岩岫”,仍然可以有人“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而这种渴望或向往,是不是也能算作一种你说的“去往何处”?
澎湃新闻:嗯。在小说形式上,《我们骑鲸而去》的叙述插入了大量戏剧片段。我想到《松林夜宴图》中也融入了书信、诗歌。这类形式上的探索,是你有意为之吗?但这类文本的加入,对小说本身也构成了挑战。寒潮来临后,老周的木偶戏“一幕接着一幕”,其中剧情是否对小说有所影射、有所预示或者构成象征,让人浮想联翩。我总忍不住去揣测这些“虚构中的虚构”有何特别意味。那么,你对这部分内容的加入,包括体量、位置、内容、节奏控制等,都有何考虑?
孙频:我很喜欢你的这种说法“虚构中的虚构”,就像小说中的小说,构成了一种小说的副文本或者说复调。不错,在近两年的小说里,我做了一些尝试,就是在小说的形式上融入了书信、诗歌、非虚构的采访、戏剧等各种镶嵌方式。这是因为,平铺直叙的叙事方式已经无法让我感到满足了,况且,一个稍微虔诚些的作家都愿意把自己的文字当做艺术品,既然是艺术,那么,在小说上多作些探索是不是也是正常的。
在《我们骑鲸而去》这篇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小话剧,这些话剧又分两类,一类是莎士比亚的经典戏剧,另一类是老周这个前导演在海岛上自编自演的话剧。莎士比亚的话剧自然无需多言,因为它与小说中的人物灵魂暗合,可以作为一种替主人公发声的方式。另外一类小话剧也都是有深意的,也就是说这个岛上的所有秘密其实都隐藏在这些小话剧里,每一个小话剧都影射着三个主人公的一段真实的处境或心境,最后的两出话剧则揭示了两个大秘密,一个是岛上十个采矿工人最后的去向,而另一个则交待了老周的来处。
如果不用这些话剧的副文本,那就还需要大量的笔墨和空间去一一交待这些情节与秘密的构成,但是我只是把它们都一一藏了起来,藏在了这些由木偶人表演的小话剧里。真实与虚构的交错,过往与未来的混淆,叙述与表演的杂糅,我期望这些共同构成了一篇梦幻般的小说。
澎湃新闻:在王文兰之前,你已写过很多女性形象。有读者认为你笔下的女性大多敏感而脆弱,有关其身心、情欲与生死的描述都太过压抑和残酷,充满戏剧性,对此你如何回应?
孙频:我认为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是有真诚可言的,在于它是有心跳和体温的生命体,有真正动人的东西凝结在里面,而不是经过粉饰的扭捏作态的“假声”或“圣徒”。我在生命的不同阶段看到了不同的风景,这些风景未必都尽如人意,而且并不是一种固态的存在,但都有着独特的生命力,我愿真诚地把每一个阶段有限的认知都写出来。
澎湃新闻:我还发现,在新近的《我们骑鲸而去》《鲛在水中央》中,你都尝试使用第一人称男性视角。这是一种刻意为之吗?今年《十月》做了一期“新女性写作专辑”。你怎么看待“女性主义写作”这一标签?
孙频:是的,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因为我想把我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性别掩藏起来,让读者不要感觉到这是一种所谓的“女性写作”。我并不太喜欢“女性主义写作”这一标签,我想把自己作为是一个“人”的写作也许会更自在一些。
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社会文化角度来说,这个社会虽然已经很进步了,但毕竟还是一个男权社会,女性与男性在很多方面仍然是不对等的,女性也会有更多的顾虑,事实上女性的艺术作品也容易有更多的争议。很多时候,女性更多的是想保护好自己。我想,一个社会对一种性别的宽容和理解,首先就会体现在艺术作品中吧。
从个人角度来说,我觉得这种标签把作家框在了一个并不开阔的笼子里,性别成了一种束缚,且性别意识太强的话,写作的时候会不自觉地产生一些偏颇。我想一个更开阔的空间肯定是更好更自在的,也许会有不同的视野和新的世界观进来。
澎湃新闻:在上大学之前,你都在山西交城生活。年少时的经历与记忆也在不经意间丰富你的文字。不久前《花城》做了一期“在县城”的特别关注,你的县城书写也在其中。在你的多次讲述里,你与家乡小县城是血脉相连的。但在县城之外,你近年也写到了戈壁滩,写到了海洋。这可否理解为你也在试着开拓自己的文学版图?
孙频:迄今为止,我写的最多的可能是县城,是因为我对县城太熟悉了,而且因为就在那里长大,在情感上有很深的链接。我至今还是认为作家写自己最熟悉的环境才有可能写好,那种浮光掠影的联系是很难深入到肌理内部与情感深处的,而小说是一种有情感的事物,而且,它需要被滋养,只有很深的滋养才能培养出“火之焰,珠玉之宝气”。
不过我也在思考,一个人终其一生不可能只写自己的家乡,所以近两年里,我还是刻意会在写作地域上偏离开我的故乡,比如去写戈壁滩,去写海岛。写自己不熟悉的事物也有好处,那就是强烈的好奇会刺激你的神经,但是好奇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要想把写作落到实处,还得你努力地去接近它,了解它,甚至做些严谨的田野调查。
澎湃新闻:你以中篇见长。朋友圈里有同行转发《我们骑鲸而去》时提及“长篇”,你还特别纠正了它其实是“大中篇”。为什么对中篇格外偏爱?今后有没有其他计划?
孙频:有的作家喜欢写短篇,有的喜欢写中篇,有的喜欢写长篇,我想这还是由作家的内在气质决定的。除了喜欢,还有个适合不适合的问题,能找到让自己舒服的写作体量和写作方式,那便不应该太多地去计较写长写短的问题。至于写长篇,那是一件缓慢庄重的事情,且需要水到渠成,就更不能着急了。往中篇小说里注点水变成一个小长篇,那又有多少意义?我觉得在写作这件事上,还是“节花自如”一点的好。
(本文原载于澎湃新闻,作者罗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