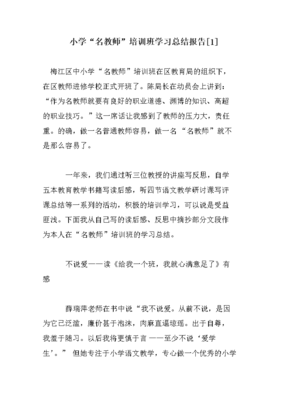自传性反思读后感摘抄
《自传性反思》是一本由沃格林 / 桑多兹著作,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平装32图书,本书定价:22.00元,页数:19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自传性反思》精选点评:
●挺有意思。
●令人惊艳。天才所走的发光之路,以及沿途他的眼中所见。挽救哲学以及哲学家的尊严。
●2010年4月18日,P75。2015年2月12日。
●看完更觉得哀伤而绝望了,短评也集中在意识形态那篇,因为它最让人有共鸣。
●“哲人光辉”……倒是不假
●看似好读,其实内容蛮丰富。最后那篇《论沃格林对政治理论的贡献》草草地读完,感觉沃格林超越了政治理论或政治科学的范畴。看来需要好好整理一下笔记。
●沃格林的阅读范围和理论深度实在让人折服。对经验、实在、哲学、意识形态等相关论述可以说在一个统一的层次上向我开启了一个崭新的领域。简直是神人。
●只能看懂大概意思
●极其精彩的学者自述
《自传性反思》读后感(一):古典心性就是复现实在
秩序与历史最佳文学范本想必是《神曲》。在这重意义上,神曲才能被理解为“史”诗。两者间的巨大张力指向“审判”观念。 新生在释放掉不知所谓的热情之后,在升入大二之际应当读《什么是自由教育?》,在大四结业心志明确时再读《为什么做哲学?为了再现实在!》(收于《自传性反思》)就会看出,显明的平庸与伪装的高雅在校园里装腔作势,互相争抢地盘,真正的路总是那么难走。什么是古典以及古典教育?这个问题依旧被悬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重返古典绝非膜拜幽灵——不论是古希腊的幽灵还是二十世纪的幽灵。不要幻想进了哪个组织就会有一位Virgil陪伴着你,更别说有Beatrice引导着你,保你平平安安逛了三界还能到达净火天膜到Boss。Dante说的很清楚,还乡之旅就是Odyssey,犹如美丽而危险的玻璃幻境,没有被Siren拐走便是幸运了。
《自传性反思》读后感(二):“迷津”还是“迷宫”?
沃格林《自传性反思》(徐志跃译,华夏出版社,2009)第98页第二行的“迷津”,原文是maze,应该译作“迷宫”吧。
徐氏也真是的,连摆在面前的究竟是“迷宫”还是“迷津”都傻傻地分不清,就要带领人们穿越,以至于其追随者们真正穿越的,大概是徐氏的低级错误的语言所形成的充斥着陷阱的,散发着臭气的腐败的沼泽罢。
说到阉割,徐氏的译本在出版过程中倒是压根就不需要阉割,因为原作的精义,原作的爆炸性力量,早已在徐氏的文字沼泽中湮没无余了。
呜呼!哀哉!
《自传性反思》读后感(三):穿越腐败语言的迷津
“穿越腐败语言的迷津”一语出自心岳师译沃格林《自传性反思》
“在致力于穿越腐败语言的迷津,以寻找某种方式通往实在及其表达的恰切语言时,出现了某些不总让当代知识分子喜欢的规则。我的研究中,在方法上首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规则,乃是回到孕生象征的经验。”
我猜,当代知识分子喜欢的规则是分析判断结合后验判断,即,自洽的逻辑推演结合观察验证。
问题在于:逻辑自洽无法涵盖逻辑的前设,也就是说,逻辑始点不在逻辑自洽中,必须单独拿出来叩问。观察经验只能表明事物的偶然性,所以,逻辑起点若从观察经验中来是相当有局限的。逻辑起点若不加判断而直接取自其它逻辑推演的结论,则是知性懒惰。
总之,逻辑始点,不能用逻辑证明,不能用观察证明,它是明证与自明的共振。明证与自明乃鲜活的哲思过程的两面,明证对应表象行为,自明对应表象对象。
(一)
马斯克(Elon Musk)正在复兴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性原理”思维,第一性原理,就是那些不证自明、不言自明的原理。基于这些原理,整个体系得以自然生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爱因斯坦《相对论》都是这样的体系建构。
亚里士多德在《第一哲学》里提出:任何一个系统都有自己的第一性原理,是一个根基性命题或假设,不能被缺省,也不能被违反。
问题在于,这个根基植根于哪里?
古希腊城邦是以神庙为中心和纽带的。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想里,城邦的人民需要成为philomythos,爱神话者。人之生存是朝向神性根基敞开的,并以之为秩序之源,这是神话经历象征化所得以孕生的社会。
这时的人具有二分心智(the bicameral mind),而不具有意识(consciousness)。二者如何区分?
人类,明了起因蕴含结果。
逻辑起点在哪里?
若逻辑起点植根于人的心灵深处,我们称这种因果律为心智;心智的逻辑起点不可证实。
若逻辑起点由人造作,我们称这种因果律为意识;意识的逻辑起点皆可证伪。
意识起源于二分心智的坍塌。爱神话者分化为philosophos爱智慧者与philodoxos爱意见者。前者接受张力并接受追问,后者逃避张力并拒斥追问。在柏拉图那里,philosophy(爱智慧)有一个明确的对立面——philodoxy(爱意见)。philosophy始终向追问敞开(转向根基eperiagoge),哲学的生存是意识到人的人性的生存,而且这种人性是由其向着神性根基的张力所构建的;而philodoxy着眼于结束追问(转离根基apostrophe),向着一个被设想为无需由其与神性根基的关系来构建的人的自我。转向根基和转离根基成为描述人的生存中的秩序和无序的基本范畴。
举个例子。
豆友monologue为《记忆》一书写了个一个读书笔记“由ousia引发的现代性”。豆友Shakespere的回复相当精彩,分享如下:
沃格林的意思,是说ousia被译为substantia完全是个形而上学性质的偏离(从鲜活的哲思→形而上学命题推演),根本站不住脚。沃格林试图恢复的,是ousia这个词背后的亚里士多德的哲思经验:神话和哲思的交织,形成了一个智性神话(myth of intellection/intellect/nous)。ousia的意义,就直接来源于神话经验中的“物”(好比我们说“东西”):神是“物”,人的灵魂是“物”,从感官穿透进入人的也是物。前两者是非客体性的“物”(有、实在),后者是客体性实在。ousia继承了该词在神话经验中的丰富蕴涵,却被形而上学的substantia变得扁平化。ousia成了“实体”,成了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说几嘴的一个“哲学范畴”,和它的经验语境——神话——已经完全剥离。形而上学是实在的客体化(外在于人的“物”成为唯一真实的“物”,神和人的灵魂本身的非客体性被排除在哲学话语之外),真理的客观化(经验真理→命题真理)。从这个意义上,沃格林告诉我们:ousia关乎那种几乎是强迫性地“经验到或被经验到”,它是用来表达这种现实经验的象征,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形而上学“实体”。
因此,沃格林说,ousia在希腊语境中的同义词是aletheia——“真实/实在”。实在,总是经验中的实在;经验,总是灵魂(人)的经验。人作为一个言说者,要言说一个comprehending reality,就不得不把这个comprehending reality也当作一个客体来指示。当作,就是这个包罗万象的实在不是客体,而是“好像它是”客体。这是ousia歧义的来源:语言指示客体实在(花、草),语言也指示非客体实在(“我”、“神”)。如果把指示非客体实在的语言(诠释经验的语言)直接当做指示外在于人之客体的词,那么,形而上学的偏离就开始了。
(二)
《未来世界的幸存者》阮一峰说:“我相信,未来最大的那些机会,一定是技术带来的机会。……这个《每周分享》系列只谈技术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其他东西没有那么重要。”
从卡西尔那里我们已知:原始人并不缺乏对自然进行经验和“科学”观察的能力,但是,他们并没有发展这种能力,而是沉浸在与自然之间的“天人一体”的情感联系之中。
我觉得,意识乃内置于人的AI,在未来数十年,这种土AI干不过人类创造的超级AI。AI没有灵魂,而人有。爱智慧,心岳师的译文句式是,经由对神性存在之爱而对存在之爱,并以之为秩序之源。这才是鲜活的人。
心岳师提及沃格林不否认城邦的自然性,以及城邦共同体是人的生存的一个目的。但在这背后,还有沃格林称为"生存之真理"的问题:"行动之易变易动的领域,是人达到其真理的所在地。"一个行动是正当的,不仅仅是作为特定语境下进行明智思虑的结果。沃格林强调,这种思虑必须是"存在中的运动的一部分,流自上帝,终结于人的行动。正如上帝移动宇宙万物,神也移动我们内心的一切"(语出亚里士多德《尤达米安伦理学》)。
《自传性反思》读后感(四):意识形态及其异化
这本书作为本年度生日礼物,并且我于生日同一天领洗,似乎有着诸多预示,这算是我得到的信仰经验的一部分吧。因为这本书给予我的一些深刻启示,令我感到无比振奋,它同时给我带来了一位学习道路上的明灯——沃格林。
沃格林认为一种政治理论,尤其是它要应用于分析意识形态时,就必须以古典哲学和基督教哲学为基础。更令我感到惊喜的是,沃格林认为将极端意识形态份子遏制住的威权主义国家,最后可能捍卫民主的这一洞见,与枫林仙不谋而合。
沃格林一生的研究致力于发展政治科学,并为了恢复实在的秩序——即神性秩序而不懈地努力着。他深信恢复与实在的联系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求助于以往没有脱离实在的思想家,这就使得他一头扎进浩瀚的历史资料中,研究古典哲学与基督教哲学,乃至近东文明。并且他通过培育学生来反对意识形态的传播。他尽量避免让自己一手搭建起来的研究机构被庸人所占据,他的研究所极少数的非意识形态的科学堡垒。我对沃格林的敬慕油然而生,并与此同时更能体谅到枫林仙目前所做的工作,在自己有限的教席上尽量播撒传播真理的人。目前他所培育的学生中,终于有了值得把这一工作坚持下去的反馈。我们这个世界的美好,得益于这样奉献自己的人。
秩序一词,沃格林很清晰地指出,是经验到的实在结构,以及人向着一个不属于他的制作(his making)的秩序(即宇宙秩序)调适。我对这一理解丝毫不感到费力,这得益于我研读哈耶克而累积的知识,任何一位熟悉哈耶克演化理论的人对此不会感到理解上的困难。
另一个重要的词及其含义,是经验。这也是困扰多数哲学家的问题。经验到底是什么?是纯粹的对外部世界的意识?还是纯粹的内心产生的意识?沃格林引述了詹姆斯的解释:纯粹经验这种东西,即可放入主体意识流的语境,也可放入外部世界之客体的语境。沃格林进一步阐述:詹姆斯识别出了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东西,即经验参与的主体与客体。他后来发现,柏拉图在更大范围内也探讨过这类分析,并产生了他的间际(metaxy,in-between)概念。经验既不在主体中,也不在客体的世界中,而是在间际,那意味着介于人与他经验到的实在在这两极之间。更重要的对这一洞见的理解来了,沃格林接着说:对于理解神性显现之运动的反应来说,经验的间际性变得至关重要。因为,对这类运动的经验并不处于人的意识流之中——内在论意义上所理解的人——而是处于介于神性与人性之间的位置上。经验是神性和人性同时在场的实在,只有在经验发生后,它才能或是分配给人的意识,或是分配给启示名下的神性语境。
经验,既不是唯心论,也不是唯物论。这点很重要,尤其是对自由主义者来说。间际中有关经验张力的实在,也正是理解权利的关键钥匙。特别是对研究哲学的人说,意识的敞亮并非是主体意识的敞亮,而是从两极进入经验的实在的敞亮。由此,沃格林严厉批判意识形态对语言的摧毁。他提及在自己读完谢林后才明白,“观念史”这个概念是意识形态对实在的扭曲。意识形态,不论是实证主义的,或马克思主义的,或国家社会主义的,都沉浸于知性上站不住脚的构建。毋庸置疑,意识形态就是知性上的不诚实。更可恨的是,意识形态还要强加于人,一旦意识形态充斥学界,知识分子的处境就岌岌可危。人人都大谬不然,因此足以维持对峙,为的是至少获得部分正确。如果任何事物都具有意识形态及其思想家的特征,那就是对语言的摧毁。对于黑格尔或马克思主义类型的意识形态份子,沃格林体会到一旦与黑格尔主义者辩论,他们就会说,除非你接受黑格尔的前提,否则你就不能理解黑格尔。反观十九世纪后期二十世纪的意识形态的跟屁虫,他们矮化了知识辩论,赋予公共讨论一种明显的暴民统治色彩。那些甚至连知识骗子也称不上的人主导了对历史知识和哲学知识的谴责,由于他们的意识水平的低下,而连自己的客观性欺诈也意识不到,所以最好把他们看做是自我夸大的强烈欲望的半文盲。这些完全无法阅读哲学著作的人在低俗层面上对知识语言歪曲。低俗之人创造并主导了知识氛围,在那样的氛围中,像希特勒这样的人物才有可能上台。这种意识形态狂热分子,不可能是讨论的对象,而只能是被研究的对象。
拒绝统觉理解,就是意识形态的倒错和扭曲。为了捏造的体系之建构成为可能,所以经验的实在的那一部分被排除了。受排除的实在可能多种多样,但有一项总是被排除在外:人对其存在之神性根基的张力的经验。所以说,意识形态这种东西,是对真正的知性的不诚实,用掩饰、欺瞒的手法,用对外部实在中的对象的感性知觉的模型来构造意识。沃格林指出,黑格尔核心部分《精神现象学》是从感性知觉开始,并从这一基础发展所有更高的意识结构。这种做法引人注目,但黑格尔怎么说都是一个历史哲学大家,他当然知道,像古典哲人著作中出现的意识之初始经验,并不关乎感性知觉,而是关乎结构经验(例如数学结构)和转向生存之神性根基的经验——神性根基发挥效力激发这一转向。他丝毫也不怀疑,有着黑格尔那样历史知识的人,故意忽略了意识的直接经验,并代之以高度抽象的、历史上非常晚才出现的外部世界之对象的知觉模型,以便形成一个表达其异化状态的体系。在黑格尔的任何著作中,他都没发现黑格尔反思过自己的知识欺骗的手法,而且马克思在后来还把这种手法变得更明目张胆了。
因此,与神性实在相连的所有精神现象和知识现象现在都被他们扭曲成为有关超验实在的命题。而转向神性根基与转离根基成了描述人的生存的秩序和无序状态的基本范畴。沃格林提及廊下派是最早观察到这一现象的(廊下派到底是哪些学者?偶不知道。。。),不过廊下派研究经由转离根基、并因此出离自我而导致的生存扭曲的科学,成为精神病理学的核心。我突然想起米塞斯骂过的傅里叶和傅里叶病态症。
经验的实在的恒定性,即所谓的原始人经验到的实在,与现代人经验到的实在,并无不同。这句话万分准确,自然法是恒定的。你不能说原始人没有人权,而现代人有了人权,只能说现代人发现了人权。这一观点支持权利是被发现的论说。由此,未扭曲的人类生存范畴就成了准则,扭曲的生存和体系必须借此来判断。意识形态体系本身成了这一过程中的历史现象,该过程尤其反映了人类的张力,即存在的秩序与无序之间的张力。我认为这段可以很好地用来理解现实生活中人们探索权利边界的张力,以及任何一个普遍理论,都是具有张力的理论,否则就是死的理论,静态的,僵化的。沃格林用美国越战作为一个例证来说明:北越毫不迟疑地将越南人民置于战争的毁灭;而从美国一方,尤其是通过电视报道,让美国人民了解到,毁灭乃是美军所为;北越侵略柬埔寨,美军随后抗击此一侵略行为,却被知识分子扭曲成军事讨伐,是美国人的入侵。在一个不发达国家进行规模较小的摧毁,则引起了惊恐。引发这些惊恐的,是意识形态的党派,而非美国政府,人们忽略了这点。现在让我们再看看指责美国对抗恐怖主义的人,以及支持美国政府逮捕斯诺登的人,他们无不是意识形态的跟屁虫而已。
推荐阅读
拒绝哲学食人族
豆列:指路明灯沃格林
y 荔枝
2013-7-7 补充:
在书中,他对“威权国家”(authoritarian state)和“极权国家”(total state)做了区分。前者的例子是经历内战后的1934年奥地利宪法及其政府,后者的典型是试图取代这个宪法和政府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我猜一定有人抨击沃格林和枫林仙是五毛了。)
沃格林认为,比较而言,威权国家的存在是对像国家社会主义者这样的极端意识形态分子的遏制,从而可以对民主起到保护;而像国家社会主义这样的极权方式是“意识形态的极权”,人不是从外在被强迫接受Volk(德语,既有“人民”也有“民族”的意思)至上的观念,而是发自内心、在精神和知识上都认同。这样的统治已经不限于维持社会秩序,而是一种精神力量,一种宗教。
《政治真相:初读沃格林和桑多兹》
《自传性反思》读后感(五):沃格林:《自传性反思》读书笔记
沃格林,1901年1月3日出生于德国科隆。据沃格林自陈,他进入“真正的高级中学”学习,“这意味着要念8年拉丁文,6年英语和作为选修科目的两年意大利语。此外……额外学习初级法语。”【《自传》,8】期间对相对论感兴趣,还研究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一度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而后沃格林在维也纳大学法学系问学,1919-1922年间完成博士学位。据其自述,之所以选择读政治学博士,主要有三点原因:“部分出于经济考虑,部分出于原则。就经济状况来说,我很穷,而一个可以在三年内完成博士的课程系列特别令人动心。法律博士也需要求四年时间。至于原则问题,其实是那时候的一个含混但强烈的冲动,即,我要从事一份科学职业。法律博士有这样的诱惑:一个人假如不成为一名独立律师,就可以落脚公务员职位;而我并不想成为一名公务员。此外,选择政治科学还取决于教师的吸引力,其中包括凯尔森和斯潘这样的著名学者。”【4】博士期间的课程中,斯潘、凯尔森和米塞斯的讨论课令格瓦拉记忆深刻,并与优秀的学者建立了关系,如考夫曼、哈耶克等,最终结晶出了一种所谓的Geiskreis(精神或知识圈子)建制,其成员“都是在追求这门或那门科学上的知识兴趣而走到一起,且同时有相当数量的成员不单单属于大学,而且还从事种种商业活动。”【6】
而对马克斯·韦伯的阅读则对沃格林科学态度的形成至关重要。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因此知道了马克思的问题所在,完成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弃;其次,是“学术与政治”讲座及其中的缺陷成为沃格林要解决的大问题;最后,则是韦伯比较知识的宽广范围,也就是对文明进行比较的知识,他通过研究马克斯·韦伯、阿尔弗雷德·韦伯、梅因、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而获得了相当大的知识储备。
此外,“斯太芬—乔治—克劳斯圈子”也对沃格林的研究至关重要。1870后德意志帝国时期,德国遭到根本性毁坏的语境,修复语言是年轻一代有意识努力的要事,这意味着恢复用语言来表达的主题,而这就意味着摆脱现在的小资产阶级的虚假意识(包括这个头衔下的实证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关心语言便是抵抗摧毁语言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由于意识形态型思想家与实在脱离了关系,发展出来的各种象征不是用来表达实在,而是用来表达脱离实在的异化状态,意识形态便摧毁了语言。而克劳斯和乔治及其朋友则通过修复语言来穿越这种虚假语言并修复实在。【17-18】沃格林指出,“若不借助《瓦普克斯第三夜》以及《火炬》那些年发表的评论,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严肃研究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里,知识分子的困劲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这一困境必须理解为希特勒之所以能上台的背景……德国知识生活在当代的毁灭,尤其是大学的毁灭,乃是导致希特勒上台并受其政权统治的致命毁灭。”【19】
最后,则是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沃格林对其表达高度赞赏,并强调“在有关纯粹法理论的根本有效性的看法上,我与凯尔森之间从来没有分歧。”【21】而两个人的分歧,在沃格林看来“源于纯粹法理论中的意识形态成分,这些成分被附加在严格意义的法律体系的逻辑上,但不影响该理论的有效性。除去这些成分无损于纯粹法理论的核心。这一附加的意识形态就是新康德主义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决定了一个科学的领域,亦即,由用于科学的探索方法所决定——在本案例中,就是由法律体系的逻辑所决定。由于在那个时代的常规术语中,凯尔森作为教授代表的领域是政治理论,由于新康德主义方法论为其法律体系的逻辑方法所限定,故而,政治理论也就不得不成为法理论。凡是法理论之外的东西都不会再成为政治理论的一部分。”【21】当然,因为在之后的《威权主义国家》第三部分中,沃格林表达了对“纯粹法理论声称是政治理论的替代品”的反对,他与凯尔森的关系万劫不复。【54】
后来,沃格林获得奖学金参加牛津一个暑期学院的学习,并见识了“最富有活力且与众不同的英国学术风格。”【27】在洛克菲勒奖学金的支持下问学于美国(哥大、哈佛和威斯康辛),对其发展带来极大的断裂。在哥大,杜威对沃格林有着重要影响。沿着其《人的自然和行为》,沃格林发现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常识概念,“作为一种人的态度,融入了哲学家面对人生的态度,但又无需哲学家的技术装备,反过来,古典哲学和廊下派哲学也可以理解为,对常识态度专门的、分析性的阐述。这种概念对我理解常识哲学和古典哲学有着持久的影响。正是在此期间,我第一次觉察到,基于常识层面的、持续不断的古典哲学传统,即使没有一种必要的亚里士多德的技术装备,对于知识分为和社会的团结,会具有重要意义……德国社会领域明显缺乏的,恰恰就是常识传统这个因素……没有根植于完好无损的常识传统的政治建制,乃是德国政治结构的一个根本缺陷,而且至今没有被克服。”【29】在哈佛,怀特海则留下深刻印象,并努力搞懂《观念的冒险》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在威斯康辛,康芒斯拓宽了沃格林对美国的知识,研读桑塔亚纳的著作也是一种哲学上的启示,在其思想中,卢克来修的唯物主义乃是继发性的体验,这对后来在巴黎理解法国诗人瓦雷里及其卢克来修式动机具有相当重要性。这两年美国之行对此后新康德主义方法论大争论的理解有着重要作用,沃格林反思道:“在我作为学生所经历的方法论争论中,这些背景显得黯淡无光(即便不能说销声匿迹):1776年和1789年伟大的政治奠基背景,以及这种奠基行动藉此而展开的背景,即主要以律师的指导和高等法院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同时,还有基督教和古典文化的强大背景。简而言之,存在这样一个世界,在知识上、道德上和精神上,它与我成长的另一个世界都不相干。应该有这种多重的世界,这个结论对我具有摧毁性的效应。断开我的中欧或一般的欧洲地方主义,而又没让我坠入美国地方主义……在各种不同文明中实现的人类可能性,其多重性我在这几年获得了理解,而且是一种直接的体验,即活生生的体验。”【32-33】
之后,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沃格林继续到法国研究,学习法国文学和法国哲学,并掌握了俄语(尽管因研究俄语材料的机会少而几乎忘光了)。1934年沃格林又去了巴黎几个星期,彼时对十六世纪的法国,尤其是博丹的作品感兴趣,并逐渐认识到“蒙古人的入侵和十五世纪的一些事件,尤其是泰摩兰对拜亚吉德一世的临时性胜利,已成为十六世纪政治进程的一个模型。实际上,每个重要作者都处理过这些事件,因为这些事件全然外在于西方的常规政治经验,并展现了无法理解的统治模式,而这种模式影响了西方文明的生存,并作为一个要素进入了世界历史。”【36-37】同年,沃格林花了几个星期在伦敦首次接触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炼金术、天文学和复杂的诺斯替象征符号论,这有助于理解“从中世纪经文艺复兴直至现在的西方知识史的连续性。”【37】
最后沃格林回到维也纳。在研究种族问题时,猛然发现“一种政治理论,尤其是它要应用于分析意识形态时,就必须以古典哲学和基督教哲学为基础。”【38】为此,沃格林开始学习希腊语,以有能力阅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事件对沃格林的进一步思考产生刺激,包括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在这些逐步发展的运动中,并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案例中,钻研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种族概念所暗含的生物学理论问题。而1933年后奥地利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抵抗导致了1934年的内战局面,并导致了威权主义国家的建立,这促使沃格林留意宗教通谕,并由此掌握了中世界哲学及其问题的知识。】沃格林在36年出版的伪威权主义国家的研究的专著是其试图洞彻左右意识形态在当代处境下角色的首次重大尝试,并试图理解,“可以将极端意识形态分子遏制住的威权主义国家,最有可能捍卫民主。”【41】
(二)移民与流亡生涯
沃格林自陈,他从1920年代起就一直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理由有三:其一,对意识形态的信奉是一种知性上的不诚实(韦伯影响下),这有悖于科学;其次,他非常厌恶为了取乐而杀人;最后,则是一个喜欢保持语言干净的人的动机,他不认可意识形态及其思想家“对语言的摧毁”,【47】他们“矮化了知识辩论,赋予公共讨论一种明显的暴民统治色彩”。【50】
奥地利沦陷之前,沃格林本认为西方民主不可能让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但西方大国什么也没做,以至甚至一度想加入国家社会主义阵营。后来他恢复理性,却因为反国家社会主义的态度遭致大学开除,最终选择了移民。【42】
1938年,沃格林来到美国担任哈佛的兼职讲师,后来去往阿尔巴马大学,这对于沃格林熟悉美国政治,提升英语水平,主要讲授“政治观念史”。他不满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但自己关于政治观念史因袭的先入之见在理论上并不恰当,“‘观念史’这个概念是意识形态对实在的扭曲。要是没有关于直接经验的象征,根本就没有观念。再者,在‘观念’的明目下,你难以处理埃及人的加冕典礼,或撒玛利亚人在新年的节庆场合吟咏埃努玛—埃利什史诗。”(后来沃格林发现,在廊下派的共同意见中或许可以发现“观念”这一概念的起源,这是洛克《人类理解论》第一章批评的出发点)【64】而在1945-1950年陷入彷徨。直到1951年在芝加哥做威格林讲座时采取的突破,这也就是后来的《新政治科学》。
90年代后期,沃格林前往慕尼黑执教。他既可以组建自己的研究所,培养年轻学者赓续其研究;薪水高;史学家和哲学家戴姆普夫等老朋友一直在做工作,沃格林也不反对进入这一意气相投的知识和精神环境。由此,他把一种国际意识的元素和民主态度的元素注入到德国政治科学中去。【92】
(三)哲学与哲学家
沃格林自陈道:“我的研究在历史哲学中达到了顶点,所源出的动机是简单的。它们来自政治处境。一个生活在一战结束以来的二十世纪的人……发现自身被意识形态语言的洪水从四面包围,即使不说是遭到了挤压——因此,意识形态的预言也意味着预言象征,后者佯装为概念,而实际上是未经分析的传统主题或话题。此外,任何暴露于这种支配性的舆论环境下的人,都不得不应对语言乃社会现象这一问题。他不能把意识形态语言的使用者视为讨论伙伴,但他必须把他们作为探究的对象。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表们根本没有语言共同体。因此,为了批评意识形态语言的使用者,必须首先发现(必要的话则要建立)他自己想使用的语言共同体。”【《自传》,94】
“为什么做哲学?为了再现实在!”沃格林指出,“柏拉图的主要概念是二分的。哲学这一术语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从它的这个对立面获得了意义,即占据优势的意见爱好者。正义问题不是在抽象中发展的,而是在与正义的错误概念的对抗中发展,这些错误概念事实上反映了环境中的非正义潮流。哲人本身的特性获得其特殊意义,乃是通过与智术师特性的对立,而智术师对实在的曲解,是为了获得社会权势和物质利益。
这就是哲人的处境,在此,哲人不得不在一个既领会过去又领会现在的共同体中,找到同类人。尽管意识形态意见总是主导着社会氛围,但也存在着,甚至在我们的社会也存在着庞大的学人族和思想者团体,这类学人还没有与实在脱离联系,而思想者则试图恢复他们正面临丧失的这一联系。二十世纪的一个典型现象就是,精神上富有能力的人冲破主流的知识分子集团,以找到失去了的实在。著名的例子有,在英格兰,奥威尔与他的知识环境的决裂;在法国,加缪与党派性知识分子环境的决裂;在德国,托马斯·曼的巨著力图与魏玛时期和魏玛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决裂,这在他伟大的历史哲学中达到了顶峰——在《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的导言中,他阐明了历史哲学。”【《自传》,95-96】
而“再现实在以反对当代的扭曲变形需要纷繁复杂的研究。你必须重建生存、经验、意识和实在的基本范畴。对于那些使日常习惯变得混乱的扭曲变形,你必须同时研究其手法和结构;你必须发展一些概念,藉此对生存的扭曲变形及其象征表达进行归类。因此,这一研究的展开不仅必须反对扭曲的意识形态,而且要反对思想家对实在的扭曲,他们本该是实在的守护者(如神学家)。”【97-98】为此,“在方法上首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规则,乃是回到孕生象征的经验。”在这一过程中,沃格林发现他不得不探索古典哲人创立的哲学这一象征的含义,其含义必须根据文本来确定。所以,这一象征的含义在时间推移中发生的这类变化,必须通过把它们与原初含义联系起来看,小心地予以确定,因为,只有在这种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你才能判断含义的改变是有根有据(因为这种改变考虑到了实在的某些方面,它们并不包含在原初含义中),还是无根无据(因为,为了建构有缺陷的新概念,实在的要素被排除了)。沃格林反对语言哲学,把它们称为“杜撰词义者的语言哲学”,他们断然拒绝了如下标准,即“语词并非是语言的点缀,而是思想家创造的、用于表达他们拥有的经验。”【98】他对意识形态分子更是嗤之以鼻,他把意识形态的倒错和扭曲称为“拒绝统觉理解”,他们总是把“人对其生存之神性根基的张力的经验”这一实在的部分排除在外。“现代意识观”“用对外部实在中的对象的感性知觉的模型来构造意识”,而非像古典哲人一样把“结构经验(比如,数学结构)和转向生存之神性根基的经验”作为意识之初始经验,这就使得与神性实在相联系的所有精神现象和知识现象被自动遮蔽。但由于它们是人性的历史,不能全然排除在外,于是必然被扭曲为有关超验实在的命题。【100】沃格林认为,对哲人和先知的象征的命题化扭曲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这个扭曲在经院哲学中高度发达,在笛卡尔的现代形而上学转型中进一步强化,然后作为一种次级正统为意识形态思想家所延续。他把命题性形而上学是哲学的扭曲,在教条性意识形态中一直延续看做自己较为重要的发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