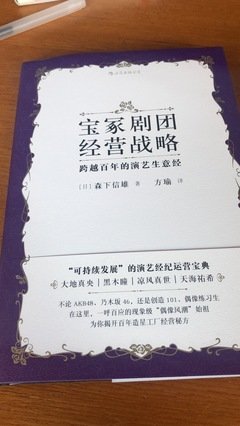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读后感摘抄
《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是一本由[英]埃玛·伯恩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1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精选点评:
●好多内容以前都看过。这书居然是新出的?
●一半和脏话关系不大。
●不知所云,通篇文献,无聊至极毫无用处
●#2020017#
●脏话简洁,含义丰富,这是文化的延伸啊!
●有一点散 各方面的介绍还行
● 篇幅较短,趣味性适中。略有些枯燥……作为一个科普型的书,也差不多了。 尽管人类先祖到底如何进化还不甚明了,但可以肯定:语言在人类中出现,也就代表着脏话的问世。 不论黑猩猩还是人,要说脏话,必然就要洞悉他人的心理,并对思想存有成体系的理解,如此才能预判到语言的效力;情感上也必须活跃,没有情绪的体验,脏话也就无从出口;头脑须要复杂到能够熟知社会的禁忌,如果不能对区分不同行为有一些哪怕朦胧的概念,羞耻和禁忌也就无从谈起,语言也就“脏”不起来。
●学到很多新词汇
●前面两章还可以,第三章开始有点不知所云,写的太散了
●挂嘴多年的脏话居然写错了,cao
《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读后感(一):看了评分我想说——bugger off
认为这本书太发散的人一定没有做过研究,因为仅仅围绕着说脏话的神经学效应来写,其实三页报告就能写完了。
而且你们根本就不知道研究这种内容有多难,在英国每一项实验都首先要向大学伦理委员会申请取得道德许可,这一点本身已经很困难。而且脏话研究在心理学语言发展的领域绝对不能算是主流。
但学术界需要的就是这样的贴合日常的不正经。
再说回这本书对个人的启发,本书从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和神经学的角度分析了说脏话带来的效益,颠覆了我对脏话语言的认知。
结合我自身经历来看,自从叛逆期过后,我就再也没有说过一个脏字,后来在英国哪怕用第二语言骂脏话会比较没有触发禁忌的心理负担,但我也坚持了这样的原则。甚至因为出于对女权的尊重,我拒绝使用“装逼”“傻逼”这样带有女性生殖器官的字眼。
所以当有人脏话以对我时,我会感到倍受伤害,因为在我的认知中骂脏话是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事。
但在给teenage做咨询的时候你偶尔会遇到一些充满强烈攻击性的孩子,他们用脏话回应。有时在叙述过程中他们会加入fuck off或者fuck的所有其他语法形式,也正是他们教会我bitch可以加ing当作动词来用之类的地道青少年俚语。
原先我对脏话的看法一如史蒂芬 平克,认为是低端脑皮层的自我扭曲和动物性的示威。但看过这本书之后,其实在脏话的技术性分析中可以揭开咨询者最深刻的情绪内幕。
比如一位小时候因为超重而有过被霸凌经历的波兰移民女孩,在我和她围绕家庭环境的那次咨询中,她在谈论自己的姐姐时用了类似于fucking doing something的叙述,这是她在谈话过程中唯一一次使用脏话,而且她描述的那件事非常平常,而且一句带过之后就转移到了其他家庭成员身上。直到我看完这本书才受到启发地回想——她的姐姐很可能是小时候霸凌她的人之中的一员。所以她才会无意识使用破坏性的语言。
而现在回顾当时我竟然错过这个重点,只是记录下她对姐姐有强烈的情绪,然后着眼于她对我叙述的学校同学的霸凌,但其实很可能她自己都没有准确意识到来自家庭内部也有一个霸凌者的存在。
如果我再读过这本书之后再遇见她,我可能会更着重地分析她与姐姐的关系。
唉
人对自己轻视的事物总会出现偏差忽视,甚至是错误的贴标签。对任何已知的人类行为都应该保持开放的态度和思想,希望这本书能为同行们带来更多语义学上的启发。
《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读后感(二):总结 最后
不算书评,没有条理和逻辑,权当自说自话。
一、
从高中时期做的社科类英语阅读题,到扇贝阅读上推送社科文章,它们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非常类似。冲破牢笼的我们,终于卸下了面对面课堂对老师箴言警语的唯唯诺诺,敢在文章的评论下发声——“外文社科文章总是洋洋洒洒,然后告诉我们一个早就知道的事情。”
确有其事,而且高赞。
我并不认为他完全错了,但有人已经实名反对。
“我要说的是,这种观点从一开始就错了。常识和显而易见的事物通常都是在事实之后提出的。假设我提出了与事实相反的观点,积极心理学发现我们不需要关心他人的想法和行为,“那些到死的时候拥有最多玩具的人是胜利者”,追求生活的意义是傻子的行为。“我已经知道这些了,”那些批评者又会这么说。这样我们无论怎么说,只能得到再次发布常识的评价,正反两个方面反正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打开积极心理学之门》)这就是为什么本书陈述了诸多证据和事实,还会叫人懵懵懂懂的原因,因为科学研究非常重视方法,从不轻易下结论(那是咪蒙),也尽量客观公正、谨慎小心,避免偏颇歧义的表达方式叫读者误会,因此才会就某一论点多方陈述反复重申——这在本书中比比皆是。
二、
本书的主题是“脏话”,与生理、心理、社会都有关,虽然许多科学家已经就此做出了不小的努力,然而这层面纱基本没有揭开。(我看到豆瓣评论有说不知所云的,看来大家都没明白脏话究竟为何而来23333)
可以将各个部分视作某一主题的重要研究汇总,作者一面笔触细腻,逻辑清楚地介绍实验的精华,一面又从社会人文的视角发出理性的批判。
最喜欢第1、3、5章,左右脑分工在很早之前有过涉猎,温故知新,体验很好;抽动秽语综合征虽然是全新的概念,我却万幸从这里了解(别把重点放在患者的污言秽语上,他们正经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漫长的黑猩猩手语实验,充满科研砥砺精神和人类温情关怀。讨厌第6章,不是反对作者的观点,而是放眼望去的男女鸿沟即使在下一个文明到来之前,也不会改变的现实,让我有点头皮发麻。第4章,我认为作者的一些推理欠考虑,社会学研究里满满都是回归也筛不掉的混杂因素,仅仅将脏话和领导能力直接挂钩,我觉得不够合理。虽然不是脏话方面的专家,但就常识而言,我也无法赞同。请注意我反对的并非使用适当的脏话可以融洽氛围、促进交流等,而是“超级小组”部分,这点我已在文中标注想法,不再赘述。
三、
写这本满眼艹字的科普书还是需要勇气,即便在学术界都能招来质疑,更别提公众了。我对这位准妈妈的能力和才气都很佩服,字里行间都是她的幽默风趣和自信骄矜,生活中想必也神采飞扬吧。别人说她浪费科研经费,她就说我只花了一瓶红酒的钱,别人说她不如去攻克癌症,她就说那应该让与有识之士。
但若论全书最佳,还应当属翻译,游刃有余又云淡风轻地把不同时代和背景的脏话与中文词汇相对,不仅如此,恰如其分地引经据典,就如最后一句“幸甚至哉”,做到最灵活生动地贴近本意,然而这还不够,最难的是对科研部分的精准翻译,这不仅考察的是作家的文学素养,还有非一夕一时之功积累起来的科学素养。
最后感慨出版社的“胆大妄为”,想起红楼的青少年读本里没有智能儿的情节,86年剧版里薛蟠的女儿歌也只唱了两句,如今,这艹字春花烂漫,终于见了天日了。
《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读后感(三):为脏话正名
我在约莫9岁的年纪,因为叫了我弟弟一声“傻屄”(twat) 而挨了耳光。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这词原本的含义,只不过当它是“挖苦、嘲笑”(twit)的一个学名。我在那个耳光过后明白了两点: 第一,不同的字眼在感情程度上是有差异的;第二,某些感情程度强烈的字眼,要谨慎使用。
当然您看,我终究没能改掉说脏话的毛病,反倒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今步入职业女性道路的我,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脏话跟男同事们打成一片。要知道,作为一名研究人员,对着仪器大喊“该死的狗屎”(fucking piece of shit)往往可以算作某种入团仪式。
总算有一天,我发现学界竟不乏致力于研究脏话的前辈,“脏话有效用”论也并非我独创,我真***松了一口气!真正令我认识到脏话的内涵不止于谈笑或污蔑他人的,是参与主持一项神经科学实验——实验里有67 名勇敢的志愿者,一桶冰水,一句脏话, 还有一块秒表。就是在那之后,我全力转向了对骂脏话现象的探询:人为什么骂,怎么骂,以及骂脏话揭示了人的哪些本质。
图片来自网络什么是脏话?
历史上的脏话往往是以发誓或诅咒的形式出现的。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一类词语中蕴含有某种灵验的效力:恶语既出,可以呼风唤雨,变天降灾。
现如今我们说脏话,其实打心底里并不相信它有实际的法力。就比如骂某人“日你祖宗”的时候,大概私下里是不会想着让此话一语成谶的吧!虽说天打雷劈、七十二变的神力不存于人间,然而每当脏话出口,我们依然盼望着它能幻化为一道无形的剑气去挫伤对方的锐气。也就是说,恶语也好,咒骂也罢,仍在源源不断地从迷信和禁忌中汲取能量。
但问题又来了:现实生活中的脏话不光被作为攻击和侮辱的武器,而且被用于表达人自身的愤懑不平、亲友间的同仇敌忾,或是亲昵的调笑、逗乐——这点在调查研究中已经得到了反复印证。脏话的功用如此多元,真是像滑溜溜的泥鳅一样令人抓不住要害,该怎么剖析、定义它呢?我在翻阅了数百项相关研究之后,得到了两条学术上通用的脏话定义:第一,情绪激奋的情况下使用的词语; 第二,指代普遍禁忌的词语。回想一下您所知道的脏字、脏话,应该全部符合这两点。
是什么把脏话跟其他词语区别开来——脏话之“脏”,触动的是视听,还是骂者的心弦? 是不是所有语言都有脏话?为什么小孩子骂起人来屡教不改?如今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知能有所进益,从维多利亚时代的外科医师,到现代的神经科学家,都有贡献。只不过碍于脏话的负面形象,这些知识迟迟不得进入主流社会,只能在学术阅览室里积灰。
图片来自网络脏话向我们透露了不少更高层级的思维过程
在工作中骂脏话来拉近与同事的距离,我绝对不是个例。相反,从研究来看,脏话确实具有加强同事之间联系纽带的功效。不论是在工厂车间,还是在戏剧排练场,科学家们都通过对照观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同事之间互用脏字、粗口的团队往往比不用或少用脏字、粗口的团队工作更高效、关系更紧密、业绩更显著——再进一步说,骂脏话在减轻工作压力甚至身体痛感上的效用,胜于任何所谓“团队建设”的活动。全凭酣畅淋漓的一句——“我日!”脏话研究也帮助神经科学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脏话用于情感测评、量化,在近现代科学研究中经久不衰,已有超过150 年的历史。由此我们获得了大量关于人脑结构的事实,包括大脑分为左、右半球,以及特定脑内结构如杏仁体在情绪发生、控制之中的作用。
脏话也向我们透露了不少更高层级的思维过程。比如说,人在用非母语说脏话的时候面临较小的心理压力——这一点指引我们去探寻人在早期教育阶段如何逐步了解情绪和禁忌。又比如,说脏话会使人心率加快并给予大脑暴力的暗示,与此同时却降低了实际使用暴力的概率——真是应了“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俗语。
在集体的语言储备之中,脏话还是异常灵活易变的一环。社会禁忌不断变迁,脏话的面貌也得以代代变异。曾经的指天咒骂能够演化为喜悦之情的流露——足球球迷满口不堪的字眼,众所周知是不限于发泄愤懑与诅咒的。
在一次和伦敦大学同事的研究中,我们调查了数千名足球球迷在比赛期间的脏话行为。对于脏话出现的频率,尤其是像“日”(fuck)、“ 屎、狗屁”(shit)这样的字词泛滥成灾的情况,我们早有准备。但是两者之间(“日”“屎”)呈现出某种比例关系且能与胜负形势高度吻合,倒是令人始料未及。是这样的:几乎毫无例外,“屎”等粗口对应的是球队失球或其他赛场上不利的状况,而“日”则不区分形势利与不利。另外,脏话连篇的球迷尽管看似鲁莽,其脏话的攻击性却远不及我们想象中的程度——在网络媒体上观测到的球迷骂脏话,几乎全部指向自己支持的球队或球员,而非赛事对方。
这项研究一经发表,着实让我品尝到了当过街老鼠的滋味。最先上门的是英国某著名报社的记者。这家报社我不点名,但对于它雷厉风行的道德急先锋姿态,以及一面披露大幅女星长焦裸照,一面煞有其事地批评其“出位”,可谓老少皆知。两个质问劈头盖脸扔过来:一、浪费了多少钱在这项研究上面;二、可不可以从事一些有用的研究(比如癌症治疗)。我的回答是:第一,统共6.99 英镑——研究小组自费的一瓶超市红酒,是我们在制定研究假设的时候喝的;第二,我与另外一位此次项目的负责人都是计算机科学家,在医治肿瘤方面没有丝毫的专长,不得已只能把癌症患者托付给相应的专业人士。之后那家报社便再没回音,舆论风波不久也平息了。虽说如此,脏话研究仍为公共舆论所不齿,确实通过这次事件得到了验证。
尽管您可能对脏话也抱有“稀松平常”“不值一提”的成见, 但要知道在科学界,脏话研究却是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历史学家都对其抱有长久的兴趣,实在是有极好的缘由的:脏话现象看似不值一提,却恰恰能告诉我们人脑、思维以及社会是怎样运转的。
图片来自网络脏话属于最早的语言形式之一
人人都看到脏话的不登大雅之堂,却不晓得它还有那么多细致的可取之处——只要骂得恰当,粗俗的语言也能演绎出风趣、滑稽、放荡、侮辱等不同的意味;不论亲口说还是听到他人骂脏话, 都关联到我们自身一系列奇妙的体脑反应;言语上的不检点,能帮助我们应对疼痛、减缓压力,更能促进同事间的关系,甚至有助于语言的学习;除人类之外,其他的猿、猴之属同样具有各自独特的骂脏话行为,而且这些“非人类”脏话的作用还挺他妈大的——据此我们可以推测:脏话属于最早的语言形式之一。
经常听到有人说:真正的大人物和智者不说脏话,说脏话的人不是词汇贫乏,就是缺乏文化修养。我可以很确定地告诉您:脏话不光能骂出大智慧、大气场,连在日常的社交和情绪活动中也缺它不可。我们研究心理和社会科学少不了脏话,而且要是告诉您我们怎么研究的、研究出来哪些成果——哇靠,您铁定要大吃一惊!
脏话一旦咸鱼翻身,我个人以为定是天大的福音——不仅是从言论自由的原则上这样讲,更是因为骂脏话行为原本就是为我们个人和全体人类服务的。我们以脏话太过激烈为由,理所当然地想要将其淡化。但是科学研究的结论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更加仔细地倾听脏话,因为“败絮”之中往往暗藏玄机。总而言之,我虽不鼓励人们把脏话整天挂在嘴上,但是以后再面对这些语言中的奇葩时,务必请您***放尊重点!
她为脏话写了本书
埃玛·伯恩,一名科研领域的特立独行者,像这篇文章开头讲的,因为小时候无意说了一句脏话而被扇了一个耳光,在此之后,他反而对说脏话这件事生出浓厚的兴趣,并且投入极大热情,以一种非正统的方式、秉持严肃的态度对其进行了研究。她结合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探究了脏话的起源及进化,以及说脏话的各种妙用,令人耳目一新。
埃玛·伯恩说,在她这本《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中,并没有把脏话作为单独的现象来剖析。她认为脏话非常“屌”的一点,就在于它的触类旁通、无孔不入,所以写着写着,必然会岔得远一点,甚至在有些章节中不提任何脏字。但是从日语拐弯抹角的语式,到黑猩猩的坐便训练,不管乍看之下再怎么不可思议地离题,她保证“我们是如何骂脏话的”这一点将会贯彻始终。
有人会问:写这本书,是不是为了宣扬不和谐、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非也。埃玛·伯恩说,她绝对不希望看到脏话泛滥成灾。况且,脏话之所以还能有脏话的作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情感上的震慑效果。反观过去一百年间主流脏话的变迁,可以轻易发现早先的脏话或消减于社会上的过度使用,或没落于普遍价值观的变革,而新的禁忌又不断被制造出来以填补空缺。与过去以不敬神、没有信仰为根基的脏话咒骂不同,当今社会视种族、性别歧视为大忌,也就因此衍生出了相应的咒骂。到底这是象征了新自由主义“政治正确”的霸权,还是代表了抗击恶毒偏见势力的可喜进步,这点就要留给读者您自己来判断了。
《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读后感(四):***本书内容不可描述***
1848年,一个名叫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Gage)的包工头在铁路施工爆破现场被一根飞出的铁棒击穿了脑颅。据医师(Edward H. Williams)回忆,当时盖奇受伤后坐在那里,谈笑如常,甚至绘声绘色地描述起了自己受伤的经过。过了一会儿,盖奇“起身呕吐,有约半茶碗体积的脑组织伴随着呕吐受压排出”。在这番惊悚场面过后,盖奇竟然依旧神志清醒。约翰·马丁·哈洛(John Martyn Harlow)是随后接手治疗的医师,他通过对盖奇案例的研究,完成了两篇记录伤情与治愈过程的传世之作:《头部被铁棒穿通的调查》,《头部被铁棒穿通后恢复的调查》。此人心理承受能力超强,说服了盖奇允许他直接用手触摸颅内以探明床上的具体状貌。最后他得出结论:盖奇的左前额叶已经损毁(即流出的“半茶碗”物质),而右侧得以保全。盖奇在受伤前,个性随和、勤勉不已,而在伤愈之后却令领导大失所望。去世前,他只能在地里做杂活。 ……躁动不安,口无遮拦,时常无端使用极其猥亵的词语(与其过往言行形成反差)。……《头部被铁棒穿通后恢复的调查》,约翰·马丁·哈洛 ——也就是控制不住地骂脏话。维多利亚时代,神经科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时上流社会不屑于骂脏话,医生也多自诩典雅,往往对病患的这种行为视而不见,而科学家约翰·杰克逊(John Jackson)对大量精神病人进行了研究,他不顾世俗记录下了病人骂脏话这一事实,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直到20世纪80年代,脑损伤患者研究纷纷证实,除却个例,失语症患者普遍存在有谩骂习惯。在1999年,美国神经科学家 Diana Van Lancker 与 Jeffrey Cummings 冲破禁忌,列出了患者常用的敏感词如 bloody hell , fuck off , oh you bugger , 以及一系列高频短语如 well I know , wait a minute 。他们的研究对象中有一位患者,此人整个左侧大脑都被摘除。后来他再也不能说出物件的名字,如卷尺、手表等,复述词语时也会有许多差错,比如他会把 remember 说成 November 或者 sandwich 。但是在骂人方面他没有退步。在五分钟的录音档案里,研究员得到了7次 “该死”,一次“老天”,一次“狗屎”。骂脏话之轻松远超推敲日常短语,而且语句清晰流利,毫不含糊。还有一次,研究人员向他出示了里根的照片,竟收获奇效:“总统的名字被夹杂在一连串出奇流利的污言秽语中成功说出”。 “原来此患者不仅政治立场鲜明,而且不乏直抒胸臆的胆略。”《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 而脏话在其中起到了润滑的效果。如果一个人左脑受损,那么有相当可能发展出失语症:因为语言官能所需要的组织一般位于左脑。研究右脑损伤则比较困难,一般右脑受损的症状比左脑更症候隐蔽且不易孤立观测。有一位右脑受损的患者,平常对话时察觉不出异样,但时间一长就发现他遗忘了许多本该烂熟于心的习语,比如祷告词、祝福语,甚至从一数到二十也不十分流利。这还不算完,此患者原本就不爱说脏话,后来更是想骂一句的冲动都没有。 “研究人员问他在各种场合习惯上用哪些不文明的词语,他一个都想不出;拿写下来一半的骂人话给他,他也填不出“你妈”中的空档。”《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 大量实验表明:左脑半球大致容纳的是负责“循规蹈矩”语言的部分,而右半球包含了大量帮助处理情绪的部分。右脑受伤的人容易变得“不近人情”,说话直来直去,幽默感降低,很难理解笑话和比喻。脏话行为和情绪是紧密相关的,故而右脑受损影响了脏话的输出。其一,患者自身失去了骂脏话的动机,他们感受情绪的能力减弱了,“脑中自无情,口齿复清净”。其二,脏话是一种技术性与情感性兼备的语言,需要骂人者推测脏话出口造成的情绪反应,而缺失右脑的人即便想骂人也捉摸不到情感。而对于左脑受损的人来说,他们的情绪一如既往,但由于语言功能受损,这些情绪只能通过仅存的出口来宣泄,而脏话恰好包含在幸存的语言之中。大脑里的其他组织,如杏仁体,可以刺激和控制情绪,让人骂出脏话。杏仁体是一颗形状大小与杏仁略同的大脑组织节点,左右各有一颗。杏仁体偏大的人更加善于交友,人脉更广。杏仁体的体积也可以预测一个人的抑郁倾向。在手术中摘除杏仁体,人的情绪反应总体会降低。大脑不具有感应痛觉的官能,所以做脑部手术开颅只对颅部进行局部麻醉,整个人神志清醒。这种做法并不是残忍,原因有三:其一,全身麻醉有致死可能,一般应尽量避免全麻;其二,手术前要直接对大脑实施少量电击,以此探测脑组织,以免切除重要的组织;其三,对于科学研究,手术期间能够观察、采集到大脑的反应。两位苏格兰医生在手术中用电流刺激了病人的杏仁体,病人立刻爆发出一阵不文明用语,然后转瞬即逝,甚至自己都对那一串脏话感到惊讶。人们在很多场合说脏话。感受到疼痛时,脱口而出的咒骂会在精神上产生减轻痛苦的程度。人产生的情绪不可能只有一种,恐惧中往往混杂着愤怒,这时候也会不假思索地骂脏话。甚至在工作场合,骂一句“***”,也能无形间拉近人们的距离。而想要融入一个集体时,掌握这个群体的习惯用语——尤其是打趣和脏话,是一条捷径。 黑猩猩是与人类最接近的物种,为了探究黑猩猩的语言能力,科学家做了各种各样的实验。由于黑猩猩发声器官的构造与人类大不相同,它们的舌头细薄而声带位置较高,可以简单发音,却远不如人类的语音繁复,所以它们不能像人类一样“开口说话”。黑猩猩在自己的生活范围内大多数时间都是沉默的,相互啼啸也只是为了传达情绪,日常沟通大多依赖比比画画。人们以为黑猩猩吵吵嚷嚷只是因为在电影里有一群人去骚扰它们,迫使它们发出惊惧的呼叫,“对于熟知黑猩猩习性的人来说,听到这些配音无异于亲临残酷折磨的现场”。但是黑猩猩的智力足以掌握手语。20世纪30年代,凯洛格夫妇在纽约以抚养孩子的方式培养了一只黑猩猩,让这只名叫Gua的黑猩猩与他们的儿子唐纳德一同长大。但是这个实验只进行了九个月便迫不得已终止了,因为Gua有了些人样,而唐纳德却猴模猴样起来。另一个计划,宁姆计划,完全不同。这个实验完全在实验室中进行,一切工作人员都不允许与黑猩猩发展“特殊感情”,所有教授手语的课程都极其冷漠严肃:展示手势,等待黑猩猩准确无误地复述后才给予奖励。实验完全忽略了培养语言的内在动因:发自沟通本身的愉悦。所以宁姆计划不出意外地失败了,黑猩猩宁姆在两种语言之间不上不下,落了个半吊子,除了出于获得奖励目的的鹦鹉学舌之外一概不知,更不用说理解句法与语法、倾诉衷肠。美国的罗杰·福茨教授毕生致力于研究黑猩猩。他是华秀计划的创立者。随着观察的持续,福茨越来越相信黑猩猩的语言能力不光局限于简单沟通,他们还能自发地掌握脏话。1966年,内华达大学的学者加德纳夫妇决定重做凯洛格夫妇的实验,他们收养了一只名叫华秀(Washoe)的幼猿,对华秀完全视如己出。他们在4年间教会了她用杯子喝水、使用刀叉、穿脱衣服、上厕所。后来他们又陆续收养了四只黑猩猩,组成了一个大家庭。人类的孩子牙牙学语不光直接通过对话,还有环境的熏陶。同样,在以手语为主的黑猩猩身上,只有在手语的环境里成长才能完全掌握语言。研究团队为了不让黑猩猩以为认为手语不是通常的人类语言,所有人都在华秀面前保持沉默,连外人的交流都一并抵制。就算出门去麦当劳买零食,也要谨小慎微。华秀可以“朗诵”,她一边翻阅图书,一边比手画脚,出现错误还可以倒回去纠正。过了一些时日,华秀已经能比画出类似“给我/糖/然后/你/我/去/外面/快点”这样的短句。她学习的不只是个别手语符号,而且能将其串联,汇入自己的感受。黑猩猩能理解抽象符号,能构造新词,能用语言描绘世界。随着它们的语言水平日益精深,脏话也终将在人类之外的物种身上再度发明。为了教会华秀在适当时间、地点排泄,研究人员教给她一个观念:“脏脏”是不好的,但在小桶里“脏脏”没有问题。经过一番苦功,华秀已经比不少人类还要像样,在树林郊游的时候她因找不到便桶看起来很是窘迫,直到有了空咖啡杯才勉强解决了问题。在加德纳家的黑猩猩之间,“脏脏”的手势被用来形容排泄物、脏衣服、外穿的鞋,以及排泄行为。“脏脏”手势重复两遍,则是用来加强语气,表达愤怒或者羞愧。无心闯了祸,“脏脏/脏脏/对不起”。人类会因恐惧他人揭发自己不规矩的行为而编造出弥天大谎。黑猩猩一旦被人发现在做不正经的事,也会同样努力隐瞒或扯谎。因为它们理解“脏脏”的禁忌,所以另一只黑猩猩露西才会在随地排泄之后试图撒谎。 福茨走进房间,眼见遍地是露西的“杰作”,于是问道:“那/什么?”不想露西演技高超,佯装无辜道:“那/什么?”福茨轻易不会上当。他追问道:“你/是/知道。那/什么?”露西答:“脏脏/脏脏。”福茨又问:“谁的/脏脏/脏脏?”此时休也跟来讯问露西(休是当时福茨聘为研究助理的硕士生。此前福茨根本没有想过她会愿意卖力到这种程度——可见攻读博士的学生在压力下是能够做出极不寻常的举动的)。福茨穷追不舍:“这/不是/休。那/谁的?”露西眼见穷途末路,不顾一切地辩道:“福茨。”福茨恼了,训斥道:“不对/不是/我的。谁的?”露西:“露西/脏脏/脏脏。对不起/露西。”《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 没过多久,在华秀的语言中,这个词就被添上了其他意义。没有人教过她要把“脏脏”一词多用,她全凭自发地在烦恼时将其作为谤语或叹词使用。华秀抗议福茨将它关在笼子里时会比画“脏脏/福茨”,翻译过来大概是:“福茨,你***就像一坨屎”。 ……(华秀)对一只前来挑衅的猕猴比画道“脏脏/猴子”。 实际上“猴子”这个手势同样得到了华秀的灵活应用,发展成为指代其他不会手语的猿猴的词语。也许我们不乐意也得接受一个事实:基于身份的污蔑语早已深深地植入了人与黑猩猩的语言当中。 《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 华秀虽然只有一个脏词可骂,但骂的方式却非一成不变。一个人在骂脏话时可以声嘶力竭、破口大骂、咬牙切齿,“脏脏”一词也可以被赋予额外的力度。“正常‘脏脏’的手势是将腕背抬至下颌处——而有时黑猩猩手腕比画的力度过大,整个实验室咔咔声回响不绝。”黑猩猩非但有能力学习语言,还可以教授语言。华秀移居俄克拉荷马大学期间产下一子,但由于实验室严重照顾不周而在出生几天后夭折。为缓解华秀失子之痛,福茨找到了一只十个月大的黑猩猩卢利斯。没过多久两只黑猩猩就情同母子,华秀十二隔空演示,时而把住卢利斯的手逐字比画。卢利斯从华秀以及其他年长的黑猩猩那里学会了手语。经历过加德纳家的宽敞独栋、俄克拉荷马大学暗无天日的笼子、中央华盛顿大学的蜗居生活,华秀最终搬到了新建的六百多平方米的家园。 在这敞亮而安适的温柔乡,华秀走完了它42岁的一生。它死去时是在2007年。床榻边围绕着它的,是两个深爱它的物种。《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 黑猩猩具有高度的自我意识和复杂的情感活动,更不寻常的是它能够体察情绪。福茨的同事Kim在宝宝夭折后返回工作,用手势对华秀说:“我的宝宝死了”。接下来,“华秀略微凝视Kim的双眼,然后一面轻手轻脚的比画‘哭’,一面碰着它的脸颊,向下比画出人类流眼泪的轨迹”。黑猩猩能够理解情感与禁忌。了解禁忌的同时也就赋予它一定的情感,关联到禁忌的词语时能引发情绪的唤起。“不论黑猩猩还是人,要说脏话,必然就要洞悉他人的心理,并对思想存有成体系的理解,如此才能预判到语言的效力;情感上也必须活跃,没有情绪的体验,脏话也就无从出口;头脑须要复杂到能够熟知社会的禁忌,如果不能对区分不同行为有一些哪怕朦胧的概念,羞耻和禁忌也就无从谈起,语言也就“脏”不起来。” 既然脏话源自禁忌,而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忌讳,常用的脏话自然大不相同,一门语言里的茶余闲话到了另一种语言里可能就是晴天霹雳。对于最重视血缘与宗族的中华文化区,有关直系亲属的脏话自然最多也最能让人火冒三丈。加之汉语音节简单而表意丰富,作为孤立语可根据需要自由组合音节、具有空前强大的信息携带能力,更让脏话艺术如虎添翼。在意大利骂脏话总绕不过上帝、圣母,德国人的“畜牲”就不好使。对于土耳其语中常见的带有宗教色彩的诅咒如“真主会制裁你”等等,对非伊斯兰教徒根本毫无杀伤力。而有关生殖系统和消化系统的脏话,世界通用。 在学校学外语的时候,“读书破万卷”,最先破的总是关于敏感词的那几页。而长时间寓居国外的人,为了融入当地环境,也免不了学习脏话。但归根结底,还是婴幼儿时期学到的语言最能引起人的情感共鸣,甚至听到录音带中来自母语的训话,反应都会比第二语言强烈得不止一倍。而无论一个人的外语说得多流利,总会觉得用母语骂脏话更带劲儿。俄剧《叶卡捷琳娜二世》第一季中,初来乍到的叶卡捷琳娜走在草地上,脱口而出的还是一句德语。 有一本书叫《英语委婉语词典》,列举了成千上万种表示各式意思的俚语。这本书的序言中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货币学中的格氏定律指的是在流通过程中,人们倾向于收藏成色好的钱币而把成色差的花出去,即“劣币驱逐良币”。语言学的格氏定律是讲某个词一旦具有了贬义的引申义,久而久之它的本义就会被贬义意义所取代。啊哈,cherry。 脏话在中国 先秦时代的脏话没有多“脏”,只把人比作动物:东郭狼、硕鼠、狡兔三窟、禽兽。 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 秦汉时期,伦理被引入了脏话体系。老流氓刘邦就擅长做别人爹。再多也不过一句“竖子”。要了解这个时候的脏话,参考文献只有:《高祖本纪》。隋唐时期脏话的词汇量才形成规模,有骂长相的、骂辈分的。最重要的是歧视少数民族的,标准句式是某某狗、某某奴、某某獠。安西节度使夫蒙灵察就骂过高仙芝“噉狗肠高丽奴”。 何不扑杀此獠?!《新唐书·褚遂良传》,武曌语 到了宋元时期,脏话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进步。 傻屌!放手!《荐福碑》(元曲) 经过宋元的积累,明清骂人话是真正的集大成者。 野牛肏的,胡朝那里跑!(王熙凤)我们肏不肏屁股,管你几把相干!(茗烟)糊涂油蒙了心,烂了舌头,不得好死的下作娼妇们,别做梦!(王熙凤)你快夹那些屄嘴离了这里,好多着呢!(鸳鸯)真真小短命鬼,放着尸不挺,三更半夜嚎你娘个丧!(巧姐奶娘)《红楼梦》 最后……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汉中去,你强要往汉中去,如今果然折了许多兵马。驴球子,入你妈妈的毛! 钦此 据传为张献忠御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