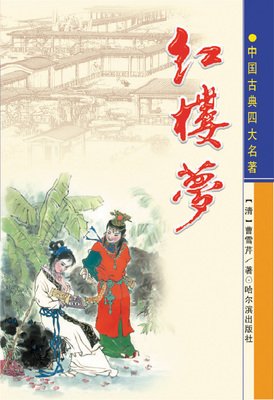希望的敌人读后感100字
《希望的敌人》是一本由林赛·沃斯特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0.00元,页数: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希望的敌人》精选点评:
●有过之而无不及
●扯了一堆话,就那么个“研究的书的质量和数量与职称(教授终身制)之间的关系”以及为了自己的“人类学”的尊严吐糟了一番。
●时下想做社科研究的必读 不过最好读英文版 翻译不给力呃
●2011-05-21,读完这本书就可以辞职滚蛋啦?2012-05-04,是的。
●小书大思想,既揭露了问题,也指明了出路,翻译顺畅。
●新年第一本吐槽小書,真的是,天下烏鴉一般黑啊⋯⋯在學術功利化,大學市場化的資本潮流中,試圖恪守傳統價值的人文學科變得愈發艱難。書中寫道:“二次大戰之前,幾乎所有的高等教育機構都是以宗教為名義建立的。那時,因為大學的最終參照係是神,而神又是無法界定的,所以校園裡的各項活動有著極其遼闊的天地⋯⋯那時的學院生活是神職(calling),而不是工作(job)。但一旦美元成為了最終參照物,天地就縮小了。”作者認為,學術活動的真正追求,對於自然科學而言是新的實驗,對人文學科而言則是新的經驗。這個觀點倒是有意思。如果可以不被體制壓迫得蠅營狗苟,我倒願意在大學裡做一個文化和價值的傳承者。不用刻意去創新或發表,那些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也許真是愛之深責之切吧,離這個終極的生活狀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呢~
●其意如题
●如果所言属实,那么中美的学术有啥区别呢?或者说,中国是在被同化?不知道这本书说的是不是真的。
●如今的学术生产机制是不是有问题?本书给出了一种答案
●有些地方还是难懂
《希望的敌人》读后感(一):“无人阅读”与“不发表则出局”
书很薄,但是信息量也不算小。之前直觉地感受到美国人文学界非常地“能出书”,而且大型学术出版社的出版资格总给人以因通货膨胀而贬值的观感。从这本书来看似乎确实如此,至于微观上是否有这样的区别,不停地出书和不停地发论文对学术有何不同影响还未可知。
当然,很多书和论文都是没有读者的。作者提到旧时大学的研究以神为参照系,所以研究范围更广,这也部分地提示了发表本身而非“发表之后”成为学术意义的原因(主要是人文学科),即书中所谓的“无人阅读”。人文学科似乎倒是有一种办法来搞到读者,就是鲜明地为诉求和立场服务,但是是不是还有别的路径来获得读者,以免在学术获得表面上的独立的同时走向封闭的乃至于传销似的局面,可能才是更应该追求的东西。
《希望的敌人》读后感(二):学术圈的市场经济——《希望的敌人》读后
近些年,我们与世界接轨,不仅仅是市场经济,就连学术圈也要与世界接轨,于是乎出现了张维迎版的北大改革计划,据说要想在北大获得一个职位,至少要有获得欧美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不仅如此,据说连学术制度也在迅速向美国看齐,比如我们所周知的“不发表即淘汰”,迅速在国内流行开来,于是乎国朝上上下下忙着抄论文、争课题。
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小册子将美国这个学术工厂揭了底朝天——他这部小册子的副标题叫做《不发表则灭亡如何导致了学术的衰落》。这个标题非常耸人听闻,但没有听说美国学术完蛋了啊,我隔壁的某某同志还想到美国留学呢。但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大编辑应该不会信口雌黄,毕竟在国朝大学出版社在大量排印垃圾读物的时候,哈佛大学出版社早已经是享誉全球了。只是不知道,沃特斯在这部小册子中,给我们带来了美国学术界的那些轶闻。
在198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543本新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802本。到了2000年剑桥升至2376本,牛津升至2250本。所有大学出版社的总出版量在2000年为3100万册。
我推想,这个数字在经历了新世纪的曙光之后,应该会翻一番。而国朝的出版量,我实在是不敢想象,毕竟在大学扩招,文凭扩招的情况下,每年五万博士,就意味着五万本博士论文,还不要说其他各式各样的课题和论文集。随着而来的是伴随滚滚金钱浪潮的海啸。
而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呢?据说,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政府要求大学对核武器进行研究,拨了巨款在这个毁灭人类的武器之上。随着战争的结束,政府向大学的拨款并没有结束,而是更加源源不断地流入了大学。沃特斯说,来自政府的资助迫使大学为了自己建立了一个日益膨胀的官僚机构,为了应付来自哥哥拨款单位的文件。
金钱改变了大学自身的面貌,而身在其中的人文学科更加尴尬。美国某大学校长说,他对于人文学没有任何期待,因为他们是没有前途的。而美国的纳税人又是如何看待学校里的那些人文教授的呢?说实在的,他们也同样不喜欢那些供职于各个名牌大学的名流们,那些人文笔晦涩,根本就是垃圾,还不如灭了他们算了。
对于以上的判断,我想中美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差别,而伴随着经济起舞的步伐,两国的人文教授们疲于发表文章,频繁做学术报告,由此而生产出来的学术产品数量的攀升速度肯定要高于最近不景气的道琼斯指数。人们对于学术创作的热情,正如网络经济的泡沫造就了纳斯达克的繁荣,也同样造就了学术出版市场的繁荣。但是,泡沫经济从来不会持久。
这个制度已经濒临崩溃了,据统计美国2002年版《学术图书馆调查》的统计,图书馆订购的印刷品从2000年至2001年下降了6%,在2002年又下降了大约8%,具体到学术专著的销售趋势,数据就更加不容乐观了。仅到2002年6月图书馆订购的大学出版社书目实际上就下降了12%以上,而精装书更是下降了20%。换句话说,也许学术出版的末日就在不久将来的某一天。
《希望的敌人》读后感(三):读书笔记
希望的敌人:不发表则灭亡如何导致了学术的衰弱
[美]林赛·沃斯特著 王小莹译 商务印书馆,2011.4
第一部:兵临城下
我不在意你脑子慢,我在意的是,你发表的速度比你思维的速度快。
——沃尔夫冈·泡利
使年轻作者们走向毁灭的是粗制滥造;而导致粗制滥造的是对钱的贪婪。
——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
#“做假账”(cooking the books):二次世界大战与大学的转变#
1、现代化的、极其复杂的量化方式被用于评估学术界的工作,其始料未及的结果是,学术工作被淘空了意义。 P8-9
3、1973年,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吉拉尔德•普拉特(Gerald M.Platt)在《美国大学》(The American University)一书中警告说:“任职理性价值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将对大学造成伤害,因为这将会支持官僚体制化进程的简单化价值。学院生活是神职(calling),而不是工作(job)。学者需要投身的是整个一个领域,而不是一个受上下班时间表控制的例行公事活动。
4、来自政府的资助迫使大学为了自己建立了一个日益膨胀的官僚机构,为了应付来自各个拨款单位的文件。P11 #一个管理阶层的发展#
各大学都发现,现在减少给人文学科的拨款越来越容易了。人人都必须自立!新自由主义学说的兴起让纳税人普遍觉得,社会的所有服务机构都必须私有化。有些城市甚至把小学和中学都交给了“私人企业”。但人文学的教育很难私有化。提高文化水准也许是大家的共同目标,但和许多其他共同目标一样,没人对它富有特别的责任。P18
#判断的中心地位#
对康德来说,判断首先是个人行为:“启蒙意味着自己思考。” P35
汉娜·阿伦特:判断所需要的前提……不是高度发展的智力或老练……而是自觉地与自己共处,与自己交流的品性。 P37
第二部:从玩世不恭到全盘否定:现有秩序的卫道士
一个典型的学者愈来愈让人觉得像一个查理·卓别林的《摩登世界》中的人物,拼命而麻木地为了生产而工作。 P50
一股怯懦之风正弥漫着整个学术界。如今的至理名言是,别问太大的问题……还是知趣为好,在细枝末节上做文章。 P51
#向否定主义的滑落#
过去我们有许多创新,是因为有人尝试自己领域之外的想法。……现在我们接受了这样一种想法,那就是,每一个领域都是独立的,博览群书对专业人员毫无用处。 P79-80 ( 专才 VS 通才 )
#无论如何书还是很重要#
奥古斯丁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人正好相反,后者掏空了书的所有意义和内容,而奥古斯丁则相信,一件东西,一本书,(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电影,或者一首歌,或者我身外的某个人造物,都能吸引我与之交流,并因此而改变我的灵魂。 P82
人文学科若要重新兴旺起来,我们就不能再坚持让各个学科泾渭分明,而应该让各个学科的想法、方法以及资料充分流动起来。P83
#学术与沉默#
正如伊莱·弗里德兰德所所说:“沉默的反面不一定是有理之言,而是噪音”。如今,学术界到处都是噪音,而我们应该寻找的事一种平衡,不光有学者出书,还有学者乐于读书并认真与之对话。P87
写作中的书和阅读中的书之间,存在着一种绝对的对称,一种相遇,正是由于这种对称,书才有了它特殊的美。 P89
海德格尔:自苏格拉底以来,西方所有的大思想家都不得不是流浪者,不管他们有多伟大。P93
如果人文学关乎的是判断,那么我们需要判断的则是,在我们和艺术作品的互动关系中是否有新的东西出现。 P96
《希望的敌人》读后感(四):反驳与批评:《希望的敌人》存在吗?
《希望的敌人》这本书是一位学社科的朋友推荐给我的,听说里面有很多对当今学界(尤其是文科研究)现状的真实批判。我本来对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抱有很高期望,因为在中文图书市场上,系统论述学界体制,尤其是这么新(2004年美国初版)的作品极少。但读完之后,我对它的很多论点和结论产生了一些疑虑。特别是和哈佛一位做英国文学研究的教授(他可算是本书讨论主题里的正统“人文学者”了)进行了一些讨论后,“哪里不对劲”的感觉愈发强烈。写的这篇书评,其实主要应该算是驳论。
不过我接受的不是人文学科训练,也不了解中美两国目前人文学科的实际处境,批评的角度,主要还是基于自然科研圈子的常识,若是有了解美国人文学术圈体制的读者,还请指正。
一、两点特殊之处
首先很明确的是,林赛·沃特斯(Lindsay Waters)写这个册子,主观立场挺强。林赛从博士毕业之后就在哈佛出版社做编辑,根本不做学术,未必理解圈内的情况或者圈内人的管理出发点。用我那位认识他的哈佛教授的话来说,这个册子的论点不奇怪,因为作为一个搞图书出版的编辑,“of course he would say that”。
其实从书里也能看出作者缺乏一手资料,因为列举的实例和数据寥寥,少数的证据主观性也很强(大多数是某某教授给他的信里讲了某句话之类)。而且集中对某一两个人火力轰炸,难免令人怀疑夹带私情(这点后文再谈)。尤其书的后半部分,靠文艺理论和抒情辞藻而非摆事实讲道理,作为一篇“檄文”,说服力差了很多(也可能是为什么如此大的题目只撑起了一本小册子的容量)。
其次,美国大学的评价制度似乎和中国很不同。按照书中的表述,似乎美国大学对人文学者的考评,主要(甚至完全)交给该大学附属出版社的编辑们,根本无需通过做学术的同行审议。这种行为被作者称为“外包(outsourcing)”(p26)。
我不太懂这个机制,但按照书中的原话就是:“终身教职评审推给出版社……是筛选的一种手段。(校领导)对出版社和审稿人的信任远胜于对各个系的信任。……大学出版社在决定一个学者是否有足够的水平应该被授予终身教职的过程中不失为最好的机制。”(p29)以及:
一个重要出版社的评审程序,是我们在人文学界可望企及的客观公正的绝对典范。(p30) 我大多数的同事(原注:此处略去系和大学的名字)都觉得他们不能评价彼此的著作。我们只好听从你和你出版社的同事的意见。(p27) 在相当程度上,各个系已经不再自己判断一个申请人作为学者的优劣,而是等待出版社做这个决定。(p26)对我这种学自然科学的人来说,这种行为听起来非常荒谬——哪怕在美国!有哪艘飞船要动工,或者新品种奶牛繁育前,会把具备专业能力的评审委员会撂在一边,先去询问附属出版社的编辑们怎么想?虽然不清楚美国人文学科是何种制度安排,但我猜想,总不至于与自然科学分成两套截然不同的评价体系吧(因为它们之间有很多难以划分的交叉学科)?如果不是,那么林赛的叙述可能并非客观实情。
退一步说,假设此事确凿,那么学术体制正常运转了几十年,如今在美国语境下所说的“出版社编辑”,恐怕和中国常说的、商业化出版社面向社会招聘的那种“编辑”,也不是同一个概念。册子作者不介绍培养这些学术编辑的体制,而一味用“编辑”的名头否认“外包”的可靠性,这种不顾一切的自证,是不是有点太急功近利了?
无论如何,“美国制度”的特殊性,似乎不足以让整个学术世界衰落。
二、管理层究竟怎么样?
除了这两点特殊性,林赛提出的其他问题还是很值得考虑的。他抨击的第一点是“一个管理阶层的发展”(p13),即大学商业化后涌入了大量管理人员。管理层不尊重人文学者,削减他们的经费。“人文学在大学里的角色无足轻重。”(p16)在作者眼里,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是大学中的两个阶层,“这是水火不容的两组人,谁也回避不了这件事实”(p17)。
我对这点持怀疑态度。林赛提出的问题不难解决:只要有人文学者在管理层中担任角色。哪怕有少数管理人员从事过人文教育,作者极为介意的校方对人文学者“疯疯癫癫、文笔晦涩垃圾”(p18)这样的误解,也就不复存在了。如果一定要找问题,那么最直接的原因或许并非是大学有管理层,而是不合理的管理层选拔制度。单纯否定管理层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
况且,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未尝有那么泾渭分明。就国内的大学制度而言,除了直接委派的最高领导,其余的学校管理层很多是从各院系的管理者中提拔起来的,而且在管理的同时依旧保持学术工作。这二者的关系就像小学班里的组长和同学:这两个群体真的水火不容吗?或者倘若存在隔阂,真是由于制度不合理吗?在作者下的定论里,我似乎嗅到了一点个人经历的味道。
三、自相矛盾的出版与购买数据
作者批评的第二点是,学术专著“既没有人读,也没有人买”,“印刷读物作为研究工具已经寿终正寝”。(p31)。他举了里克·安德森(Rick Anderson)的一段话:
据2002版《学术图书馆调查》的统计,由图书馆订购的印刷读物总数出现下降……而且下降幅度很大:从2000年至2001年下降了6%,在2002年又下降了大约8%。具体到学术专著的销售趋势……数据就更不容乐观。根据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年度统计,仅到2002年6月为止,由图书馆订购的大学出版社书目实际上就下降了12%以上……若具体到大学出版社所出版的精装书,该协会的数目就更令人不安了:从2001年6月至2002年6月……下降了20%。大学图书馆购买电子读物和杂志,在作者看来是可耻的行径:“许多图书管理员愿意买电子设备,而不是书。北美的一些图书馆正被一些营利性的杂志出版社敲竹杠。譬如,纽约大学图书馆的预算有25%用来从……购买杂志,而又有25%从另外两三个营利性出版社购买杂志。订书的钱越来越少了。”(p32)
由此,作者愤怒地诘问斯坦利·菲什(Stanley Fish)院长(这个人在整本书中都被火力轰炸)和其他管理层: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问问菲什和其他院长、校长以及各位高层管理人员们,这个新体系的客观性有什么可值得自豪的?书籍,起码是那些出版了的书籍,已经在这个体系中蜕变成我们用来扳着手指头计算和崇拜的象征物,而不是用来读的。我们(出版社)有销售数据,但这些数据实在糟透了,让我们的财务官员面无血色,也让那些尚能保住工作的组稿编辑们脸色煞白。(p32)我仿佛看到一个出版社总编表情扭曲,愤怒地大声咆哮:你们身为附属大学!为什么不买我们出的书?为什么要去买那些赚你们钱的杂志?!为什么?!为什么!!!!
非常自相矛盾的是,作者同时又抨击出版社的产品,说它们是一堆“既没人喜欢也没人阅读的出版物”(p8)。他谴责这些废话的出版越来越泛滥,引用威利斯·瑞杰尔(Willis Regier)的话:
在过去20年里,由加利福尼亚、哥伦比亚、麻省理工以及普林斯顿等大学出版社发行的新书增长了一倍,印第安纳大学和耶鲁大学增长了两倍,耶鲁大学增长了五倍……在198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543本新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802本。到2000年,剑桥升至2376本,牛津升至2250本……所有大学的总出版量在2000年为3100万册。(p8)且不谈作者引用这个数据有没有说服力,且不谈新书的增加是不是绝大部分由蓬勃的图书市场导致的,也不谈学术读物对上涨贡献几何。单说作者的论点——如果像他说的,“大学的各个人文学系已经完全停止了创新”(p6),膨胀的图书出版数量只是急功近利的“做假账(Cooking the Books)”(p7)行为,那么大学减少购买这些“垃圾读物”,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吗?
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我们急于著书立说,让各个图书馆都汗牛充栋,结果某些东西就损失掉了”。为了改善现状,订书的钱当然应该变少。难道大学明知出版社出的是臭鸡蛋,还偏要打开吃吃不可吗?
如果出版社在评审中真的占了这么重要的地位,那么出版垃圾增多,更应该从趋炎附势的出版社自己身上找制度问题。要把错误完全归到人文学科的衰落头上,是不公平的。(也并非毫无关系,后文会谈)
四、实体书与电子刊物
林赛是一个坚定的网络反对者、电子出版物反对者(这可不是在上世纪,而是在2004年!)。他说,“某些人甚至异想天开地以为,与书相比,电子出版这个新领域是一个进步。这些人没有意识到,电子出版只能使目前的情况变得更坏”(p87)。为什么?作者没有论证,可能不屑于说罢。
他用嘲讽的语气说,“我们不妨拭目以待,看看达恩顿(Robert Darnton)本人以顾问身份参与的美国历史学会网上发表获奖博士论文计划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网络作为文字的媒介是否合适,我们并不清楚。但对色情图像来说,网络的确很合适,因为和电子复制的所有形式一样,网络善于凸显姿势,……把人变成了领袖意志的附属。写书的人可不这样。”(p88)
这是什么话,把电子论文比作色情图像,讽刺它能凸显“姿势”?在这种暗含人身攻击的、含糊不清的论证中,我感受到的不是对客观现象的冷静分析,而是冷嘲热讽的酸味。实体书与电子书的利弊,这个论题当然值得讨论。但作者似乎并不想讨论,而是“我们最好别再说这些蠢话,而是开始敦促图书管理员和我们自己,去更好的珍视书”(p87)。这种一屁股坐稳的态度,不禁让我开始怀疑,他究竟是出于对人文学科的担忧,还是因为他们的出版社业务受损而反对?
事实情况是,在十年之后,电子刊物成为了最主流的学术读物。像《Nature》《Science》这种周刊,也已经主要以电子形式发行。如果没有网络化,一个杂志社每周发行数十本副刊是不可想象的。日新月异的学术研究,也需要网络出版的便捷性、即时更新性。对于现在的学者而言,尽管出版的实体著作仍然是评价的因素,但论文的质量和数量,已经等而越之了。
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在2004年预言电子出版的一系列必败的弊病,“会从根本上瓦解支撑着书文化的原则”(p87),已显得有些可笑。用网络化来说明人文学术的颓败,显然是自己树立的稻草人。
另一方面,作者虽然大力赞扬“书”,说它是“神圣的”、“特殊的美”,读书人和书之间存在着“一种绝对的对称、一种相遇”,“书不是而且永远不会是一堆废物”(又是与前文矛盾的一句论断)(p87),“无论如何书还是很重要”(p81),学生们需要回到书本,“拿起书来读一读吧”,书能“改变我们的灵魂”(p82)……但他却丝毫没有给出书的范围。
什么样的书属于作者所说的那种?如果说弥尔顿的作品是“书”,那么难道菲什批评弥尔顿的书就不是书了吗?当作者颂扬苏格拉底抛弃文本而重视口语时,却忽略了记录苏格拉底言论的柏拉图著作,正是最传统意义上的“书”。一边肯定“书”的价值,一边否定现今出版的书,无疑是欠妥的。
如果从人文学科的特性出发,林赛所指的,恐怕是那些所谓的经典——小说,诗歌,史著……只有那些古老的读本才称得上他口中对“书”的赞扬。这实在是有些厚古薄今。林赛所言,其实是一句听烂了的口号的复述:我们应该回归经典,应该回归文本本身……
当然,这不错。但是如何回归经典?不携带任何目的性和系统性的阅读吗?作者似乎否定一切学术训练的流程,否认规划哪些书需要阅读是学术训练的必需部分,而肯定学生刚接触的时候“迸发的火花”。在他看来,读书应该强调个人体验和特性,书不该有普遍客观的研究价值,书的内容形式“不应该听从哪怕最有本事的读者的摆弄”(p70)……
呃,当然可以这么想。阅读是私人的,阅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阅读体验是不可付诸分析的。但是这种观点听起来很像是出自学术门外汉之口。
五、大问题
作者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人文学者着眼太小。“Big Picture Guy”是贬义词(书里反复批评这点),学者只在细枝末节上做文章。“一股怯懦之风正弥漫着整个学术界。”(p51)
在过去三十年里,“意识”、“经验”以及“真理”等字眼在大多数人文学者眼里已经成为极其令人尴尬的字眼。(p66)……在过去三十年里,“此路不通”的信条在人文学界越来越盛行。(p72)在作者看来,这种自我约束是一种可悲的无能。“他们在芝加哥大学聚会,声讨自己年轻时也曾有过的愚蠢希望,以为他们的任何想法都会改变学术发展的轨迹。……他们没有羞愧地垂着头。相反,他们喋喋不休地夸耀着自己的变节。”(p65)
但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人文学科。在自然科学里,初入茅庐者也总是希望能解决那些大问题。宇宙的起源,外星人之谜,暗物质暗能量……但是学术训练的目的,就是让学生意识到,究竟自己能做什么。一口吃成胖子是不可能的,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去啃那些硬骨头。雄心壮志也要与自知之明相互搭配才好。
目前的情况似乎是,我们都朝着某个大目标前进,但走的是一小步一小步。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如何“think big”,而是“take which small step”。从这个意义上来说,“Big Picture Guy”描述的更像是一类能力比不上心气的人,而不像林赛所说,代表了学界对大问题的不齿。
的确,应该鼓励研究者去攻克那些大的、难的问题。但如果研究者清晰地意识到了自己能力的局限,选择那些力所能及的课题,未必应该被骂作“懦弱”。
林赛想指出的,似乎是某些人文学科在最近二三十年内出现了低谷。但这并不罕见。实际上,要强求某个学科持续性、高强度地产生变革,制造大的突破,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的。
高能物理逐渐沉寂,弦论也风光不再,数学的某些分支也几无研究者。即便在人文学科繁荣的“金色的往昔”,在某些二三十年的间隔中,也未必在全学科、多领域内都欣欣向荣。但是,目前人文学科真的遇到了什么理论上的阻碍,或者至少在表象上看起来受到阻碍了吗?至少在本书里,并没有给出论证。
六、主观攻击
本书作者绝对和斯坦利·菲什(Stanley Fish)有梁子。书里几乎隔几页就闪现菲什大名,以各种憋屈的方式出场:“菲什之流”、“菲什声称”、“大家不妨去读读菲什的大作”、“菲什却宣称”、“上帝不喜欢盲目的美德,但菲什院长喜欢盲目的思智”……菲什的公开言论、作品价值、私人信件,都被批判了个底朝天,真可谓被360全方位无死角吊打。
我稍微查了查斯坦利·菲什(Stanley Fish)这个人。他是杜克大学法学专业的一位教授,在《纽约时报》上开设专栏评论美国政治。此人与作者并非一个单位,研究领域也不一样(作者是历史学博士),能得到如此“热情关注”,恐怕二人早就有什么新仇旧恨。不知道菲什在报上发表了什么高见,引得林赛如此大动肝火,不惜拉着整个人文学科下水,也要把菲什供成“我们挚爱的东西正面临灭顶之灾”(p7)的主犯?背后应该是个蛮有意思的八卦。
在书里,林赛一直试图制造两种对立:一类人资历较老,维护官僚主义,对问题视而不见,否定创新,阻碍后进,滔滔不绝地发表废话;另一类人是新锐,具有智慧,敢于自我批判,懂得珍视经验,惜墨如金,著述不多。看看菲什和林赛的履历,很容易判断出哪个是喋喋不休的前者(即便著作等身也肯定是“做假账”!),哪个是拥有沉默美德的后者(作品少才光荣!)。
特别有意思的是,书中专门指出了60年代学者对70年代后辈的打压。
1970年代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理念世界,它使60年代的所有经验都黯然失色。(p53) 上一代人不愿意提供这种指导,上一代人不愿意为下一代人助一臂之力。(p53) 老一辈人要求年轻人做到的,是尼采所谓的“盲目的勤奋”。(p54) 代沟问题非同小可。我们必须承认学术界不同代人之间的冲突,以及老一辈人如何以从客观讲很不公平的方式试图控制年轻一辈,譬如把一些他们本人没有达到也无法达到的发表著作标准强加给年轻的同事们。(p54) 我们的时代和过去许多时代一样,上演着一个持续、残忍、但又隐秘的老年人对年轻人的战争。(p55)我查了查菲什的履历: 1962年以博士论文《约翰·斯克尔顿的诗》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 出版有《为罪恶所震惊:<失乐园>中的读者》(1967) 。——都是60年代!
我又看了看林赛的履历:"Lindsay Waters earned his PhD in 1976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Ha, they all make sense! 果不其然,而且还是老梁子啊。
七、有效建议
令我感到遗憾的是,作者空费一个如此美妙的题目,却没有给出与之匹配的雄辩论证。内容安排是紊乱的,实例缺乏,情感激昂;就连旁征博引,引来的也都是冷僻的比喻,纯有炫耀知识之用,而无论证效果。
纵览下来,人文学术圈不过还是——正如各行各业一样——几样老毛病,没有多少与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目前制度直接相关的根本性问题。说什么(人文)学术的衰落,不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诸神黄昏,而更像是夸大其词以鸣己悲,让我强烈想起了微信公众号里看过的北大老师骂学校领导的文章。
当然,说林赛的书完全是报私仇、讲偏见,也不太公平。至少它指出了学术界存在着权威对后进的打压(是不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什么爱因斯坦和牛顿的故事之类),以及盲目追求指标数据——这倒是不仅在人文学界,也在其他学术领域适用。在书中指出的是,人文学术界正大量出版没什么人读的书,用来取悦上级。“我们只考虑出版的数量,哪怕是没有人读的出版物。”(p19)
为了鉴定“有人读”,现在的评价体系里基本都有“引用量(影响因子)”这个指标。但很显然,IF不是最终解决手段。发表10篇文章被引用45次的笑话已经屡见不鲜了。就算是真金白银的顶刊文章,也未必不能灌水。只要考评是以数据为指标的,就总有以数据为目标的工作方式。
这些问题,外人听者摇头,行内人听者叹气。也许是因为林赛的书第一次把它们写了出来,这本书才得到如此多肯定。但平心而论,就这本书而言,讲得真不怎么样。
林赛给出了一些建议:我们必须勇于面对新事物,发展新理论;我们必须重新拥抱艺术,让互动关系促使那种能使我们灵魂升华的瞬间体验;我们需要在大学里重新为人文学定位……(p95-96)这些没有错,但没有一条可行。不客气地说,这些建议都是正确的废话。
我倒是知道个办法。某次与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玉良院士讨论评审制度对研究者的负面影响,杨院士持有一种很果断的看法:唯一的规避方案就是干脆不设评审。拿出足够的钱,立一大堆tenure(终身职位),十年不出成果也不必担心被辞退,每个人都有充足的钱自由发挥。
我相当程度上同意这种看法。想要让学术不被发表影响,只需让学术生涯完全与发表无关。但即便像中国现行体制内的终身教职,只要有差异,仍然有竞争,还要继续提高待遇。这种思路其实有点像明代以薪养廉,先让大家都饱和,从而不需要再在这些事上动歪心思。
这样动用政府力量喂养学术,完全实现了林赛所说的,不让大学商业化干扰学术。美元不是最终参照物,天地不再狭窄。只是,搞人文学术的教授们,能不能让政府从医疗、教育、军事……的经费里抽出大一笔闲钱,养一大批闲人呢?
这恐怕就要看人文学者们的嘴皮本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