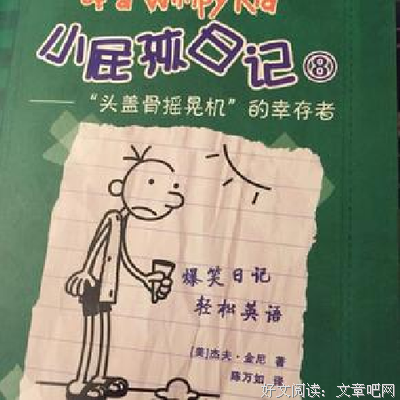《纳人说》经典观后感1000字
《纳人说》是一部由汪哲 / 徐大拿 Dana Xu执导,木帕杜基 Mokpel Dhundrup / 杜基次尔 Dhundrup Tsring / 五六主演的一部纪录片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纳人说》观后感(一):“不安静”的纪录片
《纳人说》——非常直白的片名,其实在一开始就已经剧透完毕。
既不是你说,也不是我说,更不是他说,里面只有摩梭人在说话,说他们自己。
片子四分之三都是各个主角在对着镜头吧啦吧啦,再加上毫不吝啬的音乐,以及并不慢的节奏,我怎么也无法将它和刻板印象中慢慢悠悠,安安静静的纪录片画等号。
但是不安静的纪录片不是我对它的负面评价。
不安静的纪录片≠不需要静下心看的纪录片≠糟糕的纪录片
里面印象最深的是“爱”。
“走婚”是什么?
这个摩梭人最出名的关键词,它的由来,它的目的,它与当代婚姻的不同……这些东西在网络上稍微找找就有详细的资料。
但是没有资料告诉过我它是包含爱的。
不过从前我似乎也并不在意走婚和什么爱不爱的有没有关系,只是用一种审视和打趣的目光看待这一习俗。这和我对当代婚姻的态度截然不同。
对于当代婚姻,我们常常会思考很多制度以外的问题。
是否因为爱在一起?
是否是因为觉得对方可以搭伙过日子而在一起?
是否出于图财?
是否能携手走完一生?……
关于制度上的质疑咋一看似乎没有,就好像我们已经非常肯定它的合理性,但并不尽然。如果我们非常坚定现在婚姻制度的现状,那么不可能每年的婚姻法依旧是热门论题。
在和走婚做对比的时候,我们放弃了“出轨”“骗婚”等等一系列不利因素,只是觉得从一夫多妻制走过来的当代婚姻必然是优于从久远的过去承袭至今的民族习俗。于是其他都不重要了。
比如爱与忠贞,比如责任和尊重。
《纳人说》信息量不大,全程是摩梭人关于自己的自述,既没有某个习俗的由来,也没有展开讨论摩梭族在这些年遭受的社会毒打。
不过如果我要看民族介绍与发展史,要了解泸沽湖有多大,我大概不会点开它。
《纳人说》观后感(二):纳税的纳人说
有人问「纳人说」的摄影师马天亮:听说你拍了个纳税人的片子?(笑喷)
「纳税人」是个太容易想到的词。没有人不纳税,哪怕买个饼子花5毛,其中也有几分甚至几毛是税钱。「纳人说」是关于摩梭人的,他们自称“纳人”。如果说纳人和纳税人有什么关联的话,纳人也是纳税人。
「纳人说」片长47分钟,有点像一堂网课:近景、一个一个讲述者、注视着我、对我讲话、唱歌,大部分是摩梭话,画面上有中英文字幕。空镜、全景等等其他的加起来好像不到4分钟。我开始觉得节奏有点慢,后来却觉得时间有点快。在和讲述者对视、聆听、观察之际,片子一下就演完了,让人回不过神,想往下看,可是没有了。
最初看到预告片吓了一跳: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一张张脸!连脸上的雀斑和皱纹都有诗一样的韵律,好看得不真实。我曾设想,实际本人的脸可能没这么好看。后来在《纳人说》首映式看到两位纳人嘉宾,一位小哥哥和一位小姐姐,都是一脸的胶原蛋白,也挺好看,但赶不上片子里我注视过的那些脸。小哥哥小姐姐的脸我不会看呆,而片中的每张脸,都能把我把我目光定住。那些脸哪儿来的这么大魔力?
看第二遍时,我开始怀疑配乐是幕后黑手。配乐舒缓悦耳,滴滴入心,可能暗地里美化着讲述者的脸。我关掉声音再看,似乎真的有点不同,那些脸好像变瘦了(自我暗示的结果)…… 但没多久,那种节奏慢、时间快、把人定住的感受再度弥漫了。
片中的讲述者不是一直絮叨,有大段时间是无声地看着镜头,有的自在、有的严肃、要的要笑场。但无论是什么样的状态,他们的NVC(不用说话而表达出来的“语言”)都不可阻挡地飘舞出来。那些眼神、表情、手势一时不停地在表达,滔滔不绝。盯着寂静画面里的纳人,他们慢悠悠涌来的NVC把我的目光吸在了他们的脸上。他们的NVC很容易让人看进去,很容引起共鸣,所以很容易让人一直想看下去。这让我注意到,当无需顾忌的、放松地注视他人的时候,这种“看进去”和“共鸣”如此的轻而易举。也许,无言的注视特别方便我们投射自己的意识,把我的理解、愿望、好奇随心所欲地投射到讲述者的眼神和表情里。可能是因为这样,每位讲述者的影像都承载着我的意念,很快我就和讲述者产生了共鸣,我想其实那里面更多是自己和自己的共鸣。
无言的对视让人萌生爱意,也许是因为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我们一直想要肯定的自己,和我们共鸣共感的是我们投射上去的爱欲、评判、悲悯。我对摩梭人的概念是神秘、浪漫、原生态,都很抽象而模糊。注视这些讲述者,神秘、浪漫、原生态的概念清晰和丰满起来,我似乎还为此频频点头,觉得这纪录片充满了真实。我们眼中的真实常常是这样,我们投射了什么,就相信什么。如果抬杠的话,片中的脸比现实更好看、有配乐的视相比现实更诗意,讲述者极力辩解“走婚”的说法… 这些算不算与真实的冲突?
片中有两位讲述者是达巴,达巴是摩梭人信仰的达巴教的神职人员。我可能因为对苯教略有接触,就想当然地把纳人的”达巴“与苯教的“敦巴”(觉者)进行连接,希望是同一个词。在听到过的一些研究中,有些观点认为摩梭人与古代象雄人有关联。象雄是1千多年被吐蕃灭掉的一个漫长的部族时期,象雄人的信仰苯教。苯教观点认为,绝大多数人误解了真实,比如看到水中的月亮,会认为看到了真实的水面和月影。实际上水面和月影的相一直地改变,即生即灭,绝不重样,没有任何一个刹那的内容能原样地延续到其他刹那里。所以内容上的“真实”本质上并不存在,因为定义时的内容到了表达时已变得不同。事物没有被能真实定义的内容,只有能被概括描述的状态。按照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把对“真实”的期待,从内容转向状态。
比如,好几位讲述者都说“走婚”不是纳人原本就有,而是外人为赚钱搞起来的,这和一些研究资料里讲的不同。按照上面“真实”的观点,其实我们不必费心考量这个说法的内容是否“真实”,这当然不是暗示讲述者在说谎,而是因为这就是讲述者在那个当下的选择,就是他当下的状态,是我们完全可以确认的“真实”。再如片中的脸比现实的脸好看,配乐使那些脸更有诗意,这些当然会和现实有出入,可这不就是我们选择观看影片的原因之一吗?我们期待从这些艺术家的创作里获得享受的体验,不仅是因为我们缺少亲眼去看亲耳去听的时空机会,更因为我们知道,艺术家具备高于生活的状态,能呈现给我们即使亲眼去看亲耳去听也不易得到的“真实”。汪哲导演说,别人的声音不能代表我们,我们更希望自己为自己发声。听到她这么讲,我也确实看到和听到了她所记录下来的真实:真的纳人,真的自己讲述,讲述他们真想表达的东西。
沉浸在纳人讲述者的对视中,尤其无声的片段,我感觉一些幼稚的投射清晰起来,尤其是自己那些以审判者、救世主自居的起心动念,如此的鲜明。其实,纳人跟我一样,也是纳税人。
《纳人说》观后感(三):无处安放的族裔
上初二的一天课间,有个男生忽然跑过来对我说:“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吃猪肉了!因为猪是你们回族人的祖先!”说完他笑嘻嘻地走了,留下稍显错愕的我。
这件事至今已经过去了大概三十年,那个男生是谁都已经忘记了,只是这句话我却一直清晰地记得。它显然是一种伤害。现在的我可以把它归结为少年的无知,或是实在无聊的日子中一次随意的消遣。但无论如何,它是一种伤害,对一个人所属族裔的伤害。
10月17日下午,我去到MOMA的百老汇电影中心参加纪录片《纳人说》的放映会。“纳”即是摩梭人的自称,这是一部摩梭人的集体告白。如果我们真的想了解一个族群的习俗和文化,最好的方式应该就是这部片子所呈现的——直接的凝视与对望,以及充满敬意的聆听。
很多人对少数族裔都充满了天然的好奇,但往往都是一种猎奇或游人的心态。一提起摩梭人,便讪笑着说:“哎呀,听说他们走婚!”这种口吻与总是问回族人为什么不吃猪肉一样,其实并不是真的想了解或关心,而只是轻佻的语言调戏。
值得欣慰的是,《纳人说》这部片子最大的特点就是让摩梭人直视镜头,自己发声。在影片放映后的文化沙龙中,来自人类学专家的评价,以及年轻的摩梭族人的自我表达,也都呈现出了一种理性而宽容的认知态度。面对误解与伤害,报之的都是真诚解答与诉说。
而其中最打动我的,是在提及摩梭人和少数族裔如何应对社会发展变化时,吴乔老师说的那句话:“变与不变由谁决定?我们应该把决定权交给文化的承载者,也就是那个民族自己。”这一句话,几乎是一瞬间便深入我心。甚至可以称之为一束心灵之光,让人温暖与释然。它豁然帮我解开了一直以来纠结于里的那个关于族裔的心结。
在我母亲的家族里,她是同辈中唯一嫁给汉族人的回族女子。四十七年前,我的父母结婚时就已商定,未来孩子的民族都随我的母亲,包括生活习惯。这是个听上去有点浪漫的爱情故事。所以在我的童年里,有机会参与到传统回族家庭的很多仪式。
比如,每一年姥姥家里都要为去世的姥爷做周年(回族人把去世叫“亡(wú)上”,也有人说是“无常”)。我会趴在窗前偷偷看阿訇如何给待宰的羊念经;看舅妈如何炸出一锅一锅的油香;跟着所有亲人一起跪在地上,一边听着阿訇诵读《古兰经》,一边随着老人的提醒“接堵哇”。这些充满宗教仪式感又满含家族温情的经历,常常让我觉得那便是一种族裔的特有归属感。
可随着亲人的故去,个人成长与时代环境的不断变迁,在我28岁之前,作为一个回族人的特征就只剩下了不吃猪肉。而就是这么一个饮食习惯,我坚持了多久,也就面临了多久的现实无奈。
现在想想,我从初中开始住校,每天去食堂吃饭都未尝不是一种考验。因为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是汉族,所以绝大多数的菜也都是有猪肉的。记忆中我最常吃的就是烧茄子,因为只有它是素菜,而一旦由于下课晚了买不到,那一餐便或许要挨饿。
班上有一个和我一样情形的男生,早早地就与猪肉和解,每天开心地和同学们一起聚餐。而那时的我却一直在坚持,宁愿饿着也坚决不吃猪肉。也许更是一种虚荣心吧,因为觉得自己是回族,因为不吃猪肉,而感到多少有些与众不同。
大学的情形好了很多,有一个小小的清真食堂。但那里已是新疆学生的天下,作为一个一看就不是人家同类的我,常常需要穿过无数质疑的眼神丛林,把脊背挺直地坐在角落,默默吃下一份西红柿炒蛋。坚持了一年,我就再也没有去过。
好在食堂的菜样越来越丰富,口袋里也有余钱可以去校门外的饭馆。我带着最好的朋友一起开发出了“牛肉做的锅包肉”这种估计只有我才会点的菜品。只是毕业后,对每一次同学聚会都要因为照顾我而只能找清真餐馆,而不免心存愧疚。
终于有一天,还是和我那个最好的朋友一起去望京吃烤肉。望着烤盘上滋滋作响的五花肉,本来只是看客的我,忽然脱口而出地说:“这看起来很好吃啊!”于是在朋友的怂恿下,吃下了平生第一口猪肉。彼时她正和我同住,开心地说:“哎呀,终于可以回家炖排骨吃了!”
可以说,我是带着一种羡慕的心情,在观看《纳人说》的。听摩梭人自己讲述对于祖母屋、家族、故土的依恋时,我能够感受到那种族裔的归属所带来的内心安定。来自家族的牢固维系,让每一个行走在外的年轻人,都会被族裔的深情所眷顾。
文化沙龙里的两个年轻的摩梭族人,会很坦然地说自己的父母只有一方是摩梭族,但因为他们都是在摩梭大家族里长大,所以他们可以自豪地说自己就是摩梭族。这是被族群认可的,被家族认可的,同时便拥有了强烈的自我身份的认同。
现在想起来,可能只有姥姥家才是我的族裔被认可的地方。而随着姥姥的去世,不止是我,就连我的母亲也没有了族裔的现实依靠。
回族作为一个长期散居在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除了宁夏、甘肃等西部有连片聚居区外,更多的城市中都很少再有类似北京的牛街和常营那样的回民聚居街道,往往只有一个清真寺可去。在我的记忆中,只知道姥姥姥爷的老家是河北唐山,他们或许是最后一波闯关东的回族人,而我们的族裔源地在哪里呢?其实我从来都不知道。
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一天在姥姥家里,忽然有一个头戴白帽身穿白布的人走进院子来,一见姥姥便跪了下来。姥姥迎上去,口里不断叫着:“主喂,主喂!”这便是关里的老家来人报丧了。而姥姥嘴里的“主”便是真主安拉,她一辈子都是这样叫,就和我们说“天哪”,“Oh,my god”是一样的。
那时候,经常会听到姥姥念叨着“关里家”(关里的老家),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重要的亲人在了。她有一个好听的姓:云。她说老家一个回民村子的人都是这一个姓。也教会我记住了很多回族的习俗,或者一些特别的语言禁忌。比如我的大姨属猪,但只能说属亥。而原姓朱的人,则改姓黑。那么,为什么不吃猪肉呢,因为我们是穆斯林,《古兰经》里面说猪不洁,所以我们不吃。
这些幼年的记忆如此清晰,就仿佛姥姥正坐在对面轻轻念叨着。而那些话像经文一样,使人神志清明,意念平和。但成年的我也分明知道,世事变迁,我们已不能和姥姥一样,甫一出生便成为一个正宗的穆斯林,终生信奉真主,亡时入土为安。我们只有选择通往自己的道路。
作为一个汉族和回族通婚的后代,我的民族身份并不是一种自我的选择,而是在未出生之时便为父母所定。我遇到过无数像我一样的“回族人”,都选择了与汉族人无异的生活,包括都吃了猪肉。
如果说我偶尔还是会为此有所顾虑的话,就如我前面所提到的,在听了吴乔老师的话以后,这个顾虑已被完全打消。吃与不吃,请把选择权交给我们自己。
而关于无处安放的族裔,放在哪里,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