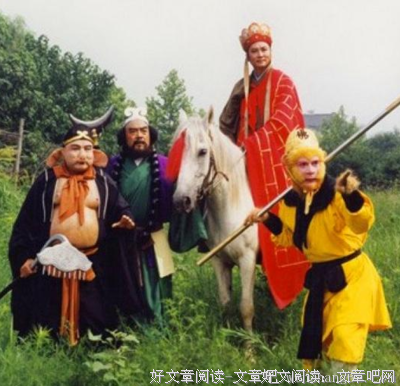Miguel Street经典读后感有感
《Miguel Street》是一本由V.S. Naipaul著作,Vintage出版的Paperback图书,本书定价:121.00元,页数:22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Miguel Street》精选点评:
●2019.4.28 这应该是这个月读的唯一一本书!比我想象中的好读太多了!一页可能有两三个生词。于是读得很流畅。米格尔街上的人们一个个都很生动。很喜欢中间那篇B.Wordsworth,虽然他不是主要人物
●please me good good.
●很適合當睡前故事 大千世界無奇不有
●这种写法真够俗套的,老弄一些假装治愈心灵的“鸡汤小文”,每个故事都够没劲的,确实像贫民窟里的人干的。
●大赞。
●虽然有点俗套但是啊真是太好看啦
●想起王老师说 我们也有后殖民经验 所以还蛮有共鸣的 喜欢Hat
●很好读 8.17-8.19
●奈保尔最擅长的就是一两句话描写出复杂的情感和人性
●簡潔,俏皮,勁道十足,好像一只蹦跳的橡皮球。
《Miguel Street》读后感(一):奈保尔的苦味幽默
读最后两章时,感觉“我”突然长大,这杯生活的咖啡也变了味。之前还觉得可爱的人,现在看到的只有他们的缺点。时间没有改变他们,却改变了“我”――“我”长大了。“我”是小孩的时候,许多人都是有趣的,尽管他们满身缺点。但“我”长大后,“我”就是以大人的视角看待周围的人,“我”似乎渐渐变成了“母亲”。“母亲”想让“我”离开米格尔街,而当“我”最后的不舍也遭受冷落,“我”也想逃离。这种突然长大得感觉真的不好受,上一秒还是喜欢的人,下一秒就不知为何讨厌起他们来。当成长不可避免,又如何不改变过去的模样?
“我”所怀念的情感是寄托在过去的身上,如果过去被改变,情感也会渐渐消失。但客观存在的过去只有一个,而每个人主观印象里的过去却各不相同。有时候,过去在“我”眼里的样子未必客观,它或许还有“我”的想象。哈特入狱后,部分的“我”就死了。在“我”眼里,米格尔街怎么可以没有哈特?即使在别人的故事里,哈特也很有存在感。而当我有特的回去告别米格尔街,哈特冷漠的回应让“我”觉得是米格尔街要离开“我”。而“我”也瞬间意识到自己只是米格尔街上一个可有可无的人,“我”从观看了不知多少次离别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所谓成长,似乎也是这种身份的转变。
幽默只是调味品,咖啡还是苦的。
《Miguel Street》读后感(二):诗人,闯入生活的一场梦
奈保尔一共写了16个人,而这其中与米格尔街气息最不同的就是诗人。诗人自诩为诗人,而他到底是不是呢?说他是个假诗人,似乎也可以,因为能读到的也只有那么一句“the past is deep”,他真正的诗歌素养怎样真的存疑。但又觉得他是真诗人,因为他已经把生活过成了诗,即使这首诗有点悲。他是乞丐诗人,却不是诗人乞丐。一首诗卖4分钱,也卖不出去。若他肯学学前面几个乞讨者,得到4分钱根本不是问题。可是诗人哪能不爱自己的尊严?既然卖不出去,那不卖也罢。
诗人说“我”也是诗人,大概因为还是小孩的“我”有一颗与他一样简单的心,但诗人的心甚至可以说比“我”更单纯。当诗人把秘密告诉“我”,我失望了。因为诗人的秘密是写诗,哪个诗人不写诗呢?,这个秘密可不像“我”经常听的那些八卦那么吸引人。
当“我”觉得生活逐渐有了诗意时,诗人却在逐渐衰老。如此突然,往往预示有不好的事要发生。果然,诗人告诉“我”那个男诗人和女诗人的浪漫故事是他编的,而那个秘密也是假的。诗人刚讲完,“我”便跑出他家,像他在说这个“有趣的故事”之前说的那样“when I have finished this story, I want you to promise that you will go away and never come back to see me”。“我”一年后才又回到阿尔贝托街,可是却发现诗人的房屋已被推倒,芒果树也被砍了,好像诗人不曾存在过。
“我”住在米格尔街,诗人住在阿尔贝托街。诗人走到米格尔街遇到“我”,“我”与诗人在阿尔贝托街分别。闯入生活的梦主动而来,又主动离去。诗人说的那个有趣的故事或许是真的,或许是假的。诗人也许觉得自己把生活过成了诗,而生活却鲜有回馈,他在生活面前始终是个逐渐衰老的弱者。所以他告诉“我”他在撒谎,无非就是不想让“我”也过跟他一样的生活。
梦离去后,“我”又重回米格尔街,“我”的生活与从前一样,仿佛诗人不曾存在过。“我”长大后,离开米格尔街,邻居的生活与从前一样,仿佛“我”不曾存在。所以,好像谁都不曾走进他人的生活,至少“我”是这样觉得,在要离开米格尔街的那一刻。但今后的生活,谁知道又会怎样?
《Miguel Street》读后感(三):米格尔街的人物塑造:仪式感与动机滑坡
关于米格尔街 我想到的关键词是“仪式感”
我原计划要写的关键词是“人格可视化” 一个人的动作与物品就是这个人本身 我高中时接受一些关于“可视化”的写作训练 我做的很多作业是通过动作与物品的细节(惯用动作/口头禅/牛仔裤品牌/烟酒品牌等)来进行人物塑造 然后我读了米格尔街 立刻感到它是一部“可视化”的典范
但紧接着 我不得不开始思考 这“可视化”的方法究竟将我们引向何处
米格尔街是一部优雅的书 充满了优雅的韵律 这种韵律就是生活本身的韵律 和社会阶层或经济水平无关 即使在米格尔街这样的地方 生活的交响乐依然准时上演
它与同样是写作课教科书的哈利波特不同 哈利波特是成长小说 它的人物踏上旅途 主要有两个动机 第一个是显性动机 即为亲复仇/打击邪恶 第二个是隐形动机 即自我成长 最终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若是悲剧 则人物在实现愿望的过程中失败或死去 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伊利亚特的阿喀琉斯、变形记的伊卡洛斯… 这是一种古典的人物塑造模式
但是现代文学越来越多地关注另外一种模式 米格尔街的模式 若是拿我国的文学来说 就是少年闰土、骆驼祥子的模式 即“人物的欲望改变 达到更高或更低的境界”
即使像B.Wordsworth这样的人物 他们表面上在坚持一个行为的同时 内心已经发生了改变 他们一方面还保留着原本的欲望 另一方面很清楚愿望不可实现 所以不以目的为动机 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呢 我把它称之为“仪式感”
“仪式感”就是Hat与Bogart每天早晨的问候 是我与Mr. Popo关于“你在做什么”的问答 是不想开蓝色垃圾车的青年每天梳洗整洁、去培训班上课…
这种改变的发生比闰土的写法更隐晦 少年闰土与中年闰土之间的差异是肉眼可见的 但是米格尔街上的希望与失望掩盖在“仪式感”的下面 就像从内部腐烂的水果
利用仪式感的不变与改变 米格尔街制造出“动机滑坡”的效果 从云层间以很快的速度坠机 它开始的地方可能比你自己的生活更高 但坠落至看不到底的地方 一切都在转瞬之间发生
一个很好的对比是Raymond carver 他同样是短篇 他的人物从一开始就处于较低的海拔 读Carver需要一个潜在的前提 你必须知道 在故事发生以前 生活曾经是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的 你看到的是结尾的俯冲
对于我的一些朋友提出过的疑问:我阅读时是否带入自己?是的 但读者和人物之间能够共享的不只是坠落的情绪 也是一种品味、一种对美的感知和认同、一种对物品的迷恋、一种对习惯的坚持 是“烟火师-纵火犯”的激情 是像烟火一样破碎的伟大与圆满
米格尔街是一部悲剧 但又或许不是 作为一个读者 我看到的究竟是什么还不好说 我感到米格尔街的失败正是米格尔街的成功 因为米格尔街是一种理想 是一种最好的人生和一种最好的结局
《Miguel Street》读后感(四):对艺术的最高评价是自然
反复阅读的一本书,中文版太喜欢,又把英文版找来读,更喜欢了。
一、重复
可能是奈保尔的第一擅长。
1.字句
充斥着语病、错别字的纯口语对话:you quick quick(你快快) it easy, easy(这容易)it light light(火柴木轻轻)。
当人们长期说一件事,这件事就变成了idiom。pay the loader是没钱,material是捡来的杂货。
我有次和车间副组长(也就是峰哥)聊天,我想问峰哥下午几点开始干活,我一时间怎么都想不出自然的问法。「我们几点开始工作?」不对,太正式;「几点上班?」不符合我们行业;「几点劳动?」简直是荒谬;「几点干活?」有点自恃(毕竟我只是学徒)。到点了,峰哥脱口而出:「起来。准备搞事了。」
这种纯熟自如的语言才能构成自然而然的对话,最后才能汇聚成一气呵成的段落。比如p128.
2.对话
10 Ha, boy! That's the question. I making the thing without a name.(Popo)
45 I really like the work. (Elias)
58 when you're a poet you can cry for everything
对话的重复是艺术电影常用的一个手法,随着情景、语气的变化,同样的台词可能代表多重意义。进一步,艺术电影里的人物会说反话,台面上、当着人、写在信上的话可能与真实心意完全相反。毫不相关场景里的台词可以预示未来,这种技巧在「戏中戏」里常见,比如《推销员》。
奈保尔就是这样。他在同一句台词里加了深浅、正反、转折,就像古代汉语里的「而」一样。
opo 的「无名物」是他诗意生活和理想的象征,他自知丢掉了,无法再改变命运,于是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禁止别人再提起这个。
如果 Elias 真是 really like the work,他会在得知「我」要上剑桥时,第一时间跑来我家门口骂吗?会直接侮辱「我」妈妈吗?
Wordsworth 刚见面时说诗人会为任何东西哭,最后他死了,把我赶走,我一边奔跑回家,一边哭泣,「就像个诗人」。这不就是预示吗?如果牵强一些解读,Wordsworth 是一对诗人夫妇,他们的孩子死了,所以成了悲剧。那如果他们的孩子活着会是什么?会是一个小诗人。"but this poet was never born"(p61) 那最后谁成了小诗人?
「我」。
(关于 Wordsworth 这一篇毕飞宇有分析,可见:https://book.douban.com/review/7922615/)
3、动作
开头就是 Hat 的日常重复动作:问候 Bogart。
opo永远在造,George在打妻儿,Man-man 在写字,Hoyt 忽悠人,Laura 在生,巴库永远在修车。
这都是经年累月、持续重复的动作,持续性塑造个性。故事都是短篇,小几千字,怎么塑造个性?抓重点,或者说抓怪异的地方。只有他做别人不做,或者别人不做,他做,而且他持续做。
二、童年视角
小说的视角有三大捷径:小孩、残障和怪兽。整个《米格尔街》就是采用「我」的小孩视角。奈保尔非常善于把这个视角的作用挖干掏尽。
11 喂奶喂早了,奶牛不喜欢,and the cows didn't like it. ——奶牛可以有情感
51 既然特立尼达有那么多宗教和普通人都说自己见到了上帝,那我想 Man-man 在我们这片看到他也很正常了。——小孩不会想这些都是骗人的
103 (英国人在这儿修了防御堡垒)居然还有人把我们这破地方看得这么重要——小孩比成年人低微、弱小,这也符合特立尼达的地位
比如p44,Elias得知我上剑桥后对我吼:你妈妈替你疏通了什么关系?我想打他但被饿拦住了。Eddoes说:he just sad and jealous. He don't mean anything.
这很自然,就是小孩子会有的反应。但如果作者这么写:I was going for him but I stopped. I thought of him just sad sad and jealous. He don't mean anything.
一下子成了最惹人厌的「小大人」视角(苏联文学常用,集大成者的人物类型是检举家人反革命的少先队员)。
小孩视角是反闪回的(福克纳常用手法)。文学里的闪回我理解是说现在的事,然后马上穿插一句事后的追溯。比如:毛军第一次见王奇是夏天。30年后的毛军再想到这件事时,会马上后悔那天他穿了白衬衫。回忆类文章也爱用这种写法,甚至来回闪回,这取决于作者有没有意识到和意识到了想不想控制。比如金宇澄的《繁花》没有,但《回望》大段大段用。我个人不喜欢用,因为用得不好会落俗、故作聪明。
我觉得奈保尔没有意识到,因为小说后半部分开始出现少许这类段落。在小说前半部分,他本能性地控制住了。我归因于写疲了,累了。
三、诗意
诗意和童年视角是一回事。诗人都是儿童,儿童的敏感像诗人。
诗意是什么?诗意是无用。
无用是经济上不实用。造没人要的东西,拆修完好的汽车,写没人看的诗……都是无用。
无用还包括答非所问。这条街上一半人都答非所问,因为他们凭感性而非逻辑行事。人们习惯了(教化的)逻辑,常常忘了我们其实是感性的动物。
60 警察问:你在干什么?
Wordsworth 说:我问自己这个问题已经40年了。
他回答了这个问题吗?没有。但他也回答了: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诗意也是友爱。米格尔街上的人互相取笑、打架、轻视,但他们对弱者和遭受不幸的人怀抱友善。他们取笑胖子,但从不取笑真正胖的人。
111 当 Nathaniel 嘲笑发胖的 Ricaud 女士时,大家觉得:这很没品。因为 Ricaud 女士已经胖到应该被同情的地步,而绝不能再被嘲笑了。(如果这话从一个大人,比如毛姆,口里说出来恐怕会有反讽之意)
诗意是简洁。技巧上说,诗歌因字斟句酌的简洁而直击人心,如果能诗意地介绍人物、故事也一定是短促直接。怎么用三言两语塑造一个人的独特之处?比如介绍怪人 Man-man,除了他本身性格乖戾,和他亲近的人要么没有,要有肯定也怪异。他奇怪到,以至于「我」看到什么怪人,就会想:是他给 Man-man 投票的吗?
这方面汤浅政明非常厉害。
是山吗?是海吗?对不起我离开了你,我还是最爱乒乓啊;
唉,打前锋就要输了,不过也许海王乒乓球社的衰落正是以招进了我这种水平的社员为标志吧;
我辛辛苦苦进了国家队,只因犯了一丁点错误就来到这个岛国,难道我苦练了这么多年就是要被你侮辱吗?(《乒乓》)
免费散发这等妖气的人物,占卜没有不准的理;
要是说坠落的方法的话,我非常清楚,下定决心去飞就好了;
不碍于根本毫无用处的情面……可以把别人的不幸当下饭小菜并吃三大碗饭的人(《四叠半神话大系》)
诗意是自得自适。Popo 拿着一杯朗姆酒大摇大摆走街上,Hat会说:谁喝不起朗姆酒呢?我就喝得起,但我不这么走着喝。后来 Popo 老婆走了,小孩问 Popo 你的朗姆酒呢?Hat 抬手就要打小孩。
每个人做着无用的事,过着贫穷的生活,有人在意,有人离开,但没关系,生活照常过。
最后,诗意是不谈柴米油盐。米格尔街方方面面都讲到了,偏偏没提人们是怎么挣钱养活自己。Hat 从早上十点读报到晚上六点,还养着两个私生子;女人几乎没人出去打工,男人如果不是有公差,基本也在赔钱。「我」每天吃的从哪里来?不知道,也没关系,因为我是个小孩嘛。小孩会关心白菜多少钱一斤,砧板是2块钱还是200块钱吗?不关心,他们只知道乐事薯片9.8一盒,妙脆角3.5,米奇水彩笔25。
115
「米格尔街的一大奇迹就是没人挨饿。如果你坐在桌旁,拿纸笔一算,你会发现这不可能。但我住在这条街上,我可以保证没人挨饿。也许有人偶尔饿肚子吧,但也从没听说过。」
四、结构
这是这本书最独特出彩的地方。人物独幕出场,环境次第展开,你中有我我有你。这种结构我只读过《小城畸人》,而且《米》人物更紧密,背景更外向。
开头是 Hat 呼喊 Bogart,但 Bogart 很快就走了,所以第一篇的重点其实在带出 Hat,最后也是以 Hat 坐牢,回来街上已经变了,我的一部分也消逝了作结。同样,再见到出狱后的 Hat,我发现米格尔街竟然如此简陋破败,人们无趣矮小,于是童年视角结束了,我也该走了。
除了人物的勾连,这种结构的另一个好处是读者逐渐熟悉,就像认识老朋友。
125 清道夫 Eddoes 说遇到麻烦了,Hat 回应:你不会想告诉我你的那些「材料」都是偷的吧?
读到这句我摔书大笑,这简直是一句官方吐槽!第二篇 Popo 就是偷,就连装修房子的刷子和颜料都是他偷来的。
第三章是 George,一个混蛋,读者越是讨厌这个父亲,就越是喜欢 Elias。George 这一篇的结尾,他死了,"Elias turned up for the funeral. " (这一句也非常四两拨千斤,想象一下换成「Elias没有参加葬礼」?)
接着就写 Elias。写 Elias 不直接续上刚才的说,作者先聊聊 Eddoes和清道夫们。清道夫何许人也?扫大街、捡破烂的。在中国常常被视作最低贱的行业。但在米格尔街,他们地位崇高,动辄罢工,米格尔街没有技术方面的「专家」,清道夫们就是专家。扫帚不是你想拿就能拿。「我」开始崇拜 Eddoes 并且极度渴望做一个清道夫,并且一度觉得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像他那么高大专业。
话锋一转,但是Elias不是这样,"But Elias was not that sort of boy. " 接着就自然说起「隔壁家小孩」Elias 的故事。顺提,一般写隔壁家小孩(多见新闻报道或者公众号回忆类文章)都容易写成「王子复仇记」,这非常狭隘和蛮夷,基督山伯爵那是血海深仇,你可能只是绩不如人,就记恨一辈子,没意思。但奈保尔就写得大大方方。
那回到开头,为什么要用清道夫开场呢?如果只是一个引子会不会太长了,不是说短篇惜字如金吗?之前 Wordsworth 用别的乞丐开场,怎么说也是同类人。
看完想想,明白了,这篇叫做 His Chosen Calling,「被选定的职业/召唤」。原来 Eddoes 不是引子,是终点。是 Elias 屡屡不得志,奋力飞升但却只熟练掌握了降落技巧的归宿。这便有一个悲凉的落点。包括 Caution(不相信报纸的)或者 Love, Love, Love(逃婚富家女),都是这样。没有戏剧性,没有激烈的冲突,就是很简单很普通的失败了,不成,没磨合好,猜不准,被骗了,没追到。仅此而已。
TDK 的 slogan 是 What would happen when an unstoppable force meets an immovable object? 非常有张力,给劲,很多人也很喜欢。但在米格尔街上不是这样,就是没成。很自然,就像我见到的生活。追一个女生追了很久没追上也不知道为什么,学一门课学得很认真没过、老师法外开恩给了及格,做一份工作做得好好的结果毫无预兆老板跑路了。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不可避免的道理,也没什么不为人知的内幕,you just failed, that's it, plain and simple.
《Miguel Street》读后感(五):译一篇
.华兹华斯①
V.S. 奈保尔②
舶良指玄 /译
三个乞丐每天准时拜访米格尔③街上热心的住户。先是十点左右,一个穿白夹克衫、缠着腰布的印度人到访,我们在他背上的口袋里倒进一小罐米。到了十二点,一个抽泥烟斗的老太婆来了,她得到一分钱。下午两点的时候,一个盲人由一个男孩带路,也来讨他的那一分钱。
有时我们也会遇到无赖。一次一个男人来这儿说他很饿。我们就管了他一顿饭。他又向我们讨烟抽,我们不为他点烟他就赖着不走。后来这个人再也没来过。
一天下午大概四点的时候,最古怪的客人来了。我已经放学回到家,穿着家里的衣服。那个人对我说:“小家伙,我能进你家的院子来吗?”
他是个瘦小、衣着整齐的男人。戴一顶帽子,穿一件白衬衣、一条黑裤子。
我问:“你进来干嘛?”
他说:“我想看看你家的蜜蜂。”
我家院子里有四棵小棕榈,上面聚满了不请自来的蜜蜂。
我跑上台阶,喊道:“妈,有个人在外面,说要看咱家的蜜蜂!”
妈妈走出来,看看那个人,很不友好地问道:“你想干嘛?”
那个人说:“我想看看你家的蜜蜂”
他的他的英语好得听起来有些不自然。,我看到妈妈显得非常担心。
她对我说:“站这儿别走,他看蜜蜂的时候给我好好看着他”
那个人说:“真感谢您啊,夫人!您今天做了件大善事!”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字正腔圆,好像每吐一字都要花自个儿的钱一样。
我们看蜜蜂,那个人和我,整整一小时蹲在那些小棕榈边儿上。
那个人说:“我喜欢看蜜蜂。小家伙,你喜欢看蜜蜂吗?”
我说:“我可没那闲工夫。”
他沮丧地摇着头。说:“我平时就做这个,就是看,我可以看蚂蚁看上好几天。你看过蚂蚁吗?还有蝎子、蜈蚣、两栖鲵什么的,你都看过吗?”
我摇摇头。
我说:“那你做什么工作呢,先生?”
他站起身来,说:“我是诗人”
我说:“是个好诗人吗?”
他说:“是全世界最好的诗人”
“那你叫什么啊,先生?”
“B•华兹华斯。”
“比尔的B吗?”
“布莱克,布莱克•华兹华斯。怀特•华兹华斯④是我哥哥。我们哥儿俩共用一颗心。看到牵牛花那样一朵小花我都会哭出来”
我说:“为什么哭呢?”
“为什么,孩子?等你长大就明白了。要知道,你也是个诗人啊。你是个诗人的话,所有事情就都能让你哭出来。”
我不再笑了。
他说:“你爱妈妈吗?”
“她不揍我的时候爱。”
他从屁股兜里掏出一张印着字的小纸片儿说:“这张纸上是关于妈妈的最伟大的诗篇,我愿意低价卖给你,只要四分钱。”
我走进屋,说:“妈,你愿意花四分钱买一首诗吗?”
妈妈说:“给我听着,叫那个混蛋夹着尾巴滚!”
我对B.华兹华斯说:“妈妈说她没有四分钱。”
.华兹华斯说:“这就是诗人的悲剧。”
他把小纸片放回兜里,看起来毫不介意。
我说:“这样到处转悠着卖诗可真好玩儿,唱“卡吕普索⑤”的才这样呢。有很多人买吗?”
他说:“从来没人买。”
“那干嘛还到处转悠呢?。”
他说:“这样我能看到好东西啊,我也想着能遇上别的诗人。”
我说:“你真觉得我是个诗人吗?”
“你像我一样棒,”他说。
•华兹华斯离开的时候,我祈祷着能再见到他。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下午放学回家,在米格尔街街角又见到他。
他说:“我等你半天了。”
我说:“你卖出诗了吗?。”他摇摇头。
他说:“我的院子里有棵西班牙港最棒的芒果树,现在芒果都熟了,又红又甜,还有好多汁呢。我在这儿等你就为告诉你这个,请你来我家吃芒果吧。”
他住在阿贝托街那片儿正中央一座独居室的小屋里。院子里充满绿意,生长着一棵大芒果树、一棵椰子树和一棵杏树。整个地方显得很荒凉,一点也不像是在城市里。整座街上看不到一座混凝土的大屋。
他说得对。芒果真是甜,汁也多。我一连吃了六个,黄黄的芒果汁顺着胳膊直流到胳膊肘,也从嘴里顺下巴流下来,把我的衬衫染得的花花的。
回到家妈妈说:“上哪儿野去了?以为你翅膀硬了可以到处撒野了?给我撅根鞭子来!”
她狠狠揍了我一顿,我跑出家门赌咒说再也不会回来。我去找B.华兹华斯。那时我气急败坏,鼻子上还淌着鲜血。
•华兹华斯说:“不要哭了啊,来我们出去散散心。”
我不哭了,但还是抽抽嗒嗒。我们出去散步,从圣•克莱尔大街直走到萨瓦纳最后来到赛马场。
•华兹华斯说:“现在,我们来躺在草地上看看天空,我要你想象一下那些星星离我们有多远。”
我按着他所说,看到了他想要我看的。我感到一切都已不存在,有生以来我从未有过这样广阔而强烈的感受。我忘记了所有的愤怒,所有的眼泪和从小到大挨过的揍。
我说,我感到好多了,他便讲起那些星星的名字。不知为什么,我他别清楚地记得猎户座。直到今天我仍能指出猎户座的方位,其他的星座却都忘光了。
后来一束光突然打在我们脸上,一个警察出现在眼前。我们从草坪上坐起身来。
警察问道:“你们在这儿干嘛?”
•华兹华斯说:“四十年来,我也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华兹华斯和我成了朋友。他告诉我:“千万别告诉别人关于我和芒果树、椰子树还有杏树的事儿。这是咱的秘密。你要是告诉了别人,我可是会知道的喔,因为我是诗人。”
我起了誓,并一直守着这秘密。
我喜欢他的小屋,就像乔治⑥的前屋那样没什么家具,看上去却更干净、清新。但同样也显得孤独。有一回我问他:“华兹华斯先生,你院子里的灌木怎么从来都不修剪啊?这样弄得这儿多潮啊。”
他说:“听好了啊,我要给你讲个故事。从前,有个小伙子遇见一位姑娘,他们相爱了。他们是那么深的爱着彼此,于是就结婚了。他们俩都是诗人。他爱着词句,她爱着花花草草,还有那些树木。他们在一间小屋里过得非常幸福。后来,有一天诗人姑娘对诗人小伙子说:‘我们家里又要添一个诗人了。’这个诗人却没有降生,因为姑娘死去了,小诗人也在腹中随她而去。她的丈夫伤透了心,他说他不会再去碰姑娘花园中的一草一木。于是花园就成了这样子,草木丛生,茂盛而荒凉。”
•华兹华斯讲起这个美丽的故事时我一直注视着他,他显得更加苍老。我懂他的故事。
我们一起散步,穿过长长的路途。我们到植物园和岩景园游玩,在黄昏时分爬上“大人”山,看夜幕缓缓降临西班牙港,城市、轮船和码头的灯光都渐渐亮起来。
他做任何事都是像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他做任何事都像是在做礼拜。
他会对我说:“现在,一起去吃点儿冰淇淋怎么样?”
我说好,他就变得非常认真,说:“那么,咱们光顾哪家馆子呢?”就好像这是件极其重要的事一样。他会琢磨一会儿,最后说:“我看,得进这家店问问价钱。”
世界变成了最令人激动的地方!
一天,在他院子里,他对我说:“我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
我说:“真的是秘密吗?”
“至少目前还是。”
我看着他,他看着我。他说:“记着啊,只有你知我知。我正在创作一首诗。”
“噢。”我挺失望。
他说:“这可不是首一般的诗。这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诗啊!”
我吹着口哨。
他说:“五年多以前我就开始写了,还要再写22年才写得完,如果我能保持现在这个速度的话。”
“那你写了好多吧。”
他说:“没写多少呢,我每月只写一行,但我保证是美好的一行。”
我问:“上个月那美好的一行是什么呢?”
他举目望向天空,说:“往昔是深邃的。”
我说:“很美的句子。”
•华兹华斯说:“我希望能把每月的体验都提炼成一行诗。这样的话,22年后我就会写成一首献给全人类的诗。”
我充满了惊叹之情。
我们继续走着。有一次沿着码头的防波堤散步时,我说:“华兹华斯先生,我把这颗钉子扔到水里,你觉得它会浮起来吗?”
他说:“世上无奇不有。扔吧,看看会怎样。”
钉子沉了。
我说:“这个月的诗怎么样呢?”
但他再也没告诉我什么诗句。他总是说:“喔,就快写出来了,你知道,就快出来了。”
有时我们坐在防波堤上看那些大船驶进港口。
但关于那首最伟大的诗篇,我却再也没有听他说起。
我觉得他正一天天衰老着。
“你怎样生活呢,华兹华斯先生?”有一次我问他。
他说:“你是问我怎么弄钱?”
我点点头,他狡猾地笑了起来。
他说:“在卡吕普索的季节唱歌。”
“这能维持你一年的生活吗?”
“足够了。”
“但等你写出那首最伟大的诗篇,你就会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了。对吗?”
他没回答。
一天,我到他的小屋看他,看到他躺在他的小床上。他显得那么苍老、那么虚弱,我真想哭出来。
他说:“诗写得不顺利。”
他不看我,透过窗子望着那棵椰子树,说起话来仿佛我并不存在。他说:“二十岁的时候,我觉得浑身的劲儿使不完。”这时,我几乎眼看着他的脸变得愈发苍老和疲倦。他说:“但那——那是好久以前了。”
这时——我特别想哭,像是被妈妈抽了顿耳光。我清楚地看到死亡在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上,谁都看得出。
他看着我,看见我流泪,他坐起身来。
他说:“来。”我走过去,坐在他的膝上。
他注视着我的眼睛,说:“哦,你也能看见它,我一直都知道你有诗人的眼光。”
他看上去并不悲伤,这让我放声大哭起来。
他将我搂在他瘦弱的胸前,说:“想要我给你讲个可笑的故事吗?”他向我鼓励地微笑着。
我却说不出话来。
他说:“等我讲完这故事,你得答应我离开这儿,再也不要来看我。你答应我吗?”
我点点头。
他说:“很好。好吧,听好:我讲过关于那诗人小伙子和诗人姑娘的故事,还记得吧?那不是真的,全是我编出来的。所有那些谈论诗的事还有那世界上最伟大的诗篇,也都不是真的。这难道不是你听过的最最可笑的事吗?”
他的声音突然停了。
我离开了那间屋子,哭着跑回家,像个诗人那样,看到什么都想哭。
一年后我又走过阿贝托街,却再也找不到那诗人的小屋。它不是消失掉了,却也差不多。它被拆了,一座两层的大屋取代了它的位置。芒果树、杏树和椰子树都已被砍掉,到处都是砖石和混凝土。
就像B•华兹华斯从未来过这个世界。
注:
① 本篇选自奈保尔的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该书讲述米格尔街上小人物们的泪与笑。原文见http://social.chass.ncsu.edu/wyrick/debclass/bword.htm
② V.S.奈保尔,英国移民作家。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的一个印度家庭。祖父1880年作为契约劳工从印度北部漂洋过海移民特立尼达。奈保尔年幼时,父亲凭自学谋到特立尼达英语《卫报》记者之职,于是举家从乡间小镇搬迁到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 西班牙港的市井生活才是年轻的奈保尔眼中“真实的世界”。但另一个世界也许更为真实,那就是英国文化与文学的世界。至于他当时对印度的印象则完全来自英国作家(毛姆、艾克利和奥尔都斯•赫胥黎)笔下的印度。换句话说,他自幼就从英国人的视角来认识与他没有直接关联的印度。
奈保尔在西方享有盛誉,他和拉什迪、石黑一雄并称“英国移民文学三雄”。其作品曾获毛姆奖、布克奖等不少重要文学奖,200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重要作品有《米格尔街》、《河湾》、《抵达之谜》等。作品主要写印度、非洲、加勒比地区人的生存状况,表现了后殖民时代的世态人心(摘自豆瓣网和百度百科)。详细介绍见此:http://www.kirjasto.sci.fi/vnaipaul.htm
③ 米格尔街是特里尼达西班牙港旁的一条大街,一个贫民窟,现属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Republic of Trinidad and Tobago)是位於中美洲加勒比海南部、紧邻於委内瑞拉外海的岛国。全国是由两个主要的大岛特立尼达岛与多巴哥岛,再加上21个较小岛屿组成。特立尼达岛原为印第安人阿拉瓦克族和加勒比族的居住地。1498年哥伦布经过该岛附近,宣布为西班牙所有。1781年被法国占领。1802年据《亚眠条约》划归英国。多巴哥岛历经西、荷、法、英多次争夺,1812年据《巴黎条约》沦为英国殖民地。1889年两岛成为一个统一的英殖民地。1962年8月31日独立。1976年8月1日改为共和国,仍是英联邦成员国。
位於特立尼达岛西岸的海港城市西班牙港(Port-of-Spain)是该共和国的首都也是最大城市,在中南美洲的经济圈里占有颇重要的地位。
特立尼达及多巴哥最主要的两个人口族群分别是印度裔特立尼达人与非裔特立尼达人,合占全国人口约79.8%的比例,其中前者是殖民时代由英国引进到此地工作的印度劳工之后裔,后者则是非洲来的奴隶后裔。英语是该国的官方语言,但民间最常使用的语言却是特立尼达英语与多巴哥英语(二者皆可视为是英语的方言,是以英语为基础的混种语言。(摘自百度百科)
④Black Wordsworth,White Wordsworth原意黑•华兹华斯、白•华兹华斯。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是英国湖畔派诗人。
⑤卡吕普索,希腊神话的海之女神,她将奥德修斯困在她的俄吉吉亚岛上七年。小说中的“卡吕普索”指西印度群岛上的一种小调,常以讽刺时事为主题。
⑥乔治,《米格尔大街》另一短篇《乔治和他的粉红屋》中的主人公,是个住着破旧的小木屋、性情暴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