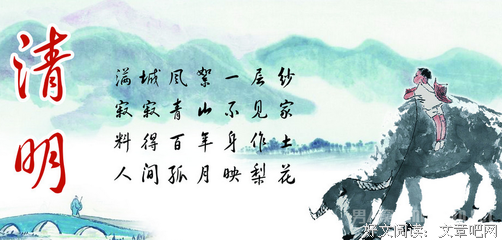咀华集·咀华二集读后感100字
《咀华集·咀华二集》是一本由李健吾著作,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2.00元,页数:18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咀华集·咀华二集》精选点评:
●李健吾的印象主义批评,卓然自成一家,颇有可观之处。
●近4⭐。 《咀华集》的文字和见解比《咀华二集》要通透,且掷地有声。西渭先生的文字常有一种礼让和商量,他即使对所论之人的作品再多不喜,也不会意气用事,而是谦恭且理待,文贴并析见。 然,这并非说明西渭先生是一妥协之人,批评界的老好人,而是他的言辞足够和缓,是以《诗经》之“兴”起,渐而敷衍各派风格,从欧及中,遂达其妙意、病灶,涵泳沉潜。 尽管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评论,置于今日,仍可资我辈为文。
●以印象式批评出之,表面上从流飘荡,实际却启迪了无数的文学史家,类似于鲁迅说的“作家手笔”和“史家眼光”,至少比起朱自清的观点,我更能接受李健吾眼中的李金发。本书与朱光潜,沈从文,周作人等人的文艺批评,构成了30年代中期对左翼话语的集体抗议,也是压激愤于平淡之下。
●个人化的美文批评。
●超级赞的小书
●老师推荐。从未知评论也可以这样写。
●作为批评者的李健吾远不及作为译者或是作者的李健吾
●好多书看过都忘记M了。虽然M不M无所谓 但是名分真的很重要啊!
●以美文的文体进行文学批评,这无疑是李健吾先生的最大特色之所在,无论他的分析是否到位(当时就曾被多名作家质疑),这般评论文字读起来就很舒服。
●推启发良多。
《咀华集·咀华二集》读后感(一):不为批评而批评
这本书是非常精致的中国印象式文学批评。
作者有深厚的文学功底,文笔优美,饱含深情。
喜欢由大作家引出小作家,似乎偏爱废名和巴金。
在批评作品时,作者不愿意直说人短,多是称颂和鼓励。
愿意将不足看作是可以延伸的特点,给予期待。
作者的鼓励并非是一种中庸的态度,而是为了给作家自由。
他不愿意以个人见解束缚作家的可能性,
对作家的努力始终给同情和欣赏。
文笔非常非常优美!令人惊叹。
《咀华集·咀华二集》读后感(二):寻求非学院派的评论方法
我已经脱离了学院的生活,然又不甘做一位纯粹消遣娱乐的读者,所以,寻找一条非学院派但又真挚地感悟作品的评论路径成为必需:真诚地和每一部作品相遇、相识,重视阅读时的感性体验,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依托打入作品表述的经验,通过评论将自我的思辨展开并表现……
想要达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首先还是要学习前辈,如李健吾先生,如刘海燕女士,都是这类印象式的评论脉系。不过李健吾先生那种略生涩的白话文读来有点不太适应,而且他一写到理论就阻塞了他文章的行进,觉得冗长乏味。但我的确喜欢他评论乡土作家和艺术性极强的作家,每当这时,他那散文式的灵慧和雅致就揉错进文章中,禅机般一语道破,又令人回味无穷。
《咀华集·咀华二集》读后感(三):是智慧散文,又是情深批评
细读《咀华集·爱情的三部曲》
我可能也要做一个人性的批评者,和健吾先生一样,尽管在现在的术语中,我也不占。说是细读,是为偷懒的辩白,此前便已读过全书,但总如他所说“总进不进去”。原因简单,心情浮躁,见识短浅,固执一词,语言不通。可能你要笑话了,前好理解,“语言不通”?必是打着叹号、鄙视,确然,把我拦不进去的正是之,在读了古白话的作品后,回来我才慢慢理解文句意思,行文风格,也才体会到健吾先生批评中的人性真情,他同爱着自己的文字,不甘心只做嫁衣裳。可以说都是他自己的散文作品了,他自己的性情、他的思考,不理解时繁琐,相通时际会,是哪里都有。他的文字自然,而顺畅,杂古简深,时常充满智慧的见解,但有可能你会自有看法,可不得不说,很多道理于今也是适用,他对人生阶段状态的理解同样可行。但这一方面过多,下了大力气,对于批评的作品无乃绿叶?当然,不可否认他对人物的解读很有深度,帮我们理清了三位主角千丝万缕联系,让我们认真思考三书带来的人生意义,而不是只有热情流淌过后莫名的温度,也更去了解了一个作者,了解他的作文,他的创造,了解了一个时代的青年心声,甚至于点评中还教会我们一些技巧,但这些都需要我们阅读的自去注意,自己吸取。他的话是明白的。
行文从规劝批评者摈弃成见,给出自己批评态度——有人性之阅读批评,阐述这一根据和意义以及做法,其中夹杂自我的反思,顺其而自然走进巴金的世界,又讲述巴金的热情,对作品的钟爱,作品特色,再分析文字、三书主人公性格中的热情及热情的力量收束全篇。
这是智慧的散文,又是情深的批评。
《咀华集·咀华二集》读后感(四):摘抄
她的幸福就是接受人生,即令人生丑恶也罢。然而沈从文先生,不像卢骚,不像乔治桑,在他的忧郁和同情之外,具有深湛的艺术自觉,犹如唐代传奇的作者,用故事的本身来撼动,而自己从不出头露面。这是一串绮丽的碎梦,梦里的男女全属良民。命运更是一阵微风,掀起裙裾飘带,露出永生的本质——守本分者的面目,我是说,忧郁。
儿童并不更好,这只是一个儿童,生活是一团朦胧的氛围,用天真体会繁难的世事,因而分外隔膜。
散文缺乏诗的绝对性,唯其如此,可以容纳所有人世的潮汐,有沙也有金,或者犹如蜿蜒的溪流,经过田野村庄,也经过城邑,而宇宙一切现象,人生一切点染,全做成它的流连叹赏。
每人有每人的阁楼,每人又有每人建筑的概念。同是红砖绿瓦,然而楼自为其楼,张家李家初不相同。把所有人和天的成分撇开,但以人和物的成分来看,则砖须是好砖,瓦须是好瓦,然后人能全盘拿得住,放有成就。远望固佳,近观亦宜,才是艺术。我知道,有的是艺术家,而且伟大的艺术家,根据直觉的美感,不用坚定的理论辅佐,便会自然天成。
左拉坚信舞台可能的唯一再生,是把“世纪的科学与实验的精神传播到舞台上去。”他用他的剧本做例往细里诠释道:“动作含在人物的内在斗争之中,不复含在一个什么故事里面,这里是一种感觉与情感的逻辑,不再具有事的逻辑,解决变成问题一种代数的结果。于是我一步一步尾随小说,我把戏关在同一房间,湿而且黑,好不剥夺一丝它的凹凸,它的命运,我选了一些愚蠢的废料,好在我的英雄们的强烈痛苦之下,显出日常生活的庸俗。我不断用力把舞台挽住我的人物的平常的事务,因为他们不是在演,而是当着观众生活。”没有比这几句话似乎更能骚到夏衍先生的痒处,更能发挥《上海屋檐下》的企指。
雨果以为艺术和自然各有自己的王国,却又相依为命:“自然和艺术是两件东西,缺了一个,另一个就不存在。不算艺术的理想的部分,艺术还有一个积极的属于土地的部分”,他进一步推论戏剧的镜子看法,往深里追究道:“万一这是一面平常镜子、一个平光光的面,映出来的东西仅是一个发暗而不具凹凸的形象,忠实,然而无色。我们晓得简单的反射照不出色与光来。所以戏剧必须是一面集中的镜子,不唯不有所减弱,反而聚敛增浓有色的光线,把一星星亮变成一道光,一道光变成一团火”。
这是一种内在的要求,一种孕育的结果。我们没有方法去“创造”任何新奇形式,假如我们不把灵魂浸润在每一分钟每一地点交相影响的人生的大小变化。《上海屋檐下》的造诣就在它从人生里面打了一个滚出来。这是现实的,和广大的人群接近,这是道德的,指出一条道路给大家行走。不属于纯粹的悲剧,没有死亡,没有形而上的哲学,没有超群轶众的特殊人物,不属于纯粹的喜剧,虽说作者命之曰喜剧,因为人物并不完全典型,愁惨并不完全摒除,这里不是自然主义的现实,我们明白作者在介绍芸芸众生的色相之下,同时提出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些人与人之间的纷争。他不讽刺,他不谩骂,他也不要人落无益的眼泪,然而他同情他们的哀乐。
亚里士多德的那句名言,最真实的不是历史,而是诗。
《咀华集·咀华二集》读后感(五):被遗忘的《咀华二集》初版本
被遗忘的《咀华二集》初版本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李健吾先生或以笔名刘西渭或以本名写下了一批灵动飞扬的文字,结集成《咀华集》、《咀华二集》,交付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两部集子早已因其新颖的架构、精到的结论、别致的文字名动文坛,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经典之作。直到如今,咀华篇章依然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存在,一个很难企及的高度。
《咀华集》出版于1936年12月,收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三集,出版后大受欢迎,一再重印。《咀华二集》有两个版本,初版本1942年1月出版,收入“文学丛刊”第七集,再版于1947年4月。《咀华二集》初版本流传甚少,通常见到的是其再版本。研究者往往忽略了两者的区别,误以为再版本只是个重印本,在征引时想当然,不加区分地一律标示为1942年1月版。这种习焉不察的状况一直到2005年才先后有两篇研究文章提出质疑。①由此,近乎被遗忘的《咀华二集》初版本才得以重回读者的视野。
《咀华二集》初版本缘何流传甚少呢?据李健吾的妻子尤淑芬回忆,1945年,日本宪兵到家搜捕李健吾的时候,搜到了他的一些藏书,此外还“搜查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抄走了全部成书的《咀华二集》和所有的文学丛刊”②。李健吾在散文《小蓝本子》中也确认《咀华二集》“被敌伪没收”③。在《陆蠡的散文》中,李健吾也提到1942年4月12日“文化生活社被抄,没收全部新旧《文学丛刊》”④。
最近,在国内知名的孔夫子旧书网上惊现《咀华二集》初版本,恰好由一位朋友拍得,笔者亦有幸近水楼台先得月,得窥一直存于想象中的初版本之全貌,解了不少先前的疑惑。硕士论文做的是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在资料方面唯一耿耿于怀的就是这一版本问题,如今真相大白,实在是兴奋莫名,看来,我与健吾先生还是大有缘分的。
从初版本到再版本,初版本扮演了一个过渡性的角色,由于上述原因,亦成为一个被遗忘的版本,再版本才被视为定本,甚至是唯一的本子。在没有见到初版本之前,依据再版本我推测它可能是一本非常薄的小册子,当时即讶于其出版的仓促。其实,上世纪80年代李采臣为李健吾编选的《李健吾文学评论选》收入了三个版本(《咀华集》、《咀华二集》初版本、再版本)的绝大多数文字,两位李先生肯定是知道初版本的存在的,只是我们这些后来者不知情而已,由此还引来一些额外的猜想。⑤
初版本与我先前的想象存有明显的差异。初版本署名李健吾,依照《咀华集》的先例以及“咀华”文章结集前通常的署名,当是刘西渭更符合惯例。况且再版本亦署刘西渭。全书篇幅292页,近于《咀华集》以及再版本的一倍。全书分为四类:甲类,《朱大枬》,《芦焚》,《萧军》,《叶紫》,《夏衍》及其附录《关于现实》;乙类,《悭吝人》,《福楼拜书简》,《欧贞尼•葛郎代》,《恶之华》;丙类《旧小说的歧途》,《韩昌黎的〈画记〉》,《曹雪芹的〈哭花词〉》;丁类,《假如我是》,《自我和风格》,《个人主义》,《情欲信》,《关于鲁迅》,《致宗岱书》,《序华玲诗》。
各篇刊发情况大致如下:
《朱大枬》,写于1931年,是在亡友逝世近一年后,再版时易名《朱大枬的诗》,原刊于何处不详;
《芦焚》,原题为《读里门拾记》,刊于《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二期,1937年6月1日,再版时易名《里门拾记——芦焚先生作》;
《萧军》,原题为《萧军论》,刊于《大公报•文艺》(香港)第544、545、546、547、550、551期,1939年3月7、8、9、10、13、14日,再版时易名《八月的乡村——萧军先生作》;⑥
《叶紫》,原题为《叶紫论》,刊于《大公报•文艺》(香港)第809、810、811期,1940年4月1、3、5日,再版时易名《叶紫的小说》;
《夏衍》,原题为《夏衍论》,刊于《大公报•学生界》(香港)第267期,1941年2月21日;《大公报•文艺》(香港)第1036、1038期,1941年2月22、24日;《大公报•学生界》(香港)第268期,1941年2月25日;《大公报•文艺》(香港)第1039、1040期,1941年2月26、27日;《大公报•学生界》(香港)第268期,1941年2月28日;《大公报•文艺》(香港)第1043期,1941年3月3日;《大公报•学生界》(香港)第269期,1941年3月4日;《大公报•文艺》(香港)第1044期,1941年3月5日。⑦1942年1月经整理后刊于《文化生活》⑧,再版时易名《上海屋檐下》,《关于现实》是这篇文章的附录,原刊于何处不详;
《悭吝人》,原题为《L’Avare的第四幕第七场》,刊于《大公报•艺术周刊》(天津)第61期,1935年12月7日;
《福楼拜书简》,原题为《福楼拜的书简》,刊于《文学》第五卷第一号,1935年7月1日;
《恶之华》,原题为《鲍德莱耳——林译〈恶之华〉序》,刊于《宇宙风》(散文半月刊)第八十四期,1939年11月16日;
《欧贞尼•葛郎代》,原题为《巴尔扎克的欧贞尼•葛郎代》,刊于《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三期,1937年7月1日;
《旧小说的歧途》,原题为《中国旧小说的穷途》,刊于《大公报•文艺》(天津)第108期,1934年10月6日;
《韩昌黎的〈画记〉》,刊于《学生月刊》,1940年3月15日;
《曹雪芹的〈哭花词〉》,刊于《宇宙风》(散文半月刊)百期纪念号,1940年6月1日;
《假如我是》,刊于《大公报•文艺》(天津)第333期“书评特刊”,集体讨论“作家们怎样论书评”,1937年5月9日;
《自我和风格》,刊于《大公报•文艺》(天津)第328期“书评特刊”,集体讨论“书评是心灵探险么?”,1937年4月25日;
《个人主义》,原题为《个人主义的两面观》,刊于《文汇报•世纪风》,1938年11月9日;
《情欲信》,刊于《学生月刊》第1卷第5期,1940年5月5日;
《关于鲁迅》,其中《“空头的荣誉”》原刊出处不详;《鲁迅和翻译》,刊于《大公报•文艺》(香港)第428期,“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专号,1938年10月22日;《为什么鲁迅放弃小说的写作》,原题为《为甚么鲁迅放弃小说》,刊于《星岛日报•星座》140期,1938年12月18日;
《致宗岱书》,原题为《读〈从滥用名词说起〉——致梁宗岱先生》,刊于《大公报•文艺》(天津)第318期,1937年4月2日;
《序华玲诗》,原题为《诗人华铃论》,刊于《星岛日报•星座》,1938年11月;后题为《论诗与诗人——序华琳先生的诗集》,刊于《大公报•文艺》(香港)第476期,1938年12月21日。
在跋语中,李健吾主动向读者坦承初版本的“驳杂”,的确,这批入选的文章较之《咀华集》要宽泛得多,最初在报章上发表时的署名既有刘西渭,亦有李健吾。⑨四类文字中大概只有甲类大体吻合《咀华集》“作家作品论”的惯例,故再版时只保留了这一类。然后增补了1946—1947年间所写的《清明前后》、《三个中篇》、《陆蠡的散文》,署名变回刘西渭,跋语亦作了相应的增删。如此一来,无论是体例还是署名,均和《咀华集》保持了一致。⑩
署名的更改最能见出李健吾对“咀华”文字的心意。“咀华”文字的风流毕竟是属于刘西渭先生的。李健吾比较得意的批评文字一向是以“刘西渭”的名义发表的○11,跟自己专业有关(譬如关于福楼拜、司汤达、梵乐希等法国文学名家)的文字方用本名。除了几个较为亲近的朋友之外,一般人很少知晓李健吾即是刘西渭,刘西渭即是李健吾,默不则声的“刘西渭先生”几乎成了文坛一个不大不小的“索隐对象”。
其实,这种景况,李健吾先生是要付一定“责任”的,换言之,这未尝不是李健吾先生兼刘西渭先生苦心经营的结果。
还在《咀华集》结集之前,李健吾就在《大公报•文艺》(天津)“书评特刊”上以本名发表了《刘西渭先生的苦恼》一文。文章的构想以及布局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鲁迅的《孤独者》,李健吾以刘西渭的老友面目出现,回忆了与刘西渭先生的几次对话,将批评界的“孤独者”刘西渭先生遭遇的委屈与苦恼一股脑儿倒出。以“书评”名家的刘西渭先生处境显然不妙,形单影只,四处树敌,愤懑不解至极。“闷极了”的刘西渭先生决意改换生活样式,“到别处走走”。在与刘西渭先生的对话中,李健吾故意处处刁难,频频揭对方的短,惹得刘西渭先生情急之下慷慨陈词,颇有明志的意味。如此安排,更可明白见出刘西渭先生的个性及其追求,相当动人。李健吾此举,可谓煞费苦心,不过也收到了效果,不明内情的读者恐怕无论如何也不会知道这对老朋友原是一人吧,刘西渭先生的苦恼原本就是李健吾先生的苦恼,本文只是一篇“自述”罢了。对于刘西渭先生的身份,李健吾口风着实很紧,仅仅透露他是陕西人,所谓“西渭”,当解为“渭河以西”。这大概是李健吾自己对“刘西渭”这一笔名的正解吧。李健吾的批评文字在当时被目为“印象”式的,从字面上去理解,印象一词似乎含有贬义,这也几乎成为李健吾的一块心病,因而申述自己的批评观就成了必要之举。在刘西渭先生的述说中,这类文字占了相当篇幅。“批评的成就是自我底发见跟价值底决定。”“一个批评家是学者跟艺术家的化合,他的工作是种活的学问,因为这里有颗创造的心灵运用死的知识。”“我不能禁止我在社会上活动,喝酒交朋友,但是当我拿起同代人一本书,即使是本杰作,熟人写的也罢,生人写的也罢,我精神便完全集中在字里行间,凡属人事我统统关在门外。我不想捧谁,不想骂谁,我是想指出其中我所感到看出的特殊造诣或者倾向(也许是好,也许是坏),尽我一个读书人良心上的责任。”“他具有深厚的个性,然而他用力甩掉个性,追求大公无私的普遍跟永久。”○12立论平正公允,坦坦荡荡,是牢骚,亦是宣言。
尽管李健吾为行将“隐遁”的刘西渭先生写下了这样一篇奇特的纪念文字,三个月之后,刘西渭先生竟又亮相了,而且还端出了色香味俱全的《咀华集》。这本小册子为刘西渭先生挣下了很高的荣誉,犹如一股清凉的风,吹过当时的文坛。
《咀华集•跋》将刘西渭先生的“苦恼”着意发挥,演化为整部集子的批评原则。“我不得不降心以从,努力来接近对方——一个陌生人——的灵魂和它的结晶。”“批评最大的挣扎是公平的追求。但是,我的公平有我的存在限制,我用力甩掉我深厚的个性(然而依照托尔斯泰,个性正是艺术上成就的一个条件),希冀达到普遍而永久的大公无私。”○13此后,李健吾在“书评特刊”上相继发表了《自我和风格》和《假如我是》,这两篇文章的署名方式颇值得玩味,前一篇用“刘西渭”,后一篇用本名,如此,即拉开了李健吾先生与“书评家”刘西渭先生的距离,明摆着强调这分别是两个不同的人。在这两篇文章中,李健吾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批评观,后来的研究者的不少观点即是对此所作的发挥。同样,也正是因为这类文章中的蛛丝马迹,再加上朋友间的口耳相传,“刘西渭”慢慢就变成了一个“公开秘密”。○14
词锋犀利、文笔美妙的咀华文字让刘西渭先生名满天下,同时招来的,有善意的批评,亦有恶意的诽谤。《咀华集》出版之后,粗暴如欧阳文辅先生者,将刘西渭先生斥之为“印象主义的死鬼”,“旧社会的支持者”,“腐败理论的宣教师”。○15这惹恼了李健吾,在《咀华二集》初版本跋语中,他宣称“从今日二集起,我改回真名实姓,一人做事一人当,既不否认过去我的存在,更遂了刘西渭先生销声匿迹的心愿”,亲自跳将出来,亮出自家真实身份,进而代刘西渭先生痛陈欧阳先生不可理喻与矛盾之处,作为刘西渭先生“归隐道山之前”的“辞行酒宴”。○16
将李健吾与刘西渭的文字公开合为一集刊行,如此编选《咀华二集》,李健吾同读者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权作二人的“联合声明”。至此,关于“刘西渭”的文坛索隐彻底休矣!然而,你料想不到,这事并不算完,李健吾在跋语的末尾老调重谈,大摆迷魂阵:
刘西渭先生放了一把火,自己却一溜烟走掉。平时洁身自爱,守口如瓶。他轻易不睬理别人的雌黄,如今惹下乱子,一切由人担当。我向他道喜,从此债去一身轻,可以逍遥于围缴以外。我为自己悲哀。但是,他逃不脱干系,我要借用他的书名,直到没有人分出他和我的存在。我和他是两个人,犹如书是两本,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然而,多用些心,读者会发见他们只有一条性命。○17
一分为二,合二为一,原只是“一条性命”。《咀华二集》的读者读到此处,少不了会心一笑——“此中有真意”。
初版本跋语宛如三段答辩词,第一段针对的是“前进作家”叶灵凤先生指责其作品与“抗战”无关;第二段针对的即是欧阳文辅先生的谩骂;第三段针对的是“前进的评论家”黄绳先生指斥其“悲观”“消极”。到了再版本中,李健吾又变回了“刘西渭”,整本书又恢复了“咀华”专题的模样。跋语亦作了相应的文字处理。譬如更改了距《朱大枬》一文的写作时间,剔除了“李健吾”的口吻,保留了第二段辩词,以及大谈批评者的自由及限制所在的相关文字。一切做得严丝合缝,略过初版本,读者自然会把再版本《咀华二集》和《咀华集》看做一气呵成,一脉相承。
《咀华二集》选择在1942年出版,大约与巴金的推举有关。《咀华集》的出版大获成功,趁热打铁推出续编似在情理之中。巴金对李健吾的咀华文字相当推崇(即使有过文字的交锋,但也在友谊的正常范围之类),从其主编的“文学丛刊”入选的作品来看,亦可见一斑,第七集十六册中仅《咀华二集》一册属于批评类。按韩石山先生的说法,巴金以及文化生活出版社对李健吾相当关照,凡是李健吾的作品,总是无一例外地给以出版。这中间的考量恐怕既有情谊,亦有名人的品牌效应吧!抗战爆发后,李健吾一直待在“孤岛”上海,1941年12月,最后一座孤岛也沦陷了,生活益形艰难,巴金特将李健吾的剧本搜集在一起,为他出版了《健吾戏剧集》一二两种。○18据此推测,《咀华二集》的仓促出版似乎亦有此意。
从另一面看,《咀华二集》的出版亦见出李健吾对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支持。抗战后,很多文化机构内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负责人亦陆续去了内地(武汉、重庆等地),剩下陆蠡在上海维持工作,“挑起那想不到的责任的重担,拣书,打包,校稿,以及任何跑腿的杂差”。○19巴金于1940年7月离开上海去了重庆的办事处,1945年短暂回过上海,直到1946年才完全回到上海,据他回忆,“抗战后陆蠡在上海维持文化生活社,他(李健吾)帮过一点忙”。○20这种忙帮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但《咀华二集》书稿的提供带有对朋友支持的意味,应该不成问题。1942年4月12日,文化生活出版社被查抄后,陆蠡于次日亲自到巡捕房办交涉,就此失踪,一去不返。1947年,《咀华二集》再版时,李健吾特意增加了一篇“陆蠡论”——《陆蠡的散文》,文章的立意既是总结陆蠡文章的风格,但更多的是谈其人格的笃实厚重,应当是对朋友最好的纪念。
注释:
①参见拙作《〈咀华二集〉版本考》,《山西文学》2005年第5期,亦收入笔者硕士论文《“咀华”之旅——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历程》附录,略有增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2005年7月;汪成法:《李健吾〈咀华二集〉出版时间质疑》,《博览群书》2005年第10期。两篇文章都注意到了再版本收入的文章包括了1942年以后的三篇,由此对《咀华二集》出版时间提出质疑。惜乎未见初版本,基本上都停留在猜测与想象的层面上。
② 淑芬:《重印后记》,《咀华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页160—161。
③ 李健吾:《小蓝本子》,《切梦刀》,文化生活出版社,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初版,页84。但他亦提到日本宪兵“从家里搜到的不是大成问题的《咀华二集》,乃是这个久已被我冷淡的手册”,即读书笔记“小蓝本子”(页82)。
④刘西渭:《陆蠡的散文》,《咀华二集》,文化生活出版社,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四月再版,页149。
⑤李健吾:《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李先生在该书《后记》中说这本选集“收的大多是三种版本的全部文字”(页334),这句话并不全对,或许是另有《李健吾戏剧评论选》(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的缘故,这个选本未收入论及曹禺、夏衍、茅盾等人戏剧的文章;亦未收入《悭吝人》、《福楼拜书简》、《欧贞尼•葛郎代》、《致宗岱书》以及《咀华二集》初版本的跋语;他所说的“三个版本”当指的是《咀华集》以及前后两版的《咀华二集》。不过有学者疑心除《咀华集》、《咀华二集》外还有一部《咀华记余》。关于《咀华记余》是否成书,一直是言人人殊。李健吾的女公子李维永先生说李健吾在世时曾说他除了大家常用到的《咀华集》、《咀华二集》外,另外还有一个薄本《咀华余集》;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在其《中国新文学史》(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年)中也认为有这本书;吴泰昌在回忆文章《听李健吾谈〈围城〉》中提到李健吾编有一本《咀华余集》(《我认识的钱钟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不过,韩石山先生在《李健吾传》(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中考证甚详,他认为李健吾写过,想写成一本书,却没有写完。比较而言,韩先生的说法是可信的。“咀华”乃健吾先生文学批评的精魂,是一辈子的坚持与牵挂,除却 “咀华记余” 的吉光片羽,健吾先生在晚年亦有重开“咀华新篇”的打算,可惜天不假年,只留下《重读〈围城〉》、《读〈新凤霞回忆录〉》以及《读本•琼森〈悼念我心爱的威廉•莎士比亚大师及其作品〉》(前两篇载《文艺报》1981年第三期,后一篇载《文艺报》1981年第十期,均署名李健吾,详见吴泰昌《“熟人的文章有时也很难写”》,《新民晚报•夜光杯》,2005年10月8日)。
⑥《萧军论》收入《咀华二集》再版本时没有注明写作时间,后来出版的《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中亦没有注明,而在《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则注明“1935年”,参照文章内容可知,这个时间明显错误,因为文章讨论的虽是《八月的乡村》(容光书局,1935年8月),但同时也提到萧军的另外两部短篇小说集《羊》(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1月)和《江上》(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同样的错误也出现在《咀华集》中评论《篱下集》和《城下集》的文章中,原版本中前者没有标明写作时间,后者仅注明“五月十二日”,但在宁夏版中前者标明“一九三五年”,后者标明“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二日”,这两个时间都错了,它们都写于1936年。宁夏版《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处理作者落款时间不够严谨,时有错讹。郭宏安选编的《李健吾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基本上是以宁夏版为底本的,错误一仍其旧。200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咀华集•咀华二集》,由书前的出版说明明显可知它是以珠海版为底本的,因而再次重复了前书的错误。
⑦文章很长,而报纸篇幅有限,所以在“文艺”上连载时省略了资料出处,收入《咀华二集》时才作补充,李健吾在连载结束时对此作了交代,并向读者作了预告,云此文收入文化生活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咀华二集》之中。
⑧夏衍:《忆健吾——〈李健吾文集•戏剧卷〉代序》,《文艺研究》1984年第6期。
⑨署名刘西渭的仅有《芦焚》,《旧小说的歧途》,《自我和风格》。《关于现实》由于不清楚原刊出处,故署名情况亦不得而知,还有待进一步查找。
⑩增补的三篇文章发表时均署名刘西渭,分载:《文艺复兴》第一卷第一期,1946年1月10日;《文艺复兴》第二卷第一期,1946年8月1日;《大公报•文艺》(沪新) 第126、127、128期,1947年3月5日、4月4日、4月8日。依照这一标准,还可以收入的文章有《风雪夜归人——吴祖光编》、《咀华记余•无题》、《三本书》、《方达生》,分载:《万象》,1943年10月号;《文汇报•世纪风》,1945年9月12日;《文艺复兴》第一卷第三期,1946年4月1日;《文汇报•世纪风》,1946年7月2日。
○11出乎意料的是,在《大公报•文艺》(香港)上连载《萧军论》、《叶紫论》、《夏衍论》三篇专论时,用的都是本名。
○12李健吾:《刘西渭先生的苦恼》,《大公报•文艺》(天津)第214期“书评特刊”, 1936年9月13日。
○13刘西渭:《跋》,《咀华集》,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页ⅰ、ⅱ。
○14少若(吴小如):《〈咀华集〉和〈咀华二集〉》,《文学杂志》第二卷第十期,1948年3月。
○15参见欧阳文辅:《略评刘西渭先生的〈咀华集〉——印象主义的文艺批评》,《光明》第二卷第十一期,1937年5月10日。
○16○17李健吾:《跋》,《咀华二集》,文化生活出版社,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一月初版,页287、292。
○18韩石山:《李健吾与巴金》,《文坛剑戟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页67—68。
○19刘西渭:《陆蠡的散文》,《咀华二集》,文化生活出版社,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四月再版,页148。
○20巴金:《致达君》,《再思录》(增补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280。此信录自张爱平《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巴金谈李健吾》,原刊《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四期,据张爱平言,此信为“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巴金就李健吾历史问题所写的证明材料。
(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