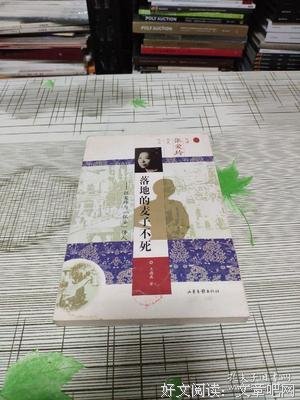《落地的麦子不死》的读后感大全
《落地的麦子不死》是一本由王德威著作,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5.00,页数:22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落地的麦子不死》精选点评:
●王德威,唉,
●王德威一再说朱天心是“老灵魂”,王的文字也自透出前世绮蘼,一如祖师奶奶的华丽苍凉。
●为着对“张派”作家谱系有一个很好的梳理,才买的。论文细腻的很呵,间有一点文青腔:)不过文青腔比起“张派”的诸多繁饰周致来,倒还是健康的气息了。
●重复的论述太多了
●专著里排得上名的,可还是输给张均。
●王德威的文字太华丽了 华丽到浓得化不开
●覺得王威德說的真好,可以那麼一語中的。 一路張派,台灣的三三作家,鐘曉陽,蘇偉貞等等;香港的有黃碧雲,施叔青;大陸的有蘇童,葉兆言。 這些作家大都愛,看到鬼言鬼語的那些,內心真是顫慄。寫黃碧雲的那篇,好吊詭,好暴烈。
●王派文评,蔚然可观。
●很开眼界,用拉康、Julia Kristeva的理论来诠释“张”的作品;张的传人里有穆时英、施蛰存,还有当代的苏童、叶兆言,真是开眼——实则前年4月辞世的台湾女作家林奕含也是“张”的门生;但这种“哥特式的”,在英美文学如勃朗特姐妹的作品里也常见,不知苏童、叶兆言私淑谁家?
●受益。话张爱玲笔下鬼影重重,提及西方文学早有先例,“古堡式恐怖小说”,奥斯汀Northanger Abbey、玛丽雪莱、勃朗蒂Jane Eyre等,女性主义视角看来女作家的恐怖故事亦是探讨自身意识的表征,古堡充当女性逃避外界威胁的安身之地和身心禁锢的幽闭象征。五四以后的女作家叙事重心却落于男作家为主的“为人生而艺术”,张爱玲是“庸俗反现代”。张派“鬼话”实在不乏后继。顺便,王德威的辞藻真够写张爱玲了。 刷完牙好饿……
《落地的麦子不死》读后感(一):鬼话正说
正如老牛所说,王德威写的东西总在水准以上,可就是杂里咕咚。什么叫杂里咕咚?就是很杂,但切得很深,砸的人心里咕咚咕咚的想要一读为快。
“张爱玲的小说以写实为基础,避谈怪力乱神,却自能召唤出一颓废荒凉的恐怖世界”,确实如此,而且惊觉这也是自己如此喜爱她的原因,甚至自己的文字也不自觉地营造着一丝丝鬼气,却始终不愿意脱了现实。
难得的是对所谓张派传人们的一个个或浓或谈的诠释,几乎可以按图索骥地去找来读,不得不读。
《落地的麦子不死》读后感(二):【书摘】落地的麦子不死
张爱玲小说的魅力,不只出于修辞造境上的特色,也来自于她写作的姿态,以及烘托或打压这一姿态的历史文化情境。她所谓“参差对照”的美学,其实也代表了她观察世路人情的结论。在宣传文学狂飙的年代里,张爱玲反其道而行。她摒弃了忠奸立判的道德王义,专事“张望”周遭“不彻底”的善恶风景。她从浮华颓靡的情爱游戏里,看到人间男女素朴原始的挣扎与渴望;她从庸儒猥琐的市井人生中,找寻闪烁不定的道德启悟契机。蔡美丽教授曾谓张爱玲以“庸俗”反当代,正是一针见血之见。不仅此也,张爱玲更有名言:“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这一对“生趣”的强烈关注,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张爱玲是中国女性主义的另一声音,由此可见一斑。
私淑张腔的作家,多能各取所需、各显所能。女作家如施叔青、朱天文、朱天心、钟晓阳(《停车暂借问》)、苏伟贞、袁琼琼,甚至三毛,男作家如白先勇、郭强生、林俊颖、林裕翼等,都有值得追溯的因缘关系。施叔青与白先勇是60年代的张派重要传人。施写在欲望与疯狂边缘煎熬的女性经验,缤纷却阴森的洋场即景,活脱是《金锁记》及《倾城之恋》的延仲。白写凋零虚脱的世家,繁华散尽后的欢场,一片怀旧气息,为张荒芜的末世观,作为了有力注脚。
《落地的麦子不死》读后感(三):片段想法
王德威列出一个名单,指出当代作家中“私淑”张爱玲的许多人。就我读过的几个,我不认为是这样的。拿白先勇来说,我比较同意他自己的说法,即他和张爱玲只是有共同的老师,即《红楼梦》。叶兆言和苏童则更不是。难不成所有不以宏大叙事和宣传腔调为主旨,注重细致描写,关怀个人悲剧命运(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的激烈冲突)的作品都是“私淑”张爱玲?《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和《1937年的爱情》比起张在1940年代的作品,更多关怀是透过私人的经历来展现一个时代,而后者的关怀更多是在私人命运本身。
王德威又认为张在1950年代的小说,与其自身相比不是好的作品。这一点同样不能同意。《秧歌》和《赤地之恋》与1940年代的作品相比,确实完全不同。难不成一定要重复自己才能成为张爱玲?这两篇小说因其是“绿背”作品,所以贴近现实主义。但它们所展现的现实带来的力量,因为不需隐晦,所以比《活着》更直接,也因之更强大。
不过张爱玲是不喜欢这种写作的,《赤地之恋》写到韩战部分的时候,她明显失去了耐心,并且给其安上了一个宣传腔调的结尾。这个结尾让张本人成为她所抒写的那种悲剧。正如鲁迅在左聯时期成为类似的悲剧一样,私人最终都被社会道德挟裹。
在语言风格方面,张爱玲确实是天才。"太阳像一只黄狗拦街躺着。”(《秧歌》);刘荃和戈珊偷情,关了灯,“黑暗啪的一声打在脸上。”(《赤地之恋》)。这样的语句,只读一遍,就像彩色的图钉,一只只摁在脑中。
《落地的麦子不死》读后感(四):重复·记忆
我觉得看一些现代学者的作品时,还是应该分清哪些是经典之作,哪些是衍生或者重复之作。经典之作比如作者费尽心力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的书,就很可能会是作者一生中质量最高的作品(或者加上之一)。这本收在华师大策划的阅读张爱玲书系中的《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只能算是杂感的结集。可能只是作者经典之作的重复、衍生。再加上对这些“张派”传人,现在也不过是对朱天心了解一点,所以粗粗翻过,摘了几处。
“现代文学与文化的主流一向以革命与启蒙是尚。在这样的号召下,我们的中国想象莫不以开创新猷、与时俱进为前提……自鲁迅、茅盾至杨沫、浩然,现实及现实写作的意旨性(meaningfulness)及有效性(utility),总浮现于字里行间。相对于此,张爱玲一脉的写作绝少大志。以‘流言’代替‘呐喊’,重复代替创新,回旋代替革命,因而形成一种迥然不同的叙事学。我以‘回旋’诠释involution一辞,意在点出一种反线性的、卷曲内耗的审美观照,与革命或revolution所突显的大破大立,恰恰相反。”(《张爱玲,再生缘》)
“朱天心的爱走路,从《击壤歌》中的小虾漫步西门町、中山北路,乃至远征剑潭、士林已可得见。到了《古都》,她把走路的能耐与她的历史忧思合为一处,一步一脚印,真正出入在台北历史/地理之间。熟悉新马理论的评者可以再搬出本雅明的‘游荡者’(flâneur)来比附朱天心的伪观光客……与其说她是游荡者,更不如说她是个福柯(Michel Foucault)定义下的考古者。”(《老灵魂的前世今生》中四、当历史变为地理)
《落地的麦子不死》读后感(五):简单阅读指南
这是山东画报出版社张爱玲套书中的一本,全套包括:
《张爱玲的风气》(陈子善)
《记忆张爱玲》(陈子善)
《再读张爱玲》(刘绍铭)
《替张爱玲补妆》(水晶)
以及王德威的这本《落地的麦子不死》。
书名出自书中收录的一篇文章,副标题为“张爱玲的影响力与‘张派’作家的超越之路”,基本可以概括整本书的内容。相较于许许多多单独点评张爱玲,或者把张爱玲和另外某个作者一对一讨论的出版物,此书涉猎的范围相当广博,既讨论了和张同时期的文人,也剖析了数位后来的小说家对张式文风的继承和发展。
记住王德威是因为另外一本书:《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麦田出版社,大陆至今尚没有引进版。那是相当八卦的一本书,涉及很多革命时期女文人的情感故事,连带我对作者的印象也八卦起来。翻开此书才知道,人家是正正经经的文人,写起评论文颇有想法见地。
对于我这样一个业余的张爱玲爱好者来讲,这书是一次读不懂的。比如讨论张叙事学的这一段:“我以为这一冲动所构成的‘重复’(repetition)、‘回旋’(involution),及‘衍生’(derivation)的叙事学,不仅说明张腔的特色,也遥指其人的题材症结”。还有后面与之呼应的一段:“重复不只是有样学样而已。化一为二,对照参差,重复的机制一旦启动,即已撼动自名惟我独尊的真实和真理。重复阻挠了目的式论的动线流程,也埋下了事物时续延异、播散的可能。”
当然,虽然一次看不懂,但也不要被这些词句吓到,因为在提纲挈领的表明自己的观点后,作者继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论证他的看法。虽然我联系上下文许多次也不敢说自己真的看懂了,但它其实不是一本晦涩的书,特别是当针对张爱玲有感而发的上半部分结束,进入张派继承者的单独点评后,数篇文章都有很大的信息量和清晰的观点。如果对张派文风和类似的作者有兴趣,这是很好的阅读指南。王德威的风格在我看来就是活泼和严肃相得益彰,比如他在评须兰时称贾平凹的《废都》为言情小说中的一条新路,这个观点我相当喜欢。
为了更好的阅读领略这本书,以下为自行选择可提前做功课的作者,
白先勇 (《台北人》,《孽子》);施叔青(香港三部曲);朱天文,朱天心姐妹;王安忆(《长恨歌》);叶兆言(《夜泊秦淮》系列);苏童(《妻妾成群》,枫杨树系列);须兰,苏伟贞,黄碧云……
在和张爱玲同一阵线的作者之外,王德威亦把鲁迅,巴金,矛盾,丁玲甚至钱钟书与张做了参差对比,进一步说明张爱玲的文章对时代的看法和作用,之于我是相当有趣新颖的观点。
最后,以作者自己的一席话来概括我对此书的印象:
本文论张爱玲在过去数十年对台港大陆作家的影响,原无意“对号入座”,强作解人。影响研究其实是极虚构化的论证方式。从依样画葫芦到脱胎化骨,无可不为影响。所要强调的是,在张爱玲这样强大的影子下,一辈辈作家如何各取所需,各显所长……
我其实现在都不是很明白什么叫做参差,可能大概就是我读完亦舒的《我们不是天使》,接着看池莉的《生活秀》,然后想,原来这两个作者是一个风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