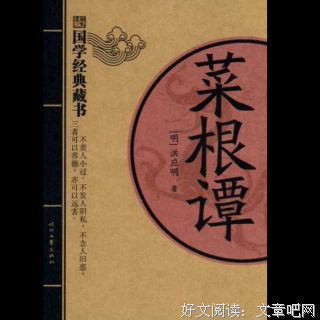《伍子胥》读后感摘抄
《伍子胥》是一本由冯至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2019-10-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伍子胥》读后感(一):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蜕变
个人觉得这是象征派最好的小说,明显受到了里尔克《旗手里尔克的爱与死》的影响,语言风格中也有学习鲁迅《故事新编》的成分。
作者选取了几个典型的地名为标题,截取了伍子胥逃亡路中的几个片段,通过他的内心独白及与其他相遇者的对话,细致地反映出了伍子胥逃亡途中心理变化(尽管是作者虚构的),充分展示出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在仇恨和颠沛流离中向现实主义转变的历程,这其实是抗战年代中国年轻知识分子在漂泊西南期间的心路历程。
除了诗意化的语言之外,这部小说另一大优点是作者虚构出的伍子胥与子产、季札之间单向的心灵沟通,把伍子胥心中的理想主义情怀具体地展现出来,《宛丘》一章也很有新意。
《伍子胥》读后感(二):命运多舛
提到伍子胥,首先让人们想到的就是他的掘坟鞭尸,这个人之所以对楚王恨之入骨,就是因为他一生中有一段生不如死的经历。他是春秋末期吴国大夫,同时也是一名有名的军事家。这本书很细致的记录了伍子胥的生前事迹,在那段历史中能够经历这些的必定会在历史中留下一个重要的地位。他是一个楚国人,但由于遭受到陷害,一家人被楚王杀害,伍子胥的身份也一落千丈,并且成为了通缉犯,本来生活已经没有希望了,还好最后找到了一个机会逃出了楚国。
后来的事情就发生在吴国了,在吴国之后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这本书刚好是把这段逃亡的过程写了出来,让我们看到了最为精彩的一段历史。冯至对于历史的敏感使他笔下的故事都很有戏剧性,且不说故事的真实性,伍子胥这个人的性格确实很符合。就是因为他的性格,才使得他最终的命运一直未被改变,哪怕是逃到了吴国,依然躲不了过去躲过一次的遭遇。
伍子胥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军事家,他的缺点就在于难于看透身边人的心,所以总是遭到陷害。其实最后看他的结局的时候有点像现在的电视剧,明明我们局外人觉得事情其实很简单,但偏偏伍子胥的好心得不到理解,最终还让人好心当驴肝肺,最后他的语言也成功了,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他再一次完成了复仇。
哪怕是在逃亡的路途当中,这一段也有很多戏,作者通过伍子胥可能经过的地点为题名,通过地图的形式叙述了这段经历。在这一路上,他遇到了很多熟人,通过第三视角了解到了更完整的伍子胥。他坚定的信念支撑他走下去,为了复仇,很多他本来身份不需要去承受的那些他都忍受了下来。虽然是从楚国逃了出来,但是逃亡之路并不比之前好过,哪怕是这样他也坚持着。这点就很值得后人去学习,当然不是为了复仇,而是化悲痛为力量,如果自己有目标,就要坚持不懈的去达到。这段历史才是最精彩的,这体现出来了一个完整的人性,后事如何早就已经有了结局,也就不用多说了。
《伍子胥》读后感(三):重构故人 ——《伍子胥》,代号化的人物 私人的感受
重构故人
——《伍子胥》,代号化的人物 私人的感受
讲起伍子胥,其实很多人对于春秋战国时候的这个现在都可以叫做“狼灭”的狠人,了解都不太深。毕竟那个时候没有照片,没有卧底纪实,没有侧面描写,就知道这样一个人,一夜白头逃出城,躲避追杀最后复仇。伍子胥在春秋战国的史书当中也不过寥寥数笔,这寥寥数笔已经是他的极限了,因为还有更多的芸芸众生没有这样的寥寥数笔,刻在竹简上的文字,能承载的东西有限。
但是和现在饱受各种鄙视的同人文不同,对于历史的书写,我们曾经有一种讲法叫做“演义”,让这些历史上的人物,都鲜活的出现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当中,同时,也让这故事活在了听故事的人的心里。
冯至先生的《伍子胥》就是更加细致刻画了心里活动并且穿插各种史实的“演义”,在不违背原有人物的个性的同时,进行了扩充和重构,让他在历史里面讲起话来,这个时候,伍子胥又仿佛从一哥没有生命的代号化的人物,化成了读者私人的感受。
他会写他逃出楚国的仓皇,路上军士的模糊的身影,尚且茂密的森林和仿佛消失了的城市。他遇到了好心的渔夫,他从竹简上面下来,说了一句“朋友”,就此让一个莫名渡江的空缺的背影,有了属于他的名字;他还见过浣衣女,被省略的湖泊和池塘里面的水也突然流动了起来;他走进了吴市,市场上有一个艺人,在提供音乐,让人感受到了生活的美,他想起的“举报”的武器也不禁放下了,因为他被感化了,那一瞬间,忘记了仇恨……
这似乎是一个合理化的伍子胥,他符合那个故事,但又不仅仅是伍子胥,颠沛流离的冯至先生,在经历抗战的至暗时刻的时候,也是在这样守候光明的吧。一路上他见过毁灭,见过相互救助,见过坚守,见过依旧保有美丽心灵的人……于是他为这些可能在历史上也留不下名字的人塑造了属于他们的人物,这个历史又不仅仅是这个历史了,他在书当中,又活了第二次。
“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他也想不到后来有些人的“在路上”会是无意义的放纵,是反叛。在冯至先生的“在路上”,他一直相信前方有一盏灯,他经历的磨练和坚守就会像伍子胥一样充满了意义。他后来“捏造”的两个偶遇,其实只是在历史的夹缝中,加入了无殊的可能罢了,也许在某个时空中的伍子胥,也能够对那可怕的“陈国故人”机智逃脱吧。
所有历史,不过都是当代史罢了。
y 林怿
2020-4-4 22:46:28
写于御庭园
《伍子胥》读后感(四):逃亡路上的故事
说到伍子胥,不少人听说过“伍子胥过昭关须发皆白”的典故,很多戏曲中也都有演绎。虽然我知其人,但对他的功绩、故事知道得还是甚少,此次借冯至冯老的《伍子胥》这本小书对伍子胥这位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做一番系统的了解。
书中的目录设置为伍子胥生平中所关联的九个重要地名为章节标题,九个地方,是伍子胥来到吴市前走过的几段关键路程。原本他想和兄长扎根城父,过一方平静舒适的生活,但是动荡的局势、偌大的楚国却容不下他们,兄长决意奔赴故里郢城和父亲一道,这是云寻找死,而伍子胥远走他乡去求生。此后,他一路经过林泽、洧滨、宛丘、昭关、江上、溧水、延陵、最后到达吴市。这奔波逃亡的行程,记载了一个向死而生的伍子胥的意志。
历史上的他功过纷议,身负家仇国恨,他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报父兄之仇,在世人看来过激且暴虐;他是影响吴国兴亡的关键人物;他屡次劝谏吴王夫差杀勾践,夫差不听,直至后来吴王听信谗言,令他自杀时,他对门客说在他死后把他的眼睛置于东门之上,他要看着吴国灭亡。伍子胥一语成谶,他死后九年,吴国被越国所灭。
虽然这本《伍子胥》里并没有写他后来进言、被吴王误会、以及被逼自杀等事,但是从这前面逃亡投吴的历程中,从伍子胥的言行里,我们已然能看出他这个人的性格和信念。他性格刚烈,视复仇为终极目标。在当年父亲被囚之时,兄弟二人所做的选择可见,伍子胥是一个相对理性的人,他自己做什么事做了也是白做,他选择逃亡、活下去,才能为父亲报仇,而不是直接去送死。他能隐忍,他的一生忍辱负重,他是有敏锐的政治眼光的,只可惜吴王昏庸,一代英豪死不瞑目。
再看冯老的这本《伍子胥》小书,写的是客观通达,让人仿佛穿越至那时,一路跟着伍子胥去走他所走过的的路,和看他所经历的事,以及在这逃亡的过程中他的品行展露。他是个知恩图报之人,离了昭关,在江上,他要将自己的宝剑送给渔夫留作纪念,以示对他的感恩。
冯老的文字是很有魅力的,不仅在于对伍子胥人格的客观展示,还有对这一路上景象的描写,以及景与人物心情的对接、投射。在溧水,
“寂静的潭水,多少年只映着无语的天空,现在忽然远远飞来一只异乡的鸟,恰巧在潭里投下一个鸟影,转眼间又飞去了:潭水应该怎样爱惜这生疏的鸟影呢。——这只鸟正是那挟弓郑、楚之间,满身都是风尘的子胥。”伍子胥的孤寂谁人能懂?冯老是一定懂的!世间英雄无数,能如此朴实地讲述一个历史名将的书很难得,好好读读会让我等对伍子胥认识更多、更深入。
《伍子胥》读后感(五):诗人历史小说中的伍子胥
或许是“卧薪尝胆”这个故事太过于深刻了,之前我对于伍子胥这位历史人物的印象,总是停留在吴王夫差受奸臣谗言,命他自尽的那一段。临死前他曾对门客说:“请将我的眼睛挖出置于东门之上,我要看着吴国灭亡。”或许是这一段故事中这句话太过于悲烈,让我全然忘记了他在进入吴国之前的另一段往事。
他本不是吴国人,他的故乡原本是在楚国。父亲也是朝中重臣,一场变故却使他一夜之间失去父兄,只能只身一人逃离楚国前往吴国。这本由中国现代文坛代表性作家冯至所著的经典小说《伍子胥》,讲述的就是伍子胥由楚国前往吴国时的那一段逃亡的经历。
此段故事无论是在正史还是野史中均有记载,并且也算是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只是史书上所记载的终究不过是寥寥数百字,只能够大致讲述出当年的事情大概。若想进一步的感受历史人物当时的实际遭遇与心路历在此之前程,怕还是得由这些历史小说来完成的。
千百年前的时代不可能有岁月的光影流传下来,我们不能亲身邂逅那些历史故事中的人物,也不可能具体知道那个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场场、一幕幕,只能够从史料的记载中寻得蛛丝马迹,从历史小说家的笔下感受人物的真实情感。
历史小说这东西,说好写也好写,说不好写也不好写。好写是因为原本就有历史的框架摆在那里,照着样子将故事大致复制讲述下来就好。说不好写,那是因为这些故事往往被人们太过熟悉,想要不流于俗套写出新意,并且不被读者诟病为胡编乱造,也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冯至先生用他手中的那支笔将伍子胥那段颠沛流离,惶惶不可终日的经历生动的讲述了出来。那个时代的作家,讲究的是严谨求真,写文章是要求有根据且符合逻辑的,绝对不可能出现为博人眼球而胡说八道的可能性。冯至先生是学者,更是一位诗人,《伍子胥》一书虽然是历史小说故事,但却能够让人从创作的言辞中隐隐感受到一种现代诗歌的意境。这也为伍子胥的这一段经历的讲述,增添了不少悲壮的氛围。
伍子胥他因为一段“谗言”而被迫来到吴国,在此取得了为父兄报仇的机会,也成就了自己的功名利禄。可后来也是因为一段“谗言”,他失去了在吴国往昔的一切,甚至还有自己的生命。或许他的一生,注定是与那些佞臣小人绕不开的。
后面所发生的那些与“卧薪尝胆”有关故事,在我看来其实更加的让人感到叹息悲凉,但冯至先生并没有将其改编创作成小说。虽然“假如”这种事情对于过去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我还是很好奇,如果冯至先生当年有兴致将这一段故事进行改写创作,将会又是怎样的一个故事。
《伍子胥》读后感(六):冯至写子胥的孤愤
(文章刊于《长江日报》2020.12.1,有改动)
文/俞耕耘
太史公写《史记》,最想抒发“孤愤”。大概真正的愤恨,多是孤寂,如暗夜踽行,唯有独自负重。最贴合这二字的,一是屈原,二是子胥。两人又有大巧合:都是楚人,皆去国怀忧,成了千古悲剧。冯至先生的小说《伍子胥》,在抗战期间完成,成了感时忧国的精神寄寓。“当抗战初期,我在内地的几个城市里流离转徙时,有时仰望飞机的翱翔,我也思量过写伍子胥的计划。可是伍子胥在我的意象中渐渐脱去了浪漫的衣裳,而成为一个在现实中真实地被磨炼着的人”。
也许和鲁迅写《故事新编》心境一样,冯至渴望在历史的老干上开出新芽。国人在抗战时的流离失所,痛苦迷惘,家国之恨,都在伍子胥身上得到映射。离乡是为了更好的归来,那种坚忍与克服,是人生和历史中的分量。作家写伍子胥,正赋予忧患中人一种超拔的现实感。伍子胥的流亡,其实是民族心灵之写照。“不管是为了爱或是为了恨,不管为了生或是为了死,都无异于这样的一个抛掷: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
小说中,伍子胥和伍尚面对父亲被囚郢城,楚王设套诱捕,做出了生死抉择。作家将其上升到永恒的戏剧矛盾:一个是赴死,一个是求生;前者成全忠孝,后者为报父仇。这就像伯邑考和文王父子的两种选择。冯至深刻洞察出,子胥兄弟是一种相互成全,它是民族价值义理的一体两面,既合二为一,又一分为二。哥哥的死,赋予弟弟生命以重量,引长了其人生道路。“谁的身内都有死,谁的身内也有生;好像弟弟要把哥哥的一部分带走;哥哥也要把弟弟的一部分带回。”
一个理想主义者,如何变成现实主义者?伍子胥的流离出奔,逐渐远离了那套礼乐为代表的理想,父兄之仇就像石头一样压在心头,让他永无停歇、无法逃避。有意味的是,冯至只写伍子胥入吴,却不写面见吴王,如何复仇,含恨身死的悲剧高潮。或许,冯至只想描摹悲剧的肇始与根源,并不愿陷入机械的历史复写中。作家“索性不顾历史,不顾传说,在这逃亡的途程上又添了两章:宛丘与延陵。”
从入郑陈,折返楚地,出了昭关,过江入吴。伍子胥与孔子周游,有某种相似,都历经了衰颓凋敝,都不知何处是归,无以为据。小说中,子胥对郑国子产已逝,无从得见,无限怅惘;对吴国季札美德,虽是仰慕,终未寻访。这正是伍子胥对道路的坚定选择。他的人生不允许偏离,说服吴王,洗冤复仇才是唯一主题。因而,伍子胥有无人理解的困厄与孤独。太子建,变成狭隘的阴谋家,好友申包胥,则成了熟悉的陌生人。“他们将要各自分头去做两件不同的大工作,正如他们在儿时做过盖房子的游戏一般:一个把一座盖得不满意的房子推翻,一个等待着推翻,然后再把它从新恢复。”而这房子,正是楚国。
在子胥看来,林泽中洁身自好,并不能长久到老,终将幻灭。楚狂与他,虽有贯通之处,但又格格不入。季札观乐,墓前挂剑,他只是仰慕,却不会有浪漫闲心,问礼乐之事。渔夫与他的心境,更加不同。“子胥深感又将要踏上陆地,回到他的现实,同时又不能不和那渔夫分离”。溧水的浣纱女子,也只能捧出一碗饭,给他一个休憩停顿的瞬间。这些人物,都可视为子胥面临的一系列选项。是选避祸山林,还是礼乐理想;是渡去仇恨,还是沉溺温柔?这也许是冯至在抗战背景下,反映焦虑痛苦的大隐喻。救亡才是唯一的主题,闲适隐逸,都将是逃避退缩。
《伍子胥》读后感(七):伍子胥仕吴之前
由楚到吴,伍子胥复仇的故事已经为人所熟知。为了给受费无极谗害、和自己的兄长一同被楚平王饮杀害的父亲报仇,伍子胥走上了复仇之路。他当然需要帮手,或者说首先需要一个立足之地,需要能帮他复仇的力量。最终,他找到了吴国、找到了吴王阖闾,而且当时吴国还有写出了《孙子兵法》的孙武。可想而知,伍子胥的复仇终究是成功了。故事到这里本应该结束就刚刚好。复仇之后,伍子胥见好就收,找个地方隐居是最佳结局,反正吴王是肯定不想让他另仕他国成为劲敌的。但是伍子胥还是待在吴国,并最终因多次劝谏吴王夫差杀勾践却反被诬陷企图投靠齐国反吴,被迫自杀。按理说,这个家伙还是挺有见识的——伍子胥自杀前对门客说:“请将我的眼睛挖出置于东门之上,我要看着吴国灭亡。”伍子胥死后9年,吴国终为越国所灭。
伍子胥的最终悲剧,就在于他没有看清楚形势,不知道君王们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他是忠臣,既受了吴王阖闾、夫差的信任,就投桃报李,也实打实地干活,做了一个臣子该干的事。他却没想到,自己在吴王心里其实只是一个外来者,只是来干活的,连土生土长的吴国人都不是,凭什么还要告诉吴王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呢。君王心里想的事太多了,他不需要时时事事听别人在那儿说三道四。所以,伍子胥的死也就在所难免,而且他死得很不甘心,所以他要人将他的眼睛挖出置于东门之上,说是要看着吴国灭亡。他确实证实了这一点——他能看到这一点又如何呢?!
这些故事,《史记》《左传》《国语》《吴越春秋》等史书中以及野史笔记里已经讲过很多遍,由之产生的演义也已经很多,姑且不论。而诗人冯至要想讲好伍子胥的故事,肯定需要动些脑筋。他“瞄准”的是伍子胥从楚国逃亡到最终入吴市这期间的经历以及心路历程,最终也呈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关于伍子胥的故事,足以让人眼前一亮。
伍子胥兄弟俩对父亲的感情确实不一般,但他俩的个性不同。怎么说呢?伍尚有点儿愚忠、愚孝,“父亲召我,我不能不去;看一看死前的父亲,我不能不去”,明知道去了有什么后果,他还是要去;只不过,他也知道伍子胥的心意,“你还要一步步地前进”。兄弟俩作出了不一样的选择,而伍子胥从此也踏上了逃亡之路。
为吴所用之前,伍子胥显然经历了太多。冯至在《伍子胥》这个中篇小说中,分别以伍子胥可能经过的地点为题名,首先是郢都外的“城父”,接接着是两处水域“林泽”和“洧滨”,随之是两处陆地“宛丘”和“昭光”,接着又是两处水域“江上”与“溧水”,最后则结束于另两处陆地“延陵”和“吴市”。由“陆”到“水”又到“陆”又到“水”最后归于“陆”,具有一种回环之美,但更多地是为了预示什么。而在这个过程中,狂人问伍子胥:“今天,你能不能暂时把仇恨和匆忙放在一边,在我的茅屋里过一个清闲的夜呢?”他深知伍子胥的内心深意,只是没有点破。而在郑国听到了子产的故事,在陈国见识到了楚国的影响,在吴国延陵拜访了季札的墓地……就在这个过程中,一步步地强化了伍子胥的坚强内心:他把父兄的仇恨看得比什么都重,宁愿为它舍弃家乡、舍弃朋友、甚至舍弃生命。这样来看,最后在吴国,终于报了仇之后,实际上那个时候伍子胥显然已经无欲无求了,死也算不了什么——那个时候,伍子胥的内心已经平静下来了……
总而言之,冯至讲了一个很别致的关于伍子胥的故事,虽然看似一路奔波,却很有收获。这个收获,既是属于伍子胥本人的,很显然也是属于每一个读者自己的。
《伍子胥》读后感(八):卞之琳丨诗与小说:读冯至创作《伍子胥》
《伍子胥》写于七十多年前(1942年冬),影响深远。
作者冯至曾经两度酝酿《伍子胥》的写作,虽然都是受到里尔克《旗手》的触发,但在经历过抗战的流离后,他写出来的作品已经与散文叙事诗完全不同了。他在《后记》中说:
当抗战初期,我在内地的几个城市流离转徙时,有时仰望飞机的翱翔,我也思量过写伍子胥的计划。可是伍子胥在我的意象中渐渐脱去了浪漫的衣裳,而成为一个在现实中真实地被磨炼着的人。冯至在吕根岛,又想起写《伍子胥》文学史家钱理群曾经这样评价冯至:
《十四行集》《山水》《伍子胥》堪称冯至的‘三绝’:这‘生命的沉思’,提供了不同于他人的另一种战争体验,并且以其艺术的完美、纯净,特立独行于四十年代,以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之林。与书友们分享诗人、翻译家卞之琳的书评:诗与小说:读冯至创作《伍子胥》。
诗与小说:读冯至创作《伍子胥》
原载《冯至先生纪念论文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冯至与卞之琳卞之琳(1910—2000),人在风景中的诗歌琢玉者,“汉园三诗人”之一。江苏海门人。师从徐志摩,深受赏识,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诗歌流派"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的诗精巧玲珑,联想丰富,跳跃性强,尤其注意理智化、戏剧化和哲理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的内容并进一步挖掘出意料不到的深刻内涵,诗意大多偏于晦涩深曲,冷僻奇兀,耐人寻味。代表作:《三秋草》《鱼目集》等。二千年前,春秋末期,伍子胥的出亡故事,从城父到吴市的一段,在少年冯至的天真眼光里已似“天空中的一道虹彩”(《伍子胥》后记,《冯至选集》第1卷,第369页);冯在小说正文里也就用过“彩虹”的比喻,说“渔夫的白发、少女的红颜,只不过使子胥的精神得到暂时的休息,是他视界里的一道彩虹”(《伍子胥》第八章,《选集》第1卷,第358页)。原始故事的传说梗概与细节以纷陈的色彩,历见古人正史和稗史的记载,到近代还片断见诸旧戏舞台的表演,熠熠生辉。
冯至的这个比喻,似更适用于他自己在中年(40年代初)用这个历史传说写成的《伍子胥》。它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虽不像一些皇皇巨著“红火”一时,独放的异彩,却也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冯写出这部中篇小说以后,在说了原始故事像一道虹彩以后,紧接着自称当时看这个故事已“好似地上的一架长桥”。
冯晚近回忆说:“我在1942年终至1943年春写的《伍子胥》可以说是一架桥梁,它一方面还留存着一些田园风光,一方面则更多地着眼于现实。”(《立斜阳集》,第132页,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两道“弧”分别“负担着”“所应负担的事物”。我看《伍子胥》的创作则是兼挑了两道“弧”的重担。
昆明郊区杨家山的林场茅屋,冯至在此创作了 《山水》《伍子胥》《十四行集》等重要作品我曾混用了冯先生看待伍子胥故事的虹与桥的弧形喻象,把他在昆明二三年里相继写出的《十四行集》和《伍子胥》并列(当时还连带了冯加进几篇新作构成的《山水》散文集)说是一道“弧”,“在他艺术创造历程上,即不算顶峰,总还是突出的一道‘弧’,一弯彩虹。
《伍子胥》的写作,也就像这个小说主人公的过昭关,从一个境界过渡到另一个境界”(见我写的短文《忆‘林场茅屋’》,香港《诗双月刊》,1991年《冯至专号》,第27页),我现在想加上说“一种蜕变”(冯在《伍》正文昭关章也用了他素来爱用的蜕变喻象比了过昭关,见《选集》第1卷,第343、341页),特别有意义;而从相辅相成的《十四行集》也可以得到一点阐明。
冯至在他的《十四行集》的第二十七首即最后一首,作为尾声也有点像总结的样子,又用出了二合一的喻象,“水瓶”与“风旗”,先说“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取水人取来椭圆的一瓶,/这点水就得到一个定形;/看,从在秋风里飘扬的风旗,//它把住些把不住的事体,/让远方的光、远方的黑夜/和些远方的草木的荣谢,/还有个奔向远方的心意,//都保留一些在这面旗上。……”(《选集》第1卷,第149页)。
他到盛年借了里尔克较为松动的变体十四行诗的“定形”表达了自己的创意,而他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作出了一个抉择,企图用历史传说的框架“把住些”捉摸不定的感受,使这些感受也得以自在舒展(参看《伍子胥》后记,《选集》代序,《选集》第1卷,第370、20页),亦即以之“定形”。
手迹十四行诗《深夜又是深山》十四行诗,又译“商籁体”,是对英语Sonnet的音译。十四行诗是欧洲一种格律严谨的抒情诗体,有点像中国古代的格律诗。十四行诗最初流行于意大利,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诗人彼特拉克的创作使其渐渐趋于完美,所以又称“彼特拉克体”。
冯少年时代喜欢伍子胥故事,深受感动,并非有什么个人的切身经历可以引起对伍的深仇大恨特别的共鸣,若说有共同的忧患意识,则无非是当时人民都难免地感到社会现状的不公平,至多像小说正文里也提到的对于“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之类的义愤(《选集》第1卷,第342页)。
关于伍子胥的传说故事,作为青少年,冯所神往的主要是浪漫色彩的这个出亡人物和“江上的渔夫、溧水边的浣纱女”这样优美的“遇合”;“昭关的夜色、江上的黄昏、溧水的阳光”这样的诗情画意在他都曾经像音乐萦回脑际却并没有“把住”(《选集》第1卷,第20、370页)。这是说他还没有足够的自己从现实生活中来的新的感受以充实那些飘逸的幻象与画面。只有日久从大千世界积累够了新的体验,他才像偶然间一有际遇,便“把住”了这些古远的霞光云影,赋与了自有特色的美学和哲学意义。
时代前进,人类的思想感情也随之复杂微妙化,在文学体裁中已不易用本来单纯也单薄的诗体作为表达工具,易于单线贯串的长篇叙事诗体在高手或巨匠手中也不易操作自如以适应现代的要求。
从青少年时代以写诗起家的文人,到了一定的成熟年龄(一般说是中年前后),见识了一些世面,经受了一些风雨,有的往往转而向往写小说(因为小说体可以容纳多样诗意,诗体难于包含小说体所可能承载的繁伙)。他们既不满足于19世纪拜伦和普希金那样写诗体“小说”,进而也不满足于20世纪初年诗风正在转变的里尔克写《旗手克利斯托弗・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那样的散文叙事诗。他们真像要所谓“屏除丝竹”就用散文体写小说,其中也不乏写出了成功的长篇小说的实例(虽然写出的还不一定像小说家的小说)。
《伍子胥》,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再版冯至写起了中篇历史小说《伍子胥》,基本上也合乎这种规律。他早年也是从写诗入手的,可是有所不同,他一开头也就写出过三首受人注意的叙事诗,带有梦幻色彩、神话传说色彩,而且还用散文写出了两个成功的短篇“历史故事”。
他在1928年二十三岁的时候(根据他在1944年写《伍》后记所说的“十六年前”推算),第一次读到《旗手》,“就被那一幕幕的色彩与音调所感动”,当时就想,“关于伍子胥的逃亡也正好用这样的体裁写一遍”(《选集》第1卷,第370页),写一篇“叙事诗或小说”(《选集》第1卷,第20页),后来在30年代游学德国假期泛海旅行中,在抗战初期随工作单位内迁,在几个城市里流离转徙中,屡次动念想写,总没有下笔(《选集》第1卷,第370、20页),直到1942年借偶然的机会(我修订旧日从法文转译的《旗手》请他帮助用德语原文校看一下)出于“一时兴会”,才像“狂风乍起”一下子写出了“城父、林泽、洧滨、昭关、江上、溧水、吴市七章”(《选集》第1卷,第370页)。随后又因为自认把这段逃亡故事写成了“含有现代色彩的’奥地赛’……索兴不顾历史,不顾传说……添了两章:宛丘与延陵”(《选集》第1卷,第371页)。这样,整段伍子胥的出亡故事在冯至的冶炼下,获得了许多新的内涵,成了完美的艺术品,别具简练的魅力,处处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世界上成文的历史,出于人手,都不可能是人类历史完全如实的记录(照相也有角度不同等造成的差异)。中国古人笔下的史籍自然也难免有许多地方与神话之类难解难分(原始社会人类生活和思想方式本来也多近于此)。我们文明古国的各种史乘中自有不少古拙可爱的佳话懿行的流风遗韵,尽管总有种种避讳,也自透露了不少丑恶、残酷和野蛮。孔子作《春秋》,在简单纪事中也自存褒贬,而讲仁义礼仪、温柔敦厚的他这位圣人,也会把动辄开杀戒视为等闲。经典如司马迁的杰作《史记》显然有意无意中也会有所疏漏,有所掺杂。赵晔所著的《吴越春秋》则是小说家言,杂凑词书中的伍子胥传说,增了些声色,也加了些荒延。冯至从这些历史文献中取材写他的《伍子胥》,都有所依据,只有宛丘与延陵两章,进行了他所谓的“捏造”(实为进一步艺术加工),但是伍“从那两个地方经过,也不是不可能的”(《选集》第1卷,第371页)。这样冯取历史“定形”创作小说的艺术过程中也就提炼了历史,并给历史加了不少可为今用的调味。
正因为冯至选择了伍子胥出亡故事中从城父至吴市的一段行程,恰当处理了一路上可能遭遇的美与丑、善与恶(《选集》第1卷,第20页),点明了小说主人公的刚毅素质,与整部小说的情调一致,与小说主人公的基本性格相符,就免于着笔写以后有关的种种耸人听闻的事件,不是隐瞒而是涵盖了它们,正如小说中提到的伍子胥张弓吓退了追捕的楚兵,引而不发。传说中的一些突出事件,主要是伍子胥终率吴师攻入楚都郢城,因楚平王已死,就掘墓鞭尸三百,最后又是自己受谗人陷害,在吴王夫差不听忠告防越,反报以赐死面前的激昂陈辞,要求死后把眼睛挖悬吴都城门以观越军入城之类的壮烈或惨烈,都免于涉笔了。至于《吴越春秋》里增加的声色和迷信以及无稽的节外生枝,小说里更严加选择,小取大舍。例如江上渔夫,渡伍过江后的自沉,浣衣女子,应伍乞食后的投水,都不但无端或者庸俗,而且隐寓陈旧的伦理观念或带狭隘的市井眼光。
冯至与梁遇春根据冯至喜爱平凡中出奇的艺术创作倾向,不但撇开了渔夫拒绝报酬而还一提代价的铜臭渍斑,而且点缀至伍子胥受吴季札为友人墓上挂剑佳话的启迪,拿他佩带十年的家传宝物的一把剑捧给渔夫,得到的回答是:“你要拿这当报酬吗?我把你渡过江来,这值得什么报酬呢?”作者还设想:“渔夫的生活是有限的,江水给他的生活划了一个界限;他常常看见陆地上有些行人,不知他们为什么离乡背井要走得那么远。既然远行,山水就成为他们的阻碍;他看惯了走到江边过不来的行人,是多么苦恼!他于是立下志愿,只要一有闲暇,就把那样的人顺便渡过来。”(《选集》第1卷,第351页)渔夫没有自沉,只是“拨转船头向下游驶去”。伍独立江边,望着那只船越走越远了,再一看他手中被无名渔夫拒受的剑,“觉得这剑已经不是他自己的了:他好像是在替一个永久难忘的朋友保留着这只剑。”(《选集》第1卷,第351页)这就纯化了、淡出了这个场面,使之更近情理也更具诗意。
冯至处理本来就富有诗情画意的伍同浣衣女子的遇合、乞食、奉食,整章都在“你”和“我”,“取”和“与”的关系上作了哲理的抒情。这个好像亘古初醒的天真女子施舍给一个远方来的生疏男子一钵米饭,想像“这钵饭吃入他的身内,正如一粒粒的种子种在土地里了,将来会生长成凌空的树木。这画图一转瞬就消逝了,——它却永久留在人类的原野里,成为人类史上重要的一章”(《选集》第1卷,第355页),即此一例,可见整章小说的色调。而所舍弃的《吴越春秋》所写这个女子随即投水自尽,则显然更具后汉时代作者的一点封建意识,对于这个亲切的哲理抒情场景,自然成了外加的污染,不能相容。
传说故事中直接或间接有关的人物,也有所屏舍(不让出场,只是提说),有所增益(虽不出场,而着意渲染)。冯至直接写到专诸,写出了他的本色、叨光伍子胥这段行程的恰好完结,免了张扬紧接上来的刺王僚的血腥场面,在林泽的楚狂家里伍也与出场的申包胥打了照面,而且和这位旧友不寐谈心(三人都不满腐败的楚王朝而取三种态度:楚狂的遁世,伍子胥为反抗出行,申包胥为了避免朝廷上谗人的锋芒,对内政不闻不问,偏重外事活动,奔波在外)。申的意志坚强也点出了,也点明了两人“将要各自分头去做两件不同的大工作”,也叨光了故事行程的适可而止,免写了申后来痛哭秦庭,请兵救楚的轰动铺排,只是轻描淡写了一句:“正如他们在儿时做过盖房子的游戏一般:一个把一座盖得不满意的房子推翻,一个等待着推翻,然后再把它从新恢复。”(《选集》第1卷,第323页)冯在小说中也常有这样微含嘲世意味而不露针芒的幽默笔触。
迫使伍子胥出亡的元凶,谗臣费无忌,在冯著小说里也没有出场,只是在笼统叙述中一笔打发了:“这个在伍氏父子的眼里本来是一个零,一只苍蝇似的人,不知不觉地竟忽然站立起来,凌越了一切,如今反倒把全楚国的人都看成零,看成一群不关重要的飞蝇了。”(《选集》第1卷,第311页)伍子胥所景仰的一些历史人物中,郑国的治国贤臣,未及亲见,只从叙述他死后的众口交誉中,也与在郑国亲见一面的逃亡在那里的太子建堕落的形象对比中突出了他的操行。至于小说中伍子胥显然最钦佩的吴季札,也没有出场,但是在伍诸多的言行中烘托了他的风采,甚至以《延陵》整章在当地群众的普遍称誉中突出了他的风范,以至亲自想去登门求教而终碍于自身所负的不同重担而未去叩门。
小说对伍子胥传说故事的一些细节进行了近情理的改动也别具意义,例如一方面既在“浣衣女子”的场合,删去投水这个意外,屏除了可能隐含的不良暗示,另一方面根据传说写吴市城厢区专诸在家门前骂街,甚至拔刀要动武,由门内女人一喝就乖乖回屋,引起对立群众讪笑一场中,把《吴越春秋》里说这个女人是这条汉子的妻子改为老母,这也就免除了予人以勇汉惧内的庸俗化口实。
冯至在还没有对现实生活积累相当足够的体验与感受的时候,写不出自己的《伍子胥》小说(写出来也一定会是另一副样子),反过来,他动手把伍子胥出亡故事注入了更多诗意和深沉的寓意,加以一清如水的抒发中,也就处处揭示了写作当时(抗战期间)所谓“大后方”“眼前的现实”(《选集》第1卷,第20页)。这些当时大家耳闻目睹的腐败现象充斥了《伍子胥》小说中,但都像经过艺术升华作用,或者起了艺术“间离”作用,不再令人难于直面了,例子也不胜枚举。《昭关》章中写楚国的士兵害病将死而还有一口气的时候就被抛在外边“让他那惨白无光的眼晴再望一望晴朗的秋空”,“他还有气没力地举起一只枯柴似的手来抵御”渐渐接近他的“乌鸦和野狗”(《选集》第1卷,第344页)。这不是出于凭空的想像,而是生动的写真:当时昆明人大家都知道郊外路旁就有过从四川“拉”来的病倒“壮丁”被这样抛弃的,也作出过这样的姿势!
全书对于众多人物与事件,如前举若干例那样,进行了诗的处理,炉火纯青的语言也就在冲淡中见隽永的醇味。早年冯至初读了里尔克的《旗手》,向往写一篇类似的叙事诗或小说,因为时移世易,自己的思想和心情也变了,十六年后写出的《伍子胥》小说,“也没有一点相同或类似的地方”(《选集》第1卷,第371页)。的确,全书没有一贯的诗以至散文诗的较为整饬的节奏。当然散文写得好也自有散文的节奏,但是散文小说《伍子胥》的现代而有点古拙可喜的语言中也随诗情诗意闪出整饬的诗节奏。(附带说一句,正因为这部小说重要表达方式是通过著者的叙述描写,语言自然,避免了现代历史话剧、历史电影剧使古装人物学古人说话、不文不白、矫揉造作的腔调)
例如小说中叙述伍子胥那天晚上决定出亡的一刻,说“他觉得三年的日出日落都聚集在这一瞬间,他不能把这瞬间放过,他要在这瞬间做一个重要的决定”(《选集》第1卷,第313页,冯常用的“抉择”、“负担”,还有“把住”这个实际上把“抉择”与“负担”合并为一义的用词,似乎正符合存在主义哲学的语汇),紧接在前边的伍子胥的说白:“壁上的弓,再不弯,就不能再弯了;囊里的箭,再不用,就锈得不能再用了。”这就是道地诗节奏的一闪现。这种语言与节奏,在所引诸例中,也就足见一斑。而全书最后一段描写伍子在吴市吹箫(《选集》第1卷,第366-368页)就成了多种形象、情调、色彩与声音融汇在一起的一篇散文交响诗,达到了高潮,也正给全书作了恰当的总结(可惜这里不能全引)。
我在这里只有总结一句:冯至文学创作,由写诗一度转入用散文写历史小说,既有意对我国以一则经久的传说为典型的历史进行了精致的艺术性提炼,也在无意中符合了现代世界严肃小说的诗化亦即散文化(不重情节)这样的创作潮流。
1992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