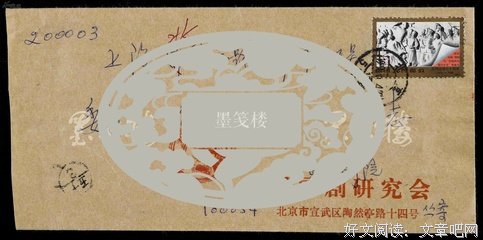《昆曲日记(修订版)》读后感锦集
《昆曲日记(修订版)》是一本由张允和著 / 欧阳启名编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页数:9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昆曲日记(修订版)》读后感(一):读后一些建议
一些建议和勘误,希望出版社不要生气。
1. 第一页允和照片下的出生年份误写为1901年,应为1909年。
2. P899 合肥张家世系简表里中 充和的出生年份误写为1914年,应为1913年。
3.前面的照片不少是大合影,下面标示的人名很难对得上照片里的人。如第三张照片,即周有光的右页,说是“从左至右从上到下”,如果不是非常熟悉的人,根本无法把名字和人对上。伊克贤到俞平伯(可以认出)中间有4位,但我各种数法,也无法准确数出4人。建议以后这样的大合照,人名按照片上人物的位置而排列,现在电脑排版很简单的事。
5. P153页9月10日 里面的 “9月8日在袁敏宣的母亲家唱了一台戏----开始的一段,到下一页的9月9日丁西林茶叙。” 我感觉应该是1956年9月10的日记,而不是现在所排的1957年。几个旁证:
A.1957年7月28日记载去袁家给老太太八十一岁生日祝寿,只有华粹深和允和,并未唱戏。
. P793页 有1956年9月9日丁西林请俞平伯周有光二队夫妻茶叙。不是在1957年。
C. 1983年12月4日的日记里记载1956年袁二姐家彩排(老太太生日)。
6. P155 9月13日 里面9月12日也不是1957年,而是1956年。其中给胡忌的信提及的9月8日彩排,应该就是1956年9月8日为袁母八十大寿的堂会。这时应该不需要给胡忌写信介绍北京曲社情况了,因为胡忌1957年4月已到北京工作,他们经常见面。见1957年4月19日的日记。
《昆曲日记(修订版)》读后感(二):读张允和 《昆曲日记》札记 之二 曲社小友
日记里经常出现的曲社三个小社员:胡保棣和许宜春许淑春姐妹。一曲小《游园》大获好评。
胡保棣是随着母亲爱上昆曲,许宜春许淑春姐妹是跟着爷爷而许宜春许淑春姐妹。昆曲的,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总是第一的。
图1是允和《昆曲日记》里和小曲友有关的部分。
图6是1960年16岁的胡保棣,和沈盘生在北京昆曲研习社演出《春香闹学》。
《昆曲日记(修订版)》读后感(三):读张允和《昆曲日记》札记 之一 张家父亲
读了张允和的《昆曲日子》,60万字很快看完。允和说她父亲曾经带着他们姊妹乘一叶扁舟,跟随江湖上的奇妙船队,昆曲传习所的“青龙”船,到处看戏。这样的父亲,不是为了在起跑线上的赢,而是给了孩子一辈子的爱好和快乐。传字辈的青龙船从苏州阊门解缆,从年初一到腊月底,沿太湖而行,一个又一个的码头。在江南的绿水里,船外的月光,舱里的牡丹亭,小人儿在窗边,听笛声清扬,摇橹声声,秋虫唧唧,这样童年,真是姹紫嫣红。
1957曲友们在北海公园漪澜堂晚宴,画舫唱曲,画舫上还要写上“昆曲晚会”,最怕人说是绍兴戏。下得画舫又上山继续拍曲,真是风雅极了。少年时羡慕大观园里的诗社,现在又让允和他们的曲社迷住。
1960年9月14的颐和园,张允和和周铨庵一人带一条船,在知春亭集合,泛舟昆明湖上尽情唱曲,从早晨到夜幕,曲终人不散,这样的雅集,再也没有了。
《昆曲日记(修订版)》读后感(四):兴亡梦幻,悲伤感叹——昆曲日记阅后琐碎
允和先生的《昆曲日记》再版,得到毛边精装本,十分喜欢,只是不大会拆,弄得坑坑洼洼,觉得有些对不起。此次书多了很多内容,比之前的两版厚实多了,粗粗对比下,多了照片,关于昆曲的一些文章和曲人名录之类。只是也有一些不该有的错误,连我这个校对门外汉都发现了。
允和是合肥张家第二女,家中称二姐。受父亲影响,她自小便与大姐元和、三妹兆和同学昆曲,教授的老师是父亲重金请来的老曲家,所以可以说师承正派,于唱念身段上都算正宗。她们不仅学唱,也学身段,还登台表演。
允和的昆曲生涯大概可分为三段,49年前,56年到64年,79到87年。
说起曲人,大多数人是陌生的,这个人群的出现和认证,应该是在近代,张家四妹充和有一本《曲人鸿爪》,里面题字画画的各位先生就是所谓的曲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天南海北,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古典学识,算是知识分子,都因为擅长唱昆曲而被称为曲人。
曾见有人问,唱戏不是下九流的行业吗?怎么能和知识分子关联。这是很有趣的问题,昆曲在明代的参与人群,最初就是市民,这些市民包括了士农工商。士大夫因为懂得诗词格律,又有闲情逸致,便投身剧本的创作中,成为一股主导的力量。因此后来有了园林演剧、家班演习、厅堂娱乐这些被写到小说里的真实生活细节。
又因为囿于世俗偏见,士大夫们自觉与伶人保持了距离,提出了“清曲”和“剧曲”的区别,强调声腔念白,不重表演身段。这种情况到了清末民初,渐渐改变。一是因为昆曲式微,几乎失传,二是因为封建社会结束,思想开化,文人们都乐于与伶人交往,拜师学戏。
合肥张家就请了不少苏州传习所的老艺人指导,并且十分礼遇。
昆曲在明代开始,随着士大夫们的各地迁移而流播开来,苏州附近的无锡、南京、扬州、上海、杭州、嘉兴、绍兴等地均有昆曲班子和曲人世家。这些人群在常年的互动集会中形成小的团体,结成曲社,定期集会。苏州的曲社就有道和、契集、幔亭。无锡有天韵。上海有啸社等。
允和的昆曲生涯自苏州开始,后到四川,重庆,上海,北京,美国都有参与曲社活动。但49年前她的昆曲记录不算多,很少有舞台的独立演出,多是参与曲会活动。
解放后,大约是50年代中期,她随丈夫周有光定居北京,因为一些原因辞去工作,但不甘心赋闲,便与当时在北京的曲人们发起建立了北京昆曲研习社。
1956年8月19日,北京昆曲研习社正式成立,当时的社长是俞平伯先生。说到他,倒有一个前缘。在抗战前,俞平伯任教清华大学,他与校内爱好昆曲者成立了谷音曲社,当时张家四妹充和、大弟宗和均在其中。如今曲社里又有二姐允和,不可不说是一种缘分。
曲社成立初期,因为资金、场地、人员、笛师等问题,事务繁杂,困难重重,允和作为骨干,在其中尽心尽力,做了不少有用的事情。这实得益张家早期的人脉和她非凡的办事能力。
这段时间,允和与在北京的定和三弟,往来密切。定和是作曲家,亦懂昆曲。昆剧《十五贯》的作曲人就是他。定和参与的一些工作需要用到昆曲时,便来随时请教二姐,记录下二姐的唱腔唱谱。当时在贵阳的大弟宗和,海外的四妹充和也与允和保持着联系,交流着对昆曲的看法见解。56年时,借出差之机,宗和也曾到北京参与曲事,在俞平伯家唱曲,可算是对当年谷音社的一次温故。
昆曲日记上半部记到了59年,而曲社在64年后停止活动,自行解散。这是允和第二段昆曲生涯。其中原委,与文革脱不了关系。
1979年,曲社沉寂十五年后复社。笛声曲声又复响起,台上演员们光彩仍在,允和不禁怀念起了在文革中过世的几位曲友,吴南青(戏曲家吴梅之子)被打死,伊克贤、苏锡龄一同自缢。家里人为了不使她难过,更隐瞒了大弟宗和在77年去世的消息。
以及曲社诸人行头、乐器、录音设备均在劫难中被抄走,俞平伯先生劫后余生,却决意不再出任社长。
后来经过众人一致推选,时年73岁的允和出任社长,直到87年卸任。这段时间,是允和的第三段昆曲生涯,也是最丰富多彩的。她开始做昆曲资料的整理、收集,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写了许多关于昆曲的学术性文章。其中有关于红楼梦中昆曲部分的整理,猜测是为后来电视剧拍摄服务的。
在这段日记里,有一段细节令人难忘。82年9月底,允和因为胆囊炎一度病危,进入医院抢救。她在日记里写:翻开这一页,如同隔世,我又闯出了生死界。(注:又表明她之前也经历过生死考验,出生时她就因为脐带绕颈而昏迷),在病中,她甚至有交代后事的举动,还录音给曲社曲友。她又写:能活得下去,我还是要自己支持自己,不能靠任何人。淡淡的、沉沉的哀感在心头。
幸好,吉人自有天相。允和不久后康复。她是自强不屈的,且张家子女大多都得享高寿,大概也是一种良好的基因吧。
1984年底,允和与丈夫有光一同访美。有光因为公务,而允和则是探亲,她哪里都没去,在美的四个月,先是和三十多年未见的元和大姐相聚,后又一同到四妹家,姐妹间有讲不完的家事曲事。允和写:在四妹家,两人在楼下饭厅内,往往谈到凌晨一两点钟。
有一段日记写的特别感人,摘录如下:
安娜(充和的昆曲弟子)吹笛,四妹(充和)唱寻梦:“花花草草……生生死死”。
我则老泪滂沱,我想到大弟(宗和过世的消息想必已知)的“淅淅零零”曲,阿荣(苏州笛师,与张家相熟。56年去世,允和曾撰文纪念)的“点点滴滴”。
到四妹身边,哭泪何其多也,三十年至六十年的往事都回到脑中,好像失去的东西找到了,乐极生悲,有眼泪就是“欢喜”的表现。
此时,距离张家姐弟的大团聚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大弟、二弟更是先后过世,此情此景,白发相见,允和心中定是百感交集,悲喜相煎的。
此次聚会,还促成不少好事,元和充和等人成为海外社友,为社团注入外资,允和也从大姐、四妹处得到不少珍贵的戏曲资料。
在国内十年动乱期间,在美的曲人仍是不废曲笛,积极乐观的组织曲事,自娱自乐。他们缺少现成的头面服饰,便自己动身做。充和更是训练外籍的养女唱曲,与自己配戏。效果显著。
允和自87年卸任后,其实并未完全歇息。在96年,她以87高龄,号召姐弟,复刊家族刊物《水》,并自任主编,学习打字。这项举动,真令人惊奇赞叹。
2002年8月18日,允和去世,享年93岁。她在去世一年前得知昆曲成为非遗,十分欣慰。在她身后,丈夫周有光先生力促《昆曲日记》出版之事。
四妹充和这样评价允和:二姐后半生是多彩的、充实的。她为昆曲做了很多有用的事,写了很多文章,又恢复了《水》。最重要的是抗战中的苦难,锻炼了她的大无畏精神,虽然她本来也不是个畏首畏尾的人。只看红卫兵来抄家时,她那种幽默、潇洒不可及的态度。所以她满意一切,也没有带走一点遗憾。
这本书,大概并不适合所有人。但若有对昆曲的兴趣,却不得不看,它会告诉你,当代曲人的生存状态,对戏曲的独到看法以及一种现今不多见的,对古典美好事物的传承信念。
作为九如巷张家的迷妹,昆曲的入门者,我有幸,读到了它。
附:错误几处
封面允和生日应为1909,写成1901
890页,唱思凡应为充和,非允和
附录合肥张家简表,宗和续弦是刘文思,非刘以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