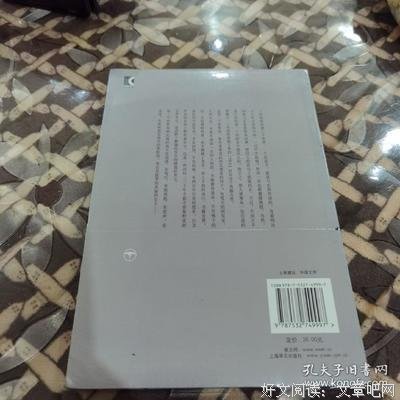《三四郎》读后感精选
《三四郎》是一本由[日] 夏目漱石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页数:26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三四郎》读后感(一):一些零散的记录
才刚刚接触日本文学,不知道为什么,看这本的时候就想起了四叠半神话大系(原作还未拜读过),特别是与次郎—小津,广田先生—樋口师父,有些微妙的相似。
1.广田先生的哲学之烟
圆灯笼 只能模糊地照亮自己坐处周围两尺的地方
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阐释 伪君子(徒具形式的亲切)与真恶人
用利己代入利他 以真恶来行伪善的奇妙做法
2.野野宫君
从事外国都为之注目的研究工作的人
若在外国便会发出光来 然而身在日本便黯淡至极
蝉翼似的缎带
3.伟大的黑暗与二十圆钱
4.第一章火车上的女子:“你是一个很没有胆量的人哪。”
第七章母亲的信:你从孩提时起就非常胆小。
《三四郎》读后感(二):时光的依恋
漱石的《三四郎》,写一位青年的恋爱故事,这是一部非常精巧、拥有不可思议的印象美的小说。 青年经历了几个女人,所谓的经历,有亲近、邂逅的意味,三四郎对于美祢子的态度是踌躇的,美祢子是欧化的日本女郎,美祢子的脸正如东京这座大都市一样陌生,令人生疑、恐惧又向往,三四郎爱慕这个女人,却无法坦然亲近她,漱石小说里的主人公,与外界往往是隔绝的,惶恐与惊愕是青年面对世界的态度。 三四郎的表现像一个孩童,广田对三四郎说,母亲的话,应该尽量听从。 随即谈到结婚,青年对于结婚不抱有任何看法,要听从母亲的意思,母亲是无比亲切的,而陌生的年轻女性是让人恐惧的,这种感受对于日本人而言,是完全自然的。 小说最优美的片段,是青年见到了一个夭折的孩子的出殡式,那随风转动的风车,庄重的寂灭之祭让青年体悟到了美的安宁,原本死是叫人悲痛的事,青年对于已逝生命产生了和谐感、亲近感,对于生者却产生了苦恼与疏离,青年想要做一个旁观者,最后也只能成为旁观者。 于是一切在粘稠的失意中终结。 小说归根结底只是一种印象,小说不会向你昭示什么,如果非要说漱石的小说里存在什么,恐怕是时光的依恋吧,无尽的其后,谁也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无常的时光徒然流转……
《三四郎》读后感(三):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三四郎的境遇吧
读一本小说,就如同走进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暂时忘记自身的烦恼。我也是最近才体会到,小说让人放松的感觉。抱着这种心情来看书,相对于闲暇或者爱好,又不一样。
在这个阶段,恰好读起了夏目漱石。
‘积极‘主流的入世,与‘消极’的避世之间的矛盾,总是那么尖锐。可能积极的,恨不得让每一分钟都产生价值;而消极的,可能在白云徘徊间让时间任意流逝。当书里的某个人,在走一段小路或是经过一片森林时,总想跑进书里呐喊,“喂,你就这样浪费掉了一下午的时间,可真是随意又幸福啊。“
就这样按照自己的价值来生活、与人交流,又有什么不好呢?一定得按照,规定的那样去生活吗?可是不去争取,会清贫又清贫呀。当脑袋里闪过这些杂念,不禁又十分愧疚。读个小说,尽然带进了这么多的一厢情愿。
三四郎在去东京的车上,遇到皮肤黝黑的小妇人,他就再也回不到熊本了吧。黑黑的皮肤,跟他同样来自类似于熊本的地方;清瘦穿着旧长服的中年人,却坐着三等车厢,三四郎认为他生活并不得意甚至是失败。
不知道三四郎以后究竟会怎么样?是像广田老师,还是像一心专研的野野宫,或者像忙于社交周旋的佐佐木,或者继续做迷途的羔羊。比起三四郎与美弥子的‘感情’,其实更对广田老师、野野宫、佐佐木、美弥子的状态感兴趣。
每个人都会因为情形,做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广田老师,会在白天的梦中,想起曾经在车上遇到的女孩;在选择一次,可能会与她结婚。美弥子选择了与自己阶层相符合的婚姻,没有让意外的爱情发生。
书读完了,还想再读一读。下次因为心境的变化,感受可能又不一样。
如果去日本,想去东京大学看看三四郎池。
《三四郎》读后感(四):故乡、大都市与事业
夏目漱石的爱情三部曲第一部,时间是大学。全书以三四郎单人视角叙述,所以书名恰如其分。书里总共有七个主要角色,三四郎、与次郎、广田先生、野野宫君、原口先生、美弥子、良子,五男二女。
三四郎从故乡来到东京,在名古屋与路途偶遇女子独处一室而不好意思拒绝,从此处便可看出这个主人公的闷骚。再到后来,他借了钱给与次郎,反倒变成自己理亏的模样,也是够可怜——被闷骚的性格所折磨的生活。
三四郎面前主要的路就是回到故乡、走近纸醉金迷的都市以及像野野宫君那样发展事业。没有给出他的选择,但是他的大学生活起初也是在不停地努力上课,在想多学一些的心理中度过。追求与美弥子相关的情感,算是他的走近都市的一个投影,但是在书末破灭。
说到男女情感,美弥子应该是书中被所有男性喜爱的那位,野野宫君撕碎了请帖、与次郎本被怂恿买她的肖像,诸如此类。但是夏目漱石认为“这不是女性喜欢同龄的这些幼稚男性的年代”,借与次郎的口又说出“她们只是没等到我们的伟大显现出来”,未免有些大男子主义。这么想来女性形象也是挺单一的,除了外貌和神神叨叨,好像并没有太多刻画。从另一个角度想,也许不是夏目漱石的问题,而是三四郎的问题——他有些蠢笨,动心的不过是他想象中的、遥远的、几乎模糊的美弥子。
反观男性,每位有自己的特点,也被作者相对地赋予一些“使命”。譬如野野宫君的物理实验属性、广田先生的“博闻强识”属性、与次郎的时而幽默时而深沉喜欢瞎忙活不太顾及别人感受的属性、原口先生的画画属性之类。
开篇东大的景色刻画,总让我想起同济。东大抗议而制止了门口通电车的计划,又想起通不过清华的地铁线路。
夏目漱石的文字特别生活化,很灵,站在普通人的视角看世界,写出那些我们会想但是不好意思说的话。有些地方不经意地埋伏笔——在前头埋伏笔只当是生活里的无关家常,不会在意也根本不会记住(与情节关系不大的孤儿情节很容易忘记),所以偶尔需要偶尔翻回去看——毕竟生活也不是事事无缝衔接的。能把生活中平平淡淡的事情写得吸引人,是不可多得的功力。
《三四郎》读后感(五):Stray Sheep
写于2018.7.21 他面对着的是三个世界。 想回到故乡吗?那是“一处后退的落脚点”——卸脱下来的过去所尘封的地方。还是去翻阅那生着青苔的砖瓦建造成的宽大的房子里摆放着的书籍——二三十年才很不容易积成的战胜了静谧岁月的宝贵灰尘?再向前看,却又是一个宛如光灿的春天的世界——电灯、银质匙、欢声、笑语、杯里直冒泡沫的香槟酒……。 同样的选择啊。 第三个世界里,还有美祢子在,还有那出类拔萃的美丽的女子……可她喜欢你吗?就算喜欢你,她会嫁给一个她自己瞧不起的人吗?既然这样,她又何必将浸透了海里奥特鲁帕浓郁味道的手绢伸到你的面前?时亲时疏,时近时远,时而倾心,时而嘲弄……呵,“男的只有被愚弄的份儿。”与次郎这方面是够明白的,但他又真的跳出了这至死茫然的打字机的人生了吗? 或许沉浸在第二个世界中钻研学术的野野宫君更像广田先生,可真看清了那光灿世界的真面目,又何必将无视就好的请帖随身携带却撕碎在地上?洋流与传统的冲击,既是那时的特点,亦是现世的特点。看似新时代的青年,却仍然在桎梏之中原地不动地大步行走罢了。不然的话,又何必说出“我知我罪,我罪常在我前”呢? 是该回到那令人怀念却又破旧的有着母亲的故乡吗? 是该将心思都放在那喧闹中保持宁静的小小学术之地吗? 是该追寻着最有好感的那太空中的闪电吗? 三四郎不知道。可无论如何,总没有完美的选择。是厌烦三轮田的阿光也好,是在短暂休息中感受到持续的孤独也好,还是在兴旺发达求之不得的世界中作茧自缚也好,将三个世界搅和成一团的目标总难以实现——“把母亲从乡下接出来;娶一位美貌的妻子;然后投身到学习中去。” 平淡且平凡而已,甚至仔细想想都可以将那短暂的接触解释为自作多情的感觉。可真当本已明了的残酷真相揭露在面前,又是那么的难以接受。不过嘛,“在本人看来,也许是近于悲剧的事情,而在他人看来,并没有那么痛切的感受。” 但至少美祢子击碎了三四郎眼前的第三个世界,在就像是患的流行性感冒——不大又不小——过去之后,选择也会不再那么艰难。 所以请不要在不动声色的眉毛之下露出那置于远处却又非常不放心在远处的眼神了。
《三四郎》读后感(六):夏目三四郎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把握日本人对于情感的认识。
在他们看来,男女之间灵魂与情感的相互触及似乎在实际发生之前就已经存在。而其后的一切缘分,都是为了拉开这种距离。就好像终点位于起跑线之前,当你真正开始追逐时,已在镜中越跑越远。
况且他们只对最微妙和最真诚的情感感兴趣,因此温柔与残忍的统一则是他们所着迷的。
好似三四郎的恋爱,在微妙之中面对一个女孩儿,她的一举一动都那么显著。而且因着机缘巧合总有机会面对她。
但面对爱人时就如同面对一项错误。他手足无措、言不由衷,几乎是无声的。
美弥子少女怀春,应当是倾心于野野宫,但心之所属却很复杂。她愿意所有的男孩都是胶泥做的,好叫她把身边几个男孩子揉在一起。而她做不到,她是一汪水,反而溶进几块泥中,无能为力了。所以她自觉陷入迷途之中,如迷失的羔羊。
一阵风吹散了三四郎眼前的雾,他看清了美弥子。一会儿雾又泛起,一切不再真切了。
从故乡的现实,到东京的缭乱,再到学府中的浪漫理想。这让他心慌。
唯有那心池让人平静。
而在心池边遇见的姑娘,如春水的一汪涟漪,将他荡漾在水影当中。
三四郎的故事里还有一个矛盾,是夏目漱石专有的,即他对与日本西化的消极哲学。从理性上对西化警惕,但同时也认可,只不过偶有几句对西方的赞扬却并非出于对西方文明的好感,而是对日本人的厌恶。这是他所有作品的基础氛围,顽强而屈辱。
所以当三四郎从九州乡下出发前往东京时,几乎是一头扎入了夏目搭建的这种卑微的气氛当中,十分和谐。
三四郎的足迹带我回到曾经的日本生活,以及同他一样,于诺大都市中,我也只认识那么几个人而已。但三四郎走到哪里都能遇见相熟的姑娘,这点我是比不上的。
另外,把东大的心池改作三四郎池,我看也是大可不必的。
《三四郎》读后感(七):我们这群当代中国的“三四郎”
1868年开始推行的明治维新,使日本由传统的武士封建社会走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让日本跻身于世界经济和军事强国之列。
40年后的1908年,夏目漱石写下长篇小说《三四郎》。小说主人公离开家乡熊本,来到东京上大学。在这个受现代文明冲击的大都市中,三四郎面对着三个世界。一个是安安稳稳的故乡熊本,一个是不慌不忙的知识世界,一个是光怪陆离的浮华世界。而三四郎渐渐迷失于对美祢子的暗恋中,最终,在浮华的世界,成为了“迷途的羊”。
彼时三四郎所面临的三个世界,也是当时多数日本青年面临的境况。40年间,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加剧,社会深层次变革,价值观西化,年轻人,特别是刚从农村走向大都市的青年学生,面对如此繁华的大都市,难免彷徨迷惑,难免成为“迷途的羊”。
三四郎躺在被子里,把这三个世界放在一起互相比较,接着把这三个世界搅和成一团,他从中得出一个目标—总而言之,最好莫过于:把母亲从乡下接出来;娶一位美貌的妻子;然后投身到学习中去。这目标何其平凡,也何其困难,正如我们现代中国青年所面对的一样。
我们就是这个繁华社会下无人问津的“三四郎”。 我们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城市,由陌生蛋熟悉,反而故乡成了一年难得回去两次的他乡,故乡的一切变得朦朦胧胧,甚至我们与之格格不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是不想回去的——那是最后的退路。
而我们融入了这座越来越熟悉的大都市了吗?我们习惯了高企的生活成本,习惯了繁忙的交通,习惯了冷漠的人情,但我们也会渴求平静安定的生活,渴求他人关怀的目光,我们也想慢下来,去看晨光熹微,看暮云叆叇。
爱情,更是很多年轻人无可企及的幻想。这世界何其美好,有电灯,有银质匙,有欢声,有笑语,有杯里直冒泡沫的香槟酒,谁不曾想进入这如同在光灿的春天里荡漾的世界;这世界就在眼前,但颇难靠近,仿佛是太空中的闪电。
我们这群当代中国的“三四郎”,面对着这个繁华的社会,在大城市中,忙碌奔波着,偶尔怀念起远方的故乡,憧憬着美好的爱情。但愿,你我都不要成为“迷途的羊”。
《三四郎》读后感(八):迷途的羊
二十三岁的年华,从熊本开往东京的列车,小川三四郎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平生第一次去大城市,不知会有怎样的际遇。时间匆匆,返乡后再来到东京,三四郎站在入冬寒冷的东京街头,比第一次来时更加迷茫,口中不停地默念:“迷途的羊,迷途的羊。” 在熊本的传统文化和东京的现代文明环境下,三四郎始终彷徨,始终对未知充满了怀疑。三个世界同时包围了年轻的小川。 第一个来自故乡,远方,一切平平稳稳,然而一切也都朦朦胧胧。在东京站不住脚,他可以随时回去,回到那个朝九晚五的农耕乡村生活。但年轻气盛的小川还想在这里闯一闯,瞧一瞧。 第二个来自野野宫君和广田先生的学问世界,在东西交融的现代化大都市东京,难得还有这样沉得住气潜心治学的人。小川与野野宫君是同乡,又与广田先生有在火车上的短暂交际,所以在这里很受二位的欢迎和爱戴。他也尝试向这两位大学问家靠拢。在学校,在课堂,努力地学习,做功课,记笔记。 第三个来自现代都市的浮华世界,这里与熊本一点也不同,就算小川交到了好朋友与次郎,但与次郎也偶尔把他另眼看待,时时把“你是熊本人”挂在口中。第三个世界对三四郎影响颇深,缘由是他遇见了有着显著现代女性特征的里见美祢子。一次偶然的邂逅再加上美祢子与广田和野野宫都相识,使得三四郎对她的感觉迅速升温。他渴望每天遇见她,渴望能与她交谈。他可以为了能与美祢子小姐处在一起随意改变想法,由着她的性子,只要能待在一块儿,他就心满意足。美祢子也时时表现出被三四郎触动的感觉,也心生情愫,这让三四郎很是满足。但美祢子心里究竟在想什么,三四郎也不得而知。因为害羞和含蓄,三四郎不敢直抒胸臆去表达心中的爱慕之情,但他做了除了一句“我爱你”之外所有的举动。而美祢子也许猜透了三四郎的心思,也许也是懵懂状态,总是保持暧昧含糊不清。他们一起坐在小溪边看风景,短途游玩,美祢子告诉三四郎四个字“迷途的羊”,让三四郎迟疑不已。每天在这种揣测和期待中生活,三四郎活得够累,直到一天,美祢子订婚了,男主不是小川,他没有出席婚礼,没有任何想表达的东西,只是头脑昏热,不知所措。小说在循环的“迷途的羊”中戛然而止。 小说的定位是爱情悲剧,但我并没有在夏目漱石先生笔下读到传统的爱情故事。三四郎和美祢子从来就没有在一起过,也没有那些沁人心脾的情话,至多是三四郎的单相思罢了,连对美祢子的心理描写都寥寥无几,刻意把美祢子塑造成一位无法摸透心思的现代女性角色。在新时期,女性得到解放,女性不再是谁的附庸,不再被男性钳制,也可以追求自由恋爱,也可以天马行空地猜想。所以,美祢子就是在只言片语中呈现出这样的角色。而处在新旧思想交替的三四郎一面被根深蒂固的传统控制,一面又受到新潮的文化牵连,在面对前所未见的新女性时,他常常不知所措。所以,从这一层面看,这的确是不现实的爱情,是一出十足的悲剧。 抛开那么多时代背景,单从小人物看,三四郎的情感经历实在让人痛惜。一个大男孩不敢表达自己的情感,一直去猜想和揣摩心仪女孩的心理,却越发的模糊,越发的陌生。女孩的表现也有些弊病,你既然不爱,为什么还要保持暧昧?小川就是被这样吊着胃口一直死皮赖脸不愿放手。 在读的时候,可以从三四郎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来到大学,一面念着家乡小城那点风味,一面想融入到大学的学术圈里,一面在与异性交往时想象着一些可能性。这像极了小川三四郎的三个世界。也许每个离开家乡的大男孩心里都住着一部《三四郎》吧。谁都有心中的难言之隐,尤其在青春时对爱情的希冀。不想把珍贵的“我爱你”说得那么随意,却又找不到能说出这三个字的合适时机。不想随意放下一个一直惦记的人,但有时四年却化为一种难言的痛苦。我喜欢你,我本该在想你的时候笑意盎然,然而面对你的含糊不清,每每脑海里出现你,却衍生出一种失落。你就在眼前,你只是一个人罢了,我得不到你,我也摸不透你。 就在正式失去一个人的时候,那不妨也为她高兴一下吧。爱她,就希望她的世界里没有烦恼,就希望她可以过得很好。独自走在路上,回想这段单方面的苦相思,这也是难以忘怀的经历。 合上书本,脑子里想着发生在小说里和自己身上的复杂的事也渐渐停息。眼睛有点昏花,洗把脸,瘫坐在椅子上。心中不断默念:“迷途的羊,迷途的羊。”
《三四郎》读后感(九):三四郎与他的现实世界
读夏目漱石的《三四郎》以前,只看过他的代表作《我是猫》。这部经典的讽刺小说以一只猫的视角描写了二十世纪初日本中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以猫的口吻批判了当时社会上一股虚假腐朽之风。而《三四郎》则与这部作品完全不同,漱石放下了批判之笔,写出了一部平实朴素甚至带有青春期色彩的小说。
主人公是一位来自熊本(想到部长!)刚刚高中毕业的乡下少年,来到东京这座他幻想已久的大都市读书。从离开九州一路向北的火车开始,他遇见了各色各样的都市人,他的生活和思想逐渐开始破碎、重组,最终达到他所向往的一种平衡境界——拥有一份都市人的心态。如村上春树在《海边的卡夫卡》里所说,“这是一部所谓的近代教养小说,三四郎在故事里成长,碰壁,碰壁后认真思考,争取跨越过去。”
现实世界
书中前半段反复提及三四郎的现实世界,我将以此为线索,跟随他一起破碎瓦解、重新思考。
如果说这种激烈的生活本身才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世界,那么自己迄今为止的生活就根本不曾触及现实世界的皮毛,简直就像是局外人在白天睡大觉。自己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并列在同一平面上,但绝不相触。现实世界就是这样动荡着抛下了自己而走了。是在没法安心。此时,三四郎刚刚到达东京。不久之前,他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位向他主动示爱的陌生女子以及一位说出日本“将会亡国”,却始终不慌不忙悠闲自在的中年男人。而东京又是怎样一幅盛况呢?到处能够看见叮叮当当的电车和从车里上上下下的人,到处都在拆毁和重建,他被眼前的景象和遇见的人们惊呆了。这里,果然已经不是熊本了。
总而言之,如果说到自己与现实世界的接触,那么眼下除了母亲之外恐怕别无他人了,此外还有一个人,就是火车上同车厢的女子。那是现实世界的闪电。三四郎收到了一封母亲的信,将他拉回了现实世界。同时他想起了火车上那个女子,虽然只有一段短暂的相处,也想不通她究竟是怎样的人,但她的突然出现,像是原子弹爆炸,轰的一声巨响,拉开了他现实世界的大门。
望远镜中的刻度无论怎么动,与现实世界并无瓜葛,这是很明显的事。野野宫君也许终生不想与现实世界接触吧... ...自己索性也与活生生的现实世界斩却一切瓜葛,一心一意就此度过人生吧。他听从母亲的建议,找到东京唯一的熟人,野野宫君。穿着朴素,以地窟为根据地,乐此不疲的研究光线压力的野野宫君,成了他在东京认识的第一个人。野野宫君远离了现实世界,却成为三四郎现实世界的一部分。三四郎最终会明白,现实世界就是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世界。
三四郎面对着三个世界。一个在远方,有着明治十五年以前的风味......第二个世界里有生着青苔的砖瓦建造的房子,书籍摞得很高,那里的人大抵长着懒得刮的长胡子......第三个世界宛如光灿的春天在荡漾... ...在遇到与次郎、广田先生、野野宫君的妹妹良子小姐以及里见小姐后,三四郎的内心发生了很多变化。远方有母亲的世界已经逐渐远离自己的生活,“不到万不得已,三四郎是不想回去的”,他把那里当作一处后退的落脚点,而不是久留的居所。第二个世界是包括他在内的读书人的精神世界,那里的人们沉醉其中,无所忌惮,毫不在乎。与其说人们是为了逃离现实世界而创造了它,不如说是这个世界以其自身的魅力吸引他们来此。第三个世界则是三四郎的爱情世界,也是他“最抱好感的世界”,他恳切的希望自己能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人公。
在自己曾经分析过的三个世界里,那第二、第三个世界正可用这一团人影为代表。人影的一半微微发黑,另一半明如花卉盛开的原野。于是在三四郎的头脑中,这明暗的两部分浑然相合,融合在一起了。不仅如此,三四郎也在不知不觉间自然而然地被织入其中了。这一团人影就是他所遇到的那群人,他们每个人身上一半模糊,一半明丽如花,两个部分相互融合,成了独特的人。随着他们的日渐相处,三四郎不再如当初般怯懦惶恐,虽然依旧青涩憨厚,不时会为了自己的不会说话、没有新颖的想法而感到懊恼。但似乎已经模糊的感受到了一些不曾有过的体验。
小说在这里以后便再没有出现过描写三四郎“世界”的字眼。而是把重心放在他与里见小姐的感情线上,即他的第三世界。不再提及不表示没有存在,只是三四郎已经成长为不需再诚惶诚恐的思考“这里究竟是怎样的世界”“而我又处在哪个世界”的少年。他坎坎坷坷却也顺利的融入了这里。
“特立独行”的少年
作者虽以三四郎为主线,也侧面描写了东京城内几位“特立独行”的少年。
与次郎:一个奔波在各种名流场所,立志让广田先生成为大学教授的怪诞少年。他赌博输钱,借钱不还,写匿名稿东窗事发后以三四郎的名义顶替。而三四郎对他的态度,也从羡慕、敬仰到不解、无奈。
里见小姐:一个默默喜欢着野野宫君的温婉女子,却也有着刚强任性的一面,最终嫁给了一个不喜欢的人,迷途的羊没有迷途知返。
野野宫君:这个在三四郎看来一直默默致力于研究、无欲寡欢的少年,却一直将里见小姐的结婚请帖放在身上,在最后的时刻,将它撕碎扔在了地板上。
而广田先生则像是漱石的化身,一直保持着他云淡风轻的态度,却屡屡说出一些有讽刺意味的话。
比起熊本来,是东京大得多。比起东京来,是日本大得多。比起日本来,是脑袋大得多。一成不变是作茧自缚。伟人也好,凡人也好,无非是在社会上出头的时间有个先后罢了。那些博士、学士的,与他们交谈一下,没有任何了不起的地方。我们做学生的时候,一举一动都考虑别人,一切以别人为中心,想到的是:君,亲,国,社会。总而言之,那时候的青年学生都是伪君子。当社会的变化使那种伪善终于行不通时,便渐渐地在思想行为方面输入以我为主的体系,这么一来,就导致自我意识发展过了分,现在的状况和以前不一样了,不再是什么伪君子,而净是些真恶人。这本书总的来说是以三四郎的成长感受为主。在他脱离原生家庭,迈向“现实世界”的过程中,我也发现并消化了当初青涩、惶恐的自己。
《三四郎》读后感(十):《三四郎》:乡村青年初入都市的阵痛
《三四郎》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なつめ そうせき)的长篇青春小说。讲述了,考入东京大学的乡下青年三四郎,由落后的熊本县进入大都会东京市求学的经历。在东大的校园生活中,三四郎结识了各色人:油腔滑调但一心希望“文学复兴”的同学佐佐木;高山流水且曲高和寡的野野宫教授与广田先生;初显现代女性雏形的里见美祢子等。同时,由于东京都市氛围的影响,三四郎在物质、学术、情感等多方面固有的信念,均受到剧烈的冲击。 在阅读过程中,以下片段(吴树文 译)我很喜欢,便摘抄下来,方便回顾与欣赏。片段内容,包括三四郎在从熊本去东京的火车上的见闻;三四郎经历东京校园生活后,产生的“三个世界”的想法;三四郎初次接触现代女性后的感受;三四郎与母亲的通信;以及,广田先生奇幻的梦。
《三四郎》,[日] 夏目漱石,吴树文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具体如下(有删减): ① 从熊本去东京的火车 这女子是从京都上车的旅客,与三四郎同乘一节车厢。她上车时就引起了三四郎的注意。第一个印象是肤色黝黑。三四郎从九州换乘山阳线,随着火车渐渐向京都、大阪靠近,他看到女人们的肤色渐渐白起来,不禁感到了一种远离故乡的轻愁。所以这女子走进车厢来的时候,三四郎不由得产生了一种有了异性朋友的心情。这女子的肤色属于九州肤色。 这肤色与三轮田的阿光相同。直到离开故乡为止,阿光总还是个叫人嫌烦的女人,能够离开她真是谢天谢地。可是现在看来,像阿光那样的人还是很不错的呀。 ② 火车上,陌生男子的前卫言论 这时候,先前的那个男子从后面伸过头来。 “还没有要开车的迹象吗?” 他一边说一边望了一眼刚从眼下走过去的洋人夫妇。 “哦,真漂亮呀。” 男子小声说着,旋即要想打呵欠。三四郎觉得自己实在显得太寒伧,赶快缩回脑袋,坐了下来。男子也跟着回到了座位上。 “洋人实在漂亮哪。”男子说道。 三四郎没什么可答的,只是表示同意地“嗳”了一声,笑笑。 “我们都很可怜哪。”于是这个长着胡子的男子说。“这副长相,这么无用,即使日俄战争打赢了而上升为一流强国,也是无济于事的。建筑物也好,庭园也好,仪态都不妙,不比我们的长相好多少,不过——你是第一次上东京的话,还不曾见过富士山喽?马上就能看到了,你好好看看吧。它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名胜,没有东西能比它更值得自豪啦。然而,这富士山乃是天然形成的,自古以来就存在着,非人力所能左右,也不是我们造出来的。”他又独自笑了。三四郎对自己竟会在日俄战争以后碰到这样的人,实在感到意外,简直觉得对方不像是一个日本人。 “不过,今后日本也会渐渐发展的吧。”三四郎辩解道。 于是男子装模作样地说道:“将会亡国呢。” 如果在熊本说出这种话来,立刻就得挨揍。弄得不好,将被视作叛国贼。听到这一席话,三四郎觉得自己是真的离开熊本了,同时领悟到在熊本时的自己乃是一个非常怯弱的人。 ③ 三四郎的“三个世界”理论 三四郎回去后立即上床。与其说三四郎是个用功的学者,倒不如说他是个爱思索的人。他不大读书,但一旦遇到某种触及灵感的情景,便会在脑海里反复琢磨,求其新意而不胜欣喜,好像感到其中存在着命运的真谛。今天的情景若是发生在平时——例如正当神秘的讲课内容讲到高潮的时候,电灯突然亮了起来——三四郎本该反复琢磨而感到欣喜,但是母亲有信来,先得对付信件的事。信上说: 前几天,阿光的母亲来商谈,说:“三四郎不久就要大学毕业的,毕业后把我家的姑娘娶去行不行呢?”阿光姑娘长得端庄,性情温柔,家里又有很多田地,再说两家人本来就有关系,事成的话,双方都很合适的吧。 下面还附上几句补充的话:阿光姑娘大概也会很高兴的,至于东京人嘛,其心难测,我不喜欢。 三四郎把信纸折好,装入信封,放到枕边后闭上了眼睛。老鼠忽然在天花板上乱蹦乱蹿起来,不一会儿又静了下来。 三四郎面对着三个世界。一个在远方,有着明治十五年以前的风味,一切平平稳稳,然而一切也都朦朦胧胧。当然,回那儿去是很简单的事,想回去的话马上就能回去。不过,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三四郎是不想回去的。换言之,那儿就像是一处后退的落脚点。三四郎把卸脱下来的“过去”,封在这个落脚点里。他想到和蔼的母亲也被埋在那个圈子里,忽然觉得这太不应该了。于是,只能在母亲来信的时候,才在这个世界低徊一会儿以温旧情。 这第二个世界里,有生着青苔的砖瓦建造的房子;有宽大的阅览室,大得从这一头看不清另一头的人的脸。书籍摞得很高,不用梯子的话,手很难够得着。由于翻破了书页,加上手指的油污,书籍发黑;金色的字迹发亮。羊皮封面,牛皮封面,有两百年历史的纸张,以及所有的东西上都积着灰尘。这是一些历时二三十年才很不容易积成的宝贵灰尘,是战胜了静谧的岁月的静谧的灰尘。进入这个世界中的人,因不知当前的世界而颇不幸,也因能逃离烦恼的世界而颇幸运。 第三个世界宛如光灿的春天在荡漾。有电灯,有银质匙,有欢声,有笑语,有杯里直冒泡沫的香槟酒,有出类拔萃的美丽的女子。这个世界是三四郎最抱有好感的世界。这个世界就在眼前,但是颇难靠近。 三四郎躺在被子里,把这三个世界放在一起互相比较,接着把这三个世界搅和成一团,他从中得出一个目标——总而言之,最好莫过于:把母亲从乡下接出来;娶一位美貌的妻子;然后投身到学习中去。 不过,这样一来的话,就使一个渺小的妻室代表了那广阔的第三世界了。只认识自己的妻子就感到满足的话,那自己就像是一个不让自己全面发展的人了。 ④ 现代女性 三四郎揿了电铃,对传话的女仆说:“美祢子小姐在家吗?”话说出口时,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真不可思议。在别人家的正门前,询问一位妙龄女郎在不在家,这是三四郎从未有过的事,所以感到很难启口。女仆却出人意料地认真,而且彬彬有礼。 ...... 两个人默默无语地并肩走了半町左右的路程。在这段时间里,三四郎的思想始终没有离开过美祢子。他想:这女子显然是娇生惯养长大,而且在家庭中享有非普通女子所有的自由,遇事无不唯我独尊;从她不需征得谁的同意便与我三四郎一起在马路上行走这一点来看,就可以明白。她没有上了年纪的长辈,年轻的兄长采取放任主义,所以才能够这么样的;如若在乡下发生这样的情况,肯定够她受的;要是叫她去过三轮田的阿光姐那样的日子,不知会有何感想呢;东京与乡下不同,万事都很开明,所以这儿的女子也许多是如此的,不过从远处带着想象来看她们,似乎仍有点儿旧式的成分。 ⑤ 母亲的信 回到寄宿处,三四郎的酒意已醒了,他总感到闲得无聊极了,便在写字桌前坐着出神。这时女仆提着一壶开水上来,顺便拿来了一封信。又是母亲的来信。三四郎立即启封。今天读母亲的亲笔信,三四郎感到异常兴奋。 信写得相当长,但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尤其是只字没提三轮田的阿光小姐,真叫三四郎谢天谢地了。然而,信里有一段奇怪的忠告。 你从孩子时期起就非常胆小。胆子小当然十分吃亏,逢到考试这一类的事情时,简直无所措手足。兴津的高先生,学问那么好,尚在当中学老师。他每次受审核考试时,全身发抖,没法好好回答试题,可怜至今没加过月薪。后来恳求一位当医生的朋友,配了制止发抖的丸药,在考试之前服了药去应考,据说依然发抖。你还不至于有嗦嗦发抖的现象,所以可请东京的医生配点儿平时常服的壮胆药试试看,也许能治好。 三四郎觉得母亲实在糊涂,但在这种糊涂中,三四郎又感觉到莫大的慰藉。他深切地体会到:母亲真正是无比亲切的人哪。当晚,三四郎给母亲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一直写到一点钟左右。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东京并不是很惹人爱的地方。 ⑥ 广田先生的梦 “刚才我白天睡大觉,做了个有趣的梦。这梦简直像小说中说到的那样,我竟突然梦见了生平只遇见过一次的女子。这话题比报上的那篇报道有意思多啦。” “嗯。什么样的女子?” “一个十二三岁的漂亮少女,脸上长有黑痣。” 三四郎听到“十二三岁”,有点感到失望了。 “什么时候遇见过的呢?” “大概是二十年前。” 三四郎又感到吃惊了。 “您竟记得这么清楚呀!” “这是梦呀。因为是梦,当然就记得了。也正因为是梦,所以美好得离奇。我仿佛在大森林中走着,身穿那件褪了颜色的西式夏装,戴着那顶旧帽子。是啊,当时我好像在思索着什么难题。所有的宇宙法则是不变的,但是在法则支配下,整个宇宙的事物没有不变的。于是,这种法则不得不存在于物外。醒来一想,这问题毫无意思,但是我在梦中很认真地思索着这个问题,在我走过森林时,突然遇到了那位女子,不是她走过来碰到的,而是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我朝她望去,只见她的面貌依旧,服饰依旧,头发依旧,黑痣当然少不了。总之,完全是我二十年前看到的那个十二三岁的少女,一点没有变。我对她说:‘你一点都没变呀。’她对我说:‘你老多了。’接着我问她:‘你怎么会一点都不变呢?’她说:‘我最喜欢长有这副容貌的那一年、穿着这身服饰的那一月、梳着这种头发的那一天,所以就成了这样了。’我问道:‘你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呢?’她说:‘是二十年前与你相见的事喽。’我说:‘那么,我怎么就这么老了?自己都觉得奇怪呢。’她解答说:‘因为你一心想比从前那个时候变得更美、更美呀。’这时我对她说:‘你是画。’她对我说:‘你是诗。’” 参考内容: 《三四郎》,[日] 夏目漱石,吴树文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