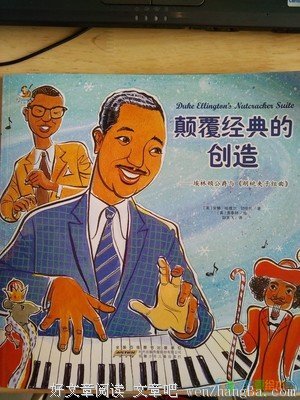大师经典读后感10篇
《大师》是一本由[爱尔兰] 科尔姆·托宾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00元,页数:329,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师》读后感(一):大师们
看这本书的缘由无论是出于对科尔姆·托宾的好奇,还是出于亨利·詹姆斯的名气,大师写大师,本身就会是个惊奇。不仅如此,柏栎的译文语言流畅,用词精准,丝毫不会让人读起来感觉有翻译腔,在我看来,很好地还原了托宾用沉稳的语言营造出来的细腻、平静的心理小说氛围。
“有些晚上他梦见死去的人,熟悉的和似曾相识的面孔,飞快地浮现出来......”
这句话是全书的第一句话,引领了全书的核心:回忆。虽然小说是以日期作为每个章节的题目,但其实主要内容和时间顺序并没太大关系,只是亨利在不同的日子里,回忆起不同的人。那些有过深刻印象,在心中扎根的人们,不仅是出现在脑海里,而且还影响着亨利此时的创作。托宾处理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方法很巧妙,一方面,他领着亨利生活在1895年1月到1899年10月的实实在在的每一天---写作、应酬、旅行;另一方面,他不动声色地给亨利以各方面的提示,暗中指引着他发现当下和过去的联系。托宾像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导游,但不意味着亨利是他故事的傀儡,相反,这本以第三人称写的小说给我带来的那种真实、亲密(甚至是隐秘)的感受却是很多第一人称小说都没能做到的。
随便翻到哪一页,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托宾能做到将亨利的内心完全坦露给读者。比如说,亨利回忆起年少时,为了能够安心待在家中,逃避因未参战而将可能带来的内疚和父亲的责备,从而决定向父亲宣布自己决心选择攻读法律的情形。在描写这一段回忆的时候,托宾没有像大多数作家会做的那样去着重描写亨利和父亲谈话的过程,而是更多地把注重点放在了亨利的心理上:思前想后选择谈话时的措辞、在心里排练父亲的反应...... 因此,读者感觉亨利就在眼前,焦头烂额地考虑着每个细节。
托宾能够体会到亨利细腻的内心,不仅是由于他天生敏锐的本性,也由于作为作家的共同之处。托宾在谈到这本书时说过:“文学的迷人之处正在于它是一种穿越的形式,你从自己的国籍、家庭、背景当中移出来,进入另一个人的灵魂。虽然詹姆斯生活在一百多年前的美国,但我和他可以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并且,同性恋身份也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大师在写大师的时候,作为普通人的我除了惊叹以外,只有致以崇高的敬意了... 托宾构建出了一个城堡,亨利的真实经历是砖瓦,托宾的想象力则是所有的装饰和家具。所有其他人---即使是被完全带入情节的读者---也只不过是城堡暂住的客人。我想这是一个人能对另一个人所做出的最高形式的爱和崇拜了。
《大师》读后感(二):你心里的一个缺
两年前写的书评,偶然翻出来了。
现在我还常跑去听文学院LDQ的文艺理论。我乐于看着他敲着脑袋的苦闷模样,再悠悠地自问自答:“创作的积累其实是什么啊?是情感创伤的积累。”如果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我想托宾累积的情感创伤也许能和亨利詹姆斯比肩。
有段日子,我的魂像掉在托宾的《大师》里了,那冠以文豪之名的人物在三百多页纸张间变得具象、亲切可触。托宾使我惊讶,亨利詹姆斯让我目瞪口呆。经托宾揣测描画的亨利是我不能放弃的意向,他直指隐晦的内心。他们属于一类人,正是木心所说的殉了道的人。我瞧出来了,他们对自己的纤敏与孤独有种刻意的痴迷,他们养着自己的病,不自觉地爱上了它,而他们竟是如此满意这状态。
艺术家多数没有归属感,他们有的彻底醉了,像画《呐喊》的蒙克;有的还在苦恋着尘世的暖,像萧红。
托宾在写这部书时一定未多加克制地移情了(移情在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里竟是两个迥异的概念),他没有刻意节制,大约忘了尼采说的“人是需要被克服的东西”,然而达到的艺术效果是惊人的。这种巨细靡遗的描绘使那个敏感、纤弱的亨利詹姆斯格外真切,我就几乎要忘了他不是那个真的文豪亨利詹姆斯,他只是托宾的“亨利”。《大师》如此传神,这个亨利身上披着托宾自己的几多重影子。
对于每个对表达(或者说写作)有着强烈诉求的人而言(譬如说我自己),亨利詹姆斯那种阴郁、敏锐的特质经过托宾的处理,必定显得十分动人心魄。这是著述者借文字的手,与百年之前文豪的一次惊人神交。
书由亨利的噩梦起始,调子就已经阴冷,到最末兄长来访收尾。有些人从他生命里走过场,跟风吹过去了一样,没留下什么痕迹;有些人竟是蚀骨铭心,这样的人极少。因为少,因而在他们身上着墨更多。从头细数,剔除父母、妹妹爱丽丝、表妹明妮、挚友康斯坦斯(如果只能定义成挚友)、仆人哈蒙德、雕塑家安德森,他的生命就会显得过分简白。
母亲自始至终都是亨利心中的一抹温柔,在母亲死后借灵媒之口也在给予他无限关切。而父亲,这个似乎时刻遭受死神威胁的父亲,也许是亨利早年敏感的全部来源,他毕竟有个压抑的童年时代(童年对于人心性的塑造力量如此巨大,例如看完张爱玲的《小团圆》也就不再惊叹她一生是如何创造出那些曲折离合的故事,她所写的原本就是她经历过的事)。 爱丽丝与亨利的品性最为相像,但她勇敢地去赴死了,到最后一刻也不畏惧。表妹明妮本是最有可能与他结合的女性,在病怏怏的她伸手索取他的温暖时,他沉默无言的拒绝其实尤为残忍。似乎是为了赎罪或是偿还,他在《贵妇肖像》中以她为原型,带她游了意大利——这大概是他尽力做的于事无补的挽救。
哈蒙德与安德森不说了,鉴于托宾在多部作品中对于同性恋倾向的晦涩描述,多数人都会把这两个人物的安排看作是对亨利詹姆斯同性恋倾向的注解。何况书里还插了同时代的王尔德的那段。至于王尔德因同性恋有伤风化被捕入狱对托宾的隐射意义,我未看出什么。只是这两位大师同时摆在眼前,忽然觉得十分讽刺。书中的詹姆斯大约永不会赞许王尔德的讥诮语气、大卖的戏剧。王尔德成功的时候正处詹姆斯最灰暗的时候,詹姆斯写的戏不受大部分平庸观众的待见(嘻,文学与商业的矛盾那时候就这么尖锐了),他写得太精英了,或者太文气了,并无心迎合取悦大众——也许他是太高估这些受众了;就在他小心翼翼做出尝试但一败涂地的时候,他竟然有点扛不住了。王尔德指向放浪形骸,詹姆斯就指向隐忍内敛。
我接触这本书的由头其实是梁文道的《我执》,梁在书里提起《大师》时,侧重给了康斯坦斯。原本指望瞧出惊心动魄恋情的我着实失望,他们的感情没有跳出全书的格调,仍然隐晦,虽把各自的心思揭露地赤裸裸,几近难堪。梁的书中引了康斯坦斯自杀前的未写完的一条小说线索:“想像一个男人生来就少了一颗心,他善良,正直,彬彬有礼,但就是没有那颗心。”这也许是对亨利的最好阐释,他少了那颗心,他只在不断描述不断创造。执着于小说里多少年的他,再想抽身多少有点来不及了。多少年前明妮的死对于亨利的冷漠已经是个伏笔,“她失去生命后,他知道拿她怎么办”。他是个巨匠,却是个爱的无能者,他无法真正爱身边的人。也许出于恐惧,也许是因为他觉得无法把握。与情绪打交道的人对情绪的感知有异于常人的敏感,但控制起情绪来,又有了可怕的冷峻。苏有贞说亨利:“他投注了一生的精力和意志,潜心要把生命中黏腻且不合秩序的情感和欲望,奋力地强压到意识的海底。”此时的他未免已沦为一个悲剧的前景,托宾在书里给亨利安置了一段念白,“有时他觉得他的生活似乎归属于另一个人,归属于一篇尚未写下来的小说,归属于一个还没有充分构思出来的人物”。这句话似万金油,使得我们会加注在亨利身上的种种怨念戛然而止。
当年我看《梅兰芳》的公映,里面有段话好像这么讲的,原话已记不太清楚:梅兰芳的心里有个空缺,如果填满了,他就不是梅兰芳了。亨利詹姆斯至此已经化作一个艺术符号,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像文森特梵高。他们都必定是孤独的,只是有人极端热烈,有人如此隐忍。他们不属于自己,他们是为艺术而生、而死的。
《大师》读后感(三):大师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是19世纪蜚声欧美文坛的小说大家。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Colm Toibin)的《大师》(The Master)就是一本以他为主人公的小说。作者截取了他1895年到1899年四年间的一些生活片段,采用第三人称,用现实和回忆交织的手法,大段的内心独白,不仅把读者带入到亨利詹姆斯生活中19世纪的美国和欧洲;也带入到这位大师隐秘生动的心灵世界。
一八九五年,已被后备作家称为“大师”的亨利詹姆斯梦想着以一部戏剧征服伦敦。然而,他的第一部戏剧就一败涂地。在失败的阴影下,他接受了爱尔兰贵族的邀请,在酒筵歌席中独自品味他人到中年的困顿和创伤。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一直写到一八九九年他的兄长威廉詹姆斯去他隐居的英国拉伊小镇去看望他。这四年中,他的生活虽然平静,但内心却波澜四起。他常常怀恋那些他生命中的重要过客,她们以不同方式在他的作品和灵魂中留下印痕;他为自己的性取向困扰不安;他回想自己的家庭,亲人们对自己的影响;他渴求温暖和慰藉,却时时不忘留一份孤独和安静给自己……
整本书分为十一章,而几乎每一章都有相应的主题,可以独立成篇。心理描写是这本书最大的亮点,这一点尤其表现在描写作家情感的那几章,这里不仅有异性间的相互吸引,也有同性中的微妙暧昧,在作者含蓄又不失深沉的处理下,显得既不动声色又暗流汹涌,让人读后在心里产生久久回响。托宾典雅细腻的笔触,平缓蕴藉的叙述,让大师的敏感与矛盾,孤独与痛楚像一幅交织着复杂和精美的画卷向我们缓缓展开,而这也是他半生飘零,孤独终老的一个缩影。
身为小说家的亨利詹姆斯虽出生于一个纽约的上层知识分子家庭,但长期旅居欧洲,而且终身未婚。在小说中,和他产生过感情女性有两位,一位是他的表妹明妮 坦普尔,一位则是同是小说家的康斯坦斯 费尼莫尔 伍尔森。这两位都是不寻常的女性,前者冰雪聪明,高贵机智;而后者特立独行,智慧卓绝。她们都很独立,而且都深深地爱着亨利詹姆斯,最后也都落得相似的结局。明妮坦普尔年纪轻轻便因病而亡,而康斯坦斯 费尼莫尔 伍尔森则选择用跳楼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她们的死都对亨利詹姆斯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不断忆起她们,怀念在一起的种种往昔,怀着悔恨负疚的心情把她们写进自己的作品,用这种方式让她们永生,永远和自己在一起。但在她们生前,他至始至终无法安放她们对他的感情,只能粗暴地拒绝或者沉默,甚至在她们临死之前都不愿意伸出援手。他明白是自己将她们推向了绝望的深渊,这种想法让他痛苦并充满罪恶感,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必须撇开她们,以便去“继续走他自己的天赋和天性之路”,在对她们的回忆里,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两种想法是怎样在他心中剧烈地挣扎和撕扯“……他转身朝向屋内,觉察到一个让人不堪忍受的尖锐想法正盯着他看,像空气里的什么食肉性的凶猛活物一般,悄声对他耳语:他更希望她死去,而不是活着,她失去生命后,他知道该拿她怎么办,但他温柔地像他求助时,他却拒绝了她。”他的选择成就了作为大师的亨利詹姆斯,却永远地失去了爱着他的女人们。
在他生前,关于他性取向的怀疑和猜想就已经开始了,他十分清楚这些,但不打算给任何人答案,也给不了自己答案。小说的第四章写到当时英国著名案件:剧作家,诗人,也是亨利詹姆斯对手的奥斯卡王尔德因为和贵族美少年阿尔弗莱德 道格拉斯(波西)的同性之情被波西的父亲告上法庭,闹得满城风雨。案件的始末在亨利和朋友的对话中展开,借这些对话,托宾巧妙地把这两位“大师”做了悄然对比,王尔德的行事张扬,激情浪漫越发衬托出詹姆斯的沉默内敛和克制隐晦。这样一来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从小说第一章起他就只能默默地在他人窗下徘徊,“站在那里,仿佛漂泊在海上,心知踏出那一步,就会走进那不可知的飘渺之方。”但他终不会踏出这一步,他唯一能够做的只是想象,像写小说那样想象,想象屋里那个人发现了他,想象他们一起上楼,想象接下来将会发生的事情,但这一切永远都仅仅是想象,“那一晚,他伫立雨中,直到窗口的灯光渐渐淡去。他又等了一会儿,看看是否会发生什么别的事,但窗子始终黑着,什么都没有泄露。于是他慢慢回家。他又踏上了干燥的陆地。衣服湿透了,鞋子被雨毁了。”被雨水一同毁掉的还有他爱的能力,终其一生,亨利詹姆斯都没有给任何人他们想要的爱情,当然也包括他自己。
从保存下来的文字记录来看,现实中的亨利詹姆斯为人沉默寡言,彬彬有礼,对写作和观察生活都极其认真专注,但始终和他人保持着一定距离,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他的大部分作品风格晦涩幽微,也没有留下关于自己的详尽回忆文字,所以,《大师》里面的亨利詹姆斯只能是托宾心中的大师,而不是完全现实的那个生活在19世纪的亨利詹姆斯。《大师》是小说,而不是传记。福楼拜的母亲曾经对儿子说,“你的心早已枯死在对文字狂热的执著里”。托宾笔下的文学大师亨利詹姆斯正是这样的一个人。穷尽一生,他全部的激情,热望,勇气和爱意都奉献给了世上最美的文字艺术,这是个人生活的悲剧,却是小说家的命运。
《大师》读后感(四):因写作而枯萎的心
因写作而枯萎的心
亨利•詹姆斯是著名的作家,而我第一次知道他是读梁文道的《我执》,那篇《没有心的男人》讲的就是他的故事。“想象一个男人生来就少了一颗心,他善良,正直,彬彬有礼,但就是没有那颗心”,写下这句话的是一百多年前的一位女作家康斯坦斯•芬妮摩。
亨利•詹姆斯与康斯坦斯•芬妮摩的暧昧持续了十多年,但他始终一边表达着自己需要她一边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在听说康斯坦斯•芬妮摩自杀后,他赶到她家,在帮她整理遗稿的同时,把涉及到自己的文字一一找出来烧掉。他害怕人们知道康斯坦斯•芬妮摩曾经爱过他,更害怕人们会认为她是因为他的冷漠而自杀。他没有找到类似“我不愿意活下去,是因为詹姆斯不能爱我”这样的遗书,却在康斯坦斯•芬妮摩的一份写作提纲里看到了这句话“想象一个男人生来就少了一颗心,他善良,正直,彬彬有礼,但就是没有那颗心”——他的一生,或许恰恰印证了这样一句话。
在我看来,科尔姆•托宾的《大师》就是围绕这句话,将亨利•詹姆斯的一生缓缓展开。《大师》是一本以亨利•詹姆斯为原型的小说,从一八九五年写到一八九九年,都是他步入中年在写作领域有了相当名气后的岁月。虽然这四年的生活对亨利•詹姆斯来说相对平静,但大段大段对往事和故人的回忆弥漫其间,读者也因此能够窥见他的一生。《大师》的文字极为细腻,几乎使得读者能够贴近亨利•詹姆斯的灵魂,体味他的写作与人生相互交织纠缠,以及他为了写作而“牺牲”的那些感情。对于爱过自己的人,亨利•詹姆斯从未回报相应的爱,他冷酷地观察那一个个与他生命有着密切联系的人,并把他们化为了自己笔下故事里元素。这是亨利•詹姆斯最为残忍的地方,他细致地观察和刻画她们的情绪,却始终没有“那颗心”,那颗懂得去爱一个人的心。梁文道评价:“很难有第二个男作家能像他这般,无微不至地同情笔下的女性,刻画她们的无奈和伤痛如自己亲历。可是,他却是一个没有能力去爱的人。”
在《大师》中,亨利•詹姆斯回忆康斯坦斯•芬妮摩的自杀前后,他清楚自己如果在冬天去威尼斯看望她,她就不会自杀。“由于他心里有些什么抵制了她,由于他对传统和社会礼仪的尊重,他把她丢在了那里。他可以救她,只要他送去一个信号”。他需要她的感情,但又逃避她的感情。他所做的,只是在报上读到她的自杀消息后,自我安慰自己并无责任:“他想,他什么都不欠她,也没有答应过她什么必须要做的事。他们不是情侣,也没有血缘关系,他安慰自己说,他欠她的唯有友情”;之后,他在整理她遗稿的同时,把她留下的跟他有关的信件全部找出来烧掉了,他甚至没有再看一眼自己写给她的信。
除了康斯坦斯•芬妮摩,亨利•詹姆斯还有过一位红颜知己,那就是她的表妹明妮•坦普尔,他们互有好感,但他最后却放任她孤独地离开人世。多年后,他找到她写给她的那些信,那些明明白白向他发出请求的信:“假如我想尽办法,明年跟朋友在罗马过冬,我能见到你吗?”“亲爱的,想一想我们一起在罗马的快乐吧。仅仅想到这我就要疯了。只要能在罗马过冬,我可以不惜一切”……亨利•詹姆斯没有帮助明妮•坦普尔来罗马,他甚至没有鼓励她,后来她也不再这样直接请求了。在那时的他的心中,自己观察世界创造作品的空间不容任何人来打扰:“那年,他逃入了他盼望已久的明亮的旧世界。他写着短篇小说,领略着种种感受,慢慢构思着他最早的长篇小说……他不想要她疾病缠身的表妹。即使她身体健康,他也不确定自己是否会欢迎这样一个具有率性的魅力和好奇心的人在身边。他当时要的是观察生活,或者用自己的眼睛想象世界,如果她来了,他就得透过他的眼睛看世界了。” 更为恐怖的是,“他更希望她死去,而不是活着,她失去生命后,他知道该拿她怎么办,但她温柔地向他求助时,他却拒绝了她。”这一章的结尾并不是亨利•詹姆斯的悔恨,而是他因为想起明妮•坦普尔,改变了他一篇小说的写作思路,他要再次挖掘他表妹明妮•坦普尔的生与死,以更好地塑造他笔下的故事。
《大师》用细腻的笔法,还原了亨利•詹姆斯那颗因过于投入写作而枯萎的心。他可以思绪万千,但始终保持着生活的一种平衡。他因写作而主动地选择孤独,但又用写作来抗衡人生的孤独。他未曾好好对待爱自己的人,但又让她们的灵魂在他的笔下得到永生。《大师》很清晰地道出了作家与他自己的人生的复杂关系,对笔下文字的狂热反衬着他现实中的冷漠。那些在他生命中留下痕迹,又被他深深伤害,最后随着他的文字而得以让灵魂流传后世的女人,是多么不幸。“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没有心”的亨利•詹姆斯没有这样的“肩头”,却用写作把她们都送上了悬崖。
《大师》读后感(五):借尸还魂的美梦
一边读着托宾还原的他自己心中的大师的时候,一边就在想,如果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喜欢的人可以在我的笔下借尸还魂,我会怎样来写他,怎样去揣测他的生活忧虑和快乐。恰好我一直有为一个旧识借尸还魂的打算。从四五年前开始就在断断续续地写着他的故事,用我仅存的模糊记忆,加上我的伟大想象力,试图还原当年的他。除了他现在并没有死,其他的都跟托宾的意图一样。
托宾自己一定是爱着大师的,所以在大师死后将近一个世纪,还紧紧抓着大师的故事不放。就如他自己揣测大师对于女性的描写是一样的。托宾一直一直在强调,大师在自己的书里面写着自己的表妹。大师在明妮死后让她到了欧洲,让她生活在欧洲,让她有了财产,让她可以得到外在的独立,改变她的困窘境遇,让她不只活在他一个人的回忆里,还尽可能多地让她为世人所知,并尽可能得让她活得比生前快乐。
“如今她死(明妮)了,他可以控制她的目的地,给她她想要的经历,并将戏剧性赋予一个被残酷缩短了的生命,他想这事是否发生在他之前的作家身上,霍桑或者乔治•艾略特是否为了起死回生而写作,他们日夜不懈地劳作,像魔法师和炼金术士那样,挑战命运、时间,和所有无法消解的因素,是否为了重新塑造出一个神圣的生命。”
我也有这样的打算。我想把我的旧识那几年的故事写下来,因为那几年的经历不够圆满,而那些不圆满一直都横亘在我心里,偶尔在梦里都会看到圆满的结局,只是醒来之后,失向来之烟霞。于是总是很强烈得想要去还原我心中的那个形象,让他被我塑造和润色。然后在我写的故事里,他的境遇从头到尾都逻辑分明,故事的脉络从头到尾都被我掌控。我想让他快乐时他变快乐,我想让他伤心时他便伤心。
托宾为了能够让大师死而复生,一定查阅过很多资料,看到小说最后作者附上的参考书目,我也非常感动。他笔下的大师并不是真的亨利•詹姆斯,只是他心中的大师而已。即使这样,他还是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力图自己理解的大师并不会与真的大师相去甚远。文中的大师却没有这样的忧虑。因为他要写的人写的故事都在他自己的脑中,即使是听到的别人的故事,也是建立在自己的理解和想象之上的。所以他不需要征询他人的同意,他甚至希望他所写的人是死去的,这样就没有人会左右他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他只用自己的视角去回忆,于是那些故事才是还原了专属于他的回忆,在他的控制之下。
我想说的就是在写作者的控制之下的角色或人物。
在我看来,不管是托宾还是托宾笔下的大师,都恰如其分地体现出写作者自身所追求的那种控制感。托宾写大师对待明妮的态度,写他不愿意带着明妮一起来欧洲,是因为明妮来了,大师觉得自己会被影响,会通过她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大师怕失去自己对于自己生活的控制。在我看来,大师从美国一路远离来到伦敦定居,想要的恐怕就只是控制感而已。在那里不用被兄长威廉影响,不需要透过明妮的眼睛看待世界,自己的生活虽然时不时被朋友们打扰,可是大多数时候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
直到康斯坦斯•伍尔森带来的变化。起初遇到康斯坦斯的时候,大师被她吸引,我想除了她特殊的气质、才气,更多的是康斯坦斯所具有的那种不想被人控制也不愿意控制别人的性格。于是在大师心中,康斯坦斯是安全的存在,因为不需要为了得到与她的关系而奉献出自己对于生活的控制权。其实这在我看来本身也是一种控制。大师一直控制着他们关系的远近亲疏,需要她时就去找她,不需要她时就离开,并且以为他们可以这样忽及忽离一辈子。我猜想大师心里面并不是真的安全的,因为他们的关系虽然表面上在他的掌控之下,可是两人彼此的信任并没有因此而增加多少。所以当康斯坦斯突然不在大师的控制之下时,大师就呈现出无法接受的情绪了。他以为他们的关系一直在他的控制之下,所以他以为他可以预测康斯坦斯永远不会向其他的朋友很熟悉地谈起他,袒露他们比其他人想象的要亲密很多的关系,可是康斯坦斯却说了。这样的诉说本身就像一个秘密被泄露了出去。试想少时小姐妹之间的秘密被泄露之后,一方会因为另一方的行为受到很大的伤害。虽说大师和康斯坦斯都不是小朋友了,可他们的内心在我看来脆弱不堪,不比小朋友坚强。所以这样的泄露本身就相当有杀伤力。加上这样的泄露意味着大师所引以为傲的控制感的流失,大师一时间就完全无法适从了。所以大师没有去意大利,没有再见过康斯坦斯,两人曾经一度疏远,直到康斯坦斯自杀而亡。
看到其他的评论,有责备大师的也有同情大师的。现在边写边想,我有了很不一样的感觉。如果是我,我会怎样对待我与旧识现在和将来的关系?寒假就在家遇见了他,虽然没有春心萌动小鹿乱撞,多少还是有惊喜的,想来他也是一样的,所以两人很自然地开始聊天。他比从前的话多了,当年那些带些稚气的话都没有了,话题围绕在找工作周围。我笑着说你现在讲话很在行了啊,他也笑着答,你对我的记忆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的,早就变了。分开之后我就一直在想着那句话,回忆变得黯淡无光。当天晚上就梦见跟他并肩坐在公交车上,他还是当年的模样,我困了,他轻轻地笑,我就靠着他的肩膀睡着了。于是醒来,感慨万千中,决定无论如何要写一个他的故事,让曾经的他起死回生。寒假时也有交换过电话号码,但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想过要打给他。大概他的变化或者成长是我控制不了的,而我能控制的,只是我们的回忆和我自己笔下的故事而已。所以不敢去主动联系他,不敢介入他的生活,不敢让已经改变的他介入我的生活。这个时候的我,跟书里面的大师是一样的。我们都害怕,害怕在不受自己的控制的时候,自己会被控制,自己会不自由,自己会被伤害。
所以大师疏远了康斯坦斯,就像疏远其他所有的人。大师想要他自己的世界,于是活在自己写的故事当中成为最安全的选择。而那些故事,故事里面的人物,人物之间的关系,会渐渐地进入他的生活,成为他的真实的一部分。大概又因为那样的故事本来就来源于他真实的故事,所以才那么容易起死回生。
“他知道,作为一名艺术家,安德森可能知道,或者至少也有所了解,他每写一本书,每描绘一个场景或者创作一个人物,它们都会成为他的一部分,进入他的创作灵魂,如岁月流逝般积淀下来。他和康斯坦斯的关系很难解释。安德森可能还太年轻,不知道回忆和悔恨可以交织在一起,不知道有多少悲哀可以承载,也不知道那些只有在逝去或丢失后才具有形体和意义的东西,即使如此,在一心一意的压力下,又有多少事可以忘记后又在夜里带着刺骨的疼痛回来。”
大师是后悔的。我仍然好奇,再一次给他选择的机会,他会怎样。不管是从前的明妮还是后来的康斯坦斯,我猜想,再有一次机会,大师仍然会缩回壳里,放弃她们。这是大师自己的风格吧。他要让他的人物全都在他的笔下生根,不管他们发生何种变化,都必须经过他的批准,不能有差。而有的人不会这样。有的人会让笔下的人物自由地流动,大概会给他们设定一个背景,给他们一些关系,然后人物就活起来了,有的时候在写作者不能控制的情况下自己活着。不知道是不是我对大师的了解过少,我觉得大师不会这样。而我自己,常常是为了让人物起死回生而写作,于是不愿意他们不经我的允许发生改变。可是这样的故事终究属于自己,不承担任何风险,他们与我的关系也没有曲折坎坷,一切都是从我下笔时就决定好的。现在偶尔会想这个,偶尔会有一点点遗憾,如果我让笔下的人物自己去玩,会不会更加精彩。如果我愿意放开一点点保护,如果我愿意哪怕胆怯着踏出一小步,会不会有不一样的人生。
《大师》读后感(六):于追忆中失去
■ 梦醒了吗? 最初翻开《大师》时,想到《在天使手中》。 同性恋作家写同性恋前辈,是自我抚慰;在致敬之外,更是领会精神,怎样敏感才能流芳百世。两者都以虚构内心为主导,但视角全然不同,费尔南德兹的《在天使手中》是俯瞰式的白描,虽有第一人称的口吻,帕索里尼的生活印痕却被头顶上的叙述者看透,另一种讲述;托宾的《大师》则像亦步亦趋的尾随者,亨利·詹姆斯的一举一动皆被窥伺,其心理流动则变成第三者的代入遐想,一种玩味。 另外,在结构上,《大师》只选取了短短几年的横截面,却思绪迸发地向过去绵延进军,比着力浩瀚编年的《在天使手中》迂回婉转得多。 但同时,《大师》的章节标题极具误导性,从第一章的“一八九五年一月”到第十一章的“一八九九年十月”,短短五年不到,“实时”故事少得可怜,且大多流转于聚会、拜访等社交场合。这种框架像是一种提醒,亨利·詹姆斯的追忆远远飘出现实囚笼,在反复撞击往事中挖出不为人知的隐秘之情。 关于创作,关于贪恋,关于亲情,关于模糊未定的陪伴。在走马观灯似的交际活动间,内心向的亨利,在梦境中追寻,在黑暗中自忖。 他渴求被拥抱。 他希望不被打扰。 他想消除自我。 全书十一章的内容可以玩笑般地如此概括:一章梦醒,一章爱尔兰之旅,两章鬼故事,两章手疼、手继续疼,一章家族往事,两章康斯坦斯,一章重游罗马,最后一章,哥哥登场。 从始至终,亨利·詹姆斯对自己的写作坚守信念,并怀有纯艺术化的骄傲,这亦是他从情感上得不到的满足。在繁花乱坠的社交描写中,夹杂了大量名人八卦及评说,比如对王尔德的嫉妒及花边追讨,对乔治·艾略特的丑貌平常一视,对霍桑作品的第二眼鉴赏。关于亨利·詹姆斯自己的写作之见,则融进了回想,变得感性。他就像黑暗中的孩子,以强化鬼魅来还击鬼魅,追求刺激,戏剧性,以及纯粹释放。 ■ 还寂寞吗? 在世时他已被尊称为大师,在世纪末的舞台上,他却有点无所适从,王尔德的天才让他钦羡,他只有更勤奋,而更多的是,他真正“最亟须写下来的东西却不能示人,无法发表,不会有人知道和理解。”(P8)无论他走到哪儿,都受人景仰,其作品在闲暇时屡屡被提及,无数女人想成为、想装扮成他笔下的黛西·米勒,就连他购置别墅时,房东听闻他的大名和职业,大吃一惊后很快签约。即便如此,亨利·詹姆斯也并不觉得写的小说有多了不起,《大师》塑造的亨利,有着意想不到的反讽效果,以及清醒自怜的出世形象。 他似乎“决心为极少数人写作”,“也许是为将来写作,却不收获他现在享有的回报”。正因如此,他拥有骄傲,他从未妥协,他一直为“创作纯粹的、不完全被功利心左右的艺术品”而奋笔疾书。在持续手疼时期,他却认为这种疼痛正是神明旨意,握笔并无不适,即暗示着他要一直写下去。 当然,这是作者科尔姆·托宾眼中的作家亨利·詹姆斯,完全可以说是他虚构中的亨利·詹姆斯。将私人化创作谈交织进一个世纪前的回望里,很聪明也很大胆,托宾并不关心怎样还原大师,而是直接深入大师,细节真实是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追求在于体现情绪张力。以己代入的做法无疑是说起来容易,可是如同书中坦言的那样,“阅读和写作一样,沉默、孤独、私密”,那么托宾要做到化身亨利·詹姆斯,简直就是要在沉默中爆发,让孤独发光,令私密悦人。 是两个灵魂的来吧我们穿越的同声呼求。 在后来,与雕塑家安德森相处时,亨利正构思一篇“死后”文。其中提到的创作理念非常有神韵,不难想象,托宾同学写到这里一定通体愉悦: 【与安德森创造的城市相比,它什么都不是,又什么都是。在细节、对话、缓慢的情节和神秘气氛中,它反对抽象,反对单调乏味,也反对愚蠢的大而无当的概念。然而它茕茕孑立,弱小而缺乏保护,几乎没有存在感。 P274】 对于易感的托宾来说,揣测一下或者说矫揉一下亨利·詹姆斯的敏感——敏感是超越才华的存在——有什么难的,那都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古风同人又不是考据传记,加上自身同性恋身份的恰到好处,对“得不到”即“失去”的权衡可谓是水到渠成。 全书的行文框架,也喻示着将亨利·詹姆斯罩在一生未婚的柜子里。 总之,他是个好人。(咦?) ■ 还苦闷吗? 开篇是经常梦见,亨利在梦中看见逝者,已经失去了的母亲似乎要传达点什么,她表情苦楚,他莫名无助。到了第十一章的尾声,嫂子爱丽丝详述了通灵一事,母亲通过灵媒之口说出对亨利的担忧,以及一种希望他不会孤独的祝福。 他到底有多深的孤独,无人能知。能确定的只是,他孑然一身,他像他的作品那样,是为极少数人准备的,甚至是留给未来的可追求伴侣。有一种悲哀,在艺术追求上走得越远,能陪同你走下去的人就越少。 说起来,亨利·詹姆斯也不是没有喜结良缘的机会。 《大师》里重点抒发了对三位女性的难以释怀之情,抛开妹妹爱丽丝,另两位那也都是个性强烈、天赋异常的佳人嘛。值得批评的是,亨利的怯懦、躲闪、优柔寡断,每到关键之处,他就拒绝、逃避、抱头掩面。人家一个姑娘家家说要过来,你为什么羞得像另一个姑娘家家似的。 也可以理解他这种纠结心理,女性越界对他来说,是件多么恐怖的事。亲密交往可以,但再进一步会让他崩溃。可最终呢,他没崩溃,她们崩溃了(嗯我在夸张)。 体验过与女性同居的生活,对于他来说,人生似乎无憾了。第八、第九章是献给康斯坦斯的回忆,并且再次照应开篇,“贝尔索加多是一座城堡”,亨利与康斯坦斯的同居极为微妙,“她活在内心里,他认为很不寻常”,可由于彼此才华的共鸣,他俩之间有着一种共享性质的舒适。 可亨利是不可能依赖她的,也不希望被过分骚扰。随着亲密关系的磨损,事态开始变化。 不过他是个好人(咦,又来了?)。 他不愿意给他的女性朋友们造成伤害,又出于性格问题,没法解开彼此间的结,于是闷到死。 ■ 还敏感吗? 最后来说最敏感作家的最敏感之点。(终于到了!) 先回到开篇。一、亨利·詹姆斯对奥斯卡·王尔德的戏剧卖座简直就是红眼加咬手帕;二、与王妃朋友闲谈时,提到一个久违的名字——保罗·约科斯基,与亨利在二十多年前的巴黎,发生了点什么,但只有场景以及亨利的凝望,其余皆淡去;三、在第二章爱尔兰之旅,遭遇稳重的陆军下士“兼”男仆哈蒙德的服侍,两人都有点心照不宣的沉默,在日常问候中飘忽不定的刺探隐隐作祟,但此时的亨利认为,他与哈蒙德间的静默对峙应该被一个路过者或旁观者打破,欲说还休充满了诱惑色彩,隐在目光之下。 总强调自身在“黑暗中”的亨利,对渴求拥抱实在是无比强烈,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内心需求,而变成近乎“空无”——“通向理解上帝之路的一步”——的信仰。说通俗一点,他一个人太久了。 开篇埋下的隐情,后来一一延展开来。在第四章里,第三次涉及王尔德,只不过在此,是关于王尔德的有伤风化案的八卦传闻。亨利对王尔德的才华是无奈地嫉妒,文人相轻很好理解。可一听起王尔德的八卦,就相当有味,积极找两位朋友“轮班”来给他讲述新消息。其实,亨利此刻的表现,就像在打听同类的苦难遭遇。王尔德很爱秀,亨利不敢;王尔德不仅结婚生子了还频繁找男伴儿,亨利不敢;王尔德是招摇受,亨利是隐忍受,唔鉴定完毕。 当然,这一片段并不能带出亨利·詹姆斯的隐秘之心。 《大师》里真正涉及对男性的向往或说对男色的渴望,仅有三处,而这在全书转来绕去的追忆里只在很小的一部分。它们强调的是“不可得”及“失去”,这份隐秘情感成为亨利生活的底色,而非夺目的泼洒。 第二章,与哈蒙德的相处,亨利处于宾客地位,该收敛的都收敛好了,除了两眼光光,还能说点什么吗?送书给你?没问题,回伦敦就寄给你。在这一阶段,亨利在观望状态,连最肤浅的意淫都没有,非常纯洁。 第五章,回忆中与霍姆斯的共处一夜,这下搞大了,亨利非常有福地看了一场壮男脱衣戏,霍姆斯本人世故,亨利评价他“内在戏剧十足”,确实如此。裸身的霍姆斯极具视觉诱惑,亨利却能审美状地看成“静止雕像”,可见定力不错。在某种有色期待中,亨利克制也故作平静,此刻,霍姆斯爬上床说了句“我希望你不会打鼾”,挑逗加喜剧意味。故事没有终了,在睡还是不睡的生存困境面前,睡不着才是大头。亨利心跳多少没有统计,亨利渴求拥抱无需赘言,他反复推测霍姆斯是否入睡,却在对方一个很自然的拥怀下睡去。 第十章,重游罗马邂逅雕塑家亨德里克·安德森(Hendrik C. Andersen),安德森年轻俊美才华满溢,积极主动忠诚如狗,可谓活半个世纪才能遇上的一只尤物啊。安德森请求陪亨利一起去“无论那是什么地方”的地方,于是两人相约来到墓地。看到这里,我有种错觉,仿佛《在天使手中》末章中可怜的帕索里尼被年轻男孩诱拐出去的感觉,然而看下去,才发觉这竟是《大师》全书里最温情的一幕:安德森抱住了因逝者生忧的亨利。安德森是那么甜美(让人酥软),他把亨利当成自己的人生寄托(很有目的),目光如炬,虔诚跟随。亨利在美貌软化下、在温存感化下,邀请安德森去自己在拉伊的兰慕别墅做客。 亨利先回到了拉伊,将之前买下如今寄到的安德森的伯爵雕塑放置在客厅,满心雀跃地为年轻朋友的到来做准备活动,并且,陷入粉红色的“与安德森一起生活”的美妙遐想中。此时的亨利,全身心都献给了安德森,被彻底虏获了,假如看到接下来他把自己的遗产也留给这位俊男,我也不会吃惊。 而故事同现实后妈一样,总要无情击碎各种幻想。安德森只过来短住三日,亨利有点萎然,老天爷也不给情面,天气不好,家里蹲对一个年轻人来讲是多么沉闷的事。 他们除了聊天,没事可干。 安德森聊起他的世界城市的理想,亨利同时构想着一个不简单的鬼故事。 【“我们最需要的是,”安德森说,“把这个计划宣传出去。” “确实如此。”亨利应道。 “我想,由于你很熟悉我的作品,你能否为此写篇文章发表到什么杂志上去?”安德森问。 “我想我只会写小说。”亨利说。 “你写过文章吗?” “写过,但我现在只写微不足道的虚构作品。我想,我只知道这些。” “但你跟有影响力的编辑很熟?” “跟我合作过的大多数编辑不是已经死了,就是退休了。”亨利说。 “但你要写一写我的作品和计划,如果杂志对此感兴趣的话。”亨德里克问道。 亨利沉吟着。 “我想,”安德森继续说,“我能在纽约找到对此感兴趣的人。” “或许我们应该把艺术批评交给艺术批评家。”亨利说。 “但如果能找到一个想要我作品描述的编辑呢?” “我会为你做我力所能及的事。”亨利微笑说道。他从桌边起身,外面已经天黑了。 P274-275】 此时的亨利相当克制,亨德里克则是句句追问,其目的不言而喻。当然这也不算太过分,安德森有才华,亨利有名声,他需要借助欣赏(爱慕)他的他的伯乐之笔,以获取更多的关注。 步入暮年的亨利,无可奈何地表现出一种对年轻肉体的迷恋。在安德森最后留宿的夜晚,他在楼下读书,听着楼上安德森脚步声开始愈加大胆地想象对方逐件脱衣脱裤直至裸身躺在床上的景象。 次日早晨,安德森告别。他握住亨利的手接着又抱住他。他对亨利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对我太好了,你相信我,这对我太重要了。” 看吧,好人卡发出! ■ 还需要吗? 还是最后。 在安德森离去后的第十一章里,哈蒙德再次出场,与亨利拘谨对话,在第十章亨利等候安德森来访时再次带出保罗·约科斯基的名字,那是一个久远的过去,于是回到过去。早年的亨利,曾为当素描模特的表哥裸体驻足。早年的亨利,避开战争,从准备进修法律到发表小说,再到旅居海外,身为次子的他隐约在逃避什么。在终章里,嫂子爱丽丝旁敲侧击谈论起妹妹爱丽丝的同性恋倾向,而这种指摘俨然刺向了亨利那并不勇敢的心上。 与此同时,兄长威廉也身体力行地挤兑了可怜的亨利一把。在这里,要赞美一下写作者科尔姆·托宾——为我带来全书唯一的笑点: 【威廉对自己的【务实】品质十分自豪,他是【一个有家室的男人】,【一个不写虚构作品而做讲座的男人】,【一个言行举止都很平易的美国人】,代表的是那种【粗线条的男子汉】气质,而非他弟弟那种优柔的腔调。 P284】 由此可见,威廉是多么为自己的直男身份而自豪呀。 可怜的优柔的亨利,你没有遇见一个务实的、粗线条的、言行举止都很平易的、不写虚构作品而做讲座的、能带给你一个“家室”的攻君,是多么的悲惨! 不过没关系,你在你的追忆中、我们的追忆中永生。 没关系,我们坚信,【你是个好人。】 04/02/2010
《大师》读后感(七):A Layperson's Review of The Master
A friend recommended the Master by Colm Toibin to me when I told her I really enjoyed reading The Hour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The two novels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in that both are about the life of a novelist(Henry James and Virginia Woolf respectively) but neither is a memoir. They are fictional stories based on the lives of real people.
In the middle of reading the Hours, I was irritated, thinking, Michael Cunningham was stereotyping the three women. How could he know what Virginia Woolf was going through in her life or what thoughts were going through her mind? How audacious he was to presume that she committed suicide the way he described it! But later the book won me over, because I saw his point of paralleling the three women's lives and the theme seems to be, if I understand correctly, at least one of the themes seems to be: Life is composed of hours/moments that are similar to everyone. It transcends time and space. No one is too ordinary and no hour of anyone is going to waste.
If my reading of The Hours went from "dislike" to "like", my experience of reading The Master went the other way around. I put aside novel-readings at the beginning of April because I felt my resolve of working on my accent was fading. But I got tempted to read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Master two weeks ago and got hooked on it right away. I emailed my friend saying that it seemed The Master was really my cup of tea, even more so than The Hours. But as I went on, I got less enthusiastic. I kept on wondering, waiting for a big climax and expecting to find out: Was Henry James GAY? maybe I was too gossipy and voyeuristic. But come on, isn't sexual-orientation part of a person's identity? If you want to know a person really well, you expect to know whether he is in the closet or out. It took only one semester for my graduate school classmate to tell me he was gay. The book covers five years of Henry James' life in 300+ pages. Don't I deserve to find out whether he was gay or not after reading it?
From the beginning, a friend mentioned Paul Joukowsky's name to Henry and he was disturbed and agitated about that poignant memory. I was eager to find out what had really happened between them. But no, the story continued and there was this servant guy Hammond that waited on him in Ireland. The way Henry was observing Hammond and being self-conscious really hinted that Henry was gay. But both threads didn't go any further. The story went on to tell the story of Henry's family, his sister Alice and a cousin Minney, both of whom died before the story started in 1895. Henry seems to feel guilty about their early deaths and felt that he could have done something or have been closer to them. Instead he left them and stayed in Europe, kind of on "self-exile".
Henry had a fellow American novelist, Constance Fenimore Woolson, who corresponded with him and they exchanged comments on each other's writings. She apparently admired him, as many writers, esp. female writers did at that time. To me, they were almost like soul-mates. But once Henry heard from a friend that Constance mentioned something that indicated the closeness between her and Henry, he freaked out and cancelled his trip to Florence where Constance lived for that winter. She committed suicide afterwards, partly because of her chronic depression during winters, partly, maybe of Henry's withdrawal and distant attitude.
Chapter 10 is about a younger sculptor friend, what's his name? Hendrick Anderson. They met in Rome and he came to Henry's house in England for a brief visit. The way Henry thought about him before his visit and the anticipation of his arrival, and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Henry's imagining what Hendrick was doing upstairs before going to sleep. I was like, he is totally in love with him! But that didn't go any further either. Hendrick was on his way to New York and was very excited about his trip, which he embarked on after a three-day stay in Lamb House.
The last chapter is about Henry James' brother William, who visited Henry at the end of 1899, the end of that millenium, with his wife and daughter. We got to know more about William's struggle. Also, through a medium, Henry's sister-in-law said, Henry's mom said Henry was going to outlive all of his family, but he wouldn't be alone because his mom was watching over him.
That's about the end of the novel, which left me unsatisfied. Maybe because the story only covers 1895 to 1900 that I only see a slice of Henry's life? Or was it because of the genre, fictional story based on a real person? I have to say, not a big fan of this way of storytelling. I want to know Henry Jame's sexual orientation! Although I understand the theme is about his repressed sexuality. But is he gay? Wait, Let me google Henry James' sexual orientation. While I was putting "Henry James' sexual orientation" in google search bar, I laughed at myself: Maybe this is the brilliance of the novel. I guess, if I want to know Henry James' sexual orientation for a fact, I can go to a documentary or a memoir. If I want a fictional character, I can go to one of many Henry James' novels. This half-memoir, half-fiction story actually attracted a lot of readers because it is unique, it is different from a memoir or biography of Henry James, and a fiction. And Colm Toibin knew he couldn't beat Henry James if he created a fictional character. Instead, creating a fictional character out of Henry James's biography made the book a sensation. The theme, according to Wiki, is "not of someone who just represses his self and his sexuality but of something more complex and ambiguous, of somebody who copes with life exerting a control on how much he'd reveal, even to himself, and choosing to be a writer in order to achieve precisely that". I guess that's why I am just a 俗人, 哈哈, therefore the title "A Layperson's review of the Master".
As a side note: the book was only short-listed for the Man Booker Prize but didn't actually win it. Maybe there are other people like me out there, being annoyed by this genre.
《大师》读后感(八):漫长的告别
要描述托宾,下意识想到的词是细致、缓慢。他的悲哀乍看过去并不磅礴,像一滴滴细小的水珠,由檐角日复一日地落下,日久年深,才慢慢洇出模糊的一块。就像他笔下的人,似乎总是无话可说,或欲言又止。当全世界都在大声呼号时,他们退到角落去,默默咀嚼,久久凝视心中的深渊,企图通过一次为时漫长的内在角力来消化所有难言的悲哀,与一切告别。
有的作者选择在事件情节中急奔突进,追求短跑般的刺激和发泄的快感。托宾更像一位马拉松选手,在漫长的赛道上一点点消耗心力向前,探取所有细节,内里情绪跟着汗水逐渐挥发,等到停下来时,不过轻轻喘出一口气。
他的长篇小说《大师》,结合真实与虚构,写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书里戏剧性场面与真正具备起始转折结尾的故事均寥寥,和这位擅长描摹人物心理情绪的小说家亨利一样,托宾揉碎了情节,朝里探测挖掘这位作家的内心,并站在他的心底观望外部世界。 1895到1899年,亨利·詹姆斯已年届五十,历经创作的挫败,亲人离世,永别故友,退避社交而又深切渴望陪伴,孤寂却从未表露,几乎一辈子都在独自生活,这位笔法细腻的作者,将自己禁锢在其内敛而封闭的灵魂深处,永远维持一副翘首期盼却又掉过身子佯装无动于衷的姿势,本应有所动作但还未迈出第一步就停滞下来。在《浮生一日》里提到已消亡的亚格汉语,其中有个词汇是“Mamihlapinatapai”,专门用以描述双方都企图行动却均不愿迈出第一步的这种悬停、一触即发、利箭脱弦前的状态,而托宾笔下的亨利·詹姆斯,克制隐忍得几近残忍,他折断了那支本应射出的箭,并硬生生刹住了脚步。 托宾同样残酷,他贴近亨利身侧,探查他千折百回的情绪变化和深掩于心的、幽暗曲折的秘密,却未以浓墨重彩铺陈,所有的描摹都冷静且克制,人物的庞杂心绪不断涌现交织,到头来也只浮现出些微末端,就更显得触目惊心。 如他这样写亨利·詹姆斯于深夜,在其心仪的男性友人窗下徘徊(节选): 黄昏时,他站在这座美丽城市的一条巷子里,抬眼往上瞧,等待三楼窗口灯亮。灯一亮起,他就使劲地看,想看到保罗的脸庞出现在窗口。 天色已暗,他知道自己在无灯的街上不会被瞧见,也知道自己动弹不得,既不能回自己的居所,也不能去保罗的房间——一念及此,他就屏住了呼吸。 那一晚,他一直伫立雨中,直到窗口的灯光渐渐淡去。他又等了一会,看看是否会发生什么别的事,但窗子始终黑着,什么都没有泄露。于是他慢慢回家。他又踏上了干燥的陆地。衣服湿透了,鞋子被雨毁了。
整部长篇里没有太多大起大落的情绪波动,只有一次又一次内心情绪的微晃。对于异常敏感的人来说,写作实在是种消耗,在反复检视内心揭开回忆的过程中磨骨抽筋,挤榨心血,孤寂恒久笼罩,经年累月地一层一层剥削,亨利·詹姆斯一定深受折磨,却从未离开他的书桌和纸笔。 《大师》中有这样一段: “你写了一整个图书馆,”安德森说,“我想全部读一遍。” 安德森转过头看着亨利。 “你早就知道自己会写这么多书吗?” “我知道下一句话是什么,”亨利说,“也常常知道下一个短篇是什么,我也为长篇小说做笔记。” “但你从没计划过吗?你从没有说过这就是我一生要做的事?” 他问了第二个问题后,亨利就转过身,面朝窗口,不知为何眼中蓄满了泪水。 托宾克制的笔法,同样作用在读者身上。他从不让人恸哭,只是会使你突然鼻酸,犹如被针芒微微刺痛,泪水集聚,却又强忍下来。所有异乡客,读他的短篇集《空荡荡的家》,大概都会犹如他乡遇故知,千头万绪积攒在心,反而难以落泪,情绪全都化成洪水涌上来,涌上来,就这么哽在喉腔。
面对伤口,有人选择刺破和裸露,而托宾,托宾只是轻轻揭开纱布一角。并借由写作一次次温柔抚触那些小小的结痂。 和长篇《大师》不同,托宾的短篇写的大多是平凡人。《母与子》,通过各类故事展现不同的母子,描摹各类情绪张力。《空荡荡的家》,满是离开故土多年而又重返家乡的异客,对他们而言,故乡定义早已模糊,无论在哪一块土地上,他们都是陌生人。 托宾在短篇中“变本加厉”的克制,和海明威、雷蒙德·卡佛、理查德·耶茨相似,在一行行客观冷静的句子间,情绪的表现都几近于零,大部分情感潜藏于海平面之下,暗涌,而表面纹丝未动。这样隐而不发的沉默力道,几乎要扑上来把人一拳打倒。他说过——“我的写作主题都是关于迷失和孤独。另外,我对沉默感兴趣,人们压抑情感,无法表达或不愿意表达,是很戏剧的过程”。 读他的小说,就总是会想到这样一个场景:某人将与所爱永别,本应泪雨滂沱地再说些隽永言语,但到头来却只潦草道别一声,就背过身去选择了缄默。 但再一想,就连这个,都已经被托宾描写过了。 托宾年少丧父,他曾在一篇评论性文章《丧失亲人后的乖张》中描述自己亲历的一个场景: “在我父亲去世的几周后,我和姨妈去她和我母亲的一位老朋友的家取点东西。当姨妈说我的母亲在外面的车里时,这位朋友后退了一步,用无言的方式明确表示,她未做好应对的准备,情愿我的母亲留在车里。我望着这一幕,步入幽暗中。没有人知道,在饱受丧亲之痛的人面前,应该做什么,或说什么。 ” 而他的新作,《诺拉·韦伯斯特》,描述一位寡妇的生活。一篇采访里提到,这部小说的开头似乎早在多年前写出,但直到现在,读者们才得到整部作品。 故事的一部分原形,就来自他的记忆与对母亲的描摹。在完成某一幕的困难写作后,他说: “写完后我下海游泳,竭尽所能地呆在水里,久久不上岸。那一幕写下了,我本可以畅快地说如今我终于卸下了这一切,通过书写,我以某种方式将那抹除,或说有了一个完整的交代,打破了那份沉默。可是写作需要讲求如此之多的技术,如此冷静客观的深思熟虑,所以那不是一种自我治愈的方式。动笔之时纸上是空白的:那不是一面镜子。我写小说是因为那压在我心头,我写小说,是因为压在我心头的东西有一种脾性,会近乎自然而然地变成律动。但不管怎样,我知道,这大概是某些我不会回首的事,所以,它的结束,在写出来以后,那本应给人一种释然,可是,诚如其他记叙过丧恸失亲的作者必然知道的那样,事情从来不是那样简单的。 ” 同样,读完他的书,我们也总只是轻轻喘口气,而非真的如释重负。像是经年累月下来,终于能够挥别什么,尽管仍有残余滞留体内。 没有故事能真正使人痊愈,但托宾的故事,多多少少会让你感到好受些。
《大师》读后感(九):大师写大师
一百年前名作家的生活比较有距离感,什么游历创作交际啊,什么老房子老装饰啊,我是想象都想象不出。但这同时也是对怀旧者神秘的吸引力。
托宾细腻地写出我们想到甚至反复想到但开不了口的东西,或许是因为羞愧,或许是觉得不值一提的,或许是没法表达清楚的,这些心理活动真实到琐碎甚至是卑鄙,反而会可爱。
书中现实与回忆的巧妙融合是一种形式美。其实每个章节的主题内容都很清楚,用时间点当小标题是一种展现新意的小花招么?
“安德森可能还太年轻,不知道回忆和悔恨可以交织在一起,不知道有多少悲哀可以承载,也不知道那些只有在逝去或丢失后才具有形体和意义的东西,即使如此,在一心一意的压力下,又有多少事可以忘记后又在夜里带着刺骨的疼痛回来。”这种情绪是托宾常爱表达的,我爱这种调调。
《大师》读后感(十):Henry,Henry
最近看了本书,主人公的名字叫Henry。
所谓伤害,究竟是直截了当的刺痛,还是转而避之的冷淡更厉害呢?
说的正直一点,Henry认识了一位文采风流志趣相近的女子。
时髦一点,Henry和一个女人搞上了暧昧。
他们同住佛罗伦萨的山间别墅,再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他们同游英国乡村,住不同的旅店,约在黄昏散步。
他们同聚巴黎,不过是旅途的中转站,马上就要分开,却装出不谋而合的快乐。
那些相交的愉悦,那些会心的微笑,都是真的。
我想,Henry一定是喜欢她的。
但他说,今年冬天我不会来意大利了,我其实并没有长住威尼斯的打算。
于是Henry的她,从威尼斯的窗口,跳了下来。
指责Henry是负心汉的人并没有那么多的底气,因为他做得够委婉够体面。他说我们只是朋友,更何况她本来就有忧郁症,随时都有自杀的倾向。
可是大家心知肚明。
Henry的心底自然也明白得不得了——就算她精神脆弱,他冷淡而迂回的拒绝究竟起到了怎样的催化作用。
可我竟想为Henry鸣不平。
他们相交之初,正是她的独立于群自主衿傲吸引了他。他欣赏她,大部分是出于他们相处摸式对他来说很安全。即使闲人说他们的八卦,他知道她会和他口径一致。
可是她怎么突然就转了性,不但和威尼斯的社交圈子打得火热(那是他们都不屑的),还兴致勃勃地找了个XX夫人相陪替Henry寻找威尼斯的度假公寓。
这个消息从XX夫人的信中传来时,Henry几乎连尾巴上的毛都要竖起来了。
他感觉自己被确实地背叛及冒犯了。
如果他们之间有那么一种不言而喻的规则的话,打破它的人不是Henry而是她。
一直和从前一样,若即若离的关系,有什么不好,为什么非要踏近那一步?
Henry一定很委屈。
Henry是个坏男人,因为他不但冷漠,而且还残忍。
表妹去世,Henry在悲伤的同时,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情。
比起活着的时候,他还是比较习惯处理死去的她。这样,他就可以把她写进自己的小说,让她成为自己的灵感女神,赋予她各式各样永恒的生命。
如果不明白他的心思,在外人来看,这种追忆与惋惜倒很是凄美。
可有时候我们沉浸在错过或失去的怅然中时,是不是也常有这样的如释重负。
是不是因为已经失去的东西,很安全,随便怎么yy都可以,所以很轻松很爽。
所以我们永远也珍惜不了现有的,只能哭丧失去的。
Henry和我一样是出门会死星人。
他起床,等待天空渐渐明亮起来,开始一上午雷打不动的工作,即使有再重要的客人也不能相陪。
午后是轻松休闲的时候,或者阅读,或者陪访客聊天,傍晚的时候要散步。
晚餐后至睡前是希望得到保证的阅读时间,如果没有收到任何出门的邀请,他打心底的高兴。
其实最喜欢的,还是那种整整一天尽握在自己手中,即使全都用来发闲或浪费都没有关系的自在感。
人想要掌握自由,不就是从掌握时间开始的么?
那种能够比常人更加享受独处的妙处的人,一定是能够比常人更加在意到自己的独处的人。
如果一个人常常在意自己一个人,那究竟是太寂寞了,还是骄傲得不屑寂寞了?
Henry为了清静,从伦敦搬到了乡间别墅。他希望和所有的朋友分享新居,每每客人来临,他又感到一种由衷的恐惧。
他犹如动物一般,一旦有人靠近自己的领地,就要把毛竖起来。无论,从哪个方面。
最最不能接受别人接近自己的内心,不许窥探自己的心思,不想被人发现自己小说素材的来源,更不屑相信这个世界上真正有人能够了解自己。
他是国王,别人都是臣民。
他允许别人的亲近那是他的施恩,他翻脸不认人那是他特权的理所当然。
Henry,Henry。
其实他的愿望那么简单。
很小很小的时候,他就那么希望,在英国一幢古老的房子里,炉火烧得旺旺的晚上,他在读书,不需要任何陪衬任何声音。这样,就足够了。
他,也真的做到了。
代价是什么,Henry自己明白。
明明什么也没付出,为什么总觉得失去了什么?
那个原因,其实Henry一直都明白。
Henry史上确有其人。
只是可怜的Henry,如今终于轮到他被别人来yy了。
死后被人如此赤裸地分析心思,还要被区区之辈如我写字来同情,Henry怕是气得毛都要掉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