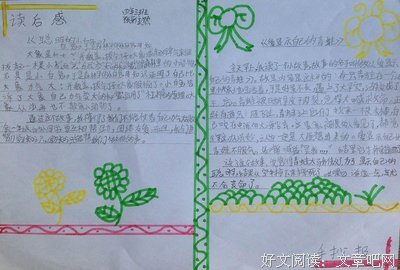被偷换的孩子读后感10篇
《被偷换的孩子》是一本由大江健三郎著作,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0.00,页数:26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被偷换的孩子》读后感(一):重生
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来读大江健三郎的《被偷换的孩子》,倒不是因为书有多厚,而是因为这实在是一本让人看了极其抑郁、内容也很枯燥无味的书。几乎每次我开始翻书不到二十页,就歪在自修室的椅子上睡过去了。但是这次是下了狠心要把书读完——只读好读的书,只看轻松的电影,鉴赏能力永远不可能得到提高。
《被偷换的孩子》大意是说,电影导演吾良自杀之后,他的妹夫、好友长江古义人(以大江本人为原型)通过“百日”的修养、思考,回忆两个人的故事,而他的妻子、吾良的妹妹千樫,则在这段时间内确定了自己一直以来的想法:从前那个英俊、善良的吾良,在十七岁那件事以后,就已经被哥布林(欧洲民间传说中用冰雕的丑陋小孩偷换人类美丽小孩的妖精)们偷换了。小说的最后,千樫和怀孕的浦小姐有一个计划:将浦小姐的孩子当成另一个吾良来抚养,保护他的纯真、美好不被哥布林偷走。
书中古义人回忆起小时候生病发高烧担心自己会死去的时候,母亲对他说,如果你死了,我就再生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孩子,把你经历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他,这样他就是你了。古义人病好以后常常在想,这是原来的自己,还是妈妈再生下的自己?这样的想法,有点类似于庄周梦蝶了。
然而终究每个人都是只能活一次的,没有可能让你的生命在另一个新生的生命上延续,就算是血脉相连的父母与孩子,就算是再相似的人,也毕竟是独立不同的个体。千樫和浦小姐能做到的只是尽力守护孩子身上美好的品质不被哥布林们偷走,却不可能把他培养成另一个吾良。不可能,对那个孩子也不公平。
哥布林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年龄?认知?外力?然而无论是什么,他们都是无处不在的。孩子不可能永远是孩子,除非是像古义人智障的儿子阿亮那样。因为不懂,所以单纯,因为被父母保护着,所以不会受伤。但我们大多数人却和吾良一样,无法给自己套上隐形衣,避开哥布林的耳目。你原来是一块棱角分明的钻石,却逐渐被冲刷成了黯淡的玻璃球;你原来是一张雪白的宣纸,却逐渐被染上点点墨迹。玻璃球无法再被切割成钻石,因为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墨迹也无法从宣纸上去除,除非咬牙撕下,却和从骨骼上剥离皮肉般惨烈。
性善性恶又有如何的差异,该被偷走的还是会被偷走。宿命论的腔调自管悲伤地在人性的天空下颤颤,但谁也无法阻止我们相信:我们有能力让那个球不那么圆,也有能力尽量避免墨迹的沾染。吾良是努力过的,千樫看到他最后一部电影时为他找回了自己欣慰,却不曾料想不久以后他就自杀了。绝望之中的希望,既然已经看见了一束光,就应该牢牢抓住不放,为何却对自己说,我抓不住,然后甘愿堕入深渊?
力量是“相信”给予的,背弃了信念,也就是背弃了连微笑都散发着馨香的自己,闭上眼睛随着哥布林去了。
“忘却死去的人吧,连同活着的人一同忘却,只把你们的心扉,对尚未出生的孩子敞开。”
忘却已经被磨去的棱角吧,忘却已经被染上的墨迹吧,用相信的力量,抵御哥布林贪婪的攻城掠地。
《被偷换的孩子》读后感(二):承认
承认自己的局限和不足,承认读不懂某本书,承认自己认知的有限,大概也是一种渐渐认清现实的方式。
昨晚在陌生的地方坐着略硬的木椅似懂非懂地翻完《被偷换的孩子》,边读边心跳加速,有些心神不宁,后面更是整个人都加快速度阅读(与其说是阅读,还不如说是视线从那些纸页上略过),就像八百米的最后一圈,没什么力气,却咬着牙昏头昏脑地冲刺。
刚刚看了书评,才意识到changeling这个概念:偷换掉刚出生的美丽婴儿而留下的丑陋妖怪。
书的内容并不十分复杂:作家古义人在其妻兄兼好友吾良自杀后,开始与吾良之前寄来的录音带进行断断续续的“对话”,同时也在回忆与时间推进的两条线中交错着试图进一步靠近和了解真实的吾良。
书中的吾良和古义人,在我看来是似近又远的惺惺相惜的知音的关系。吾良自杀前给古义人寄了一些记录自己想法的录音带,大概也说明了这一点。录音带中不止一次地提到当年对他们影响不小的兰波的诗句。这是本书中我最感兴趣的一点。
1.“已是秋季——又何必为永恒的太阳叹息,如果我们是发现神圣的光明的使者——那么,就要远离随着季节推移而恍惚处死的人们。”——兰波
古义人在想选择自杀的吾良到底把自己归类于“发现神圣的光明的使者”,还是“随着季节推移而恍惚处死的人们”。这两种看似是完全不同的类型,有没有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得到融合?如果有可能的话,那么这样的融合是很伤人元气,并且具有挫骨扬灰的力量的吧:一个人从心里渴望能够发现神圣的光明,朝光亮的世界迈进,但同时心底另一个模糊的自己不受控制地随着时光季节和环境的改变而恍惚地朝着晦暗的地方走去。我觉得这并不是不可能。世界上的各种元素和不断变化的环境太多太丰富,人的控制力非常有限,更多的时候是被世界控制,而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更多时候只能起到自我安慰和激励的有限作用。这种“有限”的自控自励和世界“无限”的波浪的两种力量都称不上构成一场拉锯战。因为大多时候,后者赢,几乎没什么特别的悬念。
那么人又能做些什么呢,在最后的结局还未到来之前,缓慢或急速地朝着光亮观望,如果可以的话,迈出步子。而被裹在黑暗里,也不是多么丢人的事情,就是有些让人遗憾。
2.“别无选择!我必须将自己的想象力和回忆全部埋葬!因为艺术家以及小说家头上的光环已被掠走!”——兰波
记得在看讲述兰波生平的电影《全蚀狂爱》时,影片快结束时已不再年轻的兰波就是这样决绝地表示埋葬了自己继续写诗的可能性。一直很纳闷这样干脆的手起刀落,尤其是对自己的想象力和回忆,这样毫无余地的斩断实在太凌厉。
不知本书中,吾良的想象力和回忆对他本人而言又是多么残酷而无法承受的事情。(关于吾良和美国人皮特的交往以及他中年被黑帮袭击的这几段经历,我实在没太看懂。)
3. “总而言之,请原谅我用谎言作为食粮养育自身。该出发了。然而,没有一只友爱之手伸向我!我该向何处寻求拯救?”——兰波
吾良也出发了,去往所谓的另一个世界,其实就是割断与现在的这个世界的一切联系。这么说起来,这样的告别,好像真的只要说声“再见”就够了似的,只不过确确实实不会再见了。
至于吾良心中所指的“友爱之手”,也许不仅仅是知无不言、互相了解的挚友,而是与这个世界沟通并继续相处下去的可能性。他与古义人当然还是友谊深厚的好朋友,疏不疏远也并不很重要,因为比起是否有这样挚友而言,自己能否与世界相处下去的“友好”更能决定一个人选择是去是留。
所以在我看来,这里的“友爱之手”并不全权指友情,而是和这个世界的微妙角力。或者世界并没有对其不友好,但他却失去了将其解读为“友好”的能力。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却也无法改变。这才是最平静却最掐断呼吸的力量。
4.“等到拂晓,用热切的忍耐武装起来,我们要向那光辉的城市挺进。”——兰波
来了,我最最喜欢的一句(好像有之一)。高中时吾良和古义人最喜欢这句诗。
《被偷换的孩子》读后感(三):Changeling -- 被偷换的孩子
每当美丽的婴儿出生后,侏儒小鬼戈布林便常常会用自己丑陋的孩子偷偷换走那美丽的婴儿,这个被留下来的丑孩子,就是changeling了。
大江健三郎把有关导演伊丹十三的真实事件和自己对自我人生的诠释结合在一起。通过“田龟”作为一种媒介,不断的去回忆,去深入,去挖掘从儿时到现如今的的转折,一步步走向好友自杀坠楼的真实。
而Changeling在故事面变成一个具有多面性的复杂意想。人人都是Changeling,这个世界到处出充满了戈布林。他们威胁着我们的人生,威胁着我们的未来。部分有自觉的人孤独又痛苦的去寻找一种自我的救赎和外部世界的赦免和拯救。
“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就象变了一个人似的。“这是人们对changeling最通俗的表达。
很久以前就一直用“带着伤口的人”来形容自己,而从阅读完这本书之后,对此我有了更准确的认识。
Changeling的偷换概念涵盖了时间、空间和事件。在催眠式的回忆一些记忆深处的经历,不管是印象深刻的还是想被遗忘的。一连串的错枝末节贯穿了到目前我的整个人生,乃至对人,对事的判断。因果显著,而这并不仅仅是宿命。
当纯真已不再的时候,一再的强调希望自己是个孩子,不愿长大。为什么呢?也许潜意识里已经开始了对已不是自己的自己有了很深的恐惧。一种对自我的陌生感,对下意识的一些观念和行动的害怕。
也许潜意识里就一直想着自救,所以会对心理学、宗教、哲学等一切悬疑的东西如此的感兴趣。而自从和狗狗相识,这个更加敏感、有着很强思维能力和与我达成很好的神交的家伙之后,我无法预计这是对我自身伤口的填充还是越发的撕裂。我只能用他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来形容他对我的影响,因为那使我感到安全。
有段时间会通宵通宵的和狗狗冒险,尝试着去揭开被包裹了层层之下的自己。这真是一个奇妙的体验,我们用电话通话的方式来执行。一个问题深入着一个问题,不断记忆的堆砌,用自以为的成长中的一些事例来应征心态上和行为上的一些改变。仅仅是浅尝即止,我们已经深深的意识到了这件事情的可怕。突如其来的对彼此的害怕和陌生感以及对自己的罪恶感,然后是大段大段时间的沉默。
“等到二十年后,我想我们也许可以尝试这种“田龟”式的对话。”看完这本书后我在电话里对他说,“那个时候我们有很长一段的共同经历,我相信我们能达成一种默契或者说是规则来完成现在我们无法做到的一些事情。”
“如果那个时候我和你做这样的事情,应该是种悲哀。”狗狗的话仿佛从很遥远的地方飘来。
我们又一次沉默。
我想到了作品中作者讲的一段让我印象深刻的故事,作者小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故在弥留之际他与母亲的一段对话:
“妈妈,我会死吧?”
“不会的。有我给你祈祷呢。”
“医生说这孩子没救了,我听见了。我会死的。”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说:“要是你死了,我就再生一个你,你就放心吧。”
“可是,那个孩子和死去的我是不一样的孩子吧?”
“不,是一样的。我会把你以前看到的,听到的,读的书,做的事都讲给新的你听。这样新的你就会用你知道的词说话,所以说,这两个孩子是完全一样的。”
真的会是完全一样的吗?真的能完全的保护孩子不给各种各样的戈布林偷偷换走吗?
也许就如大江健三郎最后肯定的表述一样,“忘却死去的人吧,连同活着的人也一同忘却!只将你的心扉,向那些尚未出生的孩子敞开!”
二十年后,我和狗狗如果真的在用如“田龟”的方式做如此交流的话,也许真的是一种悲哀……
《被偷换的孩子》读后感(四):多语种复合型人才君,我很严肃的想你
--1。进入纯文本的解读
这是这篇小说结尾最闪光的地方,古义人从柏林带回一本画册《Outside Over There》,千樫看的时候很是触动,认为那个苍老茫然的母亲,和名叫爱达的小女孩都是自己,她看着,
这里首先进入的时候就预设了“这画里叫做爱达的女孩,就是我。”这样的前提,然后进行的就是纯文本的对画册出现的故事情节和人物的解读。同时我们注意到,千樫同时看到的还有古义人在柏林参加研讨会时大家对这本画册的评论。评论的人不见得都把画册的人物想成自己,但是他们的说法也是从文本直接走出来而不参与其他的怀疑。比如:
塞达克的画册里,爱达抱着从葛布林那里解救出来的妹妹走在森林小路上,在她的前方,有一棵枝干伸展的树。在这棵树的阴影里,五只可怕的蝴蝶在飞舞。爱达的神经很紧张。
quot;这表示爱达争取到的安宁仅仅是一瞬间,那幅画里四处充满了预示着前方有危险的声音。她能够安宁的只有极短暂的时间。"
quot;真的吗?"研讨会上有人问道。塞达克进一步做了说明:
quot;是这样的。那棵树眼看就要抓住她了。飞舞的五只蝴蝶意味着那里有五个葛布林。"
我觉得从文本直接走出来的联想是很不严肃的,但是我们除了进行这样的联想,并且扩大它,使别人接受我们的联想而外,没有别的道路。
2。没有冰孩子的立场
这篇小说,以及大江这位作家,都是以其柔和的心和对和平的呼唤而著名,我们又一次读到了大江在现实中接受了的残障儿子“光”的角色。对无理取闹的舆论的谴责,对自己和孩子同一立场的坚持。(关于这一立场的出现,关于这一立场出现时的复杂心理,他已经在《个人的体验》里做了繁复的讲述,很大程度上,我们认为他在《个》里面,进行了不避讳的压力释放。但是,显然,压力恒有,在十多年后做这一篇小说时,大江还是要为自己的儿子解释一遍,对着这么多年来折磨他们的人们,娓娓道来。)
但是《被偷换的孩子》里,又是结尾的地方,出现了一个起码我看来很不和谐的声音。
在引用了古义人的一段发表在报纸上的回忆
(现在农村已经不像从前了,那时把被褥直接铺在铺席上,我躺在褥子上。几天几夜没阖眼的母亲坐在枕头边,正瞧着我。我用自己都觉得怪怪的微弱声音问道:
quot;妈妈,我会死吧?"
quot;不会的。有我给你祈祷呢。"
quot;医生说这孩子没救了,我听见了。我会死的。"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说:
quot;要是你死了,我就再生一个你,你就放心吧。"
quot;可是,那个孩子和死去的我是不一样的孩子吧?"
quot;不,是一样的。我会把你以前看到的,听到的,读的书,做的事都讲给新的你听。这样新的你就会用你知道的词说话,所以说,这两个孩子是完全一样的。"
我还是不完全明白,可是能安心睡觉了。从第二天开始渐渐好了起来。好得非常慢。入冬时,我自己要求去上学了。
在教室里学习时,或在操场上打棒球时--这是战争结束时盛行的体育运动--我都会不自觉地陷入沉思。现在在这里的我,会不会是那个发高烧的孩子死了以后,妈妈又生的新的孩子呢?我感觉好像妈妈把那个死去的孩子所看到的,听到的,读的书,做的事都讲给了我,就像早已存在的记忆似的,而我是继承了那个死去的孩子用过的词这样思考、讲话的吧?
在这个教室和操场上的孩子们,难道都是听了大人讲了那些没长成大人就死了的孩子的所见所闻,成为他们的替身的吧?其证据就是,我们都在使用同样的词语讲话。
而我们不正是为了使这些词语成为自己的东西而到学校来的吗?因为不仅是国语、理科和算术,就连体操也是为了继承死去的孩子的赐予所需要的!自己一个人去森林,照着植物图鉴对照眼前的树木的话,就不能替代死去的孩子,成为和那个孩子同样的新的孩子。所以我们才这样到学校来,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游戏的……)
之后,来拜访的姑娘说:
quot;我想要为死去的孩子再生一个孩子。把死去的孩子的所见所闻,所读的书,做的事都讲给他听……我要成为把死去的孩子讲过的话教给新孩子的母亲。"
这样的考虑,是太以画册的故事为现实了。画册里被坏小鬼葛布林替换来的,是一块孩子形状的冰,而现实是,这里被这位姑娘预设了人生的却是活的人类。
3。还是没有逃掉国民性(试论)
这样说要引起很多误会,但是我直感上想到这个词,而且想不到更合适的词。或者说“战前日本国民想法的影子”。最后千樫很支持姑娘的决定,甚至给她资助房租,还要亲自飞到柏林照顾她。她们是在为了心里的神圣(对千樫是哥哥,对那个姑娘是恋人),来共同谋杀将要到来的孩子。如果说被偷换,如果说反偷换,是这个小说想要讲的东西的话,那么下面这个孩子呢?不是受害者又在亲自加害于新的纯洁吗。只为了这一个故事的圆满吗。这一个的圆满如果是这样达到了的话,那不正是什么都没做的回到了被侮辱的地方了吗?
4。语言
这里我搞笑一点结束,看起来大江和村上都是多语种复合型人材。好好读书,学无止境。
《被偷换的孩子》读后感(五):回忆日本作家
前天在周末上看到小森阳一的访谈。小森是东京大学的文学教授和批评家,他这样评价几位我恰好读过一些的日本作家——
最欣赏大江。
川端只是将美国所期待的那种日本印象,用自己的文学手法进行了构筑而已,并因此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换句话说,他只是将已有的东西做了一些演绎而已。
三岛同样也是根据欧美所期待的日本印象,在自己小说中进行了再生产,他还通过自己的死法,对这重再生产进行了完美的演绎。也就是说,他利用已有的最大众化的某种日本印象,比如说剖腹、自杀的方式终结人生,并因此获得了一种代表日本文化的资格。在我个人看来,大江的文学就是对三岛制造的日本印象的不断解体与批判。
对一个已经美国化的年轻人来说,村上制造的是一个共性世界,因此给了很多人一种意外之喜。从某种意义上讲,村上的文学是将日本所有的历史性一概排除之后形成的。
大江和上述作家恰恰相反,他通过小说的方式,逼自己不断认识历史,认识侵略战争的责任。
想起自己看《伊豆舞女》的情形,把某次失恋后的旅行想象成相似的行为,还写了游记,结果再次翻开《伊豆舞女》,两相对照,觉得自己很弱智,呵呵,情绪太实在了,毫无川端的暧昧飘渺之美。和新感觉派比感觉,算是撞枪口上了。
想起在北京,躲在办公室里看村上的《舞舞舞》下酒的情形。想来那种有点想法、不失善良的公司男,最适合读村上了。另外一种翻译叫做《青春的舞步》。
读三岛的金阁寺,觉得很着迷,但没看懂,翻过头又看了一遍。喜欢那种纠缠的写法,把观念思辩和生动的情节纠缠在人物身上的写法,象是在写一个读书人的生活。
大江看得最晚,但他的确触动了一些严肃的部分。或许是责任吧,成年男人的话题。《个人的体验》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半自传的方式更以其真实性让我信任。我曾想,如果我面对作为智障的阿光,我会如何选择,我如何得到勇气承担,如何能挖掘阿光身上优秀的地方?我并没有见到关于大江有特殊的信仰的资料。重大问题进入我生活的时候,总有一本书出现,尽管有时完全是在误会中出现的,所谓“六经注我”,并非一种狂妄,其实是相信伟大的经典与当下的我,有发生联系的可能。这样的经典才是活的。而我像一个标准的呆子或孩子一样,被现实困扰时不去迎难而上,而是埋下头,相信书里会有好的建议给我。
有时这种态度未免消极,似乎限于接受,并没有把全副精力、智力都运用出来。所以反思GZ的第一次治疗时,我对她说“当形势需要我当一位司令官的时候,我却只是做了一个后勤部长”。而她竟还不满意,修改成“当形势需要我当一位司令官的时候,你却只是做了一个炊事班长”,呵呵。
前些日子读完了《被偷换的孩子》,读这本书,感觉大江的创作路径完全清晰地显露出来。尽管不免觉得他或许不是那种以虚构能力取胜的小说家,半自传的创作方式最容易给人这个感觉,但心中亦知,这是一个完全以对现实的严肃思考、以责任感、以人格力来比拼的老人,值得敬重。
《被偷换的孩子》读后感(六):好的东西需要等待
说实话,看完这本书花了我很多力气。在看的中途,常常会因为觉得过于晦涩而心生退意,会放弃的时候,经常这样告诉自己,这本书没有到最后,贸然的放弃所失去的,会成为我的遗憾,而且,追悔莫及。
是抱着勉强的心情看完的。大江先生的书,闻名遐迩,而自己居然还未看过,光光这一点,就让人汗颜呐。印象中,大江先生的书本应该如此晦涩。或许照片上的他过于严肃,所以在某个瞬间,就暗暗下了这样的定义。我不是很懂,这本书所承载的,大江先生所包含的情感,只是在吾良和古义人身上,渐渐看到大江先生本人和其妹夫伊丹十三,两人深刻而真挚的友情。这就是自传吧。同样的自杀,同样留下的录音带,同样试图与死去的挚友进行灵魂交流。
田龟的出现,一开始会让人觉得他是不是发疯了,由于对方的自杀,接受不了这一现实,于是古义人幻想出一个工具,与吾良的所有交流说到底其实只是古义人一个人的自欺欺人?人很悲伤的时候,是会产生幻觉的。随着事情的发展,渐渐我们得一窥见,他们年少时所经历的种种,他们身边亲人所带给他们的一切,这些对于外界的感知,每分每秒所发生的事情,在一开始我们以为我们我们会忘记,就像平常所发生的所有另外的日常一样,但是潜意识的存在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我们还毫无察觉的时候,它就已经悄悄替我们存储一切,记录,归档,日后会在不经意间突然弹出,而你就恍然大悟一般“啊,原来如此”。那30盒录音带,是我最好朋友留给我在这个世上的一切,是仅仅属于对方的所有,他的每句话,磁带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他在冥冥之中,对还留在这个世上的我的提醒,有些话,吾良在生前,没有同我讲,原因并不明了,因为我原以为,那样的吾良是绝不会以自杀收场的,黑社会,暴力,黑帮,家庭,这些东西,外界归结于他死因的各种猜测,在我看来,并不确切,正因为连我也不知晓,所以吾良的死,会让我如此震惊。对所熟知的一切,其本身以超出预料的发展,这种意外让人开始怀疑自己先前的判断。我所熟悉的那个吾良,究竟是那个样子的吗,还是在很久以前,他就已经不是吾良了。我活在自己的世界太久,除了写书就是修改,慢慢与这个世界分割起来,打开电视机的时候,小盒子里的那个世界,让我觉得竟有些陌生。每次听录音带的时候,就想像那是吾良在和我说话,像少年时代那样,像兰波的诗一样。有一段空白的记忆,我始终无法记起来。吾良一定知道吧。那段记忆的盲点,最终还是复苏了,关于大黄,关于美国军官,关于我们狼狈的逃回家。泥泞不堪的路,在大脑中越来越远。我全都知晓。只是最后我选择性过滤了它。那改变了我的一生,修道院场发生的一切,父亲的一切,妈妈残缺的耳朵,吾良的父母,在德国的教学,在回忆里翻涌,塞进我们的脑海中,我全都知晓,而对于这一切,我选择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