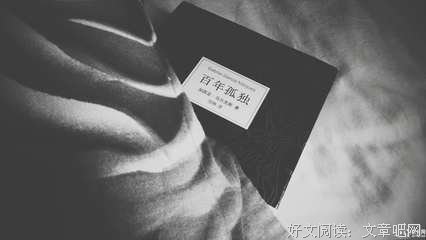听水读抄的读后感10篇
《听水读抄》是一本由陆灏著作,海豚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0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听水读抄》是陆公子安迪的第三本随笔集,和之前的《东写西读》《看图识字》一样,辑的是发表在《深圳商报》上的专栏文章。陆公子爱美,书籍装帧自不用说,手工包的布面精装,用的是英国美术家威廉•莫里斯的绿叶纹样,书里还有篇文章,叫《花纹要往精细里做。钦此》。
我三月在英国,有天去维多利亚&阿尔伯特美术馆看珠宝展,看到饥肠辘辘,奔去一楼餐厅吃点心。刚坐下,收到公子短信:有没有看到威廉•莫里斯的绿房子?我抬头张望一下,餐厅四壁都是绿色图案,美得惊人,于是回信:我正坐在绿房子里喝下午茶。他恨恨地说:我以前来时没开门,只能隔着玻璃朝里张张,你竟然坐在里面喝茶!我心想,你都把他的绿叶印在书封上,还想怎样。
翻开内页,简直恨妒到不行。陆公子爱收藏美笺,然后请相熟的文化老人在美笺上题字,平日都锁在深闺不让人看,这次居然破例拿出十六叶印在书前,有冯至、施蛰存、金克木、王世襄、黄裳等老先生的字,“如同演唱会请大牌明星当嘉宾,助阵撑腰”。如此美笺配诸老墨宝,这不是拉仇恨是什么。
作为资深“钱迷”,陆公子将五分之一的内容贡献给了钱锺书,正经读书之余,少不了带着“小报记者八卦眼”。一篇《窃听张爱玲私语》,写他读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翻就翻到张爱玲对钱锺书的议论,如获至宝。钱讨厌张,大家都知道,不稀奇,“但张爱玲对钱锺书怎么看,却不曾听说……张爱玲读了夏志清写的《重晤钱锺书》,一九七九年九月五日给夏的信中说:‘他(指钱)去年在意大利才知道你写‘中国现代小说史’。跟你合摄的照片上他眼睛里有狂喜的光’。”夏志清用英文写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将张爱玲和钱锺书“挖掘”出来,捧为1940年代中国文学的高峰,影响了西方甚至大陆的现当代文学史书写。钱虽不满与张并列,但对夏大约相当欣赏。公子点评:“她从照片上看出钱锺书‘眼睛里有狂喜的光’,不能不佩服她的眼光敏锐独到。”
陆公子的八卦内心,在《宁愿她不守口如瓶》一篇中展现无遗。他说张爱玲选丈夫的眼光极差,但选朋友的眼光却极好。张的闺蜜邝文美女士终身守口如瓶直至去世,公子曾为《万象》向邝女士约稿不成,八卦心没能满足,于是说:“作为张爱玲的读者,却宁愿邝女士能‘出卖’朋友……少了一个朋友,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而文坛多了一番热闹,岂不快哉!”八卦资历尚浅的人,读到这里自然满心欢喜,有前辈作表率,下次八卦时更可以理直气壮。
《听水读抄》读后感(二):【坐评】聽水讀钞
刚读完,说下基本的感受。
首先在书的质量上,非常不错,至少在我见过的书里,能排前几。布面精装,手感很不错。里面的纸张也很厚,翻起来常常有两张的错觉。文章的印刷排版也很舒朗,读起来很舒服,不累。
其次,是书的内容。主要是作者读书的一些零散的笔记和感想。至于笔记是什么对读者来说并不是很重要。如果以前没接触过作者读的书(比如我,就没听过邓之诚),算是一种知识,但不深,点到即止,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找来认真看。如果接触过这些书,甚至有研究,那作者提到的这一点零碎的知识也没有什么增益的效果。所以,可以闲读。至于感想,也没有多么矫情造作,这也是我能看下去的原因。很多感想,很直接,有些与我自身的想法也不太相同,有些甚至有点反感。但这些真性情,还是让人感觉欣慰的。
就是这样一本书,闲读挺好,放着也不会感觉浪费。
--------------------------------------------------------------------------------------------
【坐评宗旨】在豆瓣,一直关注的类别就是读书,但我不是什么文人墨客,没那个水准,也没有把一句话写成十段话的能力。读书就是兴趣而已。读一本书之前,先来豆瓣看一下大概的内容,也成了一种习惯。当然,要是准备买就更会看一下了。这就看出来我是个俗人了。我买书会关心书要多少钱,人家文人、雅人,都不提“钱”,人家说“泉”。这是没救了。所以还是依然来豆瓣看书评。看了几次,都快要放弃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书评,写的比书本身还高深,让人一看就自觉形秽,感觉自己是无知小儿了,但书里说了什么,或者说基本内容如何,完全不知道。所以,我决定在看过的书下面,有时间就写写书的大概情况和内容是什么,以防有和我相似的俗人想知道,又看不出来而着急上火,反正我是会的。没有文采,没有意义,书的小标签而已。
《听水读抄》读后感(三):同砚
《听水读钞》中有一篇文章写俞平伯和顾随的关系。其中俞平伯的文字里有云:“羡季与余有同砚之谊。”说他俩是大学同学。
查同砚这个词条《汉语大词典》作:
【同硯】语本《汉书·张安世传》:“ 彭祖 又小與上同席研書。”研,通“ 硯 ”。后因称同学为同砚。《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九八回:“好在我們同硯,彼此不必客氣。”《恨海》第四回:“我與他若是向不相識的,倒也罷了;偏又是從小同居同硯過的。”
同砚也写作同砚席、同砚友、砚友、同笔砚、同笔研等等。
同砚大概比较直接的出处,我们可以勾连到刘禹锡《谢柳子厚寄叠石砚》(刘梦得文集外集卷八):常时同砚席,寄此感离群。(宋立民等《中华别称类编》之《门墙桃李何莘莘——学生的别称》把离群写作群离。误。)
《听水读抄》读后感(四):东写西读陆公子
陆灏陆公子,搁古代可入《世说新语》。开凤鸣,办《万象》,编万有,化脉望,“威海路梁朝伟”。江湖传闻太多,我记下我见到和读到的。
第一次见陆公子是在社里,他来开会,我很想一睹风采。会刚开完,我们完颜主任往走道一声吼:谁谁不是想看陆灏嘛!臊得我和一行同事没好意思近前,也避免了“看杀卫玠”的重演。
后来因工作关系,和陆灏先生有一些联系,比文字还生动,他真是个很好玩的人。一次座谈会后我们收拾桌子,发现一只香蕉上用水笔画了仕女像,是陆公子开会无聊时的“杰作”。有一阵他忽然想收集自己的出生年一九六三年的所有学术书,刻两方章钤在上边,一方印“癸卯同生”,一方印“人书俱老”。
我喜欢从书里读人,尤喜读读书人。陆灏出得少,至今仅三本半:《看图识字》、《东写西读》、《梵澄先生》(与扬之水结伴),和今年这本《听水读抄》。
从《听水》知,九十年代中,陆灏提议邓瑞先生整理其父邓之诚日记中的读书心得,后又写信给邓先生的弟子王钟翰,商量日记整理事宜。同时期,协助王元化先生编辑《学术集林》。陆灏九八年主持《万象》,在此之前做的事,似乎都在为此做积累。
我一个做报纸编辑的朋友,收齐了陆灏时期的全部《万象》,前些时候忽然感慨:陆灏在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已经在编《万象》了。见过几张他年轻时候的照片,眉眼里满是谦恭和真诚。《听水》书前祭出的十几位助阵嘉宾,多是他的作者。陆灏当年拜访完他们总是“恭恭敬敬地用毛笔写封信”,“一张信笺三四句就写满了,约稿有时也不用明说”。金性尧先生视陆灏为“暮年知己,不仅仅为文稿事”。施蛰存先生生前还替他担忧:“我们死光了,谁给你写?”更打动我的,是陆灏在书里讲到的他和《古今》杂志的主编周劭先生的忘年之交。周公满腹晚清民国掌故,在陆公子约请下写成不少文章。多少笔底明珠,因陆君未虚掷。
黄裳先生过世时,我看到这样一则微博:
“The grievance that is beyond words. 上午去龙华告别黄裳先生。老先生不希望哭哭啼啼,所以大家在古典乐中鞠躬致敬,献红玫瑰。瞅
见眼睛红红,一直没说话的陆灏,黑T恤上‘words have no meaning’。真是知己。”
博主Sean励应是励俊。可补一笺:据黄先生女儿称,黄裳先生过世前两三年病中极少说话,只与人笔谈,至后来一言不发。
陆灏与前辈的交往令人艳羡,然难学;他与平辈作者的交往可学,然难得。一次与傅月庵先生谈天,他推陆为那一辈大陆编辑中第一人。很会写信。不时写信问候作者,并及家人。作者拖稿,不催,自己挺过去。偶尔致信,称在某处见一文章,和我们之前谈过您要写的文章有些相似,或见着您可能需要的资料,寄来供参考。如果觉得文章不够好,绝不妄改,直接致信指出具体何处欠佳,作者自知惭愧,主动改稿。但绝不会第二次退稿,自己承受下来。下一次作者肯定会写来好稿子。
扬之水和陆灏的交谊,我也颇感兴趣,一南一北好编辑。《听水》里陆灏称她“我的朋友宋远”。董桥兄为余英时的《中国文化史通释》写序说:我和余先生有缘做朋友,靠的也许竟是彼此都抱着“旧文化人”的襟怀。陆扬之交想也如是,气味相投。爱读书,勤写信,一手好字。《〈读书〉十年》里,扬之水多处记到陆灏给她寄书,她到上海时,陆灏带她拜访沪上文化老人。陆灏也曾提起,他到北京时,扬之水和他一人一骑自行车,一天走访多位作者。我也八卦一下,陆灏和扬之水用的是“情侣包”,上博大克鼎金文纪念手提袋,陆灏送给扬之水的。
陆灏说过,“如果说我崇拜一个人,只有钱锺书。”读《听水》就知道陆公子真是钱先生的高端粉,圣徒狗仔兼之。所谓圣徒,“我所知道的一切,他都在行。可是他还有一个世界,而那个世界我一无所知”。所谓狗仔,“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人知道的一部分”。
陆灏连读书趣味、方法都和钱先生相类。中西通吃,爱抄书,每从书中寻常处读出别人见不着的趣味。陆灏曾发下“宏愿”,要把《管锥编》中提及的英文书全部找来读一遍,不知是否遂行。杨绛先生说,钱先生在牛津时,为放松头脑,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陆公子也爱读侦探小说。他说自己读法国学者多米尼克•拉波特的《屎的历史》,“像以前读福柯的书那样,采用买椟还珠的方式,专看书中所引的例子,而对作者的那套理论分析,只能抱歉地原套奉还”。让人想起钱书先生庞大建筑和木石砖瓦的比喻,“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断思想”。
杨绛先生在《〈钱钟书手稿集〉序》里说,“锺书自从摆脱了读学位的羁束,就肆意读书”甚至“随遇而读”。陆公子也在《东写西读》后记中说:“读书是我的一项爱好,对我来说,除了消遣取乐,读书并没有其他功效,既不为考试,不为研究,也不是为了写书评。”在一次访谈里,他说自己特别幸运,从小到大没人逼他读书,更没有谁逼他读不喜欢的书,换句话说,他没有读“伤”过。“我从不愤世嫉俗,读书时很开心,读书时可以做古人和外国人。”这开心,便胜却人间无数。
《听水》延续了陆公子的风格,毛尖笔下的“万象特色”:“讲故事,不讲道理;讲迷信,不讲科学;讲趣味,不讲学术;讲感情,不讲理智;讲狐狸,不讲刺猬;讲潘金莲,不讲武大郎;讲党史里的玫瑰花,不讲玫瑰花的觉悟……”小考水浒兵器,统计梁山好汉家小,让人想起钱锺书对李元霸兵器重量的津津乐道。为一本一九四五年的旧《大众》里夹的电影票根,心血来潮跑图书馆翻《申报》电影广告,享尽钱先生所谓“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书中不时冒出的奇想,也很有意思,似乎听得到陆公子的笑声,“我曾经有这样的想法,评论《西游记》是否高明,关键看对猪八戒的分析”。
读陆灏前两本书,就觉得好玩好看。读《听水》,似乎看出了陆灏深藏的眼光。陆公子读史料,也编定史料。读掌故,也记录掌故。他频频回顾那个人人各具声气的时代,钱锺书在潘金莲“老娘这脚”旁批注的“江青所师”,陈寅恪《柳如是别传》里的“呵呵”,“臭尚书”沈曾植扪虱而啮之,章太炎的书房里“壁上趴着一条硕大的鳄鱼标本”,邓之诚笔下“满身火气,宜服清凉散”的陈垣,都不会再有了。他记下的吴祖光先生关于遗忘的故事,黄苗子顺走杜月笙家工艺品的轶事,也没人再听到。还有胡风舒芜对一次会面的两种表述,吴梅和吉川幸次郎对彼此的迥异印象,真相从来只有一个。 或许就像书中所说,“历史的扑朔迷离往往还有另一种现象,表面冠冕堂皇的道理之下,或许只是一些细碎末节的缘由”。正如钱钟书先生在《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语言、一篇小说》一文中,引诺法利斯和梅里美的话:“历史是一个大掌故”,“我只喜爱历史里的掌故”。
有一遗憾,陆灏的日记写得太精简, 看《梵澄先生》,都是些流水备忘。 我刚读《〈读书〉十年》那会,一次问起他是否也会出版日记,他说自己的日记仅备以后查检之用。又问起是否会写传,他笑说,等我一百岁的时候吧。我疑心亦期愿另有一版日记,买书记录,读书心得,师友交往,臧否人物,正如伦明(哲如)咏邓之诚的诗,“此外当编今世说,笑嬉怒骂总关情”。
扬之水日记里,她访梵澄先生,说起陆灏,他说,总觉得太可惜了,——人这样聪明,却没有好好攻一门专业,“人总该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可以留下的东西”。(《梵澄先生》,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廿八日)我想,陆灏先生应该不会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可以留下的东西应该已经留下了,不过是在他那个我们一无所知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