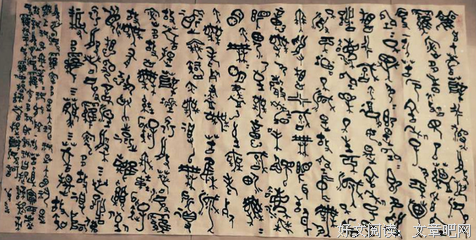《心經隨喜》读后感精选10篇
《心經隨喜》是一本由胡蘭成著作,如果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NT$300,页数:21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心經隨喜》读后感(一):读要
胡公的文字,每读都有新的灵感,像初恋新鲜充满了可能,又自在。昨晚心情有些扰乱,翻开畅读一刻,渐渐回复平静。犹记得大学现当代文学课上丁敏老师讲张爱玲时提及胡文,女同学鄙夷唾弃的神情:“汉奸!”换做现在我亦不会与她相争了,也许一人对自己的感知便正是对世界的体悟。要说男人的柔,不要理解得过于狭窄了,一如女子之飒爽。等春天一来,什么计较都会显得多余。总之对胡文的喜爱尊敬,让我活得有滋味似的。
《心經隨喜》读后感(二):由《心经随喜》而想到的
偶然机会得知胡兰成有本用日文著的《心经随喜》 ,大陆一胡迷尝试着翻译过来,并保持胡兰成的文笔风格,说明喜爱并坚持做就可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话说回来,《心经随喜》是胡在日本讲佛教的讲稿修饰成书,正如译者所说的,世人如何不屑的人和事,只要给你生命的启发,或让你感觉自在欢喜的,便可以以之为师,心经本是深奥的,可胡兰成简单的比喻,举例,古今中外信手拈来,不愧为民国的才子,也难怪张爱玲这样的大才女也要为他所倾倒。
举书里一小例,胡说他在亡命途中,在一人家读到一汉译美国儿童读物《大象的故事》,那调教的效果是用手枪射击象200次,每射击一次就喊一次“不准动” ,作者感慨万千,并懂得了释伽的慈悲,由此作者联想到为了命运正义而落下的禁忌,就与象一样可怜可悯。
今天微博有人吐槽诺贝尔奖获得者没有一个在中国读中学小学的 ,说中国基础教育考试制度扼杀小孩的创造力想象力 ,哎,读一读《心经》。
《心經隨喜》读后感(三):闲愁万种
《闲愁万种》(胡兰成著·朱天文编·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
当年诗人沈浩波策划了一套胡兰成的作品,大概是1949年后第一个胡兰成的大陆版本。读其《今生今世》,写张爱玲那篇,风流倜傥,当属关于张爱玲的最好文字。后来,我北上京城,从华文天下的同事小北兄那里得到胡兰成的另两种,《闲愁万种》即是其一。《闲愁万种》乃胡兰成最后一部结集作品,据说也是“最能丰富体现其各方面思想和才华的著作”。该书初版由台湾朱天文(胡兰成弟子)编定,收录旅居日本时的十篇散文,十八篇诗作,二十八则书句,或记事,或言情,或抒志,可视作自传《今生今世》的续篇补记。另有说理文《民志篇》《劫毁篇》,论述中国历史上民间起兵的传统和机缘。最后的《日月并明》是胡兰成未完绝笔,其中探讨男女文明之起源和区别,为胡兰成晚年独特的文化见解。此次大陆版本,小北兄做了增补,譬如《神伤尾崎士郎之丧》一文及胡兰成的部分诗词、题句。按主流定论,胡兰成乃是大节有亏,小节亦是如此。翻看《闲愁万种》,发现胡氏的一句话:“我是如同神,俯视着人间的真实。”这句话或许暴露了胡兰成的人生秘密,既然以神自居,对人世间的些许政治、情爱不免凉薄,他有更大的野心(或雄心)——复兴中国的礼乐文明。正如胡兰成自己所说,他要的不是个人的修行,而是民族的修行。据说胡兰成还致书邓小平,提倡新中国的礼乐之治,自然,不会有回音。《闲愁万种》有一些思考值得关注,但认真说来,他的大部分见解,并不足观。尤其是他对东方女性(特指中国和日本)及中国男人的赞美,其论据完全站不住脚。又譬如他在《日月并明》里讲的:“不要只看眼前的西洋为霸的唯物质的世界,那是要劫毁的,他的原来亦就只是假主,真主只可等中国文明。”这句话确实让大部分的中国同胞所喜欢,但证诸当下,怕是中国人自己亦愧不敢当吧。不过话又说回来,胡兰成的著作能够出版,“自是时代有了转机,也是要感激欢喜的。”(小北兄语)
《心經隨喜》读后感(四):据说此书首印已经卖完了,最近又加印了2500册
据说此书首印已经卖完了,最近又加印了2500册
《心經隨喜》读后感(五):据说此书首印已经卖完了,最近又加印了2500册
据说此书首印已经卖完了,最近又加印了2500册
《心經隨喜》读后感(六):胡兰成:真想对这个时代发出惊人之语(曾园,南方都市报)
胡兰成:真想对这个时代发出惊人之语
曾园
□编辑,广州
读完胡兰成的日文著作《心经随喜》,心情有些复杂。这本书没有想象的好,但也不坏。
朱天文在序中透露:一九五0年胡兰成离开大陆,自香港偷渡至日本,在静冈清水市池田笃纪家暂居半年,每天去教日文的先生那里,开始学日文。六0年代中期,胡兰成应邀在名古屋讲《心经》。胡兰成在序中说:“因有梅田美保女士为我润笔和誊写,我才敢于用日文书写,要说是两人合作而成,我亦欢喜。”
石刻家山田光造说:“胡先生的日文写作很特别,常常不合文法,却正是魅力所在,如果把他修饰得合乎日文,反而失掉什么似的。”这种情形大约与苏联哲学家兼间谍科热夫用法语讲授黑格尔类似,他那种怪腔调在未来法国名家听来,颇有些奇特的魅力。六0年代,科热夫恰好也到了日本,后来在自己的《黑格尔导论》的新版序言里说,我原来的论断错了。他大概是被日本人之间的那种谦卑劲儿给镇住了,觉得自己那套主奴辩证法、承认与争斗的理论有修补的必要。
同样,在筑波山演讲的胡兰成也被筑波山农民的谦卑触动了。农民常说(淳朴中未尝没有狡黠的成分),筑波山的煤渣也都是麦克阿瑟元帅的。《心经随喜》也用大量篇幅讲到谦卑与感恩。
读者如果是第一次接触胡兰成的书,可能会对他的写作心存疑虑。实际上,不少学者对他的书都抱有敌意,李欧梵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就说过:“胡兰成的美学都是骗人的。”
比如说,下面一段话我们该如何理解呢:
为何可以称观音作观世音菩萨,或观自在菩萨呢?前面我说过观音是新石器时代的神。旧石器人是洞穴壁画的时代,新石器人是太阳、音乐与数学的时代,因为与音乐有关系,遂称观世音。又添加了念珠。而心经说的是菩萨的修行,观自在就是其修行的心得。
对佛教稍有了解的人,比如说读过吕澂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渥德尔或平川彰的《印度佛教史》、迈克尔·卡里瑟斯的《佛陀小传》等可信书籍的人,恐怕会接受不了胡兰成的这种叙述方式。
更多的人听过钱文忠教授在电视讲过,“观世音”其实是梵文A valokiteshvara即“观自在”的误译,这个错误早就由玄奘发现并在《心经》中改正过来了。
事情也未必就那么简单,据钱文忠的师兄云中君考证,玄奘关于观音的说法其实只是他自己的一家之言。玄奘的著作里到处说某某梵文名词的汉译不对,某某梵文名词的汉字读音为讹,有些是有道理的,有些则并没有道理。因为印度语言本身也在变化。A valokiteshvara存在着另一种写法:A valokitasvara.前者拼写中的“ishvara”即“自在主”,而后者拼写“svara”即声音,所以“观世音”与“观自在”都没错。
玄奘的梵文有问题,云中君这种说法可信吗?学者徐文堪提到过,美国学者那体慧(JanN attier)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论:《般若心经》最早是从《大品般若》中抽取一些段落,再回译成梵文,而回译者就是玄奘本人。但再把《心经》与梵本《大品般若》比对后,发现前者的梵文语言多有不妥之处。这是不是说,玄奘梵译汉挺好,汉译梵就不那么让人放心了?
随意扫视上述梵文专家眼花缭乱的迷人辨析,我们至少会感觉到“观世音”与“音乐”之间的任何关系都可能是不成立的。
2
研究胡兰成的台湾学者薛仁明在他的专著《胡兰成·天地之始》中说过:“胡的著作,有太多‘似非而是’的东西,乍看之下,处处矛盾,非得深入了解,否则不容易读出背后更高的统合。”他还说:“胡的《今生今世》若以知识性来看,实在不及格,里头的引文,处处有错(他大部分是凭记忆来写);但这完全无损于该书丰富之生命性;又如《中国的礼乐风景》,若从专业角度来审视,胡谈中国音乐,不乏谬误之处,但这也丝毫不妨碍他对中国音乐整体之观照成就。”(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如果在比较长的时间段里读过胡兰成的书,应该会觉得这是不刊之论。胡兰成这种古怪的写作方式会不会是他与学者打交道的特殊方式?
在谈论佛经的时候,提到佛经里不存在的十八罗汉是否慎重?我们仔细想想看,十八罗汉的确是中国人的创造,但胡兰成也说过“如果说文明在于它自身的展现,那么佛教已然展现了我们的文明”。也就是说他谈的是“我们的文明”,如果这么看,《心经》其实也是中国人的发明。十六罗汉加两个、观世音与音乐的联系,其实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也许是因为讲座的辑录,所以内容不太像一本书(虽然装帧极好,很有想法)。当然书中也不是没有新内容,胡兰成依然讲到了中国的礼乐文明、汉字共同体、对西洋文明缺失的再三强调、对农村社会的重视……引起我注意的是胡兰成与学术界的奇特关系。众所周知胡兰成的书里对现当代学术与教育界是不满的。但《心经随喜》中谈到的《心经》与《西游记》的关系却是与学术界暗合的。没有证据表明胡兰成会去读余国藩教授或者中野美代子的著作,但研究《西游记》的重要大家柳存仁很难说胡兰成不去关心。他们之间似乎是认识的,至少在局部上曾经算得上是同事。
所以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胡兰成与学术界互不往来却暗通款曲;二,胡兰成真的完全不理睬学术界。即使是后一种关系,胡兰成长期批评学术界的时候,为了话题常变常新,还是可能会浏览一些期刊。
虽然胡兰成随口就会说出一些警句,比如说,“在中国弹曲唱歌叫度曲,度厄亦如度乐曲”,“《老子》与《孙子兵法》很慎重地教我们如何身处被动”。但有些话,实在与当代思想界关系更紧,与传统文化似乎比较远。比如说,“现代人对死的无感是史上不曾有过的”。
即使我们相信胡兰成的话,传统上我们对待死亡的方式更合理更文明,但对死亡的反思,似乎传统文化还没有达到过如此深度:“死是生的余韵”以及“动物的死只是结束,唯有人的死是可以有所为”。
西方关于生命与死亡关系的想法很多,其中比较有意思的一种大概可以表述为“生命只不过是死亡的一种形式,而且还是比较稀有的一种形式”。胡兰成仔细回应并扭转了西方文明的看法。
无论我们对胡兰成有怎么样的成见,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有时候他的想法虽然显得大而无当,但其实都来源于他的真实生命。否则我们不好解释这样的感悟:“取胜……远不及杀身成仁来得意义重大”;还有“古代武士面子受损时,有时亦不能当下拔刀斩杀对方。不得已而受侮辱,这种受侮辱是比受恩更难”。
现代福利社会最大的问题也许是让《心经》中对苦难的看法与忍耐哲学丧失了价值。但植根于城市的福利社会又有什么不好呢?一生致力于提倡农村文明高于城市文明的胡兰成对此当然会有所发现:“现代人认为光靠租金与月薪,或是凭福利国家的权利义务的保险即可万事无忧,大可不必从别人那里接受恩情,要说有什么值得感激的,顶多只是商店里的折扣优惠价,他们不认为接受过世上的任何好意。”
3
胡兰成对福利国家的不满肯定不仅仅立足于宗教理由。他说:“所谓的现代福利国家只谈生活,无论哪个内阁的施政演说都不谈礼制。”礼制的好处在哪里?普通人都能“因礼制而成就人世风景”。
这种“人世风景”是有现实意义的。熟悉胡兰成著作的人会在《今生今世》中读到很多。只是因为胡兰成的“人品”,未必有很多人会相信浙江省嵊县胡村真的有他说得那么好,“中国人家可是向来农村里也响亮,城市里也平稳”。在《中国乡党制度沿革考》里他宣传“中国人因此享乐了一千多年的农村生活,直到满清中叶以前,没有尝过欧洲那样阶级压迫的痛苦”,“在农村内部,不存在阶级压迫的事实”。
在《心经随喜》即将结束的第203页,胡兰成突然说道:“真想对这个时代发出惊人之语。”
惊人之语的作用自然是惊人,那么值得信服吗?
刚出版的新书《余英时访谈录》(中华书局2012年3月版)里,我们会邂逅下面这段文字,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起了胡兰成的胡村:
几百年、甚至千年聚居在一村的人群,如果不是同族,也都是亲戚,这种关系超越了所谓阶级的意识。我的故乡官庄,有余和刘两个大姓,但两姓都没有大地主,佃农如果不是本家,便是亲戚,他们有时交不出田租,也只好算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地主凶恶讨租或欺压佃农的事。我们乡间的秩序基本上是自治的,很少与政府发生关系。(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另一段还有如下内容:
中国传统社会大体上是靠儒家的规范维系着的,道德的力量远在法律之上。道理(或天理)和人情是两个最重要的标准。
我们至少可以确信,在二十世纪初的浙江与安徽部分农村,的确与我们想象的不大一样。胡兰成那番关于社会的大道理,的确是有其现实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