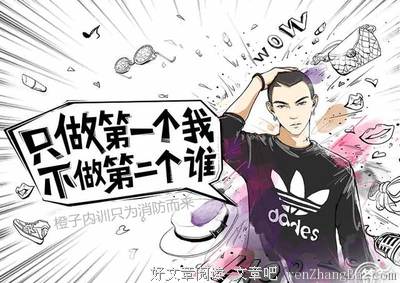再也没有比记忆更危险的事物了丨单读
单读“新青年”创作计划正在进行中,我们希望发现仍在坚持文学创作的年轻人,并定期发表其优秀作品。之前推出的两篇都是小说,但我们也期待收到更多样的虚构或非虚构类的作品。今天推荐一篇书评,来自陈儒鹏。他所写到的《通往北方的细路》,是澳大利亚作家理查德·弗拉纳甘(Richard Miller Flanagan)根据父亲二战期间参与泰缅铁路修建的经历而创作的小说,题目则来源于 18 世纪日本诗人松尾芭蕉的同名俳句集(中译名为《奥之细道》)。这本小说曾获 2014 年布克奖。
为了忘却的……
陈儒鹏
故事是引人入胜的节奏,而叙事如洒水车般将事物遍洒各处--那些扣人心弦的瞬息,未曾了结的爱情,绵绵不绝,百转千回。但故事本身是更为基础的,却也奇幻得抽象。
——理查德.弗拉纳甘
近几年的布克奖到了很多读者都无法忍受的地步,这也无可厚非,毕竟英国病人的顽疾很难治好,而包括澳大利亚、爱尔兰等国的文字也有了一些颓然之势。但是若以这个趋向来否定这些年来的布克奖作品不免有尖刻之嫌,称不上传世佳品并不代表没有阅读品鉴的价值,而且在这些作品当中也总是有那些光辉的瞬息和叙述者的真诚。在一个充满了忘却的时代之中,只有真诚的人才会被记忆着,因为炽热的心跳是抑制不住的。
相比理查德·弗拉纳甘的《通往北方的细路》( 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 ) 而言,不少得奖作品胜在聪明的运笔和轻逸却不失悬疑的节奏(比方说艾琳娜.卡顿的《发光体》),但弗拉纳甘是用叙事者的真挚和光影的变化征服了读者:这种征服是潜移默化的,尽管白云苍狗世事无常,印记是无法磨灭的。在这条通往北方的细路面前,文字的独裁者们或者说是品味的鉴赏家们终究放下傲慢与偏见,因为这些现有的门户之见无法解释这样的一本富于野望,却也失于野望的书给人的冲击:是一种近似于对史诗的欣喜感,尽管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并不是史诗,而是一个成年男子对于生活与命运的反思,这是一本现实主义的小说,正如卢卡奇所说的“小说是一个时代的史诗,其中整体的生活并非给定,内在的意义亦已成疑,然而小说依旧以思索生命的整体为己任”。
▲格奥尔格·卢卡奇( Szegedi Lukács György Bernát,1885.4.13-1971.6.4),匈牙利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也是极富争议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代表作有《心灵与形式》《小说理论》《历史与阶级意识》等。
这是一条路而不是一个终点,如果这本书以其主人公 Dorrigo Evans 作为标题,我们获得的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与《奥德赛》相匹的现代史诗。乔伊斯的野望是难以复刻的,正如乔伊斯在寄予他人的信件之中谈及《都柏林人》一书,“我要为都柏林写一本道德之书”,史诗以及带有史诗信念的意图往往伴随着先定的生活的整体性 ( totality of life ),故而史诗性的文字中的沉郁更像是对于神话和至高秩序的诉求。这一诉求并不是节奏,而是框架,时间与旅程皆然,将人物和事件置于秩序之中。但是小说记述的是生活本身,以及意义在消逝和重获之间的节奏,叙事的艺术在于播撒事实也在于收获事实的露珠在一草一木上的倒影:叙事所收获的意义是未知的、朦胧的,是通过故事的情节来铺展开来的。而在所有的小说内人物的惊惧与好奇之中,读者们阅读故事并且同样寻找意义,小说的文本成为了读者本人对于生活的追求和执念。
这本小说之所以有成为史诗的可能,在于其阔大的格局,从 Dorrigo Evans 的老年生活开始,铺展开他生活之中相互交织联结的五个阶段。他的妻子是 Ella,但他在 1940 年的登岸假期时与他的叔父的少妻 Amy 有过一段难以磨灭的不伦之恋。而这段恋情在缅甸战俘营中修建泰缅铁路支撑着 Dorrigo,在修建这条通往北方的细路的艰难的时岁里,他埋葬了战友,也抛下了战友,他是奴隶也是军医,他掌管着日本人的药,却也在疟疾肆虐的丛林中无能为力:这条铁路从来没有真正修建成功,缺少工具以及澳大利亚战俘一个接一个的死去激怒了管理他们的军官,却也让这份无力和瘫痪蔓延到了牵涉这条路的所有的人。日军战败之后,人们有了新的生活,新的身份,迎接着老去,死亡,记忆和忘却。我们作为期待看到战争之中的恐惧和坚定,正如我们在国产剧集之中所看到的那样,但是最终我们感受到的是战争是一个剪不断的影子,是日常生活的另外一面,战争影响着日常的生活,而生命却最终包含了战争,并且将其席卷在其本身的节奏和律动之中:我们期待这是如同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那样的壮阔,然而真实生活之中的 Dorrigo 是一个他自己认为的懦夫和骗子:“越到晚年,越被‘歌颂’若有德之人,他越是憎恨所谓德性,不过是虚荣得以装点而殷切期待着掌声罢了” ( “The more he was accused of virtue as he grew older, the more he hated it. Virtue was vanity dressed up and waiting for applause” )。
▲《通往北方的细路》澳大利亚版封面
《纽约客》杂志对这本书的评述写道,《通往北方的细路》是一本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和略带做作的悲伤的小说,比方说小说的开篇就很不幸归于后者:“为何万事之始皆为光”(“Why at the beginning of things is there always light?” )。我们不妨认为这句话有失简练,也无法体现作者作为一名塔斯马尼亚人的特质,但是耐着性子往后读下去: “阴影如同扬起的手臂一般随后而来,它那黑黢黢的轮廓在煤油灯油腻腻的光中跃动着。”(“shadows came later in the form of a forearm rising up, its black outline leaping in the greasy light of a kerosene lantern”)。这时的前文之中的光被赋予了具象的形态,光和影无从分离,这样的跃动构成了故事的基础节奏,两者构成了生活的和弦;或者如同后文之中出现的海浪的意象那般"如同潜入海中再回到沙滩,周而复始"( “Like entering the sea and returning to the beach. Over and over.” )。海浪起落的节奏也正是光与影的变格,海浪升起之时,人们思绪涌动着,看到了阳光和教堂,看到在身旁爱着自己以及自己所爱的男男女女,然而海浪落下之时,又屈服于一种纪律,某种目的。如果说前者是日常生活的写照,不断地在人潮涌动和自我追忆之中寻觅自身在这个世界之中的和谐从而安慰在世上磨洗带来的苦涩,那么后者则是战争之中人的写照,是一种麻木和天地不仁的屈从,正如 Dorrigo 的哥哥 Tom 在一战结束后归家时,叙事者突然洞见了那个盯着火光之中的德皇肖像的人眼神中的疲惫和恐惧,打破了沉默:“一个人的个体感觉不总是和生活整体一致的,有时,它和世间万物皆不甚相合”(“One man’s feeling is not always equal to all life is. Sometimes it’s not equal to anything much at all” )。至深至切的不安在于一个人真实的感觉却不是外界需要我们感觉的,也就是卢卡奇所说的整体和谐并不存在,而叙事唯一能做的在于将个人的感受和经历从一团乱麻之中解脱出来,并寻找一丝一毫的能够和外在契合的和鸣,从而舒缓那份不安。
理查德·弗拉纳甘的创作是在如纪德的小说那样的赋格与交互的过程中实现人物与外在世界的对话,然而不同于其同侪对于城市生活与中产者格局的关注或是批评,弗拉纳甘发挥着外在世界作为一个空间的魔力,小说之中的对话不仅仅是人物,叙述者,读者和外在世界的对话,也是不同的世界和环境之间的对话,日本和塔斯马尼亚岛交错在这条通往北方的细路上:弗拉纳甘的野望不在于写作史诗,而是将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同时释放出来,将所能够集结到的事实四散到每个读者心中的棱镜上,让在重复浸泡在战争、回忆、大屠杀的二战后的心灵脱离麻木的桎梏,从遗忘的梦境中惊醒,重新投入到对于人的审视和理解之中。舒缓的过程和赋格的律动构成了叙事的主旋律(leitmotif):遗忘与记忆。
在小说中段的火葬之中,Dorrigo 和他手下的一个执行人发生了一些争论,是否要将一个死去的战友生前留下来的战地素描本留下来,Dorrigo 在迷茫和绝望之中念了一首吉普林的《退场赞美诗》:
我们的海军消失在远洋,
沙丘和海岬炮火已沉没。
瞧我们昨日全部的辉煌像亚述、腓尼基一样陨落!
宽恕我们吧,万邦的主宰,
让我们不忘怀,永不忘怀 !
“Far-called, our navies melt away;
On dune and headland sinks the fire;
Lo,all our pomp of yesterday
Is one with Nineveh and Tyre!
Judge of the Nations, spare us yet,
Lest we forget—lest we forget!”
(《退场赞美诗》选段翻译)
▲ 罗德亚德·吉普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 1865. 12. 30 – 1936. 1. 18),英国作家及诗人。曾获 1907 年诺贝尔文学奖,是英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Dorrigo 解释这首诗并非记忆的呼告,而代表着忘却,一切都将消隐:他口是心非地说“诗不是他的命运也不是他的律法”,但这首吉卜林的诗牢牢地烙在记忆之中,唯恐我们忘却。吉卜林写在维多利亚时代庆典的时候,在全盛的帝国的余晖之中,他看到的是衰退和落寞,尼尼微和推罗见证的暴行和残忍,英帝国见证着,却也要见证相同的湮灭,然而吉卜林并不是慨叹着湮灭,在这一刻他所想要的是就近的幸存的记忆和平安:万国的法官请高抬贵手,永志而不忘。
Dorrigo 期待着忘却战争中的折磨和战友的死去,而在这牵涉到集体的遗忘之中,他最希望遗忘的是他自己的存在,或者说彼时他最大的希望是死亡和被他人忘却,忘却于他已然是一种奢侈,从浓重的记忆之中抹去伤痕是最大的难事:死亡的愿景和绝望的无感是真正使人非人的,而在这个记忆与遗忘的变奏之中,弗拉纳甘运用的讽刺是深入骨髓的,Dorrigo 期待遗忘自己,通过抹去他人的记忆来让自己的麻木情有可原并且为人所知,这其实是一种谋杀一般的自私。作为对自私的报复,他唯一不想遗忘的那个女子, Amy, 最终被忘却了:“他记得住只言片语,光耀的余烬,舞动的火苗,但记不住她了——她的笑容,耳垂,她如同掠过一抹山茶花的笑容” (he could remember pieces, bright embers, dancing sparks, but not her—her laughter, her earlobes, her smile sweeping up to a red camellia)。遗忘和记忆的节奏在三页的方寸之地中不断闪现并且发生变化,无奈却也充满了喜剧的讽刺意味,叙述者仿佛是我们的影舞者,看着顾影自怜的人们,不禁抱着同情地嘲笑着。而更为嘲讽的是最后那本火葬堆里的素描本奇迹般免于损毁,Dorrigo 深思许久之后把它叠好放在自己身边,而以后编订战俘营年鉴的时候这些记忆竟还用得上。
记忆的变调不仅是在小范围的一个人物之中,这样的变奏在每一个人物中都获得了共鸣,战争带来的共同创伤成为了日本人和澳洲人所想遗忘的东西,他们或改名换姓(中村少佐),或深藏于心(Dorrigo Evans),或被审判处决(Choi Sang-min)但是在不同的方式背后的是相同的目的就是让自身和那个被战争创伤了或是光耀了的形象被忘却,所谓的光荣和耻辱到了战后的岁月里失去了所有的意义,因为战争已经摧毁了意义,将人类最为愚蠢而残酷的自私给血淋淋地暴露了出来,在这样的震惊之中战友的情感,坚毅的决定,甚至于为了减少工作不惜和日军军官顶撞的所谓壮举都变得苍白无力。但在这自我湮灭的潮流之中,却总有记得住的人,有些人是不断地被唤醒,另有些人则是在他人的庆贺之中怯怯地躲到一旁。
克尔凯郭尔在《非此即彼》中这么写道:“于我而言再也没有比记忆更为危险的事物了。在我记起一些我生命之中的关系的那一瞬间,这关系就这样结束了。真正纯粹的记忆的生命关系已经进入了永恒的轨道,也没了时间的羁绊。”最为纯粹的记忆是罗曼司一般的,是应该记住的东西,但是真正的记忆是在与现实的冲撞中重塑,唤醒:罗曼司是安全的,但是现实主义的记忆是痛楚的,有些应当遗忘的永远无法忘却,而被忘却了的则是最为需要纪念的。而当罗曼司的记忆和现实在杯酒之中丧失了界限,变得不那么分明起来的时候,一阵凄楚的美感便涌现了上来,这是永远无法到达的彼岸,也是在战争中的死魂灵回归故土的绵绵咏叹,中村少佐和辛田上校在对酌之中,不断地记起了那些俳师们的文句,他们变得充满深情,多了离愁别绪,哪怕身居京都都会在布谷的啼鸣中想念京都的人,只能在这如梦之梦之中回忆古都和那些曾经有过的意义:他们行走在消逝之中,却在停杯投箸间拾起忘却的纪念。
不妨回到开篇所说的弗拉纳甘作为叙事者的真诚。这样的真诚寄托在他对于现实中的记忆的了解和无奈,作者自己知道遗忘也是记忆的一部分,而没有一份记忆是完完整整的,得偿所愿的,我们祈求的平静安好不过是动荡不安的滚滚浪潮之中的沧海一粟,当我们挣扎着从记忆的海洋中捞起一丝珍藏之时,已然鼎鼎百年,在时间和忘却的潮水中,我们或是自私地投身于里或是不舍地看看身后遗留下来的残阳余影,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沉没于斯:而唯一能够拯救的,能够重新赋予旧人们以丧失的意义的方式大概便是记录和叙述了。
弗拉纳甘将这部小说题献给他过世了的父亲,而他的父亲就是在二战之中修筑这条铁路的战俘营的成员,尽管父亲的经历和 Dorrigo 相比可能没有那么多百转千回,但是这些战争中的恐惧与战栗,这些战后更加深刻的遗忘,以及那些经历过的勇气和信念,那些见证过的麻木和愚蠢:这些我们也在不断忘却的东西,我们赋予流血,恐怖以新的意义,新的代号,我们以为一个新的名称可以抹去血色的旧迹,然而这些也只是注定的徒劳。
在这条通往北方的细路上,日本人通向他们的故乡,澳大利亚人通往缅甸。但不仅如此,正如松尾芭蕉在《奥之细道》( 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 ) 的序言之中所言:“月日者百代之过客,来往之年亦旅人也。有浮其生涯于舟上,或执其马鞭以迎老者,日日行驿而以旅次为家”,无一例外,我们都羁旅于陌上。那些路边的脚印,草木零落的痕迹,流下的血,哭过的泪和嘴边的笑容,都属于我们。敢于记录上这条路上的人与物的人,我们称他为讲故事的人,而敢于真实地讲出一切的人,我们称他为勇士。
单读出品,转载请至后台询问
无条件欢迎分享转发至朋友圈
欢迎关注单读海外账号
instagram owmagazine
facebook OWmagazine
点击 阅读原文 预购《单读 16 · 新北京人》
▼▼一本明亮而温柔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