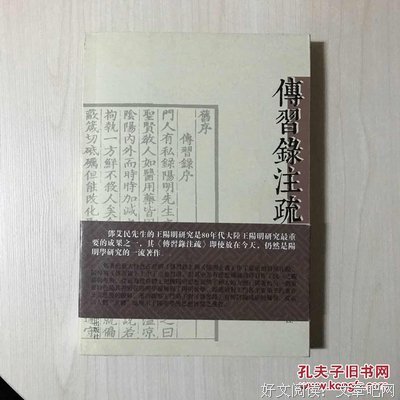《传习录注疏》经典读后感10篇
《传习录注疏》是一本由[明]王阳明 撰 邓艾民 注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29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传习录注疏》读后感(一):走进原著,莫拾牙慧
欲了解王阳明心学而非人云亦云,必读《传习录》。《传习录》在中国古籍中属于哲理思辨色彩较重的书籍,虽然大名在外,但是非真有需求者而不能读。
1.此版本为繁体字,对文字方面有一定要求。但是这个要求应该不算太高,查一查字典当能解决。对于古文有爱好者倒是更加合适。综合看来,这一条并不构成推荐理由。
2.此版本没有白话译文。本来传习录并不长,所用语言也并不深奥,稍有古文根基即可以通读。难点在于思辨和对其思想的领悟上,不在文字。读此书最好对于西方哲学、佛教思想(尤其是禅宗)、儒家思想事先有些了解。有些白话译文本有歪曲嫌疑,译文所占篇幅过长,反而有累赘之感。故而,个人建议直接读原文,尽量不要看白话译文。
3.此版本最主要的特点在于选了很多全书上的内容来补充印证。王阳明的思想也是一直在发展的,这部传习录是他的门人对其心学修行问答的辑录,并非阳明先生思想的全部,而且时间上也很难说就是王阳明思想最后的定稿。所以补充材料显得格外重要。
4.关于内容方面还有一些注释,个人认为主要是儒学方面的有价值。如果已经对于儒学有所了解,不必要再去翻看原籍,看看注释即可。
最后做一点说明,王阳明的心学可能更加接近印度教的一些教义;致良知,有先天道德论倾向。
《传习录注疏》读后感(二):左启华 后记
《传习録注疏》是邓艾民先生终身致力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项遗着。本书也与作者的经历一样,历经磨难,长期埋没于废纸堆中。艾民逝世以后,北京大学陈来博士将书稿推荐给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杨祖汉教授,并由法严出版社整理出版,本书才得以重见天日,我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艾民思想活跃,追求真理,青年时期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书即积极参加抗日运动。他坚定地认为,那个时代是需要哲学的时代,所以,他毅然离开他已经获得优秀成绩的工程学科转攻读哲学。自那时起,哲学这门学科就成为他终身探索的目标。毕业后,多年来一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
艾民一生坎坷,特别是在“文革”十年浩劫时期,知识分子成为“全面专政”的对象,加之他崇尚自由思考,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于是惨遭迫害,多次被抄家,长期被关押在“牛棚”之中,“监督劳改”于荒野之上。面对那种非人道的身心摧残,他总是心胸坦荡,坚持真理,决不同流合污。
“文革”后,正当他为了弥补失去的光阴而奋力拼搏时,癌症却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在住医院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全心投入哲学的写作,直到最后一次心跳。他在给挚友冯契教授的信中说:“得恶疾后,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有关宋明理学的一些条目;以及《传习録》的疏释和《朱子语类》的校点工作。当他已经无力执笔时,《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书稿尚未完成,逝世后由上海华东师大冯契教授为之整理、作序、出版。艾民的写作风格质朴无华,掌握丰富的资料,经过细致的分析和严密的逻辑论证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提出独立的见解,始终体现自由讨论的精神。
在与艾民数十年共同生活期间,我深深感到他是一位良师益友,是一位高尚的人。他一生追求真理,即使在逆境中,他也总是以豁达的胸怀探求人生哲理。在病中,他常常与冯契通信,坦率地讨论人性解放问题,认为心灵自由是一切创作的源泉,只有在真正自由发表意见的气氛之下才能有人性的解放,才能言行一致;而专制统治只能造就虚伪。他们也讨论人道问题,认为哲学对于人的德性的培养具有积极作用。在讨论人生的理想时,他们认为“文革”时期没有理想,只有空想,造成人性的严重破坏。他们对于中国哲学的未来充满希望,对于人类未来充满信心,认为人类终将走向个性解放。现在,冯契教授也已因病逝世,我深信,他们的共同信念会得到实现的。
如果说,艾民在青年时代就立志研究哲学,是因为他感到那个时代是需要哲学的时代;那么,当今的时代仍然是一个需要哲学的时代。本书是他毕生学术成果之一,如今得以出版,流传于世,我想这一定会告慰他在天之灵的。
左启华
公元2000年5月15日于北京
《传习录注疏》读后感(三):读《传习录注疏》札记(一)
《传习录注疏》是上海古籍出版的邓艾民注解本,早期曾以油印本作为北大哲学系研究生的教材,陈来认为此书“可以说代表了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王阳明研究的水平”。从全书的特色来看,邓先生将《王文成公全书》以及其他与本书相关的材料分别注解在相关段落下,以王解王,从而交相呼应,有利于加深对《传习录》文本的学习理解。注疏博采众长,而又简明确当,足见注者之功力。现在比较遗憾的是,还没有读到陈荣捷先生的《传习录详注集评》,不能做一番比较。
《传习录》有多重要?《四库全书》评价阳明一生时说,“守仁勋业气节,卓然见诸施行,而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也”。梁启超在推荐《传习录》时候有言, 读此可知王学梗概。欲知其详,宜读《王文成公全书》。因阳明以知行合一为教,要合观学问事功,方能看出其全部人格,而其事功之经过,具见集中各文,故阳明集之重要,过于朱、陆诸集。钱穆所指出的七部“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中,《传习录》是唐宋后仅有的一本,钱先生指出,这本书篇幅不多,且可一条条分开读,爱读几条读几条。下面我结合这本书谈谈对其中“知行合一”之教的学习体会。
据《年谱》记载,阳明38岁时,提学副使席书聘他主贵阳书院,“是年先生始论知行合一”。在跟门人的讨论中,徐爱提出“如今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孝悌,却不能孝悌,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阳明首先从“知”得定义即本体(即本来意义)入手,他认为“未有知而不行,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之所以出现知而不行的情形,只是因为“被私欲隔断”,而圣贤教人知行,就是要“安复那本体”。并举例“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臭时,已是恶矣,非闻后而始立心去恶也”,“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体”。阳明认为,关于“知”,是由行来定义的,有知必有行是谓“真知”(knowing how to do something)。其次从知行本体是个动态的过程,“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道德律令与实践理性合二为一。
阳明在立此说时曾多次强调要门人理解他的“宗旨”,若不领会他的立言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说闲话”。而阳明的立言宗旨,徐爱的序中提及到阳明平时论学时的话,“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加减之,要在去病,初无定说。”传习录中也说;“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换言之阳明对“知”和“行”都做了自己的解释,并且是一种有目的指向且富含价值判断的解释。阳明对“知”做了缩小解释,认为只有行的知才是他认为的“真知”;而阳明对行则做了扩大解释,行不仅仅是人们所看到的行为,即便是“一念发动出即是行”,人心中所发动行为的意念也是“行”。而在做这些解释和评价的时候,阳明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提出“知行合一”之教。“夫学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知行合一”之教所针对的是冥行(普通意义上的行)妄作和知(普通意义上的“知”)而不行。前者“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后者“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
在“知行合一”的视野内,“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服了”,这才是学问的工夫。阳明说:“圣学只是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换句话说,如果阳明学以致良知为圣学目的所在的话,知行合一则是为学功夫。因此“君子为学,何尝离去事而为废论说?”所以“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欲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盖阳明意义上的知行合一是为学功夫所在,而“行”本身就包含了发动行为的意念,所以在意念上去除私欲亦是功夫所在了。徐爱已能领会阳明先生知行合一之训,故而他在序言中说到:“吾侪于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不体诸身,则爱之此录,实先生之罪人矣。”因此那些不在阳明意义上范围内的“知”,即知而不能行的“知”,如“以有限精力为无用之虚文”、“溺于词章记诵”、“考据训诂的口耳之学”都在被阳明摒弃之列。盖阳明学是一种讲究实践的道德哲学。钱穆有言:“阳明讲学,偏重实行,事上磨练,是其着精神处。”
《传习录注疏》读后感(四):读《传习录注疏》札记(二)
阳明一生于事功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明史》评价他“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然“誉满天下,谤亦随之”,阳明也遭受到了常人难以预料、难以忍受的诽谤诬陷。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阳明正是“人要在此等时磨炼”,“即知即行”,最终“因明至诚,以进于圣人之道,遂以优入圣域”,达到了很高的人生境界。因此在“阳明学”的视野下考察阳明对“毁誉”的体悟也变得非常有意义了。
阳明晚年回顾自己一生,“因叹先生自征宁藩以来,天下谤议益众”,于是问待坐在周围的弟子,请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业势位日隆,天下忌之者日众;有言先生之学日明,故为宋儒争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后,同志信从者日众,而四方排阻者日力。”阳明认为他们的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有未及处。夫子因此自道到:“我在南都已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吾亦只依良知行。”退而作诗,有“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这是阳明“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所谓“从百死千难中得来”,最终的体悟就是“毁谤自外来的虽圣人如同免得?人只贵于自修,若自己实实落落是个圣贤,纵然人都毁他,也说他不着”。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毁誉荣辱之来,非独不以动其心,且资之以为切磋砥砺之地,故君子无入而不自得,正以其无入而非学也。若夫闻誉则喜,闻毁则戚,则将惶惶于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为君子!往年驾在留都,左右交谗,某于武庙当时祸且不测,僚属咸危惧,谓君疑若此,宜图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对于立志做圣贤的君子,毁誉荣辱到来之际,非独不动心则已,反而是“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炼”,平时问学讲究省察克治之功,是不是真的有所得,就要在此等关节处打通。
阳明在遇到人生的困境和外在的诽谤时,能够练就处事泰然、狂者进取的境界,与阳明平时讲学的宗旨是分不开的。阳明学的主旨是“正人心,存天理,灭人欲”,为学的工夫是“学存天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体认天理,只要自心地无私欲”。平时的省察克治之功就要用在不断地扫除廓清这些私欲,不至于被彼蒙蔽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到得无私可克,自有端拱时在。”以射箭为喻,阳明认为:“心端则体正;心敬则容肃;心平则气舒;心专则视审;心通故时而理;心纯故让而恪;心宏故胜而不张,负而不驰;七者备而君子之德成。”
而在“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中,“诚”的态度就显得非常”重要。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都有的,一个人之所以特别看重外在的毁誉,而不注重内心的修炼,只因为“心有所昏蔽”,不能真诚的面对自我。不能诚实的对待自我,就会被外在的评价所吸引,就会主次不分,本末倒置。应对之要就在于,首先在于分清“实与名”的轻重,“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认清轻重之后,“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大学》所谓“欲正其心,先诚其意”是也。孔子说:“君子嫉没世而名不称”,阳明解释为,称字去声读。亦‘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之意。实不称名,生犹可补。没则无及矣。
一个人如果能真诚的对待自己,纯此天理之心,“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来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倒的样子出来。”《易经》有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阳明因此劝诫到:“诸君只要常常怀个‘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处,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动。人若着实用功随人毁谤,随人欺慢,处处得益,处处是进德之资;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终被累倒。”
《传习录注疏》读后感(五):陈来 序一
艾民先生的书终于要出版了。
现在海内外的朋友多知道我和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的关系,但很少有人知道我和邓艾民先生的关系。
艾民先生是我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1979年夏,研究生一年级结束,当时作教研室主任的张先生(岱年),要我们“中国哲学史”专业的十个人,各报自己希望研究的方向。酝酿之后,我看大家多报“先秦”,于是就选了“魏晋”。暑假过后,张先生告我:“你的方向要改一下。”决定由艾民先生作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艾民先生专长在宋明哲学,特别是朱子和王阳明。于是我就确定以“宋明”为方向,选定朱子为研究对象。以后的研究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艾民先生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文革”前在北大哲学系主掌系务工作。他虽然在北大从事中国哲学的研究,可是他最推崇的,是他的朋友冯契。冯契与艾民先生在西南联大曾同学,又有志同道合之谊,但他们是终身相知的朋友。一般人极少推崇同行中的平辈同学和朋友,可是艾民先生多次向我说,他认为冯契的研究最好,要我注意看冯契的东西。也是在艾民先生的建议下,我去旁听了数理逻辑专业的几门课。从这里看,他似乎也很欣赏逻辑分析的方法,因为冯契的特点,就是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金岳霖的逻辑分析加以结合。
我给艾民先生写过一些读书报告,依次为“孟子”、“庄子”、“公孙龙”、《易传》、“郭象”。“庄子”的一篇在1980年北大“五四科学讨论会”宣读过,郭象的一篇发表在《中国哲学》,而艾民先生比较欣赏“孟子”的那一篇。我也写过一篇“二程”,未获发表。但我的用力所在,主要还是朱子。记得上来读王白田《朱子年谱》时,对于朱子早年的“已发未发”说,颇觉难明,就写了一页问题,请问艾民先生。艾民先生要我自思而得之。于是我自己又去用功,而终于深造之而有所得。此在愤悱启发之功,不可不归于艾民先生。
1979年到1980年,杜维明教授在北京访学,在北大的座谈结束后,与北大几位先生同游未名湖。杜教授问起艾民先生的研究兴趣,答“宋明理学”,杜即为之精神一振;又问最喜欢何人,答以“王阳明”,杜大喜之。于是两人深谈良久。当时艾民先生主持北京市哲学会的工作,即邀请杜教授在北京市哲学会讲演,艾民先生特为介绍,当时北京研究中国哲学的名流都在座,我们也参加了旁听。
1982年艾民先生从夏威夷参加“朱熹思想研究国际会议”回来,全力投入王阳明的研究,那时他给1982年入学的研究生开“王阳明哲学”的课,他写了讲义,从生平到哲学,论述很精彩、很细致。他让系里把讲义油印,发给同学,要同学在讲义上面的边、眉处写他们的读后意见。他在学期结束时把这些讲义收回,要我来看(那时我已在系里教书),学生的评价也很好(如李仁山、景海峰)。其中《王阳明生平》一章,他曾在1981年秋天“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上讲过;他认为王阳明是封建时代的圣人。听说这个讲法当时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不过他并不在意。他的想法,是以这些讲义为基础,写成一本“王阳明哲学”的书。同时,他又作了王阳明《传习录》的注释,也是交由系里油印,作为研究生的教材,希望经过讨论修改后成为专著。这个时期是他学术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他的这两部阳明学的著作,在他生前虽未出版,但可以说代表了80年代初中国大陆王阳明研究的水平。《传习录注疏》这部书,即使放在今天的学术界,也仍然是阳明学研究的一流著作。这里仅举一例: 《传习录》第一条中:“‘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四部备要》本、《王阳明全集》本、陈荣捷先生本文字皆如此。而《传习录注疏》作“然非新字义”。下出校注:“《王文成公全书》本,‘新’讹作‘亲’,据闾东本改。”这个改正显然是正确的。本书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可惜,1983年他被发现得了癌症,次年过世,否则,他给予中国学术界的贡献一定会更大。他患病住院期间,我曾多次去探望,当时他在医院仍在积极修改这两项研究。在刚刚住院时,他对我说,王阳明哲学的书,还差几章,如果来不及,希望我帮他补写这几章;而《传习录注疏》的修改如来不及,就希望魏常海帮他完成。最后,《传习录注疏》终于还是完成了。而王阳明哲学的部分后来也由冯契先生将之与艾民先生有关朱子的论文合并,在上海出版。
多年前,杨祖汉教授听我说起艾民先生有关于《传习录》的书稿,对我表示可以安排在台湾出版。于是我就将此意转达给邓师母左启华教授,她为了书稿的打字,付出了多年的辛苦。现在,这部书终于付印,既可以告慰艾民先生,也使邓师母的心愿得以达成。书将付印,邓师母要我写几句话,我就将艾民先生与我的渊源往来,略表出如上,亦用以纪念艾民先生。
公元2000年2月序于香港
《传习录注疏》读后感(六):读《传习录注疏》札记(一)
《传习录注疏》是上海古籍出版的邓艾民注解本,早期曾以油印本作为北大哲学系研究生的教材,陈来认为此书“可以说代表了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王阳明研究的水平”。从全书的特色来看,邓先生将《王文成公全书》以及其他与本书相关的材料分别注解在相关段落下,以王解王,从而交相呼应,有利于加深对《传习录》文本的学习理解。注疏博采众长,而又简明确当,足见注者之功力。现在比较遗憾的是,还没有读到陈荣捷先生的《传习录详注集评》, 不能做一番比较。
《传习录》有多重要?《四库全书》评价阳明一生时说,“守仁勋业气节,卓然见诸施行,而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也”。梁启超在推荐《传习录》时候有言, 读此可知王学梗概。欲知其详,宜读《王文成公全书》。因阳明以知行合一为教,要合观学问事功,方能看出其全部人格,而其事功之经过,具见集中各文,故阳明集之重要,过于朱、陆诸集。钱穆所指出的七部“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中,《传习录》是唐宋后仅有的一本,钱先生指出,这本书篇幅不多,且可一条条分开读,爱读几条读几条。下面我结合这本书谈谈对其中“知行合一”之教的学习体会。
据《年谱》记载,阳明38岁时,提学副使席书聘他主贵阳书院,“是年先生始论知行合一”。在跟门人的讨论中,徐爱提出“如今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孝悌,却不能孝悌,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阳明首先从“知”得定义即本体(即本来意义)入手,他认为“未有知而不行,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之所以出现知而不行的情形,只是因为“被私欲隔断”,而圣贤教人知行,就是要“安复那本体”。并举例“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臭时,已是恶矣,非闻后而始立心去恶也”,“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体”。阳明认为,关于“知”,是由行来定义的,有知必有行是谓“真知”(knowing how to do something)。其次从知行本体是个动态的过程,“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道德律令与实践理性合二为一。
阳明在立此说时曾多次强调要门人理解他的“宗旨”,若不领会他的立言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说闲话”。而阳明的立言宗旨,徐爱的序中提及到阳明平时论学时的话,“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加减之,要在去病,初无定说。”传习录中也说;“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换言之阳明对“知”和“行”都做了自己的解释,并且是一种有目的指向且富含价值判断的解释。阳明对“知”做了缩小解释,认为只有行的知才是他认为的“真知”;而阳明对行则做了扩大解释,行不仅仅是人们所看到的行为,即便是“一念发动出即是行”,人心中所发动行为的意念也是“行”。而在做这些解释和评价的时候,阳明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提出“知行合一”之教。“夫学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知行合一”之教所针对的是冥行(普通意义上的行)妄作和知(普通意义上的“知”)而不行。前者“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后者“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
在“知行合一”的视野内,“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服了”,这才是学问的工夫。阳明说:“圣学只是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换句话说,如果阳明学以致良知为圣学目的所在的话,知行合一则是为学功夫。因此“君子为学,何尝离去事而为废论说?”所以“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欲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盖阳明意义上的知行合一是为学功夫所在,而“行”本身就包含了发动行为的意念,所以在意念上去除私欲亦是功夫所在了。徐爱已能领会阳明先生知行合一之训,故而他在序言中说到:“吾侪于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不体诸身,则爱之此录,实先生之罪人矣。”因此那些不在阳明意义上范围内的“知”,即知而不能行的“知”,如“以有限精力为无用之虚文”、“溺于词章记诵”、“考据训诂的口耳之学”都在被阳明摒弃之列。盖阳明学是一种讲究实践的道德哲学。钱穆有言:“阳明讲学,偏重实行,事上磨练,是其着精神处。”
《传习录注疏》读后感(七):这是简体横排版,还是繁体竖排版?
早就想看这本书了。
请教一下读过这本书的朋友。201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的《传习录注疏》
这是简体横排版,还是繁体竖排版?
上世纪八十年代关于《传习录》研究有两部重要著作,因各种原因,今天仍未有超过他们的著作问世,一部是陈荣捷的《传习录详注集评》,另一部就是邓艾民的《传习录注疏》。 陈著长于考证,详于介绍历代各主要《传习录》的评注,但对《阳明全书》所收的阳明其他文字与《传习录》中的思想观点有何关联,却未免有所疏略,即陈著的着力点在评注而不在于义理阐发。 邓著在《传习录》版本的把握以及在文字出典的注释方面虽然稍逊于陈著,但最大特色在于将《传习录》与《阳明全书》作了严密的对照比勘,同时将《传习录》上中下三卷打通,对其中互有思想关联的条目作了统一之观察和考辨,这就为从整体上把握阳明思想提供了极大方便。邓著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在于其视野从阳明学扩展到阳明后学,也就是说,他通过对王门各主要弟子著作及其思想的了解,进而观察王门弟子对《传习录》有何评论或新的阐发,由此向人们“立体”地展示出阳明学的思想展开之进程。
《传习录注疏》读后感(八):阳明论为学——读《传习录注疏》札记
《论语》以“学而”为第一章,开篇孔子就循循善诱地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孟子谓高子曰:“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荀子》更是专辟一章“劝学”来讨论为学问题,可见“为学”在儒家的学说中有很重要的位置,虽然他们所指各有不同,但是有一点似乎特别值得注意,他们均将为学和成人联系起来。那么阳明作为卓越的思想家对此问题又有什么独特的思考呢?
徐爱在《传习录序》中引用阳明的讲话到:“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加减之,要在去病,初无定说。若拘执一方,鲜不杀人矣。今某与诸君不过各就偏蔽箴切砥砺,但能改化,即吾言已为赘疣。若遂守为成训,他日误己误人,某之罪过可复追赎乎?”在阳明眼里,人们的“纯乎天理之心”因“私欲之蒙蔽”,已成为病人矣。“君子之学,心学也”,作为普通人“心有不存,而汩其性,丧其天矣”。先生讲学的宗旨之一就是复其“吾心光明”的本性,学以存其心。针对“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和“茫茫荡荡悬空去想”,阳明认为:“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屡责之。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内,种此一大树。雨露之滋,土脉之力,只滋养得这个大根。四傍纵要种些嘉谷,上面被此树叶遮覆,下面被此树根盘结,如何生长得成?须用伐去此树,纤根勿留,方可种植嘉种。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养得此根”。阳明感叹到:“世间知学的人,只有这些病痛打不破,就是善与人同。”
为学有先后:阳明喜欢以“树”为喻,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他认为孔子“气魄极大,凡帝王事业,无不一一理会,也只是从那心上来,譬如大树有多少枝叶,也只是根本上用得培养功夫,故自然如此。”然而一些学者学孔子,却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去学那气魄,就如同从枝叶上用功做根本一样,却做倒了。以此为标准评价朱熹,他认为孔子本心是要行道于天下,道不行才退而修六籍;朱熹就有些本末倒置,早岁便要继往开来,著许多书,到了晚年才有所悔悟,在阳明看来,这是舍本逐末。
在为学资质上,阳明认为,圣人是生知安行,普通人是学知利行,另外也有因困知勉而困知勉行的。对于生知安行者,“良知原是精精明明的。如欲孝亲,生知安行的,只是依此良知实落尽孝而已”;对于学知利行者,只是时时省觉,务要依此良知尽孝而已;至于因困知勉者,蔽锢已深,虽要依此良知去孝,又为私欲所阻,是以不能,必须加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方能依此良知以尽其孝。阳明因此告诫到:“圣人虽是生知安行,然其心不敢自是,肯做困知勉行的功夫。困知勉行的却要思量做生知安行的事,怎生成得?”因此初学用功,对于声色货利,却需要扫除干净,勿使留积,不断的积累,自然能顺而应之。圣人是可学而致的。关于学与思,阳明也有自己的看法。孔子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阳明对此发挥到:“学有所疑,便须思之。思而不学者,盖有此等人,只悬空去想,要想出一个道理,却不在身心上用其力,以学存此天理;思与学作两事做,故有罔与殆之病,其实思只是思其所学,原非两事也。”
关于为学的自修,阳明认为:“学问也要点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当,不然,亦点化许多不得。”良知在自己胸中,其间的痛痒也只有自己最清楚,阳明认为一个人如果有过,听从别人的劝导而改过自新,远不如通过自己悔悟而来的真切,君子悔过以迁善。一个人在未曾悔悟前,就如同“昔镜未开,可以藏垢”,而一旦悔悟,“今镜明矣,一尘之落,自难住脚”,而这个时候恰是一个人优入圣域之机,其关键就是开悟之后能不能勤勉的坚持住。
阳明逝世之后,王门分为八派,其中的原因之一“致良知”说法的提出,发自晚年,没来得及与学者深究其旨。在阳明生前,他曾经说过,他对于朋友来问学的,都“尽吾所见”,以期有益于斯道也。“若徒入耳出口,互相标立门户,以为能学,则非某之初心,其所以见罪之者至矣”。后来门徒不仅标榜门户,而且崇尚空谈,王学最终走向没落,远非阳明所始料能及。
《传习录注疏》读后感(九):读《传习录注疏》札记(二)
阳明一生于事功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明史》评价他“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然“誉满天下,谤亦随之”,阳明也遭受到了常人难以预料、难以忍受的诽谤诬陷。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阳明正是“人要在此等时磨炼”,“即知即行”,最终“因明至诚,以进于圣人之道,遂以优入圣域”,达到了很高的人生境界。因此在“阳明学”的视野下考察阳明对“毁誉”的体悟也变得非常有意义了。
阳明晚年回顾自己一生,“因叹先生自征宁藩以来,天下谤议益众”,于是问待坐在周围的弟子,请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业势位日隆,天下忌之者日众;有言先生之学日明,故为宋儒争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后,同志信从者日众,而四方排阻者日力。”阳明认为他们的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有未及处。夫子因此自道到:“我在南都已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吾亦只依良知行。”退而作诗,有“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这是阳明“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所谓“从百死千难中得来”,最终的体悟就是“毁谤自外来的虽圣人如同免得?人只贵于自修,若自己实实落落是个圣贤,纵然人都毁他,也说他不着”。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毁誉荣辱之来,非独不以动其心,且资之以为切磋砥砺之地,故君子无入而不自得,正以其无入而非学也。若夫闻誉则喜,闻毁则戚,则将惶惶于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为君子!往年驾在留都,左右交谗,某于武庙当时祸且不测,僚属咸危惧,谓君疑若此,宜图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对于立志做圣贤的君子,毁誉荣辱到来之际,非独不动心则已,反而是“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炼”,平时问学讲究省察克治之功,是不是真的有所得,就要在此等关节处打通。
阳明在遇到人生的困境和外在的诽谤时,能够练就处事泰然、狂者进取的境界,与阳明平时讲学的宗旨是分不开的。阳明学的主旨是“正人心,存天理,灭人欲”,为学的工夫是“学存天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体认天理,只要自心地无私欲”。平时的省察克治之功就要用在不断地扫除廓清这些私欲,不至于被彼蒙蔽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到得无私可克,自有端拱时在。”以射箭为喻,阳明认为:“心端则体正;心敬则容肃;心平则气舒;心专则视审;心通故时而理;心纯故让而恪;心宏故胜而不张,负而不驰;七者备而君子之德成。”
而在“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中,“诚”的态度就显得非常”重要。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都有的,一个人之所以特别看重外在的毁誉,而不注重内心的修炼,只因为“心有所昏蔽”,不能真诚的面对自我。不能诚实的对待自我,就会被外在的评价所吸引,就会主次不分,本末倒置。应对之要就在于,首先在于分清“实与名”的轻重,“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认清轻重之后,“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大学》所谓“欲正其心,先诚其意”是也。孔子说:“君子嫉没世而名不称”,阳明解释为,称字去声读。亦‘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之意。实不称名,生犹可补。没则无及矣。
一个人如果能真诚的对待自己,纯此天理之心,“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来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倒的样子出来。”《易经》有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阳明因此劝诫到:“诸君只要常常怀个‘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处,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动。人若着实用功随人毁谤,随人欺慢,处处得益,处处是进德之资;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终被累倒。”
《传习录注疏》读后感(十):阳明论为学——读《传习录注疏》札记(三)
《论语》以“学而”为第一章,开篇孔子就循循善诱地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孟子谓高子曰:“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荀子》更是专辟一章“劝学”来讨论为学问题,可见“为学”在儒家的学说中有很重要的位置,虽然他们所指各有不同,但是有一点似乎特别值得注意,他们均将为学和成人联系起来。那么阳明作为卓越的思想家对此问题又有什么独特的思考呢?
徐爱在《传习录序》中引用阳明的讲话到:“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加减之,要在去病,初无定说。若拘执一方,鲜不杀人矣。今某与诸君不过各就偏蔽箴切砥砺,但能改化,即吾言已为赘疣。若遂守为成训,他日误己误人,某之罪过可复追赎乎?”在阳明眼里,人们的“纯乎天理之心”因“私欲之蒙蔽”,已成为病人矣。“君子之学,心学也”,作为普通人“心有不存,而汩其性,丧其天矣”。先生讲学的宗旨之一就是复其“吾心光明”的本性,学以存其心。针对“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和“茫茫荡荡悬空去想”,阳明认为:“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屡责之。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内,种此一大树。雨露之滋,土脉之力,只滋养得这个大根。四傍纵要种些嘉谷,上面被此树叶遮覆,下面被此树根盘结,如何生长得成?须用伐去此树,纤根勿留,方可种植嘉种。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养得此根”。阳明感叹到:“世间知学的人,只有这些病痛打不破,就是善与人同。”
为学有先后:阳明喜欢以“树”为喻,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他认为孔子“气魄极大,凡帝王事业,无不一一理会,也只是从那心上来,譬如大树有多少枝叶,也只是根本上用得培养功夫,故自然如此。”然而一些学者学孔子,却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去学那气魄,就如同从枝叶上用功做根本一样,却做倒了。以此为标准评价朱熹,他认为孔子本心是要行道于天下,道不行才退而修六籍;朱熹就有些本末倒置,早岁便要继往开来,著许多书,到了晚年才有所悔悟,在阳明看来,这是舍本逐末。
在为学资质上,阳明认为,圣人是生知安行,普通人是学知利行,另外也有因困知勉而困知勉行的。对于生知安行者,“良知原是精精明明的。如欲孝亲,生知安行的,只是依此良知实落尽孝而已”;对于学知利行者,只是时时省觉,务要依此良知尽孝而已;至于因困知勉者,蔽锢已深,虽要依此良知去孝,又为私欲所阻,是以不能,必须加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方能依此良知以尽其孝。阳明因此告诫到:“圣人虽是生知安行,然其心不敢自是,肯做困知勉行的功夫。困知勉行的却要思量做生知安行的事,怎生成得?”因此初学用功,对于声色货利,却需要扫除干净,勿使留积,不断的积累,自然能顺而应之。圣人是可学而致的。关于学与思,阳明也有自己的看法。孔子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阳明对此发挥到:“学有所疑,便须思之。思而不学者,盖有此等人,只悬空去想,要想出一个道理,却不在身心上用其力,以学存此天理;思与学作两事做,故有罔与殆之病,其实思只是思其所学,原非两事也。”
关于为学的自修,阳明认为:“学问也要点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当,不然,亦点化许多不得。”良知在自己胸中,其间的痛痒也只有自己最清楚,阳明认为一个人如果有过,听从别人的劝导而改过自新,远不如通过自己悔悟而来的真切,君子悔过以迁善。一个人在未曾悔悟前,就如同“昔镜未开,可以藏垢”,而一旦悔悟,“今镜明矣,一尘之落,自难住脚”,而这个时候恰是一个人优入圣域之机,其关键就是开悟之后能不能勤勉的坚持住。
阳明逝世之后,王门分为八派,其中的原因之一“致良知”说法的提出,发自晚年,没来得及与学者深究其旨。在阳明生前,他曾经说过,他对于朋友来问学的,都“尽吾所见”,以期有益于斯道也。“若徒入耳出口,互相标立门户,以为能学,则非某之初心,其所以见罪之者至矣”。后来门徒不仅标榜门户,而且崇尚空谈,王学最终走向没落,远非阳明所始料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