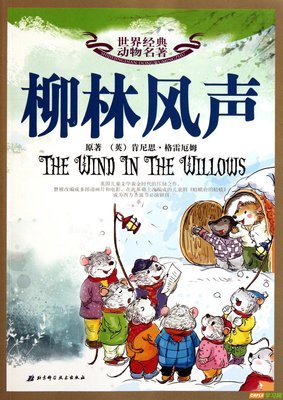我们读后感精选10篇
《我们》是一本由骆以军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34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们》读后感(一):时间停摆一刻之后
窗子外面骄阳似火,我闷坐在研究所里听不知名的鸟儿聒噪地叫着。空调自我来的那天起就没好过,室内弥漫着一股汗水混杂许久不洗澡的味道。座位四周的师兄师姐脑袋耷拉在不知是晒黑还是体垢堆积的脖子上,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看来又是一个无聊的实验室午后,我数着鸟儿的叫声,作起了香艳的白日梦。
突然,请允许我使用“突然”这个词,虽然我知道故事的转折要尽可能平缓,而“突然”是我能想到的最不负责任的、最突兀的转折,但是,就是突然之间,最后那声啼鸣像是被拉长的汽笛声,一直在耳边环绕。手本想堵住耳朵,不知怎么像是润滑油用光的机器,怎么抬都愣在那里,除了鸟叫声,刚才没在意的喇叭声,建筑工地的施工声音现在也都以相同的频率和振幅穿了进来。感觉再多忍一秒,耳膜都要裂开。然后,也是突然之间,各种声音都回复了本来的样子,那只傻鸟还是高一声低一声叫着。我睁开刚刚因为耳朵刺痛闭上的眼睛,看到所有人都晕了过去,有的趴在桌子上,有的软塌塌搭在椅背上。“难道是都被振晕了?”面对着这诡异的场景,我有点害怕,我不确定是要打急救电话,还是要报警。正在犹豫不绝的时候,一声巨响伴着火光从外面传来,我赶紧跑到窗户边看是怎么回事。楼下的马路上十几辆车撞在一起,在我看的时候又想起了爆炸声。此刻,马路上的车丢了魂似地横冲直撞,马路牙子上是躺着的人。
爆炸声还在继续,有的是从远处看不到的地方传过来的,有的就是楼下马路上传来的。我在播了十多次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都没人接听之后,确定是出事了。是刚才的怪声,还是恐怖袭击,我边乱想,边检查师兄师姐的情况。他们像是睡着了一般,有心跳有呼吸,但是却对我的各种交换和掐揉都没有反应。忙活半天,我不得不放弃了他们可能会醒过来这个想法。
对面大楼已经开始冒起了烟,看来是汽车爆炸的余威已经波及到了那里。我赶紧跑下楼,来到了大街上。对面大楼的火势非常凶猛,已经离了五六百米还是感觉火光炙人。挨着近的几棵树已经着了,树下面躺着的人却浑然不觉,街上都是撞在一起的车,成了一条河,把路的两边硬生生隔了开来。我沿着马路牙子往前走,到处都是倒下的人。
这时候,手机响了,是我女朋友,接通后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晃过神,只听到好像她在说害怕、所有人都晕倒了、她们那边已经没有电了,“待着别动,我已经在过去的路上了”,我和她说,“我知道”。
《我们》读后感(二):窥视
如果说《西夏旅馆》是借“西夏”最后的逃亡历史及“旅馆”局促的空间来隐喻台湾外省第二代的命运、历史和身份认同。
如果说《遣悲怀》是作者在友人自杀身亡之后同“时间”与“死亡”的一次对谈。就像《一千零一夜》山鲁佐德讲故事一样,他不断岔开去讲述别的故事,力图使时间停止,延 缓死亡的到来。而死亡终究会来,爱与死亡并存,活着就是一遍一遍重复的伤害。
如果说《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是作者借小说家次子的身份,讲述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是一副未来时光的预言书。在荒诞、戏谑、温情、引人入胜而又忍俊不禁的故事背后隐藏着的是作者对回忆、对遗忘的追寻。
那么这些小说背后或光明正大,或隐隐绰绰的身份焦虑、死亡思索、荒诞温情又是从何而来呢?
《我们》就是有“私小说家”之称的骆以军在自剖。
从人生体验到精神妄想,从琐碎生活到写作职场,他向读者告解他曾遭遇或见证的那些不可思议的真实的恶意与光荣:如何度过被“游街”的复读之年、如何残酷地拒绝那如此爱他且爱了很久的情书少女、如何在家中遭遇火灾时天真地聆听如人工瀑布潺潺水声的“火的声音”、如何与他的人渣兄弟们变身为妄图怯懦地与暴力对抗的街头恶童、如何在深夜被真正的恶童打破整排落地窗时为了保全妻儿低声下气委屈求和、如何为偷情失约编造关于狗尸体的怪异故事、如何心理阴惨地以父之名与怒蛇搏斗……在这五十四篇古怪故事里,潜藏着难以穷形尽相的各种怪物,这些亦真亦幻、难辨真假的人生奇遇,成功地变成一本媲美怪力乱神的荒诞故事集。
读完《我们》,你或许会莞尔,或许会在心中大骂作者的狡黠,更重要的是你会有一种吃完鸡蛋又完整地围观了一遍母鸡的快感。你会找到通向骆以军小说中种种情愫的隐秘桥梁。那些喋喋不休、阴测测、充满暴力、死亡、诱惑、情欲、迷惘、虚无的表述,将不再陌生而无解。那些废墟般的意象、充满瘟疫的时代感让你感同身受。从此你们或合谋,或沦为他恶意的对象,如此种种。你知道,在他生活和精神的后花园边上,那个隐秘的窗口,你不曾缺席。再没有比窥视更有趣的事,更何况是窥视一场精神的狂舞。
《我们》读后感(三):失控的异想世界与完美的心灵独白 ——《我们》的荒诞私小说
失控的异想世界与完美的心灵独白
——《我们》的荒诞私小说
长久以来,我们都在设想成为一个心灵上的满足者,未必是上天入地这么离奇不经的事情,但也大多和安逸、自然、平和的生活沾不上边,我们希望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而不是随便什么样子的都好的有家庭有孩子有一成不变按部就班生活的一天和一年以前没有什么两样的平凡乏味的生活,于是,《八十天环游地球》那样的奇思妙想的经历会延绵至今畅销不衰,《黑衣人》之类的外星人遐想也层出不穷,即便是我们“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古代先辈们,潜意识里也在猜想有神秘的力量的存在,不然为何《聊斋》一出,家家户户基本都能略说一二,而雷雨之极,孩童从老人那里听到的故事,也必然不会少得了雷公电母之类的难以自圆其说的哄骗小儿的谎言。
长大以后,我们会发现,这些向着某个神秘方向奔去的臆想,不是我们力之所及的,但是正如心灵上那个空虚的虫洞没有弥补依然在吞噬我们的满足感一样,我们会尝试通过对自我的认知或者说对自身意识无边无际的发散去填补我们难以平复的欲望。正如《墙上的斑点》带给我们惊鸿的震撼,抑或《喧哗与躁动》的情感的游走、《追忆似水年华》的胡说八道又引人入胜。意识流,然后是魔幻现实主义,我们渐渐离开地球表面,去追寻意识脱离躯壳的释放。也许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个非现实的,但超越现实满足感的世界。
“不伦梦境、妖孽现实、恶童往事、撒谎奇技”“你我命运交织的共同身世,媲美怪力乱神的荒诞故事”,这是写在封面角落上对于这本红色封面的《我们》的评价,平凡的本体剪影和拉长了的影子,不正是本书内容的一种最好的映射么?当生活平凡的有些“淡出鸟来”的意味,不如潇洒的成为一个追求自我心灵丰满的异类,坦然面对世界的异常以及自己的妥协与颓废,自我嘲笑成直面内心欲望的“人渣”,却更能找到内心,更能成为那个值得在任何一刻离开世界都不会觉得懊悔的人。
《我们》就是这样一本书,从头到尾,你都看着作者在发疯:有时候是诡异的用来恐吓孩子的鸭嘴兽;有时候是年少时为了莫名的原因单挑比自己大的少年,以为意气风发;有时候是编造一个自己已经写在小说里的情结去骗自己的妻子……在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一个充满想象的人,他潇洒肆意地活着,不用去惧怕什么特别的东西,坦然,然后为成为“人渣”而怡然自得。
“做自己”,是需要勇气的。一次一次,我们被现实磨去想象力的棱角,父母曾经对我们说过的“不要早恋”“还是找个稳定的工作吧”“门当户对要紧”“现实一点”“离婚了孩子怎么办”之类的,渐渐地也会变成有认同感的话,然后说不定有一天,会讲给自己的孩子听。我们也终究会变成曾经如此不屑的人吧,所以,成为“人渣”,也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后会痛苦,会绝望,会麻木,会再也不会拥有属于闭上眼睛以后的脑海里的世界,再也不会在独处的时候,想象门外面有奇特的魔鬼走过破窗而入抓住自己用最讨厌的胡萝卜填鸭式地塞满自己可怜的胃。
所以,这是一本值得所有已经忘却了自己的人读的书,充满了奇思异想和无限可能,它告诉所有人,自己放弃掉的意识世界尽管光怪陆离,依然会很精彩,是那个我们曾经独处的时候,试图找到的自己,是在“完全不搭嘎”“绝对扯淡”“什么跟什么啊”“这也可以”一类的感叹之后,却不得不承认,嘿,“我也要这样去想”的真正的属于“我们”的《我们》。
在这个失控到漫无边界的异想世界里面,有最完美最真实到血淋淋的内心独白。
y 林怿
2012年7月14日星期六
.M.13:26
写于蓝牙小筑
《我们》读后感(四):种故事的人
在没有阅读骆以军的作品之前,你很难想象那样一个憨厚胖实时常将笑脸带在身上的人写作的笔触是如此的阴暗绮丽。我们见到的骆以军,总是带着一脸的笑容,那种几乎时时刻刻都保持在脸上的,将络腮胡子挤开,将眼睛挤在一起的华丽的大笑,在一次锵锵三人行的节目中,我看着骆胖大笑着和窦文涛打趣,那笑容伴随着近似哮喘病人发作时候的急促呼吸声,真让人替骆以军担忧,感觉他或许随时随地就会伴随着那笑声而支离破碎。
于是不仅仅是骆以军的小说,连他本人,那个看起来如一只胖熊般臃肿,穿着宽松t恤和休闲裤的骆胖,也变得让人有梦幻之感,缺乏实体的飘忽和疏松感觉,像星河般的碎碎点点蔓延而去。
在《我们》中,骆以军说,在一年左右的时光中,他曾做过梦的速记练习。将一支笔和一本笔记本放在床头,在梦醒时分,打开床头台灯,在微弱昏黄的黑夜与白昼交界时分,快速记下梦中所发生的一切。在梦境慢慢收敛于一点之前快速回忆起那逐渐模糊的内容,将不断收缩的平面用力拉扯回与原本相似的模样。
骆以军就像个拨动时间的巫师,将原本一分一秒行进的秒针分针时针拦截住,在他的笔下时间在那一瞬间从三维幻化成了二维,咔嚓一声,一幅关于这一秒这一分的速写便在他的笔下形成。
在《脸之书》中,骆以军写到一个故事。曾经住过的房子顶楼空无一物,没有任何遮挡,在夏日之时烈日直射水泥屋面,让住在顶楼的他家中本来难捱的闷热愈发强烈。于是一鼓作气之下他买了几十盆盆栽,那种塑料盆装的小号盆栽,让人全部搬运上屋顶,而在之后他还买了较大的四五人环抱的塑料空盆,自己拎四袋混合培养土,提上五楼阶梯,将之前所买小盆中经过一年幸存下来的幼小植株都移植到新的有着赭红色有蟠龙纹的合成塑料花盆中。在那一段时间当中,家中每有客人来访,骆以军不在之时,妻所言不再是“他去咖啡屋写东西了”,而变成了“他去楼上种树了”。
“我时常在晚上七八点空气整个凉下时,独自在顶楼浇水。随着一大盆一大盆植物抽高,有时我拿着橡皮水管在那些绿叶葱茏,几乎皆已长到胸前的小树间穿梭,像是在一微型森林或花园迷宫里悠游,那时灰白的天空犹有微光,四周环伺着大楼的廓影(奇怪那些大楼似乎都空置着而寥寥落落只有几扇窗亮着灯,或是顶端一明一灭,孤寂透了的飞航闪红灯),有时天顶镶着一颗银白明亮的金星。树叶的不同气息像魔术在我周围旋转。近距离犹会发现叶面上积着水银般的小水珠。那些时刻,我总会为自己是在城市上空而不是山里,感到迷幻如梦……”
我想骆以军的《我们》所给人的感觉也依稀是如此吧。在骆以军对于自己过去现在和道听途说故事的叙述中,在我妻我儿我重读班的那班人渣兄弟和我之间的穿行,在自己的垃圾时光和独处时光里,在故事开始的时候逐渐变慢的时间,在故事结束时突然回归正常,那种入梦和出幻的感觉,就像在昏暗的楼道中穿行和上升,走在前面的被称作大熊的骆以军,在狭窄昏暗的楼道中,饱满低沉的开始讲话:“诶,我和你说一个故事哦……”
于是你又陷入种故事的人的绮丽荒诞的梦之境了。
《我们》读后感(五):骆以军、人渣和我们
文/Shirleysays
在我的印象里,身材健硕戴眼镜的男子都心地善良、爱心盈满,比如像骆以军这副样子。谁知骆以军自己倒不这么看,他很享受地称自己是人渣。台湾作家蔡昀臻曾如此评论:“悠游自得的人渣身份,是骆以军自诩的强项”。然而,骆以军对于自我人渣的定义是,“那似乎是我那个世代的人,用一种化整为零的方式,和那个‘不理会你撒娇’的世界,和解,并且没入其中。”这个评价来自于他的新作《我们》中的《想我人渣兄弟们》。
《我们》,这书名有意思。我们会哪个特定时刻互称“我们”?提及人类这个大族群时,必言我们;在攫取共同利益时,必言我们;在抵抗自然攻击时,必言我们。身处纷繁乱世中的我、你、他,汇成我们,不必分辨谁更像人渣。这种身份的印记,同时也会引起焦虑。陈丹青曾经说过,有机会他要写本书,就叫《身份证》,来商榷身份证对于我们的意义。在呐喊世界大同的今天,无论你持有何种身份证明,你的生命里都会闪现他人的身影,你逃不出“我们”。正因为骆以军是台湾外省人的第二代身份,他对身份有更多一层的理解。
钟晓阳在《哀歌》里说,世间没有真与假,有的只是现实和梦境。骆以军在《我们》里的散文就是梦与现实边纠结边挣扎着集合,浮生若梦。我们仿佛可以窥见从小是恶童,长大便成了人渣的骆以军似人生轨迹。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曾这样走过一遍,可我们都没有勇气坦白,宁愿把自己在阴暗里包裹得紧紧地,仿佛忘了保鲜膜即能保持新鲜,又能图财害命。难怪他在台湾被称为“私”写作的小说家。
骆以军是喜好做梦的,不论梦境好或糟。朱天文说,骆以军的眼睛就像核爆,所有东西被他目光一扫就全部变成废墟。他的梦中蕴藏充沛的想象力,有股颠覆现实的力量。就像书中的《春梦》、《客途之梦》、《瘟疫时期的怪梦》都是在写梦,那些天马行空的梦呓,恰到好处地回避了不可能存在的现实。从《围城》里的方鸿渐一直梦到宫崎骏的《神稳少女》,不乏父亲的亡魂和阿扁总统的身影穿梭其中。在他以《噩梦》为全书结尾时,仿佛人渣的梦里早已摒弃美好。荒诞,或许也是我们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命题。
如果从梦中拉回到现实,那么骆以军的国中生活以及他后来在阳明山的日子,是他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他用了最直接、最灰暗的词汇形容他的那段日子,“灰调忧郁、枯寂无聊”。一个在国中里每次考试都是最后一名的少年,或是一个大学毕业后写不出好作品而日夜焦虑的青年,他只能选择与恶童为武,或是直接变成恶童,最终自然而然地成为人渣。他以伤害别人来抵御自我痛苦,甚至动过偷考卷的念头,只有他懂得那个女人为什么要去偷一辆消防队的云梯车。因为,他们都活在一个见不到阳光的世界里。所在,他在《诚实》里写道,“然后从照相机视窗里看着他们无比美好地曝闪在镁光灯里,心里想:‘从此我和你们是不同的人了。’”这是一种人生定位的自醒。
骆以军是天生的思考者,他总是不断地对自己的身份、身边的世界以及所处的时代反思。思索杀掉了大把的时间,也让他尝尽孤独,在他心里,对于时光有特殊的待遇。《独处时光》、《秋日海滨》、《昔日酒店》和《垃圾时光》都是他对无形遁去时间的一种缅怀。纪伯伦说,昨日不过是今日的记忆,明日不过是今日的美梦。时间就像爱,无法分隔又无间隙。而骆以军在懊悔痛失光荫的同时,也狡猾地说,“那是我的垃圾时光,也是我的整补时刻”。这是一位悲世者的自我揶揄,黑色幽默反而让欢乐畅快淋漓。他说,这样就像阿嬷一样,觉得自己更靠近世界的温度一点。
那么,今天的世界是何种的温度?有的地方像火焰山,有的地方像北极地。不同的温度造就了不同的我们。有唐氏症患儿的生物老师;为了吸毒而抢劫的烂仔阿辉;在异乡帮佣的印尼女孩;以及忍受变脸(面瘫)痛苦的骆以军,他们在骆以军的笔下无疑是生活在北极地的我们,生活像冰一样冷。骆以军在整本书里没有描绘任何一位成功人士,那些人生炙热得像活在火焰山上的我们。如果北极地是一片海,那么火焰山就是一座孤岛,终有一日海会湮没孤岛,反之亦然。所以,他们逃不出“我们”。
尽管骆以军在写《遣悲怀》时,遭遇了邱妙津粉丝的抗议。但如果你读过骆以军的书,你就懂得他有种天性里的悲悯情怀,他曾经那么接近死亡,或是屡屡地靠近死亡般的绝望,他不会畏惧死亡。所以,他才会写下《我的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他擅于书写虚实相拥的作品,就像梦与现实交织在一起。纪伯伦说,让今日用记忆拥抱昨日,用渴望拥抱明日。明日依然是我们的期待,无论骆以军和我们是不是人渣。
《我们》读后感(六):不一样的人生
代序
骆以军
我曾做过一个这样的梦:梦中场景是在一类似南港线捷运终点昆阳站一带之印象,一空旷如假期之街景,一个铁道阡陌纵横、机关车维修、停歇、调换轨道的终点。戴着黄胶盔的工人,在柏油热浪的凹凸空气里埋头锁着铁轨上的巨大螺丝。我记得在梦境中我骑着那种孩童车尺寸的捷安特越野车,车后站着的我的姊夫——虽然真实世界里我并未有这么一位姊夫——他扶着我的肩,我们笑嘻嘻地任那脚踏车从出站后的一个陡坡朝下俯冲。
后来从那个梦境醒来后我自然是怅惘极了。不只是那个画面中的明亮无忧,我置身其中清晰可感的少年身体,那位未曾谋面的姊夫,梦中那个画面无论朝前倒带或朝后播放,都似乎是一组和我现在的人生完全颠倒重组的人际关系。
在醒来的这个界面细细体会,努力召唤梦中更多细节,愈清楚明白:那不只是“做了一个梦”,那个梦境向我展演的,是一个和我现在正在经历的那个版本,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我记得在我从那个车站出来之前,我是不断地在类似“侯峒”、“菁峒”“暖暖”这些侯孝贤电影里的东北山区废矿的小车站间换车转车。那些小站月台遮篷的方形木柱皆被蛀虫啃蚀中空,我脑海里浮现一句一位女性长辈曾给予的忠告:“你总是把一目了然的事实弄得那么复杂。”问题是我总是搭错车,发现后匆匆下车又必须在这巨大蕨叶密覆的无人小站,旷日费时地等候反方向折回主干线的小火车。
这之前的另一个画面,亦是在那样的某一部电影中的印象:光线暝晦的一间和式房间,人脸的廓影全在一种低抑谨慎的气氛里凑近说话。
那位在现实世界里我非常尊敬的女作家在这里变成了护士长之类的角色。在梦境中(在那个房间里),她木讷而权威地劝说我接受一旁一位沉默医生注射一种昂贵的疫苗。我记得我在梦中饱含情感地那么想着:“即使是比这更严重之事,您说的什么我都愿意相信哪。”
那样的,和我现在这个无法挽回的人生,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种人生。事情似乎变得单纯而容易解决。除了在那些车厢间的联结踏板上摇摇晃晃地醒悟:“唉,又坐错车了。”或一种窸窣的不安:“时间会不会这样被耽搁了?”
所以在后来那个画面,在明亮的光照下,走出那个车站,骑着捷安特越野车,后座载着比我年轻的姊夫——后来我才确认,这位“梦中姊夫”,真实世界里是一位命运比我坎坷的学弟。这两年来自我父亲中风倒下,我遇人总是唉声叹气,只有在这位学弟面前我绝对闭嘴:他除了要照顾已倒下的老父,还得看护另一位与父亲结拜之伶仃老人——为何会整个人浸晃在少年时代才有的,身体处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撒欢”之轻快。梦中姊夫在后座告诉我许多事:包括现实世界里因为细故而得罪,且似乎永远无望解除他对我的成见和憎恶的一位老师,在梦境里是从事外销成衣生意(所以他对我的创作生涯,没有那么大的杀伤力?),这些年赚赚赔赔,似乎也吃了不少苦头。另一位我近日刚过世的姨丈,原来只是我们脚踏车经过的巨幅西部电影看板里的,一个油漆画上去的外国演员。
“原来如此。”我在梦中松了一口气。在另外的这个世界里,我不曾娶妻、生子;没有为了逃兵而将身体变得如此胖大;那些亲手一只一只埋葬的狗们皆尚未死去;我至爱的亲人也还没开始衰老朽坏……。
那些缠结的,无法挽回的,人事上的纠葛和伤害,有的尚未发生,有的以一种让我默然以对的简单形式重新组合。
另一次我曾梦见:我和一位少年时代的古典吉他老师,一同坐在夜间无人的地铁月台弹奏吉他。事实上这位身怀绝技的吉他老师(他是“台湾古典吉他王子”苏昭兴的弟弟),二十年前我一共只跟他学了两个月左右的入门课程(我记得大部分的时间是他要我用留长修成弧形的指甲,无意识反复弹拨琴弦,感受音质的醇度)。他是我少年时代启蒙的最早的“艺术家”形象:怀才不遇、脾气刚烈、愤世嫉俗。有一些细节我忘记了,但我记得当时他不知什么原因主动收我为徒(我和一群迌少年喳喳呼呼闯进他的吉他店里挑选一把便宜民谣吉他),不收学费传艺给我。但我那时终究因性格浮躁且缺乏天分而让他失望了。后来的几次课程他几乎是不可思议地叹气、暴怒,对我对他视为第二生命的古典吉他竟如此漫不经心深受伤害。我不记得后来是他叫我不必再去了还是我因愧耻而不再踏进那间教室。我的吉他技艺便只停留在最初级几章的《卡尔卡多吉他教本》。
但是在那个梦里,我和那位吉他老师,并肩坐在冷风飒飒的地铁月台,一人抱着一把吉他,像竞技又像对这孤独艰难人世致敬,即兴却又赋格严谨地重奏着一些像阿莫多瓦电影里的,高难度的西班牙舞曲。他像用神的手指没入黄金绸缎那样炫耀地抡动琴弦,把魔术、梦境、女人悔恨的叹息、海浪击碎船只的暴力、斗牛士将长剑插进牛只咽喉的汨汨流动声……全密不透风繁花错织在那个原本空洞阴暗的空间。梦中的我竟也一手绝技,忐忑地,亦步亦趋地,颠狂迷醉地让左五指右五指在琴弦两端踢踏着舞步,随着他,闭目、摇头晃脑,无视梦境之外真实的时间定义,以我这辈子根本无法拥有的华丽技艺,伴奏着。
那么地美好。
后来那位学弟恰巧打电话给我,我笑着告诉他:“前几天还梦见了你哟,梦里你竟然成了我的姊夫。”不晓得是羞怯或创作者对对方唬烂本性的不信任,他沉默了一会,说:“真的吗?我前几天也梦见了你。我梦见我和我妹被一群歹徒绑架,绑在一个房间的椅子上,那时我心里还想我真是世上最衰的人,他们绑我,除了让家里那两个故障老人因为无人喂药喂食换尿袋而静静死去,实在一点好处都没有吧。就在这时,一个穿着消防队制服的胖子,破门而入,比我们还紧张地救了我们。现在想想,那个胖子就是你啊。”
说来真像一个四处乱搭,许多片子同时在拍摄的片场。我们知道或不知道,匆促换装地在不同剧情的摄影棚间赶场串戏。不一样的人生。有时或会穿错制服,或许慢慢忘了不同故事间的时差换算。我最恐惧的一幕或是,在那钻进钻出,颠倒换串的某一次,走进了整个片场的最角落。在那无可回身的走道,遇见某个故人,彼此想起什么,黯淡地互望一眼:“不想就过了这样的,这样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