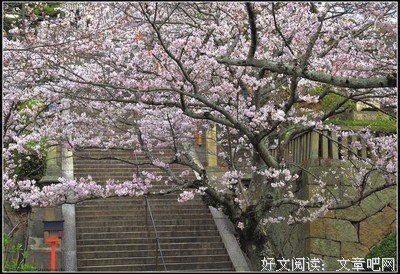《广岛之恋》观后感10篇
《广岛之恋》是一部由阿伦·雷乃执导,埃玛妞·丽娃 / 冈田英次 / 贝尔纳·弗雷松主演的一部剧情 / 爱情 / 战争类型的电影,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广岛之恋》观后感(一):用电影补偿往事
在2006年的时候,已是87岁高龄的阿伦•雷乃以他依然旺盛的工作热情和创作敏感拍摄了电影《心之所属》。
可能在大部分的电影史著作中,阿伦•雷乃的电影创作止于《我的美国叔叔》,而对于他近二十年的创作,却很少有人关注。数年来,他始终保持着对时代文字、流行音乐、漫画、滑稽戏和现代戏剧等一系列文化现象的浓厚兴趣,1980年后他的电影里他不断地在自己电影进行着叙事结构和表达手法上的创新,于是1980年来,他依然保持着法国影片的良好成绩,成为新浪潮导演的标志。1980年后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一部《向死之爱》,虽然这部影片并没有《几度风雨几度秋》、《吸烟/不吸烟》、《老调常谈》以及《心之所属》有名,却在形式创新以及主题的深度挖掘上达到了统一,堪称晚年阿伦•雷乃电影的总结。
言归正传,在阿伦•雷乃众多的电影中,《广岛之恋》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无可争议地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同时也是“左岸派”的代表作品。
这里首先引出的一个议题是关于法国“左岸派”电影的定义以及颇具争议的界定。
“左岸派”是法国的一个重要的现实主义电影流派,形成于上个世界50年代末,由于其成员大都居住在巴黎的塞纳河左岸,因此被称为“左岸派”。像阿伦•雷乃、玛格丽特•杜拉、阿伦•罗伯—格里叶、亨利•科尔皮、阿涅斯•瓦尔达等,代表作除了以上提及的《广岛之恋》(1959)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1961),还有1960年的《长别离》,1966年的《横越欧洲的快车》等。
但是,因为“左岸派”几乎是与“新浪潮”同时被人发现的,而且“新浪潮”的汹涌浪潮似乎裹挟了“左岸派”电影,所以基于此的结果是有相当多的人将其看作“新浪潮”的一部分,某些电影学书籍亦有将《广岛之恋》等归入“新浪潮”旗下的。即使二者在艺术的求新求变上体现了某种法国式的一致,但是它们在美学、电影观念和叙事语言上的差异也是很明显的。一般认为,“左岸派”在这些方面的探索较之“新浪潮”更为激进极端。它本身所带有的实验特征也更为明显。这种现代主义电影的先驱性,亦被之后兴盛时期的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以及德国新电影运动所继承,甚至在亚洲的日本新浪潮式的电影革新和我国的台湾地区以杨德昌、侯孝贤等电影导演为代表的新电影运动也可窥见其一二。
“左岸派”的主要编导大都来自文学界,或者他们深受文学影响,在他们编导的过程中,对话和人物内心的独白成为了影片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阿伦•雷乃、玛格丽特•杜拉,他们希望创造一种全新的电影语言,平衡文学文字和电影影像。
以《广岛之恋》为例,剧中女主人公(“她”)试图忘记战争年代自己在家乡内韦尔的痛苦恋情,她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了。可是当她来到日本广岛这个布满战争回忆与伤痕的时空之中,记忆却如潮汐般汹涌袭来,而影片易被人们理解的她与日本男子新建立的爱情,也无情地消失在过去的创伤中。
阿伦•雷乃试图让人们了解的肯定不是她与他的那段婚外恋似的爱情,透过这层外表,导演希望人们了解,遗忘是为了告别过去,以期获得渴望的心灵宁静。但残酷的一面是,记忆虽然可以被人用所谓的理智压住,却已经深深烙在了人的内里,用弗洛伊德的意思来理解,就是化作了潜意识,成为每个装载它的生命体的一部分,无法割舍,导演强化的其实是记忆与遗忘的痛苦对她的一生的萦绕与折磨。
“左岸派”电影的另一个特点,或者说是对电影艺术表现上的贡献,在于他们的创作中彻底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时空观念,将西方人(欧洲人)拿手的逻辑的、线性的(电影)时间改变为近乎令人费解的“心理时间”,这也给“左岸派”电影在时空跳跃转换上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例如,《广岛之恋》的结构就完全摈弃了传统的故事情节和线性叙事结构,影片中令人应接不暇的大量闪回和画外音的手段,把过去与现在,现实与想象以编导思考的跳跃性结构娴熟地联结起来,或者用通行的说法叫“平行结构”,现在与过去两个时间概念是平行发生的,在她的思绪中,导演用“闪切:将过去与现在交织在一起。从这一点分析,“左岸派”的编导们将人们熟悉的电影带入了人的内心,所以在电影史上,“左岸派”的贡献的确拓展了现代电影的时空观念,虽则艰涩,实为深邃。
有趣的是,“左岸派”的编导们自称是“电影剪辑派”,这颇与苏联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强调镜头组接有某种内在的继承性。
其实,“左岸派”电影固然强调自身在剪辑方面的重视,这在《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一片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这类影片超过六七成的价值是剪辑赋予的。所以在文章最后,可以讨论一下“左岸派”电影在电影语言的独特探索思考。
《广岛之恋》的片头显得十分特别。法国女人与日本男人不是一开始就出现于镜头里面,导演让现在的他们与广岛核爆的画面交替出现,渐渐地将男女主人公显现在画面中,这种光线的压抑感处理,使观众对这段现实与历史的交替出现没有任何突兀之感。“左岸派”电影摄影强调画面构图和用光效果。在摄影机的运用上,我们经常会发现面对一个静止的物质(或人),摄影机是缓缓拉回或推进的,细节被不断地放大及至充斥整个画面,思考一下,这不正如人的眼睛一样。但是“左岸派”的眼睛却是十分的冷峻与严肃的。
声画处理在“左岸派”看来应该是同时的,如前文提及的平衡文字与影像,他们也关注平衡声音与画面。《广岛之恋》却也暴露了至少是阿伦•雷乃的倾向,即将声音置于一种优先的地位,《广岛之恋》中声音在画外空间中的运用,男女主角对记忆的描述与过去的画面同时行进,当然这也是对白、独白和旁白的魅力所在,“左岸派”编导手中的声音被拓展到广阔的空间中。
在“左岸派”电影中,《广岛之恋》成为一部经典,如果我们撇开这些冗繁的理论和说教,《广岛之恋》其实应该理解为比“一般新闻纪录片更具说服力”(玛格丽特·杜拉评价)的具有纪实风格的电影,是阿伦·雷乃在用电影补偿我们对于和平与战争、爱情与失落的往事。
《广岛之恋》观后感(二):爱情面前太多阻碍
电影是以两副赤裸的躯体开场,相互拥抱的肩膀和手臂上都是汗水,看上去像是浑浊的水泥,在皮肤上流动。
以两人的对话开始电影叙事,女主讲述她在广岛看到的一切,那些画面穿插进来,有关广岛的一切,原子弹爆炸后的广岛,和居住在广岛的平民,那些承受不公正命运的人。一幕幕目不忍视的画面,使人看了不禁落泪,看到战争的可怕。
无论是以胜利为目的而开始的战争,还是以和平为结束的战争,从性质上说,战争都是可怕而残忍的。总有人要死去,可怕的是死去的是没有犯过任何错的普通人,悲哀的是将由这些无辜的普通人来承担命运的责难,而自己的后代也要继续承受这份不公正待遇,却不能反抗,不能说“不”。
影片的画面是柔和的灰色色调,以一种诗意的、抒情的调子展开故事。将现在与过去用淡入淡出的剪辑方式衔接起来。女主人公的一切激动情绪都受过去事件的影响,那些关于往事的片段场面让女主深受折磨,十多年前的痛苦回忆因为现在的情人而被唤醒。
他爱上了她,通过她的回答来不断了解她。
而她,深受往事的折磨,深受现在的折磨,她爱上了不能爱上的、不会有任何美好结局的异国男人。
这个“可怜”的女人,是那么渴望爱情,却不能得到爱情,只因为拥有爱情对于她而言就等同于变得不忠、不贞。她渴望不贞,她渴望爱情。
战争有时候也会制造某些不能相爱的障碍,想要忽视那些障碍就会被看作对亲人和国家的背叛。
伦理和法律也将制造某些不能相爱的障碍,忽视这些障碍将会被视为不贞。
“有时候我们应该避免去想,世界上的那些苦难,否则就会令人难以忍受。”
想要学会遗忘,怎样遗忘?
生命会继续,时间也会继续。
记忆总会被勾起。
“多告诉我一点吧。几年后,让我忘记你的时候。而且又有像这样纯习惯性的情事发生时。我将会想起你作为爱情遗忘的象征。我知道我将会想起这件事,就像要忘却恐怖一样。”
这是一个关于战争和爱情的故事。在战争里备受争议和反对的爱情,在伦理上被视为对婚姻背叛的爱情。
《广岛之恋》观后感(三):欢迎误读
虽然爱情是件梦幻而迷离的事,但估计没几个人敢真的拍一部如此梦幻而迷离的电影。套用侯麦的话说,“阿伦·雷乃的作品具有明显的贵族化倾向,有着专属于他自己的作者风格胎记,是永远也无法被模仿和复制的文本。”连侯麦如此中产阶级骚包的导演都说是贵族,可见阿伦·雷乃有多精英。自然而然地,看他的电影可以被视为是一种身份或知识阵地的象征。
[广岛之恋]是最能反应整个左岸派特征的电影。您还别嫌闷,相比[去年在马里昂巴多],它已经相当不晦涩了。作为现代电影开山之作,它截然相反于之前电影的直白单一。过去、现在、梦境、幻想被交错更迭在一起,它也许是爱情、战争,也可能是伤痕、记忆,看起来说了不少,又好像什么都没说。因为暧昧,[广岛之恋]泛泛而精确地击中了文艺青年们的不同块垒。技术至上者看得到精美的构图和繁复的剪辑;文学至上者瞧得见意识流和无理性的诗意对白;人道主义者可以看到战争对人的心灵摧残;存在主义者可以看到生命的虚妄。爱做梦的人看到梦境,爱思辨的挑得出内核。啥也不占只愿意瞎抒情的,也能看到一个撕心裂肺或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你可以说它是布莱希特似的、佛洛依德似的、萨特似的、伯格森似的或者博尔赫斯似的,因此,它只能是阿伦或者杜拉斯似的。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将来会有某个俱乐部、沙龙或论坛以它作为文艺青年资深等级的快速检测片——看完电影喊闷的显然段位不够,再仔细一看,没留胡子,肯定是伪的,胆敢混进来泡妞!!至于那些一听片名就说自己也喜欢莫文蔚的,丫根本就没被检测的资格啊。
因其复杂多义的剧情、含混不清的指代关系,也曾难倒戛纳的影评人,然而正如编剧杜拉斯说的,当时“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写不出,什么也说不了。真的,正是因为无能为力,才有了这部电影。”她和阿伦·雷乃给我们提供的,是个常被误读,也不怕误读的最好范本。最后那个被称作内维尔的女人,是留下来还是走了?这并不重要,就像我们也不知道她和他是如何相遇的一样。
《广岛之恋》观后感(四):去广岛再初恋一次
去广岛再初恋一次
内陆飞鱼
《东邪西毒》里,那个寂寞的人冷冷地抱怨,说人最大的烦恼就是记性太好,很多过往舍不得或者没办法忘记,成为思想累赘。遗忘还是记起,对很多人来说,和死去还是活着一样,真的是个问题,特别是软弱的、郁悒的、多愁善感的人,记忆可以让他们飞升仙境,也可以让他们堕入冰谷,不想记的全记住了,想记住的怎么费力去思考,还是毫无下落。记忆,一块随身携带只能照自己的镜子,我是什么的样人我自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自己也大抵知晓。好了,电影开始了,来看看,因为是故事,因为是假的,而且和你和我无关,是他们的电影,他们的故事,只管看,不必伤神。
广岛,他们坐在咖啡馆,漫步在和平广场,纠缠在旅馆里。他站在草坪上的棕榈树后,看着她在摄影机下扮演白衣天使,她听见他说,我媳妇外出了,要过两天才回来,眼波就流转起来。剧毒的蘑菇云开放过后的广岛,草木刚刚泛青的广岛,老人和孩子才露出笑容的广岛。这个法国女人,在仅仅一面之缘就让她动心的日本男人面前,踟躇在记忆的河流沿岸。巨大的飞机马达轰鸣,等待在跑道上等着她快速进入黑暗的机仓,脱离这片土地。在这个漂亮的男人面前,她忧郁了,她再次说到了遥远的涅威尔,那个埋葬了十八岁青春的法国小镇,以及那里的德国男人。
涅威尔,不在那里,不这里,在记忆里的“别处”,幽暗的地窖里生满苔藓和菌类,她用没有秀发的徒头,使劲地撞击冰冷的墙壁,头皮擦破了,留下了一道道的血痕;涅威尔,十八岁的她和德国士兵翻越篱笆,围墙,偷偷地在河畔、森林约会,在鸟的歌唱里他们象鸟一样亲昵,身体和情绪一道缠绵和沉溺。他们不在乎战争,他们不认为彼此是敌人,他们喃喃私语,只知道享受。还有比情绪和身体重要的享受吗?涅威尔,只有他们知道,曾经发生了什么,记住了什么。
现在是广岛时间,天气很暖和,这个男人静静地听着,被伤痛过后暧昧的广岛天气和眼前人挑拨,她想到了法国,想到涅威尔,想到十八岁和德国士兵,语速和神情越来越激动,甚至有些歇斯底里,指手划脚,咖啡杯差点被打泼。她的动作就要失控,她的记忆就要失火。他一巴掌掴过去,然后心疼地抱住他,抚摩她,刹那,她似乎被无形的刹车控制,惭愧地对着他笑笑,天暗下了,外面潋滟的水光晃荡着窗玻璃上。巨大的飞机的机翼在跑道上,倒计时,分分秒秒,滴答滴答。
灯火迷离的广岛之夜,海风醉人,他们三十多年疲劳奔波,熬惯不疼不痒的日子的身躯,仿佛回到了初恋,他们甚至开始承诺了,然后又幡然反悔,太远了,太假了,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各自的老婆、丈夫,现在,当下,此刻,拥抱才是最真切的。他的黑色的柔顺的头发,和她离开涅威尔后长出来的金黄的卷发,在一前一后地起伏。在涅威尔的小河边,地窖里,她没想过自己会穿着和平鸽一样的衣服来到东方,和鸽子们进入镜头,来到太平洋边的广岛,遇见这个男人。巨大的飞机的机翼又在跑道上响着了,倒计时,分分秒秒,滴答滴答。
在广岛,你看到了什么?你什么也没看到,博物馆里永远是没有头发的女人,没有四肢的孩子,没有植物的废墟的照片,那些被烧焦的钢铁扭曲成蛇一样横亘在大街上。是啊,记录片总是那么认真。可是,在广岛你什么都听到了,什么都看见了,在暖流和寒流交织的云层里,闭上眼,你就闻到了初恋的味道,涅威尔的味道,只是,一转身,巨大的飞机和机翼已经安然着陆。
《广岛之恋》观后感(五):《广岛之恋》:现代电影的先锋
说来可笑,我一次听说「广岛之恋」是莫文蔚的歌曲,而非玛格丽特·杜哈的剧本抑或阿伦·雷乃的电影。不过,当年在听到这首KTV点唱冠军的歌名与歌词后,总觉得背后应当是有些故事或者背景的。然而后来当我明白了《广岛之恋》与杜哈和雷乃的渊源时,马上觉得自己逼格未够,只得望而却步。直到想起一观之时,已然相隔经年。
《广岛之恋》出自闷片祖师阿伦·雷乃之手,想要体验娱乐性肯定是天方夜谭。但就个人观感而言,影片并没有令人感到无聊烦闷,至少比雷乃另一部闷到「惨无人道」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要好过许多。法国女人(白种女人)和日本男人(黄种男人)的露水之情率先已勾起观者的猎奇之心,再加上时空交错中那些关于前尘往事的回忆,乃至这对异国不伦恋的何去何从,九十分钟下来,端的是恰到好处。
《广岛之恋》观后感(六):因爱而爱
两个赤裸的身体蜷缩在一起,不仅仅在肉体上交流,灵魂也在交流,女子醒来后静静看着睡在床上的日本男子,让他想起自己的初恋,过去,以及战争,“我想再见你”男子跑去找女子,乞求她留下,她勾起了日本男子对爱情的欲望:在咖啡馆,女子向日本男子述说过去,女子感叹原来自己也年轻过,最后,彼此发现,男子叫广岛,女子叫内维尔。
电影《广岛之恋》是阿仑雷乃执导,艾玛妞丽娃英次主演的一部透过爱情故事折射出真正的可怕与忘却的重要性,电影开头以赤裸的身体引入,回忆性的讲述女子的过去,用内维尔作线索,串起了整部影片,影片《广岛之恋》荣获1959年12届戛纳电影国际评委会奖,法国梅里爱奖,1960年纽约影片奖。
本来人生平淡无常,可突然生活中遇见你,生活便动荡不堪,虽说爱情只是春光乍现意乱情迷,但此刻彼此深陷沉迷,女主角在深夜广岛街道痛苦游荡,衬衣衣裙,洁白得像与世无争的灵魂,男主角受着内心煎熬,紧紧跟随,正应了那句话,你知道,我很爱我的妻子,但是,此时此刻,我无法自持。电影运用了大量独白,蒙太奇手法以及镜头来表达短暂爱情所折射出战争可怕与忘却的重要性。
电影开头是一个全景,将两人身体上的接触表现的淋漓尽致,两人忘我的互相抚摸,画面中频繁博物馆,战后残局,镜头在两个人肉体纠缠和战争的伤痕之间交叉,长长的时间,看见那女的脸,只看见女子的手在男人悲伤抚摸,镜头淡化,切换到医院病房上的受难者,他们感到被人注视,冷漠缓缓地转向头来瞥一眼,镜头又回到两个人的手与背,之后再次出现广岛和废墟和和平雕塑,纪念馆,运用重复蒙太奇和复合叙事蒙太奇,如此反复,女人反复的喃喃自语,如诗歌梦呓一般,而男人总在否定他的言语,他说,在广岛,什么也看不到,是的,在广岛,你看到了好多,然而其实什么也没看到,看不到淹没城市的浓烟,看不到遍地的残骸,城市已崛起,再也看不到原子弹留下的断臂残桓,这是镜头所看到的广岛,一个恢复秩序的广岛和隐藏深处的伤痕,因为核污染而畸形的儿童,变异的生物,挥之不去的心灵伤痛,随时能促发激烈的情感,我们看见摄影机在捕捉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物质与精神,这些镜头让我联想到日本最近发生的核辐射,使世界产生了恐慌,引发了抢盐热,大家都渴望和平,所以大家拒绝战争,认真抵御灾害,战争与灾害给人心灵带来的伤痛是沉重的,
对于遗忘的记忆,并非不能提及,深藏在心底潜意识里,一旦有相似的事件发生,记忆将重新唤起。女子看见睡在床上的男子想起了过去的事,并在咖啡馆内将事全告诉了日本男子,她目睹反战队伍走过,这是日本男子出现两人相爱。日本男子唤起了女子记忆,战争,伤痕,感情,交织在一起,使两个人忘我的相爱,在酒吧,他说多少年后,当我已将你遗忘,遗忘所有像这样的奇遇,因为纯粹的遗忘习惯,我将记住你作为爱情遗忘的象征,我将会向这个故事作为遗忘的恐惧,在她旅馆中,他们仍是陌生人,她叫他广岛,他叫她奈维尔,此刻,爱情,已沉入历史,沉入两个国度的历史之中。
记忆是交织现实,广岛内维尔,回忆与现实交融,难舍难分,都是为爱而生的城市,都是伴随痛苦的城市,所以,何不相信,他们可以相爱,因为战争,他们相遇,因为战争,给他们打下记忆烙印,因爱而生的城市,因她与他,连在了一起。
《广岛之恋》观后感(七):9.22
不完全谈爱情——爱情是廉价的,电影自己这么说。那么把爱情当作认知的表现形式之一来谈呢。女演员的内韦尔是逝去,而广岛的一切都在继续,继续就意味着现实,无条件接受现实。一旦你沉浸在憧憬或者缅怀的虚妄中,就毫无防备两个巴掌打醒你。
有人说杜拉斯或者新浪潮是对自我的清醒认识与接受,是坦诚与不逃避,是一种直面。个人认为直面可以是另一种逃避,直面伴随着说服的意图,也包含着对被认同的渴求,而渴望被认同其实就是企图隐藏,这样,当你再次发声时,就可以是隐藏在附和声中,隐藏在团体力量的保护之下。
建筑师说:我还搞政治。所以,如果是追求爱情,他是在用政客的执着与不择手段来追求。如果是替广岛发声,他希望广岛被认可,与全世界的欢呼声背道而驰的苦难伤痛被认可,这个认可无法简单地从政治中求得,来自另一个战败国或另一个失势群体,却能充分地来自一段爱情。
可能跳脱来看,二战背景里的法国和德国胜负决绝不够轰轰烈烈——当然我无意拿战争作调侃,但是爱情背景里的男女双方可以,敌对阵营里的爱人死在冷枪下,与此同时城市解放,人群庆贺。整个广岛九秒钟的创伤换作初恋德国士兵一个人的死亡,整个广岛十二年的痛楚换作法国女演员所有年轻时光里的煎熬。
回到片子开头,建筑师不断否定女演员,你什么也没看到,你对广岛一无所知。她确实不懂广岛,也许只是一种趋同性使然,广岛会让她的自我缅怀更理直气壮,更肆无忌惮——和出轨并行,也许她想看看抛弃了过去的广岛过得如何,夜生活的欢声背后是否有心不安理不得——好参考以权衡是否抛开她的内韦尔。可能她又是真正懂广岛的,毕竟下一刻,女演员决定拥抱新生活,而下一年,广岛开始重建。
然而,一个城市有什么值得懂的呢,无非是河流,石头,广告牌。
《广岛之恋》观后感(八):无题
连着两个凌晨 两次看这部片子 不知道为什么
第一天 头脑中却一直徘徊着莫文蔚张洪量的《广岛之恋》
第二天 我就忘了那首《广岛之恋》 只剩杜拉斯 只剩下眼前这部拍摄于1959年的黑白片 听不懂的法文
影片中的广岛 是个象征 象征着遗忘 但需要被遗忘的 恰恰又是最深刻的部分
是杀戮的战争 是刻骨的爱情 是烙印的记忆 是封尘的史书
谁人 也都有自己的广岛吧 心灵一块被封锁的领地 出现关键的人 想起 然后继续遗忘
也许只有遗忘 才能让我们过正常的生活 但是 和最深的欲望无关 和心灵无关
只是活着 却风光着 被赞美 被认同 因为大家不约而同选择遗忘的关系
不去理会突然之间澎湃的思绪 安慰自己只是偶尔的失态 是这样吗
遗忘 因为我们无力负担记忆的重量 因为我们开始找借口向生活妥协
是吧 任谁人的广岛枯萎着 千千万万个广岛枯萎着
而 谁 又是谁的广岛
《广岛之恋》观后感(九):观后
人生真是不思议的东西,我竟然能在大讲堂看很喜欢的广岛之恋。
这个片子其实没有名字那么小资,之所以会给人小资的感觉完全是拜某首倒霉口水歌所赐
;名字好听也不好就这么乱用吧?好歹歌也好听一点。。。但总之莫名其妙的,一部文青
电影就这样被小资化了,sigh
说到小资,似乎传说小资都喜欢看艺术电影。那绝对是假的。我就不相信有几个小资能把
广岛之恋完整看下来。人家喜欢的是天使艾米莉那样温情脉脉的艺术电影。小资么,讲究
的是情调,看广岛之恋的开头多恶心啊,又是畸形又是废墟的,所以建议追求生活质量的
众小资们不要看这部片子了。
广岛之恋是有口皆碑的大闷片,电影频道也放了若干次,每次都是大半夜的,也不见得有
多少人会看,估计100%左右的都会看睡着。其实广岛之恋根本没有那么闷,起码和阿伦雷
奈的某天作 去年在马伦堡 比,还是非常有情节,有戏剧性的!而且还有男欢女爱的镜头
附赠,外加帅哥美女跨国恋等等噱头,其实已经非常不算闷了。那些嫌广岛之恋闷的人,
应该统统抓起来送去看 去年在马伦堡。
男女主角相遇了,恋爱了,坐我后面的家伙小声地说:“这不是一夜情么”然后女主角开
始分享她少女时代那段记忆。因为如果不说出来的话,她都快要忘了,即使是那样刻骨铭
心的恋情。人真是可怕的东西,不管受到怎样的打击,都是活下来了;为了获得更好,也
会忘记会带来痛苦的东西。男主角迷恋上了这个女性,以及她的那段回忆(坐我后面的家
伙说:这哥们可真够痴情的)。其实回忆这东西真的是非常奇妙的,有的时候,讲着讲着
,作为倾听者的那个人也会陷进去,仿佛是迷宫那样的东西,盘根错节,不断有新的细节
,就像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的门,看到了很多不同的房间。男女主角共同迷失在了那样的回
忆迷宫中。现实消退,他们俩成为了“纳维尔”和“广岛”,带着新的名字,生活了下去
(后面的人在电影结束的时候说:靠,这就算完了???)嗯,就算是这样的结局吧,大
概,大概。
顺便感慨一下,电影这东西,的确是要在电影院看才有感觉的。别的什么大屏幕电脑啦,
投影仪拉都不够劲。证据就是这样一部大闷片,竟然把我看得激动得不能自已以致于当晚
失眠了。但是电影院不见得每次都会放这样的片子。比如我预言大讲堂永远都不可能放那
个去年在马伦堡。所以看到喜欢的片子在电影院放一定不要错过。
顺便感慨一下中文配音,估计是80年代配的,其实很不错了,只不过那些话那中文说出来
特别特别假。
顺便期待一下,今后有某个拍记录片转行的大导演来一个“南京之恋”,然后顺带控诉一
下南京大屠杀血淋淋的事实。不过我觉得在中国范围内找出来有型的美男子演员比较难。
《广岛之恋》观后感(十):爱上~
前几天看了这部片子,可是却迟迟拖到今天才写了这篇笔记。原因之一是我看了片子之后心情非常沉重,不知道该如何去记录我的感受。
其实这部片子里体现出的“作家电影”的倾向没有《去年在马里昂巴德》那么浓厚、那么扑面而来,电影的故事主线也要清晰地多、叙事性也要强一些。在片子里,日本男人好像是家室的人,而法国女人也知道这个事实,但是两个人还是纠缠在一起。男人听女人讲她的过去,她的初恋爱人、她的住院的日子、她的现在的反战工作……
雷乃像是要表达一种反对战争、憧憬和平的人道主义愿望,因此影片中剪切入了很多的新闻片、纪录片的画面。这种把电影本身和新闻纪录片穿插展示的手法,可以让观众更真实、更具象的体会到战争的残酷和恐怖。
故事的另一条主线是爱情,主要讲述的法国女人的两段爱情都是跨越国家的。第一段是和一个德国军人,德国是以一个侵略者的形象出现,注定了这场爱情的悲剧结尾;第二段是和这个日本男人,日本是以一个受害者的身份出现,可是这个男人有妻子,也注定了这场爱情的有始无终……女人的命运是充满悲剧的,她觉得跟日本男人讲述她的初恋是某种程度上是对过往的放下,但是她却没有意识到这同时也是另一种程度上的坠入爱河——只有爱上了、信任了,才会说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