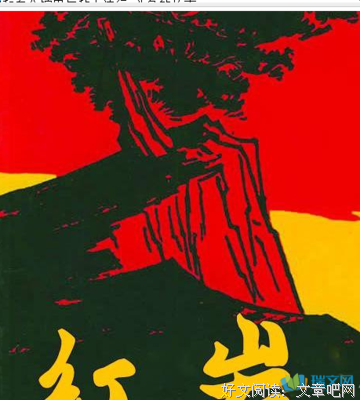速求共眠读后感1000字
《速求共眠》是一本由閻連科著作,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NTD350,页数:3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问题都还是老问题,但看他的小说经常会有几个瞬间觉得,那点问题无甚所谓,再去想的话反倒是我自己狭隘了。垃圾《丁庄梦》之后的《风雅颂》《四书》《日熄》《速求共眠》一个比一个有忏悔癖,似乎掉进老毛子黑洞里。阎连科是一个很清楚自己几斤几两的作家,近年似乎渐渐关注起文学本身的合法性,着实让人惊喜。
●和閻連科以往的作品相比,這一部顯得更實驗性,很特別,隨著一個日記般真實的開頭,展開田野調查和劇本寫作,真實與虛構交織而朦朧,很多細節的描寫(如村裏人家中掛著三個領袖的肖像mdx)以及劇本裡的官話,說不出的諷刺意味。比起情節,倒覺得更多是實驗性形式,以及作者對於當下的一聲苦悶的吶喊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能把真实事件以这种方式写成小说也是非常大胆了......就想知道顾长卫和蒋方舟读了这个小说以后会不会跟阎老师绝交-_-b
●自黑,叙述,电影剧本。这个故事还是实验性的噱头强了些,内核始终有些平淡,不是阎连科最好的作品。
●读阎连科新书《速求共眠》。一算,阎连科已经写了四十年了。四十年了,写了很多,但真正让他自己满意的应该不多吧。《速求共眠》也是如此,王炸的气势,出牌却是三带二,不免让人泄气。
●补。
●可以不看
●在收获长篇专号上看的,比起其它的长篇差太多,比起阎老之前的小说亦如是。
《速求共眠》读后感(一):文学的破坏者
这是一部让人轻松愉快的作品,和阎连科老师其他作品风格迥异。《速求共眠》像一个大杂烩,像是一种新的尝试,像是一种自我批评,像是一次跨界的行走,让人倍感轻松。感觉通过这部作品,阎连科老师还是想让读者知道他在写作,还想和读者混个脸儿熟;不过这次他不去批判任何人,而是通过批判调侃自己,彰显现实的无奈。
《速求共眠》读后感(二):《速求共眠》与现实
《速求共眠》是阎连科先生近年的新作,在这之前,也只拜读过阎先生的《日熄》,而《速求共眠》则是在《收获》长篇专号所见,网络上看到有台湾版本,但并不知道是否有所区别,在这部《速求共眠》小说中,作者与《日熄》一般以自黑为乐,明显的是,这部小说更像是作者的自黑编导传,作者通过自编、自导、自演一部电影而开始进行自黑,也许这正是阎连科黑色幽默的所在,在《速求共眠》的开篇中,作者似乎很在乎于名利,同时又以讽刺的笔调进行嘲讽,这就使我产生了一些错觉,总感觉作者只是一个劲在卖弄自己,并不是想写作,只是随想而发的感叹,这就使我越来越不想看,直至那篇应该算作引出剧本的小说出来,才发现有些看头,但此时的我还是不清楚作者到低想表达个什么,只是都已经看了三分之一了,骑虎难下,只得继续了。
文章开篇通过阎自己以前所写的一篇文章做为主题切入,并想通过这篇的文章的现实事后发展进行一个剧本的写作,并通过自导、自编、自演而做出一个艺术片,以求达到一个艺术的新高度,可是由于作者本身想出名,想通过这个剧本实现名利的双收,在与几个电影商讨过后,便迫不及待的要了五十万的定金,看似粗俗的写法,却实现了作者自嘲重名重利之心,之后,随着故事的发展,作者采访了当事人,又想法查阅了事件发生的派出所档案。但是与事先所说的事有所出入,以至作者写出了与之前所说的完全不一样的剧本,这也是后面导致作者与几位电影产生分歧的所在,在他们看来,只有通过城市与农村的畸形之恋才能体现这个剧本的不同所在,在这里,作者也是努力的黑了电影圈一把。由于作者给出了一个与事实有着较大差异的剧本,故而给导演及演员的内心造成期待过高而失望越大的现象,双方不欢而散,及至导致了作者的精神疾病,郁郁不乐的度过了许久,也许你以为故事到这就完了,那你错了,作者笔峰一转,乡下的老妈打电话过说,说出了剧本中的主角最后的命运,洽似与剧本中主人公的命运不谋而合,这也使使作者连日来疾病及郁闷一扫而空。
阎连科的作品一贯喜欢自黑,以及黑河南人,黑中国人。但是反而社之,这何尝不是自曝其短,只是社会都不喜欢别人说真话,因为真话往往都是最不好听的,所以大家都喜欢听好听的,而阎连科则后其道而行之。在这部小说中,可以尖锐的看出社会存在种种矛盾,大学生与农民的爱情、贫与福的差距、高知实与低文化人观念,作者也通过侧而的描写做出了城市人与农村的矛盾。正如文中所说“每一个城市的人,北京的人,润泽下区的人,都对农民有着同情心,可有这种同情心的人,如果他们看到一个农民工和一个城市的、又是北大的学生坐在一起了,那就怕不再会是同情心,而是莫名其妙的有解、猜忌和……报怨吧。”通过作者的笔触,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些冲突的激烈。从这些冲突中也就不难看出,为什么阎连科的作品为什么不受欢迎的原因了。
而作者亦通过多种方式对社会进行砰击,如派出所给的保证书所写道“为北京的和谐社会和国泰民安,添了乱子,制造了麻烦。”及“请民警同志放心,我一定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民工。”这些语句中,不难看出作者对某些事情的调侃。
而对当下的知识分子也写道“李静前后看看,见地库别无他人,默一会突然生硬地说道——
李静:张院长,你把我留下工作,帮我申请进京指标,我愿意把身子给你;愿意陪你……“而这些话语正是出是书中所说作者所写的《速求共眠》剧本中,作为一个北大毕业的研究生,为了得到留在北京的指标情愿给出自己保贵的第一次,而张华为让家中的老婆安心,动用了私人权利将一个当初自己以种种利诱的方式招上来的优秀女研究生辞退,可见公权力在这里只不过私人手中的玩物,同时也看到在高知分眼中,承诺亦不过随口而说罢了。
在《速求共眠》中,看到了许多,也想到了许多,但这些总是在我脑中乱成一团,使我无法表达出来,也许我学习得不够,无法用自己的语言说出吧!
《速求共眠》读后感(三):依然拥有着警醒世人的强烈现实性
《速求共眠》出单行本了?可惜中国大陆的出版社多半不会出版吧。(由于鲜有人买而会亏本,或是其它什么缘故?)本人特别爱读阎连科,在去年一年的空余时间里断断续续地读完了阎连科之前写的十二部长篇(《情感狱》《生死晶黄》《最后一名女知青》《坚硬如水》《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炸裂志》《日熄》,还有与莫言的合著作品《良心作证》),前不久才偶然挖到阎连科最新写的长篇《速求共眠——我与生活的一段非虚构》。(阎连科虽作为“最具争议的作家”,但在中国大陆还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号。)还是今年3月,偶然在逛淘宝时看到《收获》杂志长篇专号2017年夏卷的封面上赫然印着几个大字:速求共眠。更重要的是,下面还有几个小字:阎连科。当时还以为是几万字的中篇小说,买回来后才发现是十几万字的长篇,那个兴奋啊,终于不用去买盗版了。(阎连科的书也不好买正版,大家都懂的。)也不知道写的什么题材(“居然没有被禁?”),翻开杂志开始读:
「一面说着淡泊名利,一面渴求某一天名利双收——我在这高尚和虚伪的夹道上,有时健步如飞,有时跌跌撞撞,头破血流,犹如一条土狗,想要混进贵妇人的怀抱,努力与侥幸成为我向前的双翼。」
嗯,还是熟悉的风格。阎氏小说的风格。于是,我用两小时时间读了一遍,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惊喜。(阎连科的小说常常会带来惊喜,我忘了这句话是在哪里看的,但一点都不假。)阎连科从前的小说从未用过这种写法——“非虚构”,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小说讲述了那个真正的作家“阎连科”得知自己的老乡、农民工、五十余岁的李撞追求北大女学生、二十四岁的李静并被警察逮捕的新闻,想起了自己曾以李撞的往事为题材写了一部纪实小说、不到三万字的《速求共眠》,脑中灵光一闪,想到了把这个的故事拍成电影,并借此机会名利双收。于是,阎连科约出了顾长卫、蒋方舟、杨薇薇、郭芳芳,与他们讨论关于小说改编电影的相关事宜。但众人阅读了阎连科分发的纪实小说《速求共眠》后都表示失望,因为这部小说压根不适合拍电影。这些都在阎连科的意料之中,他拿出了一篇题为“虫凰相爱缘何来,莲花盛开污泥香”的微信文章,里面讲了这段恋情的始末。众人看完微信文章后都面露喜色,认为这才是一部非常吸引观众眼球的剧本。于是,阎连科开始采访主要相关人物(李撞、洪文鑫、罗麦子、李静、李社),了解到了“虫凰相爱”事件的五、六个版本,并查阅了警察局的案件卷宗,写完了剧本《速求共眠》。但了解五、六个版本后的阎连科不断受良心的谴责,改变了想法。剧本并不是以“虫凰相爱”的扭曲爱情故事为核心,而是在暗讽生活与现实。于是——
「“阎老师,”顾终于说话了,像许多电影中的江湖老大样,慢慢悠悠,却一言九鼎地问,“剧本中你怎么不写李撞和李静的爱情呢?”
我答道:“我觉得现在这对人物的关系要比他们扭曲相爱好。”
“可我们此前说好就是要写他们扭曲相爱的故事呀!”
“不是我不写,是生活的真实不让写。”
“难道艺术不是突破了生活的真实才有价值吗?”
“真正的艺术不是要突破生活,而是要沉入到生活的底部和人的内部。”」
众人都对剧本不满,顾长卫当场拒绝当导演,连蒋方舟委婉拒绝做主演:「“文坛这么小,人多嘴杂,我俩在一起本来就有人议长说短……你我都会被绯闻的口水淹死或被口水的河流冲得没影儿,那时候,我俩一辈子就都别想爬上人岸做人了。”」最后啊,剧本就荒在那里了,阎连科也「可能得了亢奋性欲望精神病」。
那天我把这部小说读了几遍,结合网上搜索“速求共眠”的结果以及阎连科原来的作品,发现以下神奇的地方:1.文中的顾长卫、蒋方舟、杨薇薇、郭芳芳等,都在现实世界中真有其人;2.搜索“速求共眠”得出的信息——“导演、摄影师吕乐即将开拍自己的最新电影《速求共眠》,编剧则是著名作家阎连科,该片计划于今年(2016年)9月中旬开机”,但未找到这部电影的其它信息(真的如小说中所述的那样?);3.长篇小说《速求共眠》中给出了纪实小说《速求共眠》全文,就是阎连科在九十年代发表的小说《平平淡淡》,只是结尾处略有不同。由此可以推断,小说中所发生的的确是“非虚构”的,至少不是完全虚构的(真亦为假,假亦为真?)。这种“非虚构”写法,在阎连科的其它小说中从未出现过,令人耳目一新。但跟以往一样,小说“黑色幽默”的手法用到炉火纯青。荒诞的现实写法,直接指向中国文艺圈小部分(或大部分)人的“唯名利是图”,所形成的各种怪现象导致中国文化艺术走向没落:
「“一个编剧为一剧之本,可他们得到的报酬却不到一个演员的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你觉得这样公平吗?而且一部电影公映后,名声也被狗日的导演、演员们占去了百分之八十多。”」
「“我是理工生,我们老师在课堂上说,当代文学都是垃圾,中国文学到鲁迅那一代,就基本结束了。关心当代文学,还不如去关心日本的动漫和韩国的电视剧。老师说读当代文学,纯粹是浪费时间,就和一个人在家无聊时,磕着坚果在屋里转来转去样。”」
阎连科怀揣一颗警醒世人的心,对社会的阴暗部分无比愤怒,但内心终究是善的。他自己从不为了名利写作,只是“仅仅想写出一部我认为好的小说来”。但面对如此结果,他也忍不住要发一点牢骚,把它写进了小说里:
「从咖啡馆里走出来,信步到书店文学书架那儿看了看,发现原来摆着我的书的书架上,全都改摆了别的当代作家的书,如王安忆、莫言、刘震云、苏童和格非等。我出来问店员:“阎连科的书都卖光了吗?”一个新来的店员小伙很诚信地告诉我:“阎连科的小说从来没人看,两个月才卖出去一、两本,我们前几天把他所有的小说都下架退回了出版社。”」
小说以“阎连科”为主人公,阎连科可能只是不想再得罪其他人了——批判自己总行了吧?把“阎连科”塑造成一个“「得了亢奋性欲望精神病」”的人,总挑不出毛病了吧?殊不知,这也是一种讽刺。顾长卫、蒋方舟、杨薇薇、郭芳芳应该都是阎连科的知音,否则阎连科也不会这样写。体会一下阎连科的良苦用心吧——对于人性欲望的思考与批判,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小说最终以一首俳句结束——
「生命苦短
欲望无限之长
然而 然而」
我还没看过印刻出版的《速求共眠》单行本。但我看到序言题目《走向谢幕的写作》后十分担心,意思是阎连科准备封笔了?《收获》上没有这篇序言。
(注:「」里的内容引自小说原文。)
《速求共眠》读后感(四):閻連科自序:走向謝幕的寫作
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樣感到寫作的無意義。
審美就像裸體外的紗幔,在馬虎的眼裏美成一首詩,而當你再定睛細看之後,僅就還有醜陋而已。
沒有意義而還要寫作,正如人活著不能不吃飯;而寫作,從本質上說,是作家要餵食自己的内心,而不是餵食讀者的需要。
若不寫作,人就真的死了。
然而寫作,也無非是證明你還活著罷了。
活著就是活著。在活著的今天,談論寫作的神聖是多麽虛僞與奢侈。
有的人說,我要寫一本死後能做枕頭的書,那是真心和真話;而我要說了,那就是一個笑話了!
經常懷疑,我一生的寫作,就是一場笑話吧。
若不是到了這個年齡,熱了吹風,冷了烤火或蹲在暖氣片的邊上操著袖子發呆和發呆,久而久之會覺得無聊、無聊和無聊,我就真的不再寫作了。
到了這個年齡,才知道寫作在我是選錯了職業。明白了,但已經沒有再可選擇的機會了。剩下的,就是握著筆桿年邁、衰老和等死吧。而在這還沒有衰老前,就是吃飯、走路和讓筆桿隨身而動著。
見過兩次史鐵生。第一次是在他家,他笑著對我說:「連科,我以為世界文學的高峰已經過去了。二十世紀的文學就是從拋物線的高峰向下滑。」
第二次是在別人家,我抬他的輪椅上台級。上去後他拉起我的手,很重很重地握了握:「少寫點!」更有悟覺和意味深長呢?!
到後來,我經常鸚鵡學舌的說:「世界文學的高峰在十九世紀已經過去了。」可是,說著說著間,我發現問題了。我不認為世界文學的高峰在十九世紀已經走過了,後來的寫作,都是拋物線的下行之滑落。
我以為,二十世紀文學舊有羈絆的一個再高峰。二者孰高孰低,幾無可比,如一個人姓張好還是姓李好,南轅北轍,無可論說。
十九世紀偉大的作品無不適直接或間接地去寫人的靈魂的。而二十世紀間,多都在書寫人的靈魂時,更多的關注通向靈魂那作家各自不同的路。拿二十世紀文學談人的靈魂和世界之複雜,它是要輸給十九世紀的。可拿十九世紀的文學談作家那通向靈魂的路——什麼敘述結構呀、腔調節奏呀、前流後派呀、創造主義呀,那十九世紀就輸了。所以說,我絲毫不懷疑十九世紀文學是世界文學的最高峰。我是說,二十世紀的文學也是世界文學的一個新高峰。
扯遠了;也說得大了些。
該說說我們自己了——忽然就發現,如果斗膽把我們得寫作放在世界文學這個平台上,果然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談論小說中得靈魂,我們壓根不能和十九世紀文學比;可是說每個作家那去往靈魂得路,我們又總是忙著拾人牙慧而少油自己得創造和修路的縞。想到此,就不免一陣心寒和惆悵,像一個鄉下人精心設計、花錢費力,用幾十年得時間,在鄉村蓋了一棟洋洋自得的樓。可是有一天,他到了城裏去,才發現那高樓漫山遍野,大胡同與小巷子,都是他家樓房的模樣兒。而且無論哪一家的哪一棟,幾乎都比他家的樓房好。
當代文學可能就是這樣兒。
好在我們總過實在是大,人口也著著實實多。倘若我們不和中文意外的作品相比較,也是能發現當代作品的千好萬好來。
可是怎麼能夠不去比較呢?哪個當代作家沒有讀過外國文學並從中汲取營養呢?像我這種人,老實說,若論中外文學對自己的影響時,比例應該為四六開。說西方文學對我這代作家的影響大雨本國文學傳統之影響,不知會不會有人罵我們是走狗和漢奸,可情況,確實又是這樣兒。
不講這些扯秧子的話,說現在。說說我自己,
開頭說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感到寫作無意義,我不是說中國文學無意義,而是說越來越感到我自己的寫作無意義。
這個最初的無意義和越來越覺得的無意義,是從前年寫作《日熄》開始的。
真的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麼覺得文學的無力和無趣。在這兒,絕不是說文以載道好。而是說,當小說無趣到人們在茶餘飯後都想不起來它的存在時,那是真的沒有意義了。
想一想,今天的現實富的像是一個礦,而小說的內容卻窮的只有幾粒鵝卵石。
想一想,我們處在一個盛產故事的時代裡,可我們的故事卻只能在離開今天後的回憶中。
想一想,我們正處在現實的巨大漩渦內,可幾乎沒一個作家都只能站在岸上眼巴巴的望,且生怕渾水濕了自己的腳。
想一想,我們以為我們的寫作正在鼎盛期,可在三年、五年前,或十年、八年前,創作的高峰卻已悄然而別,笑眯眯地離我們越來越遠了。
狄更斯說:「世界這麼大,它不僅能容下我們,也能容下別的人。」套而言之即:「文壇這麼大,它容下了別的人,也容下了我們這些人。」之所以我們還在寫,是因為別人允許我們寫。
我們還似乎很活躍。其實是我們沒有關心別人的活躍才覺得自己很活躍。
年輕的作家早就登台了,而且在舞台中央了。我們不過是左睜一隻眼、右閉一隻眼的佯裝不知或者看不見。不是因為他們寫的不好才顯得我們好,而是人家關心我們的好,而我們沒有關心人家的好。
現在似乎到了一代人謝幕的時候了。
雖然因為舊情的牽扯我們還在寫,但真的別忘了年輕作家已經寫的很好、很好了。之所以我們沒有最後謝幕和下台,是因為中國太大、文學舞台也足夠寬敞和寬敞;而不是因為我們在某些很少、很短的年約裡,果真的一部比一部寫得好。
尤其我,是真的江郎才盡、才情枯竭了。寫作的難,就像超齡女人要生孩子般。
我到了一個寫作的焦慮期和掙扎期。
無論焦慮和掙扎的原因是什麼,每次提筆都感到有手拤在脖子上,讓人呼吸不上來,使筆難以落下去。這如一個人沉在水裡的憋氣樣,倘若能夠浮出水面換口氣,也許還有一段距離可以游,如若換不過氣來,那就只有憋死在水下邊。
掙扎著。
焦慮著。
不求痛快和暢遊,只求能讓人換口氣。
《速求共眠》就是一次嘗試換氣、緩氣的小呼吸。
倘是生命讓我緩氣和換氣了,那就再繼續努力寫下去。倘不讓緩氣和換氣,就此擱筆也亦未可知呢。
年齡、生命、感受力和支撐力,創造力的衰退和最後一根稻草的脫手,都在警告著一代作家——或者僅僅是我自己寫作的落幕和卸台。
真的甘心就此打住嗎?
重新啟程的事,又哪有這麼容易喔。
魯迅說,孩子一出生,就一天天靠近著死。這麼說,一個作家一落筆,他就開始一個字、一個字、一個字,一部作品、一部作品、一部作品地走向寫作的落幕和卸台了。
準備好了要落幕扔掉的筆;也準備好了再次啟程的努力心。緩口氣,換口氣,要麼重新開始,要麼就此謝幕。
在走向謝幕的道路上,多半會碰到一堵走不出去的鬼打牆,可也許,命運好了會突然有個新舞台?
誰知道?鬼知道!
反正作好謝幕的準備就是了。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九日 於日本伊豆川端康成的腳印上
《速求共眠》读后感(五):《速求共眠》的叙事模式
这部长篇我们可以进行简单拆分为四个故事。
1.阎连科妄图以剧本成名、发财
2.洛阳农村的一个由强奸到婚姻的短篇故事
3.农民工和大学生之恋的罗生门事件
4.农民工和大学生故事的剧本
其中2和3、4除了人名有关联外,基本上是完全不同的故事;3和4在故事方向上都是在讲农民工和大学生之恋,但细节处理上完全不同,故而两个也是单独的故事,只不过共用一个框架、两个名字。
先来看第2个故事(由强奸到婚姻的农村故事)
这则故事我关心四点
1.当事人处于缺席状态,强奸者和被强奸者是本故事的中心,可该故事强奸者被强奸者只出现三次,一次剁指、一次哭哭啼啼不结婚,第一次就是对强奸行为的叙事。这种缺席状态,导致原本最该描写的人物完全沦为工具,这个工具只有两次主动,强奸和哭哭啼啼不结婚,其余都是被外在操控。这就导致本故事只关注强奸案如何解决,即它产生的社会振动如何消除,而不关心该案为何发生,或发生后主要人物的心理。换言之,借强奸案所要完成的是对社会样貌的观察,而并不关心人物内心心理。
2.对何为真实的探讨。这方面并不另我满意,故事中把真实揭穿者的社会身份定义为傻子,这个工具性太过明显。无非是想说,在这个村里唯有傻子才是正常人,其他都不是,由傻子的正常来反证村里人的癫狂。可以看到,强奸的真相完全是由傻子在说,也就是傻子在说,这起强奸案到底是怎么发生。而前面论述,强奸案只是一个工具,替换成其他没有任何实质性困难,该故事想探讨社会裂痕如何修复,那么这就导致,真实不在重要。错会这种精神(修复社会裂痕),而说出真相只能被当作傻子。而傻子与村民的对话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村民通过傻子的交代知道了部分真实,但通过故意不答来回避对强奸案真实的讨论。做一个假设如果故事选择追究强奸案本身,那么社会裂痕会被撕扯,割裂,而选择性回避,则避免了社会的撕扯。但是对真实的回避,就像我在前面论述的,对强奸案真实的回避,直接就造成了强奸者与被强奸者的回避,这直接把人给丢掉。与人而言,社会是不能被撕扯的,所以揭穿真实的人会被当成傻子,会被毒打,还要被送到医院治疗。
3.对农村社会的刻画。这个可以做一下简单提示,就是交叉感,所谓交叉感就是利益与善良并存,我一方面要算计,一方面又被这种算计所带来的必要的说话绕来绕去中的情感所打动。另一个就是信息不对等,每个人对别人能动用什么资源,都是充满不确定。在该故事中,读者是全知存在,可以很容易看到一方能动用什么资源,而另一方不能;故事中的人算靠猜。最后一个就是把权力通过空间来展开,如富人住正街,权力是背后的操手。
4.知识分子形象,把这个拿出来谈是这个可能和阎连科形象产生互文关系。在该故事中知识分子形象具有三个特点,没落、乡村老师两年的工资不如一头;真相的掩盖着,在修复社会裂痕上发挥作用;真相谋杀者,如果考虑到真相揭穿者就是这个知识分子的儿子话,无疑更有深意。
二,下面来看第3个故事
第三个故事是个罗生门的事件,不过还是需要注意一点。
1.真实性出现模糊。在该故事中,李撞先否定掉强奸案,这就是强奸案是否发生出现了不确定。乡村知识分子形象再次出现,他的出现虽然确定了强奸案的真实性,但是把李撞讲述故事的真实性给否掉,即李撞讲的故事是假故事。我觉得该故事的叙述有点失败。同一个事件的不同解读形成罗生门,但罗生门事件应该具有一个共通事件内容。如昆德拉在构建罗生门式事件时,一个事件发生的各要素是确定的,不确定在于对各要素的解读。而在本故事中,除了事件框架大致吻合外,其余皆不吻合。这就给我一种故事根本没有写完的感觉。
2.本故事在形式上最为复杂,我感觉是形式的花样将内容不足给遮蔽掉。可形式使用,也带来问题,如微信文章的使用,后面所附评论,名字与评论内容太契合,沦为一种功能(这也没办法);在采访中,几乎以一个人自述的形式展开,比较可惜的是采访者的出现,应该在采访中把拜访者完全省掉;警察笔录中,除了形式是笔录外,皆不是笔录,这就是运用形式而导致形式内容并不统一。
三:第四个故事
第四个故事我感觉失败,失败在于人物塑造。众所周知,阎连科是洛阳农村,以农村人为故事人物来进行写作,这就导致他只能写乡村的故事,人物一出乡村可能就面临问题。我读《速求共眠》的感觉,就是不再写农村了(《四书》也并非农村故事),但在对女大生学的描写上还是让我觉得失真。“为了保住工作,我可以和你上床”。我不太相信一个知识分子能把这种话大声说出来,即使有这种想法,也是欲说还休。
四:阎连科写剧本妄图成名、发财
这部分应该是整书形式的最大花样。这部分对蒋方舟、顾长卫的描写是轻飘飘的。我看不懂的是该故事中阎连科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妄想症可以很容易看出来,但一到读者姿态就变得极低,我恳请你们读读。
另外,这一部分可以切成好几部分。一部分是对自黑,一部分是和其他人谈作品,对自己的自黑我觉得似乎作家创作的焦虑症在作品中表现。作品中的话,我是分不清对话者是谁,不过所谓对话者无非有三类,作家本人、读者、作品中人物。
五:真实与虚假
本书中除了那四个故事中的真实与虚假外,四个故事互动本身也构成了虚假与真实链。
从本书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到
2.强奸案是小说:根据真实改编
3.农民工和大学生之恋的罗生门式事件:真实采访,但有极大虚假成分
4.农民工和大学生的剧本:虚假,但中间提到把妻子骨灰卖掉换钱,在真实中得到引证。
从这三个故事中很难分清哪些是真故事,哪些是假故事;或说哪些是真实发生、哪些是作家改编
1.阎连科妄图以剧本成名、发财
小说是一个纯虚拟的世界,作家本人的出场,是把作家的背景带到纯虚拟中,作家本人成了现实和纯虚拟的链接器。但作家本人是否是现实世界的作家,还是虚拟世界的作家。如在《炸裂志》、《日熄》中出场的阎连科,完全可以不把他看成真实人物,他和作家本人的不同只不过借用了同一个名字、同一个职业,而真正作家的阎连科则是故事中上帝式的存在。所以,如果把《炸裂志》《日熄》的阎连科换成其他的什么名字,对作品本身没有什么损害。不过自嘲的意味会削弱。但《速求共眠》中,不是作家一人跑到了虚拟世界,而且作家本人拉着蒋方舟、顾长卫一同跑到了虚拟世界。但这依旧是伪真实,蒋、顾二人的出场完全工具化,并不能构成一个真实世界的氛围,而故事叙事主体,是这个叫阎连科的心路历程。不过有趣的,从《炸裂志》《日熄》中的阎连科,到《速求共眠》的阎连科。阎连科的身份逐渐具体化、清晰化,但也没到清晰到可以把整个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完全磨平。不过,作家以此种形式出场也确实是在试图打破真实与虚拟之墙。就我近期看过的书来说,昆德拉《雅克和他的主人》把这堵墙打破的最为成功。
本小说附了一篇评论,其中有句话大意说,作家从黑色幽默现实到黑色幽默自己,作家似乎在说,“瞧见没,你们以前一直说我出名靠卖国家的惨,我现在也来卖自己了,你们这些指责我的可以停了吧。”我完全不认同这个说法,不过我更觉得这个说法应该是作家碰了写作瓶颈,只能让自己出场,戏谑一把。前言“为谢幕而写作”,不正说明了作家写作的焦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