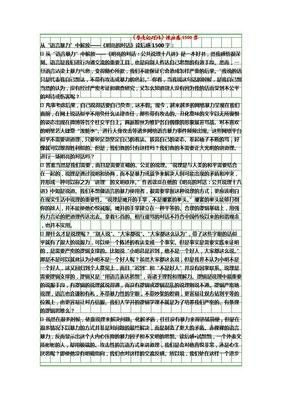《最后的对话 Ⅱ》的读后感大全
《最后的对话 Ⅱ》是一本由[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 [阿根廷] 奥斯瓦尔多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页数:4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们是命中注定的、不可治愈的现代人,我们不可能是别的什么。”
●这一套对话录质量还是很高的,当然与对话者的层次直接相关;博尔赫斯的重复永远不让人厌倦,因为如译者所言,近乎原型(译后记很感动,谢谢啦)
●总有一篇让你深陷进去
●博尔赫斯可能已经感到接近了生命的终点,他多次谈到死亡,他说死亡是一种解脱,他已经厌倦做博尔赫斯了。
●审判早已发生,如今我们看似仍在人世,却已是各在地狱天堂,我们欣狂,我们浑噩,我们一无所知。P.S.博尔赫斯老师是真“博”啊(波赫士:??),古今阿外,无一不及。
《最后的对话 Ⅱ》读后感(一):博尔赫斯用语言构建了宇宙,其中最重要的影像是他自己。
博尔赫斯用时间、迷宫、梦中之梦、老虎,这些他反复用过的意象与词语,为我们创造出那么多令人惊叹的故事与诗篇。我相信这是我们的精神财富且永不过时。
博尔赫斯是神秘的个人主义者。博尔赫斯说“一切用词语写就的文学作品都指向一个寓言”。我相信这是对的。
或许在每一个人都是对自身遮蔽难解的人的状况下来说,这唯一的谜底就是;认识你自己。
《最后的对话 Ⅱ》读后感(二):与博尔赫斯来一次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对于我这个发散性思维太强的家伙来说把发散出去的想法收回来真是难得要命,但我还是想为博尔赫斯这个神奇的老头子说上几句。
这本书的体裁与之前国内已经出版的大部分博尔赫斯作品不同,以对谈的形式记录了博尔赫斯人生最后三年对于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种种见解。其实之前广西师大倒是也出过一本他的谈话录,只是感觉那一本的重点在于谈论他自身,而《最后的对话》中他谈话的内容就要丰富得多了,真得是寥寥数语难以概括书中包罗万象的话题,感觉仿佛在一个藏满宝藏的洞穴中探险o(* ̄︶ ̄*)o
实际上,博尔赫斯失明之后,作品并不多,但他参与了大大小小的各种访谈节目,本书就取材于一档持续三年的访谈节目,而对谈人也是阿根廷文学界颇有名气的人物—— 奥斯瓦尔多·费拉里,算是博尔赫斯的后辈了,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些对话也可理解为阿根廷两代文学人士的对话,让人不禁联想到那个可以在各种形而上的话题上畅所欲言的古希腊时代。如今,这种机会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了。在对谈中,他的见识、他的洞见自然而然的流淌出来,毫无生搬硬套的痕迹,这也许是读书的最高境界了。
比起博尔赫斯失明前的作品,《对话》中我看到了他更为丰富的想象力,他对于各种主题的理解也更具深度。博尔赫斯本人也曾坦言:“相信我,眼睛看不见对于我来说绝对是利大于弊,如果我能看得见,我不会离开房间,我会一直待在室内阅读我周围的书。现在它们离我像冰岛一样远了,我曾去过冰岛两次,而我却永远看不到我的书了。但与此同时,我不能读书这一事实却迫使我……做梦和想象。”
翻毕《对话》,真心感觉博尔赫斯的脑子里仿佛装着一座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中有古希腊哲人,有英美文学和诗歌,有阿根廷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世界各地的艺术作品,当然,他所熟悉的远远不止这些。只是遗憾,他还未能道尽他脑海中构建的那个神奇而有趣的世界就先去见了上帝。
我相信,各种层次的读者都能在《对话》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博尔赫斯的对话永远对怀有好奇心的人敞开大门,他探讨的话题都是具有永恒性的人文经典,只要你对这个世界还怀有一丝纯粹的兴趣,你都会渴望在博尔赫斯的神奇世界中一探究竟。
《最后的对话 Ⅱ》读后感(三):最后的对话
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里说:喜欢一个离世好久的人比喜欢一个当代的人要靠谱,留下来的都是熠熠生辉的,而且与自己遥相呼应的东西。
博尔赫斯已经离开三十多年了,最熟悉的就是那句: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
这套《最后的对话》是他在八十五岁时跟好朋友费拉里的对话,博尔赫斯在六十岁之前就失明了,费拉里整理了这些对话,真好。我先拿起的是第二本,被吸引进去,都舍不得停下来换第一本从头读起。
谈的是十九世纪的文学,哲学,诗歌,绘画,音乐很少。大师就是大师,真诚而精彩。
由柏拉图跟苏格拉底开始,他说:柏拉图的对话录反映或是源自于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怀念。也就是说,苏格拉底死去了,柏拉图当他依然活着,继续和他讨论各种话题。这大概就是 magister dixit(师云)的意思吧。有一个毕达哥拉斯的例子:毕达哥拉斯不著文字,好让他的思想在他各个弟子的思想中分枝延展出去。而柏拉图,不顾苏格拉底肉体的死亡,依然假托或梦想苏格拉底还在世间;让苏格拉底将自己的原型理论应用于万物,这样柏拉图便能将苏格拉底的原初理念,大概是善的原型的理念推得更远,去想象恶的原型,万物的原型最后终于抵达了一个原型的世界,在其中原型像个体一样多,从而需要另一个原型的世界,以此类推以至无限。
他说文学与哲学开始于友谊与师承,荷马造就了维吉尔,维吉尔创造了但丁。但荷马不一定理解《埃涅阿斯纪》,维吉尔也理解不了《神曲》。
博尔赫斯专门有一本书收集了他给别人写的序言,非常精彩。他对于写序言的态度非常虔诚,他说:序言是介于批评研究和祝词之间的类别,也就是说,众所周知序言必定是有一点过誉的,读者自会打折扣。但与此同时,序言又必须是慷慨的,而我,经过了这么多年,在太多年以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人只应该写他喜欢的东西。我相信恶评是毫无意义的:例如,叔本华认为黑格尔是一个骗子或是傻瓜,或两者兼而有之。现在两人共存于德国哲学史上。诺瓦利斯认为歌德是一个肤浅的作家,仅仅正确,仅仅优雅而已,他将歌德的作品比作英国家具店…呃,现在诺瓦利斯和歌德是两个经典。
博尔赫斯开玩笑说他已经85岁了,一不留神就86了。根据叔本华的见解,在人的一生中,标准应该是一百岁。因为假如一个人在一百岁之前死去了,他是因病而死的,其偶然性不逊于落入河中,或是被老虎吃掉。所以一百这个数字是准确的,因为一个人只有在一百岁之后死去才不会有痛苦,而是自然而然的,也就是说,忽然间无疾而终。而之前则不然,之前需要,像一场疾病,或一场意外,这样偶然的事情,来将他杀死。
仔细一想跟博尔赫斯这样的大师在这个星球上共同存在了十多年,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跟他对过去的所思所想,对未来的期待几乎是一样的。
对于人究竟有没有“自由意志”他在谈话中两次提出那个“象棋”理论。对于棋子来说,每个棋子认为自己是有自由的,只要符合规则就可以在棋盘上自由行走。对于棋手来说,也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可以安排棋子,对于安排棋手的神灵来说,也认为自己是自由的........
对于自己的失明,博尔赫斯开玩笑说是神灵的安排,最大的折磨就是不能看书了。但可以思考了。
发现博尔赫斯最喜欢萧伯纳,每次对话他都要提萧伯纳。
《最后的对话 Ⅱ》读后感(四):最后的对话
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里说:喜欢一个离世好久的人比喜欢一个当代的人要靠谱,留下来的都是熠熠生辉的,而且与自己遥相呼应的东西。
博尔赫斯已经离开三十多年了,最熟悉的就是那句: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
这套《最后的对话》是他在八十五岁时跟好朋友费拉里的对话,博尔赫斯在六十岁之前就失明了,费拉里整理了这些对话,真好。我先拿起的是第二本,被吸引进去,都舍不得停下来换第一本从头读起。
谈的是十九世纪的文学,哲学,诗歌,绘画,音乐很少。大师就是大师,真诚而精彩。
由柏拉图跟苏格拉底开始,他说:柏拉图的对话录反映或是源自于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怀念。也就是说,苏格拉底死去了,柏拉图当他依然活着,继续和他讨论各种话题。这大概就是 magister dixit(师云)的意思吧。有一个毕达哥拉斯的例子:毕达哥拉斯不著文字,好让他的思想在他各个弟子的思想中分枝延展出去。而柏拉图,不顾苏格拉底肉体的死亡,依然假托或梦想苏格拉底还在世间;让苏格拉底将自己的原型理论应用于万物,这样柏拉图便能将苏格拉底的原初理念,大概是善的原型的理念推得更远,去想象恶的原型,万物的原型最后终于抵达了一个原型的世界,在其中原型像个体一样多,从而需要另一个原型的世界,以此类推以至无限。
他说文学与哲学开始于友谊与师承,荷马造就了维吉尔,维吉尔创造了但丁。但荷马不一定理解《埃涅阿斯纪》,维吉尔也理解不了《神曲》。
博尔赫斯专门有一本书收集了他给别人写的序言,非常精彩。他对于写序言的态度非常虔诚,他说:序言是介于批评研究和祝词之间的类别,也就是说,众所周知序言必定是有一点过誉的,读者自会打折扣。但与此同时,序言又必须是慷慨的,而我,经过了这么多年,在太多年以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人只应该写他喜欢的东西。我相信恶评是毫无意义的:例如,叔本华认为黑格尔是一个骗子或是傻瓜,或两者兼而有之。现在两人共存于德国哲学史上。诺瓦利斯认为歌德是一个肤浅的作家,仅仅正确,仅仅优雅而已,他将歌德的作品比作英国家具店…呃,现在诺瓦利斯和歌德是两个经典。
博尔赫斯开玩笑说他已经85岁了,一不留神就86了。根据叔本华的见解,在人的一生中,标准应该是一百岁。因为假如一个人在一百岁之前死去了,他是因病而死的,其偶然性不逊于落入河中,或是被老虎吃掉。所以一百这个数字是准确的,因为一个人只有在一百岁之后死去才不会有痛苦,而是自然而然的,也就是说,忽然间无疾而终。而之前则不然,之前需要,像一场疾病,或一场意外,这样偶然的事情,来将他杀死。
仔细一想跟博尔赫斯这样的大师在这个星球上共同存在了十多年,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跟他对过去的所思所想,对未来的期待几乎是一样的。
对于人究竟有没有“自由意志”他在谈话中两次提出那个“象棋”理论。对于棋子来说,每个棋子认为自己是有自由的,只要符合规则就可以在棋盘上自由行走。对于棋手来说,也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可以安排棋子,对于安排棋手的神灵来说,也认为自己是自由的........
对于自己的失明,博尔赫斯开玩笑说是神灵的安排,最大的折磨就是不能看书了。但可以思考了。
发现博尔赫斯最喜欢萧伯纳,每次对话他都要提萧伯纳。
小金说:博尔赫斯又给开出一书柜的书单。至少,萧伯纳跟维吉尔应该是要买来瞧瞧的。
《最后的对话 Ⅱ》读后感(五):作者写下文本,读者杀死作者
《最后的对话·下卷》与《最后的对话·上卷》一样,总共收录45篇对话,对应的是博尔赫斯与费拉里公开播音的第二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 或许是之前将近一年的对话,让费拉里得以近距离了解博尔赫斯,并使之与博尔赫斯建立起某种默契。费拉里在《最后的对话·下卷》中的整体表现要优于上卷——尽管与博尔赫斯相比仍然处于弱势,但至少不再单方面的迎合——而是针对性地发表自己的观点。 就像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维多利亚·奥坎波和女权主义》一篇里,费拉里补充了一些博尔赫斯所不知道的、关于伍尔夫的事实——比如那句来自父亲的“no writing,no books”的禁令;而在《埃德加·爱伦·坡》一篇中,费拉里甚至在博尔赫斯说出“我不相信坡从来没思考过美国的民主”后,立即用“不。坡思考的是贵族体制”进行反驳。 如果说在《最后的对话·下卷》,费拉里开始舍弃“工具人”的身份,而逐渐配得上“对话引导者”。那他作为“对话发起者”的身份与上卷相比就略有不足:下卷收录的45篇对话所涉及的领域范围要略低于上卷,而且有将近一半——20篇左右的对话专门用来谈论作家或哲学家。 但很难想象读者会对自己毫不知晓的作家和作品的谈论感兴趣,或者引发共鸣。就像对基督教一无所知的人,如何能对《圣经》产生共鸣? 因此,《最后的对话·下卷》对读者的文学素养就有极大的要求——尤其是阿根廷文学和法国文学,而前者实在有些强人所难。 但博尔赫斯在谈论作家和作品时,所传达出的有关文学的态度和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这些和文学相关的观点,在上卷虽已有所提及,但到下卷才算完整地浮出水面。 在《最后的对话》里,博尔赫斯先后两次引用艾略特的观点表达他对创作的态度:为了配得上缪斯的偶然来访,一个人必须要有写作的习惯,否则他就配不上他的灵感或者难以将其表达。 也就是说在博尔赫斯看来,写作应该是一种目的,而不是一种手段。写作并不是为谁而写,而是一种必须要这样做的内在需求,或者是缪斯造访的一种冲动。 写作就像是作者的命运,他们通过写作谈论想要谈论的诸多主题,虽然这些作品可能会被遗忘。但在《埃德加·爱伦·坡》里,博尔赫斯同样提出,如果运气够好,那么作者将会通过作品,留下自己的形象。 这句话不难理解,毕竟读者接近作者的最佳方式就是阅读作者的作品,然后通过作品在头脑中勾勒作者的形象,就像我们通过阅读博尔赫斯的小说与诗歌来想象或体会博尔赫斯。 但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语言的局限性,任何语言都不能精确地写下一个人所设想的东西;二是语言的活动性,语言的含义并不固定,它总是随着环境的变革而发生变化。 基于这两点,博尔赫斯在《贡戈拉》提出自己的疑问:在何种程度上我们面对一个十七世纪文本所感受到的东西就是作者感受到的东西? 在博尔赫斯看来,在文本完结那一刻,故事就脱离作者的掌控,故事本身的寓意并不是由作者,而是由读者完成。因此在《天堂与地狱之书》里,博尔赫斯开玩笑说,他对于自己小说的解读未比其他读者的更有价值。 文本的寓意由读者完成的观点,博尔赫斯在其以前的作品《〈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里有所涉及。在故事里,皮埃尔·梅纳尔通过体会塞万提斯,创造出十九世纪的堂吉诃德——两人的作品一字不差。然而对两人作品完全相同的一段话,博尔赫斯却做出不同的解读。 皮埃尔·梅纳尔通过体会,用他勾勒的塞万提斯覆盖了原本的塞万提斯,而博尔赫斯又通过解读将皮埃尔·梅纳尔覆盖,博尔赫斯又同样会通过阅读被读者覆盖。文本的寓意、作者的形象,只有通过读者才被赋予意义。 这就像柏拉图在《理想国》创造新的苏格拉底,萧伯纳在《易卜生主义精髓》更新易卜生。每个读者都从作者的文本中发现作品所没有的东西,而且因为知识经验的差异,每个人形成的形象与解读也各不相同。一如博尔赫斯在《关于序言》说的那样:每一位批评家都以某种方式,更新了他所批评的作品,同时又将其延续。 或许就像博尔赫斯说的那样,阅读就是用作者的大脑进行思考。我们在头脑中勾勒作者,并用勾勒的形象覆盖作者。一如阿隆索·吉哈诺“杀死”堂吉诃德,然后成为堂吉诃德。 在这层意义上,故事就像作者的一场梦,作者又成为读者的一场梦,双重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