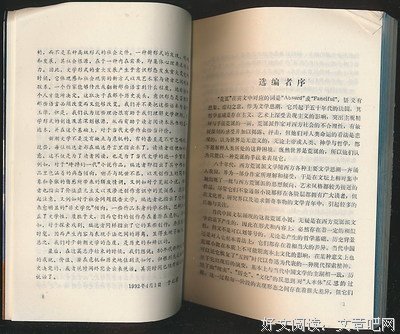褐色鸟群读后感100字
《褐色鸟群》是一本由格非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页数:201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迷舟》和《褐色鸟群》都值得读三遍。
●刚刚读了格非成名作《迷舟》,一部以北伐战争为背景,却刻画的是一位面临死亡的将领生前七天发生的故事,用七天表现了主人公的爱恨情仇,似乎七天就是一生的写照。小说最妙的就是心理描写,一位表面冷峻的处于反面势力的军官却有着细腻的心思,深爱着一个女子。在这部小说里,讲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性,虽然军官萧处于孙传芳的队伍中,看起来是个反面角色,但也有他温情的一面,而那位最终杀死萧的警卫员虽看似处于正面立场,但他的做法又显得缺乏人性,战争是残酷的,在战争中的人也许并没有那么复杂的阶级关系,他们也是在乎生死在乎尊严在乎自身命运的人。
●看了头几篇,格非的文字在先锋小说家里是很有造诣的,文字风格也一直延续到江南三部曲时期。不过细细想来,他的长篇的驾驭还是不如中短篇。
●忘记标了,不打分,看不懂。先锋,退学了。
●春梦江南
●爱上,不算深爱。从边缘读起格非。
格非前期的小说一直在践行他的文学先锋实验,这一时期的短片小说文字典雅绮丽,富有中华文学的风韵,故事情节却怪诞荒谬,文章结构也不拘小节,往往出其不意,令读者读罢后才幡然醒悟。总结起来,这些短篇还是值得细细品味的,因为当中的隐藏的细节不花点时间,根本无处寻迹。
个人推荐《迷舟》《傻瓜的诗篇》《锦瑟》,这几篇字里行间散发着格非小说中浓重的个人风格,景物描写用字颇有古韵,细节描写往往一针见血,故事情节也相对曲折,十足一部微电影的感觉了。相对的《褐色鸟群》,恕在下实在愚钝,理解不了作者想要表达什么,或许真的越看不懂越伟大吧。
《褐色鸟群》读后感(二):褐色鸟群
罗兰·巴特说:“小说是一种死亡,它把生命变成一种命运,把记忆变成一种有用的行为,把延续变成一种有方向的和有意义的时间。”先锋叙事是要与这种死亡抗争,用各种形式消解掉传统叙事内置的因果律、自带的秩序,把生活的扑朔迷离充分剥开。
《褐色鸟群》是标准的“观念写作”,它就好似“存在与时间”哲学课堂后的一篇作业——一座工巧、精致的空中楼阁,依靠叙事主体的裂变、故事间的嵌套构建出了一种迷宫般的叙事。夹杂着种种隐喻,褐色鸟群表现“时序的嬗递”,棋和镜子、叙事的圈套等等。换句话说,它的“玄奥”来自于其结构和包袱,依靠着神经症主体的精神错乱式叙事、闪回式意象构建出一个情节和人性的谜语。
如果你读它的时候不探寻背后的理念,这篇小说应该对你基本没什么触动,当你探究完,它也就不再是一个故事了。作者的一篇“作业”变成了一个已解开的题干。
我想,没有根的文学,最多也就是适于把玩了。
《褐色鸟群》读后感(三):其实看的不是这个版本的
书里面有很多的短篇小说,都是悲剧。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我看了6个故事,格非写的很好,很特别,有美的有丑的。我很喜欢他。 《追忆乌攸先生》:曾经书香为伴汉字为媒,如今如隔万重山。(村子里的人好冷漠 《紫竹院的约会》:一个在朋友裴钟的帮助下我和吴颖认识结婚的故事。 我也很喜欢江南的风景 《迷舟》:一个从此迷失在山林里的将军萧的故事,很悲哀,无论是家庭还是爱情的角度。最后警卫员毫不留恋的一枪,打碎的是信任,串起来的是悲凉。 《褐色鸟群》:应该是格非很著名的一篇,先锋文学的代表作,也的确很难懂的,我只能从很表面状态去解读。褐色的鸟群贯穿了始终。里面穿插了很多的故事,很多都不符合逻辑和常理,但是故事叙述来说,还是在复杂的矛盾中展现背景和作者的思想,很特解我也很喜欢。 《傻瓜的诗篇》:还是忍不住用特别这个词来形容,没想到精神病医生最后成了精神病人,你看,一个人的精神是会被影响的。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故事,情节说出来挺简单的,叙事方面和心理描写是重头菜。
《赝品》:没看懂,故事没有什么结局?不够完整,但是可能作者有深意。
《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归种子的道路》:我真的没想到格非可以写的这么好,他写小说的时候是冷漠的笔触,但是又能感受到他的温度。但是他写马尔克斯,是用客观冷静的笔触,真正阅读了、考查了相关的拉美文学,我窥见了哥伦比亚或者是美洲文学的一点点,很开心可以跟着这位文学大家,写的很好,真的很厉害。
《城堡的叙事分析》:我
《褐色鸟群》读后感(四):某种无法言喻的神秘性
追忆乌攸先生
只有几个小伙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小媳妇的叫声他们一点都没听清楚,因为他们光顾着看小媳妇粉红的衬衣里面的小肉团在跳动了。事后,小伙子们向人们谈起那天早上的情形时,他们说,他们第一次看见那个媳妇跑,周围的一切生命都像停止了。《追忆乌攸先生》中最有趣的一段话,粉红衬衣的小肉团,而不是白色衬衣里的粉红小肉团,后者就显得色情很多。但粉红衬衣似乎分解了跳动小肉团的那种明显的色情意味,好像粉红衬衣是粉红衬衣,小肉团是小肉团。就像面不改色的讲一个能让人笑24小时的笑话后转身离去,甚至留下了一丝冷飕飕的小旋风。
迷舟
就像法医验尸时没有一丝表情的陈述死者身体的情况,死者的身体上是凝固的情绪,作者的语言很平淡,波澜不惊的叙述着战争的一角,浅浅淡淡的叙述将情绪向下铺陈。杏的结局似乎就是死亡,萧想找人将发子弹一一打出,最终也结实的打进自己的身体里。叙述的语言就像人狠话少面无表情的男人,在无声处将深壑一一凿穿。
陷阱
要想认识村子,必须试图找到一条从中出走的路并且充满仇恨。意思是说被走出的那条路有一部分原因可以是充满仇恨的
仇恨的是什么
各有各的仇恨的具体内容
牌没有吱声。看得出她对于这类问题不感兴趣,她只对不假思索地编织故事的神秘氛围自我陶醉。感觉说的是大部分时间自己想要竭尽全力进入的事情,但总是因为或多或少的佛陀说的那种基于自我执念的无知无法进入。摒弃什么进而进入一些虚幻的神秘而陶醉的幻境,关键的步骤是摒弃什么,但似乎怎么也摒弃不了,就像自己一边拼命用钩子勾住上边的悬崖边缘,而另一只手却抓着那一侧世界鲜绿草地上疯长的高草草皮松软马上被我的抓力掀起,即将到来的倾向性不言自明但始终不肯松手。
也许我想同时存在于同时占有。
且要相信总有一种方式共存。
妇女们坐在河堤上,把脚伸入咖啡色的河道,进行着另外一个世界的永无休止的争议。在闲聊时,进入的总是另一个与我无关的世界。
危险不来自天上而在于你意念深处的一次滑坡所以说最危险的人是未知的自己
牌说这很正常,你陷入疑惑是因为你多愁善感。问题的全部意义不在于死者是谁而在于送葬。人们在世间的一切荣耀和耻辱都越过了时间的空当,跃入此刻,一切都是为你而准备的。所以“圈套”说的应该是世间的种种现象,而喜欢编造故事的我们总会以自己解读世相的方式编造一个故事让自己晕头转向的不停迷失。一切都是为生者准备的,就像正在写字的我也是为正在阅读的你的准备的。
我凝视天空的开阔就如正视自己的衰老。我喜欢格非的语言,而我喜欢的总是相似的。也许都是我散落在自己喜欢之中,种种样样。
《褐色鸟群》读后感(五):格非:开环、博尔赫斯、记忆、性冲动与本土观照
读格非是一个相当偶然的过程:在豆瓣动态里看到一家出版社的宣传,加之久远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好奇,搜索了这位学院中的作家,进而尝试阅读他早年引得重名的作品——这本《褐色鸟群》。
读格非最先被吸引的,无疑是他早期作品中的先锋特征——故事曲折模糊,情节因果混乱、令人费解,叙事要么交错矛盾要么悬置空白,形成一个个互相嵌套的开环。一个典型的代表,恐怕就是《褐色鸟群》这篇被称为当代中国最难懂的小说:三层叙事互相衔接又互相冲突,借前后矛盾的细节描写邻接为三个莫比乌斯环,叙述者同样被困于叙事当中,留下一连串从未揭开的谜底。《青黄》中,作为标题和故事源动力的“青黄”在大段情节中缺失,又在结尾留下多义性。《陷阱》则更加复杂,四层叙事连续出现(幸好在最后连贯收束),在荒诞的城市语言中让读者坠入莫名其妙的陷阱。《蚌壳》和《背景》则将叙事成块打散颠倒,以让读者自行梳理脉络,挖掘潜在的答案。
此外,格非的这些早期作品毫无疑问地呈现了博尔赫斯的巨大影响,有些作品几乎可以直接称为对博尔赫斯的露骨模仿。但此处一个区别在于,如果将博尔赫斯称为回环、重复、多义性,那么格非则是开环、交叉、无答案。换言之,尽管尚未摆脱博尔赫斯的语言,格非能够在内核更进一步,将博尔赫斯的现代性叙事推进到了八十/九十年代的后现代叙事:叙述者从他人大量地复归自我,因果混乱,记忆从不牢固、若隐若现,意外和力比多主导结局(这一点下文还会提及)。
记忆是贯穿格非这本早期中短篇集的一个鲜明主题。几乎每一个故事里都有叙述者对过往的大段回忆,有对于记忆的妙语和逃避。记忆成为所有故事的引子,又在引子处宣告其本身的模糊与脆弱,以维持结局留白的自洽。如:
那个遥远的事情像姑娘的贞操被丢弃一样容易使人激动。既然人们的记忆通过这三个外乡人的介入而被唤醒,这个村子里的长辈会对任何一个企图再一次感受痛苦往事趣味的年轻人不断地重复说:时间叫人忘记一切。 ——《追忆乌攸先生》回望从前,我似乎觉得只是经历了一些事的头和尾以及中间琐碎的片段。甚至,这些湮没了故事的附属部分也许根本就没有发生。 ——《陷阱》我猛然一惊,我的如灰烬一般的记忆之绳像是被一种奇怪的胶粘接起来,我满腹焦虑地回忆从前,就像在注视着雪白的墙壁寻找两眼的盲点。 ——《褐色鸟群》他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显得非常吃力,仿佛要让时间在他眼前的某一个视点凝固或重现。 ——《青黄》我怔了一下,“噢,是你——”我说,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她是谁,我的记忆之中早已尘封的区域像冰一样化开了。流水四溢,寻找归宿。 ——《蚌壳》她的记性已经坏了,她用相同的词语形容每一件事物,把经年的流水账压缩成一个简单的句式,在记忆中断的地方不断重复,在语塞、长时间的停顿中显出悲伤而又无能为力的样子。 ——《夜郎之行》如是种种,格非的这些小说很容易让我想起达利的《记忆的永恒》:处在记忆边缘、已然无法保真的内容重现,与梦境混为一谈又无法分辨,展开成互相扭曲交叠冲突的环状现实。记忆一度坚固,但必然倒坍倾颓,进而构成故事的摇曳底色。
与记忆相关联的一点,则是这个中短篇集中反复出现的故事动力:性冲动。不少读者不无道理的批评是,女性角色在格非的故事当中仅仅沦为了性冲动的来源,而缺乏其他深层次的塑造。《迷舟》中,萧对杏的迷恋导致了故事意料之外的悲剧结局;《大年》中,丁伯高、唐济尧和豹子对二姨太的渴望构成了整个故事;《蚌壳》和《没有人看见草生长》中,故事起于偷情而终于偷情;这个角度下最典型的恐怕是《背景》,记忆或往事(“我”无意中看到父亲和“瓦”的母亲的偷情、“我”的恋母情结、母亲的死)成为了背景,构成了故事的后果(“我”和“瓦”的偷情、父亲的死)。以这个角度看,早期格非的这些作品是非常弗洛伊德的。
此外很值得提及的是,格非如何将博尔赫斯“中国化”。如上文提及,他的早期作品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远离拉美背景而指向东方生活。处女作《迷舟》指向动荡的军阀割据时期;《大年》和《风琴》以残酷的抗日战争为底色,都或多或少掺杂了对历史的令人不安的隐喻(尤其是《大年》);《傻瓜的诗篇》则叙述文革创伤。时代之外,格非的笔触对中国城乡环境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描述。《迷舟》、《青黄》、《背景》等农村背景小说都充斥大量对乡村生活细节的捕捉描写,而《陷阱》、《蚌壳》中对现代城市生活的思考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陷阱》中对艺术的描写令人想到科塔萨尔。
这些中短篇当中,有些格外值得一提的元素。从情节上,《唿哨》是最为平淡的,但也恰恰最具东方意蕴,格非对孙登和阮籍的新解具有说服力。《夜郎之行》更是几无情节可言,似乎是一篇虚构散文,却早在三十年之前展露了与毕赣的凯里叙事(尤其是《地球最后的夜晚》)同等迷人的氛围与内核。而《锦瑟》可能是最接近“博尔赫斯中国化”这个标签的一篇,结构的巧妙和暗含的哲思都达到了整个集子的高峰。另一方面,格非的一些作品暗含着许多非典型中国作家,也非博尔赫斯的标签:《追忆乌攸先生》、《大年》、《风琴》等篇中的暴力(性暴力和肢体暴力),构成了现代作家对抗战时代的一种独特摹写;《迷舟》、《青黄》、《褐色鸟群》和一些其他篇章,隐含令人不安的意象与悬念(算命、历史、战事、宰杀牲畜的隐喻),使得作品甚至带有些哥特式的风格,尤其是《青黄》对超自然的《聊斋》式指向。
总体而言,抛去(或某种程度上也归功于)阅读时被迫全神贯注的体验,这本集子里的格非是稍显稚嫩、仍在试图寻找自己的语言但也魅力无穷的。尤其是对现当代中国文学完全陌生的我而言,格非是一个意外之喜:这本作品再次提醒我审视改开到世纪之交那个时代的魔幻,但也没有囿于而是几乎完全超越了那个魔幻时代,而在今日仍然毫不过时,继续闪烁着先锋派的光芒,让今日的许多作品在对比下黯淡失色。最后,此书代序当中,格非坦诚自己惊讶于几十年来文风的变化。怀着更大的好奇,我去阅读了他近来最富盛名的中篇《隐身衣》。阅读此篇的感受令我既满足又失望:满足是因为《隐身衣》所展现的格非的确文风大变,完全摆脱了博尔赫斯(或其他人)的痕迹,且还保留着《褐色鸟群》般的开环;失望则是它并未带给我畅快的、深邃的阅读体验,而显得浅薄、世俗、生硬。当然,我并未阅读他近来的其他作品(如《江南三部曲》),因此这样的评判有待商榷。但仅以这些早期作品出发,格非是一个我会铭记且期望的作家,他的这些作品也值得更多的阅读,值得在我们回望这个骤然勃发又被骤然打断的时代时,惊讶于这些作品的大胆与鲜活。